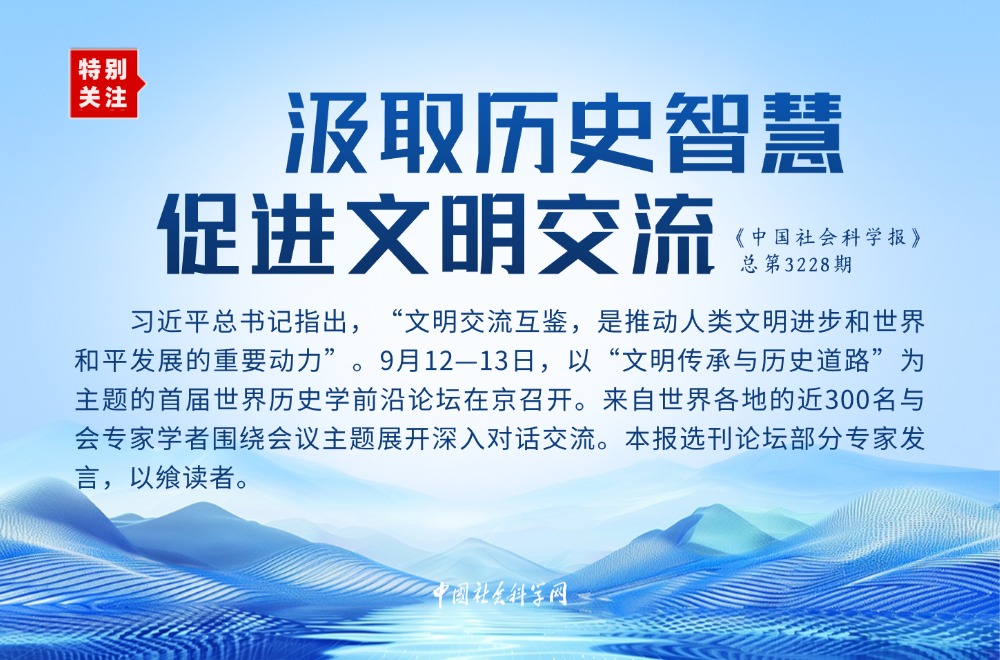

历史是人类共同的记忆,文明是世界共享的遗产。以历史为鉴、以文明为脉,在传承中开拓新局、在对话中凝聚共识,是推动人类走向更加包容、可持续未来的根本途径。我们所处的时代,挑战与机遇并存。人工智能正在重构人类的知识生产与认知模式,气候变化、能源问题、宗教冲突、环境安全、贫富差距等全球性议题则愈发呼唤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共同智慧。在此背景下,深入理解文明传承的内在逻辑与道路选择的根本差异,不仅关乎我们如何解读过去,更关乎我们如何塑造未来。
阅读原文: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509/t20250926_5917225.shtml

传统的世界史通常将海洋视为陆地的附属物,是连接不同大陆板块的手段。本文提出的海洋世界史改变了这种叙事视角,试图从海洋视角重新审视亚洲、世界、自然、历史和文化。它将海洋视为一个自在的世界,并试图将陆地的特征和状况广泛地归因于海洋。这需要审视海洋的概念、起源、动态以及它与各种历史行为体的关系。此外,人类如何构建以海洋为中心的生命体系以及海洋与陆地之间的内部循环结构,都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重要课题。
阅读原文: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509/t20250926_5917226.shtml

中国重新崛起为全球经济、技术与地缘政治大国,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这是一次新的起点,还是其18世纪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地位的复兴?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重新审视明清中国的优势及其衰落的原因,并将其与西北欧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者历史轨迹出现了明显分化。
在欧洲,制度将商业活力转化为系统性变革。而在中国,尽管有类似的活力,但缺乏相应的法律与制度框架,限制了长期影响。要解释这种分歧,有三个核心维度:作为历史性制度的市场;法律在保障连续性与可预期性中的作用;通过商业纠纷体现出来的讼师地位与帝制中国民法的有限发展。
阅读原文: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509/t20250926_5917227.shtml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美国历史学家开始质疑区域研究(Area Studies)这种学术建构的价值。区域研究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由针对全球不同区域(如东亚、南亚、西南亚和东南亚)的跨学科研究中心组成。这些研究项目得到了大量研究资金资助。这些研究资金在很大程度上资助了我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区域研究方法的批评者认为,由此产生的学术研究往往忽视了这些区域所处的更大范围的全球背景。正如肯尼斯·柯蒂斯(Kenneth Curtis)所指出的,区域研究把学者困在“地区泡沫”之中。
阅读原文: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509/t20250926_5917228.shtml

《中华文明史》是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团队组织撰写的一部多学科融合的学术著作,中文版于2006年出版面世。之后不久,《中华文明史》的英、日、韩三种译本也相继推出。2013年7月,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与北京大学签订俄文版出版合同,并约定于2017年底向中方交付译稿。
阅读原文: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509/t20250926_5917229.shtml

文明不仅是过去的珍宝,也是未来的明灯。我们要通过深化对话,塑造植根于我们所代表的文明的新愿景。从这些深厚的根基出发,我们可以抵达更为广阔的天地,也就是一个更加互动、更加包容、更加紧密地连接全球社群与文化的未来。但是仅有对过去成绩的狂欢是不够的,我们也肩负着共同的责任,那就是要通过开放、互联与互动这种方式来保护我们的遗产。交流和互鉴必须是公平、平衡、包容的,从不强加于人,也不局限于单一的路径。唯有如此,人类文明才能不断地进步、繁荣并得以传承。
阅读原文: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509/t20250926_5917230.shtml

自近200年前建立共和国以来,洪都拉斯一直面临着动荡和政治暴力的问题。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分析家指出,缺乏包容性的国家认同是贫困、环境恶化、种族主义和政治分裂的根源。作为非西方化本土文明过去的建设性遗迹,许多前西班牙时期的文化遗产在19、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被毁坏。而本土民族仍然存在的活态文化表现,也正受到单一现代性的威胁——这种现代性没有容纳多元文化和历史观念的空间,它建立在消费主义和生产主义的简单化发展理念上,将所有积累的知识视为必须抹去的过去的象征。
阅读原文: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509/t20250926_591723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