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玄奘因明的伟大成就应向国内外广而告之。它是汉传因明具有文化自信的根源,是汉传因明立足于世界因明之林的雄厚资本。
关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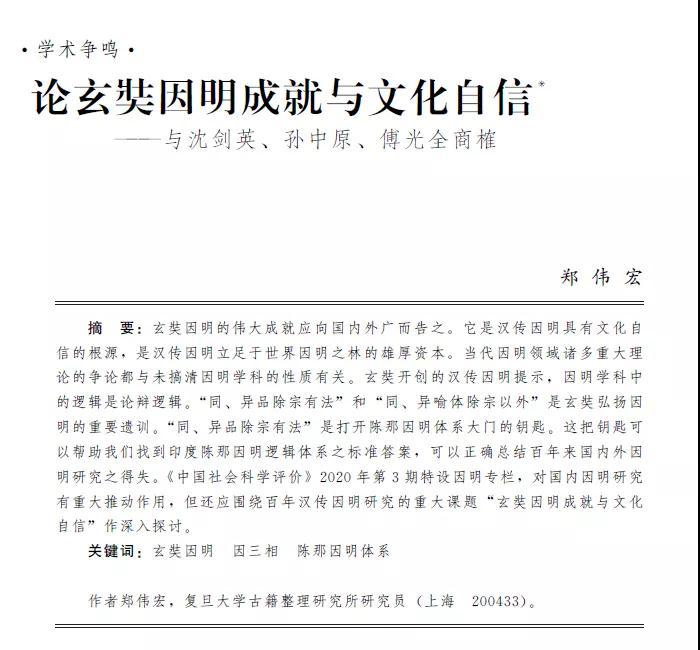
摘要:玄奘因明的伟大成就应向国内外广而告之。它是汉传因明具有文化自信的根源,是汉传因明立足于世界因明之林的雄厚资本。当代因明领域诸多重大理论的争论都与未搞清因明学科的性质有关。玄奘开创的汉传因明提示,因明学科中的逻辑是论辩逻辑。“同、异品除宗有法”和“同、异喻体除宗以外”是玄奘弘扬因明的重要遗训。“同、异品除宗有法”是打开陈那因明体系大门的钥匙。这把钥匙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印度陈那因明逻辑体系之标准答案,可以正确总结百年来国内外因明研究之得失。《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3期特设因明专栏,对国内因明研究有重大推动作用,但还应围绕百年汉传因明研究的重大课题“玄奘因明成就与文化自信”作深入探讨。
关键词:玄奘因明 因三相 陈那因明体系
作者郑伟宏,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433)。
一、玄奘因明成就与文化自信是汉传因明重大课题
百年以来,尤其是近四十年来,因明研究领域成果丰硕,盛况空前,但面临瓶颈。要推进因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认真总结其得失。其最大的得,在于“绝学”不再,不可能再出现历史上有过的失传风险。其最大的失则是玄奘法师因明成就的弘扬不力和因明领域文化自信的严重缺失。
当此之际,《中国社会科学评价》在2020年第3期特设专栏,为冷门的因明学科一次性发表三篇论文,其重视程度和影响之大,除《因明》杂志外,在国内寥若晨星,非常难得。沈剑英、孙中原和傅光全撰写的三篇论文,其学术观点无论读者赞同与否,客观上都对因明研究有推动意义。傅光全的《因明何以成绝学》这篇论文探讨了因明在历史上曾经失传的原因,作为仅此一篇的专论,引人关注。该文回顾了因明从印度到中国(汉、藏两地)几个重要历史转折点,“从佛教、语言、观念以及思维习惯等方面做一些尝试性的解读”,的确比一般的泛论更为深入和更为全面。沈剑英的《因明研究的学理要义与现实使命》就学理要义向国内外学者郑重重申自己几十年因明研究的一贯主张,并表示了因明学者的使命感,“要令绝学不绝,重兴于世”。其学理要义是否得当,有待商榷;其使命感令人感佩。孙中原的《因明绝学抢救性研究的意义》提出三观,一是“世界逻辑整体观”,二是“研究范式转换观”,三是“逻辑传统比较观”,且都很重要,笼统说来,每一个合格的因明研究者都必须具备这三观。这三篇论文代表了国内的传统观点,是汉传因明百年研究的一家总结。稍有不足的是,专栏缺少了两家学说的交锋,不免寂寞。沈剑英文中多处批评了不同观点,其多数是笔者的一家之说。
笔者以为,汉传因明研究最重大的课题,是揭示玄奘法师真正的因明成就,并进一步向国内外宣传汉传因明的文化自信。玄奘法师的因明成就在国内很少有人知晓,在国外也鲜有宣传,这并不奇怪。在国内,完全否定玄奘和汉传因明成就的,至今也仅有一人一文,因明界普遍赞扬玄奘取得的因明成就。然而,玄奘因明的主要贡献究竟在哪?至今还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因此,对玄奘因明成就有辩明之必要,有大力弘扬之必要。向国内外进一步广而告之,对汉传因明工作者来说责无旁贷。印度陈那因明体系的原貌是什么?用西方逻辑的眼光来衡量,其逻辑体系是什么性质,或者说是什么种类?印度逻辑史家维提布萨那的《中世纪印度逻辑史》和《印度逻辑史》讲不清楚,苏联科学院院士舍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也未讲清,日本名家大西祝和宇井博寿亦没有跳出欧洲学者的传统。他们望文生义,都不得正解。这是因为他们忽略了因明的论辩学科性质,他们的因明修养和眼光与当年在印度那烂陀寺学习和实践的亲历者——玄奘不可同日而语。标准答案在哪里?毫无疑问,应从汉传因明中找根据,应从玄奘因明思想中找根据。
唐代玄奘法师西行取经,“道贯五明,声映千古”(其弟子窥基语)。学成回国之前,玄奘的因明修养已达到全印度超一流高度。述说玄奘法师的因明成就,可分为印度求学和回国弘扬两大阶段。在讲述这两大阶段之前,需要追述他在西行之前的准备工作。玄奘法师准备了充足的精神资粮。他能创造中外佛教史上的奇迹,还与他个人的天赋分不开。他自小随兄出家,有良好的佛学熏陶。他有常人所罕有的“最强大脑”,他挑战了一系列不可能,年少便精通并能宣讲诸多经论,西行前已成为誉满大江南北的青年高僧。他有国内游学四方的经历,积累了丰富的旅行经验,再加上他有重大决心、非凡毅力和过人胆识,才能排除万难,绝处逢生,最终到达印度。求得真经(学习大乘有宗的代表性著作《瑜伽师地论》)是他西行的主攻方向。因明研习虽说只是副产品,但他在印度的17年间,自始至终,殚精竭虑致力于这项最重要的副修。在求学阶段,他既是研习因明的楷模,又是运用因明的典范。
玄奘法师是那烂陀寺中能讲解50部经论的十德之一,是由那烂陀寺众僧推派并由住持戒贤长老选定以抗辩小乘重大挑战的四高僧之一。他又是四高僧中唯一勇于出战的中流砥柱。四高僧之一的师子光曾在那烂陀寺宣讲龙树空宗而贬斥瑜伽行大义。应戒贤长老之请,玄奘登坛融合空有二宗,驳得师子光及其外援噤若寒蝉,哑口无言。足见玄奘的学术和论辩水平在那烂陀寺达到了超一流。 第一,他学习因明的起点很高。他得到了印度几乎所有因明权威的亲自传授。在印度大乘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佛学权威百岁老人戒贤住持不辞衰老,复出讲坛,专为玄奘开讲《瑜伽师地论》和陈那因明代表性著作。玄奘游历五印,“遍谒遗灵,备讯余烈”。第二,学习的内容非常全面。可以说,玄奘几乎研习了他那个时代新、古因明的所有代表性著作,甚至通晓小乘和外道如胜论、数论的学说,在学问上做到了知己知彼。第三,反复学习。在那烂陀寺一住将近五年,除听戒贤法师讲三遍《瑜伽师地论》(内有古因明)外,又听《因明入正理论》和《集量论》各两遍。还到各地访学,反复请高师解答疑难。我们不能不惊叹,没有逻辑工具作指导的玄奘法师对陈那因明三支作法及其论证规则的领会和阐发竟能做到如此精准。第四,继承和整理三种比量理论,使陈那因明臻于完善,并且运用这种理论在辩论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玄奘对待自己的老师,也不轻易盲从。玄奘对共比量、自比量和他比量三种比量理论的整理发展是对印度陈那因明的独特贡献。第五,玄奘是运用因明理论于论辩实践的典范。他“留学”17年,以辩论始,以辩论终。他善于运用,敢于超越,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玄奘本人在戒日王于曲女城召开的全印度各宗各派参与的大会上甚至表态,有人能更改一字则“斩首相谢”。玄奘的唯识和因明修养,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大会持续十八天,以玄奘的胜利而告终,获“大乘天”“小乘天”称号。第六,回国时,玄奘法师带回因明著作36部。回国后,他对因明的弘扬是述而不作,把全部精力放在译讲上。由于玄奘的弘扬,因明传播到了日本和新罗。特别是日本,一千多年历久不衰,对汉传因明典籍有保存之功,并且反哺了中国。第七,发展了陈那新因明的过失理论。陈那、商羯罗主二论的过失论,限于共比量范围。玄奘把它扩大到自比量和他比量,使得过失论更为丰富和细微。第八,留下一把打开陈那因明体系并引导破解逻辑体系的金钥匙。第九,对陈那新因明核心理论因三相规则的翻译极其准确甚至高于原文。笔者的评价是“既忠于原文,又高于原文”。翻译怎么能“高于原文”呢?原来,他把原文中固有的隐而不显的义理用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就更准确地表达原著的思想。这说明玄奘对陈那因明体系的把握是何等透彻,即使今天用逻辑眼光来审视,也精当无比。第十,玄奘法师弘扬了那烂陀寺当时的最新见解。因明大、小二论本来都把宗作为能立三支之一,但陈那晚期代表作《集量论》改变为以一因二喻或者以因三相代替能立三支。每每研读唐疏,都以为唐疏有误,其实为正解。
二、“同、异品除宗有法”是玄奘的重要遗训
由于玄奘法师对印度陈那因明的弘扬,重点放在对立破学说的译传和阐发上,因而其最重要的因明遗训就在这里。国内因明领域的重大分歧也集中在同、异品要不要除宗有法上。什么是同品、异品?印度人喜欢争辩声音是无常的还是常的。因明中的论题称为“宗”。其主项称为“有法”(体),其谓项称为“法”(义)。例如,佛弟子对婆罗门声论派立“声是无常”宗。具有“无常”法的对象被称为“同品”,瓶等一切具有无常性质的对象都是同品。不具有“无常”法的对象被称为“异品”,例如印度人共许的虚空和极微。什么是除宗有法?佛弟子赞成“声是无常”宗,声论派则反对。声音是无常的还是常的,要靠辩论来回答。只要立论人与敌论者双方坐下来辩论,同品、异品的范围就已经定了。它们都不包括声。同品的外延必须把声除外,异品的外延也必须把声除外。否则,就不要辩论了。在这一辩论中,双方共许,同、异品都除宗有法(声)。其中的逻辑规则带有明显的辩论特点。以纯逻辑眼光看,声音既不算无常的同品,又不算无常的异品,显然违反了形式逻辑排中律。但陈那因明是论辩逻辑,而非纯逻辑。这不是一个在书斋里讨论的纯粹的逻辑问题,在除宗有法的基础上来讨论陈那三支作法的论证种类,才是逻辑问题。
玄奘法师的遗训除了对陈那文本逐字逐句的诠释,还有对文本上没有专门论述的隐而不显的言外之意的阐发。他深知要把外来文化移植到中国,就必须交代清楚该理论产生和运用的历史背景。从古因明发展到陈那因明,偏偏有一条最重要的辩论规则不见诸文字。这个法则在玄奘法师翻译的因明大、小二论文本中,除了《理门论》关于因的第二相“于余同类,念此定有”中强调过宗有法(例如声)之“余”的才是同品外,就没有做过特别的说明。
“同、异品除宗有法”,对立、敌双方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潜规则。它是一条铁律,是题中应有之义,是陈那因明的“DNA”。在因明论著中说出来便是多此一举。同、异品,用数理逻辑的语言来说,它们是两个初始概念。一座陈那因明大厦就建立在这两个初始概念之上。陈那因明关于因的规则的建立(九句因理论)、因三相规则和同、异喻的组成以至三支作法整个体系的逻辑性质,都要坚持“同、异品除宗有法”。这是每一个因明家,每一个逻辑学家都应懂得的最基本常识。 假如双方都不除宗有法,则双方都会循环论证,不分胜负,辩论回到原点;假如双方都除,那么双方都不占规则便宜,就得另举论据;假如辩论的规则偏袒了一方,同、异品只除其一,使其中一方凭规则稳操胜券,另一方则未辩先输,这样的辩论赛还有人参加吗?同、异品不除宗有法或只除其一的辩论规则只能是今人在书斋里想象的产物。
“同、异品除宗有法”并非笔者的创见,它有文献依据。在日本僧人善珠所撰《因明论疏明灯抄》中引用了唐代总持寺玄应法师《理门论疏》中关于同品定义的一段话:“玄应师云:‘均等义品,说名同品者,此有四说。一有云,除宗已外,一切有法皆名义品。品谓品类,义即品故。若彼义品有所立法,与宗所立邻近均等,如此义品,方名同品。均平齐等,品类同故。彼意说云,除宗已外,一切有法但有所立,皆名同品,不取所立名同品也;二有云,除宗已外,一切差别名为义品,若彼义品与宗所立均等相似,如此义品,说名同品;三有云,除宗以外,有法、差别,与宗均等,双为同品;四有云,陈那既取法与有法不相离性,以之为宗。同品亦取除宗已外,有法、能别不相离义,名同品也。此说意云,除宗已外,有法、能别皆名义品。若彼义品二不相离,与宗均等,说名同品。’今依后解以之为正。”
可见,以上几家唐疏在给同品下定义时虽说法不一,但都强调了“除宗已(以)外”即“同品除宗有法”。按照佛教论著说法的习惯,异品也是除宗有法的。汉传因明向有“互举一名相影发故,欲令文约而义繁故”的惯例。窥基释同品不提除宗有法,释异品定义“异品者谓于是处无其所立”则标明“‘处’谓处所,即除宗外余一切法”。以异品除宗来影显同品亦除宗。日籍《因明论疏瑞源纪》里不仅保存了唐代玄应法师的记载,还补充说明三家归属。第一家为文轨,第二家为汴周璧公,第三家佚名,第四家为窥基。查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原文,未明言同品除宗(实际也主张除),异品处则明言“即除宗外余一切法”。玄应说唐疏有四家在给同、异品下定义时强调了“同、异品除宗有法”。又据敦煌遗珍中唐代净眼的《略抄》可知,净眼法师也有此一说。可见,连同玄应疏,唐疏共有六家主张此说。这应当看作玄奘的口义。唐疏不仅揭示同、异喻依(例证)必须除宗有法,其代表作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疏》更是进一步明言同、异喻体必须“除宗以外”。该疏在诠释同法喻时说:“处谓处所,即是一切除宗以外有无法处。显者,说也。若有无法,说与前陈,因相似品,便决定有宗法。”在诠释异法喻时说:“处谓处所,除宗已外有无法处,谓若有体,若无体法,但说无前所立之宗,前能立因亦遍非有。”用今天的逻辑语言来说,就是“同、异喻体是除外命题”。
从唐疏对陈那因明体系的诠释中我们可以整理出陈那因明的逻辑体系。三支作法的同、异喻体从逻辑上分析,而非仅仅从语言形式上看,并非毫无例外的全称命题,而是除外命题;因此,陈那三支作法与演绎论证还有一步之差,笔者称之为最大限度的类比论证(即三支作法是归纳,其同异喻并非临时归纳所得)。与古因明相比,它大大提高了论证水平,能“生决定解”,有助于取得论辩胜利。这成为印度逻辑史上一大里程碑。
然而,沈剑英认为,同、异喻依要除宗有法,而同、异喻体以至整个因明体系却不要除宗有法。他说:“这原本就不成其为问题,却有学者于此大做文章,将举譬时需‘除宗有法’,扩充到喻体也要‘除宗有法’,从而又冒出一个所谓的‘除外命题’来,以否定陈那因明具有演绎的性质。”说初始概念要除而整个体系不除,这有违逻辑常识。
百年来,国内老一辈因明家大都重视玄奘的这一重要遗训。太虚法师的《因明概论》认为,陈那因明的“同喻体多用若如何见如何”,如果同品不除宗有法,则“辞费而毫无所获”。其后,几乎所有因明家如熊十力、吕澂、慧圆(史一如)、陈望道、周叔迦、龚家骅、密林、虞愚、陈大齐等,都有“同、异品除宗有法”之说。其实,在玄奘的译本中,既用“若”,又用“诸”,都不做“如果”解。唐疏把“若”和“诸”当一个词用。汤铭钧曾发现,梵本的原意是“如同”“像”,是举例说明,没有假言的意思。笔者查《汉语大词典》,“若”既可解作“如同”“像”,还可解作代词“如此,这样”,或“这个、这些”,而“诸”除了“全体”的意思外,还有“众多”之意。在奘译所用汉语词“若”和“诸”有多种含义情况下,不能轻易断定其为“如果”或“全体”,也不能一见“若”和“诸”就轻易判定三支作法为演绎论证,因为其语言表达不等于逻辑形式。更重要的是看其逻辑规则能否保证其为演绎论证。
虞愚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著作中第一次把维提布萨那在《中世纪印度逻辑史》中因的后二相释文和陈那因明为演绎论证的观点都照搬过来,对汉传因明有很大误导。其照搬行为也曾于1944年被吕澂所批评:“不明印度逻辑之全貌,误以论议因明概括一切实为失当,又抄袭成书、谬误繁出,以资参考为用亦鲜,似不应予以奖励。”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陈大齐,作为逻辑学家,撰写了《因明大疏蠡测》和《印度理则学(因明)》。二书以正当之理由论证同、异品必须除宗有法,若异品不除宗,则无任何正因可言,毫不讳言因后二相亦除宗有法,甚至不讳言同、异喻体并非毫无例外的普遍命题。陈大齐能持有上述见解,十分难得,可惜他对陈那逻辑体系的总评价则不正确。他误以为三支作法既是演绎又自带归纳,每立一量则必先归纳一次,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缺乏依据。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又以为借助“归纳的飞跃”可以获得全称命题,有违逻辑常识。
笔者在很多论著中都阐明了陈那因明与法称因明在辩论术、逻辑和认识论三方面都有根本差别。20世纪上半叶以维提布萨那、舍尔巴茨基为代表的印度和欧洲因明学家不懂得陈那因明的潜规则,不了解玄奘译传的遗训,从而在比较研究方面失足,一点也不奇怪。他们完全用法称因明(论证形式相当于三段论)来解释陈那因明,既拔高了陈那因明的逻辑体系,又贬低了法称因明的历史地位。
总结我国百年因明研究,吕澂和陈大齐各擅胜场,他们分别在梵汉藏对勘研究和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最大的教训是,多数人未能以玄奘遗训为指南,把它逻辑地、内部一致地贯彻到整个因明体系中。又误以为陈那三支作法另外自带归纳。须知归纳说犯了窥基《大疏》中所说的“成异义过”和“同所成过”,即转移论题。详细的解释另见专论。陈大齐的失误则在于他所处时代还未有法称因明的译传和研究,完全不了解印度陈那、法称两个体系的根本不同。这是他所处时代的局限。
中国逻辑史学会第二任会长周文英就承认自己的论著,“在评述‘论式结构’和‘因三相’时有失误之处”,“这些说法当然不是我的自作主张,而是抄袭前人的,但不正确”。这令人肃然起敬,在自己赖以成名的研究领域,敢于检讨失误,充分体现了一个襟怀坦荡的大学问家实事求是的治学品格。这是讲究学术规范的一个杰出榜样,教训是偏信了印度和苏联的传统观点。
三、因明学科性质与标准答案
对印度陈那新因明逻辑体系的研究,是有标准答案的。尽管陈那因明中的逻辑是论辩逻辑,然而其逻辑成分仍必须用形式逻辑来衡量。形式逻辑只有真假二值,是就是,非就非,没有模糊一说。有人称其为“初步的演绎推理”。那是模糊逻辑,而因明与模糊逻辑无关。形式逻辑就像做四则运算,1加1等于2,只有这一个标准答案,除此之外其他千千万万个答案都是错的。因明的逻辑最多是做中学代数,不需要很高深的逻辑学问。有准确的三段论知识就够了。衡量标准答案有客观标准。众所周知,假说被普遍认可为科学,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自洽性和无矛盾性,即自圆其说。其二,对已有的发现不但能准确描述还能圆满解释并且符合现有科学实践。其三,据此做出推论和预知。因明的标准答案也应满足这三条。根据我们的观点,能一通百通地解释整个陈那因明体系而没有矛盾。不但能圆融无碍地解释整个陈那因明逻辑体系,还能和谐一致地把陈那因明与后起的法称因明的异同讲清楚。对诤友们的各种非难,全都能给予合理解答。反之,则寸步难行,矛盾百出。
因明已经作古,本身不再发展,但是,以之为研究对象,找到了标准答案,还可有推论和预知作用。例如,在梵、汉、藏、英文本对勘研究中,汤铭钧曾发现意大利著名学者杜齐用英语将《理门论》转译时,就漏译了因的第二相“于余同类,念此定有”中那个关键词“余”。这位享誉世界的因明大家稍有不慎就与“同、异品除宗有法”擦肩而过。又如,前文提到,汤铭钧发现吕澂把同、异喻体上的“若”解作假言的“如果”是一误释。再如,有人认为,陈那因三相没说异品也要除宗有法,批评我们对因的第三相解释过多。为此,汤铭钧根据《集量论》藏译(金铠译本)对应文句作了汉译:“而且在比量中,有如下规则被观察到:当这个推理标记在所比(有法)上被确知,而且在别处,我们还回想到(这个推理标记)在与彼(所比)同类的事物中存在,以及在(所立法)无的事物中不存在,由此就产生了对于这个(所比有法)的确知。”汤铭钧解释说,两个藏译本都将“别处”图片即“余”作为一个独立的状语放在句首,以表明无论对“彼同类有”还是“彼无处无”的忆念,都发生在除宗以外“别处”的范围内。藏译力求字字对应;奘译则文约而义丰,以“同类”(同品)于宗有法之“余”来影显“彼无处”(异品)亦于余。两者以不同的语言风格都再现了陈那原文对同、异品都应除宗有法的明确交代。
美国学者理查德·海耶斯从陈那《集量论》藏译本的字里行间读出了正解,值得大力弘扬。其主要观点在《佛家逻辑通论》中引述过。几乎同时,笔者在1985年,从唐代疏记中也推出了相同的逻辑结论,可谓殊途同归。多年过去,陈大齐的许多具体论述和海耶斯的正解还未被国内的因明工作者接受。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当代越来越多的欧美学者接受了海耶斯关于陈那因明非演绎的观点。海耶斯谙熟因明的体系和现代逻辑,对九句因、因三相和陈那的逻辑体系发表了精到的见解。他主张“确认”不是“证明”。认为佛家认识论采用的是经验科学推理,而不是数学与逻辑的严密论证。他说:“在描述陈那如何探究有关问题前,我想先说明,大部分佛家认识论的现代解释者们,偏好理解Sādhana为证明(proof)而非确认(confirmation)。但谨慎的作者们通常仅在数学和逻辑的领域里才使用proof这个英文字,那些领域里的定理系由公理推衍出因而得视为是确然为真。但在日常实际的领域里,在经验科学中,几无任何科学是确然为真的,只能视为是与已知证据相一致而仍可能为未来的证据推翻。佛教认识论在其目标和方法上,都更接近法律和经验科学的实用推理,而非数学与逻辑的严密论证,因此借后来的术语来讨论并不恰当。”
沈有鼎不满于除宗有法带来的非演绎的后果,他提供了一个方案来保证陈那三支作法为演绎,却不合因明常识。巫寿康将其设想演绎成博士论文,被誉为“解决了久悬不决的千年难题”。另有学者又发现,比沈有鼎更早,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美籍华人齐思贻的《佛教的形式逻辑学》,就把陈那的同品除宗和法称的异品不除宗合在一起,既不符合陈那的同、异品除宗,又不符合法称的同、异品不除宗。这四不像理论,似乎满足了演绎的主观愿望,却犯了替古人捉刀、反历史主义的方法论错误,而且颠覆了陈那因明整个体系,并非古籍研究之所宜。
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国内哲学界爆发了一场形式逻辑大讨论。复旦大学的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力排众议,取得了胜利。其重大启示是,因明研究的前提条件是搞清楚因明学科的性质。周谷城讲清了形式逻辑不同于形而上学(20世纪50年代艾思奇把形式逻辑当形而上学批判),它只管推理形式、不管推理内容,三段论推不出新知识等常识性问题。总之,讲清了这门学科的性质,在全国范围内空前普及了形式逻辑学科的基本知识。从此,该领域不再有众多常识问题的争论。
因明学科是论辩逻辑这个论断,还远未取得共识,因明研究落后形式逻辑研究60多年。来一场学科性质的大讨论,该领域的所有重大分歧当迎刃而解。
四、与《中国社会科学评价》所发三论商榷
傅光全的论文《因明何以成绝学》既然将因明作为讨论对象,那么为什么称印、汉、藏的佛教逻辑学—认识论传统为因明,作者似应作必要说明。因明这个名称的标准梵语对应hetuvidyā,不仅在《正理藏》中没有出现,而且在因明公认的经典学者陈那的著作中,目前也无法确认哪怕出现过一次。尽管这个名称见于《瑜伽师地论》及关联文献,它显然没有成为印度佛教逻辑学—认识论学派的标准名称,在西藏亦然。作者还应交代,抢救和保护的是因明,还是对因明的研究。如同问:抢救和保护的,究竟是佛教,还是对佛教的研究。如果抢救的是因明,便有必要说明因明这门学问有别于现代逻辑学的独特意义。为什么我们有了现代逻辑,还要使用因明?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特别是1983年中国逻辑史学会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六·五重点项目“中国逻辑史”(五卷本)为标志,因明研究盛况空前。虽未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显学,但已不可能重新成为绝学。如果抢救的是“对因明的研究”,那就首先应当抢救玄奘的伟大贡献,才能真正了解今天所要抢救的对象的本来面目。这应是探讨“因明何以成为绝学”不能回避的前提。“对因明的研究”属于现代学术的范畴,与此文着重论述的是印、藏、汉古典因明传统在对待因明这门学问的态度上似乎存在差异——就好比佛教史家与教内的大师对待佛教的态度是不同的。如果认为“因明”与“对因明的研究”是一回事情,最好也要给出理由。以逻辑的眼光衡量,此学也实在算不上“高明”,它在陈那阶段离西方三段论水平还有一步之差,即使是法称因明也不过相当于三段论第一格水平。它与欧洲中世纪三段论理论体系相比,逻辑理论过于简单。按照作者所引《现代汉语词典》的标准,绝学指的是“失传的学问,高明而独到的学问”。在汉地曾经失传则无疑,有三合一特色也还算“独到”(其实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就在并非纯逻辑的《工具论》中),但与“高明”距离较远。更准确地说,我们花大力气正在抢救的只是冷门学科。在实际生活当中,人们宁愿用逻辑而不会去用因明。除藏传因明,它没有实用性。此文一大缺憾是没有提到,汉传因明失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唐代因明典籍于中国历史上几近绝迹。明代因明研习者研读的因明原著也仅限于陈那弟子商羯罗主著的《因明入正理论》,陈那本人早期代表作《因明正理门论》提都未提到过。宋代有17本因明著作。在明代,除了仅见有关因明的《宗镜录》外,其余16本片纸不存。更看不到唐疏,研习因明好似盲人摸象(唐疏代表作窥基的《因明大疏》其实在抗日战争中于山西广胜寺连同其他宋藏遗珍被发现)。这不能不是因明失传的一个重要原因。
沈剑英论文的学理要义问题则在于,他往往背离因明经典原著的界定,甚至批评《理门论》自相矛盾,批评《入论》定义片面,因而要修改同、异品定义。在此文中,他说:“因明的核心理论是因三相,因三相是因的三个方面,其主语都是因。有学者误将第一相的主语读作‘有法’,将第二相的主语读作‘同品’,将第三相的主语读作‘异品’,这就难以准确地诠释因三相的含义。”姑妄认可汉译因三相语句的“主语都是因”,但我们要讨论的对象是因三相的逻辑形式,即因三相命题或判断的逻辑形式,而不是语句。命题主项不等于语句主词。因的第一相汉译为“遍是宗法性”。古今中外,几乎举世公认第一相的逻辑形式为“凡宗有法(论题主项)都是因”,即“所有宗有法都包含于或真包含于因”。沈剑英的论著也从不反对该命题主项为宗之有法而不是因概念。例如,“凡声(宗有法)是所作(因)”。
话说回来,因概念也可以作为命题主项,但是,第一相的逻辑形式相应改为“因包含或真包含宗有法”。两种表述逻辑等值。这是中学逻辑代数的基础知识,无须多言。按因明的惯例,遍是宗法性常用的实例是“凡声(宗有法)是所作(因)”,即“宗有法包含于或真包含于因”。可见,沈剑英以第一相“遍是宗法性”省略了主语因,以因概念一定是第一相的逻辑形式的主项,作为第二、三相主语或命题主项也是因概念的理由,显然不成立。按照陈那因明体系,只要有一个同品有因,就满足了第二相“同品定有性”。用形式逻辑概念间所具有的五种关系来说,相容关系的全部四种都适合,即同品概念与因概念是全同关系、包含关系、包含于关系和交叉关系。这一逻辑规定显然不适合沈剑英对第二相逻辑形式的描述。第二相根本不是全称命题,它只能是特称肯定命题,即“除宗以外,有同品是因”。
沈剑英还认为第二相与第三相不等值是错误的。刚才说,只要承认有一个同品有因,就满足了第二相“同品定有性”,第二相的逻辑形式只能是特称的,并且主项非空类。因此,必然与第三相不等值,第二、三相不能互推。第三相“异品遍无性”是说没有一个异品有因。主项可以是空类。从主项空类的第三相推不出主项空类的第二相。这也是形式逻辑基础知识。沈剑英还主张第二相与同喻体等值等一系列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错误,笔者在自己的论著中一再评述,此不赘言。请注意,沈剑英的因明要理,除“主语”理由外,均见维提布萨那、舍尔巴茨基和宇井博寿,并非创见。
日本的末木刚博教授研究陈那因明,用的是数理逻辑工具,由于不理解陈那因明体系基本知识,重走了维提布萨那、舍尔巴茨基和宇井博寿的老路。孙中原说:“末木刚博的《因明的谬误论》,用数理逻辑符号,分析因明33种似能立过失,是齐思贻、杉原丈夫、林彦明、宇井伯寿、北川秀则等诸家学说的集大成。”北川秀则与末木刚博是否有联系,尚需存疑。北川秀则是日本20世纪50年代主张同、异品都除宗有法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同、异品除宗有法,因三相是独立的,因的第二相不等于第三相,后二相不能互推,二喻体并非全称命题,同喻可以推出异喻,异喻则推不出同喻,三支作法非演绎,这一整套观点都与后学末木刚博和沈剑英、孙中原所主张的大异其趣。由此,末木刚博的论著成为“诸家学说的集大成”也应存疑。与此同时,黄志强在其《佛家逻辑比较研究》中,解释了因的第一相的逻辑形式,其赞同沈剑英的看法,第一相的主语和主项都是因,却认为第一相的逻辑形式是“因法遍是宗法性”,即“凡因都是宗法(所立法)”,违背古今中外公认的解释“凡宗有法(论题主项)都是因”。该文所举例为“凡所作皆无常”,完全等同于同喻体,而不是三支作法中的因支“凡声(宗有法)是所作(因)”。这一谬误得到一批相关专家的赞同。有专家评论道,第一相“因法普遍具有宗法性”,“这一解释很接近梵本原文”,即“宗法性”,还认为此文“根据权威的古典经论”,连同其他一系列新观点,“基本上是准确的和正确的”。这一评论完全违背权威的古典经论《理门论》。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存在一词多义和一句多解的情况,而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每一字、词、句的含义又是确定的,不容随意解释。抛开汉传因明的权威经典,仅从字面意义来谈论上述新解与梵文原文“宗法性”“很接近”,未免有欠谨慎。
几十年来,笔者一直认为,要得到印度陈那因明体系和逻辑体系之真解,必须具备因明和逻辑两方面的准确知识。有数理逻辑知识更好,但“杀鸡不用牛刀”。如果不真正了解因明,那么工具再好,也很难避免南辕北辙之误。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薛刚
扫码在手机上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