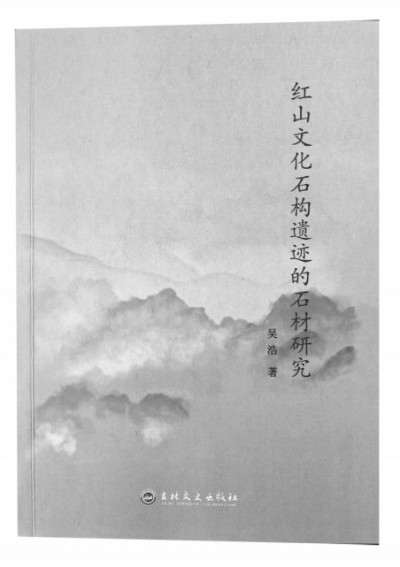红山文化(约6000—4500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性文化类型,尤以精美复杂的玉器和古朴神秘的彩陶器而闻名,素有“南良渚、北红山”之美誉。相比之下,石构遗迹似乎不够光鲜亮丽,也难以第一时间吸引人们的注意。对于石构遗迹的研究,多集中于祭祀习俗和建筑形制等领域,因此“石”这一概念大多以集体形式出现,甚至只有当它聚集形成建筑、积石塚、墓葬之时才具有被公开谈论的资格。“石”如同深沉、温厚的大地一样,永远沉淀在红山文化的最下层,却默默托举起一切文明的表征。能关注“石”之本身,即石材的人,想必也具备这种踏实、坚毅与朴素的品质。
从“石材”这一视角,切入红山文化研究并形成独立课题,在既有研究中未见先例,青年学者吴浩撰写的《红山文化石构遗迹的石材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25年2月)首开先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成果汇报,它更是诞生于年轻学者那份蓬勃探索欲与求知欲中的一次跨学科突破尝试。作为吴浩的学业导师,我愿意以见证者的身份介绍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分享我对其研究历程及付梓之路的观察。
本书首次将“石材”作为核心对象,借助材料学、地质学、考古技术等多学科的方法,针对石材的来源、采选、加工与使用方式展开系统的研究,并沿实证路径还原了红山社会在技术体系、资源组织与观念结构上的多重面貌。这种“从材料出发”的研究思路,突破了传统考古学对于器型与纹饰的路径依赖,将“物质性”视为理解古人精神世界的钥匙。这个尝试既是一种理论范式的更新,也是一种学术思维的勇敢转向。
本书始终坚持“实例-技术-文化”三者相互交织的分析路径。正是这种建立在证据之上的缜密推演,使得研究成果具有说服力,且富有启发性。书中提出的“石材并非仅作为建筑原料,而是红山文化技术体系与信仰系统的物质载体”这一论点,不仅突破了学界对红山文化的固有理解,更提示我们:材料的选择,从来就不是中性的,它必然反映技术水平,也揭示观念结构。
经常与石材打交道的法国雕塑家罗丹曾说过:“生活中从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我认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研究与著作领域。好的研究看似刻板却总是引人入胜,而研究者更是在智慧层面解决问题、追寻探索的深刻美感。在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章节中,我尤为关注作者对红山遗址石材来源的追溯与技术路径的复原。这部分内容没有局限于类型学的描述,而是结合岩相学分析、地质构造图层与实地采样考察,在辽西至蒙东的广阔地带构建起红山时代石材使用的地理逻辑。从物理成分、纹理走向、运输路线到加工痕迹,每一环节都经得起细细推敲。更重要的是,研究并未停留于“技术复原”的层面,而是进一步提出了选择背后的认知机制。例如辉长岩、片麻岩等在不同功能空间中的差异化使用,其所传达的并非纯粹的物理效用,更可能承载着对宇宙秩序与精神世界的认知。这种由微观至宏观、由材料至观念的思维方式,不仅为考古研究提供了物质证据,也在不动声色中重塑了我们对红山先民精神世界的理解。
与此同时,这本书的田野部分体现出的一份“踏实与克制”。红山文化遗存大多地处偏远、地势复杂,考察期间所面对的困难往往无法越过文字亲身感知。而本书从未以“条件所限”来弱化数据质量,反而在若干无法取样的情况下采用非破坏性检测方法,并通过比对历史图像与前期调查资料进行推演补充。作者的严谨程度令人钦佩,由此可见,学术的根基从不是纸面上的术语堆砌,而恰恰在于这种“不放弃一处可能证据”的执拗与坚持。
在本书的诞生过程中,我目睹了吴浩一次次深入实地的奔赴,一次次面对资料断裂的困顿,也见证了她在反复推敲、厘清论证中逐渐形成自己学术风格的蜕变。她的著作,不是机械地堆砌数据,而是试图与石材、与遗址、与远古的人们建立一种“理解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得本书既有学理的严谨,也有情感的温度,不失一份难得的人文关怀。
当然,这项研究尚非尽善尽美,无论是样本的覆盖、技术路径的完善,还是理论建构的进一步深化,未来仍有大量工作值得投入。但可喜的是,这本书所体现出的思考方式与学术志趣,已经高于学业阶段的常规范式。本书建立的多学科研究框架具有可扩展性,对石材的分析方法亦可应用于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关于石材运输路线的建模分析经验,可为史前贸易网络研究提供技术参照。
考古、文博、历史领域的研究不仅仅是对过去的重构,更是与当下的对话。吴浩以石为媒,以材为引,将我们重新带回那些尚未完全解释清楚的红山遗址之中。在这些静默的石块之间,她不仅聆听到了红山先民的脚步声,也令我们看到了年轻学者探寻文化源流的坚定目光。愿这份目光,能被更多读者感知、被更多同行激励。
(作者系赤峰学院历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