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陈旭光教授新著《影像中国与光影未来》(中国文联出版社2025年5月版)入选《啄木鸟文丛——文艺评论家作品集(2024)》。如果从这本书去透视作者的心路历程,我们会有怎样的发现?而这条心路历程的转变又会对我们有着怎样的启示?
文化史的关切
《影像中国与光影未来》从现实观照的角度切近了新时代中国电影,为当代中国影视文化立此存照。因此,《影像中国与光影未来》是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中的一朵浪花,它以影视为对象展示了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波澜壮阔,它是一个学者的心灵感悟,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化转向”。
不仅如此,这一点恰是呈现出了文化史的五彩斑斓。近年来,历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成为显学。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大众文化史”的转向。在陈旭光的《论作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电影工业美学》论述中,“大众文化转向要求尊重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特性,包括娱乐性、消费性,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对普通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的尊重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大众文化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显现出了思想的底色。从中国电影的现场出发关注中国电影新力量、分析中国电影新现象、提炼中国电影理论新学说,在中国电影宏大叙事中重视民间的力量,在草蛇灰线的缝隙中求证中国电影理论的主体性和原创性。“电影工业美学”“想象力消费”“影游融合”正是这样的尝试。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实践在前理论在后,理论是对实践的归纳、总结和提炼。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如果没有及时的理论归纳和总结,实践往往成了明日黄花。忽如一夜春风来,中国电影新力量导演崛起在中国电影舞台上,这其中“跨界”的“斜杠青年”成了一个典型的现象,新力量导演的集中爆发改变了中国电影的市场格局,中国电影走出去有了更强烈的主体性新力量。新力量导演挑战了老导演的权威,技术的平权更进一步消解了导演的定义,在这个意义上如何来关注这批新力量导演的创作实际上是中国电影值得重视的大问题。“电影工业美学”应时而生,“电影工业美学”不仅在美学意义上对“技术—艺术”这个古老的二元对立难题做出了符合中国电影实际的阐释,从深层次上讲是从“青年文化性”的基底中尊重新力量青年导演所蕴含的创造力。《论作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电影工业美学》成了不断“接着写”的学术旨归。“想象力消费”紧随其后,“想象力消费”不仅紧贴着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科幻电影,更是将“想象力”这个人类最具有神性的艺术创造能力拉回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这个严肃的历史命题中,《“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命题与电影的“想象力消费”理论》便构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对话,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被压抑的鬼狐志怪获得了新的生长空间,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了新的可能。与此同时,影游融合与元宇宙等饱含着青年特性、时代特点和科技赋能的现象凸显为研究对象,《“元宇宙”思考三题:电影理论扩容、想象力的悖论与伦理预警》等文章所阐释并回答的问题不仅是对中国电影未来的判断,更是陈旭光对当下青年人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文化娱乐、生活方式的分享,是一个年长学者向青年学习的过程。说得更直率的一点,是再启蒙的开始和掘进。
思想史的进路
我更愿意把《影像中国与光影未来》作为思想史来阅读,我更想通过此书对其个人进行“思想考古”。一个学者的沉淀是漫长的,文字就是思想的赓续,在思想的变化与转折之处,中国当代学人的共性特点跃然纸上。
那么,如果要做一个考古,《影像中国与光影未来》的思想源头在哪里?在我看来,《影像中国与光影未来》的思想源头在谢冕先生这里。其中,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师承关系。
20世纪90年代初期,陈旭光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在思想成长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启蒙的召唤,在中国当代文学共生的语境中,思想在不断地发芽与绵延,所不同的是,电影成了论述的对象。在思想的萌芽处,谢冕先生发现中国文学中“忧患”的主题。在陈旭光的论述中,“忧患”就是对中国电影的盛世危言,就是永不停歇的呐喊。为什么中国电影各个类型都有发展,但是科幻电影却始终薄弱,是中国电影缺乏想象力吗?如何激发中国科幻、玄幻、魔幻类电影的想象力?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呐喊和追问,“想象力消费”才可能应时而生。在思想的流变处,谢冕先生发现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在陈旭光的论述中,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被电视剧《繁花》直接点燃。他认为,《繁花》之所以受到大众热议,从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来看,是因为该剧切合了人们对那个遍地机会,尽皆可能,充满机遇、冒险与挑战的黄金年代的想象式回忆和梦幻般凭吊,充满了只可远观意会不可言传的感伤哀婉气息。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用具体的作品证明了文学/艺术与时代的关系,在那些或为经典,或为寻常的作品中闪烁着弦歌不绝的思想之光,那是古老中国所遭遇到的现代性危机,那是两代学人用思想编织起来的芦苇,芦苇在层层黑夜中飘动,飘扬着当代中国学者的思想之光。
未完成的启蒙
但是,《影像中国与光影未来》并不完美,尤其是将其放置于“思想考古”的视野下,这种不完美就显得尤为突出。这种不完美的根本在于每一位学者成长的历史条件与环境不同,这既证明了“学术即性情”的普遍道理,也言说了启蒙在中国的命运。
在我看来,陈旭光教授之所以取得今天之成绩不是偶然的,温润的性格、勤勉的努力、持续的探究、对“度”的把握实际上在性格深处成就了陈旭光的为学为文。但是,他身上的温润性格实际上也抵消了学术研究的锋芒。尤其是将他早期对第三代诗歌的关注、醉心于新诗的形式结构和语言特征的情况相比,锋芒的力度、问题的深刻、力透纸背的阐释总是有“留白”之憾。
我只能说,这是一种宿命——它在深层次上体现为当代中国学人的心态史观的共性特点。由此感知,从陈旭光身上所代表的恰恰是一代学人的心态史观,在中国电影走向电影强国的征程中保留着呐喊和彷徨的自由,在影像餍足的当下允诺着诗性精神的绽放,在启蒙日渐式微的当下充当着提灯者前行的形象。
因此我想说,更重要的是要把《影像中国与光影未来》当成解剖中国当代学人精神密码的样板来阅读,在这本书里,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能够自由呐喊的限度。这个限度,就像朱国华教授在《漫长的革命》里面所写到的,这是“我们的极致,也是我们的极限”。毕竟,对于当代中国学人来说,我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所热爱的思考写作,所焚心般滴血都是未尽的启蒙。如此而言,这场“漫长的革命”才是这本书真正的文眼,也是我们这一代学人肩负的历史使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新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流变及其机制研究”(2000—2024)前期成果(24BC049)】
(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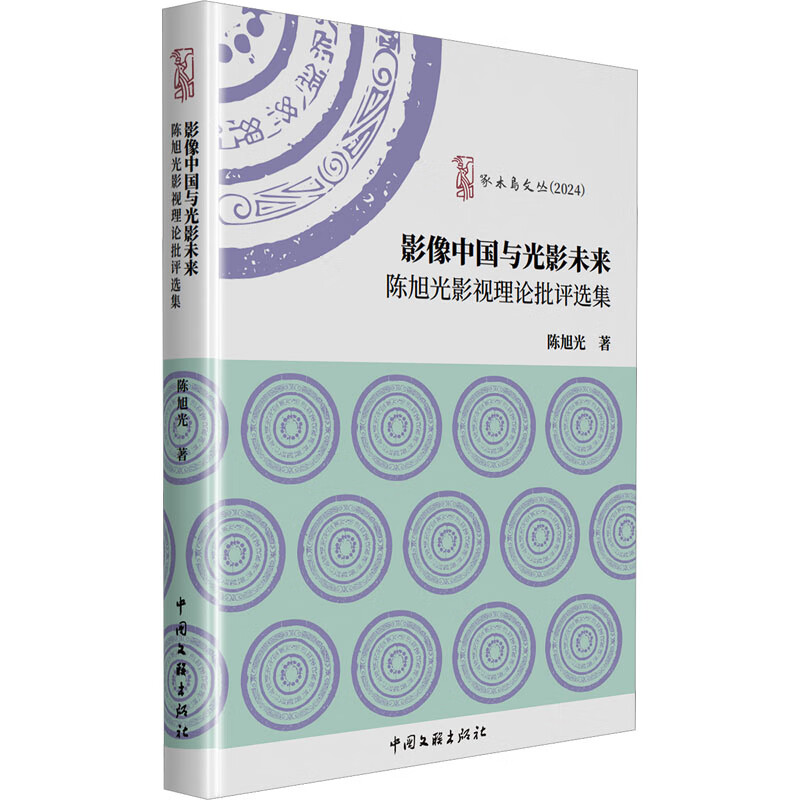
陈旭光 著《影像中国与光影未来——陈旭光影视理论批评选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