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云落》的历史坐标是改革开放,张楚以同时代人的感觉经验写出了众生万象的心灵史。万樱是张楚小说的元叙事,她作为哲学层面的“真实”象征,内含着同情的理解方法和恒定的时间体验,成为反思现代性经验的创伤性存在。与之相应,小说铺陈出日常生活的消费秩序和欲望审美化,勾勒出世俗时代的倦怠和羞耻。而在一个加速时代里怀旧是小说内在于改革年代情感结构的必然选择,不过身世之谜也造成了旧日的裂隙。三个代际的人物携带着精神原乡在变动的时代里浮沉和寻根,最终发现解释从何而来固然重要,但思索该以何种心态、向何处去更是我们面向未来的题中之义。《云落》的小说诗学糅合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诗性经验和现实主义的认识论,这既是当代叙事的历史性修辞,也意味着小说家正在重建内部经验与外部世界互为关联的诗学世界。
关键词:《云落》;张楚;现实主义;内在经验;抒情主体
作者姜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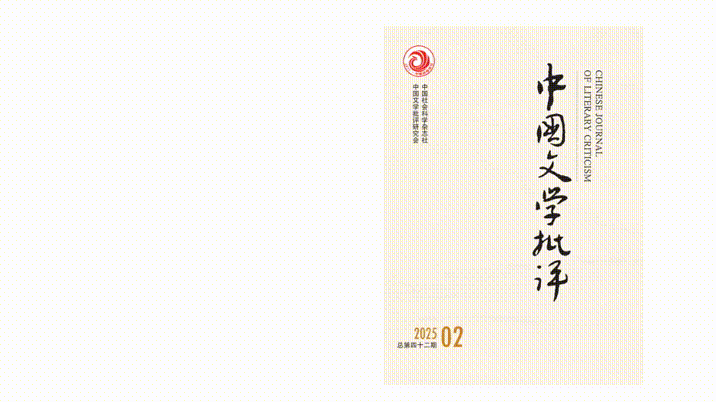
张楚的小说诗学体现出存在主义哲学的诗性经验与现实主义认识论的结合。一方面,小说对孤独感、偶然性、荒诞性等存在主义哲学气质有着难以言喻的审美偏爱,另一方面,小说叙事的认识论则偏向于现实主义。尽管小说家深知文学或许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人的存在困境,但他仍用小说的形式努力为人物命运和世事因果寻找历史与现实的根源。从更为深层的角度来看,文学的形式表征文学的历史性,小说的笔法往往是历史感觉的形式再现。张楚小说诗学所体现出的丰饶与含混也即一种历史性修辞。
《云落》的历史坐标是改革开放,这同时也是小说家形成感觉结构和美学经验的历史环境。小说里那些熟悉的地理风物,似曾相识的行动细节,一如既往的语言节奏,都在宣告这部作品是张楚小说世界的一次整合和集中呈现。作品虚构与非虚构并行,结构起伏有致,情节草蛇灰线,经验内外糅合,事件具体清晰,众多人物在高度还原的场景里热乎乎地生老病死,沉甸甸地日复一日,联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世界。而几位主要人物与小说家俱是同代人,这便使得作品不仅是他曾允诺的倴城众生万象的心灵史,更是小说家个人的心灵之书。
作为“真实”装置的万樱
万樱是谁?这可能是小说读者最先好奇的问题。这位不断变换名字,在张楚小说世界里慢慢成长、默默度日的女性,始终未曾离开小镇,一直懵懂天然、淳朴赤诚。这位女性人物一再出现,自然不只关涉一个典型形象的成立,更是有意味的形式,“万樱”可以被理解为张楚小说的元叙事。
《云落》中的万樱是小说“点线串珠”手法的核心之所在。所谓“点线串珠”又称“流水场子”,原是传统戏曲讲故事的创作方法。与西方戏剧板块式的紧凑结构不同,传统戏曲受先秦史传的叙述方式影响,常以事件发展顺序(多为时序)串联人物和情节,讲究故事的首尾完全、细节的伏笔预设、事件的曲折迂回。《云落》的故事层并非以惊奇取胜,叙事层整体节奏又偏缓慢,小说之所以能产生故事戏剧性的关键,正是在于作家将事件时序与讲述声音交叉重叠于前后贯通的线索之中。万樱无疑是这条具有结构性功能的线索,在她的眼里和口中,读者方能了解云落的边边角角、人物的种种性格和事件的来龙去脉。这里有她的姐妹来素芸、蒋明芳,她的男朋友常云泽,她的房客天青,她的雇佣者常献凯、老太太,还有她难以宣之于口的爱恋罗小军,以及围绕着主要人物交织的事件。
然而,被众多朝夕相伴的人物包围和信任的主要线索万樱,却无法在熟人的视角中得以呈现。即便是小说隐含的全知叙事者,也只是不停白描万樱每天的行动,提供一个勤劳朴素的侧影而已。万樱的声音、脸庞和心惊胆战的秘密,只能在前来云落旅行的天青眼里立体呈现:
这样的人,可能不怕黑夜里的闪电惊雷,却怕陌生人漫不经心的一声叹息。她身上也没有这个年岁的女人惯有的水果微糜之气,倒是那种旷野的清朗,那种隐隐传来的掺杂着深夜里的玉黍、稻谷和甘草的气味。
他暗地里观察着万樱张望常云泽的眼神,观察着万樱的穷酸样,观察着这个笨嘴笨舌的女人说着蹩脚的谎话……他丝毫没有偷窃别人隐私的快感,相反,却有种类似彗星穿越恒星时的恐惧……与羞耻。(第178页)
可以说,万樱对人伦和契约的理解,对进步时间的感知,都具有鲜明的前现代性特征,如果说现代性经验是构成现实原则的基石,那么以前现代经验存在的万樱必然成为现代性车轮碾压的创伤性真实。不过我们也要意识到对前现代性经验的偏爱是一种小说的修辞,它不等于质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正如小说家迷恋的是美学意义上作为时间修辞的静态县城,而非事实层面的县城封闭。反而正是由于县城的发展不曾为历史的想象提供应有的活力,即便在小说家还未离开县城时,就早已为此处吟唱乡愁的挽歌。
世俗时代的倦怠和羞耻
与万樱的真实存在经验不同,她藏在心底的爱恋罗小军,则是一位不得不习惯现实社会生存法则的商人。小说行至中后段,罗小军遭遇事业危机,昏昏沉沉之际梦到了万樱,“恍惚间他抱住了她,仿佛抱住了一株散发着香气的植物……醒醒吧,快醒醒吧!他嘶吼起来……”(第301页)尽管只有“真实”才能为迷失人海的云落游子带来家园般的安全感,但在全速行进的世俗时代,“真实”已经被甩在达成共识的进步时间之外。云落有名的钻石王老五罗小军对潜意识梦境击溃现实原则裸露出来的真实时刻爱恨交织、惶恐无措,并且感到十分羞耻,“扯淡!荒唐!”(第153页)
小说主线故事大致开端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现象,莫过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9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加速融入全球经济流动,由此社会转型高速行进,世俗时代喧嚣降临。在这一过程中,现实原则快速改变了个人本真性,现代人的伦理关系和精神状况发生剧烈变化,这构成了当代思想史、情感史的重要议题和显性线索。
中年罗小军偶尔也会出海探险,不过不是为了达成年少之所愿,而是去南海钓新鲜的金枪鱼。这种象征新兴中产阶层身份的饮食,价值早已与生理需求无关,吃不吃得上新鲜的金枪鱼似乎不重要,跟谁一起吃鱼才重要。罗小军的钓友们“喝着勐海普洱谈着华尔街股市,脖上套着波罗的海蜜蜡项链,手上戴着莫桑比克象牙手环,这掌心里,最次也得攥一对极品麒麟纹官帽核桃”(第21—22页),在推杯换盏之间比拟着海明威《老人与海》的男性气质。类似场面可谓《云落》对世俗时代的另一重生动写照,食色溢出人性合理界限,欲望早已被审美化所接纳。
在《云落》里,“饮食”是世俗时代日常生活的文化符号。饮食书写作为世俗化象征在当代文学史中形成了一条较为鲜明的文化线索,在不同时期内含着异质性的历史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饮食往往作为留存于特定地域的风俗文化出现,较有代表性的如陆文夫《美食家》、阿城《棋王》、贾平凹《商州初录》等作品,皆以饮食象征非规范性的民间意识,以此唤醒被掩藏的俗文化接续历史断裂带,具有历史反思性的话语内涵。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饮食则成为全社会非理性情绪蔓延的欲望符号,此时的饮食书写便体现出鲜明的历史批判性。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莫言的《酒国》,这部写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小说寓意独特,在主要人物丁钩儿眼中,酒国里的大小筵席展开一幅享乐、欲望、金钱、枯竭的消费主义拟象,尤其是小说中的“驴肉一条街”,猩红残酷,宛若地狱。
旧日裂隙与身世之谜
在一个加速的世俗时代里怀旧,是《云落》内在于改革开放情感结构的必然选择,即便二十几岁无旧可怀的青年常云泽在与万樱姑姑的亲近中也暗藏乡愁的焦虑,这也构成了小说以纯文学文本与大众文化现场对话的可能性。不过更为有趣的是,云落的男人们希望以向后看的方式获得归属感,当他们回望时总会找到云落的女人们,但相较于过早怀旧的男性,这里的女性倒是生动地活在当下,她们的鲜活甚至摧毁了旧日的神话。
当然,更深的旧日裂隙仍在于身世之谜,云落的每个人都携带着一个关于出身的故事,事实上无法辨认自己的身世,也正是社会发展速度过快的精神症候。小说里有三代人,形成历史中连贯的三个代际。第一代人万永胜的精神原乡是20世纪60年代,他们是跨越历史转折的革命一代人。万永胜17岁进工厂,90年代中期国企改革下岗后带着罗小军谋生,跑大货、开水泥厂、公私合资转私营医院,2000年包揽建筑工程,2007年涉足房地产,顺着改革开放的巨浪沉浮。他“身坯魁实,虎口如钳,一步顶旁人两步”(第28页),几十年来只喝自来水,抽七块钱一包的“阿诗玛”,没坐过几次飞机,骑着二八自行车,任谁见了他都要尊称一声“万爷”,俨然小城江湖的总舵主。尽管时代风潮在变化,但目标清晰、意志坚定、杀伐果断的万永胜,每一步都清楚自己该往哪里走。
他觉得云落越来越陌生,这座他诞生的老城,正在以某种超越了自然力量和法则的速度膨胀着,也许比宇宙大爆炸的速度还快……他发觉自己的身躯正随着步伐的摆动慢慢缩小,他的胳膊、手掌、脚和腿都缩成了少年模样,然后当他躺在一棵悬铃木下时,他发觉自己俨然变成了婴儿。他根本动不了,只能透过黑色的树叶和枝干窥望到星辰稀朗的夜空。他迷迷糊糊地想,他马上就要回到他母亲的体内了,他会变成一颗受精卵,分解成一枚卵子和一枚精子, 然后,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就像那些消失在大海里的雨滴。(第125页)
同样在临近尾声处,出现了第四代人少年麒麟,他是罗小军的儿子。麒麟仅出现在“麒麟之海”一章,正处于他爸爸曾经狂热收集地图的年龄,他这次却选择离家出走,去寻找妈妈临终也未能看到的大海。麒麟是个爱写作的孩子,他的笔记本里除了与父亲的和解,还有对宇宙的玄想。张楚的小说经常出现的宇宙意象,除了关于人类时间的直觉,也联系起后人类的未来想象。毕竟目前来看,全球化作为内在于人类的一种概念,似乎已经不足以让我们理解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或许当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宇宙的行星思维,以一种敞开未来的新方法接受共同存在的世界轮廓,然后才能回归人类的本源,在不确定性里理解“我”究竟是谁。
重建互为关联的小说诗学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进入《云落》的诗学世界了。回到开篇提出张楚小说诗学的历史性修辞问题,所谓“历史性”,“并不表述某种关于事件过程联系,说它是真实的,而是表述处于历史中的人的存在方式,人的自身存在基本上只能通过历史性概念方可理解。瞬间概念也属于这种联系。它指的根本不是表明历史,决定历史的时间点,而是人类此在的历史性得到经验的瞬间”。
而在内在经验与外部世界抗衡之时,在抒情主体与批判主体的较量之中,小说也会陷入理论、生活、语言、经验的区隔,每当此时,小说的多声部不免稍显嘈杂。不过说到底,袒露形式的挣扎和犹疑才是最真诚的书写,也是每一个对小说诗学有自觉追求的小说家与自己所处时代短兵相接时,所必然面对的煎熬时刻。越是敏感于当下的变化,小说家内在经验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便越猛烈,对于身处变局时代的小说家们而言,这同样是伤痕累累的赤裸真实,一如不断浮现的、缄默的万樱。
万樱给罗小军最近一封信的落款是2018年5月18日,距离她给罗小军写第一封信过去了20多年,万樱的等待或许不如“等待戈多”锋利,能用荒诞刺穿谎言,或许不如“雅克和他的主人”智慧,在寓言里揭示进步的本质,甚至不像“杨过和小龙女”彼此笃定,足以携手完成私人与家国情感的同构叙事。但是万樱的故事却是当代人赤裸柔软的灵魂,存在于后祛魅时代的当代人注定是碎裂的个体,日常生活里的无数个黎明浮动着的无常的光斑,万樱是我们必须紧紧拥抱的残缺,是我们这个时代深刻的真诚和羞耻。
就在万樱写信的半个多月后,2018年6月8日小说家在一本小说集的后记里又谈起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结尾处的那句“他们在苦熬”。继而他写道:“然而,我更喜欢物理学家劳伦斯·克劳斯的那句话:‘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来自一颗爆炸了的恒星。形成你左手的原子可能和形成你右手的来自不同的恒星。这是我所知的关于物理的最诗意的事情:你们都是星尘。’没错,我们就是星尘,我们,也是时光本身。所有诞生并存在过的,都会在沉默中等待着与时光融为一体。”在小说行至结尾时,我们惊喜地发现那个永远跑不过少女万樱的少年罗小军,其实一直留着那些不知道名字的信,我们在漫长的时间里先后起跑,又在时间里不断重逢。
这便是张楚的小说诗学,他珍重存在经验的美感,同时又对客观必然性和决定论确信无疑,用喋喋不休的语言宣告静默,拒绝为沉重夸大言辞,发生过的事情都不必强制阐释,每个人的命运也不必横加指责,所有的一切都交付给绵延的时间,而我们终将会相遇在时间深处的真实里。这样的诗学图景像极了布罗茨基从弗罗斯特的篇章里挑出的诗行,“从远处立柱支起的黑暗中/传来画眉的音乐——/几乎是在召唤人们/步入黑暗和悲哀。/可是不,我是来看星星的:/我并不愿意步入,/即使有人邀请我也不去,/何况也无人请我”。华北的县城云落不是北美洲南部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事实上它也不必是任何其他地方。《云落》是一位成长于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小说家书写同代人故事时的理智与哀矜,其所代表的诗学经验,也是当下小说叙事所能抵达的修辞历史性。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 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