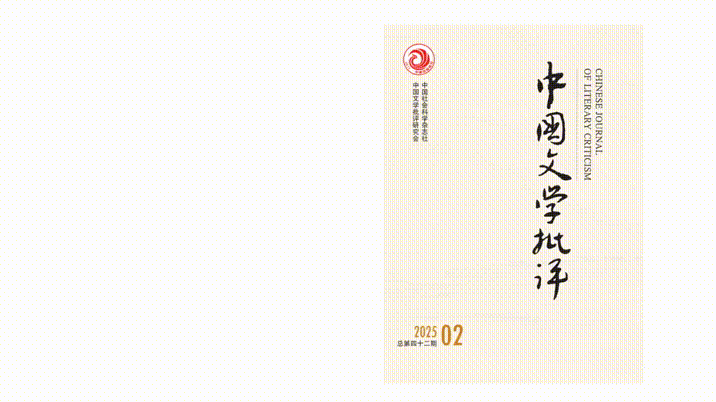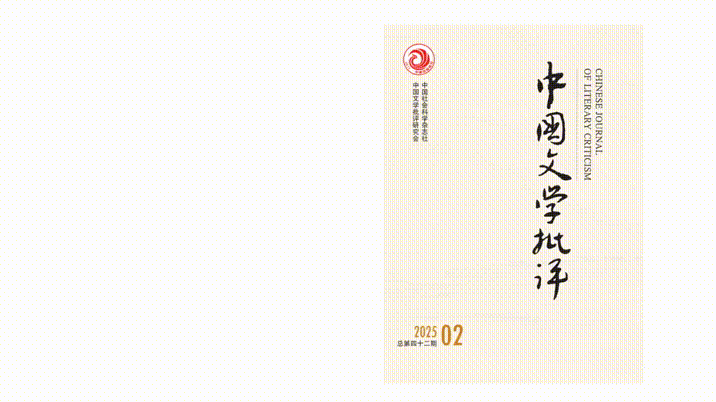
在写下这个题目时,我颇踌躇了一番,担心读者会产生误解,一来以为我套用名词,将评论写成不忍卒读的高头讲章;二来以为我在这两个词中内置了什么价值判断而多加揣测,其实不然。关于张楚,我几年前写过专论。现在整体看他20余年的创作时,我感觉到有一条叙事曲线在隐隐闪动,那是由内而外、由“物”而“景”、由“精神现象”向“知觉现象”进行的美学变迁,其背后既有写作主体的观念迁移,也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镇化进程相关。总而言之,这个题目并非故弄玄虚,而是我在钩沉张楚的叙事历程时“自动”浮现出来的。
一、辩证性的“物”之诗学
2003年,张楚在《收获》发表了短篇小说《曲别针》,一举成名。主人公李志国匍匐在雪夜里,一边熟练地把玩着曲别针,一边为爱女拉拉的病心焦如焚。治病费用是个巨额数字,为此他不得不忍受经济、情感、道德的多重困境。这篇小说最大的贡献是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精妙的“物象”——“曲别针”。作为被时代抛弃的冗余,它与遭受煎熬并最终进行自我“清理”的主人公形成了某种同构。这个物象也间接地透露出张楚的身份,是的,“曲别针”是典型的办公室用品,只是早已过时。只有在庞大的体制性无聊中始终保持敏感与锐度的人,才能将这份平淡的经验积淀下来,淬炼成文学的征象。
《曲别针》并非张楚的处女作,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2001年的《火车的掌纹》,其后还有《U型公路》《旅行》《一棵独立行走的草》和《关于雪的部分说法》。这几篇小说虽然也部分透露出他日后的特质,但《曲别针》以高度的完成性与自洽性表明这是“最张楚”的一篇,无论是写作风格抑或题材。不同于魏微、徐则臣、付秀莹、弋舟等同代作家以成长和青春叙事走上文坛,张楚的青春书写被他自己锁进了抽屉,正式发表的作品一起笔就是中年,而且是被命运一把推到深渊里的中年。《草莓冰山》(2003)中,拐男人花两万元买了一个老婆,生下智障女儿后,女人毫无悬念地离开了。《细嗓门》(2007)中,杀猪匠林红长期忍受着丈夫的暴力,在发现他性侵自己的妹妹甚至导致怀孕的妹妹大出血后,她忍无可忍手刃了丈夫。《梁夏》(2010)的男主人公梁夏被三嫂诬陷强奸,他到镇里县里到处告状反被嘲弄猜疑,像极了一路打官司的秋菊和潘金莲。在《七根孔雀羽毛》(2011)中,宗建明的妻子曹书娟为追求物质享受背叛了婚姻,成为大款郭六的情妇,离婚后又傍上了丁盛。为了赚一笔钱把房子买回来、把儿子小虎接回身边,宗建明参与了对丁盛的谋杀。这些中年人也曾纯真地爱过,也曾与命运展开过对决,但最终在生活的锤击下选择了放弃,在露出“软肋”时被命运一击而倒。
当然,这样的转述过于平淡,委实对不住张楚精湛的叙事技艺。我想说的是,张楚早期小说大抵包含着一个鲜明的“物象”,这一点已为许多研究者关注,比如“七根孔雀羽毛”,它们“色彩斑斓鬼魅娇艳”,来路不明也不值钱,却被宗建明视若珍宝。林红在杀掉丈夫后,从唐山到大同看望昔日闺密岑红,旅行包里揣着一盆微型蔷薇,“单瓣蔷薇在寒风里瑟瑟抖动,发出极细小的呜咽声”。这样的“物”还有不少,如《长发》(2004)中王小丽黑瀑布般的“长发”,《樱桃记》(2004)中的“地图”,《夏朗的望远镜》(2011)中的“天文望远镜”,《大象》(2008)中孙明净喜欢的“塑料大象,橡皮泥大象,绒布大象,积木大象,电动大象”。
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中,早期张楚或许是“70后”中最爱书写物象者。这代人擅写“物”,但用意有所不同。如果说魏微在《一个人的微湖闸》《拐弯的夏天》中主要用“物”来安妥日常生活秩序的话,张楚则不然。那些美丽可爱的“物”以与主人公的腌臜现实形成鲜明对比的姿态将自己编码为美学征象,一方面对主人公的潜意识流进行投射与缔结,另一方面又因超克了主人公的生活而自行升腾出忧郁的诗意。我以为,这些物象及其主人与他者、与世界之间的紧张感是张楚小说特别抓人的地方。你也许会忘记李志国是一个诗人、一个锹厂老板,但一定会记得他是一个爱意深重到无力到绝望的父亲。张楚并不直接展示这份“重”,而是以“轻”写“重”,以“光”写“暗”,以“喜”写“悲”,辩证性地实践着“物”的诗学。所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说的就是这个。
在这种叙事姿态之下,那些凄楚悲苦的故事往往带着几分喜兴、几分庄重的滑稽。《蜂房》(2004)中,老四千里迢迢来看“我”,一路被蜜蜂惊扰。两个大学时的老铁多年后的见面看似豪情,各自的生活早已破碎不堪。在《骆驼到底有几个驼峰》(2011)中,周丽朵向往能看到骆驼。她开心地跟随五爷周德东去县城看骆驼表演,却不知道五爷要把她卖给马戏团。比这更悲惨的是,五爷因卖血感染而死,她被马戏团老板砍掉手指打算训练成神偷,直到生命结束时她都在愧疚自己把五爷弄丢了。至于“骆驼”嘛,从头到尾就没有出现过。周丽朵是如此饶舌,如此颟顸,又如此自信,她对命运一无所感的喜剧性言行与其悲剧结局恰成鲜明对比,令人笑中含泪,泪中带悲。
张楚笔下的人物总是在泥淖中趔趄蹒跚,深陷困境。对“70后”这代作家而言,困境很少是像莫言一代那样来自饥饿,而源自“对精神生活更深一层的关注”。同时,他受到卡夫卡和奥康纳、安妮·普鲁等人的影响,前者是现代生活的预言大师或者说寓言大师,后者关注的是普通人的生活。他钟爱的《奥丽芙·基特里奇》同样是凡人“画像”,作为“小镇庸俗生活的见证者、参与者和观察者”,奥丽芙·基特里奇带着他领略“真实动人的人性”。正是基于这样的叙事观,张楚忧伤而确凿地看到了现代人的困境,将他们的受辱与反抗、情感与欲望、希望与恐惧凝缩为有形之物,并在“物”上直接投射了主人公的精神状态,如《蜂房》《冰碎片》《安葬蔷薇》。它们集“想象/形而上”与“现实/形而下”于一体,成为主人公联结“自我意识”与“外在现实”的通道。从这个层面来说,与其说张楚在“驭物”,毋宁说是在探询主人公的意识如何“由现象达到与本质的同一的过程”。他勘察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困境,让他们的潜意识逐一浮出水面,向着其所喻示的物体逐渐聚拢并缓慢而坚定地完成了自我塑形。
在张楚近年的创作中,“物”的身影开始稀疏。事实上,在《夏朗的望远镜》中,当夏朗再也记不起那架昂贵的天文望远镜放在何处而一任自己麻木地被俗务淹没时,“物”作为“精神现象学”的象征力量已然松懈。在《老娘子》(2012)中,绣花针并不是老娘子的“意识”投射,而是她面向时代暴虐的一种微弱到可以忽略的对抗。在《梵高的火柴》(2012)中,“火柴”作为物质形态并不存在,存在的是印有梵高自画像的空火柴盒,它与装着海鹏骨灰的锦盒一样,从终极意义上宣告着“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的世相本质。当“缺席”取代了“在场”,当“幻相”代替了“实存”,意味着张楚面对世界的思考与方式也在发生变化。
二、“景”的建构路径与美学形态
“风景”是当下文化和文学的研究热点,作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维度,它联结着诸多层面,比如空间、地方、性别、身份认同。当然,如何发现风景,如何绘制风景,取决于叙述主体的“凝视之眼”。“风景”不但涉及“人们如何观照自然、山水甚至人造景观的问题,以及这些所观照的风景如何反作用于人类自身的情感、审美、心灵甚至主体结构”,最终还涉及“人类如何认知和感受自己的生活世界问题”。总而言之,“景”作为叙事观与美学观的表征,所显露的主体无意识可能是最丰富且最真切的。
从创作伊始,张楚就十分重视景色、景物的描写。他说这些描写看似“闲笔”,但“正是这样的闲笔,让小说有点游离和走神,反倒可能诞生出意外的诗性”。在早期作品中,主人公相对固定地生活在某地,通常是“桃源”或“云落”,偶尔是“蓝城”。无论主人公是在乡村还是小城镇,文本所展现的风景都来自大自然。且举两例:
乡间路两旁全是粗长的白杨,愣眼瞅去,树冠似乎就要冲破云朵扎进月亮里。
树是老树了,龟裂的枝皮在雨天格外油亮,素白花朵亦没了晴日里的皱巴,水淋淋地丰腴着。有只细腰大马蜂在枝丫间嗡嘤着乱飞,金翅将细碎的雨水打得四处迸溅。
不难发现,在早期张楚笔下,“樱桃”“蒲公英”“柳树”“杨树”“细腰马蜂”和各色花朵经常出现。它们不需要任何中介物就能呈现出“直接而有形”的形态,这是生活在乡村的人才有的对于“自然”的感受。与莫言、贾平凹等前辈作家不同,这些植物和小昆虫不是劳作的对象或障碍,而是被观赏的客体。在由“视觉”主导的风景中,叙述者以线性透视法对景物的枝蔓进行删削处理,自然景物在“观看”中构成了错落有致、动静皆宜的图景:在《关于雪的部分说法》(2002)中,“我”在小区花园里看到的景物与乡村无异,“我就是小心地逮一只细腰金色蜜蜂时发现了那只刺猬”;在《刹那记》(2008)中,樱桃透过车窗“看到了”嫩绿的柳枝和怒放的蒲公英;在《良宵》(2012)中,随着季节的变换,风景次第展开。从“四月初,清冷了一冬的村子,难免透些活泼”,到“现下清明才过,麦子返青不久,作物都还归仓,除了野花草,只有柳树顶了绿苞芽,飞着些酱色的七星瓢虫”。在主人公的视野中,风景呈现出“如画”的形式与美感。
如果将张楚早期的小说放在一起阅读,会发现在“风景层”与“叙事层”之间总有裂隙。众所周知,农民是“看不见”风景的,绝望的人所见之景也不可能鲜亮如斯。究其实,是“隐含的作者(作者的‘第二自我’)”代替了叙述者/被叙述者的视角。这种写法并不出奇,有研究者称之为“替代性的叙事人角色”,即人物的判断和抒发、议论带有作者的风格,“叙事人是作者和人物的统一体”,这在王安忆、张炜、毕飞宇等人的小说中多有所见。这种“统一”性导致叙事人的角色很难从小说中剥离出来,故事不容易被转述。换言之,这样的写作其重心不在“故事”而在“意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张楚早期创作的风景美学保持着高度的同一性——干净明亮。即便是在最悲苦的故事里,依然有白棉花般的云朵、沾着雨水的花瓣以及超现实的晶莹的“星辰的碎片”。如何解释这种裂隙,不妨引用张楚自己的话:“我希望自己的眼神是清澈的,自己的思想也是清澈的。看到了暖,写了暖;看到了悲凉,也写了暖,只不过这暖,是悲薄后的暖。”
在近年的小说中,张楚将重心从自然“风景”转移到了城镇“景观”,这一方面与其叙事发展相关,另一方面则缘于中国城镇化的现实。以张楚生活的倴城为例,他亲眼见到它和许多县城一样,“越来越光怪陆离,越来越饕餮好食,空气中的气味也发生了变化”。面对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作家的美学偏向会在叙事场域中体现无遗。细心的读者发现,张楚在摆脱“物”的叙事成规之后,题材与人物呈现出了由内而外、由男性而女性的倾向。他依然写人物的困境,但不再着墨于其阴郁的内心,而是大幅度地向着外部世界展开。他依然写“饮食男女”,但重心已然向女性尤其是在城—县—镇—乡之间流动的女性偏移,如《略知她一二》《野薄荷》《金鸡》《野象小姐》等中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云落》。这些文本的叙述者即便是男性,主人公也都为女性。从青春到中年,她们在不同的城市与地方求生存与发展,经历着情感和欲望的烈性冲刷,每段关系所勾连的场景都有着中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印痕。《简买丽决定要疯掉》(2014)的故事在云落与北京之间展开,《和解云锦一起的若干瞬间》(2020)的女主人公在顾家庄与县城之间辗转,《与永莉有关的七个名词》(2024)在空间的挪腾交织中将郭永莉的故事铺展开来,未婚早育、远走他乡并冒名顶替别人的郭永莉浓缩着县城女孩/中国女性在流动社会中所遭遇的悲剧。在张楚看来,相对于男性,女性由于“稳定性的丧失,或许更精确地来说是固着性(immobility)”而更普遍、更深重地遭受着情感与物质的褫夺。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年妇女恋爱史》(2018)。小说选取1992、1997、2003、2008、2013五个年份讲述茉莉的情感婚恋,每个年份的叙述后都附有“XX年大事记”,构成了微观与宏观、个体与时代甚至宇宙对应的“微型编年史”。这位来自清河镇的“包法利夫人”,在浪漫想象和身体欲望的刺激下不断追求新的情感,从“官二代”、县轧钢厂工人到司机、公务员,最终人财两空。
除了将重心移向城镇“景观”之外,“景”的建构方式与美学形态也有所不同。在早期小说中,张楚主要通过“视觉”来描摹风景,在近期小说尤其是《云落》中,风景的甄选与剪裁呈现出迥然于前的气息。这部长篇以《樱桃记》《刹那记》为原型,以“云落”为地理坐标,讲述了以万樱为主人公,以蒋明芳、来素芸、罗小军、万永胜、常献凯、常云泽、徐天青等为主要人物的“情感史”与“经济史”。全球次贷危机、房地产业膨胀、工业污染、高额借贷、非法集资等景象穿插其中,图绘出了极具当代性的画面。关于小说的文体、人物、“县城叙事”和“悬疑叙事”已有人谈及,本文不再赘述。我关注的是小说的“景观”书写方式。在《云落》中,张楚让风景突破了“视觉”的单一化窠臼,将“眼”的功能扩展为“眼耳鼻舌身”,通过视觉、嗅觉、味觉、听觉、触觉的多维度、多时空交错,建构起了一个斑斓丰饶、汁液充盈的“感官世界”:
四月黎明,布了层薄雾,雾也挡不住满鼻满口的香,除了花香,还有泥香和土香。耳朵里呢,除了来素芸的尖声尖气,还有洒水车的洒水声、疯子唱京剧的声、露水滚落花瓣的声、老妇人们跳广场舞的声,细碎的风声与鸟鸣声。(第165页)
类似这样调动视觉和听觉对风景进行“深描”的段落大面积存在,至于味觉和嗅觉,则因作为“食色,性也”的基本感官而无处不在。一方面,小说以常献凯的驴肉馆和蒸饺馆为主要空间,意味着人与人的交往多通过食物完成;另一方面,风俗和节气等地方性知识也多以食物形式出现。在这方面,张楚不吝笔墨,除常见的食物食材之外,不太常见的玉蝉、金枪鱼和具有地方特色的酸酱、秃萝卜顶蒸疙瘩也被纳入其中,堪称“云落美食地图”。不仅如此,小说还“发明”了通过嗅觉来塑造人物形象的独特方式:万樱散发着“旷野的清朗,那种隐隐传来的掺杂着深夜里的玉黍、稻谷和甘草的气味”(第41页),常云泽身上有“动物才有的臊腥气”(第162页),罗小军闻起来“有点像寒冬时红糖泡姜片的味道”,华万春有着“家畜的微腥,生猛浓烈中掺杂着汗液和油脂的气味”(第60页)……当种种“感觉”被细化、被放大之后,众生万象以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构成了生命的共同体。
在我看来,小说最具美学冲击力的就是上述种种“感觉阈限”的全方位展开,所谓“以通感体验世界,凭嗅觉辨识他人”、“一部很‘细’的书”皆是此意。各种感官叙事不但建构起了活色生香的“云落图”,甚至作为结构支撑起了不同空间中的人物关系,大量的白描、短语、词汇、对话的排比堆叠又不断强化着作为“感受性衡量指标”的“阈限”力度。那么,张楚为何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如此重视“感官”呢?这与万樱的人设相关。她最初出现在《樱桃记》《刹那记》中时,是一个手有残疾的憨傻女孩,成年后本性未改,还添上了宽胖贪吃、欲望强悍的特征。她毫无心机,从不算计,有着地母般的忍耐力、包容力与生命力。犹如“庞大固埃”,她认识世界的方式是感官性或者说“知觉现象学”的,即“一切知识都通过知觉处在开放的界域中”。当人拥有“一个当前的和现实的知觉场”时,也就有了“一个与世界或永远扎根在世界的接触面”:“因为我有各种感觉功能,有一个视觉、听觉、触觉场,所以我已经与也被当作心理物理主体的其他人建立了联系。我的目光一旦落到正在活动的一个有生命的身体上,在该身体周围的物体就立即获得了一层新的意义”。在这里,“感觉”作为支撑“意向弧”的材料所传递出来的不仅是“表象”,还有“意志”。
对世界的感受不但有“眼耳鼻舌身”各司其职,它们之间还可相互转换联通,这就是作家的“通感”能力,朱自清和莫言在这方面都有杰出的才华。早期张楚偶尔也会用到“通感”。在《雨天书》(2009)中,张宝林让弟弟“听”米的香气。“‘听’就是闻的意思,在桃源镇,人们总是把‘闻一闻’换作‘听一听’来用,也许在他们看来,耳朵是比鼻子更灵敏的嗅觉器官。”
正是由于万樱对世人世事世相不作评判,其所见、所嗅、所吃、所听、所感共同构成了一个无分别心的世界。这个世界拒绝二元对立,拒绝黑白分明,由此,张楚也将自己从前所喜爱的“干净明亮”的风景美感扩展为“和光同尘”,一种浑融的钝感,一种人到中年才能领略的天地之美。
我以为,正是张楚对女性情感与命运的聚焦决定了风景美学的不同形态。由于女性在面临迁徙和流动时比男性更容易受到环境与文化的影响,无论是在乡村或城市,工作或消费,还是在私人领域或公共空间,通过她们所传达出来的“地理学”都是具体且感性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张楚所建构的称得上是“性别地理学”(the gendered geography)。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中,女性的身份、阶层、经济、情感、欲望“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女主人公在命运的波峰浪谷间起落沉浮,千丝万缕地联结起了中国社会转型期和城镇化进程的时代景观。
三、“抵抗”与“感知”:面向世界的两种方式
我从张楚小说中提取出“物”与“景”这两个关键词,尝试勾勒出他在幽微复杂中隐约流淌的叙事变化,以揭橥其认知世界、讲述故事的美学范式的转换。当然,这难免以偏概全,好在关于张楚的研究层出不穷,所不足者,读者自有补益之道。
关于“物”如何实现艺术功能,阿瑟·丹托有过详细阐释,他指出,杜尚作为艺术史的先驱,“首次将来自生活世界的寻常事物微妙地、奇迹般地转化为艺术品”,在这个过程中,“审美距离”至关重要:“他将那些毫无启迪意义的物品置于特定的审美距离上,使它们成为审美愉悦出人意料的候选人”。在周轶君的访谈节目“第一人称复数”中,徐小虎认为杜尚的行为说明现代艺术的重点并不是展示艺术品,而是标榜精神的叛逆。我之所以引用艺术史的例子,是因为我发现在张楚的小说中,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寻常物”与杜尚的《泉》一样,是在写作主体的“艺术识别行为”(act of artistic identification)之下才具有了美学价值。
张楚早期专注于“物”的形塑,在他看来那是精神的分泌物,是人与世界关系的表征。人物往往通过“物”来表达对世界的看法,他们在意识到生活之荒寒苦涩后也知道无力改变现实,唯一能够做出的抵抗看似是朝向命运的反击,实则不过是无奈的自戕。李志国吞下曲别针自杀,林红杀掉作恶多端的丈夫,宗建明谋杀前妻的情人,夏朗只能用望远镜将自己与寡淡粗俗的现实隔离开来,他与来自水母星云的陈桂芬的亲密关系最终以“物”的“消失”和陈桂芬重返星云而告终,也意味着在张楚的小说中,“物”的精神象征维度与密度开始稀薄。
值得注意的是,张楚还通过“物/景”巧妙而精湛地实践着“重复”叙事或者说“镜像”叙事,从而让其美学功能成倍增值。这种“重复”叙事不是《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那样的事件性重述,而是体现在“一男N女”/“一女N男”的人物关系设置上,比如《曲别针》《七根孔雀羽毛》中的男主人公与妻子、情人的关系;《草莓冰山》中的“我”与拐男人都是不幸的,“我”最后也吃到了拐男人的女儿喜爱的“草莓冰山”,浇着草莓酱的冰激凌;还有《中年妇女恋爱史》中的茉莉与不同男人的情感纠葛。有时,张楚还会设置“N男”/“N女”的故事,在同步推进和“物/景”的展现中内置着相似的情感进路或命运逻辑,如《关于雪的部分说法》中,两位男性人物米佩与颜路的情感模式虽然不同,但遭遇的背叛伤痛都是致命的,米佩养的刺猬和颜路养的狼则是其黯淡命运的象喻。《雨天书》中的张宝林为了非亲生弟弟王一等那无望的“爱情”操碎了心,自己也遭遇了失财失友的困境。《细嗓门》中的林红与岑红的婚姻有着内在的同质性,《简买丽决定要疯掉》中“我”的故事与简买丽的故事在空间游移上形成了同构。这些多线模式犹如将人物与世界的关系投射到镜中,小说的维度及其悲剧意味都得到了强化,就像博尔赫斯在《镜子》中所写:“竟然会有梦魇,/竟然会有镜子,寻常的那俚鄙、/俗套的日程表中竟然包括着/映像织成的虚幻幽深的境地。”
这就是张楚小说虽然不长于讲故事但总是充满紧张感和戏剧性的原因。青年时代的作家无疑是一个“愤青”,当他在小城中游荡穿梭时,当他在纸上彻夜涂抹当代人的“画像”时,他与笔下人物一样意识到那或许是自己认知世界最好的方式。失去女儿与妹妹的经历则将他的心态从青年推向了中年,那无处呼告的痛苦化作娇嫩失血的花朵、可爱笨拙的大象玩具,堆积成了时间的墓园。
随着年龄的增长与写作带来的认同,张楚走出小城,走向了大城市。在这个过程中,他面向世界的姿态逐渐软和下来,你要说这是妥协也好、和解也罢,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中年人最诚实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倾向的表现。
从空间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在20余年的创作中,张楚起至“云落”迄至“云落”,仿佛一曲“归去来辞”。他的题材与叙事空间走在“返乡”的道路上,而他讲述世界的方式却向着更辽阔、更磅礴处前行。于是,“抵抗世界”向着“感知世界”的方向发生了转移。是的,像万樱那样将身体当成一个“知觉场”,全力感知世界而不是评判世界,因为“世界美如斯”。我想这就是张楚的美学历程:从“驭物”到“绘景”,他实践了也完成了从“精神现象学”到“知觉现象学”的范式嬗变。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