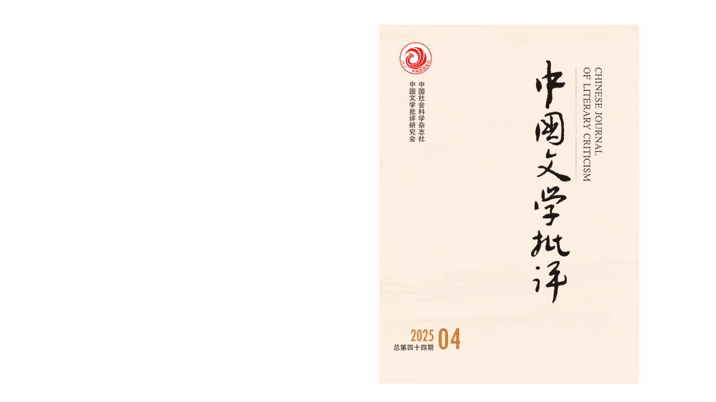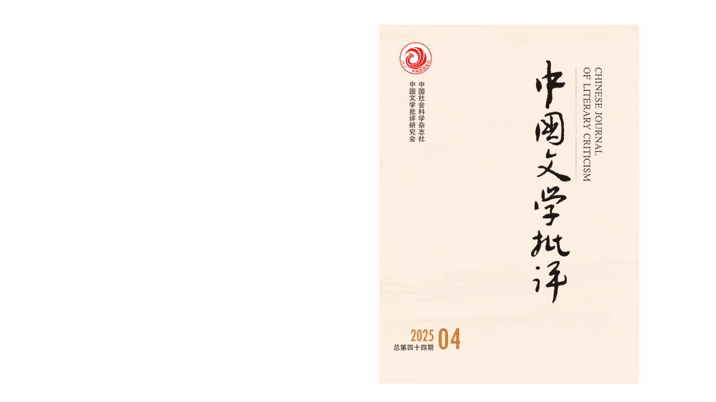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戏曲承载了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价值观念、审美娱乐的日常再生产,其以文学、音乐、舞蹈、武术、杂技、美术、服饰、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构成独特的综合性艺术,借助演员在表演空间的唱、念、做、打等活动与欣赏主体构成对话,共同开展叙事、造型、抒情和表意等活动,是民众文化消费的重要环节和快乐福祉的重要源泉,同时也有效满足了古往今来社会各阶层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在中国古代各种经典艺术门类中,戏曲最具人民性,尽管其文本创作不断经过不同身份文人参与,有些作家的创作并不直接以人民性作为创作旨归,然戏曲文体本身的特性规定了其创作与人民的逻辑关联,即便雅文化不断浸染、重塑着戏曲文体,其以俗为本体的文体创作范式始终未曾改变,其艺术规定性始终是指向舞台的,人民的内涵始终为其题中应有之义,有关的古典戏曲的评论话语也从未忽略这一方面的指向。梳理相关话语可知,只有对古典戏曲评论话语的本体、本源和本位进行科学的认知、理性的阐释和深切的领悟,才能立足中华戏曲文化性本体、依托古典戏曲历史性本源、聚焦古典戏曲艺术性本位,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更为深入地展现古典戏曲的魅力与风采。
一、双重话语形态:古典戏曲评论话语的本体性形态
中国古典戏曲的评论话语丰富多彩,序跋、笔记、杂谈、评点、诗词、文章等构成其书写方式的多样性,具有随感式、片段性和交叉模糊等特点,理论书写与感悟表达往往纠结缠绕,然涉及的戏剧问题又具有广泛、深入和理论性强的特点,在世界戏剧评论话语中可谓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就评论话语的基本存在状态而言,以双重话语形态的特征最为突出,古典戏曲中的四功五法等演艺程式、宫调曲调等音乐范畴、诗词曲格律等曲牌范式,以及情理相通、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意境意念、雅俗共赏、教化本色等理论概念皆因此而出,构成并被整合为理解、阐释和评价中华古典戏曲的专业话语系统。可以说,双重话语形态构成了古典戏曲评论的话语本体。
(一)现场还原的话语形态。戏曲评论话语的生成,总是与具体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现场关系密切,力图复原真实景观、实际语境、深层因果、传播途径、媒介情况,构成了戏曲评论话语的本体规定的基本维度。如《琵琶记》的评论话语,从明初开始直到清末,各个时代、不同群体,话语纷繁,侧重点也不一样,但共同体现了基于历史、社会和文化认知的努力。大多数评论主要从其宣扬孝道、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给予肯定,如明太祖朱元璋曾盛赞之:“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这一来自帝王的评论话语内含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将《琵琶记》作为“山珍、海错”居于五经、四书之上,更重要的是,告诫子民《琵琶记》是“忠孝”的范本,是整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必需品。此后,关乎这部戏曲作品的评论话语多以此为核心,戏曲创作也遵循这一伦理规范的指导,如后来的丘浚以戏曲“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深有所补助”为旨归,创作了同样意在“忠孝”的戏曲《五伦全备记》,明确表示:“若于伦理无关系,纵是新奇不足传。”正是对来自朱元璋的评论话语的积极贯彻。而直到清代,《琵琶记》都是戏曲作品中最被上下认可的教育读本,清初毛声山的《琵琶记》评论话语这样表述:“犹记孩提时,先大人辄举古今孝、义、贞、淑之事相告。及稍识字,即禁不许看稗官,亦并不许看传奇,而《琵琶记》独在所不禁,以其所写者,皆孝、义、贞、淑之事,不比其他传奇也。”如是,民间大众的评论话语也不免受到权力话语的影响,如对于《琵琶记》的主人公蔡伯喈,一般民众多对之行为给予批评,认为其不孝行为违背了人伦物理,其三年离家而不归、导致妻子赵五娘在家吃糠、父母双亡的相关情节,本都是可以避免的,因之而产生了诸如朱元璋登基后将蔡伯喈的原型人物王四“置之极刑”的民间说法,借以表达对这位富贵易妻者的愤怒和谴责。这是统治阶层以《琵琶记》作为“孝经”教化民众的必然结果,尽管民间大众的评论话语呈现为另外一种状态,即指向贴近生活、通俗易懂和娱乐享受。
古典戏曲评论话语在不同的官僚集团、文人群体和坊间民众中生产、传播,就有了不同的话语权力,这就导致不同类型的古典戏曲评论话语在进行理解、解读和书写时存在显著差异。官方戏曲评论话语往往强调戏曲的社会礼教作用,积极倡导符合礼教规范的主题、人物和情节,如对《琵琶记》忠孝节烈观念的评论话语与官家政治权力的表达密切相关;晚明戏曲评论话语蕴含的情感表达中往往具有个性解放的旨趣,如对《牡丹亭》中杜丽娘追求超越生死的爱情给予更多的赞赏,主要彰显的是当时文人和民众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可以看出,受制于评论话语的背景、领域、环境、视角和立场,加之特定文化权力的加持,古典戏曲评论话语必然存在差异。官方评论话语注重戏曲的审美性、政治性和教化性,这是由士大夫的精英身份、社会权力和政治责任决定的。文人评论话语则更强调戏曲的诗词格律、情节结构,以及修辞文藻的审美性、艺术性。古典戏曲评论话语的差异,反映了戏曲评论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同时,古典戏曲评论话语也具有主动辨识、协调、统筹各类话语权力的张力,努力防止这种差异带来的对抗冲突,着力将评论话语当中的差异构建成丰富多元的公共性对话,并且在对话中使各类看似相互冲突的话语构建成边界清晰、互助互补的多元古典戏曲评论话语形态。如对蔡伯喈妻子赵五娘的悲苦生活、节孝之情,人们给予充分肯定,甚至将她与蔡伯喈作为对立的形象,清初潘耒记载乡间演剧时一般观众的反应:“乡人演剧,作蔡中郎故事,观者群叹赵娘之贤,讥伯喈之不孝。”赵五娘形象所体现的官方与民间话语的上下一致,说明在建构符合某种社会结构的人际秩序方面,整个社会存在着共同的伦理诉求,而戏曲评论话语的协调、统筹话语权力的功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看到,古典戏曲评论话语的现场还原体现了知识理性与社会实践的相互作用,坚持以真实性、真诚性、整体性为基本原则,倡导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态度,尽力避免被特定权力和利益控制。如是,古典戏曲评论话语为戏曲创作者提供了指导和方向,其对戏曲思想性、社会性、艺术性等方面的要求影响着戏曲创作的理念和实践。当戏曲评论话语强调戏曲应具有深刻的社会寓意和道德教化功能时,作家就会在剧本创作中通过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等传达相应的社会价值、道德伦理;当戏曲评论话语突出古典戏曲的艺术性时,诸如李渔的“立主脑”“减头绪”等艺术创作原则就变得更为重要,促使作家构建情节更加紧凑、关目更加醒目的戏曲作品。戏曲评论话语还会通过对戏曲作品的解读和评价潜移默化地影响戏曲创作乃至社会文化。如清代乾嘉时期,戏曲评论话语注重忠孝节义的价值观,特别关注通过戏曲作品的教化功能实行对普通民众的改造,于是有关“愚夫愚妇”的批评话语频繁出现,孙为《〈两代奇〉序》:“予亦藉此笔墨。以醒世之愚夫妇。”左潢《〈兰桂仙传奇〉自序》:“而千古忠臣孝子,能使愚夫愚妇津津乐道于不朽者,半藉传奇之力。”如是,批评话语召唤着世道人心,通过戏曲创作构建整个社会对于“忠孝节义”精神的集体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社会大众的思想与行为。当然,戏曲评论话语当中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批判或反思,也能引发社会和民众对此的关注和思考,助力社会文化观念的更新。
总之,古典戏曲评论话语尽管在表示方式上比较随意,似乎缺乏系统性,然其力图复原真实景观、有助于透视特定历史时刻中华古典戏曲的状况、揭示不同社会语境中的古典戏曲特定问题与命题,构成了戏曲评论话语的本体规定维度。这对于全面地理解古典戏曲评论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与价值,准确把握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群体对古典戏曲的理解与接受程度,厘清特定现场的古典戏曲产生的特定问题、命题、话语、解读、释义等,都具有特殊意义。关键是,这体现出对各个社会群体的文化认同、教育水平及价值观立场的充分重视,进而形成对某一具体话题表述的系统性呈现。
(二)多重评论的话语形态。所谓多重话语形态,主要指在戏曲评论活动中同时存在不同来源、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的多种话语形态,彼此以各自独特的话语方式对古典戏曲相关问题进行解读和评价,相互交织,彼此影响,从不同维度共同书写、建构中国古典戏曲评论的体系性。
首先,古典戏曲话语的主旨往往是多元化的。在古典戏曲评论话语形态中,文学评论话语从文学立场出发阐释古典戏曲,多以文学观念为旨归分析、评价古典戏曲;道德评论话语则以道德标准为主题评判古典戏曲,强调古典戏曲文本与演出的教化功能;历史评论话语最关注古典戏曲历史的真实性原则,如以考据、探赜的方式评论《桃花扇》,以儿女情长言兴亡大事的评论话语比比皆是;演艺评论话语以演员的表演为着力点,评论角色演技、舞台动作等。
其次,古典戏曲评论话语的来源亦具有多元性。古典戏曲评论话语是丰富多彩的,来自不同的文化领域、知识传统和社会生活。文学评论话语源于传统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道德评论话语源于传统的伦理文化,历史评论话语基于固有的历史观和史学方法,演艺评论话语则源于戏曲表演的实践经验与审美喜好。这种话语来源的多元性使得多重话语能够通过不同层面、角度和方式进入古典戏曲,对古典戏曲进行全面且深入的理解和评论。
最后,古典戏曲的不同评论话语形态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如在对戏曲情节、戏曲人物评论时,文学评论话语形态往往与道德话语形态中的评判相互交织关联,形成对人物道德品质的判断;道德话语在评论一个戏曲人物时,也会借助文学话语强化其形象塑造、剧情营造的力度。历史评论话语形态可为文学评论和道德评论提供时代背景和逻辑语境,演艺评论话语形态则通过古典戏曲的演艺技巧、神态和形体等的解读,以舞台载体呈现方式将文学、道德、历史诸类评论话语融合在一起,使古典戏曲评论更具感性的审美魅力。由此,古典戏曲评论的多重论话语形态围绕同一戏曲作品共同发挥着表义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语义集合,对同一戏曲作品进行多角度、系统化的阐释和评价,共同构建对古典戏曲全面而立体的评论框架。
应该强调的是,古典戏曲评论的多重话语形态并非一成不变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文化的演进乃至具体言说语境的不同而在不断变化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存在差异,导致中华古典戏曲评论各种话语的语义重点各有不同。在戏曲艺术发展的早期,侧重于表演,聚焦于角色塑造和舞台演技的演艺评论构成了主流评论话语;戏曲艺术渐次进入成熟态之后,道德评论话语开始占据统治地位,发挥维护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的作用,教化功能主导着各类戏曲评论话语形态。
还需要指出的是,古典戏曲评论的多重话语维度有其内在逻辑,无论是道德、历史的评论话语,还是文学、演艺的评论话语,皆围绕古典戏曲的戏曲性来实现语义功能。所谓戏曲性,属于戏曲艺术特有的综合性,特指戏曲艺术将文学、音乐、舞蹈、表演、美术等多种艺术元素融合在一起,通过程式化的表演和虚拟性的舞台呈现讲述故事、塑造形象、表达情感、营造舞台氛围的根本特征,这是戏曲艺术区别于其他表演艺术的关键所在。中国古典戏曲评论的多重话语旨在从不同侧面揭示具体古典戏曲作品的戏曲性,文学评论话语通过剖析剧本的情节、人物和语言,评判作品的文学水平,道德评论话语关注作品所传达的社会道德伦理价值,历史评论话语探究作品的历史厚度,表演评论话语则聚焦作品的舞台魅力,各种话语形态在认知逻辑上包括戏曲创作、表演、传播、接受等环节,其从文本分析出发,逐步走向舞台表现的阐释,再深化至社会文化判断,体现了从微观到宏观、从艺术本体到社会影响的全面审视,为揭示中国古典戏曲的文化价值构建了一种独特的逻辑性存在。
二、顺时话语谱系:古典戏曲评论话语的本源性演进
谱系原是生物学概念,用于刻画、记录生物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和演化脉络,通过描述生物类群之间的各种亲缘、演化的关系展示不同生物物种或种群之间的遗传结构和进化历程,在相似性和差异性中呈现各类生物的起源、发展以及相互关联。文化发展是一个有机过程,有亲缘关系、演化脉络等谱系特征,古典戏曲评论话语亦是如此。其生成于古典戏曲创作与演出的历史进程中,体现着古典戏曲艺术评论的语义构建与表达遗传,具有复杂而多元的亲缘关系、脉络体系,并在各个历史时期、各类社会阶层和不同文化背景之中传承演变、变异创新。例如关于乐舞,早在远古文明的祭祀、礼仪等活动中已经存在。《吕氏春秋·古乐》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葛天氏之乐具有鲜明的演艺性,有关的叙事性描述、选择性表达构成了古典戏曲评论最早的重要话语;其中反映民众生活、尊崇天地自然、表达政治伦理的功能,成为中国古典戏曲评论的种子基因,流衍于各个时代的评论话语中。
秦汉时期具有讽谏功能的优人表演,是古典戏曲的雏形。根据《史记·滑稽列传》的记载,优孟通过模仿孙叔敖言行举止来讽谏楚王,这表明当时古典戏曲评论已有表演传达思想、艺术干预社会的话语意识和观念,在前戏曲形态时期,戏曲已经具有了社会叙事功能和文化批判意义。两汉盛行百戏,出土的两汉石像砖画像上有许多关于百戏表演倒立、走索、弄丸、舞蹈等场景和技艺,大量的表演场景和舞台表演图像的出现皆意味着汉代的古典戏曲评论已有唱、念、做、打等综合表演技艺范式的语义,只不过其是通过图像而非文字表达出来的。凡此,都指向中国古典戏曲是一种戏剧与歌舞二元一体的综合艺术,无曲不成戏,戏以曲传,以歌舞演述故事,乃是戏曲的基本艺术形态,而基于此的关于乐与曲、乐与舞的评论话语也成为最重要的戏曲理论话语。“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声乐器乐皆以情感表达为本,戏曲唱词唱腔都为表达情感服务,乐与曲、戏与剧都可以理育心、以心化情,这为古典戏曲评论确定了话语表达的基本社会文化规则。
进入宋代,古典戏曲评论开始进入加速发展时期,相关话语屡见于宋代笔记、杂著和诗词之中,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和周密《武林旧事》均是颇为重要的话语载体。如苏轼以诗为词之评,评论戏曲的方式亦大体如此,其“搬演古今事,出入鬼门道”就是名扬戏坛的行家之语,标志着古典戏曲评论话语文人化的开启。当其时,文人也并未轻视古典戏曲的社会功能,普遍认为戏曲可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文人的艺术素养与审美旨趣为古典戏曲评论注入独特的内容、多姿多彩的形态,创造了更多可以追踪溯源的艺术观念,提升了戏曲评论话语的艺术品质和专业水平,也给定了更多古典戏曲艺术本位解析的路径。如《都城纪胜》从杂剧体制出发,将宋杂剧分为“艳段”与“正杂剧”,揭示了杂剧末泥、引戏、副净、副末、装孤等角色的分工,为后世在戏曲起源、发展、体制、表演等方面开展评论奠定了基础。
至元代,古典戏曲评论话语渐趋成熟,专业化、多样化程度不断提升。钟嗣成《录鬼簿》、夏庭芝《青楼集》等专业性戏曲评论专著的面世是戏曲评论话语走向专门化和系统化的标志。陶宗仪等文人在笔记、杂谈中也涉及不少关于戏曲的评论,如《南村辍耕录》等。元代戏曲评论话语注重分析剧作家生平与其创作风格的内在关联,如《录鬼簿》评论关汉卿云:“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尤其聚焦于戏曲演艺内容,如《青楼集》详细记载、评述了众多女演员的表演技艺,珠帘秀“杂剧为当今独步;驾头、花旦、软末泥等,悉造其妙”,天然秀“才艺尤度越流辈,闺怨杂剧,为当时第一手”,并对演员在不同角色行当之中的表演能力给予充分关注与肯定。从理论角度看,元代戏曲评论话语执着于戏曲音乐与诗词的双重本位,开启了音律和曲词的系统性理论。周德清《中原音韵》便是一部关于北曲音韵理论的重要著作,其对戏曲创作中的音韵规范、平仄格律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影响了后来的相关理论,至清代依然被视为相关研究的典范之作。元代戏曲评论话语也关心戏曲的结构方式和情节安排,对戏曲作品中曲折离奇的关目设计给予发掘,肯定了戏曲作品起承转合结构方式的独特之处,开启了古典戏曲评论的叙事学论题。
有明一代,古典戏曲评论话语进入成熟时期,初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状态。戏曲评论的话语方式不拘一格,序跋、评点、诗词、专论、杂记、选本等多种形式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如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题辞》表达了他对戏曲创作的独特见解,冯梦龙、臧懋循等文人的戏曲作品评点以独特视角剖析剧情、人物及写作技巧,对读者理解作品具有重要的启发;王骥德《曲律》、吕天成《曲品》等专著以理论话语论述古典戏曲;张岱《陶庵梦忆》等笔记记录了当时戏曲演出情况及个人观感,以轻松随意的话语方式评论古典戏曲。古典戏曲理论专著的纷纷面世,对中国特色的古典戏曲评论话语体系的构建最具帮助。朱权《太和正音谱》问世最早,在戏曲的源流、体制沿革、角色创新等方面开创了古典戏曲艺术史评论的话语先河;徐渭《南词叙录》是第一部研究南戏的专著,对南戏的源流、发展和艺术特点等进行了系统论述;沈璟《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专门就南曲的曲律进行系统考订与规范,明确了各种曲牌的格律、音韵等要求,为南曲提供了基于曲律体系的话语规则和创作指导。王骥德《曲律》、吕天成《曲品》从作家创作、作品、演艺和欣赏等维度建立系统的理论话语。经由李卓吾及众多文人的反复评论,《西厢记》《琵琶记》作为古典戏曲经典之作的地位得以确立,《牡丹亭》则为明末清初戏曲创作高峰的到来提供了理论观念和创作经验的准备。总体来看,明代古典戏曲评论话语守前代之正,又借助繁荣的戏曲创作给予了多维度的充分展开,尤其是作为古典戏曲评论成熟标志之一的戏曲评论流派的形成,极大助推了戏曲评论话语的发展。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是比较典型的戏曲评论流派,强调戏曲创作严守格律、注重音韵、曲词本色,吕天成、叶宪祖等众多文人皆为个中同道,对以昆山腔为代表的南曲创作的规范、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曲家注重戏曲作品的思想内涵、情感表达,并不拘泥于格律的规限,强调戏曲语言应兼具文采与通俗性,既展现文人才情,又便于让民众理解接受,对古典戏曲评论话语的影响甚为深远,其在当时虽不能称为“流派”,却以“流派”的样态绵延不绝,为明代古典戏曲评论注入了新奇的理论视野、独特的审美追求,同时也促进了古典戏曲的哲理性、文学性的统一。需要指出的是,明代思想文化活跃,以心学为代表的哲学思潮等对戏曲评论话语产生了深刻影响。心学强调个体情感与意志的思想造就了古典戏曲评论中重情轻理的话语构建方式,众多戏曲评论认为戏曲应真实地抒发人的情感,肯定情感在戏曲创作与欣赏中的重要地位。汤显祖的“至情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认为戏曲应表现出超越现实束缚的真挚情感,这对此后戏曲创作关注“情”并通过对“情”的多维度体认完成对礼教传统的回归具有重要影响。
进入清代后,古典戏曲评论话语迎来了发展的高峰,完整的古典戏曲评论话语体系在这一时期形成。揆诸这一体系的总体特点,既对古典戏曲创作、文本、表演、接受等艺术要素有深入阐述,又强调古典戏曲艺术各要素之间的协调统一,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古典戏曲艺术的综合性,戏曲评论的理论话语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高度。在对前代戏曲理论梳理、补充、创新、总结、提炼与整合的基础上,多部集大成的戏曲理论著作先后问世。李渔《闲情偶寄》分为“词曲部”和“演习部”等,系统而全面地构建了戏曲创作、戏曲表演乃至戏曲导演等的理论话语,提出“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等戏曲创作原则;在表、导演理论方面,基于选剧、变调、授曲、教白等方面的舞台实践确立了周详的理论原则,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沈宠绥《度曲须知》创新了昆曲音韵格律理论话语,对南曲和北曲演唱技巧、发音吐字等进行了细致分析,为戏曲演唱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徐大椿《乐府传声》专注于戏曲声乐理论话语体系建设,对唱腔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戏曲演唱的发展影响深远。在戏曲作品和作家的评论方面,清代文人立足于对前代经典戏曲作品的评点,金圣叹以独特的文学见解和犀利的批评话语对《西厢记》的人物塑造、情节结构进行文学性评析,使其思想内涵与艺术价值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洪昇《长生殿》、孔尚任《桃花扇》一问世即备受评论者关注,纷纷就这两部作品的曲词、结构和主题发表评论,誉之为古典戏曲的“双璧”。清代中期以后,戏曲演艺高度发达,戏曲评论对优秀演员的表演技艺进行了细致评价。《扬州画舫录》记载了扬州地区戏曲演员的表演情况,对魏长生等戏曲演员的唱腔、身段、表情等方面的特点给予详细描述与评价。而基于不同地域和演艺风格的戏曲流派的逐渐形成,也丰富了戏曲评论话语有关这些流派特点的比较分析,如京剧与昆曲在表演等方面的区别,各自表演风格的形成等成为关注的重点,有关京剧大气磅礴、昆曲典雅细腻不同风格特点的探讨推动了不同戏曲流派之间的交流、发展。除此之外,清代古典戏曲与社会风俗紧密相连,节日庆典、民俗活动中的戏曲活动在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民众当中的接受程度与传播状况,也在戏曲评论话语中占有很大比重,而文人参与戏曲创作过程中展示出来的文人情怀、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等,形成了他们借助戏曲评论表达思想情感、寄托人生感悟的新的思考方式,也具有特殊的话语意义。
总而言之,从先秦两汉到明清时期,古典戏曲评论在顺时态话语的演化过程中逐渐生成了谱系的统计学规则,评论话语与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直接关联,成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民俗的表现之一,而其基本语义往往与当时的历史情境、发展趋势和生活常理相互契合,显示出儒道释等传统思想、文学及艺术等元素的多元影响和多维渗透。这是古典戏曲评论话语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性体现,也是中国古典戏曲评论迥然于西方古典戏剧评论的独特之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正是理解中国古典戏曲评论话语的理念与门径。
三、共时话语结构:古典戏曲评论话语的本位性呈现
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古典戏曲评论话语已具备了共时话语结构特征。所谓共时话语结构,是指无论在哪一个特定时刻或时间截面上,话语都会呈现出的结构和关系。共时话语结构特征并不考虑话语在历史过程中的演变和发展,而是聚焦于一般性的稳定构成与组织方式,关注话语要素在非时间状态下的相互关系、组合模式及由它们共建的整体语义。就古典戏曲评论话语的共时话语结构而言,评论话语的各个部分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结构整体,每个概念、语句或文本片段的语义因之而被决定,结构整体的功能大于各部分之和。
戏曲演进的艺术实践证明,只有在古典戏曲作品的主题构成、情节架构、人物关系、演艺程式等整体结构中,评论话语的意义才能完整地显现。这是因为,评论话语之间的横向联合关系与纵向聚合关系的联动决定了话语的基本语义。如关于本色,本是来自诗歌评论话语的概念,初见于北宋陈师道之《后山诗话》:“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但明代王骥德却如此表示:“当行本色之说,非始于元,亦非始于曲,盖本宋严沧浪之说诗。”之所以如此,并非其故意扰乱“本色”一词的知识系统,而是源于明代“诗必盛唐”的诗学传统,也因此,戏曲评论话语与严羽诗学之间构成了理论渊源。进入戏曲评论话语之后,本色这一评论话语不断出现,且多用于评论曲词,如徐渭《南词叙录》:“夫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吾意与其文而晦,曷若俗而鄙之易晓也?”王骥德《曲律》:“夫曲以模写物情,体贴人理,所取委曲宛转,以代说词,一涉藻缋,便蔽本来。”徐复祚《三家村老曲谈》:“传奇之体,要在使田畯红女闻之而趯然喜,悚然惧;若徒逞其博洽,使闻者不解为何语,何异对驴而弹琴乎?”以上三段评论话语皆针对戏曲的语言立论,却呈现出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指向。徐渭关注的是曲词通俗,可以感发人心,王骥德表达了对曲词“藻缋”的不满,认为“模写物情,体贴人理”是戏曲之使命,徐复祚则更多地从接受者与舞台性的角度体认曲体特质。如是,同样是关于“本色”的评论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呈现出表达的差异性,却使本色的语义意义得以完整显现戏曲文体的独特性追求,而这正是中国古代戏曲评论话语的特殊表达方式。
共时话语结构是古典戏曲评论话语稳定而普遍的深层结构特征,决定着评论话语的构建样态和理解方式,是古典戏曲评论话语的本位。所谓本位,就是事物占据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位置或依据的基础。古典戏曲评论话语的这种结构本位,使其在不同的话语时段中具有相对稳定的共时态结构内在规定性,进而构成了话语评论的基本话题,其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执着于戏曲道德教化的结构中心地位,以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念构造戏曲主题,将忠臣孝子、贞节烈女置于人物形象的核心位置。元末高明《琵琶记》主张“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此后以“风化”组构剧情、塑造形象、打造主题成为戏曲创作的应有之义,即便是汤显祖《牡丹亭》传奇这样的倡导“至情”之作,也不免受到伦理教化的约束。如杜丽娘渴望“折桂之夫”,但只能通过梦境拆解现实的障碍,回到现实中的她则要求柳梦梅明媒正娶,所谓“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这种基于儒家伦理的夫妇之道,是礼教建构之必然,只不过深受阳明心学影响的汤显祖在观念上更为包容,也因此选择了在创作实践中借用“梦”“鬼”等进行更为艺术化的处理。
第二,关注戏曲的叙事模式,用情节的起承转合与人物的喜怒哀乐进行叙事,形成音乐结构与关目组合的特殊性。如关汉卿《窦娥冤》杂剧,从窦娥的平静生活“起”,以其遭受一系列莫名的冤屈为“承”,待到法场上质问天地的强烈控诉,形成感天动地的“转”,最后通过冤情得以昭雪之“合”实现叙事的完整。在这一过程中,主人公的情绪往往与情节的起承转合照应、配合,借助曲词、宾白形成了喜怒哀乐情绪的腾挪转换和细致抒发,进而最后的“合”不仅是叙事之“合”,更是情感冲突的和解以及曲词审美的和谐。其中,戏曲关目的布置方式、以曲牌叙事的音乐结构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故有通人说“必若通儒俊才,乃能造其妙也”,这确实道出了中国古典戏曲各种元素极尽配合方能达成理想的戏剧形态的模式。
第三,通过生、旦、净、末、丑的角色体制,为人物形象设立忠、奸、美、丑等角色范型,借此表达浸润着丰富伦理价值的审美理想。在古典戏曲中,“一生一旦”是基本格局,忠臣往往是“生”的形象,具有维护正义、保卫国家等角色意义,或以才子形象出之,英俊潇洒、才气过人、文韬武略兼擅;“旦”则主要指那些美丽善良、温柔贤淑者,多为佳人形象,女性角色中的小旦、老旦、贴旦等往往为次一级的女性角色,多具有间性的特征。净、丑多属于坏人角色,奸臣破坏朝纲、陷害忠良、多行不义。每一类角色范型都有属于自己的曲词、宾白、装扮,在舞台上能够被一眼辨识。以差异化的曲词、宾白、装扮构建起角色身份、性格特征和社会文化的符号标识,故角色范型是人物形象被观者认可、接受的关键要素。
第四,注重戏曲作品尤其是表演中服饰、脸谱、动作等非语言符号的创制,突出性格、彰显伦理价值。如关羽等人的红色脸谱是忠义的象征,曹操等人的白色脸谱则代表着奸诈。在表演程式方面,唱、念、做、打等程式都有特定规范,赋予表意功能。唱腔的板式也根据剧情设计与人物塑造的需要形成了特定表达结构。念白的节奏、韵律,动作的幅度、姿态等程式共同构成表演的形式,传递着戏曲结构的特定意蕴。演员的特定动作更具符号意义,甩袖动作在不同情境下可表达愤怒、悲伤、决绝等不同情感。舞台空间布置与演员调度也属于结构性内容。舞台上,一桌二椅象征着宫殿、书房等不同场景,演员的站位和移动体现着情节的演进、角色的作用。虚拟空间的舞台布置与演员调度表现出实际的生活场景和人际关系的对应性结构关系,如在表现君臣关系时,皇帝居舞台中心高位,臣子则居下位两侧,舞台空间布局是对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关系的定位。
第五,将历史文化知识、民间传说、风俗习惯作为评论的话语视点,关注古典戏曲对传统文化的承载与传播。同时,主动合理平衡古典戏曲评论话语中的文人、民众、官方趣味。文人在古典戏曲评论话语中占据主体地位,其文学素养、文化底蕴、审美能力、书写方式等构成了丰富多彩的评论话语,并承接、涵容着官方评论话语的基本观念、认知,使其获得解释、支持和推广。一般而言,官方古典戏曲评论话语多从国家治理、社会稳定、宣扬正统等立场出发,具有评论话语的社会意识形态导向作用,而来自民众的戏曲评论话语更贴近生活实际,语言通俗易懂,体现了古典戏曲评论话语的民意基础,对处于评论话语中间结构中的文人而言具有“渐近人情”的文化魅力。正是因为古典戏曲评论始终注重平衡这三类评论话语,三者才可能基本处于合理稳定的张力结构中,发挥雅俗文化合力的效应。
如果从话语结构方式上立论,古典戏曲评论话语的共时话语结构本位又可以分为层叠式和循环式两种。所谓层叠式话语结构方式,是不同时代对同一戏曲作品或戏曲现象评论话语的相互叠加,如在汤显祖创作完成《牡丹亭》后,明代评论者主要围绕其“至情”理念、文辞与音律关系等展开评论;进入清代后,人们在明代基础上或展开或拓展,就《牡丹亭》的舞台演艺等进一步探讨。不同时代的评论累积,形成了《牡丹亭》丰富而立体的评论话语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时代的评论话语元素渐次融入,有内涵的传承,也有新意的不断展示,相关语义及其内涵相互层叠,丰富了《牡丹亭》戏曲作品的意义结构。循环式话语结构方式关注的重点是古典戏曲评论在某一评论中不断生成的新的相关评论,评论话语不断循环,并在新的层面赋予新的意义。如在清代花部戏曲兴起时,有关其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特征有诸多评论,而一些文人则仍不免从雅部戏曲的视角看待这一现象,话语系统中增加了大量文学性评论元素,古代戏曲中诗乐关系、雅俗演进类话语再一次渗入其中,形成花部戏曲评论在循环往复中持续深化、多元共生的状态,进而日渐丰富和立体化。事实上,不同时代的戏曲评论话语中,相似的审美观念如雅俗、含蓄之美等总是反复出现,具体指向则有不同,而且当某一审美观念在某一个时期淡化后,可能在另一个时期的评论话语中被重新使用并受到重视,凡此,皆构成了共时循环式话语结构方式。
层叠式话语结构方式和循环式话语结构方式还使古典戏曲评论话语的共时结构本位与顺时话语谱系处于共构之中。共时话语结构提供了话语在当下的组织方式和意义生成,顺时话语谱系使当下话语的组织方式和意义生成在时间纵深中不断演化、发展。共时话语结构与顺时话语谱系相互联系,互为依托,彼此换位,共同构建起全面、立体的话语语义集群和语义理解界面。共时话语结构中的古典戏曲评论对某一具体方面的关注会被顺时话语谱系追问,如在共时话语结构中被关注的清代戏曲花部乱弹的表演风格,往往会在顺时评论谱系中被追溯到明代弋阳腔等早期民间戏曲声腔,以此探寻这一表演形态的历史渊源。顺时谱系评论话语提供的历史向度为共时结构评论话语增添了深度,而共时结构评论话语中的社会观念、文化视域、思维方式变化也会导致顺时谱系评论话语中的古典戏曲问题获得重新评价。如戏曲名著《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就是在人性解放的共时结构评论话语语境中获得了更多的肯定。而对顺时谱系中古典戏曲问题的新发现也会影响共时结构之下的戏曲评论,古典戏曲剧本的重新整理和评论的新发现也会推动共时结构话语革新其评论标准和话语视角。总之,古典戏曲评论话语本源的顺时谱系为中华古典戏曲评论话语本位的共时结构注入了厚重的历史内涵,丰富了其文化意蕴,而古典戏曲评论话语本位的共时结构为顺时评论话语谱系提供了当下的语境,建立了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使顺时谱系评论话语有了明确的现实方位。二者的共构造就了中国古典戏曲评论话语在多个维度上的相互交织,促成、构造了古典戏曲评论话语的丰富语义和思想内涵。
结语
综上所述,戏曲评论话语的双重话语形态、顺时话语谱系和共时话语结构分别造就了中国古典戏曲评论话语的本体、本源和本位,是中国文化史上独树一帜的艺术景观,在世界戏剧艺术史与戏剧理论史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古典戏曲评论话语正体现了这种“突出的包容性”并以双重话语形态的本体存在形态呈现出来,古典戏曲评论话语的顺时评论话语谱系、共时评论话语结构分别从本源、本位的维度共同保障了这一点。首先,其对文学话语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评论故事立意、结构布局是否合理、人物塑造是否丰满等内容随处可见,文学考量无处不在。其次,对传统审美观念亦持开放包容态度。情理相通、情理交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雅俗共赏、教化本色一体等美学概念是古典戏曲评价话语的审美标准和艺术性尺度。再次,对传统思想精华的吸收借鉴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儒家道德规范和人伦情怀、道家的浑然天成和大巧若拙、佛家的空灵无尘和无欲超脱等建构了戏曲实践中的各个环节,形成了贴近民众生活、融入百姓情感、反映世俗百态的雅俗共赏的艺术形态。最后,对传统艺术如绘画、音乐、杂技等兼收并蓄,汲取丰沛营养。传统绘画“气韵生动”等诸多批评话语被引入戏曲评论话语中,绘画的构图布局对应到戏曲舞台上,大量的音乐形式、杂技品类留存于戏曲评论话语中,造就了中国古典戏曲评论丰富的资源。在对中国自主的戏曲知识体系进行解析的过程中,剖析中华古典戏曲评论话语的本体、本源和本位,助力中华古典戏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是本文的根本目的。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