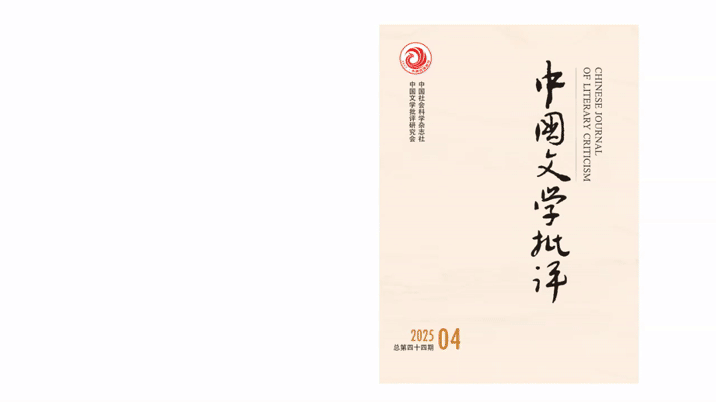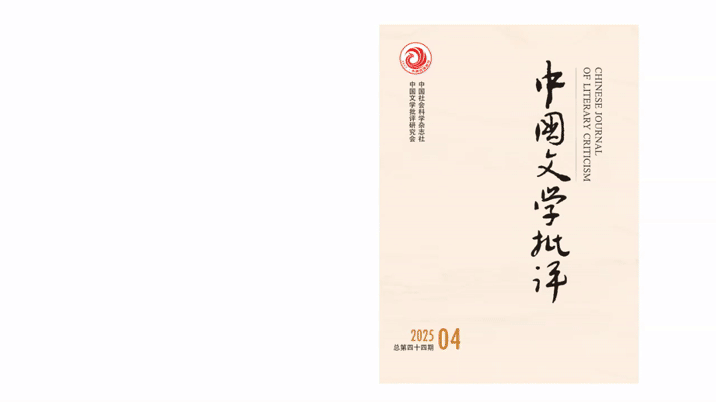
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及相关理论中,常以抒情或表现为宗。近年来,有学者言“摹仿”,颇以《易》“象”为意。其所持论,多非上古《易传》言“象”原意。故而,追究《易》“象”之论的原始面目,追溯中国文论摹仿论的早期发生与流变,确有必要。
一、“象其物宜”:摹仿及其对象
《周易》的“象”论和“象”思维,不仅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本根,也是中国文学艺术创作与理论的源泉。当代学术界对于这一传统的阐释,往往着重其民族特色,立足于“立象尽意”与“得意忘象”之间,强调其艺术形象抒情写意的特征。
近年来,有学者重新梳理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艺的摹仿传统,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引《易》象为说。如“在《周易》中,‘象’可指物象、拟象、虚象、实象,也可指摹拟行为,但首先是指未形成具体形制之物与气混合一体时不断变化的状态。”进而提出,“观物取象”所观的并不是具体的物,而是万物运动的法则,所取之象是运动中的“萌兆”或“几微”,其本身就是“道”。中国古代艺术的摹仿传统,受易学的摹仿论或摹仿思维影响,是对道本身的“准拟”,“主张图像与现象的同质性”,并“将‘象’作为行动,由此实现摹仿行为与其对象和结果的统一性”。又如,《系辞》说圣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神明’指宇宙的根本原则,即中国传统里的‘道’”。受《易传》影响,中国古代摹仿论前期是“意象式摹仿”,“人类通过摹仿宇宙中的超验形式而创造出了现实世界中的文化系统和人工制品”。
上述成果是对中国文学艺术传统研究的丰富和深化。不过,笔者以为,中国文学及艺术的摹仿实践与摹仿理论确实深受易学“象”论、“象”思维的影响,但两者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诸人所言,对于魏晋以后的易学以及文学艺术或许是成立的,但对于早期易学与文艺尤其是早期中国文学的理解,恐怕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偏移,以至于对整个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摹仿传统在认识上产生某些偏差。
首先,所谓“象”,“是指未形成具体形制之物与气混合一体时不断变化的状态”,这是汉代以后的观念,并非先秦易学的原意。
“气”是一个古老的观念,先秦言“气”,常与人之“性”“命”相关,并不及“象”,如孔子言“血气”之于“三戒”(《论语·季氏》),医和云“六气”与人体之“六疾”(《左传·昭公元年》),等等。战国以后,渐言“气”生万物,如《管子》之“精气”(《内业》),《鹖冠子》之“元气”(《泰录》),云云。至汉,方有言“气”“象”关联。如《易乾凿度》述宇宙演化,分为“太易”“太初”“太始”“太素”诸阶段,从无“气”到有“气”、有“形”、有“质”,逐一演进,是以“气”之后,方有形象区分,而万物成形。至宋,“气”“象”之关联固定下来。如张载《正蒙》:“凡象,皆气也。”“气本之虚则湛一无形,感而生则聚而有象。”可见,以“气”言“象”,是后来易学的发明,并非早期易学的观念。
实际上,在上古《易传》中,“象”常指卦象,其为人仰观俯察、比拟万物的结果。间或“象”为天象,即“在天成象”。但所谓“天象”,恐怕也并非指“太虚成象”,而是“天事恒象”,是天象对人事的感应,是上天对人间的预示、警示。《左传》中就有诸多星象与人事相互呼应的记录。与《易》同时的典籍,如《左传》之“象”,多为仿效、摹拟之意;如《诗经》之“象”,多指动物大象,间或亦有摹仿效法之义;《尚书》之“象”也大致如上。所以,《易传》之“象”,不是生成之象,而是摹仿之象。故而,《易传》又云:“象也者,像也。”即,“象”是“像”——摹仿的结果。
其次,易象的摹仿对象、摹仿行为指向的是物,而不是道本身。
作为摹仿行为,易象之“像”,不仅是对外观的摹仿(或者不完全是对外观的摹仿),而是“仿效”,是对目的与效用的摹仿,“并非仅与事物外在的状貌相像,而是与决定事物状态的阴阳的结构、关系、功能相像”。但这并不等于说,易象所“像”的不是物,而是道。后者乃王弼义理易学的新释。王弼说:“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他认为,《易》摹仿的对象是道,物与象都只是中介。后来刘勰以道为文(象)之本原,其中实有王弼的痕迹。孔颖达疏《周易》,秉持的正是王弼之学,所以他说,“象之所以立有象者,岂由象而来,由太虚自然而有象也”。上述之说,或出于此。
然而,必须注意,第一,易象是通过对物的摹仿来接近这个“道”的。《易传》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象”之所“象(像)”——摹仿的,首先是“物宜”。“万物之性各有其宜,故曰‘物宜’。”万物各有自性,它所适宜的对象也各不相同,从而,“物宜”也就等同于“物义”,即物之为物的规定性。因而,“圣人作易,神于分别物宜”,《易》只能由圣人来创作,圣人作《易》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分辨并著明物各自的特性。因此,“物宜”具有个别性和差异性,“一卦有一卦之物宜”,而易象对此具有卓异的表现能力,“各形其形,各声其声,各才其才,各力其力”。易象的高明,就在于它既能表达物理的普遍性,又能表现物体的个别性。因而,朱熹言:“易卦之形,理之似也。”又说:“象者,物之似也。”易象之摹仿所指向的,是“理”,也是“物”,二者不可剥离。这个“理”,来源于“道”,但又不完全等同于“道”。《韩非子·解老》云:“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万物各异理而道尽。”万物之成为万物,有万物自身特殊的规定性,这就是“理”。而万物各不相同,其理也就各不相同,所以“万物各异理”。而易象要摹仿的,就是这个“各异”的“理”,通过这个“理”来达到“道”。这就是“物宜”。“物宜”是蕴含在物之中的,是物自身的具体运行机制,所以,《易》尽天下之赜,凭借的是易象对诸物的笼括,“万物虽多,而八卦无不像之也。”因而,“象”是对“物”的摹仿,易象之象,是物之象,不是道之象。钱锺书说易象与诗喻的区别在于易象可以离象言道,这在王弼以后的易学中是对的,但是对早期易学来说,并非如此。
第二,在《易传》中,尚未出现本体论意义上的“道”。指向万物共通的运行机制并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道”。前者是经验性的总结,后者是超验的形上本体建构。张岱年指出,“《易传》虽以变化为一根本事实,以宇宙为一发展之大流,以一阴一阳对立迭运为道,以生为天地之大德,然未以易或道或生为宇宙最究竟之本根。”《易传》发现万物运行有其统一的规律,即“道”,但这是万物外部运动的规律,至于万物自身由来,并未归之为“道”。甚至,未必认为万物有一个统一的由来。纵观上古思想未论及万物始基,至老子始言道生万物,其后庄子继之。但是,早期《易传》主要受儒家经说影响,未必完全接受老庄观念。而且,老庄的道本体,也不是宇宙论意义的本体,而更多是功能性的本体。老子说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无为而无不为”,道只是敞开的存在之域,让万物得以成其万物,但道并不规定万物,万物乃自行成为万物。所以,郭象才称物“独化”“自生”。
因此,在早期易学中,“像”作为摹仿行为,是“象其物宜”,指向的是物自身内蕴的机制。它来自文明初萌时代的人类生产生活经验。人类初步学会使用工具、借助物来探索世界、建立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世界”,渴望获知、攫取物之用的奥秘。于是,他们“观”物、“像”物,试图用“象”来复制它们、占有它们。易象就是这种渴望及其追求的产物。《系辞》说人间帝王依照易象制器立法,这恰恰是一个历史的颠倒:人们通过对器的制作认识了物,把握了物,复制了物,建立了《易》象。
物,在远古蒙昧时代,或许带有更浓重的神秘色彩,是隶属于原始宗教活动的,是属于神的。但是,在《易传》的时代,这个“物”,已经是经验世界、日常世界之物,是人们生产劳动实践的工具和对象。从而,“物”成为古代人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重要视域。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对道的理解,往往集中体现在“物”身上。老子的“无欲”、庄子的“齐物”、孔子的“中庸”等,都以“物”为指向。而在日常生活与文学艺术中,对物的热情和兴趣更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物”叙事成为中国文艺历久不衰的“话题”。而中国文学艺术的摹仿传统,也从“物”开启。从《诗经》的“比兴”,到汉赋的“体物”、六朝诗文的“物色”,等等,“物”的书写牢牢占据着文学艺术舞台的重要位置。从“比兴”到“物色”,乃至“气韵”“兴趣”“意境”,等等,人们摹写刻画“物”的方式和途径也随着对物的认识、与物相处方式的演化而流转迁移而勃发兴盛。因而,不单中国古代文学不存在摹仿或摹仿论之说是不成立的,以为对具体事物过程或行为动作的叙事性再现才是摹仿的看法,恐怕也是值得商榷的。
二、比类:易象的摹仿方式
当摹仿的对象指向“物”的时候,摹仿的方式也就相应地调整为对“物”的安置、筹划。在早期易学与文学中,这不是对“道”的“准拟”,而是“比类”。
在《周易》古经乃至早期《易传》中,物是各自独立的,其生产的过程也是隐匿的。“物宜”是繁多的、纷杂的,难以穷尽,难以把握。于是,有了对“物宜”的共同机制的探究。
这种探究,从分类开始。《系辞》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方”,即“法术性行”“事情所向”,则“方”实即人对物的规划和安排,即万物连同人对它们的规划安排是类聚而群分的。因而“象其物宜”,也是依“类”“群”来集合与区分。而这个“类”与“群”,首先是“乾”“坤”二元。乾坤的建立,是易的根本。“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乾”象与“坤”象构建起来,《易》的大体就具备了;“乾”与“坤”若是倒了,《易》也就不复存在。而“乾”“坤”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区分。“乾,阳物也。坤,阴物也。”“乾”“坤”分属阴阳,“乾”“坤”的树立,不仅是“乾”象“坤”象本身的完就,还是以“乾”“坤”为首,构建起整个易象的系列。这就是把六十四卦象、把“物宜”尽数区分为乾坤、阴阳。孔颖达释“象其物宜”时,就把“物宜”区分为阳刚和阴柔二类,即“乾”与“坤”。由此,引而伸之,有八卦,有易。所谓“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也。
“象其物宜”的方式是“比类”。“物宜”相同相似的,以共同的“象”标识,这是“类”。而一“象”之下,同类之物事连缀而陈,这就是“比”。
“类”是《易传》的重要概念。“类”是相似,也是区分。《易·同人》一卦,《象传》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而“各如其类以比类之,则谓之类族;各如其品以辨别之,则谓之辨物”。以品类对待万物,可聚集为泱泱一族,可条析为各异的存在。这就是“类族”与“辨物”。“类族”就是相似,“辨物”就是区分。《系辞》说“以类万物之情”,这是以“类”求相似;《左传》说“神不歆非类”,这是以“类”区分异己。
“比”不止理解为“比方”“比拟”。《易》有《比》卦,《彖传》曰:“比,辅也,下顺从也。”所以,“比”有跟随、顺从的意义。“比类”即“以类相比”,即同类的亲近、聚集。《文言》释《乾》卦九五爻:“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各从其类”,就是说,相同属性的事物,自动自觉地聚集在一起,这就是“比类”。
“比类”是《易》象构结的方式。《乾》《坤》为首,举阴阳大分;八卦分列,标四时四方位次;六气重卦,演六十四象变化。诸卦列类,其下比从无数物事。《说卦》有云:“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正向人揭示,每个卦象之下,聚集连缀了许多事物。整个《易》象,依赖这样的比类,层层叠叠,构建而成,每一卦都是一类,每一类之中都聚集了众多事物,每一事物,都能代表这一类,代表其他同类。这就是所谓“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卦象之命名,或只以一物事,但由此同类相比,逶迤重沓,蔚为大观。
这样的“比类”是上古人类认识物的方式。《系辞》曰:“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孔颖达解释说:“谓触逢事类而增长之,若触刚之事类,以次增长于刚;若触柔之事类,以次增长于柔。”又曰,“天下万事,皆如此例,各以类增长,则天下所能之事,法象皆尽”。人在世间所遭遇的事物,可以划分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各自比附汇入易象的体系。通过这样比类,万物各入其类,各得其所,其内在性质功用得以明白地彰显出来,人就没有不了解、不掌控的事物了。所以,“物相杂而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类。知事物名义之杂出而比处也,非文不足以达之,非类不足以通之”。万物纷繁芜杂,必须通过比类,归纳区分,才能通达、知晓、理解它们。
从而,比类成为早期人类主要的思维原则。荀子曰,“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度也。类不悖,虽久同理”。在观人观物观事中,只要正确比类,就不惧物类的芜杂、时空的变迁。可以说,“比类”贯穿了上古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它是人间构建秩序法则的重要方式。《左传》云:“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鬼神庇佑的对象、宗族祭祀的对象,都是自己的同宗族人。“类”成为宗族姓氏的区分,祭祀礼仪构建的规则。《国语》曰,大禹治水,“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天地万物各有其类,各有其规律原则,圣明的领袖会辨别分类,依循规则,并以此教导百姓,管理万民。从而,“比类”又是治理的原则。
“比类”还是陈辞言说、传情达理的重要方法。《周礼》云,大师教“六诗”风雅颂赋比兴,郑玄注“比”曰“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注“兴”曰“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则“比”“兴”都是“比类”。《鬼谷子》说:“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观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辞也。以无形求有声。”语言可以使事理呈现形象。而事物本身是以类同的方式存在的。所以言语交流常常运用“象比”,即“比象”“比类”的方式,以繁复的形象比喻与类比,将无形的事理表达传递给他人。
其实,在早期的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比类”,如《诗经》。《毛诗》说《诗》,有“赋”“比”“兴”。“比”“兴”皆为“比类”。“物类相从,善恶殊态,以恶类恶,名之为比。”通过“比”,将丑恶的事物与丑恶的事物并列,让其恶彰显,让人得以明了善恶,从而达到讽谏的目的,这侧重于“类”。而“兴”则是“以美拟美”“叹咏尽韵”,不仅是比拟于美善,劝人向善,而且,这个比拟是尽可能地反复咏叹,是连绵不断的,这在“类”之外,更强调了“比”——同类物象的无限度地增殖、汇聚。如《鸿雁》一篇,首章以“鸿雁于飞,肃肃其羽”而兴,次章云“鸿雁于飞,集于中泽”,三章云“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三个比方,连绵陈列。所以孔安国说“兴”是“引譬连类”——连绵不断的、来自同类相征引相印证的比喻。刘勰也称“兴”为“环譬”,“环”,围绕也,围绕着对象,不断地展开一系列譬喻。而这种连续的比喻,冲击着听者、观众、读者的心灵,激起共鸣、思考,造成一种强烈的情感效应。从而使“兴”不仅是一种认识的获得,而且是一种情感的生产。所以包咸又说,“兴,起也”——“兴”是情绪情感的发端。朱熹解释“兴”,也说“感发志意”,“兴”是对情感意愿的召唤。所以孔子说“兴于诗”,对美善的认识、感受、向往,是一个人自觉自律向上的开端。“兴”中兼有摹物与抒情,故而,后人有“兴象”之说。“兴”而可“象”,可见情感情绪正是借物象而得以表现、得以传达;“象”可“兴”,则知物象不是对客观存在的被动复刻。在“比类”中,摹仿与抒情并非截然两端,而是一体的。所谓早期文学中摹仿传统被抒情传统所挤压的说法,应该再作斟酌。甚至,摹仿与抒情的这种二分也需要重新考虑。
而“赋”其实也受到“比类”的影响。“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铺陈”是以“类”为单位来开展的。司马相如《上林赋》写天子园囿,广大无所不备,分列山、水、动、植、宫室、物宝等各类,诸类名色、形态、动作、声响等,累累垂垂,绵绵迭迭。如“水”有“灞、浐”“泾、渭”“酆、镐潦潏”,其态“横流逆折,转腾潎洌”,其声“瀺灂”“砰磅訇礚”,其产有“鲛龙赤螭,渐离”,等等。所以,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赋就要以类相推,不断衍生。所以,“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赋就是事物比类相聚。因此,“比类”是赋的重要写作方式。以至于后世有人以为,汉赋可代类书。袁枚就说,《三都赋》《两京赋》声名远播,广为传抄,洛阳纸贵,“盖不徒震其才藻之华,且藏之巾笥,作志书、类书读故也”。
而早期诗赋为何以“比类”作为重要的创作方式呢?《淮南子》说,欲“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沦无形也”,就必须“揽物引类”“引人之意,系之无极,乃以明物类之感,同气之应,阴阳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远观博见者也。”直陈写物,可以使隐匿无形的道理现身出来;将物以类联想连缀陈述,可以使人茅塞顿开、眼界拓展、识见高远。从根本上来说,宇宙万事万物,就是以类相分、以类相感的。因而,对世间万物的书写,怎么可能不是“比类”呢?
三、立文:易象摹仿的目的
“比类”的结果,将万物组合成为可知的整体:“自然中的一切存在与事实,‘日月星辰、天空、大地与海洋,以及它们的所有现象和要素,连同所有非生物体、植物、动物和人’,这一切都被划分、标注和指定到一个单一而整合的‘体系’的固定位置上;在这个体系中,各个部分根据‘相似性程度’或平起平坐,或有所隶属。”
但是,“比类”的终极目标不是认识世界。“分类所划分的不可能是概念,分类所依据的也不可能是纯粹知性的法则。”“事物首先是神圣的或凡俗的,是纯洁的或不纯洁的,是朋友或敌人,是吉利的或不吉利的;这就是说,它们最基本的特征所表达的完全是它们对社会感情的作用方式。决定事物分类方式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情感,而不是理智。”《易传》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就是用“吉凶”来区分象与爻、物与事。春秋战国典籍说“比类”,多以善恶分类,用情感、利害关系来分类,“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易传》说,“象其物宜,”又说,“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象摹拟的是“物宜”,是物之为物的规定性,即“物义”。但是,对这个“物义”的摹仿,并没有针对物本身,而是指向物的功用,指向物在人的世界里充当的角色:“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所以,摹仿万物不仅是为了认识万物,更是为了使万物为人所用。故而,《易》可为“百姓日用”,可“济民行”“象事知器,占事知来。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此即“物宜”。“物宜”,作为“物之所宜”,非“宜”于物,乃为“宜”于人。物之“宜”,本属于物,人如欲得“宜”,只能被动地等待物的给予。但是,通过易象的摹拟,人掌握了“物宜”,得以如神明一般,洞察甚至掌控万物变化的奥妙,“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说”“知鬼神之情状”,并能够复制、再生产,“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人“能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用《易》,能补合牵引天地之道,拟范周备天地的化育,曲尽助成万物的发展。
因而,《易》的摹仿——“象—像”,不是对自然、对大道的膜拜、臣服,而是夺取、占有。《易》的摹仿,不是制造万物的副本或复本,而是为万物构建秩序,并以这一秩序来驾驭万物。《易》是法则,是为自然立法。“《易》与天地准”,准,等也,同也。“天地”是万物的肇生之源,而《易》最后取得了与此相等的权力和地位。
在早期文学中,摹写物,不是对物的复制,也不追求对物的形似,而是赋予它秩序和法则,给予它理想形式。比如《诗经》比类物事,讽劝抒情,孔子就要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再如,以铺陈写物著称的汉赋,挚虞批评它说:“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汉赋对物的摹写超越了现实物,编织出了宏壮的形象、缜密的逻辑、华美的辞藻,但这并不是汉赋的失实。毋宁说,这就是汉赋的审美价值所在,即对物的创造性再生产。这里,美不在物自身,而在文章之中。物要在摹写中才能得到恰当的表现。物必须被摹写,才能获得它的意义、它的美。所以司马相如才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赋的作者必须在写作中建立一个统一的有序的宇宙,安置万物。刘勰也标榜作者的“文心”“雕龙”,即其以创制“文”的“性灵”和写作技艺的能力进行创造性再生产。故而,《易传》有“立象”之说,而《文心》有“并生”之论。“立象”,“象”卓然自立,立起来,支撑起人的国度,在天地之间开创这个国度。“并生”,作为对万物的摹写表现,“文”,与天地一样,是万物化生的源泉。
与一些学者认为摹仿作为副本或复本,以“理一分殊”的方式分享原本的真理性不同,《易传》所指的摹仿本身就是真理性的。甚或,摹仿就是建立真理的方式,摹仿就是真理的生产。没有摹仿,就没有真理,真理唯有通过摹仿才能被生产出来。
所以,令人景仰追慕的不是摹仿的对象,而是摹仿本身。而后世的摹仿,尤其是先唐时期的摹仿,颇有以前人的作品为范本,进行竞争的意味。如扬雄对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班固、冯衍与崔篆:“昔崔篆作诗,以明道述志。而冯衍又作《显志赋》,班固作《幽通赋》,皆相依仿焉。”由此,“拟”成为一种文学传统、一种文体范式。
但是,与一些学者的断言不同,“拟”体绝不只是某种复古主义的写作。拟、仿,出自对对象的赞叹和认可。这种赞美,不是指向被摹写的物事,而是指向摹写了物事的文本自身。可见,摹写的价值不是来自被摹写的事物,而是来自摹写本身。是摹写赋予了事物之“丽”。而事物自身,是芜杂、繁乱的,是野蛮的蛮荒世界。要凭借作者的写作,才能将它们编组成“文”,从而变得华丽可赏。而“拟”不管有多少类型,拟“体”——摹写的语言制式都是必不可少的,“拟”其实是书写本身的再生产。“拟”又是一种竞争,在摹写技术、摹写成品方面的竞争。在这个意义上,诸摹本的价值与地位,并不是由它们与被摹写事物的接近程度决定的,而是由它们编制这个摹本的技术与审美效果决定的。这就是陈子昂说的“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致力追求文字的华美繁富,而不计与事物的关联指向。而“文体”的概念、文体的实践,正是由此成型的。“直接拟作前代文人诗的情况,是中国诗歌在积累中前行的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其可以使得诗体后出转精,在句式、技巧和声情上能够不断完善,寻找到某一诗体的最佳表现力。”“文学史的每一步前行,都是在对前代的模仿与学习中后来居上。”
直至魏晋玄学兴起,易学转向,言意之辨兴起,摹仿的观念与实践才发生变化。唐韩干以“马”为师;明王履说“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袁宏道云“善为诗者,师森罗万像,不师先辈”;又是另一个时代的事情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文论。
结语
摹仿是人类重要的行为方式之一。它在本质上是人对其他存在者的再生产,即马克思所说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这种对其他物种的生产方式的掌握,就是从摹仿起步的。因而,摹仿属于人类的类特性,具有跨越古今、横贯中西的文化普遍性。但是,由于生产环境与生产组织方式的历史流变,对摹仿的阐释必然是多元的、歧异的。不同的文化模式与意识形态话语,又会导致阐释的规范、模式的差异。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柏拉图的摹仿说长期成为历史主流,他将摹仿释为低一级的再生产,从而在神的原创与人的再生产之间划出不可逾越的鸿沟,确立了神的绝对权威。在资本主义时代,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个权威地位被自然接管,摹仿成为对客观事实的复制,从而以“真实”——物质实在性为评判标准。当维特根斯坦等语言哲学家揭示了语言及其制作品的人工性质的时候,这一摹仿观便无效了。而早期中国文学,摹仿之“象”作为“比类”,被看作与物自身的生产增殖同等甚或高一等的生产创造,树立了“人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古时期的文学自觉,植根于人在世界之中对存在的重新思考,将“物”作为自然、作为他者、作为人的本体与共在,重新构建了物我的主体间关联,摹仿论也发生了变化,朝向老子所言的“自然”开启。至当代西方,摹仿的能动效用被重新审视:阿多诺认为艺术的摹仿作为非同一性的生产,可以对同一性的历史总体构成一种否定性的冲击;利科将亚里士多德的“摹仿”概念扩展,覆盖了整个语言生产领域,并赋予后者实践性、行动性;耶鲁学派将文学摹仿看作事件的生产和时间的构造,而潜在地认同了它干涉社会形塑的可能。诸人均以“摹仿”为帜,挖掘艺术、文学、语言的生命力和行动力,为人类的前途探路。可见,摹仿实践仍然是当下人类开辟自身新的生存世界的有效方式。而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使“摹仿”变得更加值得关注。而《易》象作为上古时代人类关于“摹仿”的直觉产物,保存了人类文明的初始基因,可供借鉴。日新,日又新,日日新,生生不已,正是《易》之大义。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姜子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