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利维斯大众文明批判与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是20世纪两种经典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其在质疑大众文化生产标准化、休闲的异化以及“进步”的观念等方面有着高度的共鸣。面对现代性引发的危机,二者也都转向对文学批评的思考,但对于何为理想的文学批评、文学如何介入现实以及文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二者的回答又有重要区别,分别提出文学的实践批评与否定的辩证批评。比较20世纪两种经典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文学批评观,回顾其历史发展脉络,对当代创作优秀的新大众文艺作品、发展健康的网络文艺批评、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大众文化批判;文学批评;利维斯;阿多诺
作者赵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1024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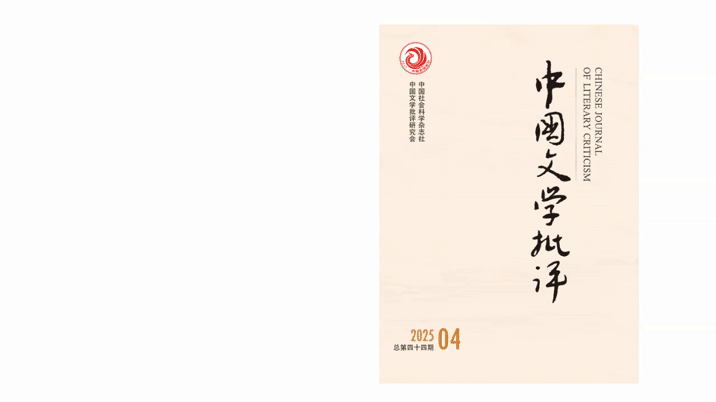
作为19世纪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产物,大众文化自出现就受到欧洲知识分子的批判。一众批判的声浪中,弗·雷·利维斯(1895—1978)的“大众文明批判”与西奥多·阿多诺(1903—1969)的“文化工业批判”成为20世纪批判大众文化的两条主要路径。国内相关研究谈到大众文化批判时多会提到这两条经典路径,看到二者的不谋而合;也有学者对二者相异之处有所思考。比如,从研究传统上看,来自英国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经验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更具有思辨色彩。在关注的重心上,批判大众文化还是大众,是阿多诺与利维斯相区别的一个主要方面。但总体而言,这种比较仅是在宏观维度上的概述,更多的研究是将二者分别置入英国“文化与文明”的传统或是法兰克福批判学派的脉络之中各自讨论。英国保守主义传统对民主进程的敌意,对道德滑坡的忧虑,对技术、工具理性的拒斥,对人文精神被放逐的失落,自19世纪以来薪火相传;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在更大的维度上服务于其对启蒙与工具理性的辩证批判与哲学思考,并构成其对国家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一环。
同属20世纪欧洲重要知识分子,利维斯与阿多诺生活年代相近,却无直接或间接的交流或对话。他们的生活经历、学术背景、理论旨趣与研究进路迥异,但在对工业文化的批判上异曲同工,有着相似的观点与态度。面对现代性引发的人文危机与欧洲危机,二者不约而同地转向对文学与文学批评的思考。但对于何为好的文学艺术、什么是理想的文学批评,又有明显不同的见解。本文从比较二者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出发,明示其“暗合”;之后勾连二者的美学思想,辨认其差异。对20世纪两种大众文化批判与文学批评思想进行比较与定位,有助于我们对当下新大众文艺生产及相应的文学批评实践进行反思,两种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脉络也对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具有启示意义。
一、大众文明批判与文化工业批判
在强烈反感美国现代文明这一点上,利维斯与阿多诺有着高度的共鸣。二者有关文化生产的标准化、物化社会中劳动的异化与休闲的意义,以及技术理性与“进步”观念等方面的批判,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阿多诺对休闲的批判是在吸收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之后,看到工业社会中文化也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个体为了消费而工作,为了商品而生活,自我价值也以金钱来衡量,由此现代社会整体都处于“物化意识的统治”之中。他由此质疑休闲的意义:在文化工业已经被工具理性逻辑支配的情况下,人们能否自由地消耗空闲时间,休闲娱乐究竟能有多少真正的“乐趣”,这些都值得怀疑。现代社会中个体在休闲中看似有很多文化产品选择,但这些文化产品都是在同一商业逻辑下生产出来,并无本质不同,全部都是“肯定的文化”,仅提供娱乐和消遣,助力劳动者恢复在工作中消耗的脑力或体力,以便第二天重新投入到异化劳动中。在日复一日对文化工业产品的消费中,人们逐渐彻底认同社会现状,毫无改变的想法。
最后,利维斯看到大众媒介铺天盖地的广告以科学理性的调查研究为幌子,时刻煽动着消费者的非理性欲望,进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伴随工业主义而来的“进步”的观念。他反复强调,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等于生活质量的提高,乐观与进步的观念通过广告和文学作品以最粗鲁的形式在全社会灌输。然而盲目的乐观是一种以拒绝看清事物本质为基础的快乐,是对问题的肤浅的逃避和不负责任,腐化并削弱人的力量。利维斯认为,这种工业文化消解了英国社会的文化权威,在整体上对英国社会的等级制度构成巨大的威胁。
二、理想的文学艺术与文学批评观
就文学批评而言,阿多诺同样反对以某一固定的标准去评判一切文学作品。这包括以意识形态这一一般概念从外部质疑文化总体的“超越式批判”或“外部批判”,也包括用文化自身结晶而成的规范来诘难文化,即“内部批判”。外部批判全盘拒斥社会,将总体像海绵一样抹去,以虚假的和谐解决客观存在的矛盾,靠近了野蛮主义。内部批判恪守着文化的观念,强调其“自在的存在”之意义,与外在社会生活相脱离,放弃了干预,从而也就为现实秩序张目,并因此在现存物化秩序中获取一席之地。从辩证的角度看,外部穿刺的批判和内部打孔的批判之间的对立,正是物化现象的一种症候。阿多诺所呼吁的否定的辩证法要求将文化批评提升到扬弃“文化”这一观念本身的高度,从而既否定文化的观念又实现了这一观念。
利维斯与阿多诺勾画的批评理论图景都赋予文学及文学批评以社会重任,但是这个重任的指涉并不相同。作为阿诺德“以文化代宗教”、文学批评是生活批评等理念的延续,利维斯坚信文学批评的根本任务是“救世”,即以高雅的文学引导知识分子和民众的价值取向,塑造情感,进而将人类文明从工业化、物质化和大众化的庸俗与堕落中解放出来。就此,利维斯设计了一整套方案并付诸实施,多管齐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透过文本细读提升英国民众对人性与道德的感知,将盲目、冷漠的个体重新熔铸成具有甄别意识的公众,建立起能够有效抵抗工业文明侵蚀的“文化共同体”。
阿多诺同样重视改变接受者的物化意识。但相较利维斯积极走向学生和公众,阿多诺的审美教育强调艺术以形式要素与社会拉开距离。日常生活中人与现实是没有距离的,好的艺术作品会激发出欣赏者恐惧或震惊的瞬间,从而切断个体日常的认同模式,将欣赏者从物化的日常生活中拽出来。“被卡夫卡的车轮碾压过的人就永远不可能与世界和平共处”,在这一瞬间,艺术欣赏者被审美意象所震颤。这种全面的审美体验与文化工业带给个体的感官刺激完全对立,它毫无愉悦可言,却能让个体看到摆脱日常生活物化现实的可能性,完成对自我和现实的批判。
三、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启示
利维斯与阿多诺在20世纪发展的两种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以及文学批评观对中国当下文化的发展与文学批评具有重要启示。
第二,文学批评不能脱离文学文本与文学实践。批评在本质上固然意味着区分与判断,但文学价值的判断与衡量远不是创造一套固定且明确的标准简单应用到作品上。阿多诺明确提出,用某个一般的概念从外部来质疑文化这个总体,或者用文化自身结晶而成的规范来诘难它,二者都是批判理论不可接受的。坚持在内在性和超越性之间二选一,就回到了黑格尔反对康德时已经批判过的传统逻辑,而辩证法意味着对一切物化的毫不妥协。在利维斯看来,批评是知性和敏感性的完美结合,需要批评家细读文本,揭示文本的内在含义,同时这也是批评家凭借个人感受力进行再创造的过程,体现了批评家个人的见识、品味和旨趣。他本人的文学批评也从来没有远离文学文本和细读,充满了对文学作品的深刻理解和细腻感受,为今天我们利用文本细读进行文学批评提供了极好的范例。
利维斯认为,一部作品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修正或改变了进行判别的观念。时代在变化,今天的新大众文艺诞生于与纯文学创作截然不同的数码人工环境,其想象力环境、主体、文学要素、文本内部遵循的逻辑、语言等与传统文学都有明显不同。一边摆放好纯文学,另一边安置好网络文艺,然后直接将两者进行比较,这么做几乎毫无意义。在进行新大众文艺作品的批评时,我们需要导入复合的视角,甚至更新批评的固有观念,看到作品创作的环境变化,有助于从现实主义视角看貌似荒诞无稽的幻想作品,读取到别样的、更有建设性的信息。
第三,文学批评要面向公众,发挥社会功能。在文学必须关注社会、发挥社会功能这一点上,利维斯与阿多诺具有共识,只是就文学如何关联社会方面,二人观点不一。利维斯认识到,解决大众文明时代的文化危机,光靠“少数人”是不够的,重构社会有机共同体,需要唤醒民众的文化批判意识。在工业文明时代,利维斯认为大众的阅读品位需要少数人引领,不能否认其中有居高临下的态度,但他的文学批评有着极强的“读者意识”和走向公众的情怀。他号召在大学之外的全社会进行英国文学教育,尤其应推动成人文学教育,工人阶级也应该阅读莎士比亚,阿多诺则认为妄图通过文化批评拯救病态的社会是幼稚的,艺术只能发挥社会参照的功能,而不能直接介入现实或反映现实,只有否定现实、挑战现实的观念,才是真正的自律艺术,也才能把握住生活的理念。
不过,阿多诺批判理论为人所诟病之处也在这里:虽然提出了根本性的问题,却寄希望于以乌托邦克服同一性的世界。但人总要与世界产生关联才能生存下去,如果不能提出有实践性的改善方针,这种批评就只剩下悲观的叹息。他指望以自律艺术完成对个体的重建,这是更加精英主义的态度。以个体去反抗社会的同一性,追求弃绝消费的自律艺术,这种要求只有极少数人才有条件争取,其解决思路几无可能实现。在实际生活中,先锋的艺术很可能对大众构成一种拒绝而非“震惊的瞬间”,最后成为一种孤芳自赏的艺术形式。
第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必须结合当下实际,努力回应现实问题,才能焕发勃勃生机。利维斯始终紧跟时代的变化,不仅坚持以批评救世,还将文学批评的对象拓展到大众文化中,在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的融合方面做出了初步的示范。也因此,其融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宗教和媒介观察于一体的实践批评范式在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欧洲文明危机与法西斯背景下,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完成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在20世纪的转型。作为流亡者的阿多诺借助《奥德赛》的文学隐喻,以切合西方文化传统的方式深刻阐述了启蒙的辩证法即资本主义走向自我毁灭的必然性,指出文化工业与法西斯极权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人类思想史上产生深远影响。
但是,对于时代的“病症”,利维斯囿于出身及经验主义传统,其回应始终缺少“朝前看”的勇气,漠视经济发展带来社会进步的一面,也有意忽略英国乡村封建宗法制的罪恶,没有看到英国社会与政治问题更深层次的根源。利维斯的愿景指向工业文明之前的田园牧歌,而在其文化传统的中心,供奉着的则是经过挑拣的英国文学传统。阿多诺则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彻底性和辩证性,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文化领域。
比较这两条理论脉络的产生与发展,不论是利维斯的保守主义还是阿多诺的批判气质,二者都没有真正努力解决当下的社会文化“病症”。而同样的话题,自20世纪50年代经过雷蒙·威廉斯的改造,成为“漫长革命”中的伟大成就。1969年,威廉斯写作《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颠覆式重读了利维斯《伟大的传统》,从将传统文化奉为圭臬到将文学文本历史化,在英国小说传统的变迁中发现新兴的元素。1977年,威廉斯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最终以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实现对传统教条和保守的利维斯主义的超越,开辟左翼文化研究的新场域。在继承利维斯主义的基础上,威廉斯始终肯定工人阶级大众的能动性,以积极的态度直面英国本土文化理论与现实困境,开辟了英国文化研究的道路,堪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英国本土化的典范。
这条道路提示我们,文化批判与文学批评有着极强的现实性与实践性。当下中国文学文化实践走向“新大众文艺”,出现了越来越多介于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新文艺形态;文化消费者的主动性也愈发凸显,他们不仅有着丰富的文化产品消费经验,而且深谙文化生产的逻辑,在各种同人创作中生产自己的话语,或以集体的力量形成对资本平台的反抗。面对今天更加复杂的文学文化现象,中国文学批评不能故步自封,在理论层面自说自话,而应努力突破二元文学批评框架,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论资源相结合,回应全球数字技术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现实中出现的新的文学文化命题,并以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学批评话语体系。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