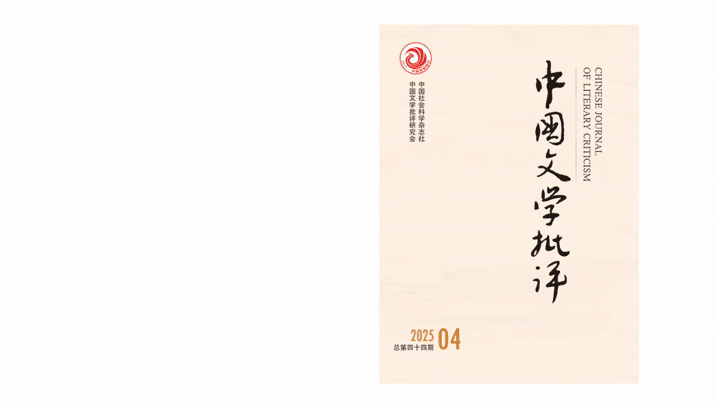通常,我们倾向于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主要由乡村和城市两类景观所构成。这是因为,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乡村和城市往往被赋予浓厚的象征意义:它们常常以二元命题的形成呈现,或彼此颉颃,或相互对照。但这样一种理解,显然是没有注意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景观和空间叙事的复杂性。在这一逻辑下,乡村和城市之间的中间状态或过渡形态常常被忽略:处在城乡之间的县城或县域总是无关紧要的,县城写作自然也不太被关注。而事实上,在中国,不论是社会学层面,还是文学层面,县城都是一个模糊的范畴。这首先是因为与之相近的家族相似性概念颇多,比如说市镇、小城、乡镇、县级市等,其结果是,这些范畴常常不能两分。但应注意到一点:县域在经济学中,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单位——“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有学者把类似于县域这样的经济单位,区分为“基层集镇”“中间集镇”和“中心集镇”三种形态,在这三种形态中,“基层集镇”既是底端,也是基本单位:“一种能够满足农民家庭所有正常贸易需求的乡村市场:农民家庭生产但不消费的物品一般在这里销售,消费但不生产的物品在这里一般也能买到”。乡镇正可以看成这样的“基层集镇”。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县域”,就包含互有关联的三种“集镇”。其次还因为,这些集镇是介于城乡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乡村和城市的中转和桥梁,也是返乡和去城的枢纽,始终是一种“在路上”的中间状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集镇构成城市化进程的前站:城市化的进程,某种程度上是与集镇(特别是县城)的扩张构成正比关系的。在城市化的推动之下,各类集镇在扩大,乡村呈缩小之势。
据此,我们提出“县域书写”这一说法,以取代“县城文学”这一内涵和外延均较模糊的范畴。某种程度上,乡镇、县城、县级市等,正好对应着“基层集镇”“中间集镇”和“中心集镇”三种形态,把这些集镇统称为“县域”是一种较为可行的做法。如此一来,县域书写这一概念就既具包容性,也具有阐释性,涵盖以乡镇、县城、市镇、小城、县级市等作为背景的小说。这些都是大于乡村但又小于“地方城市和地区城市”的基本独立的经济单位。此外,县域这一概念,突出的是一种流动性、包容性和中间色彩,它处于乡村和“地方城市和地区城市”、全球性都市的格局中的中间形态,既具有城市的地方性特点,也具有乡村的地域性特征。大凡以乡镇、县城、小城、县级市等作为创作背景的,都可以称之为“县域书写”。
一、县域文学的源头
历时地看,县域文学的古代源头,《金瓶梅》应属其中重要的一部。《金瓶梅》主要写的就是发生在中国北方一个叫清河县的事。这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县城,颇有现代都市的意味。小说里面的主人公也会不时地奔波和游历,其空间的位移包括东京、杭州、清河等,也有乡下。但即使有多重空间的转换,我们却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同。或者可以说,这些空间并不对应时间感的不同。东京城里发生的事,与清河县发生的事,所带给我们的时间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可见,在古代的小说传统中,故事的背景——即空间——在一部小说中,并不具有质的规定意义;同样,空间的变换,也并不构成影响主人公命运的枢纽。这都是因为,在古代社会,循环时间观之下,空间并不具有时间感上的差异结构。空间差异结构的产生,源自“已经变成了一个分裂因素——一个时空结合中的变化不断的动态角色”即“时间”的介入。其带来的结果是,空间的位移对应着时间感的不同;在现代小说中,空间之间的等级关系构成人物命运的隐喻。可以说,空间意义的真正凸显,是现代才有的现象。比如说中国现代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主人公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流动,显示出来的正是国家的发展焦虑的隐喻。这就产生了中国/西方、乡土/城市、小县城/大都市的二元对立模式。自此,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演变成中国现代小说的两大题材。
但正如鲁迅所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乡土文学其实是远离乡土的作家回望乡土的写作,这里面是存在空间等级关系的:乡土在现代城市文明的烛照下,虽偶能抚慰人心,但其实满目疮痍。鲁迅的话似乎表明,现代性的文学书写是建立在空间差异这一基础之上并最终强化了这一空间差异的。如果说乡土文学是远离乡土的人所作,县域也是在回望中被建构的。县域的“中间地带”特性使得县域书写相比乡土文学有着更丰富的症候性。这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如此。县域相对静止、安静,但其实也暗流涌动。《平乐县志》就表明了这点,县城这一空间,与城市并没有任何两样。主人公陈地菊本来回到县城是为了疗伤的,没想到却受伤更深。所以小说的最后,主人公才要再一次离开县城。不过反讽的是,陈地菊离开县城的资本却是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所带来的房价上涨的红利。如果没有这一红利,陈地菊的再次出走显然难以完成。从这个角度看,城市化提供了想象县域的方式方法。县域是乡土社会的集中象征,也是城市社会的自然延伸。县域写作显示了县城的保守与开放、离开与返回的双重性特征。或可这样认为,县域书写只有放在现代性的时间进程和空间的位移中加以理解,才能有效展开。
二、空间视域中的县域文学及其二重性特征
大体上说,20世纪中国的县域写作,是一种单向度的写作,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冲击—回应模式的显现:在现代化的入侵之下,县域的传统秩序遭到冲击,主人公们的命运也随之改变。虽然说,这样的小说,也会写到县域居民的外出,但多是一种被迫出走,出走的终究是少数,他们大多数仍旧停留在县域;时间会抚平创伤,一切都会慢慢平复,秩序最终恢复如初。这是20世纪20—40年代的县域写作的常态,比如说沈从文的《边城》。在此前后,因战争或社会动乱引起空间的流动,城、乡及县域之间的区分被打破,但这是文学写作中的例外状态,并不构成对传统县域写作的真正冲击,一旦秩序恢复,县域书写又会重回单向度的书写形态。
县域写作的重要变化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外面世界的改革与县域世界彼此呼应,相互迎合。比如说何士光的《乡场上》等。这是一种彼此呼应、同频共振的关系,县域的时间感与城市的时间感之间并无根本的差别。这样一种写作倾向,与改革文学具有高度的重合;或者可以说,改革文学创造了县域写作的新模式,即把古老中国的变革放在县域这一背景加以展现,其隐喻象征意味不言而喻,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大大束缚或限制了县域的独特表象与表达。
历时地看,县域写作的真正变化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城市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县域书写表现了迥异于此前的倾向。这一倾向,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有呈现。全球化时代中,空间的等级秩序逐渐显现,在由乡村、乡镇、县城、县级市(包括小城)、中心城市和全球性大都市等构成的空间等级秩序中,不同空间中的人们感受到的时间的节奏是不同的。全球化的触须正逐渐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偏远的山区,其最明显的表征就是电脑和智能手机等网络终端所带来的距离感的消失:我们能同步获悉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发生的任何事情,但同步性却不能消弭我们同全球性城市的距离感,这就是所谓的“不同时的同时性”。时间感的差异,使得由乡村走到城市的单向度过程作为不可逆的社会进程凸显出来:这已不仅仅是冲击—回应的简单表现,而是时间进程的同步性和时间感知的差异性的双重特征的复杂表征。
可以说,城市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带给县域的变化是相当巨大而深远的。它使得县域作为“中间地带”逐渐凸显。县域的“中间地带”状态,是与“脱嵌”和“再嵌入”进程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脱嵌,我指的是将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情境中‘脱离出来’,并穿越不确定的时空范围而得到重构。”这里注意两点:一是“彼此互动的地域性情境”,二是“不确定的时空范围”。前者主要是指乡村社会和县域社会,后者包括中心城市和全球性大都市。“脱嵌”反映的是如下这种社会进程,即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情境”向“不确定的时空范围”的流动。这一“脱嵌”的进程,是有着等级秩序结构的,即从乡土社会,经县城、小城,走向中心城市,进而涌向全球性大都市。县域作为这一中间结构,既是走向的空间,又是最终离开的地域。一方面是农民返乡的实际落脚点,另一方面是进城的中转站;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的前哨,另一方面是乡村接受城市现代化讯息的重要依托;这样一种二重性,导致了对县域的想象和书写充满了矛盾,颇具象征性和隐喻色彩。众所周知,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有所谓沿海、内陆的区别,有华南、东南、中西部、华北、西北和东北的分野,在这样一种区域的划分下,县域与县域之间,其实是有着较大的差别的。在文学叙事中,这样的差别虽非不重要,但实际上已被隐喻和象征所取代。县域书写常常以隐喻和象征的方式显示其“中间地带”的特性。县域文学的“中间状态”特征在不同的时代有着程度不一的表征。
三、“中间状态”与想象县域的几种方式
某种程度上,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县域书写是一种可以称之为“没有县域的县域文学”。那是一种“以城市作为方法的县域书写”。就像沟口雄三所说“把世界作为方法来研究中国,这是试图向世界主张中国的地位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为了向世界主张中国的地位,当然要以世界为榜样、以世界为标准来斟酌中国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或距离目标还有多远),即以世界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因此这里的世界只不过是作为标准的观念里的‘世界’、作为既定方法的‘世界’,比如说‘世界’史上的普遍法则等等”。以往的县域书写是以城市作为榜样和目标的写作,在这一倾向之下,县域实际上已经成为某种象征或隐喻存在。这一县域是以城市作为标准来打量和表现,并以隐喻的方式显示其特征的。
这一状况,自20世纪末、21世纪以来有了重大变化。一种以县域作为方法的县域书写开始出现。以县域作为方法,就是把县域放在与乡村、地方性城市和全球性城市的平等状况下观察、体验和表现;就是呈现县域在这一复杂空间结构中的独特表征和丰富内涵,而拒绝作单一性或隐喻化的表现。自此,县域写作以两种倾向彼此竞逐,互为参照。一种倾向是没有县域的县域文学的“变种”,另一种倾向是“中间地带”的县域书写的“新态”。两种倾向,既是历时性的演变的表现,也是当下县域写作中存在的两种倾向的概括。
就第一个倾向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县域书写,呈现了诸多新的表征。
表征之一,隐喻式的县域文学。在这些小说中,县域只是一个符号或象征,并不具有实际的意义。换言之,在这些小说中,作为背景的县域可以换成中国的任何一个县域,甚至于里面的县域可以作为中国的隐喻。这在余华的《兄弟》,以及海男的《县城》等小说中有集中表现。这是典型的没有县域的县域文学的延续:小说中的县域以掏空其地方性特征的方式,显现中国隐喻的形象特征——这些小说创造了隐喻中国的“恰当”空间形态。
表征之二,精神困境的县域景观。比如说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一日三秋》《我不是潘金莲》等,都以县域作为重要背景。但刘震云的县域景观(即延津县),却是模糊不清的,看不到“地方性”或“现代性”的内涵,甚至也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和全球化的紧张感,虽然刘震云也把县域放在了历史的景深中加以展现。县域这一空间是刘震云思考现代社会“人”的精神处境的适当形态。他把县域放在了熟人社会的角度展现,熟人社会的物理近距离与精神交流的远距离构成鲜明的反差,让我们对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处境产生沮丧感。生活在县域社会构筑的熟人社会,却感到深深的迷惘,所以他的小说主人公们才会执着于去寻找远方的人和新的关系。
表征之三,怀旧式的县域书写。这在魏微和蔡崇达的小说中有集中呈现。比如说《流年》(魏微),这是记忆中的县域,是童年生活过的地方,也是成年后离开的地方,是后来慢慢消失的所在。正是因为有着这种时空的隔阂和距离,曾经的县域才显得那么凄美而舒缓。再比如说《草民》(蔡崇达),小说中的东石镇既是疗伤的所在,也是重新凝聚力量再次起航的中场暂歇地,蔡崇达写出了闽南小镇既传统又现代的双重性。
表征之四,逆全球化县域书写。与怀旧式的县域书写相近的,是逆全球化县域写作。这在陈春成的小说中表现明显。县域是陈春成小说的重要背景,作者的主人公也生活在全球化的今天,但他们却表现出逆全球化的姿态。老家的房子已经拆除,只留下一把写着“永安”的老屋的钥匙。如何安放这把钥匙就成为主人公心心念念的问题。似乎是:只要钥匙永远放在某个不为人知但能让自己时刻想念的地方,就能很好地生活在世间(《竹峰寺》)。怀旧式的县域书写不同于逆全球化县域书写,其主要表现是,县域与全球化大都市之间构成鲜明对照关系,主人公通过对县域的怀旧,以疗救、舒缓和释放全球化所带来的紧张和压力,怀旧的结果是再次离开县域。逆全球化县域书写则不同,具体表现为,主人公虽然充分意识到全球化的不可逆,但仍旧愿意回到或固守县域;这既是身体的返回,更是精神的返回;这既是把县域作为全球化的对立面来书写,也是把县域置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老房子被拆了,“青砖的老屋,连同周边的街巷、树木,那些我自幼生长于其间,完全无法想象会变更的事物,造梦的背景,一闭上眼都还历历在目的一切,全没了。不仅如此,整个县城都在剧变”(《竹峰寺》)。其实,主人公也明白,生活在县城,其实仍是生活在全球化进程之中,但主人公仍旧愿意停留在过去。于是乎,在全球化进程中生活在县城,就成为这一类小说的倾向:在这一同一进程中自造一个安放心灵的小庙。这是在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中的返回倾向,其导致的结果是,既充分认识到全球化的不可抗拒,同时又闭眼虚化这一全球化进程。因此,小说也就具有了内在的张力和紧张关系。
前面几种类型的县域书写,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时间被虚化,以至于空间显得模糊不清。在这些小说中,我们能感受到全球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的发生、发展或流变,但作者始终以一种回避或虚化的方式处理,这就导致县域常常以一种隐喻或象征的方式呈现,县域的“中间状态”常常被遮蔽,无法充分呈现,县域的本来面目也始终得不到彰显。
“中间地带”的县域书写的“新态”,也有几种表现。这里所谓的“新态”主要是指,县域在小说中虽也难免以隐喻或象征的方式显现,但更多聚焦全球化进程下的中间状态及其现实处境,其结果是,隐喻象征和现实描摹彼此交错,相互颉颃。
表现之一,全球化时代的隐喻和“中间地带”的县域。以迟子建的《群山之巅》为代表。对迟子建而言,县域这样一种时空背景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另一重看问题的角度,更是作者思考世界与自身关系的新的基点和起点。她虽然无力也不可能解决上述矛盾,但能在自己的小说中充满诗意地表现。这类小说中,县域以“中间地带”的形态呈现,虽也有隐喻或象征的出现,但隐喻或象征大多是局部的。小说充分注意到了县域的复杂性和过渡性特征。
表现之二,对怀乡的祛魅式书写和原乡想象的解构。这在颜歌的《平乐县志》中有所呈现。小说主人公陈地菊因为情感挫折返回生养自己的县城,打算过一种返璞归真的质朴生活。但随着深入生活的机理,才逐渐发现,看似岁月安好、节奏舒缓的县城熟人社会,其实里面有太多的不堪、算计和背叛。陈地菊的最后离开,正可以看成对这一原乡性想象的否定和质疑:所谓返回,只有在想象中才是美好的,一旦真正回去,终究还是要再度离开。
表现之三,熟人社会稳定性的构筑与陌生感的表达。这在张楚的《云落》中有集中表现。小说把县域社会放在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加以展现,既展现熟人社会的温情的一面,也展现全球化时代潜藏的风险和陌生感。这是把县域置于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的角度加以表现,小说因而呈现出鲜明的对照来:温情来自熟人社会,陌生则关乎风险。不变的东西,关联着云落的地理、风物、习俗或人情,变的因素则指向未来、欲望和风险;小说虽然以略带悲剧式的语调结局,但给人的安慰或慰藉也是显然的。
表现之四,熟人社会的怀旧书写与辩证表达。这在许言午的《扬兮镇诗篇》中有所表现。小说中的两种倾向具有典型性:一是把扬兮镇放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表现,展现其缓慢但又不可逆的变化过程;二是怀旧式的抒情氛围。小说叙述者在理性上明白离开的必然性,但在感情上却表现出回归的倾向,正是这种双重性,扬兮镇作为县域书写的熟人社会特质才得以充分展现。熟人社会,一直是县域书写无法绕开的叙事对象,但大都表现出要么被美化,要么被风险化的倾向:美化是因为以怀旧的方式显现,风险则因为把县域看成全球化进程的重要一环。这样的表现,都是没有看到熟人社会的中间状态特征:既相对安定稳固,也充满流言是非。从这个角度看,《扬兮镇诗篇》把这种中间状态特征作了较为充分的表现。熟人社会的辩证特征,在小说中有较为鲜明的表现。
四、同质化与全球地方的建构
通常认为,现代性社会是时间加速发展的社会,因此必定导致“同质化”现象的发生。这在鲁敏的《奔月》中有极具症候性的表现。小说的主人公小六出逃,来到一个偏僻的县域。本以为来到了一个迥异于现代大都市的地域空间,最后却发现,在全球化时代,所谓的僻壤之地,其实已表现出与现代大都市高度同质化的倾向;这使她清楚地意识到,任何逃离全球化的努力其实都是枉然。不难发现,《奔月》所呈现的,是一种可以称之为“无地方”的文学景观:“过去的地方痕迹”被“抹除”,“各个地方看来都彼此相似”,“无法与当地的地理状况相融合”,“肤浅体验”“四处蔓延”;这一景观也被人称为“非地方”:“只为那些匆匆路过的陌生人而设计,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区域里看起来都大同小异”。显然,这种“无地方”倾向,在县域书写中也普遍存在;没有县域的县域文学,是其重要表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县域写作中“地方性”的消失。应该说,在县域写作(包括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中,地方性和“无地方”性是“交织”共存的,区别常常只在于比例或比重。当“无地方”性越来越明显且远远多于地方性时,这样的县域写作的均质化程度就显得更高。
从前面所引爱德华·雷尔夫的论述不难看出,地方性的显现,常常聚焦历史(即“过去”)和地理状况的独特显现上。这也说明,地方性多与时间感和空间感联系在一起。县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有着相对稳定的区域划分和自身的历史、文化与风俗,这也为表现县域的地方性带来了可能。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空间差异格局,也为县域书写的地方性建构提供了可能。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全球化一方面消弭了地方性,另一方面也再造了地方:地方常常作为一种景观被制造出来,以供观赏、消费和想象。最为明显的表征就是“博物馆化”。博物馆化,“其过程可以表现为对过去的村落进行改造,对城堡实施重建”,事实上,“博物馆化”所带来的,很多时候“只是人为创造出来的一件事物而已,是按照我们对过去岁月的浪漫想象打造出来的,采纳了最完美的建筑形式来呈现”。这是被制造出来的地方性,与县域文化景观的地方性并不相同。全球化时代的县域是“全球地方”的表征:全球地方的起点是全球化,落脚点却是地方性。全球化和地方性的两重性在城市书写和乡村书写中,难免以症候性或隐喻象征的方式显现,在县域书写中却能以“中间状态”的形式凸显。
在全球地方的县域书写中,时间感和地方感是两个重要命题。时间感是时间社会学的重要范畴,不同的社会结构,有着不同的“对时间的感知”。“伴随着演变的过程,随之出现的是完全不同的时间的地平线,并且因此带来了有巨大差异的行为的导向和自我关系。”这一时间感“不是经验世界的时间,而是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具有主观性。关于县域社会与时间的关系命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并作用于县域社会中的居民以及人们是如何感知县域这一社会时空的时间节奏的?县域社会处于一种不快不慢的时间节奏和中间状态:既感到岁月安好和相对稳定,也有走向城市社会的渴望;既有不能融入现代社会的焦虑,也能保有未被世界遗忘的坦然。
在对县域的感知中,时间感和地方感是彼此融合的。对地方的感知同时也是一种对地方的时间感。爱德华·雷尔夫提出了“本真的地方感”和“自觉的地方感”的区分:“本真的地方感,首先是指人作为一名个体和共同体的成员,能够在不经反思的情况下,直观到自己存在于地方的内部,并归属于他自己所在的地方。这种不自觉的本真地方感在自己的家、家乡、所属的区域或民族那里都可以明显地体现出来。”“在不自觉的地方经验里,地方以其本来的样子被人们真诚接纳;然而在自觉的地方经验里,地方成为了人们理解与反思的对象。”这里提出“自觉的地方感”首先是一种“我—你”之间的他者视角:“‘我—你’关系在本质上来说是外来者或陌生人试图敞开胸怀去体验一个地方,并积极回应地方的独特认同。”县域书写中的地方感,主要是一种“自觉的地方感”;但这里的“我—你”关系,是自我他者化的县域,即“在城望县”或“在村望县”的关系。即县域“中间状态”认知基础上的地方感建构。这里的地方感首先是一种比照关系,即城市和农村的对照关系。其次是地方性与无地方性的对照关系,也就是说在大都市中无地方性超过了地方性;而在县域中,地方性的成分超过了无地方性。最后,是对中间状态的复杂态度和矛盾心理。城市的流动性和加速发展,使得地方性的保护难以有效形成;乡村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使得乡村社会的书写变成全球化写作的重要表现。县域写作则具有了双面性特征:既相对稳定,又极具流动性;既难回归,又可作为精神的安放地;既是历史的,又是地方的;既要回归,也要离开。
而如果说地方感是一种“人地关系”的表征的话,县域地方感其实就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呈现——与“中间状态”相匹配。县域既是需要被克服的对象,同时也是被不断回望和重塑的对象。县域既难以被本质化,也难以被个体化。比如说《宝水》的命题。小说主人公在城里生活久了,退休了。但她并没有回到自己的老家县城,而是来到了邻近的县城和县城下面的乡村。在这里,县城—城市—县城—乡村,构成一种略带闭环的结构。全球化时代,故乡已经不再。因为故乡里的人,大都已经不在故乡了:或者去世,或者离开故乡跑到了国外,或者离开故乡到了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回乡似乎已经不再可能。但回乡不可能,却并不代表或意味着返回就无可能。回到乡间,其实就是在重建另一个家乡。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新的县域书写——全球化时代的县域书写。
结论:熟人社会、周遭世界与主体建构
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看,县域社会既具有小说叙事的结构功能,也是主体建构的恰当形态。就前者而言,以县域作为背景,可以避免人物的过度繁琐或芜杂,从而做到结构的相对紧凑。就后者而言,县域社会空间相对独立完整,是较为典型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周遭世界”形态,有助于我们考察县域书写的时间感和地方感。社会学中有“周遭世界”与“熟人社会”等说法。“周遭世界”由“直接经验和传递性经验”构成,是以个人生活其中的具体特定时空为表征的,与个人的社会关系息息相关。“熟人社会是通过交往来建立和维系的,交往是熟人社会的生命所在,没有了交往,熟人社会就会变得死寂沉闷,毫无生气”。“周遭世界”等概念的提出意在显示,现代认同的形成与个体在其中身处的世界范围或空间大小密不可分。这个范围,与个体所能感知、把握和把控的能力有关。从这个角度看,县域这一空间,既具有自足性,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也具有熟人社会的特征,对现代个体的形塑有着重要作用。以县域作为观察视角,可以很好地观察现代自我的形成、发展与困境,以及如何突围等命题的展开。
在传统社会,周遭世界与熟人社会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城市化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周遭世界表现出同熟人社会分离的趋势。一方面是周遭世界的内在分裂,“在很大程度上,现代性的情境早已不再有‘运气’的身影,个体在此种情境中通常会将周遭世界区分为有计划的事件和偶发事件两部分。偶发事件制造了从背景到前景的持续相关性,从而使个体得以从中形成有联系的一组行动。这个区分也使人们得以涵括现实和潜在的一系列事件,并将其放置于一个仍需对其实施最小限度监控的场景。”我们生活的世界越来越被“偶发事件”所左右。另一方面是“周遭世界”中陌生人和陌生事物的增多。这一情况,带来的是“熟悉的安全感”的消失:“在大多数传统文化中,尽管人口迁移相对而言较为常见,且长距离的旅行虽然不多但总有人去尝试,但绝大多数人的社会生活依旧还是本土化的。改变这种情形的最主要因素并不在日益增长的人口流动性,相反,场所完全为脱域机制所渗透,而这个机制把本土活动整合进极为广泛的时空关系中。因此,场所变得变幻莫测起来。虽然人们所生活的环境仍是本土情感依恋的根源,但场所已不再是经验的参数,它也不再提供传统上本土社会通常会体现出来的那种熟悉的安全感。”在县域社会所构成的“周遭世界”中,我们既感到“熟人社会”带来的稳定性和恒常性,也感受到“偶发事件”的入侵。因此,如何表现恒常和偶发就成为考察、考验县域书写的重要命题被提出。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县域的房屋会被拆毁,原始风景会慢慢消失,但人心却可以表现出不变的稳定性来;只是作家们十分清楚一点,即,对于这种稳定性,只有那些“痴傻”或“愚钝”之人,如《秦腔》(贾平凹)中的引生,《杨兮镇诗篇》中的丁晓颜,或《云落》中的万樱,才能保持;他(她)们是以面向过去的姿态,朝向未来:历史和历史的景物,就构成为县域的全球地方性的显现。他(她)们并不拒绝未来。
因此,熟人世界的重建就成为县域写作的焦点也是难点。《云落》和《平乐县志》从两个方向尝试重建熟人社会,极具症候性和典型性。《云落》中的天青,离家多年后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云落县,其通过尝试重建熟人社会,以重建自己的身份认同。虽然他最终再次出走了,但这一出走是以熟人社会的重建为前提的:在这一小说中,熟人社会所蕴含着的厚重历史、醇味温情和稳定感,既让主人公陶醉,也让他最终释然:只要在人与人之间建构起熟人社会的信任感、认同感,也就不在乎要不要换回被他人冒用的自己的名字和亲友关系网了。与《云落》相似的是,《平乐县志》中的陈地菊回归平乐县也意在疗伤和寻求安慰,但她最终发现,熟人社会到处密布着风险或陷阱,只有生活在陌生人社会才有可能真正感到安心,虽然这样的安心是以远距离或空间的隔绝作为前提;小说最后,陈地菊再一次出走县城(家乡)正说明这点。两部小说,都使得如下问题凸显出来:全球化时代的身份认同如何建立?熟人社会虽然满布风险,但缺少熟人社会的历史景深作为依托,仅靠想象的或抽象的关系所维持的认同,终究显得虚妄。因此,如何从这种复杂性中理出头绪,就成为考验作家们的难题和挑战。
某种程度上,县域书写的困境,其实也是自我认同的建构的困境。我们呼唤县域书写的新的可能。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