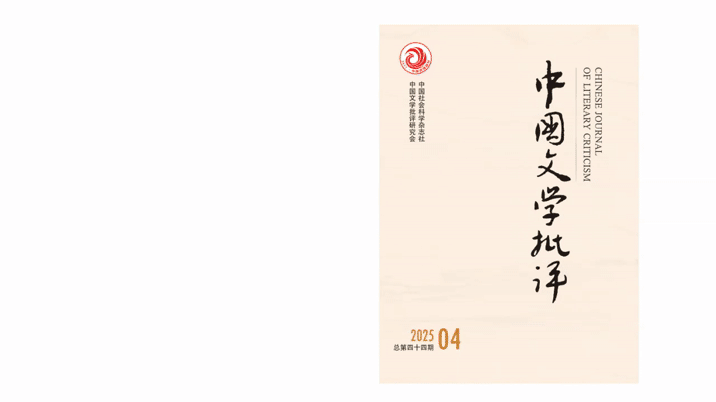唐宋转型作为中古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核心命题,其影响辐射至史学、社会学、文学及美学等多重领域。钱穆指出:“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故就宋代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学术思想乃如艺术,亦均随时代而变。”这一论断揭示了唐宋转型的全局性意义。若聚焦于文化权力结构的嬗变,门阀士族的消亡与庶族士人阶层的崛起堪称关键动因。北宋政权基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推行“崇文抑武”国策,依托科举制度的系统化改革,使庶族士人逐步取代门阀贵族,成为政治实践与文化生产的主体力量。相较于门阀精英的封闭性,庶族士人因其平民化出身与科举晋升路径,在身份认同、价值取向及审美趣味上呈现出显著差异,进而催生出具有时代特质的美学范式——平淡美。
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平淡”的哲学渊源可追溯至先秦儒道的“中和”观与魏晋玄学的“自然”论,至唐代诗学中亦不乏对“冲淡”风格的推崇。然其真正升格为自觉的审美理想,则需待至宋代。成复旺等学者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强调:“追求平淡自然,是宋代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封建盛世已经成为过去、而新的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尚未到来的历史时期的审美理想。”此论精准捕捉到平淡美与时代精神的共生关系。韩经太进一步指出,宋人将平淡诗观置于理论核心,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首次在成熟的理论自觉中确立平淡美作为终极审美理想。张法则直接将“平淡”定义为“宋人追求的理想境界”。这些研究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平淡美虽植根于传统,却在宋代完成从边缘话语到中心范式的历史性跨越,成为唐宋文化转型最具标识性的美学成果之一。
一、平淡美的情感基础:“乐”
中国古典美学的“感物”传统虽肇端于先秦,但其理论自觉至魏晋方臻成熟。宗白华指出:“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这一双重觉醒催生了“感物说”的诗学转向。萧驰认为,魏晋诗学将“情”提升至哲学维度,“感物”不再停留于物象摹写,而成为主体精神与宇宙万象的深度对话。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钟嵘《诗品》“气之动物,物之感人”等命题,皆指向情物互渗的创作机制。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更系统阐释了“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生成逻辑,为唐诗情景交融的巅峰成就奠定了理论基础。林庚的“盛唐气象”论即揭示:唐诗的蓬勃气象源于“情”与“物”的完美熔铸——充沛情感借自然意象得以具象化,而物象又因情感灌注获得生命。
严羽对宋诗的批评,恰从反面印证了唐宋美学的范式转型:“盛唐诸人惟在兴趣……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此论实则触及三个深层动因:第一,审美代际的焦虑。苏轼的一段话是广为人知的:“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这暗示北宋士人面对唐代美学高峰时的创新压力,迫使美学路径转向。第二,士人身份的转型。唐代科举重诗赋,造就“才子型”诗人的情感张扬;宋代科举重策论经义,塑造“学者型”士人的思辨特质。钱锺书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意味着唐宋文化从情本到理本的嬗变。第三,心态结构的重塑。北宋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使士人获得空前的政治参与空间,即便仕途受挫,优渥待遇仍保障其生活尊严。这种“进可兼济,退可乐生”的双重可能,催生出以“乐”为基调的审美转向。吉川幸次郎《宋元明诗概说》对此有精深的阐发:
以上说明,宋诗原本具有多角度的视线。大而言之,综观社会问题;小而言之,则深入于生活的细微处。进而如前一节所述,诗还力图表现哲学,从大的方面把握住人和环绕人的世界的状态来谈论。这是最为宏观的态度。从这种宏观中,产生了对人生的新的看法。我以为,这才是宋诗最重要的性质,并且是宋诗对过去的诗所作的最大改变。
所谓新的人生看法,是由于多角度的宏观而导致的对悲哀的扬弃。它的基石,是认为人生不只是充满着悲哀的态度。这一点使宋诗从过去诗歌的由来已久的习惯中脱离出来,过去的诗认为人生是充满悲哀的,并把悲哀作为重要的主题。
“大而言之”应该是说,庶族士人凭科举晋身,怀“先天下之忧”的淑世抱负,以天下为己任,超越了个人的得失计较;“小而言之”则是指,平民出身的经历意味着北宋士人关注被盛唐精英所忽视的日常生活,如王安石《烘虱》、司马光《和王介甫烘虱》、苏轼“但寻牛矢觅归路”(《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等诗作,皆将琐屑物象转化为哲学沉思。这种“化俗为雅”的实践,实为儒释道思想的创造性融合:既有庄子“道在屎溺”的玄思、禅宗“触目菩提”的观照,更暗合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处世智慧。宋人通过将哲理注入日常,实现了“诗与思”的深度统一,使“乐”不再囿于情感宣泄,而升华为历经沧桑后的理性超越。
北宋士人对汉魏以降“以悲为美”传统的突破,本质是哲学境界与生存智慧的革新。苏轼的“凡物皆有可观……吾安往而不乐”(《超然台记》),不仅是对日常经验的审美观照,更暗含存在论意义上的价值重估——当士人将目光从“怪奇玮丽”转向“餔糟啜漓”,便意味着对悲剧性人生观的消解。这种“乐”非简单的感官愉悦,而是历经宦海沉浮后,通过“胸中廓然无一物”(苏轼《与子明兄》)的精神净化,达到对现实困境的超越。其思想资源可追溯至儒家“孔颜之乐”的再发现:颜回“箪食瓢饮”之乐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成为士人调和“兼济”与“独善”的理想范式。朱刚说:“知见所及,在北宋中期之后,著名的士人几乎都曾谈到这个话题,可以说,‘颜子学’乃是宋代学术中一个颇具特色的领域。”即便是以政治家自居的苏辙,也在《答黄庭坚书》中感慨颜渊“无假于外而不改其乐”的境界,折射出这一命题的普遍性。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士人对“乐”的追求始终伴随着现实忧患。王安石变法失败后退居金陵,于《定林》诗中写道:“真乐非无寄,悲虫亦好音”,将政治失意转化为山水间的哲学领悟;邵雍以“安乐窝”自喻,宣称“乐天四时好,乐地百物备”(《乐乐吟》),实则是以审美纾解现世焦虑。这种“悲欣交集”的复合体验,恰如吴之振评王安石晚年诗:“悲壮即寓闲淡之中”(《宋诗钞·临川诗钞序》)——士人一面在奏疏、史论等具体的政论和文学中倾注“进亦忧,退亦忧”的济世情怀(范仲淹《岳阳楼记》),一面在山水、书画、诗文中构建“人生安乐处,谁复问千钟”(范仲淹《潇洒桐庐郡十绝·其四》)的审美领域。二程一方面说:“学至涵养其所得而至于乐,则清明高远矣。”这是体道之乐。另一方面又说:“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旁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程颢《春日偶成》)这是审美之乐。这揭示了北宋士人精神结构的双重性:他们既需以“道”“理”规训情感,亦需借“美”安顿身心。概而言之,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志于道”和“游于艺”。
这种张力最终导向一种新型的文化实践:无论理学家周敦颐“窗前草不除”的自然观照,还是苏轼“寓意于物”的书画理论,皆试图在“极高明”与“道中庸”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当王安石流连山水、邵雍醉心击壤、程颢观物吟诗时,他们本质上都在践行同一种生存策略——通过审美活动将日常经验哲学化,使“乐”从伦理命题升华为存在方式。这种“以美自遣”的普遍性,不仅重塑了士人阶层的文化性格,更标志着中国美学从“悲情叙事”向“乐感文化”的范式转型。
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时反对派的领袖,在新法施行时,退居洛阳,将自己的私人园林命名为“独乐园”,在《独乐园记》的最后,他详细描述了园林带给自己的快乐:“志倦体疲,则投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热盥手,临高纵目,逍遥徜徉,唯意所适。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独乐园’。”这是他政治的低谷时期,从他自称“迂叟”就可以看出他的心态底色是失意的。但在这长达十多年的时间中,一方面,他精心编纂史书(也就是今天的《资治通鉴》),通过“立言”表达自己的兼济理想;另一方面,通过园林,寄情山水,以美自遣。司马光在世人的印象中似乎是一位刻板、执拗的政治家和博学多识的史学家,但如果翻阅其文集,会发现他还有大量的诗歌,尤其是闲居洛阳期间,虽然其思想、艺术水平并不高,但其连篇累牍、反复吟咏的主题是一致的:闲适之乐。
既然这种“乐”是饱经忧患的,那就不是一种少年的轻狂之乐,更不是未经世事的浮浅之乐。程杰的一段话颇为精确:“‘平淡’之上升为最高的诗美理想,带有更多以理遣情,以理制情的理性主义性质,因而‘平淡’不同于传统士人之放逸而更倾向于儒者之适的平和萧散。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通向‘平淡’的路径却是不平淡的。在实际的创作中,情感的‘平淡’多见于历经磨难后的生命逆转或越过鼎盛期的投老赋闲。王安石、苏轼、陆游等大诗人几乎都经历过早期的豪健清雄,在其生命后期归于清旷闲远、自然平淡。可以这么说,真正的‘平淡’之诗属于人生的‘老’境。”
二、平淡美的思想基础:理
吉川幸次郎在《宋元明诗概说》中说:
在前一节所述的宋诗的平静,通过以唐诗作为比较的媒介而更加明确,这是宋诗重要的底色。同时这也是宋代诗人有意识地追求的东西。宋诗创始者之一的梅尧臣,在其诗集中许多地方都说到自己诗的目标是“平淡”。譬如: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所谓“平淡”正是平静的意思。过去的诗,特别是唐诗的激情,时或成为造作的激情,陷入陈套之中,使人感到幼稚。从以消极的动机对此进行反拨中也会产生平静。但有意识地追求平静,是以取得更积极的效果为目标的。即依据平静的心境,多角度地、周到地、细腻地把握和表现人世的多方面的情状。至少在梅尧臣的场合,这是一种愿望。
梅尧臣作为宋诗平淡风格的开创者,是没有疑问的。在吉川幸次郎看来,平淡的背后是平静,在我们看来,平静的实质是理性,也就是北宋士人常说的理。理与情相对而言,换言之,唐宋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由情转向理。程杰说:“唐诗主情,宋诗主理,这已是研习宋诗者的基本共识。的确,宋诗体现了对汉魏以来诗歌抒情传统的反思和反拨。”前文说平淡美的情感基础是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乐不再是“唐诗的激情”之乐,而是饱经忧患、历经沧桑的中老年之乐。其中包含了对人生、政治等的诸多理性思考与沉淀,也就是吉川幸次郎所说的“多角度地、周到地、细腻地把握和表现人世的多方面的情状”,所以只能是一种理性之乐。这充分说明平淡并不是单调的同一性,而是包含了各种异己性在内的同一性。
程颢《定性书》:“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这里既有庄子思想的影子,更是理学家自己的创见。它与范仲淹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一致的,都是强调坚守自己的内心,不被外物所左右。一方面,宋代士人地位提高,入仕机会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士人为了自己的理想陷入各种纷争,大多经历宦海浮沉,所以,他们既不会放弃对政治的认同,陷入绝望,也无法真正实现理想,需要确立强大的内心信念。
程颐在其一举成名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中说:“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仁义忠信不离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处语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则居之安,动容周旋中礼,而邪僻之心无自生矣。”这段话的要点有二:前半部分是对性情关系的阐述,性与情是一组紧密联系而又相互对立的概念,性善情恶,只有以性化情,才能学以至圣。上文说过,身处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北宋,士人大多经历过各种动荡、纷扰,不可能没有情感的波动。正是有感于此,所以,程颐从先秦儒家和佛教思想中汲取资源,提出以性(理)制情的方式,这也是对魏晋以来情的觉醒以至于泛滥的一种反拨。这段话的后半部分则更具时代针对性,“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虽然出自《论语》,但考虑到北宋士人大多都经历了朝升暮贬的宦海浮沉,程颐在写这篇文章时,也许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它之所以一鸣惊人,并成为此后理学的一个基础文献,其原因也许正在于大多数士人都有此经历,对此有“了解之同情”。苏轼与程颐素不相识,二人在司马光的葬礼上更是公开决裂,但苏轼晚年流放海南时,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然苏轼理解的“道”与程颐的性理有很大差异,但这段话却可以说是苏轼在历经数十年坎坷之后,对程颐“仁义忠信,不离乎心”观点的心有灵犀的一种回应。
北宋理学的勃兴,本质是士人群体应对时代危机的思想实验。王安石以“性命之理”重构道德根基,秦观为苏轼辩护时强调“性命自得之际”的优先性,皆表明内在修养已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核心。当“外王”理想因党争倾轧而破灭,“内圣”境界的追寻便成为必然选择。徐洪兴指出,欧阳修、苏轼等文学家通过“道”的实践,客观上为理学兴起铺就了思想路基。尽管欧苏之“理”偏重现实关怀,与程朱之“理”的形上取向存在差异,但二者共享的理性精神,恰恰构成唐宋转型的文化密钥——从盛唐的激情飞扬转向北宋的清醒务实。诚如论者所云:“宋学的根本核心是一种理性精神”,“宋代哲学、文艺的勃兴,政治中的民主空气,以及经济领域中产生的许多新思想,都是宋代士人的理性精神充分发扬的结果。”
北宋士人多为兼具学者、文人、官员身份的综合型人才,无论是学者的博学多识,还是官员的体察人事,都意味着他们不再是唐人般的高蹈浪漫,而是以务实、清醒的理性态度对待一切,包括政治、文艺。例如欧阳修,在被流放夷陵之后,唯谈政事。其在哲学上排斥谈天命、性理,一切本之以人情,同样是理性的体现。欧阳修的史学、文学、哲学大多是从现实出发,又回到现实,是为了解决北宋现实中的诸多问题。关于文章,他重视由“道”到“身”“事”,再到“文”的过程:“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关于经典,他重视经世致用:“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关于历史演变,欧阳修甚至轻天命而重人事。他说:“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这三段话反复强调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事”,也就是人事,是现实中的世事。由此可以看出,欧阳修一以贯之的是现实的理性精神。如果将这一点与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以及晚唐时期的李商隐、杜牧相比,可以清晰见出唐宋士人的转型。
这种理性精神在审美中有充分体现,苏轼流放黄州时,发现当地农民用的农具“秧马”简易实用,后来到了惠州,积极推广,并流传各地。苏轼为此写了《秧马歌》《题〈秧马歌〉后四首》等(《秧马歌并引》见《苏轼诗集》卷三十八)。这在此前的中国古代诗歌中并不多见,其根基还是理性精神。务实、理性是他们为官、为学、为文的基本特点。就为文而言,苏轼有很多充满理趣的诗文,如,流放海南时期,观看儿子与太守对弈,写有《观棋》诗:“空钩意钓,岂在鲂鲤。小儿近道,剥啄信指。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在寻常的下棋中,也能体悟到高深的哲理,表现出平淡随缘的人生态度。《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物有畛而理无方,穷天下之辩,不足以尽一物之理。达者寓物以发其辩,则一物之变,可以尽南山之竹。学者观物之极,而游于物之表,则何求而不得。……今道辅无所发其辩,而寓之于茶,为世外淡泊之好,此以高韵辅精理者。”即使是对于寻常可见的茶,也能“寓物以发其辩”,阐述“无方”之“理”,表现在审美上,当然是清醒而平淡的趣味。吉川幸次郎用“酒”和“茶”指代唐宋士人的差异,是十分合理的。
葛晓音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理趣”的生成机制:苏轼虽推崇陶渊明、王维的冲淡诗风,却通过“对人生‘一时’的珍惜”,将玄言诗的抽象理境落实为具体生命经验。这种转变的深层动力,正源自庶族士人的身份重构。随着门阀制度瓦解,科举晋升的儒士群体成为文化主体,他们既需以儒学经世,又需借文艺养性。有论者指出,宋代士人将文学追求与政治理想融合,最终催生出理性高度上的文学自觉。从欧阳修的古文运动到苏轼的“无意于佳乃佳”,从程颢“云淡风轻”的诗境到米芾“平淡天真”的画论,北宋美学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以理性精神调和“道”的崇高性与“俗”的日常性,使平淡美既承载着儒家的现世关怀,又闪烁着道禅的超越智慧。
三、平淡美的身份基础:士
唐宋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士的身份的变化。由于科举制的完善,庶族士人成为政治、文化的主导力量,科举制发端于隋,唐代已经重视,但并未成为政治的主导机制,“究其原因,一是唐代科举取士数量甚少;二是就内容而言,唐代科举尚未与儒家国家学说自觉地结合,使之成为政教合一有效的组合机制,所以对旧政府体制未能发生质的影响。”到了北宋,在确立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后,经过宋初数帝的完善,科举逐渐成为取士的主要手段。这种影响不仅是取士方式的,更是思想意识的。钱穆说:“盖自唐以来之所谓学者,非进士场屋之业,则释、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于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林继中敏锐地指出:“钱氏指出唐时‘进士场屋之业’不过是敲门砖,并不曾与儒家的‘修齐治平’联系起来。‘至是’,也就是到北宋,这才‘有意于’政教合一,将科举取士与推行儒教结合起来。开始这项工作的是范仲淹。”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开启的“庆历新政”,才真正确立了“宋型文化”,儒教是“宋型文化”的核心,北宋儒教的核心有二:一是“修齐”的理性精神,二是“治平”的兼济思想。
作为庆历新政的参与者,韩琦对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了解颇深,他为欧阳修所作的墓志铭中有两段话值得注意:“惟视奸邪,嫉若仇敌,直前奋击,不问权贵。后虽阴被谗逐,公以道自处,怡怡如也。”这段话又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北宋士人兼济天下、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思想的体现。后半部分欧阳修一再被贬,却矢志不渝,始终做到“志气自若也”。(《宋史·欧阳修传》)《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散文的核心就是“乐”,正如欧阳修自己所说的:“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唐代士人如韩愈、柳宗元等被贬时的哀怨是北宋士人所摒弃的。这是一种孟子“集义与道”的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孟子在北宋的“升格运动”并非只是理学家推崇的结果,而是北宋士人的整体取向。如果说颜渊的箪食瓢饮是退而守之的固穷之乐,孟子的浩然之气就是积极进取的阳刚之力。
韩琦为欧阳修所作墓志铭中的另一段话是:“嘉祐初,权知贡举,时举者务为险怪之语,号太学体,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预奏名。”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对于整个宋型文化的塑造,以及北宋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朱刚引用了韩琦的这段话,并加以评论:“北宋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权知贡举,‘时举者务为险怪之语,号“太学体”,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淡造理者,即预奏名’。此年登第者中有程颢、张载、苏轼、苏辙、曾巩、曾布、王韶、梁焘、吕惠卿、章惇等,几乎囊括了北宋中后期哲学、文学、军事和政治界最具代表性的一批人物,想来他们的应试文章都可以算得‘平淡造理’。”欧阳修被时人称为当代韩愈,韩愈的地位与欧阳修的推崇具有直接关系,但韩愈的古文,兼有奇崛与平易两种风格,相对来说,更偏重前者。所谓太学体,是在石介等人的引导下,发挥了奇崛的风格。欧阳修更重视平易自然的风格,所谓“平澹造理”,包含两部分内容:平淡是风格、手段,造理是思想、目标。欧阳修虽然很少被纳入理学家的视野,甚至遭到朱熹等后世理学家的批评,但从唐宋转型的角度来说,北宋士人的人格、思想、审美的整体发展,均与欧阳修等人的古文运动不无关系。从欧阳修对太学体的排斥和对石介险怪书法风格的否定来看,欧阳修并非否定石介提倡的“道”,二者在政治理想和复兴儒学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欧阳修忧虑的是这种险怪风格会影响到士人人格的塑造。欧阳修下面的一段话不仅适用于文学,同样适用于理学: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答吴充秀才书》)
身为“文坛盟主”,欧阳修反复强调的却是“道”之为本、为先,竭力反对纯粹的文学雕琢,这是唐宋文学观的一个根本区别,虽然古文运动发端于中唐韩、柳等人,但北宋有着更为明确的目标:复兴儒学。进而言之,更重视“修齐治平”。北宋的古文运动与儒学复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都以追求内圣外王为目标。内圣者,强调个人道德修养,是为“德”;外王者,重建儒家纲常秩序,是为“道”;表现在文章中,简而有法,是为“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道”“德”“理”三者是一体的。在欧阳修看来,只有“平淡”,方可“造理”。从历史发展的事实来看,无论是理学,还是文学,两宋的审美风格,都以平淡为最高境界。
如果说魏晋风流和盛唐气象分别以药和酒为代表,那么北宋人格则可以茶为代表。从魏晋时期的五石散到隋唐的各种丹药,它们大多具有令人兴奋乃至迷狂的效果。从阮籍以醉酒避祸、陶渊明以饮酒忘忧,再到杜甫笔下的《饮中八仙歌》,这些都堪称魏晋至盛唐人高蹈浪漫的典型表现。然而,到了北宋,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逐渐让位于儒学。由于科举内容的变化,北宋士人大多成为综合型人才:他们既怀有兼济天下的济世情怀,又具备博学多识的学术修养,更有道德律令在胸中的自觉。这意味着北宋士人的人格既不同于魏晋士人放言务虚、不问世事的风流,也不同于盛唐士人高歌理想、不切实际的激情,更不同于晚唐五代士人沉迷感官、流连花丛的感伤情调,而是一种理性、内敛的优雅与从容。这种人格特质催生了宋型文化的繁荣。从仁宗庆历到哲宗元祐,短短四五十年,却成为中国古代数千年历史中政治、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诸多领域群星闪耀的时期,这与北宋士人的新型人格密切相关。
王顺娣指出:“宋代诗学的‘平淡’范畴综合了传统意义上哲学、政治、伦理诸层面,其外延已扩及到人(伦理)、文(诗学)、道(哲学)三方面。在宋人看来,‘平淡’正是这三方面最高境界的体现。”这表明,“平淡”不仅是一个诗学范畴,也不仅是一个美学范畴,更是宋代新型人格的写照。北宋士人既在政治上积极入世,进亦忧、退亦忧,又在个人生活中追求世外淡泊之好的境界。以苏轼为例,“乌台诗案”后,他的政治理想受到严重打击,但他寄情于山水、诗词、绘画、书法,在审美上达到了一个高峰。对于苏轼而言,这是寓意于物的自我解脱和人格完善的方式。他对陶渊明的推崇也应从这个角度理解。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与苏轼的推崇密不可分。从苏轼大量的《和陶诗》来看,这些作品并非他文学创作中的上乘之作,但对于一生坎坷的苏轼而言,陶渊明旷达随缘、平淡自然的人格境界才是他真正向往的。在无法摆脱的政治攻击和兼济理想屡屡受挫之际,苏轼通过对陶渊明诗歌的唱和,实现了自我解脱、人格完善,也取得了美学上的巨大成就。苏轼对绘画的态度同样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被贬黄州时期,他因畏惧文字之祸而钟情绘画。虽然他此前多次论及绘画,但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将王维山水田园诗平淡自然的风格引入画论,从而奠定了王维在之后千年文人画史上无与伦比的地位。
书法也是如此。苏轼说:“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苟不至于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这与其师欧阳修的态度一脉相承。欧阳修说:“有暇即学书,非以求艺之精,直胜劳心于他事尔。以此知不寓心于物者,真所谓至人也;寓于有益者,君子也;寓于伐性汩情而为害者,愚惑之人也。学书不能不劳,独不害情性耳,要得静中之乐者惟此耳。”所谓唐人尚“法”,宋人尚“意”,这是书法史的常识。其原因固然有多种,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士人身份和心态的改变。北宋士人大多将书法等各种文艺创造与鉴赏视为完善人格、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既然如此,那么书法的创作与鉴赏过程,也是一种涤除躁动、纷扰,获得平淡、宁静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美已超越其本身,成为构造完善人格境界的途径。
黄庭坚是北宋谈论平淡美的重要代表。关于他的诗文平淡观,学术界已多有讨论。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有许多与平淡相关的语句。例如,《跋欧阳文忠公〈庐山高〉诗》中的“中刚而外和”,《与无勋不伐书》中的“混浊而志刚”,《次韵答王慎中》中的“俗里光尘合,胸中泾渭分”,以及《戏效禅月作远公咏》中的“胸次九流清似镜,人间万事醉如泥”。这些表述都体现了人格境界上的平淡。在黄庭坚以及北宋士人看来,平淡是对魏晋、唐代以来人格的超越,是“宋型”人格与审美的全新构造。
结语
北宋的平淡美在后代影响深远。从元四家的文人画,到董其昌关于绘画的“南北宗”,可以说,在很大程度是对北宋平淡美的继承与发挥。董其昌说:“作书与诗文同一关捩,大抵传与不传,在淡与不淡耳。极才人之致,可以无所不能,而淡之玄味,必繇天骨,非钻仰之力、澄练之功所可强入。萧氏《文选》正与淡相反者,故曰六朝之靡,又曰八代之衰,韩、柳以前,此秘未睹,苏子瞻曰:‘笔势峥嵘,辞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实非平淡,绚烂之极。’”这是将书法与诗文联系在一起,并直接引用苏轼的话,将平淡上升为一种近乎神秘的最高境界。清人邵梅臣说:“昔人论作书作画以脱火气为上乘。夫人处世,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后半句脱自苏轼,原本是论文字的,邵梅臣却将之用于“作书作画”,并进而扩展到人的立身“处世”,这就将平淡从审美范畴扩展到人格境界了。就诗歌而言,清初的王士祯主张“神韵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对北宋平淡观的继承与发展。“问:‘昔人云:辨乎味,始可以言诗。敢问诗之味,从何以辨?’……萧亭答:‘唐司空图教人学诗,须识味外味。坡公常举以为名言。若学陶、王、韦、柳等诗,则当于平淡中求真味。初看未见,愈久不忘。’”可见,后人充分理解了北宋平淡美的两方面含义:一是融合多样性于自身的同一性,二是一种名教与自然相统一、和光同尘的精神境界。蔡锺翔敏锐地意识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人把‘自然’和‘平淡’联系在一起,以‘平淡’为自然几乎可以说是两宋自然论的时代特色。”二者当然有区别,但宋人将中国美学史上源远流长、影响甚广的“美在自然”改造为“美在平淡”,这是一个值得充分思考的话题。这已越出本文主题,此处不作展开。
清末民初的严复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王国维认为,自宋以后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严复与王国维是同时代人,在回望数千年中国古代历史之际,都作出同样的判断。最早提出唐宋转型说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与王国维交往密切,与严复也有书信往来。今天我们重温严复等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说,平淡确实成为此后中国古代美学史乃至士人人格的主要特征。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唐宋转型当然不是完全割裂的,二者之间有诸多联系,北宋的开创建立在对前代尤其是唐代的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这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中唐到北宋,有诸多联系。杜甫、颜真卿、韩愈、白居易等人对北宋的重要影响也早有定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北宋士人是在对唐人的继承中通过创造性阐释,从而发展、成就了北宋文化。当代学术界对此已有充分关注,力主唐宋转型的钱穆说:“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然则治宋学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唐,而昌黎韩氏为之率。”本文主要着眼于唐宋转型视野下的平淡美,并无忽视或否定唐宋之间的联系之意,而是试图揭示:在门阀消亡、庶族崛起的结构性变革中,士人群体如何通过对前代文化的批判性重构,最终使“平淡”从潜流升华为主流,成为中国文化转型的审美路标。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姜子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