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陈继明的小说《敦煌》探入了敦煌的内核,绘出了敦煌的本相。小说通过“画师之眼”这一独特的叙事视角,截取时空交汇、临界的“瞬间”,展现繁复的民族史、家族史、个人史、文化史,描绘出历史内面具有景深的人间图像,摹写出充满世俗和生命气象的“人神共在”的敦煌。小说在层层嵌套的叙事视角、重重互文的镜鉴观照之中书写了“何以敦煌”的另一种精神,那就是以互文“辩经”为中心的敦煌的精神图式,在这对话映照中凸显的民间镜鉴,是从民间视角叩问庙堂,于历史背面观照有情世界,在质疑抗辩中进行自我追问和反省。
关键词:陈继明;《敦煌》;画师之眼;民间镜鉴;本相
作者张春燕,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兰州73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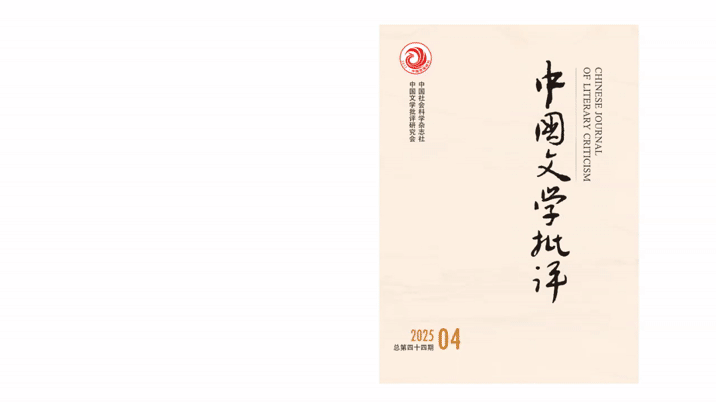
对于敦煌以及“何以敦煌”,我们在文化地理、政治历史、宗教艺术各方面都有着深入的探讨,建立了繁复的关于敦煌的意义体系。而在关于敦煌的文学书写中,井上靖的《敦煌》通过对敦煌藏经洞的想象,在宏大的历史架构中寄托着历史的深情和文化传承的期待;叶舟的《敦煌本纪》则书写清末民初之际的文化守卫,建构了诗气涌动、剑气纵横的精神图腾式敦煌;邱华栋《空城纪》中的敦煌书写,以抒情考古的方式,将七个洞窟中的宗教故事勾连普遍的人间信义。众多的敦煌书写,作者各有怀抱。陈继明的《敦煌》同样有别具一格的书写。小说以初唐为背景,以开窟为契机,在对历史的“变”和“常”的思考中,更深刻地探入历史的内面和人的精神内面,书写了具有俗世气象的敦煌。在画师之眼、小说家之眼、作者之眼的层层注视中,小说建构了敦煌的重重镜像,于镜镜相照中凸显敦煌的精神结构:对话和抗辩,这是陈继明的敦煌美学和生命哲思。
一、历史交汇处的敦煌之“变”
陈继明在《敦煌》中深入敦煌内里去触摸历史,在时空交错、虚实交错之间建构了关于敦煌的想象性文本。小说聚焦于历史的“变”,在时与势的涌荡中探寻历史内面,凸显的是民族、家族、个人在“变”中的境遇和选择。作者如何搅动叙事的
陈继明借来一双“画师之眼”。所谓画师之眼,是画师在认识世界、艺术取材、营构画面、表达意涵时的视角。小说详细写了雪祁如何画出“飒露紫”:“捕捉飒露紫垂首偎人的那个瞬间——丘行恭拔出箭,将脸贴向飒露紫的脖颈……昭陵六骏,唯独飒露紫,人也入了画,人马合一,难分彼此。”“画师要的就是一瞬间,最饱满、最感人的一瞬间,最真实,也最虚幻。”正是这个瞬间的临界感和张力建构了画面的时空、势能和意涵的层次。这一“画师之眼”是对小说整体叙事视角的映射。寻找和选择有张力的瞬间,在历史横断面的交错之间、纵向的变迁之间,在一种极度聚拢、交汇和临界之处安放故事,是《敦煌》时时在进行的匠心营构,也正是作家看取历史和世界的进路,在《敦煌》中呈现为对于“时空”的深刻理解和对于“虚实”的精微把握。
小说中的《天水村人户录》是精彩的时间和空间的“截取”,是虚,但有叙事的内在精确性。它包含着“交汇点”的张力,那惊天动地的短兵相接,被写得不动声色:“伏允三十九年夏五月。贞观九年五月初八。”一边是吐谷浑的纪年,一边是大唐的纪年,这是历史演变的真实,还有在对历史的理解中包含的空间认知:“黄山绿水/佛国沙场/地邻蕃服/家接浑乡/昔年寇盗/禾麦凋伤/四人扰扰/百姓遑遑/……”这是空间交汇的残酷的真实。“刀子放下了,那就把锄头拿好吧”,慕容豆变成汜丑儿,这是文明交汇、文化融合的状况。陈继明的《敦煌》,正是在这历史、空间和文明的交接之处,写冲突、撕裂和融合的过程,由此探入敦煌的肌理,展示历史巨变中真实的人间图景。
在历史的正面,唐太宗李世民派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集合多路大军讨伐吐谷浑,消灭慕容伏允。唐朝打通西域商道,“万国来朝”的峥嵘盛世已到,李世民的文治武功震烁古今、彪炳千秋。而小说家和那个画师更着力的,是历史的背面:“一个画匠需要走到朝代的背面去,需要看到只有你自己才能看到的那些东西。”于是我们看到,历史正面的一个轻轻“响指”,撬动了内面的地覆天翻。
一边是民族史、文明史:小小天水村蛰伏着吐谷浑人,他们大胆地进行着“活国”计划。时与空的交汇,建构出西北各民族的流动融合、互渗互生的历史,也剖开了爱恨交织的内核。小说以“慕容豆变成汜丑儿”作为民族交流互动的具象,以爱恨交织的男女之情作为文化融合的内在情感的建构,展示更深切、更有血肉感的“变”的过程。吐谷浑人慕容豆白天学习天水村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夜里梦境中真实地恐惧着“锄头”,刀子放下了,锄头却并不好拿,这是自然状态的非秩序性和文明的秩序性的冲突。
小说以画师之眼阅人述事,也由画师勾连了敦煌的艺术史。一方面,敦煌壁画风格也正在这历史节点上由清瘦向丰腴雍容转变,迎来俗世化和色彩化。小说一直将其作为重要的暗线,将历史载力和知识载力糅合,对这艺术史上的过渡时刻进行了精细的阐释和想象。另一方面,作者的确迷恋于敦煌佛窟里那些瞬间凝缩的时空所承载的关于有限与无限的抗辩:肉身的有限性才是艺术的起源。“既有天上宫阙,又有人间百态”“水乳交融”“人神共享”的壁画,以其有张力的、融汇的瞬间,建构出了敦煌内部冲突与和谐的美学意识、对话与互生的生命哲思,这是众流归源之处。慕容豆开窟记录吐谷浑民族的存亡和迁徙的历史,既是溯源,也是“设祭”,是此间的重要命题和隐喻。
以画师为具象的敦煌形成了“蛛网”,用无限的交叉的“结”承载历史的力,每一个洞窟都携带着一部民族史、家族史、个人史、文化史,每一个洞窟都有乾坤的重量。它同时在盘根错节中形成无数的空间,展示历史和人的重重镜像。小说不是在文治武功的层面建构敦煌的意义,而是在民族、社会、文化、个人的多元维度,寻找史笔和画笔叠加的交汇瞬间,寻找以“人情”为内核的历史的背面和人的内面,在重重交汇、碰撞中绘出敦煌真正具有景深的图像:撕扯和冲突,却在根柢上体现互渗、包容和整合。这是小说探入历史和人的独特视角,也是敦煌的本相之一。在历史之“变”背面凸显的敦煌,始终有着“不变”的内核。
二、世俗敦煌之“常”
小说以画师之眼作为看取敦煌历史之“变”的进路,也由其带领读者进入敦煌的内部,由画师之眼看物色之上的沙州城,看凝缩了时空、将有限化作无限的“不变”的千佛洞。千佛洞高悬而起的是佛光,却在每一个洞窟中收纳着各种“冤缠孽结”的秘密——以“天地同春、人神共舞”的景象和欢悦的内在节奏为载体,只因为敦煌的秘密,不是佛的秘密,是人的秘密。慈悲是人的慈悲,良知是人的良知,人对于生活的忠实庄严建构出来的恒常世界,是历史的真正骨骼和敦煌的内核,那就是世俗的敦煌和人的敦煌。
陈继明说:“我把敦煌当镜子,也把艺术当镜子,为的是照一照人间的图景,照一照男男女女的爱恨情仇。”照出“人间图景”“爱恨情仇”需要看透世俗的“天眼”,陈继明有观世察俗之眼,他把画师之眼和小说家之眼叠加汇聚于敦煌“人神共舞”的形构,因而小说就是作者从民间视角看世观人的镜鉴。他能够让抽象疏离的精神落下云头,幻化成鲜活饱满的凡胎。
世俗的敦煌首先是“过日子”。小说以慕容豆的视角看天水村人的生命形式:“慕容豆久久地盯着南边那些东倒西歪的老房子,继续想象着汉人的生活……他们有一整套过日子的方法……所谓生活,就真的是‘过日子’”。小说始终在凸显敦煌作为镜子的“看”的意义,也是“交汇点”书写的更深层内涵:互照中发现彼此,并确认自我。
作为画师的雪祁,第一次深入认识到的敦煌,是由风情潋滟的三娘子开始,他“被石榴红征服了”,从而看到有“颜色”的敦煌:千佛洞“有全世界最完整、最精彩的颜色”。小说从一开始就打破千佛洞“物外壶天”的图腾式想象,而还原其满身金翠,无限烟波。敦煌的“生趣”正由此而来。所以胜觉说,“黄金白银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我也很喜欢看见万物含情,人间有爱”。索如说,“千佛岩上所有的窟子里都是天地同春、人神共舞、富贵祥和的景象。我念经不多,但我从窟子里看懂了佛祖”。胜觉和尚是“佛心”,索如和雪祁是“慧眼”——物色是外相,而万物各秉其情,是世界共同的、普遍的根柢。
最能够体现世俗敦煌生生不息的,是充满了生机的女性形象。《敦煌》中的女性都是兼具“气”和“欲”的女性。比如,“足娘显然是一个心里有数的女人,温和的目光里暗藏着一股子烈气”。令狐琴在父亲死亡之际蜕变成人人称颂的女性,“韧到有侠气”,尤其不同于令狐家的男人们“执”中的颓丧。阿城说:“世俗间颓丧的多是男子,女子少有颓丧。女子在世俗中特别韧……韧到有侠气,这种侠气亦是妩媚,世俗间第一等的妩媚。”这就是《敦煌》里女性的“气”。
《敦煌》中的女性也是有着生命欲望的女性。跳胡旋舞的三娘子是持“火”之人,她像是萨福诗中的“不死的阿弗洛狄特”,令狐琴像是但丁《神曲》中永恒的贝特丽采,足娘像是王尔德笔下的莎乐美。小说写她们沸腾的欲望、不可遏制的生命力和强烈的自毁,活色生香的笔触糅合着通俗小说的气味,轻轻一点、生机淋漓,描绘出浓酽的人间情味的敦煌、流光飞舞的敦煌、人神共在的敦煌,摹得了真正的大唐的俗世气象。
鲜活旺健的人间爱欲,是民间和历史乃至文化的内在动力。小说家站在内部看敦煌,看到了敦煌的肉身,他于此给佛绘出“真像”,塑得“真身”。陈继明于这俗世爱欲中赋得满纸烟霞,并让爱欲带领小说和他的读者,从一种对于敦煌的固化的神圣情感中挣脱,从而实现了更有世俗生命气息的想象。
敦煌不变的另一重内核是“人之为人”和“自证为人”。小说以敦煌民谚“日月往西,水流往东”为全书提纲挈领,说的是天地本然:“这八个字无限接近此刻的天和地,人的语言和这个世界的真相碰巧一致。”千佛洞边上,一直和谐共生着狼窝和羊冢,这是《敦煌》最根本的天道,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气象。顾随评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陈诗读之可令人将一切是非善恶皆放下……风雷俱出,是唐人诗,且是初唐诗。”这是雪祁苦苦求索的大唐气象,也是作者赋予敦煌本相的更深层的意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
“与天地合其德”的人,身上涌动的是自然的能量,慕容豆身上奇异地混杂着新生和创世、残暴和温情的气质。他的残忍、磊落和悲壮,是《荷马史诗》式的残忍、磊落和悲壮,因他是自然节律中的人。令狐昌是“二天爷”,崖岸耿介、残忍孤洁,连死亡都只剩下干净如玉的白骨。小说本身的整体氛围即是放恣和隐忍、沸腾和静穆的奇异混合。慕容豆、足娘、贼疙瘩、令狐近知、三娘子、令狐琴、智忍花,都在一种奇怪的骚动甚至受虐倾向中,成为更庄严的人。每一个人都在人的内在激情状态中“失序”,但最终每一个人都给了生命最动人的致敬。生命恰如自然(无序)状态和伦理(秩序)体系初相交汇时的模样:神是人的模样,人本身也是神。这是整部《敦煌》内部的“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陈继明以此写出了自为的人。在这个层面上,他是敦煌的“点睛人”。
有着健旺的生命力的人恰恰是不完整的人,但他们有能力通向整全的世界。小说在这个意义上提示敦煌的精神内核是人的自证为人。因此,小说写人的最终选择,都写得非常动人。令狐昌杀子、赎罪、开窟,由颠倒梦境走向千佛洞,在羊冢中变成了清洁的白骨,这是“挑选死法”,是关于生命的清明:
下葬之前,大先生依例问:“令狐昌欠谁的账没有?”没人回答,大先生又问,“有人欠令狐昌的账没有?”有不少人都承认欠令狐昌的盐钱。大先生说:“债务两清,才能下葬。”于是那几个人纷纷掏钱还账……“两清了吧?”没人回答,于是可以下葬。
独利河边赤身来,莫高窟前脱缁去。这是质朴而贵重的人的世界。
贼疙瘩事发后可以选择逃离,“一直朝西走,就是高昌……但是,他的双脚一动不动……他心里有坦然,也有难过……他知足了,他决定留下来。他重新开始向前走。他要老老实实回到县衙去”。慕容豆们也可以选择逃离,“一切还来得及,很简单,翻过祁连山就是草原”,但是他们唱起了宿命般的《阿干之歌》,像歌中唱的一样选择了“留”:“于是,第二天早晨,一切照常进行。除了失踪者,其他人全员出动,按原有图纸修筑堤坝和引流工程,不再喝酒跳舞,集中精力干活。”
三、何以敦煌:互文“辩经”和民间镜鉴
小说在历史之变和世俗之常的交互映照中建构了敦煌的本相。以画师之眼截取交汇点,展示历史内面的人间图像,叩问的是人与历史的关系;以小说家之眼看恒常俗世中的人之为人,探索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而在叙事的更外层,是作者之眼在观照内部的对话和映照,让始终存在的对话,成为小说的结构模式,并形成敦煌以互文“辩经”为中心的精神图式。在根本上这是在互文映照中更深地探入敦煌,从民间的立场追问历史和人,建构庙堂与民间、人与自我的关系。
小说以纵向的层层递进的形式建构互文和对话,贯通着历史和现代、来处和归途。小说首先在叙事层次上形成了对话。《敦煌》以元小说的形式指示着文本内部的阡陌纵横和勾连生发:画师将真实的人和历史凝缩在一个瞬间,小说家“我”在废墟上想象和重建鲜活的人和历史;小说家“我”在想象画师的秘密,画师在想象供养人的秘密,他们都在“穷神变,测幽微”。层层递进的想象还显示在吐谷浑的命运中:慕思明和小说家在同一叙事层次上想象慕容豆的故事,而慕容豆则跟画师在同一叙事层级上,想象《阿干之歌》中遥远的民族起源。在往复之间虚虚实实,经由这重重关于真实和虚构、阐释和表达的互文,现代与传统也在游离聚合中互涉和交融。这是《敦煌》展示出来的迷人的“互文”。
小说中的那些补充性文本也以纵向叠加的形式建构了小说的互文对话结构。《阿干之歌》、《吐谷浑迁徙歌》、萨福的诗歌、敦煌民谚、“花儿”、小说家的日记、“马迷兔”废墟、《粟特村人户录》、《李世民入冥记》和《大云经》、《大云经疏》、莎乐美、忒修斯悖论……这些虚虚实实的“断章残简”,都参与到叙事中,叠加着每一条故事线上的叙事层次和语意层次,丰富着文本的指涉空间,也形成小说内部种种对话:慕容豆和慕思明、画师和小说家……小说始终在进行着穿越古今的“辩经”,在各个向度上形成对话和抗辩的声音;于虚实映照间彼此照亮、相衍相生,不断把小说的语意和寓意都延伸到更繁复的空间中。而其根本意义,依然是在彼此生发之间提供的《敦煌》内部的“民间镜鉴”,即在互文和对话中形成和凸显出来的观照历史和人的民间立场。
在这“民间镜鉴”的注视之下,小说中不时响起吐谷浑人故事的背景音——《阿干之歌》和《吐谷浑迁徙歌》。这是严峻的生存之歌,也是忧伤的宿命诅咒、漂泊体验中“如旅如寄”的悲绝,是具有“人类性”的对于自我来处的古老忧惧和哀叹;被掩盖的废墟、流荡的“花儿”,是关于死亡与爱欲的片段,有着某种精神母体的遥响;萨福的诗歌、忒修斯悖论,是“我之为我”的追问,是人辨认前身的符码……陈继明用这无数片段映照着他的敦煌,这些碎片都是敦煌历史的“指印”,它们在溯源中一点一点被照亮,衍荡出文本内部镜镜相照的巨大的“有情”世界,形成了与正史的互文对话,也不断深化着敦煌作为民间镜鉴的内涵层次。
我们不会忘记雪祁出场时是“观民风”的画师,接近于与小说起源有关的“稗官”。而“稗官”关切的是被正史遗忘或遮蔽的暗域甚至痛域。小说中的隐喻,正是那壁画之下的壁画:那隐藏了的真实和被淹没了的历史。壁画的外层是《金刚经变》,而壁画的内层是吐谷浑的民族史。小说最后出现的充满了“□□□”和错误百出的《李世民入冥记》,同样是精妙的关于创作的隐喻:用想象也是用“有情”的观照,去填补那些被遗忘、被遗漏、被抹掉的“真实”,这也是《敦煌》的民间立场的体现。“第三只眼睛”是质疑之眼、抗辩之眼,也是内面之眼、民间之眼。
在小说结尾处,作者故意以附录的形式把敦煌发现的《唐太宗入冥记》搬进了小说,给我们看敦煌作为历史以及文明的“备份文本”的意涵:《唐太宗入冥记》的核心就是将李世民“囚慈父于后宫”的隐秘大白于天下——以严厉的阴间审判、其实是民间审判的形式。这就形成了与《今上实录》的对照,对历史进行了补充和校正。这是虚构的故事,但却是更真实的历史和更真实的民间观照。
但陈继明的用意似乎还不止于此,他以这一附录对文本本身进行了嘲讽。他还是要问一问“人与自身”的关系。小说中,陈继明写到雪祁和李世民的大段对话,惟妙惟肖地仿写了崔子玉以“大圣灭族安国”代皇帝回答“弑兄杀弟”的问罪,以及想讨个官从而跟皇帝讨价还价的内心活动,俗常滑稽,满满的嘲弄意味:
他毕竟在敦煌待过两年,多少能够做到视声名为赘物,所以他马上就回答:“陛下,臣还是更喜欢留在您身边,多读读书,多画点画。”今上问:“真的吗?”雪祁说:“陛下,是真的。”他等着听今上接下来的话,只是今上的话令他心里一凉:“好吧,那朕就听你的。”
《李世民入冥记》中,在崔子玉无数次迂回试探之后,皇帝问子玉:“卿要何官职?卿何不早道!”令人捧腹又满含机锋。这是文本内部的“自照”,一种在“应然”与“实然”之间的断裂和自我消解。作者再次凸显他所说的敦煌的“镜子”意味,这是来自小说家的自我省察的镜鉴。雪祁作为连接庙堂与民间的人物,需要在这镜鉴前照一照。揽镜“自照”的还有慕思明,这个在废墟上寻根的人,成为真正在自我追问和辨识中深刻自省甚至自证其罪的人。他纵身一跃,却让人想起《水浒传》里鲁智深圆寂时偈曰:“今日方知我是我”。这句话照亮了所有人的所来、将去之径,慕容豆、贼疙瘩、令狐昌、令狐近知、智忍花都在这观照中。有“第三只眼睛”的雪祁最终变成了“独眼雪祁”,隐喻着的正是撕扯之后的归一。
陈继明说:“人如同直接生活在镜子里。敦煌是镜子,千佛洞是镜子。在镜子面前生活的每个人,同时是自己的‘终极关怀者’”。《敦煌》用层层叙事、重重互照、重重空间建构了无数互文、对话的镜子:在这镜镜相照之间、虚虚实实之际,形成了对历史的观照,也形成了人的自我追问和辨识。对照敦煌民谚说的“日月往西,水流往东”,小说开始的时候作者就给出了理解“敦煌”的答案:
甘泉水、独利河、宕泉河源源不断从东边流进来。和天下所有河流相反,三条河流不约而同一律西向而行……
水流往东,水流往西,是镜中彼此。这形成了小说内部对话的隐喻式表达。陈继明在《敦煌》中绘出的“敦煌”本相正是这永恒的对话性:小说一面从历史的交汇处着眼,绘出了历史变迁中敦煌的内在图景,另一面书写敦煌之“常”,即世俗精神和生的虔敬。历史变动中的互渗融合,世俗恒常中的生生不息,在彼此映照中凸显了小说的民间立场。正是这民间镜鉴观照中的忧患和喜乐,叠加出了敦煌的气象。而此间始终在场的依然是人,是人在永恒地追问和省察自我之“所是”和“应是”。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