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陈继明的《敦煌》以“历史的一隅”作为中西互动的想象支点,重述何谓大唐气象及其当代影响。小说主线“凿空”中西,辅线沟通古今,让唐代宫廷画师的成长故事与当代作家的寻根故事两相激荡,形成立体的叙事广宇。小说“从敦煌出发”,从文明互鉴、文化交融的角度反映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和主体性。
关键词:陈继明;《敦煌》;盛唐气象;文明互鉴
作者申霞艳,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广州5106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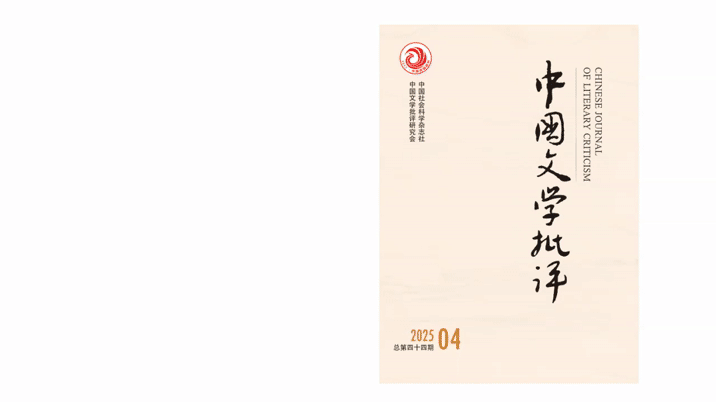
略萨在谈论《堂吉诃德》时提出“文学抱负”一词,而在井上靖之后创作同名小说《敦煌》的当代作家陈继明,则展现了自己的文学抱负。井上靖因《敦煌》享誉世界得益于当时敦煌学研究在日本的繁盛,而陈继明能够在新的时代重新讲述敦煌的故事,则得益于中国敦煌学研究的蓬勃发展。
改革开放后,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快速进程,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突飞猛进,逐渐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敦煌文化延续近两千年,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的珍贵史料。莫高窟的彩塑飞天、栩栩如生的佛像,藏经洞的典籍、绢画、文书,共同显现出大唐气象,成为当代文艺取之不尽的源泉。格局的开放、文化的包容、制度的创新成为民族文化繁荣的重要原因。文化传统不仅仅是文物和史料,更是深深地嵌入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陈继明在宏阔的历史坐标之上渐次展开叙事,深入探讨中西交流、文化融合、文明互鉴、古今贯通等重大课题。
一、祁希/雪祁:画师的成长故事
《敦煌》可以解读为宫廷画师祁希成长为“独眼雪祁”的故事。主角祁希生于家境殷实的商贾人家,自幼早慧:心慈、泪多、善感、长绘,未学会走路即会画画,记忆力、表现力俱佳,被初唐画师阎立本纳为入室弟子,悉心培育成为宫廷画师,协助起居郎褚遂良撰写李世民的起居注,编撰《今上实录》。祁希因擅长书画被委以现场采风之重任,以素描组画向皇帝汇报长安城内发生的奇闻轶事和殊方异俗。
当时的长安堪称东方大都会,印度人、波斯人、西域各族人,百鸟朝凤;商贾、艺人、僧侣、游侠各色人等聚集于此,每天都有新鲜事、每天都有奇迹,年轻的画师满怀欣喜。在画胡旋女的舞姿时,舞者的娇媚、速度与激情让祁希感到头晕目眩、真假莫辨。白居易有诗《胡旋女》,其中写道:“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莫高窟中驰名中外的壁画伎乐天就表现了胡旋女飞舞的曼妙感。在速度与激情、实与虚中祁希产生了官能的迷惑,打破了既往对图文关系的理解俗套。艺术创作中,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眼前的对象,还有流动不居的传统和主体变幻的心灵。
与胡旋舞一样令画师目不暇接的还有天竺和粟特人的幻术,技艺精湛叫人称绝。“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光徘徊,十色陆离”,受命皇上的欣喜感一扫而光,强烈而频繁的刺激让画师意乱情迷,心神恍惚。机缘巧合,祁希主动告别皇上西行,在李大亮的军队中担任随军书记官,见识了广袤的西北边地、战争的流血漂橹,战后来到心仪已久的敦煌。大隐隐于市,在沙洲城,祁希化名雪祁画师,隐没在沙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摆脱宫廷的光环、摆脱对权力的依附乃祁希成长的起点。
作为御用画师,“大传统”内在于祁希,初唐画卷随其慧眼从宫廷向西部民间徐徐打开。祁希对敦煌的初识从沙开始:一粒沙渺小而又深奥,蕴藏着天机。人类发明沙漏丈量时间,以此探寻时间的秘密。沙子将海滩与沙漠联系起来,将远在天边与近在眼前、浩大与渺小联系起来。关于沙,前人已经有了许多美妙的比喻,“一沙一世界”,辛波斯卡等创造了经典的诗歌。可见,人类总是从切近、微渺的事物中感悟生命的真谛。
对沙的深度认识改变了祁希作画的态度,他的笔墨与线条沙沙作响,仿佛与鸣沙山的沙呼应。风沙与驼铃的唱和中潜藏着历史的奥秘,亦寄寓人类的美好愿景。余秋雨在《莫高窟》一文中感叹:“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正是这奥秘、愿景让敦煌生生不息,让斑驳壁画中凝固的舞乐重新翩然、残卷间沉睡的文书再度飘逸。
敦煌之盛大、凡俗令祁希震惊。金币成为认识敦煌之丰富的视角,祁希收获的货币有罗马的金币、拜占庭的金币、波斯的银币,“这些钱币在敦煌是可以流通的,甚至更受欢迎”。金币具象地勾画敦煌贸易网络之广。无独有偶,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中对金币进行人格化的讲述:“很遗憾,这个世界是建立在我之上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稳定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罗马、拜占庭、波斯……“无穷的远方”由丝绸之路连接,沿路金币光芒闪烁。
为习得敦煌佛像画的精髓,一向凭记忆绘画的祁希“给自己定了条纪律:一律打格对临,丝毫不能走样,绝不加入自己的意图。这才发现,难度之大,远远超出他的想象。他以前有些轻看佛像,认为佛像多呆板、简单,一动手才知道,恰好相反”。这是对艺术内部规制和自由的辩证关系的实践。正如艾略特所言:“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是不断地牺牲自己,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天赋异禀的画家同样需要严格训练:缩短眼睛到手的距离,使心手合一,潇洒自由。创新从临摹中出,自由从限制中来。
与技巧并行的是内容表达,如何想象表现内容,千佛洞中的佛像融汇了画师对神的构思,也寄托供养者的愿景。雪祁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内心是否相信神话故事就是生活故事,能否将高高在上的佛想象为平常的身边的人!陈继明汲取《西游记》“神魔同源”的辩证法和汪曾祺《受戒》的平视视角。汪曾祺将和尚看成一个普通的职业,在书写寺庙空间时依然表现欲望、歌颂爱情。这部作品深深地影响了当代文学的理解力,扩大了我们对生活的感知力。
应慕容豆的请求打造吐谷浑族窟的时候,祁希展示了宫廷画师的视界和胸襟,摒弃狭隘的民族歧见,将心比心地理解慕容豆的复国梦,理解不同文化的冲突。最终,他将吐谷浑的生存史理解为一部迁徙史、生活史。求生是人类最基本的要求,具有根本的正义性。理解了吐谷浑的迁徙史,接纳鲜卑、羌、粟特、突厥等各个民族的差异性、特殊性,也就能理解华夏文化的内涵和大唐气象的边界。
第二次奉旨入敦煌要求毁灭吐谷浑的诅咒窟时,祁希听从艺术的律令,巧妙地将一层新的《金刚经变》佛像画覆盖其上,让诅咒窟得以保存。诅咒窟显示了审美悖论、灵魂的深以及艺术的“净化”。“恶”因其深刻而被严肃对待,形成艺术内部的辩证、形成艺术和人生的深度。
祁希对北魏《舍身饲虎图》的理解逐渐精进。食人乃虎的本能,理解齐物才能理解王子舍身的慈悲。对这种牺牲过于巨大、超过凡人的觉悟,祁希很长时间只能接受其为神话,而无法当成真实的故事来想象。胜觉以自己的心得跟祁希解释,让他理解了萨埵王子“宁愿以身饲虎,把自己变成一颗慈悲的种子,在未来世生根发芽”的精神。祁希听到胜觉讲起北魏时期,敦煌三次被柔然围困,而敦煌守军不屈不挠地守护的故事,若有所悟。祁希是在理解了这种献身精神之后才画出舍身饲虎的。这也是对老虎吃人进行弱、强置换来重新理解丛林法则,太子的舍身之举显现出人的高贵与慈悲。
与祁希违旨保存诅咒窟的情节并置考虑,就能够发现小说叙事的良苦用心——重估文明的价值。祁希将佛教画与具体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理解了何为匠心。匠人的心跳近在指端。百年前的指印与唐朝画师的指印叠合,十指连心、心心相印。最大的慈悲就是“用无与伦比的镇定和平静表达慈悲和牺牲”。这与柏拉图对善的理解异曲同工。精英信奉的“大传统”和民间习俗维系的“小传统”互相叠合,佛教所倡导的慈悲、救赎、宽恕,与中国文化传统崇尚的孝道、仁慈、义气合流。一种宗教能够在异域文化中传播光大,证明二者之间暗合,上至统治者下到普通百姓,都能认同其要义。
祁希的成长包含着艺术的深刻的辩证法,就像胜觉住持通过闭关来“跳出阶段性,看到不灭性”一样,祁希由佛像画跳出“大传统”,看到文化的多样性和具体性,看到不同文化的交集与融汇;并从具体的绘事上升到普遍理念,洞见善、洞见慈悲、洞见不朽。细细描绘家窟、族窟的建造,是从源头理解敦煌及丝绸之路。佛性、人性与动物性,在此交织出复杂、丰富、超越的灿烂景观。
当祁希成为独眼雪祁,他的视力受损,心眼却更为明亮。文学书写中几乎有个不成文的契约,许多盲人的形象如同先知、神,可以通灵。而被西域画师因嫉妒戳瞎一只眼睛的流言平添了雪祁的美誉,“令独眼雪祁成为所有神话、梦魇、传奇、幻象的一部分”。小说结尾,独眼雪祁带着令狐琴重返敦煌,整理藏经洞的文书,让各族文化奇葩在历史幽谧处争奇斗艳。
二、慕容豆/汜丑儿:文化差异与融合
根据汤因比提出的“刺激—反应”模式,文明往往诞生于适度的外部环境刺激。北纬30度一带环境适宜,因而文明高度繁盛,大都市林立。越往北,则生存环境愈加恶劣,生存的斗争就越激烈,也会强化人的斗志。人类的迁徙、流散亦会改造环境,并形成历史发展的合力。西北最大的限制是缺水,生命沿水而聚,沙漠深处亦成绿洲。水草丰茂的土地长期是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冲突的焦点。牧业需要大面积的牧场,需要随季节转场,跟随牧草迁徙,而农业需要耕田,需要稳定。迁徙和定居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各自的文化,差异与融合几乎伴随着整个人类历史,“文化规范不仅由它们所肯定和尊敬的东西构成,也由它们所排除、拒斥、轻蔑、鄙视、嘲笑的东西构成”。当然,冲突的过程伴随着互动与交融。
地缘政治决定文化伦理和身体政治的混杂性。丝绸之路上发生的商贸、军事、宗教活动、文化相遇背后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差异。游牧民族在身体的灵活度和熟练使用兵器上见长,借助奔马的速度在短兵相接时能够迅速胜出。但在长期适应干旱环境需要的耐力、社会秩序建设和文化治理方面,以慕容豆为代表的吐谷浑上层统治者又向农耕文明学习,熟读汉文化经典。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军事硬实力可以取胜,而从“长时段”看,文化软实力、文化认同乃最终的决定因素。文化是具体的生活方式的博弈与积存,“是在社会关系图中居于不同、有时甚至是对立地位的群体间的一种冲突,生产意义的过程(终究是文化过程)是一场社会斗争”。
吐谷浑人一度活跃于青藏高原,民歌中的“天空在下雪,我们在赶路”成为他们生存的写照。严酷的环境锻造出一种挥洒的生命态度,他们对名誉的爱惜超过生命。隋唐时期,吐谷浑政权受到吐蕃与唐朝四面夹攻,在这种历史背景中,慕容豆实施他的复国梦:霸占天水村与粟特村。历史地看,民族交往背后往往也伴随着一些差异和冲突。当吐谷浑人占据天水村后,他们速战速决,作为一家之主生活在死者的家中,换用他们的姓名,过原本属于他们的生活。
生活就像大熔炉,融化血和仇恨、爱与梦想。“一场大火中,他们这伙吐谷浑人才算是和两个村庄合而为一了。”丧生的二十五具尸体和烧死的牲畜混在一起,再也分不清哪块骨头是汉人的,哪块是吐谷浑人的,哪块是粟特人的。千户长慕容豆的儿子慕容风也丧生,彼此的血肉熔为一炉。此后经历的大洪灾将几百人的村庄湮灭,共同的灾难将他们永久地联系在一起。
历史上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漫长博弈从未间断。造房定居、驯化动植物是一种相对高级的、更为稳定的文明,但不可否认,游牧民族机警、灵敏,拥有旋风的力量,纵横天地间,其饱含元气的生命状态、不受压抑的生命力至今让人神往。2024年,根据李娟散文改编的轻喜剧《我的阿勒泰》之所以火遍全网,是由于镂刻于我们内心深处的游牧基因被唤醒。荧屏过滤了游牧生活的艰辛,草场、白云、骑手象征的轻盈与松弛,让被困在系统中的我们心向往之。可见,牧歌与田园的魅力同样经久不衰。
三、作家/人物:当代作家陈继明的叙事探索
陈继明是甘肃天水人,对故土的历史念兹在兹,散文《陈庄的火与土》表达了他的“恋地情结”。2007年移居粤港澳大湾区之后,陈继明从中国的西部移到了“南海边”。他见识了东西、南北巨大的地域差异,地大物博乃生活的具象。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他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鸣沙山。沧海与沙漠,别有一番感慨上心头。在写作《平安批》而收集素材和创作的过程中,陈继明悟到了何为“国之大者”,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互为镜像,全球视野中陆权、海权在不同时代的历史意义凸显出来。
下南洋、走西口和闯关东,曾是中原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式,背后包含着同样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亦伴随着故土之思。结合《平安批》来解读《敦煌》,便能发现陈继明的用心、用情:从边地出发与中心互动,从敦煌出发对话世界。阐释《敦煌》,我们首先要关注“讲述话语的年代”,是21世纪20年代,作家在“南海边”对初唐的敦煌故事进行重塑。“话语讲述的年代”是“贞观之治”——中华文化的璀璨之巅。
祁希/雪祁,庙堂“大传统”/民间“小传统”,融入了陈继明自身的艺术探求。《敦煌》内置当代不同族裔的“寻根故事”,与故事主体形成时空互照,古今激荡、虚实相生。作家陈继明将自己以非虚构的方式写入小说,2007年在大英博物馆查找敦煌流散的史料和文物,2016年对敦煌进行田野考察并书写日记为证。这种叙事策略既暴露叙事进程,模糊现实与虚构的界限,也隐喻敦煌已经深深地嵌入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敦煌文物的流散具有吊诡性:国外探险家对敦煌文物的掠夺破坏了莫高窟的完整性,却也从外部刺激了我们的文物保护意识,催生寻根之旅。
寻根故事中包含同事慕思明跌宕起伏的一生,少数民族的血液、对诗歌的浓厚兴趣让二人志同道合。自认为是吐谷浑后裔的慕思明对自己的来处魂牵梦萦,他在大西北寻根,渴望通过墓碑、壁画、文物等蛛丝马迹对被湮没的文化进行浪漫化重构;他出狱后南下到火热的改革前沿寻找出路,因成功讨债获得老板的信任,借钱给他从事房地产,大获成功。从教师、阶下囚变成商人,最后慕思明却在最具纪念意义的地点自杀,凸显文化记忆对个体的深远影响。
《西游记》是玄奘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更是修行的故事,是不断克服“心猿意马”的过程。西域一带险象环生,对怪力乱神的描绘展现不同文化相遇造成的误解和敌意、不同信仰相遇时的博弈。胜觉(他的名字本身意涵丰富,引人遐想)与祁希对佛教的讨论深入浅出,“下跪、磕头、烧香”这些仪式源于人类内心的需要。巫术、宗教与文学艺术,都是安顿人心的精神家园。佛教包含的因果律、扬善惩恶能够与普通百姓共情,亦与画家的内心愿景琴瑟和鸣。地方性的祆教、景教等也与此相通。
陈继明的文学抱负既表现在对大的文化观念的阐释上,也表现在理解生命的奥妙和宇宙的复杂性、天地万物的辩证性:“这个世界的川流不息、生机勃勃,永无止境,连改朝换代、血流成河,连战争、地震、瘟疫、灾荒也是川流不息和生机勃勃的一部分,甚至是更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三只眼睛具有超越性,超越地域观,也超越城乡的二元对立。从祁希到雪祁,画师的成长经过漫长的修炼:随军、卖画、观摩千佛洞、学习佛像画、修持……他对大唐气象有了全新的认识,对自我也有新的习得,正是这种认知让他成为比师父更伟大的画家,成为肖像画中无出其右者。画家的成长有技艺的部分、眼界的部分,更有心性的涵养。视野、襟怀和格局虽然无形,却能够深入艺术的根脉。
宏大的叙事抱负最终落实于对弱者设身处地展开的想象力。陈继明笔下的女子大都是美丽多情的、善良的,女性的“被看”和被动性也彰显时代的局限。在前现代的漫长时间里,弱女子毫无选择权,她们的空间是狭窄的、低沉的。令狐琴为了给亡父求一块宝地,被迫将身子给了同村的风水师;智忍花为了给病重的奶奶祈福,进了寺庙当尼姑。令狐近知的第一任妻子,在他离开的十多年中,因坚信丈夫仍活在世间被认为是疯婆娘,不得不改嫁;而远在怛逻斯的第二任妻子未曾获得叙事的观照。祁希的妻子虞月亦具绘画天赋,认为丈夫纳妾天经地义;令狐琴对祁希的爱感恩戴德。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无不是历史的囚徒、性别的囚徒。
《敦煌》的文化融合无处不在,大到公主和亲、小到“颠山婆”的随机结合,祁希与令狐琴、慕容豆与足娘、令狐近知与怛逻斯的寡妇、慕思明的婚姻都是跨族域婚姻,直接的文化融合让家庭成为文化共同体,当然也是具体的压抑结构。《敦煌》写出了性别观念对父权制的刺激,并发掘女性对历史的影响力,通过描绘女性佛窟供养人、女画师的参与,展现女性对宗教艺术的渗透。令狐近知随身携带萨福的诗,萨福是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诗人,一千年过去了,她的诗歌经由怛逻斯给唐代的东方汉子以情感疗愈。可见盛唐诗尤其边塞诗的恢宏气象,亦来自多种文化的渗融滋养。
四、敦煌/中国:地方性与普遍性
丝绸之路的魅力吸引着叶舟、雪漠、红柯、穆涛、王族等一批当代作家长期致力于西部书写。新时代以来,李敬泽《青鸟故事集》、刘亮程《凿空》、邱华栋《空城纪》、陈继明《敦煌》等力作吸引大家反观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以崭新的视角重述作为“历史的一隅”的敦煌。巴赫金在讨论小说形式时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创作想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便是确定一个完全具体的地方。不过,这不是贯穿了观察者情绪的一种抽象的景观,绝对不是。这是人类历史的一隅,是浓缩在空间中的历史时间”。关于敦煌,东汉应邵注释的《汉书》解释道:“敦,大也;煌,盛也。”敦煌见证了“地理大发现”之前“旧世界的相遇”,因缘际会,形成了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敦煌—吐鲁番一带成为“四大文化体系汇流地”,源源不断地为跨文化交流提供新鲜血液。
近代地缘政治学和文化形态学揭示西方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受到国家政治权力结构的深层影响,欧洲中心观的塑造为其海外殖民服务。早在经济殖民之前,文化殖民就开始了。在马可·波罗笔下,东方曾经是富丽堂皇、和谐有序的,引发西方人对东方的强烈向往,刺激了此后的“地理大发现”。到黑格尔、孟德斯鸠等思想家笔下,东方的形象开始被描述为神秘、落后、负面化,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20世纪敦煌学的产生、发展同样伴随着“鸦片战争的阴影”,西方中心观是西方殖民主义精心包装的叙事表象,而中国文化的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等观念,为世界文明提供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思想启迪。
萨义德的“东方学”细致地揭示了西方对东方进行的“他者化”叙述历程。针对美国主流的“冲击—回应”模式,柯文对以西方为出发点的研究框架进行质疑,他认为“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18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若干塑造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是中国的”。柯文的解释对西方固有的中国论述产生质疑。
年鉴学派以“地理时间”突出地理结构对人类历史的制约作用。全球史观强调对全球历史作整体观,不能将地方性与普遍性割裂开来,而应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差异,突出跨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旧世界的相遇——近代之前的跨文化联系与交流》以跨文化互动视角、翔实的史料描绘了丝绸之路上围绕商贸发生的奢侈品交易、技术传播、帝国扩张,以及我国与西域、印度乃至希腊文化传播、宗教交融的胜景。丝绸寄托着西方对东方奢侈品的渴望,长安则稀罕西域的马匹、宝石,以及来自印度的香料、欧洲的珍奇,阿拉伯商人及驼队恰好可以穿越大漠长途跋涉,镌刻着文化异质性的商贸活动促进宗教传播、思想交流和文化互动。
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两个古老的成语昭示中华民族改造环境的恒心。从“沙漠”以三点水为偏旁证实远古时期西北的沙漠可能曾经是海洋。人文与地理密不可分。世事流变,沧海桑田。中国古代地理边界是动态性的,边疆地区各种文化持续不断地碰撞、融合。胡服骑射、唐僧取经的故事长久地启发我们虚心向学。经过痛苦曲折的近代求索,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虚心学习、奋起直追,今天我们能够以平和心态与世界对话。我们的文学叙事也经历从扭曲的他者想象到展现中国真实形象的叙述转化,中国故事就是世界故事的重要组成。
井上靖的小说《敦煌》不仅引发了日本敦煌研究的热潮,也引发无数普通读者以朝圣的心前往敦煌参观。陈继明的《敦煌》从敦煌出发重绘大唐气象,纠正近代以来被西方叙事扭曲而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超越陆权/海权、中原/边疆的二元对立,展现出中华文化建设的自觉与自主。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