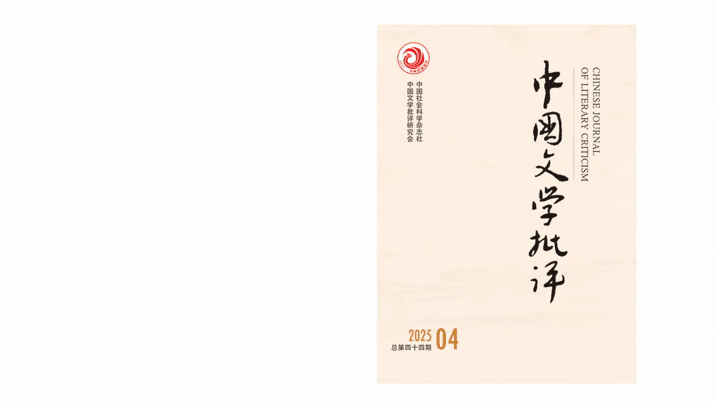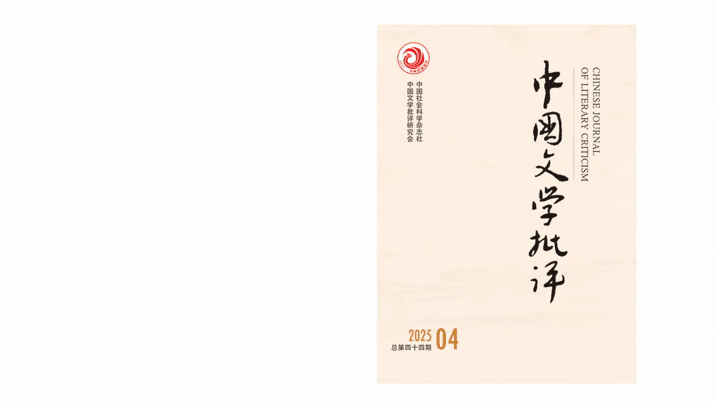
在百年中国文学的主题谱系当中,“历史”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词汇。它一方面指向历史的实存内容,即过往时空所存在的人、事、物、景等;另一方面指向历史的话语形式,即呈现历史的方式,如史志、艺术、文学、非遗等,“历史内容”与“历史话语”构成了历史存在的两种面相。在历史话语的诸多形式当中,文学充当着活跃的历史话语的构建者角色,二者呈现出同根共祖的家族亲缘关系,诸多神话史诗、传说野史、文人史志等,既是历史实践的遗存志录,也是民众情感的集体抒发,《左传》《史记》等的“文史同源”成为一种普遍的文体形态。但在现代文化的话语结构体系当中,历史和文学各司其职,它们一度上演着持久而激烈的争辩,分歧的焦点在于:是历史话语还是文学话语更能抵达过往生活的原初。两类话语体系的意趣取向形塑出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分野——“历史话语的分析单位是整体社会,文学话语的分析单位是具体人生。”操持历史话语将获得对政治、经济、科技、制度、阶级等整体社会情况的认知,但是,历史空间当中的人间烟火、日常温度、个体情感等均被遮蔽在历史主体叙事的逻辑裁剪当中;文学话语则聚焦于个体人生、日常纹理、爱恨情仇、悲欢离合、魑魅魍魉的生活化维度,虽然隐藏着陷入对历史生活展现的个人化之泥淖的危机,但它却能提供历史话语所欠缺的总体叙事逻辑的丰富生活肌理,赋予历史实存的“理性逻辑”以人性情感的“审美感性”。因此,历代作家往往执着于在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对峙当中,构建融通二者的文学叙事方法。
在对西域的历时性叙事谱系当中,敦煌有着“历史性敦煌”和“文学性敦煌”的双重属性。从日本作家井上靖的《敦煌》、韩国作家尹厚明的《敦煌之爱》,到许维的《敦煌传奇》、冯玉雷的“敦煌三部曲”、叶舟的《敦煌本纪》、徐兆寿的《鸠摩罗什》、邱华栋的《空城纪》等,敦煌早已转喻为一个强劲浮出历史地表的新地方文化圣殿,在获得被“他者”言说的资本之后,升华为具有诡谲历史想象力的“文化飞地”。正是在这样的敦煌叙事史当中,《敦煌》展示出陈继明深入而系统的文本创制和谱系革新的高度文体自觉,他对敦煌的神性想象进行了祛魅,对其人文景观进行了塑造,在典型人物和历史复现的塑形当中,完成了宏大历史话语与日常文学话语的耦合,构建出以“人物”/“事件”为轴心的打通历史与文学区隔的叙事范式——再现被宏大西域想象所遮蔽的敦煌事件肌理,重审被域外认知所湮没的敦煌人物肖像,以当代性视域激活悠远而蓬勃的敦煌历史人文精神。“《敦煌》建构的同样是一座‘当代’敦煌”,即重现事件、复活人物、发现精神,构成了《敦煌》叙事的三重空间。具体来说,《敦煌》创造性地将“文化交融空间”确立为历史叙事的总体图景,即将敦煌作为叙事原点,并将之放置于边疆/中原、游牧/农耕、宫廷/乡野、士子/乡民、人类/动物、儒家/佛家、历史/当代等经纬坐标当中,以扇形图谱的方式展开对敦煌多重面相的开掘与塑造。敦煌由此呈现出多重空间维度的共时叠加状态——它既包含着显在而宏大的事件复现(如地方深描、民族交流、迁徙流浪、战争冲突、族裔历史),也包含着隐在而日常的人物成长(如身份重构、艺术进阶、动物人化、人世忏悔、文化追溯),还包含着高远而深邃的文化价值的历史钩沉与文化践行(如艺术企慕、心灵救赎、伦理守护、儒佛崇拜、文化包容)。可以说,作者对敦煌这一“地方”进行了创造性的“赋形”,它不再是一个孤岛式的地理想象或历史凭吊。相反,它蕴含着幽深的文明密码、充沛的历史涌动和鲜活的生命热望。作者以虚构和实录、讲述和叙事、在场和离场、历史和当代的复调式文学修辞法,塑造出一个包蕴了多民族文化共生交往的文明交流、文化互鉴等多重内涵的中华文化历史空间。
一、文化交融与民族交流
当代文学的乡村叙事,通常聚焦于外在的现代性与乡村的自足性之间的抵牾,这成为作家展开乡村镜像书写的普遍文学语法。乡村文化在与现代性相遇之时的“守望自立”,往往会被视为乡村与他者激烈对峙之后的“隐形胜利”。这是乡村在纵向历史时间的现代性叙事维度。然而,乡村的现代性和乡村的民族性所隐匿的乡村历史化和乡村世界化,才是构成乡村演变的纵横动力。陈继明在《敦煌》中构建起乡村变革的融合的民族性叙事维度,开掘出乡村变革的别样历史——吐谷浑人借助于集体性的互动和生活化的交融,所引发的对农耕乡土日常生活情态的表达。作者对敦煌乡村历史的复现,一方面颠覆了乡土叙事所普遍遵循的“人的文化观念改造—人的日常生活变革”的演变模式,而构建起“人的社会结构改造—人的日常生活变革”的叙事路径;另一方面,小说僭越了现代性改造乡村文化母体所造就的“文化冲突—价值抉择”或“文化冲突—价值溃败”的叙事模式,而钩沉出西域乡土文化与他者文化对话所生成的“民族接触—文化接纳”或“民族交流—文化共融”的民族性叙事模式。这是对敦煌历史真实的重新抵达,也是对敦煌民族交流的生活展示,“内里隐含的实则是关于国家统一的情感愿望和政治想象”。而慕容豆及其吐谷浑部族与天水村之间的生活交往和精神交流,所表征的正是多民族文化之间的认同、借鉴和交融的历史图景。
首先是民族交往的历史化修辞。在历代的中国文学叙事经验当中,敦煌已然成为西域古文明的朝觐性想象符号,并被赋予神圣、幽秘、卓绝等美学修辞。《敦煌》则对这一地理美学想象进行了历史还原,即敦煌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叙事隐喻,它既浸润着日常生活的凡俗和浪漫,更充盈着西域多民族交流的自觉与活力。它一度充当着唐朝时期各民族交往的地理枢纽,也充当着中原与边疆之间文化互鉴的生活镜像。第一是民族交往的主动性。《敦煌》当中的天水村、吐谷浑、千佛洞分别被赋予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佛禅文化的文明象征符号。慕容豆在与足娘的日常交流中,始终表现出对边疆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认同”与“困惑”的双向审视,因此,他一方面信奉“仁义道德”,另一方面坚守“义存活国之想”。《敦煌》同样包含着作者对西域多民族交往历史隐喻的文化反思——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往,往往伴随着文化交融的多维效果,那些日常生活当中的诸种形式的互动交往,普遍被视为快速完成文化更新、获得身份安全、确立自我主体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主动性”是对古代西域多民族之间交流交往的历史洞察与行动修辞,也是对敦煌历史真实面相的复归与张目,由此赋予民族融合以壮阔而幽深的历史情感。第二是民族交往的生存性。《敦煌》在古代西域历史象征的叙事当中,还指向对西域各民族交往历史动机的勘探解密。慕容豆及其部族的乡村生活实践,一方面出自强烈的文化信念的集体践行,他们深谙部族的存在才是文化延续的前提,捍卫自主完整是吐谷浑人血脉传承的组织保障;另一方面是出于生存利益的权衡。而慕容豆等人在与天水村乡民的交往中,努力调适,学习耕种,这是他们对“逐水草而居”的迁徙生活所附带的不安定生存感的自我革新。人口繁衍、粮食生产、知识学习等,共同构成吐谷浑人与天水村“互动”和“嵌入”的内生动力。
其次是民族交往中的身份重建。身份认同指涉于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源自特定的自然地理、政治形态、生产方式、宗教信仰等,形塑出特定阶级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准则以及行为实践。这种人文性的文化传统及其所演变而来的文化范式,在历代的传承当中逐渐确立起其体系性和权威性,直至这种传统可能会演变为一种文化束缚。《敦煌》当中的个体之人在“静态”的多元文化生态格局当中,具有相对封闭的单元式的身份认同;但个体之人在“动态”的多元文化交流贯通当中,同样具有开放性的自我选择、自我更新、自我确立的重建可能。吐谷浑人与天水村乡民之间的相互交往无意识地形成了文化互鉴的并置格局,他们彼此获得了“文化平等”“文化互动”“文化交流”的生活可能性,由此开启了个体之人的民族身份的革新蜕变与认同重建。譬如慕容豆的身份蜕变源于吐谷浑人和天水村之间的生活融合,从饮食、劳作、习俗,到观念、兴趣、婚姻,他持续经历着从“游牧英雄”向“乡土农民”的身份转变。慕容豆拜见智忍花时听到禅语:“刀子放下了,那就把锄头拿好吧”。这让他感受到了生活与文化融合之后身份构建的方向、希望和信念。可以说,慕容豆与天水村的交融,是他的“现世理性认知”;但对他来说,长生天的歌谣、马背上的驰骋、迁徙者的浪漫,同样是他的精神生活和生命寄托,他无法决然放弃自由激越的“生活感性放纵”。于是,生活情态的耕读农民/精神漫游的草原英雄,成为慕容豆身份的悖反性存在——前者的身份是出于生存之道,后者的身份是出于精神渴望,这也成为慕容豆在开启身份自我革新时的价值共存,但正是这种生存和精神的身份共存,构建起他的新的“交融性”身份。而足娘同样经历了身份的重构。在她与慕容豆的日常生活当中,后者所展示出的生命激情、自由坦荡、张扬豪迈等文化性格,与天水村人的恪守道德、崇尚隐忍等形成显豁的文化参照。吐谷浑人和天水村的文化互动和民族交流,促成足娘文化性格的嬗变——足娘的热烈、主动、激情,展示出兼具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自由、至真、充沛的生命姿态,这是民族文化交融的肌理革新和生命效应。
最后是民族交往的文化价值共建。多民族之间的交往,必然经历文化价值体系之间的重组和聚合的漫长过程。可以说,唯有完成民族之间文化价值的共建共识,才是实现文化融合的前提。民族之间的文化价值共建是一个重大的实践命题与生活命题。《敦煌》的精妙与深刻之处在于,作品借助于慕容豆和足娘之间烟火生活的日常纹理,一方面揭橥民族交流过程中所必然面临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在慕容豆和足娘的情感互动当中,表现出生活和文化价值共建的可能性维度。第一是家国情怀。无论是吐谷浑人还是天水村乡民,都有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信念。第二是英雄主义。粟特村大火在吐谷浑部族和天水村的融合过程当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正是慕容豆及其族人在危难时刻对天水村乡民的英勇拯救,不仅在相当程度上消弭了吐谷浑人和天水村乡民之间的文化罅隙,而且他们的英勇无畏和利他献身的英雄主义,与传统文化当中的仁爱侠义精神完成了生活化的共振与应和;最重要的是,它们真正以日常生活的行动肌理,表达了惺惺相惜、命运与共的融合形态。第三是原乡主义。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都有祖宗崇拜的原乡意识,西部高原不仅是吐谷浑部族迁徙流浪之地,也是唐朝文化甚至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可以说,敦煌这里存在着多民族的血脉,而共同的原乡高地也使各民族具备了消弭文化隔阂、共建家园的可能。第四是人本主义。民族交流中的文化价值共建,归根到底需从“人”出发,以普遍的人心、人性和人情作为通约基点,坚守人的尚善至美,呵护人的高贵情感,这是构建文化价值共享的基点。譬如足娘对天水村的守护,饱含着她对与慕容豆的夫妻之情和人性之爱的眷恋与认同。第五是生命主义。超越文化差异,在生命本体的层面构建对生命神圣的呵护、对生命价值的敬畏、对生命尊严的捍卫的文化共识,是民族交往的重要文化价值公约。慕容豆、令狐昌、贼疙瘩、李世民,以及当代叙事者“陈继明”,对由于自己的信念、角色、使命甚至是无意识的行为而导致生命逝去的心灵忏悔,无不表征出他们对生命主义的坚定秉持和价值崇尚。
二、使者伦理与文化行旅
敦煌作为文化地理载体,呈现出一种结构性和相对性的历史景观。从文化结构性而言,敦煌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空间场域,也是多民族部落繁衍生息的生活场域,多元民族文化的共存形塑出其以“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互交融为底色”的世界认知——他者或远方皆为异域,“昆仑山居中,是世界的脊梁;其下是中原,也就是滋养万物的沃土”。对于西域各民族来说,他们既有着总体的文化认同性,但也存在总体性内部各文化体之间的角逐,生成多民族之间的生态圈层秩序。但相对而言,西域往往被赋予更多悖反性的历史修辞,因此,很长时间以来,西域和敦煌丧失了自我呈现和自我表达的基本话语能力,只能成为人们认知当中的边地,留存于他者被动的言说当中。这是对西域和敦煌历史的遮蔽。小说《敦煌》则以“文化行旅”为叙事视域,开启对敦煌历史本真存在的主体言说和自我表达。
小说赋予主人公祁希(后改名雪祁)以“使者伦理”的叙事功能,一方面他具有展示和言说中原文化的话语能力,另一方面他还具有体验和彰显敦煌文化的言说能力。他借助于“西行学艺”的行旅流动方式,不仅赋予敦煌以文化主体的言说权利,对敦煌进行了历史的重新发现和还原正名,而且也激发出开启中原—西域之间文化交流的自觉,完成了对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互鉴的裁定和参悟。敦煌所蕴藏的文化精髓,凝聚了边疆多民族生存智慧的要义,同时也饱含着中原乃至世界性因素的文化奥义。这一空间不仅可以视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而且构成了对中原文化的一种赈济和互补——以敦煌为典型的西域地方文化具备了与中原文化对话的条件;从敦煌作为“文化互动”的想象性符号视域而言,其地方文化的交融性甚至具备了超越中原文化传统的美学分量。
首先是中原士子身份的守望与践行。对异域文化的发现、体验和判断,总是从自我中心视域展开,它既赋予观照他者以相对稳定的价值视点,也赋予文化发现以确定的价值参照。对异域文化的言说效应,或者是再次确认对自我中心的认同,或者艰难转向对他者文化的归顺,或者是以辩证法思维确立“各美其美”的价值观。陈继明的《敦煌》则构建出超越上述三种模式的“文化参照—文化再造”的文化互动观,即以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和民族交往为基体的使者伦理,而“相对国家机器与既定辖域而言,战争机器与游牧方式均有破除既有状态,在差异与重复中不断逃逸或生成新的状态的性质”。使者伦理赋予祁希以唐朝文化的使者身份自觉,尽管他的西行漫游是出于对宫廷画师角色的厌倦、对敦煌异域美学的欣羡,同时兼备了解民风、搜集信息的政治使命,但是,在他与西域各民族的日常生活和画艺之道的主动交往当中,祁希始终保持着对自身所附着的唐朝文化的使命自信。譬如,在三娘子的身体上作画引发其他西域女子的跃跃欲试、祁希中原风格画作在西域市场的畅销、胜觉和令狐昌对祁希唐朝士子身份的尊重推崇,甚至他对西域女子身体的微词,无不彰显出他面对西域日常生活之时的坚定士子身份认同。或者说,即使祁希身处西域多民族文化的浸染当中,他仍始终葆有对唐朝士子的身份认同,譬如他对李世民纵横沙场、开辟盛世的感佩礼赞,对其施仁德、行仁政的德性敬仰;他对妻子虞月的眷恋尊重、对师父阎立本的艺术敬仰、对中医文化的迷恋信任。更为重要的是,当他被西域壁画艺术所折服,当他沉浸于敦煌风土人情当中,当他受命为李世民破解石窟诅咒而第三次返回敦煌并定居于此之时,展示大唐气象、彰显王朝气魄,始终是他的文化热望和政治使命。而他对中原家国的坚定认同,最终完成了唐朝故事与西域壁画的艺术再造,即东部与西域这两类异质地方文化,在石窟壁画当中实现了重组新生,“风景也会受到自身与非风景之间关系的影响而进行内部聚焦和组织——比如说,一个有着英雄行为的人物形象”。因此,祁希的使者伦理实践,是要积极发挥在中原文化和边疆文化之间的文化沟通作用,始终呈现为对家国政治使命的恪守、对中原传统文化的传递、对王朝盛世的彰显;同时,又保持对西域各民族文化的尊重、景仰和汲取,并从内在的思维认知、文化观念,到外在的积极行动、艺术融通等多重维度,完成二者的交汇与互融。这是祁希使者伦理和使者实践的重要含义。
其次是异域美学景观的发现与震惊。祁希所秉持的使者伦理,赋予他始终以大唐文化作为主体观照视域,并由此展开对他者文化的审视判断;但是祁希的士子伦理,以及这种身份伦理所自载的艺术进阶渴望,又消解了他以唐朝文化视域进行审视判断所可能附带的文化偏狭。于是,在“交流互鉴”的敦煌场域当中“凝望、发现、体验”,就成为祁希作为艺术家的文化观照实践。在小说《敦煌》当中,祁希对千佛洞壁画艺术的态度经历了从懵懂不解到惊艳钦羡再到膜拜敬畏的艺术参悟进阶,这也是他逐步突破文化中心主义,而开始具备文化多元主义或文化交融观念的一种经验转换,直至他发现并震惊于千佛洞壁画艺术的智慧、创新、博广的画艺之道。譬如他对颜色的体悟、对刺孔法的发现、对佛陀禅意的自悟等,使千佛洞成为自我艺术修养、自我心性境界提升的艺术启蒙物象。这是他作为使者的角色和责任使然,也是其作为艺术家的文化开放性投射。可以说,正是祁希及其所携带的中原画艺之道与敦煌壁画之道的相遇,完成了祁希艺术生命的第二次启蒙与成长。与此同时,祁希的使者伦理功能同样开启了他对西域和敦煌景观——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发现与体验,譬如鸣沙山的神秘、贼疙瘩的驯养蛇、大漠深处的诡异、骆驼萨仁的通灵、黄羊的死亡、墓冢的仪式、狼族的人化、狼族与令狐昌的生命相依等,但对于祁希来说,对西域的震惊更多来自对敦煌之“人”的发现。较之于三娘子、智忍花、虞月等,令狐琴是他最重要的发现与信仰。祁希的妻子虞月自载文化的同质性,个体生命的情感奔涌和生命释放更多让渡于传统礼制下夫妻相处之道的恪守。与之相反,三娘子则是西域市井文化的代表,妖娆而热烈,与祁希所自持的士子文化审美之间有疏离。祁希与之只是上演一场从猎奇惊艳到放逐分别的“始乱终弃”的情爱悲剧。智忍花则是佛禅文化的代表,她对祁希实施的身体伤害,不啻是一场绝望地反抗礼制压抑的乖戾而疯狂的行动。对于祁希来说,令狐琴之所以成为他最欣赏的女性,甚至为和令狐琴结合而不惜与三娘子分别、向结发妻子虞月求情,正是因为令狐琴所体现的敦煌文化的交融性——她负载着西域与中原、游牧与农耕、士子与民间、礼制与自由、节制与率真、内敛与勇敢,甚至男性的刚武与女性的柔媚相互叠加的文化性格和人格合体。这是祁希对令狐琴所承载的人性魅力和文化美学的震惊与发现,是祁希对自我固有审美认知范式的革新与突破,也是他对西域文化交融的美学、伦理、人格、性情、心性的重构和确认。祁希将令狐琴绘入洞窟里的壁画,不仅是将令狐琴及其家族的故事进行历史画录,更是宣示出祁希将令狐琴确立为时代、地域、文化的人物美学范式,在完成生活人物向艺术形象的转换之时,也昭示出民族交流语境下所形塑的人物之美和艺术之美的和谐与永恒。
最后是文化敦煌空间的捍卫与信仰。陈继明在《敦煌》当中,一方面将域外想象的敦煌进行生活化的赋形,既展示出敦煌多民族交往的历史修辞,也雕刻出敦煌各民族文化交融的艺术瑰魅,敦煌被遮蔽的历史悖反面相由此获得了自我言说与自我表达的能力。另一方面,他还以文学形象的方式,深入开掘作为文化地理空间的敦煌,表现它对生活于其中的芸芸众生所具有的精神价值、情感价值、心灵价值和信仰价值。祁希所操持的使者伦理,不仅包含对边疆和中原不同艺术美学的互鉴汲取,譬如大唐气象与吐谷浑洞窟壁画的融合,千佛洞的画艺之道与中原唐朝绘画体系的互嵌等,而且包括对文化西域主体性的正名。譬如祁希与李世民的对话,实则是其使者伦理的话语践行,开启了李世民对于西域和敦煌的重新认知。从西域与中原、西域与世界的地理关系,到西域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关系,从敦煌历史的战争动荡、苍生劫难的描述,到西域佛教的生成兴盛和生活功能的释惑,祁希一方面履行着唐朝使者的政治伦理,甚至不惜以忤逆之言进谏李世民,以期君王能广施仁德、惠泽西域,这是他作为使者对苍生苦难的生命悲悯与行动拯救;另一方面,祁希也生发出对苍生的悲悯、对人世的虚无、对大道的体悟,他作为使者的体验最终转化为对敦煌文化的坚定回归,并将敦煌作为他的文化根脉、精神家园、心灵寄托、生活信仰的圣地。而祁希和令狐琴定居敦煌,并用余生整理搜集文书,正是对精神文化圣地、对西域浩瀚文脉、对中华文明根祖的信念守护与捍卫实践。
三、伦理梦魇与生命诗学
敦煌空间中的多民族交往互动格局,衍生出多民族伦理体系的并置与参照,形塑出对各自伦理观念和伦理实践的评价话语。无论是游牧民族抑或农耕民族,个体对所属社会、政治、族裔、阶层等伦理法则的恪守,是保障社会机制、权力实施、阶级关系、个体生活正常运转的经验法则,通常的评价话语是“遵礼而行”;与此同时,在现代文化的视野当中,诸多礼制往往存在对人性的压抑、对人情的压制、对人心的压迫,重礼而轻人成为诸多礼法中的普遍症候。《敦煌》一方面聚焦于多民族交往交流的文化空间,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对各自礼制恪守的生活效果,以文化现代性展开对各自礼制的参照与反思;另一方面,小说以人道主义视域,在发现和演绎人的心灵荒芜、存在孤独和生命沉疴的同时,也在重构个体乃至民族的情感、心灵、精神以及生命的返乡之途和皈依之道。“精神离散—生命寻家”的隐形叙事模式,既赋予人物群像一种悲怆、凄凉而自省的美学气质,也让小说人物普遍呈现出丰盈、高远而超拔的人生姿态。
首先是自足伦理的情感迷狂。民族文化伦理不仅是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隐形约束,而且以隐秘的“因—果”民间惩罚机制,保障着伦理体系的奏效与延续,当个体偏离文化伦理的规约,所接受的不仅是阶级群体的惩罚,而且将经受自我良知陨落的责难。小说《敦煌》当中的悲剧人物,几乎都因游离文化伦理机制而陷入现实、心灵和情感的迷狂沉沦。令狐昌出于个体对官府征兵政策的反抗,或者说因为对子女亲情价值轻重的世俗评估,亲手杀死了傻儿子令狐近勇,维系了“二天爷”的个人虚名,却践踏了父子亲情伦理的传统礼制。贼疙瘩为了个人求生而背弃乡土伦理、民族大义,投奔慕容豆并杀害汜文胜,终究招致律法严惩。慕容豆的求生行径同样违背了万物有灵的天道观,心灵的自责使他只能以营救乡民和敦煌开窟等方式获得精神抚慰。令狐近知十多年未在家族尽孝,且又未恪守战争殉国之道,忠孝两难全的俘虏身份和不孝身份,使他失去了马营乡民的尊重而游走乡野做骟匠。智忍花违背佛教戒律,因嫉妒令狐琴与祁希的世俗恩爱而伤害祁希,既让自己的心灵万劫不复,也经受了生命的悲凉谢幕。《敦煌》一方面对诸多个体背离民族伦理规约的动机及其后果进行了“因果惩罚”的叙事设置,另一方面也同情与悲悯个人欲望受到压抑的伦理越轨者。这种伦理并置的悖反式存在,既是西域多民族文化伦理共生交汇的隐喻,也表征着伦理的多元化对既有单一伦理体系的隐形解构,直至确立起具有文化交融属性的生存伦理法则。因此,在作者冷静的去道德化的叙事基调当中,尽管他们有违伦理规约,但并未彻底泯灭人性,在个体生存、善恶并存等生活情态当中,作者消解了从单一视域对人物进行道德审判的坚定与明晰,展示出文化交流语境当中“人”的生存的无力、妥协和羸弱,演绎出西域多元文化场域当中“人”的生存的历史真实,以及这种生存选择的历史宿命。
其次是个体忏悔的心灵救赎。在传统文化语境当中,违背民族伦理规约的个体,一方面将经受民族群体的道德或生活惩罚,另一方面,个体也将陷入沉重而撕裂的心理枷锁当中进行反刍式的灵魂拷问——忏悔是人对自我伦理道德意识本能的反观和觉醒,忏悔也是进行自我意识与行动重构的内驱力,它或者导向对外在他者,譬如宗教的信任和皈依,或者导向对现世人生的拯救和弥补。《敦煌》具有相当显豁的“忏悔美学”和“忏悔精神”。这种忏悔既生发于人的世俗行径对自我价值信仰的背离,也生发出人对心灵沉沦进行积极救赎的行动。譬如慕容豆与天水村的“交往”、令狐昌对令狐近勇的“冷酷”、令狐近知的俘虏标签和骟匠行径、贼疙瘩对汜文胜的“残忍”、李世民对兄弟的“阴谋”,甚至“陈继明”因讲述莎乐美的故事而导致慕思明殉道的忏悔等。同时,这种忏悔普遍生发于伦理规约的恪守与他者自由的尊严之间的抵牾,并以“生命”作为矩阵焦点:慕容豆与天水村的“交往”是为了复国、令狐昌的“冷酷”是顺承国家征兵号令、令狐近知在令狐昌离世后的“漫游”是证明德孝礼制的奏效、贼疙瘩的“残忍”是报恩慕容豆的赦免、李世民对兄弟的“阴谋”也是着眼于王朝的传承兴盛。以偏离民族伦理、漠视个体生命,去捍卫世俗生存和家族传承,这是他们普遍遭遇的超越善/恶判断的伦理道德困境。而他们纾解这一道德困境的忏悔方式,就导向了现世的行善尚善——或者借助于生活化的行动实践,来完成心灵的救赎,如慕容豆对足娘的挚爱、对天水村的善治、在火灾危难时的勇武,令狐昌对白鬃狼生灵的生命守护,贼疙瘩对祁希的忠诚与敬仰,李世民的施仁政、善亲民的仁德盛世的开创;或者导向对外在艺术性和象征性“物象”的投射、寄托和信仰,来完成心灵沉沦的拯救,如令狐昌家族和慕容豆在敦煌的开窟,这是他们向万物生灵的忏悔,也是他们自我警醒的镜像,“艺术已然承载‘上帝’的某些功能了,由此开启了艺术宗教化的进路。艺术的宗教化实则是人的能动性、自由自觉的实践意识的逐渐苏醒”。这种救赎既包含着以石窟物化的方式,对家族史、民族史的秉笔图志,它同时还是一种将家族、部落、民族的历史义举,向同时代的外来者和后世的继承者宣谕“人本主义时代到来”的图画声音。
最后是精神漂泊的生命皈依。敦煌作为“文化交汇空间”,为多民族文化的共存共生提供了完备的地理场域,但这种交往流动性也赋予万物生命以普遍的漂泊感和动荡感,诸多个体生命必然面对非封闭性的文化蛊惑,甚至会呈现为个体身份的深刻而内隐的分裂。因此,《敦煌》当中的文化西域一方面为个体生命提供了共时体验多元文化的选择机遇,从而能够实现自我伦理认知和价值观念体系的持续更新,在体验和选择当中完成个体精神漂泊的文化皈依,并不断赋予个体生命以蓬勃持重的生命安守;另一方面,个体生命身处多元文化场域当中,还可能激发自身渐趋湮没的文化认同的生命渴望,并对附着于个体生命的诸多外在蛊惑进行自我净化和提升,向内谛听本真生命的召唤、遵循自由心灵的启悟,向外放逐人世凡俗的聒噪、荡涤伦理规约的束缚,最终完成个体生命向彼岸的抵达。小说所营构的西域和敦煌生活普遍氤氲着“在路上”的悲情诗意色彩:慕容豆融入田间劳作生活的行动,并未消解他对草原生活的记忆回望;祁希对敦煌博大精深的壁画之道的痴迷,反复激发他“行旅西域”的漫游热望;令狐昌在千佛洞的修行是永不停歇的精神磨砺;足娘顺应生活之流和命运之流的人生姿态,最终演化为孤身守村的凄凉无望;贼疙瘩随遇而安的生活情境是他漂泊人生的精神表征;令狐近知从怛逻斯漫游回马营村却成为家园弃儿,吟咏萨福诗歌与漫游乡野大地成为他的精神生活;“我”的朋友慕思明拥有和令狐近知相似的文化精神气质,他人生经历的起伏跌宕,不啻是一场生活斗士的精神迁徙。但是,敦煌赋予每个人物“在路上”的生命美学基调之时,个体生命始终未放弃回归“精神家园”的信念,尽管这种回归并未以“实有”的方式存在,但是他们对家园、家国乃至彼岸的心灵企慕和寻觅行动,同样形塑出他们皈依生命家园、守护文化信仰、自我积极拯救的虔诚而高贵的精神肖像。譬如祁希在履行完使者伦理和家国责任之后,以敦煌艺术精魂的守护者、以中华文明源头的勘探者的文化自觉,与令狐琴定居敦煌三界寺,从而确认了自我生命的伊甸园;令狐昌在对傻儿子令狐近勇的心灵忏悔中,以对狼族和黄羊群等生灵的生命呵护和情感相依,寻找到了个体生命的大地皈依;漫游行吟者令狐近知在与九珍的爱情复燃当中,在诗意的远方“婼羌”寻觅到了熨帖的情感家园;慕容豆在营救乡民的英雄义勇壮举当中,完成了民族交流中对身份的坚定确认;贼疙瘩出于对伦理礼法的敬仰和捍卫,选择慷慨赴死而放弃越狱潜逃,以此方式寻觅到了自我生命的价值归属;足娘则以对萧凉乡村的大地守望和对慕容豆情感期待的坚守姿态,抵达了悲情、虚无而荒凉的家园彼岸。《敦煌》当中的流浪者群像对生命圣地和精神家园的企羡,已经升华为一种人生艺术化的自我救赎,展示出独属于敦煌的忧郁、悲凉、壮烈而浪漫的“唯美主义”生命诗学。
结语
陈继明的《敦煌》是对矗立于西域大漠的圣性敦煌的生命力点燃与复活,小说打开了中原/西域过渡地带深邃而鲜活的“边界”空间,重新将敦煌放置于中国与世界的交汇之巅,一方面开掘出它棱镜式的历史面相,包括吐谷浑人的迁徙流浪、天水村的历史肌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西域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交融、敦煌壁画艺术之道的博深卓绝、佛禅教义的世俗化、民族血脉的后世传承等;另一方面,小说当中敦煌西达世界、东达中原的特殊文化位置,也营造出一个以“文化共生”和“文化交融”为基底的活色生香的自足的地方空间。同时,小说中敦煌的地方性及其历史纹理既通达西域又通达中原,既形塑出从世界、从外部向内凝望敦煌的“他者化”视界,又形塑出从敦煌向外审视世界的“在地性”视野。最终,在敦煌的文化互鉴和文化交融的场域当中,那些来自他者的固化的文化观、伦理观、信仰观、生活观遭到冲击和解构,取而代之的是多民族文化之间的周旋、碰撞、耦合、重组,并在生存、家国、人性、爱情、情义、生命、自由、英雄等公共命题当中,完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话语的理念融通、经验共享和文化共建。因此,陈继明所讲述的敦煌故事,不仅是西域故事,它本身就是中国故事,也是世界故事!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