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陈继明的长篇小说《敦煌》不仅写历史的敦煌,也写现实的敦煌,既实证研究敦煌,也虚构想象敦煌。陈继明渴望写出文明创生时的美学景象,尤其想以磅礴大气的大唐气象来比照现实,在缅怀大唐辉煌的同时,也探讨一种文化的传承、精神的流转在当代的真实境况。《敦煌》的叙事,总是往返于虚实之间,以期在一种现实和历史的实相之中,创造出巨大的虚,由实到虚,又以虚证实。因此,这也是一个有肉身的、朝向尘世的人间敦煌,是一个现代的敦煌。
关键词:陈继明;《敦煌》;虚构;以虚证实;人间敦煌
作者谢有顺,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广州510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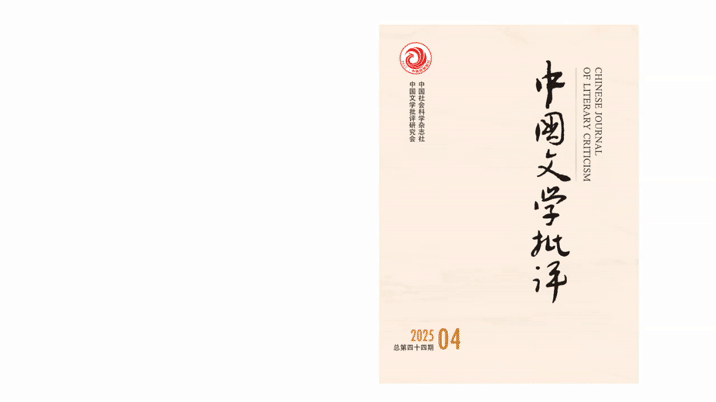
写作长篇小说《七步镇》之前,陈继明的小说一直不温不火。《七步镇》为陈继明的小说写作开辟了新的道路,他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爱欲与救赎、记忆与遗忘、欢悦与酷烈交织的美学时空。穿过生命巨大的迷茫,经由自我内在的辩论,那个亦虚亦实、似前世又似今生的一段内心旅行,所从何来,又去往何方?《七步镇》写出了这种现实的重影和灵魂的歧途。核心的写作方法就是虚实相生、虚实互辨。这样的写作深得中国文化的神髓。中国文化之所以伟大,照钱穆的研究,在其有正反合一观。如言死生、存亡、成败、得失、利害、祸福、是非、曲直,莫不兼举正反两端,合为一体,大到言天地、动静、阴阳、终始皆是。由是推之,中国艺术的妙处,也在于这种辩证归一,如黑白、虚实、浓淡、疏密、奇正,实为“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石涛语)。小说是一门特殊的艺术,虽说是从俗世中取材,以细节、场景、对话、命运来谋篇,但如果仅以实证的方法,是写不出好小说的。小说是以俗生活为底子,通过虚构和想象来创造一个世界,有与无、虚与实的交融,才是小说写作的常道。陈继明深谙这一点,他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敦煌》,贯彻的就是这种虚实相生的叙事策略,他自己也说:“《七步镇》结束的地方是《敦煌》开始的地方。”
一
但凡关涉历史的小说写作,作家都喜欢强调史实与实证,陈继明则不然。他在《敦煌》中强调的是虚构,并认为“真实比虚构更陌生”。小说从雪祁、胜觉、贼疙瘩等小人物出发,讲述了一段不一样的敦煌传奇。“我是一个擅长虚构的作家,又是一个敦煌学和吐谷浑史的业余爱好者”,作者以虚构创造真实,并以此为小说理解敦煌这一伟迹的重要视角。
以虚证实的书写策略,既突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认识论框架,也响应了怀特的理论主张——“叙事与其被当作一种再现的形式,不如被视为一种谈论(无论是实在的还是虚构的)事件的方式。”就小说而言,叙事即虚构,萨特更是直言:“审美的对象是某种非现实的东西。”他以绘画为例,认为“美”是一种不能被知觉经验到的,其本性在世界之外的存在。陈继明《敦煌》中所写千佛洞的画作,既是一种单纯的、审美性的存在,也是一种空幻的哲思,使小说人物雪祁(原名祁希)躁动的内心得以安静下来。雪祁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宫廷画师,画风独树一帜,他的画,不是单纯地复刻现实,而是发挥自己的虚构能力,将所见所闻付之笔端。“祁希笔下的事件和人物往往和原貌有出入”,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只是“为了取悦皇帝,博得今上一笑”,其中也暗藏讽谏意图。那时的雪祁沉迷于俗世的欢乐,追求名利。一次机缘巧合,他看到了胡旋女的舞蹈和天竺男子的幻术表演,那种如梦似幻的场景勾起了他对敦煌的向往,也令他生出精进自己画艺的渴望。
《敦煌》借雪祁之口,讨论了绘画中的颜色艺术。作为中西贸易上的重要一环,敦煌能够采集到各地颜料,雪祁也据此对颜色有了新的认识:“其实我画的不是颜色,是颜色的魂。”敦煌凌晨和傍晚的颜色,给了雪祁重要启发,让他意识到色和彩的同与不同:
色彩是两样东西:一是色,一是彩。彩高于色。彩是总合,是新的东西,是生活中不见得有的东西,是虚幻。色是实有,色不过是红色、蓝色、黑色、白色。彩是产生于所有实有之上的虚幻。
在绘制吐谷浑窟时,雪祁的画艺更上一层,他闭上了仅剩的一只眼,却打开了心眼,人与画就此融会贯通,彻底抛开了一切桎梏,“你需要梦幻泡影,需要曲解、误解,需要胡思乱想”。在梦幻泡影的加持下,灵与肉充分解放,于是,雪祁在敦煌领悟了颜色的虚,也收获了人生的实。这让我想起阿甘本所说的“感性确定性”一词,许多时候,我们对世界的直觉反而是真实和准确的,人类可以通过直觉来认识世界,感官的确定性并非都是虚幻的碎片,也可能是一种可靠的知识形式。小说就是通过直觉来感知生活、建构世界的艺术,所不同的是,它要把这种直觉抽象为语言,进而塑造一个感官中的自我。
尽管直觉往往是语言所难以描述的,但好的小说有时不仅是一种确证,也是一种否定。言说那不可说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否定,而有些事物,只能在否定中才能把握它。比如绝望是对实有人生的否定,但绝望又是把握人生的重要方式之一。再以雪祁为例。他走进千疮百孔的千佛洞时,是有些遗憾和失望的。一番静坐过后,他从偶然吹到自己额头上的一粒沙中,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重量与沧桑。雪祁同沙粒的相遇意味深长:一方面,雪祁的手先触碰到沙粒,这是直觉层面的感知;另一方面,这粒沙吹到额头上,也让雪祁有所顿悟。恒河沙数象征着无限,而额头指向人的智慧,摸到沙粒的瞬间,雪祁泪如雨下,他瞬间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兴亡更迭,更感受到了千佛洞的无穷奥秘。沙粒无言也有言,沙粒有形也无形。“那一粒沙子现在像个人一样悄悄藏在他的笔墨里,令他的线条和笔墨发出沙沙沙的清响。”所谓的真实如同过眼云烟,唯有它作为瞬间或化作某个意象被人捕获时才真正存在。沙粒、瞬间、意象,这些看似细小的事物,反而是认识“敦煌”的重要角度。
“敦煌”二字,据《汉书·地理志》的注解,“敦”是“大”的意思,“煌”是“盛”的意思。小说《敦煌》里说,“敦煌的牛叫能让人想起世界之大、敦煌之远,并为之心生恐惧”。但要真正了解敦煌,反而要从细部入手。我去过敦煌,在敦煌壁画里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细节,比如佛像也有小肚腩,有些佛像的脖子上还有皱褶,这让人想起龙门石窟有穿着红裤子的乐伎形象,这些都和我们传统印象中佛的形象不太一样,但它反而增加了文学的趣味。有小肚腩的佛、脖子上有皱褶的佛,表明佛不仅是神圣的、居于云端的,也是世俗的、生活于人间的。敦煌壁画的风格,早期多复制印度的佛像,后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开始出现花鸟纹等元素,这些审美趣味的变化,也是从细节开始的。还有一些壁画,从美术角度看是不合比例的,尤其以透视法来看是不协调的,但这只是我们站着看的角度,如果跪下来看,就协调了,诚如尼采所说,这个世界没有真相,只有视角。这些让人对绘画有了新的理解。张大千画风的转变,就得益于他摹写敦煌壁画,尤其在人物塑造上,与其早期画风完全不同,除了线条处理上不一样,也和不同视角的建立密切相关。
《敦煌》里有一个改名的细节。以慕容豆为首的八十几个吐谷浑人在天水村实施了“活国”计划,杀了一些天水村的村民后,与当地人进行了换名。他们后来学习当地文化,也感受到当地文化的强大,他们对天水村有形的物理征服后面,其实受制于一种无形的历史力量。《敦煌》多有这种“元历史”的意味。由这“名”“实”之辨,小说其实提出了一个终极之问:慕容豆最后到底成了谁?是成为他自己,还是成为天水村的汜丑儿?画师祁希化名雪祁、作者陈继明和小说人物之一的陈继明这些设计,都在有意模糊虚构与真实的边界,以拓展小说的想象空间。
《敦煌》的另一条叙事线索是令狐家族为赎罪而凿窟的故事,其中所探讨的佛理,也是务虚之问,背后同样有虚实之辨。这个“虚”并不指虚无,而是指一些难以用具体言语表达的事理,人只有经验过了才能有所领悟,佛理提供的也是一种思考的角度。《道德经》言“无有入无间”,《圣经》说没看见而信的人是有福了,强调的都是以虚证实。令狐昌担心二丁抽一的兵役祸及其他儿子,亲手将傻儿子令狐近勇推进井里,为此愧疚且终日惶恐。画师雪祁的到来,让他有了赎罪的想法。其时雪祁已是“敦煌第一笔”,胜觉说他的游丝描和铁线描天下无双,刚好大儿子令狐近知从外地带回一块狗头金,开一个家窟的意愿才有望完成。起初,令狐近知并不理解父亲的做法,经历了生活和情感的多重磨难之后,他才主动加入做家窟的行列中去。参与令狐家窟建造的过程,也令雪祁对于千佛洞的洞窟艺术有了全新的认识:“沙漠中的千佛洞只能是现在这个样子,偏远、破败、凡俗、另辟蹊径、大含深意,有一种令人心惊的枯寂之美。甚至还有一种对称之美——和那些繁华世界、人间烟火相对称。”
在造窟的过程中,雪祁和胜觉和尚之间有很多发人深省的讨论,主要反思藏于历史典籍中的佛理之事。其中,狼窝和羊冢的互相依存,是一则现世寓言。令狐昌将羊冢选择为自己的往生之地,使这片土地有了一份难以言明的玄学色彩。而贼疙瘩为了报答雪祁的恩情,犯了杀业,最后死于狼窝不远处,也平添了几声宿命的叹息。如果说令狐昌的命运是历史的影子,慕思明的死则是现实的投射。慕思明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商人,却因“我”讲述的莎乐美的故事诱发了抑郁症而选择了跳水自杀。没有人能说清他的死是病发所致,还是吐谷浑人血脉中自我毁灭倾向的瞬间爆发。小说中写:“一个人死了之后,活着的人或多或少受到启发,进而脱胎换骨。”相比雪祁面对令狐昌之死显示出来的淡然,“我”是通过探究和书写吐谷浑的史诗在进行自我赎罪。雪祁认为令狐近知和令狐琴继承了令狐昌供养佛祖的遗愿,而“我”却面对慕思明之死才意识到自己对他一无所知。令狐昌生之意义在后人和家窟中得以延续,而慕思明的生命意义却化作了山洪的轰鸣声,成为“我”探寻吐谷浑历史的重要动力。存在与虚无在此刻达成了终极和解。
《敦煌》以虚构确认了另一种真实,首先是艺术维度上对美的重新理解,其次是历史想象中的真实个体的还原,再者是佛理层面上所实现的存在的和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继明所写的敦煌不仅是历史的敦煌,也不止于文化的敦煌,他更着迷的是以虚构来重建一个自己内心的敦煌,这里面有历史的烽烟、民族的躁动,有梦想的波澜、意识的腾跃,有暴烈有温柔,有罪孽有悔悟,最重要的,有天地供养的生灵万物。在陈继明看来,只有这样的敦煌,才是真实的。
二
小说真实的建构,光有史实、材料、细节层面的还原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想象和虚构来创造新的艺术真实。在材料搜集、田野勘察、文化追索上,《敦煌》显然是下了苦功的;语言上也饱满、诗性且颇具古意;关于艺术与佛理的诸多探讨,融汇于小说叙事之中,不仅不显生硬,反而使小说在经验的力量之外,因有飞扬的神思而显深邃。陈继明说,他的《敦煌》“跟历史有关,但不是历史小说,它的语调、趣味、观照方式、叙事方式,都应该有别于历史小说”。他想突破固有史实的认知框架,重构诗学意义上的历史真实。他并不避讳个人面对宏大历史时的无力与困惑,有意在小说中保持叙事距离,同时选择叙事角度。角度会决定故事的方向和重点。
同样是写敦煌,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讲述古代造窟背后的故事;可以从美学角度,由洞窟内彩塑、壁画的不同而了解不同时代的审美追求;也可以从宗教角度,研究古代僧侣如何修行礼佛;还可以从空间角度,看古人如何在宏大的山体中造型与结构。认识不同的敦煌,才能拼出一个完整的敦煌。陈继明说,他写敦煌,是想进入敦煌看看在神性无所不在的地方,人是怎么生活的,“《敦煌》这本书,没打算简单图解任何外在的东西。它的唯一愿望是,在一个宗教圣地,找到人。无论多难,向内走,找到人,替人说话”。为此,他最终选择了唐代:
我想写唐代,想另辟蹊径。原因之一是,敦煌的壁画和造像,在数量上以唐代为最,在艺术性上唐代也走向了成熟。另一个原因是,我更愿意写一些小事端,让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端在不经意中发展为大事件。事件的深处是人的内心天地,是气氛,是声音,是色彩,是可以氤氲和衍生开来的东西。
陈继明不写宋代,也不写清末、民国,尽管这些时代的敦煌很热闹、故事多,但他更愿意选择久远的历史,从初始处看一种文化的诞生与变迁,进而探讨一些“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尤其是图像的创生,有时比文字更直观,也更接近民族记忆的原型。至少在文化记忆的神圣之地——敦煌,那些壁画颠覆了人们以往对于文字的推崇,在壁画面前,文字或许是乏力的。比如,敦煌壁画中的乐舞图像,“主要依据佛经绘制,以歌舞的形式表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欢乐图景,极致地传达了诉诸眼、耳、鼻、舌、身、意的肉身体验”。这些欢乐的肉身叙事,就是唐代所独有的,那时的百姓大多能吃饱,权贵阶层更是歌舞升平,壁画中欢乐的场面就多。这也是唐代壁画跟北朝壁画的区别。北朝时的壁画有很多悲惨情景,如舍身饲虎、舍身喂鸽子。当时战乱频繁、命如草芥,死的人很多,这些都会表现在壁画中。所以,敦煌乐舞图像中表现的是两个世界,一个是神圣的,一个是世俗的,神圣世界里有天宫、飞天、药叉等图像,世俗世界有宴饮、出行、歌舞等图像,堪称圣俗交融。如果你在敦煌的洞窟中进行一场视觉漫游,就会有不同的心灵触动:与嘴角含笑的佛像相对,你的内心是平静的、烦恼消散的;看到菩萨身上的肉褶和小肚腩,你会感觉人世温暖并会心一笑;看到那些瘦骨嶙峋的苦修僧仍然表情恬淡、毫无苦相,你又会被他们的达观打动。图像作为记忆的载体,构建出的是另一套超越语言的感性认知系统。
《敦煌》写了不少造窟的过程,还原了这一文化景观发生的细节。慕容豆委托雪祁完成吐谷浑窟的创作,其实就是完成一个从口述历史到图像编码的转译过程。吐谷浑人口口相传的历史,构成了一个部族的集体记忆,造像正是对这一记忆的叙事。正因为如此,雪祁才一直强调自己绘画的叙事属性:“我画画其实在讲故事,换句话说,我差不多也是一个说书人。一个说书人,会千方百计要把故事讲好看、讲生动,于是我们难免会有增有减,难免会虚虚实实,难免会成为故事的奴隶。你想想,我们的历史是不是也是这样?整个历史是不是也是一个动力十足的故事?杨广是不是故事中的一个人?李世民是不是故事中的一个人?杨广和李世民是不是故事的奴隶?”听完吐谷浑的历史,雪祁感叹道:“这个窟子的意义不光是吐谷浑的,更是全华夏的。”于是,精通绘画叙事策略的雪祁选择迁徙和求生作为吐谷浑窟的母题,吐谷浑人千百年来的辛酸历史就此凝结在了壁画之中。而这种独特的图像叙事,讲述的已不再是什么历史事实,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记忆。雪祁的创作,并不仅是为一个部族存储记忆,而是他理解了一个部族之后的文化实践,他的艺术塑造超越了简单的口传,也重写了历史。
历史从来不是材料和事实的总和,而是记忆的积存、思想的凝聚,是历史记录者对已过岁月留下的各种印记的重新编码。《敦煌》借了历史小说的壳,但里面写到的历史,都是陈继明自己重新创造的历史。有时虚构的真实比历史的真实更可信。这让我想起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所提出的“当下”“此时此刻”“微小事物”等概念,他认为历史真理并非在时间中线性地展开的,而是通过“被人历史地领悟了的瞬间”所包含。《敦煌》似乎也在重申,那些被感知到了的瞬间、被记录下来的时刻、被重新辨正的事实,才是真实的历史构成。
三
好的小说,是把假的写成真的,它创造真实。卡夫卡笔下人变成甲虫的寓言,就是虚拟的真实;鲁迅笔下的阿Q,也用了漫画的手法,生活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阿Q,但阿Q身上却浓缩了一个民族最为真实的国民性特征。相反,失败的小说往往是把真的写成了假的,很多图解观念、主题先行的小说,就缺乏可信的现实基础和生活逻辑。写小说,经验、记忆、细节只是基本材料,更重要的还是想象。想象是对经验和材料的重组,也是在此基础上对新的世界图景的创造。想象的真实是一种精神真实,一种比具象真实更永恒的真实。
《敦煌》第六章有一段雪祁在三界寺与胜觉和尚关于画的真实性的对话,就回应了这个重要话题:
雪祁蹲下来,把草稿徐徐打开。胜觉静静看了一会儿,说:“有势,这势,多好!”雪祁说:“我还不满意。”胜觉问:“说说看,哪儿不满意?”雪祁说:“实话实说,我有一个问题还没解决,我还不能把神的故事和人间烟火对接起来。说白了,我还不相信阿育王的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胜觉说:“所以啊,势很好,但有点空,缺一点打动人心的力量。”雪祁问:“怎么办?”胜觉坐下来说:“你必须先相信。”雪祁说:“是呀,问题就出在这儿。我对佛陀和佛陀的思想五体投地,但是,我还不能相信,一百年前的童子就是后来的阿育王。阿育王从一个征战四方的统帅,又是怎么变成一个慈悲为怀的君王的?那个点,那个最关键的点,我一时还找不到。”胜觉在琢磨,如何说服雪祁相信。胜觉站起来,围着雪祁转了几圈,终于盯住雪祁的眼睛说:“慈悲并不是佛陀发明的,在佛陀出世以前,慈悲早就存在了。你难道也不相信慈悲吗?”雪祁睁大眼睛,愣了片刻,突然给胜觉跪下来,说:“我懂了,我懂了!”胜觉说:“快起来,快起来。”雪祁说:“我在给慈悲下跪呢!”胜觉说:“慈悲是不需要下跪的。”雪祁问:“谁需要?”胜觉说:“人呀。人需要,装神弄鬼的人。”雪祁问:“你没骗我?”胜觉说:“我没骗你。”雪祁问:“骗过别人吗?”胜觉说:“当下跪、磕头、烧香成为习惯,也就没必要一一劝止了。”雪祁一惊,说:“容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胜觉做出一个尽管问的表情。雪祁问:“人为什么必须闭关?”胜觉说:“闭关和磕头不一样。闭关的确有必要。”雪祁问:“为什么?”胜觉说:“我们生活在阶段性里,闭关就是力争跳出阶段性,看到不灭性,看到永恒存在的东西。”雪祁问:“你看见了吗?”胜觉顿了顿,说:“我觉得我看见了。”雪祁说:“胜觉兄厉害,还请不吝赐教。”胜觉说:“不灭性的一大半就隐藏在我们自己身上,所谓儒释道——儒性、佛性、道性,其实是天真本性的自然流露,来自人自身。每个人身上原本就有,天生就有。”雪祁问:“原本就有,天生就有,那还闭什么关?”胜觉说:“成长的过程也是受蒙蔽的过程。”
胜觉和尚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身为和尚,他牵挂俗世,一手促成了令狐家窟的落成;他热衷做媒,忙前忙后给雪祁和令狐琴牵线搭桥;他关心令狐琴,担心令狐琴在雪祁这里做小会受委屈,于是反复追问雪祁的真实心意;身为俗人,他追寻佛理,经常语出惊人,给雪祁的心灵带来震撼。不同于很多和尚的坚信,胜觉和尚是在一步步的探索中接近佛理的,尤其是探讨佛理中引人深思的实与虚问题,其中经历了几次转折。一是胜觉和雪祁对于阿育王故事的争论。雪祁不解阿育王建造八万四千佛塔的实际效用,问胜觉,胜觉回复道:“我也担心医生多了,病人也就多了。”这是一个颇具深意的回答:一方面,胜觉对于世俗中的佛理传播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另一方面,胜觉认为“多即是少”,雪祁如果对于阿育王故事思考得太多,反而容易误入歧途。胜觉指点雪祁,佛教的事情“不用脑子想,用心想”。二是雪祁的自悟。在听了阿育王施舍半颗梨子和太子舍身饲虎的事迹后,不论胜觉如何言说,雪祁始终觉得这两件事缺乏真实性。也许是胜觉启悟有方,经过几番静坐并自我发问,雪祁终有所获:“你能从鲜花、圆月中看到幻,怎么就不能从阿育王施舍半颗梨子中看到真呢?”由此可见,历史的真、事理的真和情感的真是不同的。三是雪祁和胜觉在谈及历史的虚与实时,雪祁直言佛教故事多有虚构。胜觉听了,面色“凝重又虚幻”,他没有正面回答,也没有批评雪祁的发问是种不敬,只说了一句我听懂了。胜觉深知,有限的言语并不能给予众生一个可靠的答案,还不如以恰到好处的沉默作答。
“正如真里面有幻,幻里面也有真”,终有一天,事实将化为历史,历史将变为故事,故事将成为传说。不舍昼夜的历史长河汹涌流逝,两岸沙土堆积,犹如一虚一实,共同构成了坚实的河床。《敦煌》的叙事,总是带读者往返于虚实之间,而作者的最终目标,是要在一种现实和历史的实相之中,创造出巨大的虚,由实到虚,又以虚证实。敦煌看似在那里,每天都在上演真实的故事,但敦煌又不仅是在那里,它还是一个精神幻象,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需要在某个时刻被发现、被照亮。被发现、被照亮就是一个以虚证实的过程。
正如胜觉和尚所说,看到“不灭性”就是看到“永恒存在的东西”——“永恒存在的东西”是虚,而“看到”就是一种以虚证实;而“不灭性”是实,它本就藏在每个人的身上,你只要活出本性就好。胜觉所推崇的“闭关”,其实就是去蔽的过程,清除掉覆盖在本性上的尘垢,让天真的本性自然流露,就会遇见更真实的自己。
一旦内心澄明,看见佛的静谧,也看见人间繁华,看见众生平等,看见平凡中的神性、生命里的慈悲,这就是有无相生、虚实相生。如《敦煌》里慕思明所说,如果这个世界真有佛,爷爷奶奶就是佛,或者说,天空就是佛、草原就是佛,佛在大自然里,不在书里。
由此我想到作家阿来。他是藏族人,他的族人也都信仰佛,但他对此常有追问与反思。他说:“现在,虽然全世界的人都会把藏族人看成是一个诚信教义,崇奉着众多偶像的民族,但是,作为一个藏族人如我,却看到教义正失去活力,看到了偶像的黄昏。那么,我为什么又要向非我力量发出祈愿呢?因为,对于一个漫游者,即使我们为将要描写的土地给定一个明晰的边界,但无论是对一本书,还是对一个人的智慧来说,这片土地都过于深广了。江河日夜奔流,四季自在更替,人民生生不息,所有这一切,都会使一个力图有所表现的人感到胆怯甚至是绝望。第二个问题,如果不是神佛,那这非我力量所指又是什么?我想,那就是永远静默着走向高远阶梯一般的列列群山;那就是创造过、辉煌过,也沉沦过、悲怆过的民众,以及民众在苦乐之间延续不已的生活。”关注佛,不能只定睛望天,最终还是要回到人间,回到山川、河流与生生不息的生活之中,感受尘世的悲欢,体悟生命的磨难,并持守对人性温暖的向往。这是作家的命运,也是他的责任。
四
文学关怀一种文化的存亡、一个民族的历史,常常要落实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只有写出了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命运,文化和历史才不是空洞的概念,才能拥有自己的肉身。小说是活着的历史,日常生活是文化永不破败的肉身,所有历史的潜流,在人间都会有回响。“把历史同生活的关系理解为统一关系”的克罗齐曾说,“没有一件历史事件是错觉和误解的结果,一切事件都是信念和必然性的结果。”而“信念”和“必然性”这些所谓历史自身的规律,往往遵循的是人间生活的逻辑,也就是现实的逻辑,这也是历史与当代联系的观念基础。人性的构成与变化的法则,都是藏在历史之中的。但不能返回到现实之中的历史,往往只是一个概念、一些材料,因此,在历史记述之外,之所以还要有文学叙事,就是要作家以形象、场景、细节为历史补上血肉肌理,尤其是好的小说,总是能让历史延伸到现实之中,让历史和生活统一起来。
《敦煌》就是这样的小说。它不仅写历史的敦煌,也写现实的敦煌,既实证研究敦煌,也虚构想象敦煌。陈继明渴望写出文明创生时的美学景象,尤其想以磅礴大气的大唐气象来比照现实,在缅怀大唐辉煌的同时,也探讨一种文化的传承、精神的流转在当代的真实境况。我们所失去的,我们所留存的,都有哪些?文脉、血脉又流向了何方?而这正是人间敦煌的精神底座。
陈继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人间敦煌。这个敦煌连接历史,又返回现实,那些像雪祁、足娘、智忍花、慕容豆、令狐昌、令狐琴、令狐近知一样的渺小人物是叙事的主角,那些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生活洪流是敦煌的血脉,而那些艺术上大胆的造型、颜色,以及蕴含的慈悲、热爱、虚无和博大,永远是想象敦煌的不竭源泉。陈继明笔下的敦煌,总是藏着一条精神的丝线,这条丝线会一直延伸到现代人身上来,而沿着这条丝线,现代人又能回去对话古人、探访大唐。作者花许多笔墨写的雪祁和胜觉两人关于佛教、绘画、人生及敦煌的争论和辩难,何尝不是现代人经常争辩的话题?而慕思明死后,慕思明的妻子说要带孩子回到敦煌,象征的难道不是一种不死的民族精神?慕思明一直认为自己是吐谷浑后人,也一直在整理吐谷浑人的历史,据他考证:“吐谷浑人,原本也是黄帝的后代,后来到了阴山,再后来到了鲜卑山,过上了游牧生活,新的地域、新的气候和新的生活方式,包括新的文化渐渐改变了人。于是有了鲜卑人,又有了吐谷浑人。”亡国之后,“汉、藏、蒙古、回纥、突厥、维吾尔,各民族杂居在一起,相互通婚,演变为土族”。这种民族融合,使得慕思明的存在成了一个象征,他带着多民族的集体记忆活着,他的死,也绝不是最后一个土族后人的消亡。小说里写的《吐谷浑迁徙歌》,歌词是“天空在下雪/我们在赶路/天空在下雪/我们在赶路……”现在活着的人,身上也许就有吐谷浑人的基因,并且带着吐谷浑人的民族记忆“在赶路”,这就是历史和生活的统一,也是人类精神的古今对话。我听说,有一位云南大学的老师,非常喜欢敦煌的一个菩萨,每年假期都去敦煌住一个多月,他迷恋上了那个菩萨,每天注视他、和他说话。何以千百年前的壁画、笑容仍能打动、迷住今天的我们?这种文化穿透力超越了时空,我们注视壁画的时候,是不是在换一个角度观看自己?正如《敦煌》中的“我”,在慕思明身上看到了吐谷浑人的民族性格和原始冲动,“他们是一群渴望牺牲的人”,而这,是不是又反过来映照出现代人匮乏的正是这种牺牲和忠诚?
我们不仅能在吐谷浑人身上看到自己,也能在雪祁身上看到自己。在《敦煌》中,雪祁和敦煌的关系历经了多次转换,他不自觉地从一个文化记忆的解码者变成了文化记忆的编码者。和井上靖《敦煌》中的赵行德相似,雪祁参与到了整个敦煌文化记忆的建构中。赵行德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目睹了西夏与回鹘的战争,也见证了不同文明的兴亡激荡。一个错过科举的书生,受佛法的感动,一路成长为保护和传承文化的使者。在他看来,经典不属于任何人,谁也抢不走,只要不被烧毁,搁在那里就行了。赵行德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一个文化的续命者。不同的是,雪祁并不只是一个承载文化想象的符号性人物,他是一个有自觉意识的文化主体。起初,雪祁只是来到敦煌学习画艺,但来到敦煌后,他被敦煌的气质折服。他在精进画艺的同时,发现千佛洞没有大唐的身影,深感自己“有这个义务把大唐气象留在敦煌,留在千佛洞”。他即使身患难以忍受的漆疮,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他知道自己费尽心力的画作会在百年后或几百年后慢慢脱落,“所有壁画都将在未来某一天完全脱落”,但这些不足以让他停下笔,他抓紧时间完成画作。在索如、胜觉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雪祁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完成了创作。由此,雪祁又一次实现了身份转化,他自己也成了敦煌历史的一部分。小说的结尾处,47岁的雪祁虽然功成名就,但他还是选择回到敦煌、回到三界寺,去做文书整理的工作。此时的雪祁,既是敦煌的主人,又是敦煌的“他者”。他是历史人物,也是现实中人,理解了这个历史人物面对敦煌时的热爱和激情,也就理解了现代人面对敦煌时的伤心和叹惋。
敦煌是大题材,难写的题材,每个作家面对它,可能都会有一种书写的焦虑,但陈继明没有沉迷于惊叹与赞美,也没有走单一的创伤记忆和自我救赎的书写路径,他写的是自己心中的敦煌。这是一个万物有灵的敦煌,有男人、女人、帝王、百姓,有牛、羊、马、狼、骆驼,有风、沙、雪、雨、石,他们同沐恩慈,同处人间;这也是一个文化健旺的敦煌,有酒、色、歌、舞,有理、智、情、爱,有美和颜色,有天空和想象,有罪与罚,有人性与佛理,有岩石一样坚强的信念,有毛笔一样柔软的情怀,明明是凡人的艰苦跋涉,却被陈继明写成了圣人意志的悲歌。而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有肉身的、朝向尘世的人间敦煌,是一个现代的敦煌。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