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建设“中国古典学”的使命,是在古今中外的视野中激活中华文明的本源精神,回应时代问题,为人的生活提供整体性意义。传统道论决定了中华文明总是以重新阐发经典的方式带来活力和发展。“述”与“作”之中道,是文明同一性与生成性之间的平衡,构成了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的基础。“中国古典学”在中华文明领域的研究对象应以经典化的六经为主,以经学、子学为辅,其外延可以在实践中逐步摸索修订;其研究方法应以哲学与经学的思维方式为主,以史学、文献学为辅,以诠释学来超越实证主义倾向。经学需要哲学思辨来激活,哲学需要经学的丰富性来扩容,才能在文明论视域下达成文明互鉴的目的。
关键词:“中国古典学”;“述”;“作”;跨学科;文明互鉴
作者田丰,郑州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郑州45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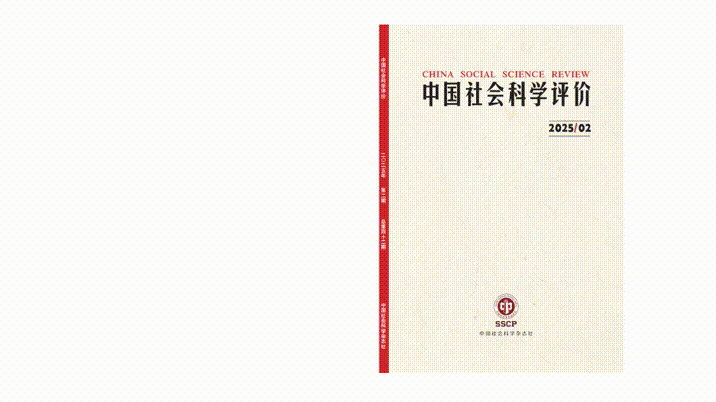
2024年11月7日,习近平主席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指出,古典学研究的使命,在于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因而,“中国古典学”首先应当是中国对自身文明本源的传承发展,其次也应当包括对全球其他古典文明的交流互鉴。前者的目的是在古今交汇的视野中重新激活中华文明本源精神,可谓取诸怀抱,悟言古今之变;后者的目的是吸纳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点,可谓因寄所托,放眼中西之外。“中国古典学”同时也应该在互鉴中通过叙述和论证,展示出一种有价值和意义的生活方式,既能够为人的生活提供整体性意义,也能够接受不同文明与观念的质疑并与其对话。中国早年的古典学建设主要体现在对“西方古典学”的引入,晚近以来,“中国古典学”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当前,“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的基本共识是应当建设一种具有文明互鉴视野、以认识古代文明整体为旨归的交叉学科,而分歧则集中在应该以哪个学科、哪种学术方法为核心来建设。本文认为,“中国古典学”应当是以道自任的“文明论”视域下涵括古今中外的古典之学。它要通过返回人类文明的重要源头,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激活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来应对时代的诸多变化与挑战,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在此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讲话为“中国古典学”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本文第一部分将在此精神指导下简要勾勒“中国古典学”的文明论目的,并结合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讨论文明与古典的关系;第二、三部分则在此目的的指引下,进一步确定其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中国古典学”的研究目的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国古典学”的研究目的不应是努力使之成为现代“科学”之一种,维拉莫威兹常被人引用的“复活那已逝世界”之言,其实是近代以来人文学科实证化的一种幻想。构成已逝世界的不是各种器物、卷宗、建筑的实证知识还原,而是在人的理解之中的意义关系。如果不能够在精神层面理解祖宗牌位对于慎终追远的意义,即使我们对其实物尺寸构造、祭祀时的诸多细节把握再翔实,也不算是真正理解了那个逝去的世界。
更具体来说,文明精神最重要的寄托物是人类经典,经典需要后来者的诠释与激活,只有不断出现像孔子、郑玄、玄奘、朱熹这样接续文明精神的圣贤,而不只是知识专家,一个文明传统才能迭代更新。圣贤的出现需要丰厚的民族精神土壤,“中国古典学”应该承担的就是为民族精神奠基的使命。
有的学者认为,思考世界整体性意义和文明理想应该是哲学的任务,古典学恰恰无法提供这样的思想资源,因为它探寻的是一个已经逝去的世界,而意义和理想问题必须始终立足于当下的反思、批判与建构。为了回应这些看法,我们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特点出发,来论述文明的日新更化与其源头(古典)的根本关系。
无论是个体对世界整体意义的追问,还是文明对于自身发展的探寻,都可以称为真理问题,中国古代通常用“(天)道”来指涉真理。“道”对于人和文明具有根本超越性——就个体而言,体现在世界整体意义之于个体的先在性以及不可彻底的澄明性;就文明而言,体现在文明对于自身的延续、秩序、活力、生灭的掌控性永远是有限的。即便至大无外的“天下(文明)”,也是在“(天)道”之“下”的有限性存在。“道—天下—人”构成了超越性的基本层次。
个体与文明都会在基本层面上追求自身的生存性延续,但生存对于个体而言只是基础性保障,它可以出于不同的理由被超越或舍弃——为了后代而自我牺牲,通过不同的功绩达成不朽或是永生。不朽与永生的区别在于前者对文明的依托性更强:阿喀琉斯需要古希腊文明的延续才能被人传颂、追忆和不朽——尽管古希腊文明的实体灭亡,但古希腊精神和经典依然被铭记和流传,作为阿喀琉斯不朽的依托。相信灵魂永生者则强调其非现世性,即便宇宙毁灭也不会影响其永生。但这种信念依旧在弱的意义上依托于某种文明论,不管它是宗教抑或是哲学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说,个体对不朽或永生的追寻,总是依赖于文明之延续的依托。
文明的延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上述古希腊文明的精神性延续。精神性延续也需要实体承载,譬如在经典、语言、制度或是其他民族世界中的实际影响,但我们依旧可以在实存意义上说大部分古代文明都已不复存在。与之相对,另一种则是文明本身的实存性(以及精神性)延续,中华文明是这方面的最典型代表。
天下作为至大无外的统一体,它的历史就是“道”通过天下之人共在生活的具现,故而中国人极端重史而不离事言理。人的有限性还意味着,“道”通过人具现的同时也在自我隐匿,它在历史中不断地向个体呈现出某种势态,但我们只能通过事(迹)从某个角度获得对“道”的理解,无法完整地窥见或体证道体本身。
中国传统因此认为,“道”在世的最高表现不是某种孤悬本体,而是“时(境遇)”中之道。中道除了具有通常理解的个体修身意义,更具有历史的义涵。仁之本为生生,仁治天下不是以现成之道维系天下之治,而是依托于圣王仁德在变动不居的历史中随时损益。在文明的历史之“时”,先王之政典通过圣人之删述,凝聚为理想典范,也成为后来者不断返回的中道。孔子的“圣之时”不仅是在各种境遇下洞见如何中道地行动进退,更是在关键的历史时刻中,在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的删述中达到了最高的中道。中华文明的道论由此始终具有强烈的境遇性、历史性与生成性。中道是在多元学派中的碰撞,在激进与退守之间衡定,在执其一端付出的代价中摇摆,它就是文明精神在历史中不息的显现与遮蔽。
上述道论或曰真理观,决定了中华文明在有史可考的历程中,其典章、制度、礼俗、思想的基本发展方式,总是以重新解释经典的方式创造新的活力和发展,经学由此构成了古代传统最重要的精神脉络。无论是个体还是文明自身,追求真理的方式不是进行历史性的逻辑推演或直观顿悟,而是通过返(反)经合道的磨炼达到“可与权”的境界。下面,我们通过检讨“述”与“作”的关系来进一步阐发经典与文明的关系。
带着上述理解,我们会看到,诸子对“述”“作”“道”“迹”的看法实乃各执一端。如墨、农、道三家以法古、法先王、法道立论,皆持有是古非今的观念,以为非返古不足以治世,非朴质不可以救文繁情伪之弊。法家则以法法、法后王证成其合法性,批评儒家法先王“迹”之无法参验,非愚则诬,并否定常道,究其根本乃是重“迹”而轻“道”。庄子后学则批评儒家总是盯住先王之迹的经典,反而失去了先王之道。这种思路的进一步推进,导向的是禅学或心学式的个体顿悟(其实质同样是贬迹而试图跨越历史,求道之本体)。上述诸家共享的前提是“迹”与“道”、“述”与“作”的分离。
相较之下,儒家拒绝上述分离,试图在变与常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在古今之际通过圣王谱系的建构,让过去重现生命力而成为当下秩序的基石。孔子尽管亟称尧舜至德,但并不一味遵古,而是“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论语·卫灵公》),强调三代之损益以及周文之备,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取法,删述五经,并于晚年作《春秋》以自见于后世。《春秋》之中道是在一个文明不绝如缕的时刻,让秩序在面对混乱历史中的善恶时,在“述”与“作”之中保持平衡。孔子对“原始经典”的删述既是对历史的重新书写,也是对圣王谱系的建构,更是对文明危机的回应。
在《孟子·离娄下》对儒家圣王谱系的描述中,每一代圣人“道济天下之溺”的手段都因时而异,其共同点在于皆为“人伦之至也”。也即是说,无论是圣人还是六经,都不是永恒真理(天道)的持有者,而只是“道”在人伦层面最极致的表现。将经典与圣人等同于天道,可能会导致对人的有限性的忽略,从而带来人对于超越者的躐等与僭越,或者是某种神学政治。更大的困难在于,今天如何看待不同文明经典及其承载的真理的关系。
经典由数代圣人站在文明源头处所“作”积聚而成,具有政治与教化双重奠基的意义。“述”经的诠释则是经典的生长蔓延,以及人们在“希圣希贤”的功夫中构成的真实历史。通过《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可以获得超越心性论的文明论层面的理解:每个文明都有其承受、开显的天命,它在历史中的具现化就是文明之道,它结晶为经典并成为文明教化之本,经典因此具有介乎天人之间的中介意义,这也是经典作为文明原初生活体验的直接性、自明性和普遍性以及它作为本源问题植根的土壤意义。
经典“占有”与“评判”人类历史,其所塑造的传统会构成我们理解的基本视域前见;但同时,每一代人的生活世界始终具有非决定论的,超越传统、前见、权威的力量。历史不仅被占有和评判,也有溢出与断裂的面向。如果传统视域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文明与历史也就不可能有断裂。断裂有时源自外界的影响,但更多是自身内在的衰落。许多古典文明在实体乃至精神层面都已消亡,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及其经典仍是我们能够依凭的精神力量源泉。古典带有强烈的实存感与共时性,与我们的当下处境交织;又具有强烈的历史性,体现出一种文明模式的持久性和有效性。在此意义上,“古典”概念可以用来指涉经典与历史的共生一体之“理想型”,它超越共时性,始终在历史中以经典解释和实践的方式与我们相遇,文明的连续性要求我们给出属于自身时代的诠释。
二、“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
就先秦经典的具体内容来说,“前孔子之经”与经过孔子整理而形成的定本六经及其诠释,是中华文明的基础。一方面,我们几乎不可能对“前孔子之经”获得整全性认识;另一方面,孔子的文明史地位也决定了“中国古典学”应该以其所定六经为主。不过,也要注意“经书”与“经学”的区分——经书专指孔子经典化的六经,经学是指先秦及汉以后诠释六经或十三经的学问,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决定了经学之流一直延续到晚清,源流难以分离。一部后世经注既可以视作释读经书之辅翼,也可以用来研究经学思想史,但“中国古典学”显然还是应该更加倾向于经书的方向。
就经子关系来说,从《庄子·天下》《汉书·艺文志》等来看,六经与诸子均是对“前孔子之经”的继承和诠释,因此“中国古典学”在以经书为主干的前提下,也必然要将先秦诸子纳入其研究领域。不过,尽管老子、庄子对于中国文明影响巨大,还有一些子书也在历史中升格为经,但升格现象本身恰恰说明经子的主次格局始终存在,因而不宜泛论“经子一体”,而当以经学为主,以子学为辅。
就古文献学、语文学等小学来说,必须明确它们应是服务于文明论古典学的研究工具,而不能将其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否则,古典学就将成为经院考据,缺乏真正的思想活力和对时代问题的回应,也无法满足那些渴望古代伟大精神并积极投入时代浪潮、不甘心于琐碎平庸之学的年轻人的精神追求。学贵乎先立志,如果没有“先立乎其大”的气魄与胸襟,“中国古典学”就将成为新式乾嘉学派,虽于学问知识或有裨益,却于人心世道无补。
我们绝不否认考据、语言、训诂等专业训练的重要性,但如果将其视作“中国古典学”的全部,那就好像以为认识了《论语》中的每个字就能理解孔子。清人说“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其实训诂考据永无穷尽,乾嘉学者们便是终身自限于此而无以窥道。如果将古代著作仅视为文献材料,必定会将古典学局限于少数高深专业的学院式研究,陷入历史重负而难以洞察古典精神,最终无法发挥古典学的社会教育功能。其实,在如今的学术体制下根本无需强调专业训练,这是想淡化都不可能的事情。故对于“中国古典学”的大本而言,重要的是首先建立宏阔的、整体性的文明论视野。缺失了“先立乎其大”的眼光与关怀,“中国古典学”的建设就无法发挥交叉学科的优势,实现文明互鉴和自我更化的目的。
总之,目前“中国古典学”关于中华文明的核心研究对象应当以经书为主,以经学、子学为辅,以传统小学为工具,并涉猎史学与考古学以知人论世。本立而道生,其外延可以在实践中逐步摸索修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锁定边界。
三、“中国古典学”的研究方法
本文认为,“中国古典学”的研究方法应当是综合经学、哲学与诠释学三者的跨学科研究,本部分将首先处理经学与哲学的关系,再讨论“中国古典学”与诠释学的关系。
“中国古典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先秦经典,但我们不能直接借用传统经学的研究方法,因为今天的经学同样面临学科重建与方法论问题。近代以来,经学逐渐狭隘化为“小学”,引向实证化和工具性的理解。经学的瓦解不是研究对象的消失,而是研究方法和视野的变化:一是以史学与文献训诂学来从内部瓦解经学,二是以哲学化的子学来替代并抛弃经学叙事,最终使得经书被现代学科建制的方式割裂瓜分。因此,经学需要哲学思辨来激活,哲学需要经学的丰富性来扩容。二者可以互补,共同在文明论视域下建构“中国古典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无论是胡适还是冯友兰,在创建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时,都依凭西方哲学范式对传统材料作了拣选,以子学作为中国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将经学划分出去。其理由在于,“‘经学’的特点是僵化、停滞,‘子学’的特点是标新立异,生动活泼”,其实质是批评经学自认为依凭圣人与六经占据了最终真理。近来不少学者指出,经学有着效法西方范式的中国哲学学科无法涵摄而又非常重要且根本的部分,并反驳了传统经学独断、禁锢思想自由、阻碍文化多元发展的论调。但是,这不等于经学能够以古代形态复活,还要进一步分析独断、质疑、信仰与思想体系的关系,才能澄清经学与哲学应该如何相得益彰。
我们首先要区分外部质疑与内部反思。前者指的是学者出于自身学理或学派立场的理由,对其他学派或文本的批评;后者指的是学者对自身尊信对象的反思。六经从百家争鸣起就一直在应对批判与质疑,在先秦有道、墨、农、法,在汉代有黄老之学,在魏晋隋唐有佛老之学等,某些时期,经学甚至因为受到佛老的挑战而走向衰微。不过,上述都可称作外部质疑。尽管今古文经学对于彼此信奉的经传文本及其义理会提出质疑,但是当学者接受某经书作为自己尊信与注释的对象时,该经书对他而言便处于不容置疑的权威状态。更何况,所有经学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不会质疑周孔代表的圣王传统。就此而言,他们似乎都缺乏内部反思,那么经学是否能避免僵化和权威的诟病呢?
人性质有不同,或有鲁钝,一时见未到得。别人说出来,反之于心,见得为是而行之,是亦内也。……今陆氏只是要自渠心里见得底,方谓之内。若别人说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别人说出,便指为义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说。……只是专主“生知、安行”,而“学知”以下一切皆废。
此即“分别内外太迫促,故规模窄狭,不复取人之善”。因此,对“圣人”“经典”诸般对象的态度并不需要放弃理性的盲信,而可以是出乎理性的尊重与承认。实际上,百年以来关于经学重“信”、哲学重“疑”的区分,是错将“古今之变”视作“经哲之辨”。这涉及形而上学终结之后,现代性思想的两个重要主张:人的有限性与真理的历史性。这两个主张以及现代多元文明格局,使得对真理限度的警醒成了现代思想的基本构成因素——几乎没有哪个思想家在今天声称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这才是我们熟知的哲学自我质疑的真正来源。
因而,近代以来经学的瓦解,既是因为经学本身与西方学科体制具有诸多方枘圆凿之处,又是因为经学的绝对真理论与现代思想整体基调的冲突,导致其权威性和神圣性的消失。这意味着今天每一位真诚的学者,都不可能再简单地以经书或圣人作为其真理性或是善好的明证性来源,必须既接受来自其他文明价值与真理的外部挑战,又要让自身的言说与论证方式接受哲学的内向反思,因为文明的神圣性基础不可能通过独断的信仰来复活。除了调动哲学的深厚思辨资源,先秦诸子以及后世儒释道三家的论辩与思考方法也应当被纳入“中国古典学”的建设之中。
此外,怀疑与批判虽不可或缺,并常常起到清扫地基的作用,但不能够被狭隘地理解为哲学的本质,哲学更根本的向度是对普遍意义问题的回答、建构与奠基。一种整体性文明论不可能仅通过理性来反驳或建构,因为它不是按照某种形而上学方法从第一原理演绎出的思想体系,而是无数人真实生活世界的历史性凝聚。各大文明的轴心突破,都是在旧时代怀疑和虚无的危机中,既依靠哲学思辨,又重返经典与生活世界,来为文明重新奠基。因而,哲学的意义探寻与有限度的怀疑批判,与经学主张的神圣性完全可能相得益彰。
接下来,我们讨论“中国古典学”的另一个重要方法——“诠释学”。作为文献释读技艺的方法论(特殊)诠释学,与关注理解普遍本质的存在论(普遍)诠释学,这两者与中国经典诠释学建设的关系已有多人论及,此不赘述。笔者想要强调的是,诠释学对“中国古典学”建设可能提供的两个重要思想资源:第一,重新理解经典的存在方式;第二,削弱关于经典本义的实证性追求。二者相辅相成。
经典的存在方式需要物质性载体,但它所承载的意义世界的存在方式并非现成性存在,而是在诠释与实践中不断生成的历史性存在。后人的注释不断汇入并成为经典存在的一部分,无数个体理解与实践的历史就是经典的具现与外化。看不到这种意义生成式的存在方式,经典就会沦为历史之陈迹(考据学追寻的事实真相),或与诠释史无涉的独断体证对象。我们不是要度越汉、唐、宋、明的层层遮蔽去直契经典本体或本义,而是重走一遍文明精神的历史道路,融汇流裔去理解原始经典。
由此可见,“中国古典学”对文明经典的研读应当吸纳诠释学的上述洞见,因其根本诉求是接受经典的发问、思考和实践的指引,而非提取现成的真理答案。其实,中国古代也对上述洞见有所领会,对于圣人之意的理解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谓的“本义”。例如,王弼将《周易》的“圣人之意”解释为“体无”而恒言“有”,又本于《系辞》将“无”之向度阐发为“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唯变所适”,并通过“忘言”“忘象”等玄学释经方法,实现了对汉代易学一味探寻定理规则的解构。朱子更是明确反对研读《春秋》是为了锚定圣人“肚里事”。中国古代关于经典的诠释,绝不能一概而视为墨守探寻“本义”的成规。
总之,在中华文明主体性与文明互鉴的视野下,“中国古典学”关于中华文明的研究方法应该是以哲学与经学的思维方式为主,以子学的思维方式为辅,以史学、文献学为理论工具;并以诠释学的洞见来超越近代古典学、古文献学和语文学中的实证主义倾向,结合中国古代的诠释传统来研读经典。
结语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莫斌 常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