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一个以党项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居地方政权。出土西夏文献以西夏文字文献为主,也有大量汉文文献,还有藏文等其他民族文字文献,而且不乏同一文献出现多种不同文字的译本。多文种文字文献的集中出现,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而附属于文献的序跋题记,更详细记载了不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细节,它们或阐述民族交往交流的重要认识,或记载多民族知识阶层合作共创中华文化成果,或记载多民族百姓共同参与生产实践。这些材料极大地丰富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料。
出土西夏文献中,有一种夏、汉双解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该书成书于乾祐二十一年(1190),作者为党项人骨勒茂才。全书按照天、地、人三才顺序排列,每部分又分上、中、下三品,将800余条日常生活用语分为9类。每条词语排列4行,中间两项字体稍大,为西夏文和汉文对照,意义相同;左右两边为注音字,最左一行以西夏字注相邻汉字的读音,最右一行以汉字注相邻西夏字的读音。夏、汉双解的编排形式非常巧妙,前三行供学习西夏语使用,西夏字形音义俱备;后三行供汉语学习使用,汉字形音义皆全。书前有序言两篇,分别为内容相同的西夏文和汉文文本,有段文字摘录如下:
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俱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
序言立意很高,直面民族交往中的隔阂与弊端——“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并指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即语言不通。这一深刻认识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语言不通一定程度上仍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的障碍,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破除语言交流障碍,加强民族共同语的推广与普及就显得十分重要。
在北京房山云居寺,保存了一本藏汉合璧文献——《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文献前面有一则题记:
诠教法师、番汉三学院并偏袒提点 美则沙门 鲜卑宝源 汉译;
美则沙门 鲜卑宝源 汉译;
显密法师、功德司副使、 卧英沙门;
卧英沙门;
演义法师、路赞讹、 赏则沙门 遏啊难/捺吃哩底梵译;
赏则沙门 遏啊难/捺吃哩底梵译;
天竺大钵弥怛、五明显密国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 乃将沙门
乃将沙门  也阿难捺亲执梵本证义。
也阿难捺亲执梵本证义。
贤觉帝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偏袒都大提点, 卧勒沙门 波罗 显胜;
卧勒沙门 波罗 显胜;
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 再详勘。
题记记载了这一文献在西夏传译校勘过程中的系列人物,他们是汉文本译者鲜卑宝源、梵译者遏啊难捺吃哩底、执梵本证义者 也阿难捺、详勘者波罗显胜及仁宗皇帝。在俄藏西夏文献中,有与之几乎相同的一则西夏文题记。二者差别在于:其一,汉文本译者鲜卑宝源未在西夏文题记中出现;其二,汉文本中的“显密法师、功德司副使、
也阿难捺、详勘者波罗显胜及仁宗皇帝。在俄藏西夏文献中,有与之几乎相同的一则西夏文题记。二者差别在于:其一,汉文本译者鲜卑宝源未在西夏文题记中出现;其二,汉文本中的“显密法师、功德司副使、 卧英沙门”不够完整,依照西夏文本,后面缺少了“周慧海番译”等字,西夏文本帮助我们明确了西夏文本译者为周慧海;其三,西夏文本增加刻本的书手李长刚。
卧英沙门”不够完整,依照西夏文本,后面缺少了“周慧海番译”等字,西夏文本帮助我们明确了西夏文本译者为周慧海;其三,西夏文本增加刻本的书手李长刚。
结合对夏、汉、藏三种文本的解读,我们获知了这一文献在西夏流传的脉络,即由梵本译成藏文,再由藏文本分别译为汉文和西夏文两种文本。也就是说,在西夏时期这一文献有了同源、同题、同时的夏、汉、藏三种文本。这三种文本就是题记中记载的诸多人物分工合作共同完成的。
汉文本的译者鲜卑宝源,姓氏为“鲜卑”,对应的西夏词语出现于西夏文《三才杂字》,为西夏番姓之一,同一词语也出现在西夏文《类林》书中,用于表示“鲜卑族”的族名。可以肯定,西夏番姓中的“鲜卑”是由族名“鲜卑族”发展而来。西夏文本译者(番译)周慧海,则是一个典型的汉姓。藏文本译者(梵译)遏啊难捺吃哩底(ānandakīrti)是个梵文名称,其人即是吐蕃著名译师贡噶扎(Kun-dga'-grags),他经常与 也阿难捺(jayānanda)合作从事梵文译藏文的工作。
也阿难捺(jayānanda)合作从事梵文译藏文的工作。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流传与翻译工作就是由上述人员合作完成的,他们是来自天竺的 也阿难捺,来自吐蕃的贡噶扎以及西夏的鲜卑宝源和可能是汉人的周慧海。除这部文献之外,还有多部文献也出自这一团队之手。操持不同语言的人们本着佛学东传这一共同目标,在短期内完成一系列多语言、多文本的同题、同源文献的翻译,这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这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创文化佳作的一个重要例证。
也阿难捺,来自吐蕃的贡噶扎以及西夏的鲜卑宝源和可能是汉人的周慧海。除这部文献之外,还有多部文献也出自这一团队之手。操持不同语言的人们本着佛学东传这一共同目标,在短期内完成一系列多语言、多文本的同题、同源文献的翻译,这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这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创文化佳作的一个重要例证。
山嘴沟石窟出土西夏文献中,有一木活字印刷文献残件,存留了这一活字本印刷工序和参与人员的详细记载。在这几道工序中,有一道工序为拣字。相比其他工序,拣字的人员名单颇为庞大,涉及14人。这段文字翻译如下:
拣印字者:皮慧照、梁慧勇、段慧照、跖吉、慧盛、梁慧成、嵬名慧善、杨慧能、妹勒慧盛、魏慧善、□慧光、危地慧胜、贾囉讹慧宝、梁朵只。
这则材料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其他工序不超过3人,但拣字多达14人,反映了木活字在创制造轮法之前检字不易的实际情况;二是从姓氏和人名来看,这组拣字工的民族成分复杂,至少涉及汉、党项以及藏族等多个民族。其中“皮”“梁”“段”“杨”“魏”皆是汉族姓氏,“嵬名”“妹勒”“危地”等都是西夏姓氏。
最后一人“梁朵只”之“朵只”一名,西夏文读若 。该词源自藏文rdo rje,意即“金刚”,寓意永恒、坚韧不拔,是藏族人名中的一个常见名字,现今多翻译为“多吉”“多杰”。西夏文献序跋题记中,这一名字也经常出现,旧多译为“那神”“那征”,实则译为“朵只”更为理想。相同概念和寓意的名字,在西夏文献中又有读若
。该词源自藏文rdo rje,意即“金刚”,寓意永恒、坚韧不拔,是藏族人名中的一个常见名字,现今多翻译为“多吉”“多杰”。西夏文献序跋题记中,这一名字也经常出现,旧多译为“那神”“那征”,实则译为“朵只”更为理想。相同概念和寓意的名字,在西夏文献中又有读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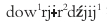 者,一般出现在元代的西夏文献中,这是参照了元代蒙语翻译藏文rdo rje的译法。蒙语中,藏文rdo rje读为dorji,rje的前加字仍发音,汉文也因之翻译成“朵儿只”,现多译为“道尔吉”。“梁朵只”的姓氏似为汉姓,他可能并非藏族人,更像是采用藏族名称的汉人或者党项人。因寓意永恒、坚韧不拔的藏文rdo rje一词,在藏族地区、蒙古族地区多作人名使用,同样在西夏时期也为汉族或党项族广为使用,这正是各民族深入交往交流交融相互借鉴的结果。从姓氏、名称上看,山嘴沟石窟这则题记中的拣字工,涉及汉族姓氏、党项姓氏、藏族人名,一道活字印刷的工序就是由包含多个民族的拣字工共同完成的,这已是实实在在的民族交融。
者,一般出现在元代的西夏文献中,这是参照了元代蒙语翻译藏文rdo rje的译法。蒙语中,藏文rdo rje读为dorji,rje的前加字仍发音,汉文也因之翻译成“朵儿只”,现多译为“道尔吉”。“梁朵只”的姓氏似为汉姓,他可能并非藏族人,更像是采用藏族名称的汉人或者党项人。因寓意永恒、坚韧不拔的藏文rdo rje一词,在藏族地区、蒙古族地区多作人名使用,同样在西夏时期也为汉族或党项族广为使用,这正是各民族深入交往交流交融相互借鉴的结果。从姓氏、名称上看,山嘴沟石窟这则题记中的拣字工,涉及汉族姓氏、党项姓氏、藏族人名,一道活字印刷的工序就是由包含多个民族的拣字工共同完成的,这已是实实在在的民族交融。
骨勒茂才深刻认识到语言相通在民族交往交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编著《番汉合时掌中珠》以推动解决番汉交流沟通之障碍;云居寺题记所载是操持不同语言的各民族学者为传播文化典籍合作分工的典范,是文化阶层在民族交往交融过程中共创中华文化典籍的实践;山嘴沟石窟题记则反映了多民族百姓共同参与活字印刷的生产实践,亦是典型的民族交融的生动例证。
(作者系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