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交通史研究中,物的流动,宗教、政治制度的扩张与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文明互鉴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但在既有研究中,以中西法治文明交流为主题的研究成果数量偏少且视角单一,侧重观察西方法治文明对中国传统法的冲击,即西法东渐。李栋所著的《东法西渐:19世纪前西方对中国法的记述与评价》一书则反向为之,以西方人对传统中国法的记述为视角展开讨论,即东法西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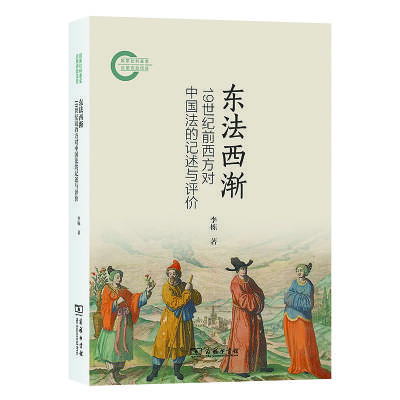
■《东法西渐:19世纪前西方对中国法的记述与评价》,李栋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9月版
史料运用情况。对于法律史作品来说,史料翔实与否决定着书的质量。该书涵盖史料时间跨度大,文字散见于游记、书信、日记、回忆录、官私文件等多种文本,数量大、类型多、内容琐碎;涉及人群多元,有思想家、传教士、商人、外交官等,其国籍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荷兰等。晚近以来,这些文字记述大都已被翻译成中文公开出版,但要将这些散见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别、不同语种、不同群体笔下有关中国传统法的零散文字搜集在一起,并进行整理、甄别、归类依然是一件耗费心血的工作。作者尽可能囊括了迄今为止与该书主题有关的全部中文文献,基本做到了史料翔实。
由于史料产生的时期不同,记述者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差异较大且目的各异,加之记述者又大都没有接受过法学教育,导致史料的系统化程度较低。学术界对于如何使用这些史料并无可资借鉴的经验,但作者却有相对成熟的想法:按时间、国别分别引用,并对史料功能加以区分。作者认为,19世纪之前,在英国人小斯当东译介《大清律例》之前,西方人对中国法缺乏系统的了解渠道,记述内容以亲身体验或者道听途说为主,具有一定的私人性和非正式性,是一种“直观”的认知,碎片化特点明显。但这种局部的“直观”认知,往往又是准确的。在制度史研究中,这些“直观”的史料只能作为档案材料的补充。但在观念史视野中,这些记述的“直观”属性却是历史现场感的最好体现。此外,记述者群体的多样,关注对象、关注视角的不断切换与游移带来了不同的主观体验,将这些体验连缀起来,其实就是某一特定时代西方人对中国法的普遍认知。需要提及的是,作者心态平和,在史料使用上既不卖弄任意堆砌,也不任性随意取舍,使用较为自然和合理。
主要学术价值。该书的议题是观察19世纪前西方人对中国法的认知状况,以及这些认知对西方法治发展产生的影响。在当下中国,这一想法虽说不上新颖,但较有冲击力,并具有以下意义:一是时代意义。该书议题以文明互鉴为立论基础,突破了西方中心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然,作者也承认当时的东法西渐是在西方主导下产生的,态度既务实又客观。二是方法论意义。在全球史观盛行的当下,该书议题为全球法律史书写提供了新的可能。以中国法为个案、以双向流动为框架进行观察,也为中西交流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此外,该书的学术价值还体现在其核心学术观点上,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梳理出西方人对传统中国法认知的多重面向。如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清承明制”,强调明清法制的延续性,甚至一致性。然而,在西方人笔下明清两朝的法律制度却差异较大。究其原因,生活于不同时代的西方人自身在知识结构、认知基础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他们以不同的观察视角、不同的价值评判尺度,对中国法形成不同认知。此外,西方人面对的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但他们往往只能观察到中国法律的某一个或几个侧面。
二是构建起西方人对传统中国法的认知图像。一方面,19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于中国法的记述呈现出一种自发的“无意识”状态,另一方面,这种状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又保持着相对稳定。该书按照历史顺序将这些认知划分为“古代希腊罗马时代”“马可·波罗时代”等七个时代,并对七个时代的历史记述进行爬梳、整理,概括出不同的特点。
三是得出相关启示和结论。该书认为,将近代以前的传统中国法置于西法东渐和东法西渐双重视角下进行定位,才更为准确。西方人对中国法的评价,经历了从“文明的中国”到“野蛮的中国”、从“君子之国”到“孩童般的义务”的递嬗。这种递嬗并不完全符合真实,但借助“他”者的观察对我们科学认知传统中国法具有启示意义。与此同时,对于19世纪前的西方人而言,遥远的中国始终是一片“想象的异域”,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基本都是在其原本对中国的想象中进行印证或修正而已。换言之,西方人对中国法做出何种想象,其实完全取决于他们的需要。在马可·波罗时代,西方人渴求财富与权力,他们便着重观察中国的富有和强大;在伊比利亚航海时代,西方人需要发展的刺激和标尺,中国法中关于道德的侧面就又被适时地展现给了西方人。
存在不足之处。一是结构相对分散。该书按照时间顺序分为古希腊罗马时代、马可·波罗时代、伊比利亚时代、耶稣会时代(一期)、耶稣会时代(二期)、启蒙时代、殖民时代等七章,分阶段进行论述。笔者以为,尽管西方对中国法的观察起始于秦汉,但真正成规模并有研究价值的记述则集中于新航路开辟后的明清时期。过于求全的章节安排,实际上分散和弱化了主要议题,直接从明清开始讨论可能会更好。二是核心结论有待进一步论证。作者认为,伴随着东法西渐,中国法参与到了西方法的建构之中,这是一个大胆且极具挑战性的结论。该书在“结论”部分对此进行了专门讨论,但论证依然偏宏观,尚需细致的梳理,特别是对关联性的挖掘。晚近以来,一些国内学者认为西方人对中国法的认知是一种“法律东方主义”的傲慢与偏见,该书研究表明这一看法并不完全客观。同理,突出传统中国法在全球法律史中作用、地位的结论也需谨慎。
(作者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