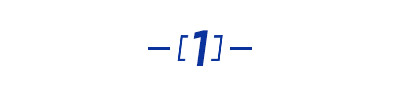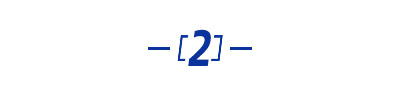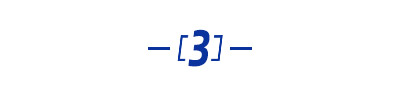知识是怎么来的?这似乎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前人已经对此作出了诸多回答。但是,在中国的学术界,这个问题似乎又必须要回答,特别是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更值得人们深思。区域国别研究早已有之,而今天区域国别学之所以成为国家急需之学,实为时代发展的必然。
重构区域国别学理论和方法的意义
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与外部世界的互动空前紧密,这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全面、系统、深刻的视角去认识世界,并主动承担起服务世界和平发展、为全球治理贡献智慧与方案的大国责任。正是这一时代使命,将区域国别学推向了显学之位。我一直主张区域国别学应是一门行走世界、认识寰宇、服务天下的大国之学、战略之学,其根本立足点即在于此。
在明确区域国别学的时代价值与战略思考后,有必要对区域国别学所需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反思和重构。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新兴交叉、务实应用学科,区域国别学的理论构建必定要上承国家战略需求,下接区域国别现实情境,避免陷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浮于虚空、自我臆想、概念堆砌”的学术困境。这意味着,其理论建设应紧紧围绕中国与世界各区域的交往实践展开,着力构建具有理论深度、实践价值与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知识体系,而非简单移植既有学科或西方理论框架。中国与世界上各区域各国家合作问题的边界在哪里,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边界就在哪里;中国与世界上各区域各国家合作交往当中的问题有多复杂,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工具、理论和方法就应该有多复杂,这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应秉持的创新精神。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一定是源于对实践的总结、提炼和升华。没有实践做基础的理论,就是玩概念,只是建立在沙丘上的大厦。即使有了实践,也不一定就能上升为理论,何况很多理论就没有实践过。
实践与应用导向性作为区域国别学的内在要求,决定了其研究方法必定超越传统的文献梳理与短期田野调查模式,因为无论是长期置身于国内的图书馆、档案室,或者是到一国一地短期访问调研,通常都只是去对一些现有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和再加工,或是对当地情况作“游览式”的浅层观察。这类研究不仅难于回应研究对象当下的核心关切,其产出的只能是隔靴搔痒、浮于表面的“二手知识”。资料固然可以做参考,方法可以起辅助作用,真正具有建设性的区域国别研究,必须立足于在对象国家或区域中长期、深入地扎根实践所积累的知识基础之上。研究者需主动融入当地社会,要去关注国家关心、社会关心、百姓关心的问题,敏锐洞察其在国家治理、社会发展与民生福祉中的真实挑战,从“观察者”转变为能够介入对话、解决问题的“参与者”“实践者”。最终目标是使我们的学者能把研究对象的事情说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也能在研究对象的特定事务上,具备“摸得到路、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的行动力。
以实践为导向构建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早就指出“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也就是说所有知识都是首先来自实践,离开实践,就不能产生真正的知识。正因如此,人们才会说“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基于实践基础。关于区域和国别的知识则更是如此,只能来源于实践。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任何研究者都要从零开始去获取一国的知识,我们完全可以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去获取知识。但是,如果要有所创新,要真正从事一国一区域的研究,则必须到实地去感受、去观察、去交流、去体悟,去检验你通过学习二手资料得到的认识,才能超越前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讲的就是既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又要超越前人。因此,真正的知识生产来自实践。
关于一国的直接知识来源于实践,关于一国理论认识必须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区域国别学的理论构建则须建立在更多的实践基础之上。区域国别学理论,不是在书斋里、沙发上能够产生的。关于一国知识的生产,比如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地理的知识,必须到现场去,所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得到普遍重视。关于理论的生产,更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积累,才有可能提出真正管用的理论。
多年以来,我经常和我的学生讲,做非洲研究,既要懂非洲,又要懂中国;既要知道非洲的需求,也要知道中国的需求,否则肯定做不好非洲研究。2007年我到浙江师范大学创办非洲研究院时,就坚持一方面要做非洲研究,一方面要推动中非关系发展。这是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2022年在各种讲座报告中,我就讲区域国别研究要“两头落地”,强调不但要“落地”,还必须“两头”都能落地。我还提出“两头能落地,中间挑得起”的理论,这是基于我近40年来研究非洲、行走非洲、力求推动中非关系发展的思考和实践的总结。通过我们的工作,我们越来越懂非洲,也越来越懂中国,促进了浙江和金华对非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中非两地人民的来往,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懂得“两头落地”的意义。我也更明白,作为学者,我们的职责就是“联系两头、挑起两头,促进两头”交流交往。
让区域国别学成为“有用”之学
反击“文科无用论”,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让文科有用。一门学科存在的价值,首先是“有用”。“有用”的标准可以多种多样,指导实践、解决问题是有用;鼓舞人心、提供情绪价值是有用;愉悦身心、享受时光也是有用。区域国别学有用,则必须能服务中国正确认识一国一地,从而有利于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推进中国与世界的合作。
2024年3月8日,中非智库论坛第十三届会议上,我们牵头联合中非50个国家智库学者共同发布了“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外交部部长王毅高度评价这一共识,“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表达了“全球南方”的共同心声。发布“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为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奠定了共同的认知基础。在峰会即将召开之际,习近平主席复信我院名誉教授、南非前资深外交官格罗布勒等来自非洲50国的学者,得到非洲学术界广泛而热烈的反应,为召开峰会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后来,为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加强中国与非洲国家在人权领域交流合作,2025年8月,我带领学术团队再赴非洲,并于当月22日与中国人权研究会、埃塞俄比亚政策研究所在埃塞俄比亚共同主办了首届中非人权研讨会。会上,来自中国和40余个非洲国家的超过200名人权领域官员、专家学者及有关社会组织、企业、智库、媒体代表等,围绕“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携手实现发展权”主题展开讨论,并共同发布了《中非发展权亚的斯亚贝巴共识》,这成为中非合作中又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知识产品。
这些区域国别学服务国家战略的典型成功案例充分证明了文科不但有用,还有“大用”。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能有所实效,首先得益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中非合作的落实落深,其次也离不开我们40年来坚持走原创的中国非洲区域国别学科建设道路,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行走非洲,和非洲人交朋友、拜非洲人为师,在互学互鉴中构建高质量的人际网络以及多层次的合作伙伴关系。
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知识,才能服务于实践;书斋里生产出来的知识,只能被用来证明“文科无用论”。我们只有坚定地相信并践行“区域国别知识是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一步一个脚印到对象国行走,才能真正生产出管用的区域国别知识,才能产生真正的区域国别理论。多年来我坚持行走非洲,积累了50余万字的非洲行纪,正是我对这一信念的认同与坚守。
回想起2024年3月,我在坦桑尼亚湖区农村开展调研时,受邀参加第四届中国区域国别学50人论坛。当时,我就站在田地中,录制了一段关于“如何建设‘区域国别学理论与方法’二级学科”的视频发言。录制结束时,天刚破晓,太阳火红,远处广阔的草原一片生机。那一刻我深切感到,区域国别研究最富活力的舞台,理应是世界各个角落的土地。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区域国别学学部主任、非洲研究院(非洲区域国别学院)院长、二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