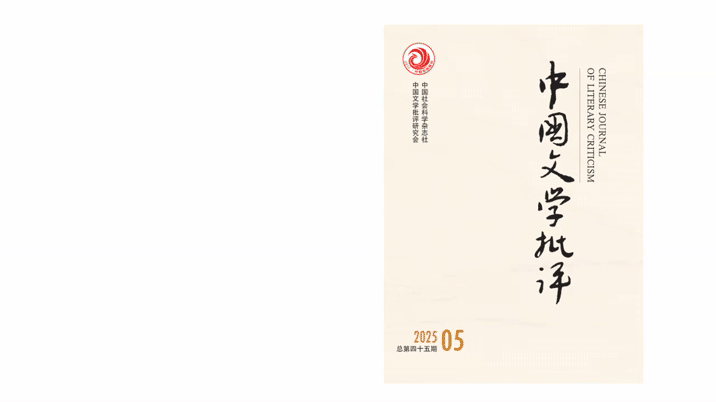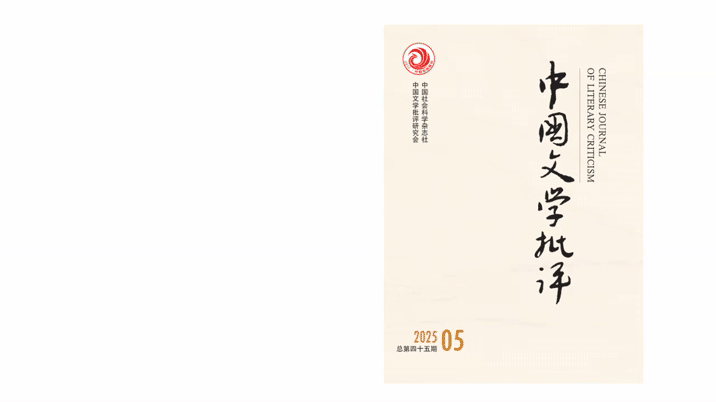
近年来,聚焦乡土生活的时代变迁,表现乡村振兴主题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宝水》《雪山大地》《经山海》等一系列作品,或注重城乡关系下的乡土变迁,或以浓郁民族特色的农村生活为表现主体,或凸显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重大主题,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活形态与生命追求。马金莲的小说《亲爱的人们》聚焦一个山村与一个家庭,按照俗世生活的真实逻辑,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脉动融入乡村日常的家长里短,谱写了一部反映乡村变迁与人生奋斗的平凡史诗。作品以细腻的笔触,耐心地讲述着西北黄土大地上的人情世态,表现乡村社会结构状况,准确触摸到几十年来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并在体味生活的坚韧中表现个体的生命之光。作家基于自身的情感记忆与伦理体验,在表现乡村农事劳动与家务活动的时间容器中,守望乡村世界的情感与伦理,深情揭示时代变迁中农民生活的幸福密码。在叙事策略上,作品中多重视角相互融合,通过日常生活与传统民俗的诗化表达,生动描绘了一幅西北山区的风俗画,也真切表现了当代农民寻求命运改变的心灵史。
一、从乡村社会结构中触摸发展的内生动力
小说融宏观的时代变化于一系列微观的生活细节,从羊圈门的通电通水、修路修桥、农民进城打工,到视频直播、网红电商、文旅结合、婚姻生育等,所有这些生活事件都以马一山一家为核心,辐射到羊圈门多元的乡村社会结构。作家以一个乡村在场者的姿态,通过抢水、修路、通电、选队长接班人等情节,真实表现了羊圈门的乡村社会结构,在烟火生活的漫长与艰辛中书写乡村普通人的韧性和憧憬。其中有羊圈门围绕队长一职竞争的家族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的现代力量、女性作为烟火生活的支撑力量。三个层面的话语力量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不断地起落和生长,共同编织成乡村社会的结构系统,展现了乡村社会自然而富有生气的生活形态。这些不同层面的话语力量,既有民间文化中出人头地的坚韧追求,也有知识改变命运的现代思维,还有乡村女性支撑起来的充满温情的“过日子”的生存哲学等。作品透过乡村社会的“常”与“变”,从乡村的历史和现实中探讨乡土中国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第一,凭着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体验,作家从多个层面深入描写了西北农村羊圈门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首先是羊圈门几个家族之间关于队长一职的竞争。羊圈门由李姓、牛姓和马姓三大家族构成,其中的劳动力、财富、教育以及来自队长手中的资源分配优势,直观呈现了乡村社会人际关系与利益关系的复杂形态。小说没有像一些家族历史小说那样,重点表现乡村世界的权力争夺和人性之恶,而是集中在家族力量的平衡与个体奋斗的日常生活中。作品走进乡村社会的现实,客观表现三个家族对羊圈门队长职位的争夺,无论是描写公共资源的分配,还是服务大局与面对风险,都纳入脱贫和实现乡村振兴的轨道。“队长”一职负责传达各种惠民政策,组织与推进各项乡村建设活动。通电、修路、通水,以及乡村其他各项事业都落在队长这一职务主体上。李有功担任队长时,鼓动村民打架,甚至阻止村集体修路。小说通过抢水和翻车两个事件,侧面表现李有功为个体和家族谋求利益的专权与自私行为。当李有功准备搬离村庄而被打成重伤后,队长一职落入同族的老实人李有劳手中,这是村中家族力量平衡的结果。李有劳的尽心尽力,带来了羊圈门社会生活的稳定,却难以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其次是马德福和马一山因为德高望重而拥有话语权。二者凭着他们的为人、阅历与学识,在几个家族中占有重要地位。马德福当过队长,为人公正,且经常看书,懂一些简单的中医知识;马一山高中毕业,当过代课教师,为人低调而厚道。二者在羊圈门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抢水打架事件在李有功的鼓动下不断升级为牛、李两族的械斗之后,马一山和马德福挺身而出,制止了这一事件。李有功不担任羊圈门队长一职后,牛、李、马三族人均认可的老实人李有劳担任队长。马一山则凭借自己的智慧和知识,在背后不断给李有劳出主意,帮助他处理村中各种事务。最后是以孔武强悍的牛三炮为代表的牛家,在村中占有一席之地,与其他家族之间形成冲突和制约。
更重要的是,小说描写了乡村家族传统的时代变化,这与乡村发展新的带头人密切相关。随着乡村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在外面坑蒙拐骗回来的牛八虎,骗取队长李有劳的信任,卷走村民的集资款外逃。马舍娃有文化有能力,一方面用法律手段解决了因牛八虎而导致的村中经济与家族之间的危机,另一方面与妻子摆兰香一起开展多种经营,踏实创业。最后在扶贫工作组的支持下,他成为羊圈门致富的领头人,结束了原来李、牛、马三个家族之间的离散状态。三个家族之间的权力缠绕,体现了熟人社会的双面性,既有个体私利带来的冷漠和阴暗,也有温情脉脉的人情纽带。小说没有像《白鹿原》那样,将视角伸向家族历史的悠远天空,而是以争水打架、翻车、通电、修路、引水等民生问题与事件为聚焦点,在呈现羊圈门的日常生活状态中,切实理解农民的日常奋斗与改善乡村生活条件的关系,把握乡村社会传统的惯性和不断前行的动力。
乡村现代化的内生动力还体现在一些现代生产工具和消费品的出现和刺激。这些现代器物一方面直接彰显了乡村生活水平的提升与改善,另一方面则体现了民间社会中“出人头地”的诉求。羊圈门通电后,三三家不惜代价,购进了村子里第一台电视机,为失明的三三和委屈了一辈子的三三媳妇赢得所有村民的羡慕与尊重,使他们在村中扬眉吐气了一段时间。嘎西购买第一台奔奔车在村子里跑运输,弥补了李有功失势后李家地位的下降。舍娃从传销组织中逃回家,马家陷入困顿,刚刚参加工作的祖祖为弟弟赊账买了村里第一台摩托车,后来又为其购买了村里第一台小汽车,这让马一山病倒后的马家重新受到村人的羡慕。这些现代器物第一次进入乡村,并不是简单表明现代伦理对乡村社会的冲击,而是关联着出人头地的潜在话语权,关联到乡村日常生活中的人心、人情和一系列人性的隐秘之处。这些器物第一次出现在羊圈门,体现了乡村生活日新月异的时代留影,更深层地体现了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欲望流动及其衍生出来的发展动力。
第二,小说描写了“知识改变命运”的现代力量。这一现代力量打破了惯性存在的乡村家族力量的平衡,将乡村引向现代化的发展视野。纵观羊圈门的发展变迁,早年的马一山和软头,都属于乡村智者形象。他们不但是传统家族力量制衡下的隐逸者,而且是推动乡村发展的新力量的培育者。软头受到李有功的挤兑,选择在荒野放羊为生,却保持清醒的头脑,分析和思考着羊圈门各个家族的未来走向。他不惜一切代价,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马一山坚持让孩子上学。祖祖在北京上大学,率先走出乡村,并考上了乡镇一级的公务员,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导者。马舍娃高考前放弃了学业,把机会让给了姐姐。他在一次次的失败之后,积极参加技能培训,最后成为羊圈门的致富带头人。他们的生活事实生动诠释了“知识改变命运”的现代逻辑。小说在马一山和软头二人的观念及其后代的生活出路中,验证了“知识改变命运”。他们身上既体现了传统的耕读文化,又有现代的科学思维。可见,“知识改变命运”不仅让年轻一代改变了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也为乡村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第三,小说刻画了乡村女性朴素的生命形态。乡村的生活除了抢水打架、通电、修路等一系列事件,还有一个最为平实的女性生活图谱,支撑起羊圈门的半边天。它存在于众多女性的家长里短,以及“过日子”的忍受与前行中。这是乡村社会充满温情的烟火世界,也是乡土小说最富有质地感和厚重感的所在。第一类形象是众多家庭女性,她们没有文化,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如马一山妻子、二虎妻子、二愣妻子等。她们内秀含蓄、隐忍坚强,既要协助丈夫在山里收洋芋、种胡麻,又要下沟挑水、上山放羊,也要做饭洗衣、伺候一家老小,还不时地与自己的丈夫、家人吵架斗嘴,将日常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充满人间的烟火气。这些女性淳朴而善良、简单又直接,对生活、对人生没有太多复杂和深厚的认识,但身上的力量却通过代际传承而稳定了乡村生活秩序,为灰暗、贫穷的日子增加了亮色和暖流。马一山妻子对公公的孝顺、对三三一家的帮扶、对丈夫的隐忍、对三个子女的呵护,直接影响了舍娃、祖祖与碎女之间的抱团互助。她作为女性的价值和美德构成了羊圈门的生活范型,既体现着一种乡村内在的生活秩序,也是一代代人延续和继承下来的最朴素也最神圣的传统力量,支配和影响着一代代人的生活内容和生活品格。
第二类形象是新一代有知识、有文化、有追求的女性,她们身上有通往新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更有传统女性的善良与包容,如祖祖和摆兰香。祖祖在家人的支持下,上了大学,最后成为一名乡镇公务员,带领农民为乡村振兴而奋斗。小说没有重点写她大学毕业后面临的城乡文化冲突,而是写她对原生家庭的报恩,结果导致与丈夫王全有的离婚。妹妹生产大出血时,她有孕在身,不仅在医院里跑上跑下,还拿出自己的所有积蓄,帮妹妹交上手术费,在救下母子二人的同时,因过于劳累而流产。面对当年为了自己而放弃学业的弟弟,她先后为其买摩托车和小汽车,并送弟弟去参加技能培训。面对丈夫一家对她的冷淡,她在生下孩子后毅然选择了离婚,全力投入乡村振兴的工作。摆兰香为了照顾病重的母亲而放弃了学业,又为了照顾父亲的晚年生活而耽误青春。她聪慧又爱学习,最终与舍娃结合。正如祖祖对准备返乡创业的弟弟说:“我们守好老家,其实就是守好了人生的后花园,有了这个后花园,一个人不管在外头漂泊多久,身后都有一条退路。这才是人生最幸福的事。”可以看出,这两个女性与时代的步伐同行,她们有了现代女性的主体意识,也体现了乡村传统的伦理美德。
第三类女性形象既体现了乡村女性意识的本能觉醒,又体现了乡村生活的褶皱和暗色,如三三妻子和碎女。年轻漂亮的三三妻子,偏偏嫁给了一个失明的男人。她常常借着进货而跟着别的男人去镇上赶集。她购买了村中第一台电视机,吸引村民们都来她家看电视,这一行为体现了她心气高却无法满足的性格,其内心的酸楚无人可知。最后,她在牛八虎的鼓动下与其一起私奔。碎女上中学时早恋,而后早婚、生子,却丝毫没有做好成家的准备。孩子的降临、生病都让她无法接受,只能在摔摔打打中忍受。她后来拍视频、发抖音,将羊圈门的本色生活推介出去,成为造福家乡的新生力量。
可以说,羊圈门的女性们犹如大地之母,她们在艰难生活中的隐忍和承受、对家人的呵护与关爱,构成了乡村社会结构中一股看不见的力量。这些不同的女性个体,支撑起乡村家庭生活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在男性世界之外营构了乡村社会的烟火秩序。这些女性的日常生活,既体现了乡土世界中传统孝悌的柔软与温暖,又隐含着一些现代女性个体的意识与追求。正是这些女性身上的力量,形塑了乡村代代相传的生活范型,为乡村脱贫和走向富裕提供了稳定与和谐的生活保证。
小说以羊圈门从通电到文旅结合等一系列乡村建设活动为纽带,将笔力落在乡村生活的细部,展现引导乡村走出贫穷、奔向富裕的各种力量。乔叶的《宝水》透过来自城市的地青萍的视角,来观察和审视乡村现代化的过程与问题。乡村与城市往往处于二元对立状态。小说表现的是乡村振兴等时代话语如何进入宝水村,而推动乡村的现代化。《亲爱的人们》则立足于羊圈门竞争队长一职的家族话语、“知识改变命运”的现代话语和作为烟火生活基础的女性话语等乡村富有质地感的层面,分析乡村社会如何面对时代需求激活内生动力。因此,小说没有在乡村权力的争夺中展现人性的复杂,也没有在城与乡、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中表现乡村生活的苦难或进步,而是在真实表现乡村的世态人心与人情伦理中,理解和把握乡村社会的传统惯性、现实变化及其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二、在乡村劳作的细节中守望乡土传统的情感与伦理
《亲爱的人们》记述了几十年乡村发展进程,但重心不在写历史,而是以乡村的农事与个体的成长为解说时间的路径,将时间定格在一系列的情感与伦理记忆中,为我们理解乡村社会和人情世态提供了有效的方式。因此,小说虽然涉及几十年的乡村历史变迁,却少有以往小说的历史反思意味,而是在乡村变迁的河床中充盈着生命的感性细节,其中有乡村“四时”劳作的繁忙与荣光、乡村生活的承受与奋斗,以及对乡村传统与伦理结构的深情守望,直接揭示了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幸福密码。
首先,四时的农事劳动不仅是求生存的手段,更化入民族性格中成为一种稳定的情感结构,形塑着乡村的日常行为和生活信仰。对于作家笔下的世界而言,这里的“情感结构”既指沿袭多年的劳作经验和生命记忆,又指这种记忆对一代代人造成的情感和心理影响,从而与人们传统的伦理情怀对接,并在日常的农事活动中对劳动产生一种类似于信仰的伦理形塑。作家熟悉西北乡村与时令紧密相关的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等农事日常生活,书写了一系列循环往复的农事活动,挖洋芋、种洋芋、割麦子、割韭菜、收胡麻等。这些农事活动上升为羊圈门人日常的生活范型,最终化作劳作经验,成为乡村共通的感觉结构。因此,作品不以一个异质空间的视角来看问题,而是慢条斯理地书写各种农事劳作的场景,在表现羊圈门的日常生活中体现一种悠徐自然的时间秩序。小说开篇便是马一山和妻子在北山梁顶上挖洋芋、拾洋芋的场景,夫妻二人弯着腰,一窝一窝地挖洋芋、抖掉洋芋蔓子,一个一个拾起来,然后抖掉湿土。种洋芋的时候,二虎开着四轮头在前头耕,二虎媳妇和马一山妻子在后面接洋芋籽。每人提个柠条笼子,跟着犁沟走,小半步丢一颗。舍娃抱一个铁盆子,匆匆跟着犁沟小跑,将一把一把的化肥撒进犁沟。小说在这些劳动场景中,既体现了西北大地生命图景的历史绵延,又深邃地表达了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生存密码。“从把农事与时间上的永远相联系起来的那一刻起,她小说中的农事就具有了自身的生命形态。”收洋芋、种洋芋等农事劳作与人的生死相互映照,指向了包括自然与人在内的生存法则——生与死、盛与衰、枯与荣。在这些反复出现的琐碎、繁重而充满烟火气的劳作中,作品产生了一种地老天荒的永恒感、秩序感,自然唤起人们对生命、幸福等命题的沉思。
同时,作品透过一系列的乡村农事与生活细节,将劳动纳入从生存到追求幸福的伦理轨道上,展现一种过日子的生活信仰。贺绍俊认为:“宁夏的文学相当精准地表达出建立在前现代社会基础上的人类积累的精神价值,它是由伦理道德、信仰、理想、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等构成的。”在小说中,“日子”是一个高频词汇。“日子”不仅是一种“循环的自然时间节奏”,更象征着羊圈门人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下坚韧的生活形态。它不是空洞的、无形的时间,而是被填充了人情、故事、血汗等一系列元素的生命存在方式。它体现了众多农民个体从求生存到谋幸福过程中的时间与节奏。作品以马一山一家为叙述核心,表现挖洋芋、种洋芋、割麦、拉麦、种胡麻、收胡麻等一年四季的农事细节,重心并非如“悯农文学”那般对农事繁苦的哀怨,而是表现一家人对于生活的美好憧憬,体现一种过日子的清苦和幸福。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羊圈门艰苦朴素的劳动生活,不但没有让人们形成一种哀叹与怨恨的苦难氛围,反而是在清苦的生活中找到独属于自己的幸福,创造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与伦理态度,从而在艰苦的环境中保持一种乐观与温情。作品赋予劳动生命的充实与幸福,将乡村传统伦理化入日常的生活与农事中,传递给读者的是生命的热度和人性的柔软,从而表达对于故土家园的无限眷恋。
其次,作家怀着对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的热爱,书写乡村日常的民间习俗和生活细节,使小说浸透着情感的温热与善良。村里马德福生病卧床时,全村各族的人都来看望。李有功当队长时自私而又专权,但其过世后,村里的人都主动前来帮忙。村里人串门到哪一家,都可以上炕吃饭,吃烙饼和汤面打荷包蛋。哪怕素不相识的人,村民也要给一口热乎饭。家中庆祝重大事情,给村中每家都要发油香,远远近近的亲戚都要通知到,杀牛,吃席坐桌。种洋芋的时候,马一山妻子、三三媳妇与二虎媳妇之间的相互斗嘴与配合,营造了一个大家庭的劳作氛围。读者感受到的是劳作中的欢快、播种的期望和亲情的热度。马一山妻子为放学回来的祖祖与舍娃做洋芋面,摆兰香为舍娃做刀切长面,小说在这些诗意化的场景叙述中,展示了羊圈门的烟火生活,还体现了亲人或恋人之间的温暖和关爱。正如有论者指出,“马金莲小说更多给予读者一种正能量,如乡村的人性美与人情美,乡村生活的质朴与厚重,农民性格的纯洁与朴实,艰辛中有美好,清贫中有温暖”。小说以“亲爱的人们”为题,透过这些乡村日常生活叙事,散发出来的是乡村世界乐观、坚韧、善良等情感热度。
小说虽然写了数十年的历史变革,但在表现时代之变中守望伦理之常。马一山家因为突如其来的洪水冲垮了牛圈,整个庭院一片狼藉。队长李有劳亲自动手挖沟引流,众人前来帮忙清理院子。舍娃外出打工被骗入传销团伙,逃出来后身体极度虚弱,精神恍惚。与马一山不对路的牛三炮抓了一只鹁鸽,送给舍娃滋补身体,这让马一山妻子感觉特别温暖。年迈的马德福在马一山的搀扶下,不顾族人械斗的危险,前往劝阻。在村中返乡青年不务正业成为风气时,他拖着病体只身前往县城寻求解决办法。马一山挺身而出劝阻村中族人斗殴,自发修挖通往村中水井的台窝,在村中作为军师不断为李有劳出谋划策。这些农民有自己的家族利益和爱恨,但总体上乐于助人、知足常乐,共同维护以传统伦理为基础的道德观念。相反,小说并没有花太多笔墨写羊圈门村民伦理缺位的地方,只是点到为止。例如,李有功当队长,利用权力打击外族,为自己和族人谋取利益;牛八虎打着资本下乡的旗号,利用李有劳的队长权力,最终卷走集资款,和三三媳妇一起私奔。小说透过一系列生活细节,真切地表现了每一个村民身上的压抑与释放、狭隘与宽容、爱与恨。然而,作品举重若轻,没有对他们的结局作出详细的描述,也没有过多地在道德上作出评判。读者感受到的是生命中充满温度的乡村伦理以及作家潜在的伦理态度。作品无意过多停留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书写上,而是适当拉开现实的时间距离,将羊圈门的日常生活温情化和伦理化。
家庭空间的内部,同样也体现出传统伦理的孝悌与礼让。父慈子孝、夫唱妻随、兄妹相助,这些家庭成员的亲密关系来自传统的温、良、恭、俭、让等伦理文化,在具体的家庭生活中,凝聚成以马一山一家为代表的良好家风。马一山每次赶集见了喜人的韭菜,都要买上四五捆,给二弟、三弟和父亲送去。马一山带着妻子炖的鸡去广州等地寻找外出打工的儿子,哪怕鸡肉坏了、儿子没有找到,他也没有舍得吃一口。马舍娃见父亲瘫痪在床,他便不出远门打工,只在家乡附近找活。马一山与妻子之间经常斗嘴,却在生活的艰难和挫折中相互支撑着走下去。丈夫病倒了,马一山妻子独自撑起家庭,家里家外的各种活儿无一落下。即使马一山后来整天在土崖下挖台窝,她也毫无怨言,营务着庄稼、照顾着丈夫,还关心孩子们的生活。马一山协同弟弟二虎一起购买奔奔车,帮着失明的三三一家种地和开一个用以营生的杂货小店。舍娃放弃高考,让姐姐顺利升入大学,并在外打工为姐姐送去学费。祖祖在弟弟最消沉的时候,为其购买摩托车,方便其外出打工。弟弟在城里打工,她又为其购买一辆小汽车。她还拿出自己为数不多的工资,帮难产的妹妹交手术费。透过马一山的家族生活,我们感受到乡土生活中的仁义、宽厚和善良美德。即便他们身处贫穷而艰难的生活中,也透出一种人间的温情和善良。马金莲的“写作……更多呈现出石舒清式的隐秘绵长,这使得她的小说在俗世的尘埃中沾染了过多的‘烟火气’,却又极力保持着某种神圣的情怀”。从这个层面来说,家族内部代际传承的善良、勤劳、真情等风气,犹如黄土大地上的一汪清泉,为当下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诸多启示。
因此,小说将乡土四时农事的劳作与家庭生活和个体成长置放于广阔的时间容器中,深情地灌注了人间的真情与传统的伦理,将其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上升到一种凡俗信仰,把对人和命运的理解推向了更高的阶段。这些传统的情感结构和伦理文化一直以稳定的样态规约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成为黄土大地上的幸福密码。作家自言:“我渴望让作品读来充满暖意,让人感觉生活是如此不易,又是如此美好。”作品没有回避人物生存的艰难和生命的沉重,而是通过情感化与伦理化叙事,真诚地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温暖淳朴的乡土图景和宁静向善的伦理世界,并思考传统伦理在现代性转型中的价值和意义。
当然,作家在守望传统的情感与伦理时,也真实地感受到乡村传统遭遇现代时的尴尬与窘困。从城里打工回来的牛八虎游手好闲、坑蒙拐骗,变卖年迈母亲的口粮,最后卷走村中的集资款和三三媳妇一起私奔。未成年的碎女没有完成中学学业,就与男人私奔。她不务正业、好逸恶劳,最后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才找到生活的出路。她既是一个违反乡村伦理的个体,又为乡村文化的推介作出努力。后来,马一山每天在山崖下挖台窝,在孤独中坚守传统的劳作方式,却无法挽留逝去的传统。这些乡村之变,正是作家守望乡村传统过程中的现代性反思,只是她更相信其对乡村生活的哺育和对人们品性的指引,因而在叙述态度上体现了一种批判下的认同。
三、多重视角的融合与日常生活的诗化叙述
《亲爱的人们》既是一部真实反映乡村巨大变革的生活史诗,又是一部深刻展露人性空间的心灵史诗。它通过多重叙述视角的融合与日常生活的诗化叙述,构建了努力奋斗而又温情脉脉的乡村振兴图景。
首先,小说以全知的视角,徐徐展开一幅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乡土现代化的风景画,表现了西北乡村的风土人情和生存方式。小说一开始就写道:“多少年来,日子都是那么过着,饿了动火做饭,天黑上炕睡觉,春天往地里下种,夏秋两季收割,冬天趴在热炕上,用自嘲的话讲,就是‘女人、娃娃热炕头,转眼一辈子活到头’。日子难熬,也好过,一眨眼,土里埋着三四辈人了。”这就将乡村日常生活置入悠远的人生长河中加以观察,使生命有了岁月沉积的沧桑感。然后叙述视线延伸,落在远处的一个山坡上,马一山和他的妻子正在弯腰收洋芋。他们手里干着活儿,嘴里数落着对方,眼睛却注意着远处的山路上,是否有自己的一双儿女在爬坡前行去赶上学的班车。这里的全知视角,犹如一个广角镜头,将羊圈门的日常生活置于视野宏阔的时空,避免了一般时代热点叙事的近距离记录,而有了民族生命历史的生动性。马金莲对此概括道:“总体来说,我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和当下生活稍微拉开距离的滞后感……这都在于我生活和书写的根据地和立足点,并且不能不再次提及一个在许多场合说到的称谓:西海固”。全知的叙述视角,主动拉开与时代现实的距离,在回望作家熟悉的村庄、田地和一个个乡亲的身影中,使小说具有守望乡土、守护传统的乡愁韵味。
其次,小说随处可见一个隐含叙述者的视角,与前面的全知视角相辅相成。这个隐含叙述者的视角既置身事外,冷静地看着村里一个个事件的发生、一个个孩子的成长。同时,它又是自在的、天然的,饱含叙述主体的情感和温度,拥抱着每一个人物的生命历程,流溢出一种对家乡和家人的温情与眷恋。这个视角犹如心灵的探照灯,走进众多人物个体的内心世界。它看着年少的舍娃在生活里一步一步挣扎,面对祖祖和姐夫的婚姻状态,在摆兰香和孟老板的女儿之间徘徊,思考婚姻幸福的内涵;看着生活一地鸡毛的碎女,在心理上嫉妒姐姐的稳定工作,怨恨父母对哥哥和姐姐的偏心,还有对家人的感激与愧疚;看着马一山妻子在丈夫整天只知道在崖下挖台窝时,想着丈夫和她之前的斗嘴、想着丈夫在家中的甩手不管、想着自己在家中的重要地位、想着子女们的婚姻和未来,而支撑起一个家庭生活的全部,其中有爱、牵挂和怨恨。这一个个独立个体的心理空间,通过隐含叙述者的逐一观照,共同编织出一部乡村世界的心灵史,折射出人性的复杂和时代伦理的变化。小说的隐含叙述者本质上是一个乡村生活的亲历者、在场者,没有局外人或返乡者视角的高高在上。《宝水》中农村出生却是省报退休记者的地青萍作为叙述者,集农村人视角和知识人视角为一体,在感受宝水村的巨变中,不断处于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焦虑与超越中。而马金莲的叙述中虽然也有失败和困境、贫穷和诈骗,但小说没有过多留下对人的焦虑与压抑的书写,而是一切都显得自然与和谐。有研究者认为,“马金莲的乡土叙述有效地祛除了‘代言人’身份的虚妄性,将乡村从被言说的对象变成了言说自我的主体”。可见,作品虽通过一些具体的时代和家庭事件来表现西北的山乡巨变,但在叙述态度上既不过分强调落后也不夸张设想进步,而是在隐含叙述者的视角下,带着作家的生命体验,贴着乡村的土地,见证有情有味的乡村人与事。
再次,小说值得关注的是后半部分作为失忆者和失语者的马一山的个人视角。马一山作为羊圈门的中生代,既背负着乡村历史的沉重负累,又主动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现实。以马一山为视角,小说能够方便地勾连起历史与现实、老人与青年,更好地打开多个层面的叙事空间,在翻开一个个细小而微的叙事褶皱中,触摸乡土社会的人情与人性。当自视甚高、喜欢独处的乡村知识分子马一山推举自己的儿子当队长失败后,他丧失了斗志。他开始长期卧床装病,后来竟然真得了脑瘤。曾经超强的记忆力丧失了,他成了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失忆者和失语者。此时,马一山在文本中行使着“讲故事的我”和“故事中的我”双重角色。他整天在崖下挖台窝,心理视角却不断来回穿梭,既见证了羊圈门的时代发展,又能随时走进每一位村民的内心世界。他见证着弟弟三三家庭的解体、妻子默默的付出和承受、舍娃和兰香的婚姻,祖祖与丈夫之间的婚姻变故、碎女早婚早育后跌跌撞撞成网红、羊圈门扶贫组长的扶助、儿子回乡创业并以文旅结合带领大家致富。自然,长期卧病在床及后来的失忆和失语,使马一山不可能真实见证乡村生活的变化,却得天独厚地展开心理流动,依循个体的生活逻辑与情感体验,自由叙述乡村的时代变革与个体的自然生长。
同时,马一山因为疾病而失忆和失语,关掉所有外界的信息联系和社会交流,自然容易联结个体的生存哲学命题,这一设计赋予作品一种超拔于世俗生活的精神力量。小说前半部分重点写马一山的劳动生活与家庭,写他协助李有劳处理好村里各种事务,其中有生命的苦痛也有欢愉。小说写超越世俗的他风雨无阻地蹲在村边路上,观察各式各样的脚印——人的脚印、动物的脚印,甚至蚂蚁的脚印,写他的浮想联翩和心灵感悟。小说后半部分则写他在乡村日常生活中遭遇了众多的“难肠事”后,陷入失忆和失语状态。他和世界交流的唯一通道就是通过无限丰富的心理视角,孤独而又自由地感受家人、家乡的变化。这一独特的视角使他超越了世俗的生命世界而持续追问、思考着生活的意义。小说的结尾处,马一山的眼睛渐渐失明,缓缓合上眼皮,犹如人生舞台的幕布缓缓拉上,既隐喻马一山所代表的农耕时代的终结,也预示着舍娃等年轻人新的时代的开始。在小说里,失忆和失语的马一山的叙述视角,放大了文本的叙事功能。这个视角不仅能够带着亲情叙述自己身边妻子和其他亲人的故事,而且还能叙述自己无法看到或者亲历的事,可以进入哲学的沉思,还可以叙述未来的可能。这个叙述主体与他此前蹲在地上看蚂蚁、分辨行人脚印等被村人视为荒诞的行为构成一致。透过马一山的视角,常规与荒诞、感性与理性、客观与主观交织为一体,超越了一般乡村振兴题材的艺术表现力,有力地拓展了小说的叙事空间。
最后,日常生活的诗化叙述也是小说的一大特色。作品在“慢时光”的节奏中描摹以马一山一家为代表的羊圈门人的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家族关系、婚丧嫁娶等,还原了乡土生活的质朴与底蕴。日常劳作的艰辛,在诗意化和温情化的叙述中变得轻盈而又富有质感。摆兰香以一双巧手耐心十足地穿针引线,用各色各样的碎布片拼出亮丽的门帘。炕上的铺盖绣着一幅五彩图案,五朵牡丹花像一家人簇拥在一起,一圈绿叶在周围衬托着,花瓣上头飞着两只大蝴蝶。无论是斑斓的色彩,还是精细的做工,都表现了日常生活的生趣与精致,又体现了她对未来生活的诗意想象。马一山得了脑瘤之后,每天只干一件事,那就是整天挖台窝。“干结裸露了几十乃至上百年的崖,黄土早就是无比沧桑的面孔,猛然间被一把磨秃了的老头一口一口啃,那黄土就疼痛一般,一股一股地冒烟。尘烟起,尘烟落,马一山被黄尘一寸寸覆盖成了一具活着的雕塑。”岁月的流逝、生命的疼痛、精神的执着,小说将马一山的生命与黄土融为一体,化作一首执着而又沧桑的生命之诗。
小说诗化地呈现了一些西北乡村生活中的传统民俗,原汁原味地描绘了一幅幅生动鲜活的乡村风俗画。马一山妻子和二愣妻子隔着一堵土墙互相扯磨。磨的是时光,扯开的却是人间各种烦恼。一番扯磨之后,二人变得神清气爽。扯磨既是乡村女性传播家长里短的渠道,也是乡村女性面对各种艰难和压抑时的治愈方式。碎女出嫁之前,牛阿旦妻子一边和马一山妻子说个不停,一边手脚利索地给她“掀脸”。牛阿旦妻子先捏一疙瘩黄土往碎女的脸上蹭一圈儿,后咬一根白线绞汗毛,再用碎瓷片满脸齐齐地刮,最后用剥开的熟鸡蛋飞快地滚一遍。整个掀脸的过程,体现了一种民间文化的精致和仪式感。透过这些民俗生活的图景,乡村日常生活的繁忙与苦累在一种诗意中变得轻盈,表现出对生命的尊重和赞美。这些关于民间习俗的生机四溢的诗意书写,生动描绘了西北乡村鲜活的世情生活与生命气质,不仅是一种文学细节的陌生化策略,更体现了民间生存的韧劲与智慧。
真正的诗意来自创作者的真诚与爱、对笔下所有人物的尊重。作家以温柔敦厚的人间情怀与生命关怀,坦然面对每一个人物命运的不确定性,书写了羊圈门的人们从求生存到谋幸福的生命历程。读者感受到的是乡村变革中的奋斗与追求,还有黄土大地上的静谧与厚重。小说不仅真实呈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山乡巨变,还在守望乡村传统的执着中体现对幸福的理解与思考。然而,作品似乎过多倚助于众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坚守与隐忍,以独特的方式诠释传统的伦理世界,能否真正通向个体的幸福,从而助力乡村的现代化事业?这个问题大概需要作家平衡好守望乡村传统与放眼现代化的关系,在以深情的目光投向故土的生活与伦理之常时,真诚揭示其间人情与人性的微妙变化。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