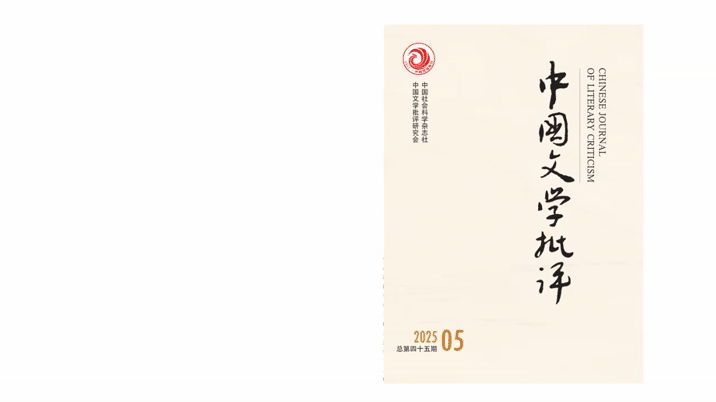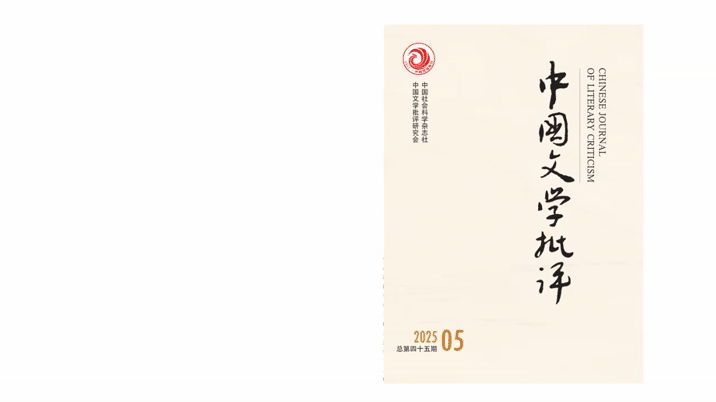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不仅站在时代前沿,为文艺发展所面临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供了新的思想方法、知识视野,也为文艺理论的发展贡献了新的理论术语、基本范畴,在实现“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的同时,也丰富了这门科学的基本概念、范畴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所提出的“中国精神”这一重要范畴,与“人民史诗”“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等重要范畴一道,形成了崭新的具有新时代品格的文艺理论范畴体系,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新的重要贡献。
一、“中国精神”的表现形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精神”这一文艺理论范畴。随后,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等有关文艺工作的一系列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论述了“中国精神”的内涵,即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同时阐明了“中国精神”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首先,从中国历史发展看,“中国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凝聚的思想理念与道德规范。
“中国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世世代代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起来的独特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基础和价值追求、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其具体表现为“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它们作为内容丰富的精神系统,构成了中华民族战胜艰难险阻的精神支柱,也对世界产生了强大感召力和重要影响力。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民族历经无数苦难考验而能挺立至今,中华文化历经无数烈火洗礼而能延续至今,并且“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这充分说明,国家精神和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行稳致远最根本的精神支撑。
其次,从革命与建设过程看,“中国精神”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身上所体现出的艰苦奋斗与坚韧不拔的追求精神。
“中国精神”既是一种历史性存在,体现为一种历史精神,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又是一种现代性存在,转变为一种现代精神,产生了重要的现代影响。“中国精神”对现代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不断进取精神。这种精神内涵丰富,形态多样,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命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如在革命战争年代锻造出来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等,正是凭着这些精神,中国人民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 正因为有这些精神,中国人民才获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些精神不仅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支撑了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
最后,从代表人物看,“中国精神”是英雄模范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与勇往直前气概。
“中国精神”不仅体现在历史中,成为一个民族特定的精神标识,还体现在具体的人物身上,展现他们独特的精神风貌。 “中国精神”是中国人民在争取国家独立自主、民族自由解放、社会繁荣发展征程中,英雄模范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信念、不怕艰难险阻的勇往直前气概、不惜付出一切的无私奉献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提出的“中国精神”范畴,立足于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和独特的基本国情,具有深厚的历史感、丰富的思想内涵、鲜明的中国特色,顺应了时代前进的潮流、中国发展的需要。“中国精神”既是一种属于过去的历史精神,它作为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起到了“凝聚人民力量,挺立民族脊梁”的重要历史作用;“中国精神”又是一种属于现在的当代精神,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同样起着“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的强大精神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精神”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他在强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为代表的“中国精神”,“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的同时,特别突出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伟大抗战精神”为代表的“中国精神”的当代价值。“伟大建党精神”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之一,就是“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伟大抗战精神”在今天仍然值得弘扬。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中国精神”的三种表现形式,从纵向看,体现了“中国精神”在不同时代的变化发展与时代特色;从横向看,体现了“中国精神”在不同主体身上的生动呈现与个性差异。三者是一个既有相对独立性,又有相互联系性的整体,并作为文化基因对中国文艺发挥着系统的影响。
二、“中国精神”的文艺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的“中国精神”范畴,从表述方式和表达语言看,似乎是讲的文化思想与价值观念问题,但从深层意蕴和理论指向看,却是文艺的功能问题,主要在于确立以“中国精神”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时代中国文艺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因为“文艺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独特作用”,所以文艺家们在文艺创作中要“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具体而言,“中国精神”的文艺价值,主要体现在对新时代中国文艺创作的引领和影响。
首先,“中国精神”奠定了中国文艺真善美的价值追求。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真善美不仅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国文艺的永恒价值,更是新时代中国文艺的价值追求。“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古代的文艺观念和文艺审美两个方面分析了文艺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
从文艺观念方面看,中国古代文艺真善美的价值追求集中表现为“文以载道”的文艺主张。习近平总书记说:“苏东坡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讲的是从司马迁之后到韩愈,算起来文章衰弱了八代。韩愈的文章起来了,凭什么呢?就是‘道’,就是文以载道。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在这段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重点表达了三个观点:一是“文以载道”中的“道”具有振兴文坛的重要功能。在中国文学史上,从东汉至隋朝历经八个朝代,其间流行的骈文追求对偶、堆砌辞藻、脱离现实、内容空洞。到了唐代,韩愈、柳宗元提出“文以载道”观念,主张文章应关注现实、务去陈词、言之有物、道济天下,使唐代散文重回“秦汉风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赞同苏轼对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评价,并强调“道”就是“文以载道”。二是“文以载道”中的“道”,其核心内容就是真善美。追求真善美是中国文艺的优良传统,坚持真善美是中国文艺批评的重要标准。在中国文艺发展史上,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与“尽善尽美”说,奠定了中国文艺追求真善美的思想基础,其后一直在中国文艺史上得到了延续和发展,直到中国现代的鲁迅仍然认同文艺的真善美追求,他在谈到文艺批评时将文艺批评标准称为“圈子”,说文艺批评史上的文艺批评家都是有圈子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离开真善美的文艺批评是极其少见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文艺家要通过自己的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三是“文以载道”中的“道”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真善美作为“道”的核心内容,对文艺创作而言,它构成了文艺作品的基本格调,显示了文艺家的高尚追求;对文艺接受而言,它影响着接受者的思想境界,培养接受者的道德标准。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文艺作品对接受者价值观的影响,要求文艺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增强接受者的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
从文艺审美方面看,中国古代文艺真善美的价值追求主要表现为“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国精神”的审美表现,是文艺真善美价值追求的艺术表达。习近平总书记不仅认为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精神”,而且还肯定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审美实践中,特别是文艺审美实践中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华美学精神”。他将“中华美学精神”概括为“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从三个方面突出了“中华美学精神”的特点。一是从情与物的关系上看,“中华美学精神”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文艺家们在创作过程中,既不是抽象地议论,也不是直白地抒情,而是通过写景状物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寄托于事物之中,从而达到情、理、物的有机融合。二是从言与意的关系看,“中华美学精神”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文艺家们在文艺创作过程中,总是力图用最简洁明了的语言,在凝练节制的篇幅中表达最完备、最深刻的意思。三是从形与神的关系看,“中华美学精神”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文艺家们在创作过程中,既追求描写对象外在形态的真实,又追求内在气韵的生动,从而使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在形与神的统一中呈现出悠长的韵味、深远的意境,给人以言有尽、意无穷的审美体验。
其次,“中国精神”构成了中国文艺常写常新的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爱国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论述了“中国精神”与中国文艺主题的关系,强调“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以“中国精神”为支撑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主义则是中国文艺常写常新的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他列举了范仲淹、陆游、文天祥、林则徐、岳飞、方志敏等人的爱国主义诗歌与散文,称赞他们的作品拥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他说:“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位卑未敢忘忧国’、‘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岳飞的《满江红》,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等,都以全部热情为祖国放歌抒怀。”这些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的作品,突出了以天下安危为己任,以国家利益为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作用,而且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至今仍为中华儿女所共同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了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意义,强调了爱国主义应当成为新时代文艺创作的主旋律。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虽然从总体上说我国文艺界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但是从具体情况看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等否定爱国主义精神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他认为,这种否定爱国主义精神现象的发生,预示着部分文艺家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忽视了爱国主义精神在新时代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然需要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思想力量、旗帜引领。他在《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肯定了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奏响了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壮歌。爱国主义是激励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在历史洪流中奋勇向前的强大精神动力,是驱动中华民族这艘航船乘风破浪、奋勇前行的强劲引擎,是引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迸发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壮丽旗帜!”正是由于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才特别强调爱国主义精神在文艺中的重要地位,特别要求“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最后,“中国精神”赓续了新时代中国文艺的文化血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的“中国精神”范畴,对新时代中国文艺界辩证认识当代生活与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科学地处理新时代中国文艺传承中华文化与创造创新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答案,赓续了新时代中国文艺的文化血脉。
从新文化运动至今的一百多年里,中国文艺界一直存在着如何处理古与今、中与外关系的问题论争;一直存在着以今非古、扬西抑中的思想倾向。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文艺界也出现过“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倾向,“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种倾向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那是缺少“中国精神”的表现,“绝对是没有前途的”。他告诫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家,“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中表现的“中国精神”,正是中华文化传统血脉的核心,“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中国精神”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而且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作为“中国精神”形象体现的许多中国故事、中国题材,也为一些外国文艺家的创作提供了资源和灵感。“事实上,外国人也跑到我们这里寻找素材、寻找灵感,好莱坞拍摄的《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影片不就是取材于我们的文化资源吗?”这再一次证明,只有坚守“中国精神”的作品,才能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只有突出“中国精神”作品,才能为其他民族提供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中国精神”在新时代文艺中的地位,强调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应赓续中华文化传统的血脉,但他并不反对新时代文艺批判地借鉴外国文化,吸收外国文化资源以丰富和发展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在如何对待古与今、中与西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主张,创新性地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观点。他说:“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论述,从立场、原则、目标三个方面,说明了新时代文艺与中外文化的关系。从立场上说,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应该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弘扬并非复古,也并不意味着排外;从原则上说,应该坚持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使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新时代的中国文艺中;从目标上说,要实现对中华文化的“两创”,即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中国精神”的理论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的“中国精神”,无论是作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概括,还是作为文艺理论范畴,都是一种新的表述,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还是对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首先,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关于“中国精神”的科学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注中国问题,在19世纪中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评论了当时发生的诸多与中国相关的人物和事件,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观”。特别是他们根据“两极相联”理论得出的“欧洲人民的下一次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的结论,更是准确地“揭示了中国革命与西方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他们还从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比较中,概括了中国人身上的“勤劳智慧”“创造精神”“自大与保守”“觉醒与反抗”等相互矛盾的精神特点。列宁也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20世纪初期发表了10多篇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在论述中国社会性质与预测中国革命前景时,揭示了中国人“不畏强暴”“顽强斗争”“真诚的民主主义”“向往自由和平”等精神气质。毛泽东熟悉中国历史,洞察中国社会,了解中国民众。他在自己的著述中,虽然没有为“中国精神”命名,却多次谈及过“中国精神”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在《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著作中,通过对张思德、白求恩、愚公等典型人物先进事迹的分析,概括出了“中国精神”的具体形态与呈现特点。如“重义轻利”“互爱互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所提出的“中国精神”范畴,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关于“中国精神”的认识。一是明确提出了“中国精神”这一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精神”范畴,概括了“中国精神”的含义,分析了“中国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论述了“中国精神”的表现形式。二是重点突出了“中国精神”范畴的文艺价值。习近平总书记结合中国文艺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的需要,重点分析了“中国精神”与中国文艺的主题表达、“中国精神”与中国文艺的价值追求、“中国精神”与中国文艺的文化血脉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了“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三是辩证地阐明了“中国精神”与文艺创新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化观,通过对“中国精神”及其相关问题的系统性分析,阐明了坚守“中国精神”,传承中华文化,借鉴外国资源的基本立场、重要原则、主要目标,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遗产理论。
其次,阐述了“中国精神”在民族文化和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精神”的重要论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阐述了“中国精神”在民族文化和发展中的意义与作用。一是“中国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辐射功能。“中国精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凝练的表达,具有很强的辐射功能,它不仅凝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而且还涉及“中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文艺创新的相互关系,具有辐射面广的特点。二是肯定了“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在世界古老民族中,一些民族或被历史淘汰或被其他民族征服;在世界文明古国中,一些国家的文明或中断或被其他文明取代。“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延续不断、一以贯之呢?习近平总书记肯定地回答,“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即“中国精神”。三是强调了“中国精神”在近百年来的巨大作用。近代以来,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都面临内忧外患。外有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经济封锁,内临军阀混战、民生多艰。但中国人民却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创举,主要依靠什么呢?一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二靠“中国精神”的支撑,“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最后,确立了新时代中国文艺创作的精神根基。
20世纪以来,西方各种学术思想和文艺思潮的冲击,使部分文艺家和批评家的创作观念和批评标准变得模糊不清,对中国文艺的精神根基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从历史经验、现实需要、未来发展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精神”在中国文艺中的地位,强调了“中国精神”是中国文艺的精神根基。从文艺的历史经验看,中国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作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对世界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文艺建立于“中国精神”的根基之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从中国的现实需要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尤其是文艺创作的“高原”“高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将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放到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这就不仅需要文艺家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满足人民对文艺精品的审美需求,而且需要文艺家们面向世界,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但不能靠模仿外国人,跟在外国人后面亦步亦趋,而是要以“中国精神”为根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从社会的发展看,走向未来需要正确地对待历史,需要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坚守“中国精神”,以“中国精神”作为自己立足的根本、创作的根基,则是文艺家坚定文化自信的表现。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正确对待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历史给了文学家、艺术家无穷的滋养和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文学家、艺术家不能用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更不能使历史虚无化……戏弄历史的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对自己创作的不尊重,最终必将被历史戏弄。只有树立正确历史观,尊重历史、按照艺术规律呈现的艺术化的历史,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立之当世、传之后人。”他要求文艺家们坚守“中国精神”、借鉴外国资源、面向未来发展。他谆谆告诫文艺家们“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提出的“中国精神”范畴,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拓展和丰富,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新成果。它既体现了中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时俱进的品格,又确立了中国新时代文艺创作的精神根基,为中国新时代文艺界创作出具有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提供了遵循,也为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方向。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