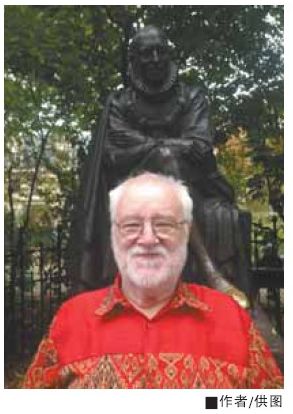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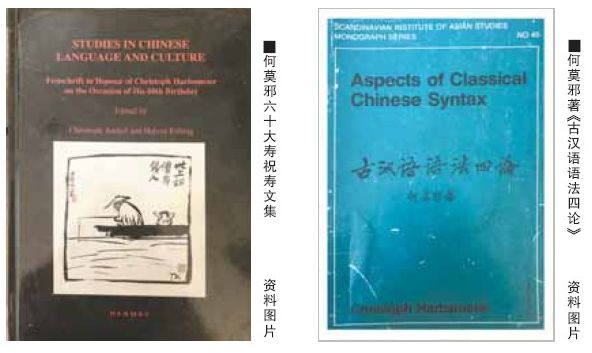

2023年3月上旬,在香港中文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主办的讲座中,何莫邪教授通过Zoom视频会议发表题为“我对汉学的一点意见”的演讲。这位自称“俺小何”的“老外”,不仅能以汉语演讲,且言谈风趣幽默,举例丰富,思维清晰,着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遂产生了访谈这位“小何”教授的想法。何莫邪教授的汉学文法训诂研究也暗合我早年的翻译概念文化史的兴趣,于是也就有了最近的这次视频访谈。
文化哲学综合的早期训练
孙继成: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视频访谈。大家都知道何老师是位语言天才,学过十多种语言,请问其中有何秘诀?
何莫邪:我小时候调皮捣蛋,酷爱体育运动,什么足球、手球、壁球,样样都学,还想成为职业运动员,只可惜身高受限,视力不佳,只好转而学习几门外语来解闷儿。十岁开始,我就学习了希腊语、拉丁语、法语、英语、俄语、波兰语等,后来又学习了汉语和其他语言。我觉得,学习一门外语就是学习一种新的感知世界的思维方式,培养自己的思想灵敏性,进而提升自己对不同文化的敏锐感知,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儿。
孙继成:请问您的家庭是否为您提供了一些学习的便利条件?
何莫邪:我家里兄弟五人,我排行老四。小时候,我是最调皮的那个,父亲在家里的口头禅就是:去看看老四在干什么,别让他搞啥破坏。不过家里孩子多,大家你争我赶,学习气氛较好。15岁时,全家搬到了哥廷根,我就开始发愤图强,勤奋学习外语及哲学。我爷爷是数学教授,父亲是牧师,也是神学教授,他们鼓励家人之间遇事要充分交流与讨论,这对我后来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影响深远,算是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也算是进行了辩证方法的早期理论训练。晚上有时候,家里五个男孩都会在卧室里追着问已穿睡衣的父亲,缠着他来讨论一些哲学及神学话题。家里人都说我继承了父亲的幽默及敏锐的观察能力。另外,作为神学家的母亲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她让我从小就珍视自己的家庭生活。
孙继成:您是如何争取到去牛津大学默顿学院读书的好机会的?牛津大学的求学时光对您走上学术之路有何影响?
何莫邪:1966年中学毕业时,我获得了罗伯特·伯利奖学金(Robert Birley Scholarship),得以去牛津大学攻读西方哲学专业;入学后不久,因结识了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1923—2009)教授而改学了古代汉语。我很喜欢牛津大学的学术氛围,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修很多课程,自己也成了老师们眼中的好学生。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我有幸结识了汉学学术道路上的两位贵人:一是大卫·霍克斯教授,他对我进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启蒙;二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葛瑞汉(Angus C. Graham,1919—1991),他教我中国古代哲学。是他们一步一步把我引上了汉学研究的大道。霍克斯教授让我改学了汉语,教学过程中阅读汉语文献时,多采用一种新鲜的文学视角,强调文本的个体化阅读体验。他还善于把具体的文本对接相关的文学史,采用人类学的视角来研读文本。霍克斯教授对我情深义重,我一直感念于心。葛瑞汉老师最初使我对汉语句法产生了浓厚兴趣,是我20多年的良师益友,自不多言;时至今日,我对汉语句法的兴趣仍然不减,其影响可见一斑。牛津大学让我流连忘返,不愿离开,为此还故意延迟毕业了好几次,俺小何就想在牛津当一辈子学生(an eternal student)。后来,我接受了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又称槟城理大)的教学邀请,去那里教授东方哲学课程。这时候,我才不得已在默顿学院拿了个汉语专业的硕士学位,匆匆毕业而去。
专业古汉语 爱好“漫画丰”
孙继成:您在槟城理大任教的三年(1973—1976)里,都有哪些收获?
何莫邪:我去马来西亚槟城理大任教之前,我的女朋友、丹麦女孩英格博格(Ingeborg R. Thaning)正在牛津工作,她的职业是理疗师(physiotherapist)。结婚后,我们又一起去了马来西亚。我在槟城理大的教学工作主要是东方哲学与逻辑。受语言的限制,我无法用马来语给学生们上课,只能选择使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解释复杂的哲学和逻辑问题。学生们认为俺小何的教学内容枯燥无趣,也批评我为人较凶,对学生过于严格。于是,学生们就推荐我去读一读丰子恺的著作,学习一下中国教师是如何对待学生的,做教师的就该像丰子恺一样温文尔雅。如此这般,俺小何就喜欢上了丰子恺的漫画、散文和随笔,自己也学着去做一个好玩的人。
孙继成:1979年,您完成了《丰子恺:一个菩萨心肠的现实主义者》(Socialism with a Buddhist Face: The Cartoonist Feng Zikai)的初稿。您是如何解读丰子恺漫画作品的?
何莫邪:我认为丰子恺的漫画是图画里的哲学,是自然智慧的一种直接表达,蕴含着一种快乐而平静的哲理。丰子恺的眼里都是有情世界。看过丰子恺的漫画,我就对中国漫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也开始广泛收集他的漫画、散文和随笔,这是我在古汉语研究之外的最大兴趣。1979年,《丰子恺:一个菩萨心肠的现实主义者》的初稿完成。俺小何认为,对丰子恺的漫画,学界不能进行死气沉沉、循规蹈矩的学究式评论,观赏者要勇于表达自己的主观感受,对丰子恺漫画可以进行童真式的评论和解说。很多人把丰子恺的漫画作品媚俗化,其实丰子恺的作品味儿是辣辣的,够劲儿。从此以后,我也有了研读中国笑林文化的兴趣。
孙继成:1976年,您结束了槟城理大的教学活动,返回哥本哈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就此开始了为期五年的苦读生活?
何莫邪:是的,1976年至1981年是我人生中最为困顿的时段,也是最为幸福的时光。我重回学堂做学生,妻子不得不重返职场,重新做起了她的老本行——理疗师。1977年,儿子三岁时,小女儿又出生,我只好待在家里边写博士论文,边照看孩子,活成了一位标准的奶爸。有时候,看书入迷,我就忘了去幼儿园接儿子。在这五年的读博时光中,我在学术上比较高产,写了几篇论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在博士论文里,我运用了大量例证,借助了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文献训诂研读方法,详细论述了古汉语的句法特点,获得了博士论文答辩评委的一致好评。由此,我也凭着这篇博士论文谋取了奥斯陆大学的汉语教职。
孙继成:1980年,您担任了奥斯陆大学汉语高级讲师,1985年就顺利晋升为汉语教授。这期间您不但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古汉语语法四论》,还完成了《丰子恺:一个菩萨心肠的现实主义者》一书的修订与出版。真可谓成果频出,春风得意。
何莫邪:在内心深处,我对丰子恺可谓情有独钟,痴心不改。在研读古汉语专业的同时,又能够兼顾到自己的业余兴趣——欣赏丰子恺的漫画世界,可谓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俺觉得,在丰子恺的漫画里,有意境,有情怀,有人性,有神韵,还有人性的讽刺与社会的批判,里面藏有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养生之道。有些漫画现在看来,还是新鲜如初。古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今有线条不虚,上达人心。
漫画藏哲理 逻辑保真义
孙继成:您在奥斯陆大学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联络汉学家同行,搭建合作平台,使得奥斯陆大学的汉学研究跻身于欧美前列,为自己和学校都赢得了盛誉,可喜可贺。2003年,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访学期间,曾参加过奥斯陆大学承办的北欧汉学研究会年会,至今心感不胜荣光。
何莫邪:2003年奥斯陆大学承办北欧汉学研究会年会时,我正好外出讲学,完美错过了你我之间的会面。当年的会议应该是由刘白莎老师负责召集的。
孙继成:是的,刘老师还专门采访了我,她对我能从中国大陆来北欧访学充满了好奇。后来,我回到北大后,还在燕园碰见了我会议论文的评阅人Hans,他当时在北大中文系访学。我们的这些奇遇都是您当年汉学拓荒的意外收获。
何莫邪:有时候,世界就是这么的奇妙。
孙继成:请谈谈您与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是如何合作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第7卷《中国传统语言与逻辑》的。
何莫邪:《中国传统语言与逻辑》是对中国逻辑思想进行深入的语言学发掘。书中我提出:“在非印欧语系的基础上,能够发展出系统的逻辑定义并有所反映的文明,非中华文明莫属。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对全球逻辑史,对基于全球科学基础的任何历史而言,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哲学就是这样,没有这种逻辑分析过程,就没法深入这种哲学所造就的文化核心区域。”现在,部分汉学家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和翻译还是很糟糕的,古代汉语作为汉学研究至关重要的工具,已经显示出了它潜在的绝对重要地位。我们有充分理由去好好研究古汉语,搞清楚古代汉语的语法框架和中国哲学逻辑的基本结构,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汉学家。
孙继成:在《中国传统语言与逻辑》的序言中,您也曾说过:“中文在逻辑上要比古希腊文透明和严谨得多……中文词常常有形态学上的词类特征……希腊文在很多地方可以省略,而古典中文却不可以省略……古典中文的句法既十分丰富,足以表达柏拉图的思想,同时又比较贫乏,须经过相当可观的句法和逻辑改造,才堪当此任。”以上所引,您究竟是想说明什么?
何莫邪:古往今来,有许多带有异国特质的逻辑特征被说成是中文特有的特征,而事实上却非如此;你上述的引文就是明证。在非印欧语系的基础上能够发展出系统的逻辑定义及其反思的只有中华文明。因此,中国的逻辑史对全球的逻辑史以及对任何全球科学史而言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概念间的关系不是中国语言哲学家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他们所关心的话题是名与物之间的关系。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中国出现了两次关注理性逻辑的宝贵时期:墨家逻辑与来华的佛教逻辑。但二者当时都属于比较边缘的亚文化。
孙继成:在与李约瑟博士的合作过程中,您对他有何深刻印象?
何莫邪:我与李约瑟之间的合作长达六年。我每次来剑桥,他都会不止一次地邀请我去他所在的学院里吃正餐;有时候,他也会邀请我到他家里见一见他的太太。我们曾就写作的方法讨论过多次,他很能包容我对他开的各种玩笑和批评。另外,使我们团结一致的是我们对欧洲思想史的共同兴趣,尤其是中世纪的欧洲思想史。而且,我们对中国科学、哲学和文化研究都情有独钟,当然,在某些方面我们也有分歧和辩论,比如,我们对古汉语的“气”和“阴阳”以及“数学在中国科学中的作用”都有不同的看法。李约瑟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儿是他的拉丁文水平很高,有时候给俺写信,李约瑟会全用拉丁语写成。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都喜欢谈论人生哲学。李约瑟为人友善,善于帮人出主意,待人和气,自己一点架子也没有。
幽默要跨界 创新靠文典
孙继成:在阅读中国古代典籍《论语》时,您是如何注意到了孔子的幽默?研读中国古代典籍,您都使用了哪些方法?
何莫邪:对于孔子可爱而幽默的一面,俺是通过研读《论语》的句法推测出来的。孔子并非后人敬而远之的圣人,不总是严肃刻板,还有幽默可爱。孔子与弟子的关系多是朋友之间的平等与友爱。在研读《论语》时,我会试着搜集相关的词,然后进行文化史、思想史和概念史的梳理,进而体会中国文化中的幽默之处。在研读孔孟老庄韩墨等先秦诸子作品时,我多采用细读法,阅读过程会密切关注中国哲学,因为哲学也是我阅读汉语的初心。我曾经从汉语典籍中搜集到700多种笑的表达法,细细品味其中的差异,就能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幽默所在。俺小何认为,幽默是一切创新的源头。研读中国典籍的方法,特别是在古汉语的研究中,要做好训诂、打好基础、厘清文化背后的基本逻辑结构等,这些都非常重要。如前所言,古代汉语的“哲学语法”(philosophical grammar)就能够满足汉语表达的精确性、清晰性的基本要求。
孙继成: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您前瞻性地开发了汉学文典(Thesaurus Linguae Sericae,TLS)项目。这有点类似于当下的数据库建设项目,也是中国概念史的历史比较,类似于大百科全书的写法,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何莫邪:汉学文典这个合作项目至今已经进行了三四十年。2016年,我们开始将TLS的文件生成数据库,转换为可协作编辑的新格式。2019年开始上线运行,网址是https://hxwd.org,欢迎大家访问查阅。汉学文典的主要特点是为读者提供汉语的历史音韵学和汉字历史的最新数据库,涵盖了古典文献语料、分析词典、同义词词典、历史关键词、概念史、句法类别、修辞方法、标准语义关系等方面的信息;基本实现了全方位检索;读者可在搜索输入字段后面的下拉列表中确定搜索范围。网站的主要管理者有蒋绍愚、史克礼(Christian Schwermann)、维习安(Christian Wittern)和我。目前汉学文典已经收录了3000多条术语,词条有4.3万多条,文本近千篇;每个词条都有句法分析、语义比较、修辞辨析及英语译文等。汉学文典为各国汉学家提供了深入合作的平台,鼓励跨学科交流,真正成为汉学家之间进行跨国语言合作与跨界合作的重要网络平台。
孙继成:您对汉学文典的未来发展有何期望?近年来,您都在忙哪些汉学项目?能否给我们透露一下?
何莫邪:我希望汉学文典能够不断得以修订与完善,成为汉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库,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参与进来,共襄盛举。
近期我正在准备专著《庄子内篇汇释》(与John R. Williams合作)的出版事宜。另外,我希望能够出版自己的译作,比如我花了几十年翻译而成的英译《韩非子》。
孙继成:2009年,您在香港中文大学做客座教授时,曾说自己十分敬佩易中天教授能够利用电视媒体来普及中国古代文化,也十分羡慕中国人对古代历史的兴趣还那么浓厚。今年当地时间4月24日,您与易中天教授相约在英国剑桥大学会面,这次你们都谈了哪些内容?
何莫邪:我以前听过易中天教授几百个小时的视频演讲,还现场听过几个小时的演讲。可以说,我对易教授神交已久,算是熟悉的陌生人。我觉得易中天教授口才很好,说话很幽默。这次我有幸出席了剑桥大学中国学联组织的题为“两宋文明之谜”的名家讲座,再次现场聆听了易教授的讲座,很是兴奋。具体来说,易中天教授对宋朝在中国漫长的朝代更替史中地位的解释,我觉得非常有说服力,这也是我听得懂的地方。然而,当涉及经济、社会、历史等细节问题时,我的理解能力常常不太能跟上,无法准确地理解易教授所讲的内容。
在这次谈话中,我发现易中天教授对希腊和中国哲学传统的对比研究十分关注,相关认识非常清晰,见解也十分深刻。对此,我很高兴,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研究兴趣,有许多可以合作研究的地方,也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和阐述。具有相同兴趣和不同阅读背景的学者之间的对话肯定十分有趣,但这却需要大量的空闲时间和坦率的思想交流。很遗憾,这次我们在剑桥期间没有足够的时间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因此,我热情地邀请易中天教授有时间来做客,到哥本哈根的家中进行进一步的交流。我们可以就全球历史、艺术史、世界文献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方法等,展开更多的讨论。
孙继成:近年来,您受邀在中国高校做过多次演讲和报告,其中您比较关注的领域是哪些?
何莫邪:近年来,我讲座的主旨多是倡导大家利用现代语言学知识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深化研究。比如,我就汉学文典进行过多次讲座。我认为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遗产并不仅仅属于中国自己,而是属于全世界;中国的遗产保护与文明传承需要全球视野,需要全世界的汉学家齐心协力,共同分析好它们,进而证明中国文化遗产自身的重要性。如果文化遗产得不到合理的保护与传承,没有了读书人的热爱与参与,那么传统就会中断,遗产就会飘零。这也是我自己从事汉学文典研究长达35年的初心与信念。我还以“全球古典语文学与中国(汉语)训诂学”为题,强调了不同语言的语文学传统之间的对话,加强中国文献传统训诂学的系统语言分析,这也是我与同仁完善汉学文典网站的底层逻辑与布局思路。
经典再好,智慧再妙,如果失却了读书人的传承,就会了无声息,归于湮灭。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建设好经典传承的共同平台,显得更加重要。
汉语全球化 关乎你我他
孙继成:您认为近年来国际汉学研究的热点话题都有哪些?
何莫邪:国际汉学研究,最重要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之间要建立起真正的友谊;就中国文化而言,就是能够利用全球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民国时期学术传统的重大意义。另外,对于中国的汉学研究者而言,很有必要去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并试着与俄罗斯、法国、德国的汉学进行对比研究。同理,西方的汉学家也要试着去解读欧洲最初的汉学文献,熟悉欧洲悠久的汉学传统。19世纪的汉学家大多能阅读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和德语文献。而今天的西方汉学成就多是英语成文,其他语种较少;尤其是忽视了俄罗斯汉学家的巨大贡献。
孙继成:为了更好地对接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大陆有无必要加强繁体字的教学与使用?
何莫邪:关于汉字的简化,俺小何认为中国学者要对此进行详细而深入的探讨。最初倡导简体字的研究人员也坦承,汉字简化带来了汉字语义的某种缺失,比如繁体字“於”与简体字“于”出现的常用混淆。我个人更倾向于学界能够把“繁体字”改称为“正体字”。简体字已经十分成熟,人们可以继续使用,其存在的意义也十分重大。不过我个人阅读中文印刷品时更喜欢看正体字,简体字的形式常常令我看着难过。中国人自己可以试着学习正体字,试着与自己的文化源头进行文字上的对接,去体会正体字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孙继成:您对从事中国学的学者有何建议?
何莫邪:俺的建议是,第一,除了英语和汉语文献,要多多注意其他语种的汉学文献。第二,作为西方学者,大家不要忘了自己的汉学贡献最终取决于对自身文化的深层理解。第三,作为中国的汉学研究者,大家对汉学全球性的关怀取决于运用中国本土的丰富文化资源来更好地解决一些全球性难题,换言之,能够为解决全球性话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孙继成:您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倡导有何评论和建议?
何莫邪:俺小何认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一定要借鉴林语堂先生当年宣传中国文化的精神,深入学习林语堂先生的策略与方法。这是一门艺术。
(作者系青岛大学外语学院MTI校外合作导师、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