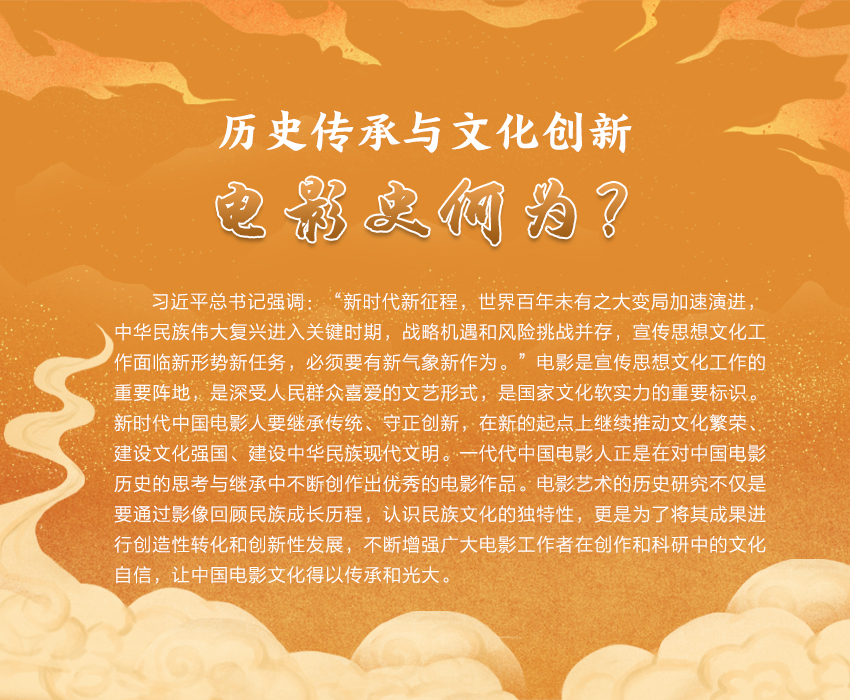

身处数字智能时代,当我们在(或通过)不同时空、平台与媒介、载体,阅读或观看特定的文学文本、图像文本、视听文本甚或社会文本时,我们阅读或观看的这一特定文本,还是其本身吗?针对电影而言,在我们的视野(或听野)中,文本发生了什么?意义在哪里?电影史何为?
显然,从文本到意义,既是人文阐释学的根本目的,也是计算机或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算法的工作原理。必须面对的处境是,从罗兰·巴特、保罗·利科到W.J.T.米歇尔,文本理论和诠释学正在步入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哲学语境;而从本雅明、威廉·弗卢塞尔、海德格尔、贝尔特·斯蒂格勒到米歇尔·福柯、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技术哲学与媒介考古学也始终在提出如下问题:如何面对作为技术文本和文本技术的电影?
正是在大卫·鲍德维尔与诺埃尔·卡罗尔的后理论与弗朗西斯科·卡塞蒂与史蒂文·沙维罗等的后电影观念里,文本的交错与意义的延宕成为必然;也正是在列夫·马诺维奇与托马斯·埃尔萨瑟等的新媒体语言和新电影史构想中,电影史重构被提上议事日程。
对于中国电影研究来说,在数字人文、媒介考古与平台建设和知识体系的基本脉络和总体框架中展开电影史重构,是一个超越了构想阶段正在走向深度探索的过程。电影史重构的目标,即建立数字人文与知识体系平台下的电影生态,在以数字学术环境与数字人文学者组成的数字人文生态里,结合知识体系平台建设而对电影生态进行总体创构和意义阐释。作为中国电影不可或缺的数字基础设施,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CCKS)的目标设定基于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视野,努力面向智慧型的电影生态,或可最终导向中国的“智慧电影”实践。
因此,无论影人年谱、电影计量,还是电影百科、影文索引,都是力图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与创新机制、评价机制的框架里,展开相关中国电影全方位、全领域和全要素的史论建设与电影生态创构。从中国电影“源代码”,到中国电影“智慧”,正是一个“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见微知著、睹始知终”的艰难历程。

作为中国电影美学原生理式探知的三大领域,发生学、生成学和影片形态学是纵向榫接又横向扩展、环环相扣的三个组成部分。其中,影片形态学是理式系统的文本化呈现。最为直接和关键的指标是孕含了“观念一实践”的“叙事范式”与“范式文本”以及具有历史动力学功能的“范式效应”。
上世纪20年代初,历经八部长故事片试制,最终定格于《孤儿救祖记》的大盛双赢。从《孤儿救祖记》以及由此引发的“国产电影运动”,就可以捋清叙事范式,范式文本及其范式效应历史动力学机制的内在逻辑。所产生的影片被命名为“文艺片”。“文艺片”一度被定义为:“是介于商业类型电影和艺术电影之间的影片类聚。具有较大的包容性。泛指制作态度严肃,主体表现具备一定积极意义,叙事表现遵从大众化形式,同时又具有一定的个人特色和风格特征。”
就本质上说,文艺片是“良心主义,现实主义—影像传奇叙事”“观念—美学”原则诉诸创作化(生产化)文本化所生成的叙事结构与形态外观。文艺片的定义绝非文艺作品改编或偏重文艺性的指认。相较于欧洲同一时期由“先锋运动”延烧而成的艺术电影和工业资本主义“大制片厂制度体系”支配下经典好莱坞的商业类型电影,文艺片显然是中国电影本土化发展过程中,谋求影片创作生产(影片形态学范畴)中存在的多极矛盾性(内、外)平衡的文本化产物。

倪震是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编剧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以“电影造型”为核心概念所建构的新的电影美学思想从一个独特的、建设性的角度切入新时期关于电影本性的辩论,并在其后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建构,是新时期中国电影理论的一面旗帜。他的学术活动和电影教育活动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人的电影美学观念和创作实践。
倪震的电影造型思想经历了“从电影美术出发”“融合电影摄影”“走向电影表演造型”“深化和扩大到电影空间”“探索电影史和导演艺术中的电影造型思想”,以及“从理论到实践:《大红灯笼》的改编和电影意象创造”几个阶段。在《大红灯笼》的改编中,倪震把小说《妻妾成群》提供的一个细节“灯笼”(短短24个字)为电影造型所提供的可能性进行了集中的、反复的强化,并对其象征意义进行了创造、深化和升华,使之成为父权制度下的一种独特的、视觉性的电影意象。
倪震的造型思想大大提高了新时期电影创作者的视觉和影像造型意识。令人意外的是,那一代电影人中有那么多优秀摄影、美工师成为了杰出的导演。从张艺谋开始,梁明、侯咏、吕乐、顾长卫等摄影师,何群、尹力、冯小宁、霍建起、戚健等美术师先后成长为电影导演。不少第六代导演也深受其惠。

上世纪50-70年代,香港电影展现出了对文学性的倚重,出现了较多根据中外文学名著、名剧改编的作品。这些影片与海峡两岸暨香港地区电影的互动分不开,电影互动为其提供了语境和动力。这类香港电影分为三类。其一是根据中国传统戏曲改编的电影,如朱石麟编导的《同命鸳鸯》(1960)改编自莆仙戏《团圆之后》;陈静波导演的《五姑娘》(1960)改编自同名越剧;李晨风导演的《生死牌》(1961)改编自同名淮剧等。这些影片,在文学性上较原著都有较大的提升,如《同命鸳鸯》的原著便是著名悲剧,而改编后的影片刻意营造了悲剧氛围,以撼人的艺术效果来表达其揭示封建制度吞噬人性的主题。
其二是根据中外文学名著、名剧改编的电影。与原著相比,这些影片更适应当时香港观众的接受心理,增强故事性和直接的冲突性,降低政治性,减轻批评性是其主要呈现。如影片《家》(1953)中对高觉新这一形象的批判减至最弱,原作中的觉民、觉慧兄弟参加新文化运动等政治活动在片中全部被取消。《阿Q正传》(1957)的改编也主要让观众享受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在根据国外文学名著或名剧改编的影片中,大部分作品把握住了原著的精髓,但又根据香港的特殊商业语境和观众接受心理融入自己的艺术观。如根据《安娜·卡列尼娜》改编的影片《春残梦断》(1955)中,女主角非但不敢反抗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最后反被丈夫诬告,被迫离开家庭。
其三是根据中国武侠小说改编的电影。其主要包括楚原改编自古龙的武侠小说,如《天涯·明月·刀》(1976)、《三少爷的剑》(1977)等。这类武侠片的文学性表现为以下方面:情节曲折多变,充满悬疑;融入凄迷的爱情;气氛优美,突出唯美格调。

电影与戏剧是最具亲缘性的艺术形式,它们互动、互鉴、互生,跨媒汲取营养,不断产生新的叙事内容和叙述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批主要从事电影创作,并兼具戏剧与电影创作经历的“跨界”艺术家,被我们称为“剧影人”。他们的出现并伴随产生的艺术现象,称为“剧影人”现象。
“剧影人”现象贯穿于整个中国电影的发展,特别是在早期电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现代戏电影创作高潮和新世纪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郑正秋、张石川、欧阳予倩、郑君里、夏衍、茅盾、石挥、张骏祥、吴祖光、黄佐临、谢晋等都是比较重要的“剧影人”。其特点初步归纳为:一是历史贯穿;二是交叉继起,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有的由剧入影或先影后剧;三是多位散发,即“剧影人”涉及电影创作的不同岗位;四是现实自觉,即在当下跨媒介传播和实践兴盛的背景下,产生了“影剧联动”新现象,新一代创作者自觉参与“跨界”转化,由剧入影,又因影推剧,产生了《夏洛特烦恼》《驴得水》《半个喜剧》等作品。
研究“剧影人”现象对研究中国电影的美学溯源、叙事传统、发展突变有着重大意义,对当下培养复合型电影人才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以社会为己任的社会观和艺术观的统一是五四运动后大部分激进艺术家的共同特点。他们努力地以艺术的方式服务社会和救国。他们在时代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斗争。如许幸之放下学业回国参加北伐。
其次,与他们激进的社会观相一致,他们的艺术观方面也受到当时世界范围内左翼现代主义艺术的直接影响,他们把“中规中矩”的19世纪经典艺术传统和秩序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秩序臣服的一种表现,而加以鄙夷。因此,他们在艺术追求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实验风格。这种现象体现在不少艺术领域和艺术家身上。他们大多展现出高度现实主义的题材选择与强烈实验色彩的非写实主义风格呈现有机结合的特点。例如,许幸之早年的《逃荒者》等美术作品;在戏剧领域中,夏衍、沈西苓的工人业余戏剧实践、田汉的超现实主义探索、袁牧之的形式主义实验等;在音乐方面,聂耳运用非常规乐器的人声和自然音响等声音因素介入的电影音乐与歌曲创作的探索。
在电影方面,基于对比蒙太奇的实验风格,早期左翼电影创作也属此列。后来在革命宣传的需要下,他们逐渐注重民众的欣赏需求,对艺术风格的追求和关注为革命现实主义提供了依据。

郑伯奇是中国现代文学、戏剧、电影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从事横跨三界的创作、批评与社会实践工作。坚持艺术规律和艺术家自我的表达,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现实,从发展的、流动的历史与现实的视野来解释文艺现象和文艺规律,是郑伯奇文艺批评思想的主要特征。
郑伯奇对艺术规律一以贯之的体察、尊重和坚持,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切身理解,使他能够不断返回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克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机械化、教条化、庸俗化弊端。他并未因或通俗化、大众化等时代亟需的启蒙样式,而牺牲文艺的艺术性。一方面,他坚持“现实的自我”,将社会、时代、政治当作艺术的“构成”因素;一方面,反对概念化、观念化,主张具体性、生活感、现实感,怀抱强烈的历史意识,在“唯物”上体现出广阔的现实深度;另一方面,对艺术本体、偶然与必然、内容与形式、旧与新等文艺核心范畴进行辩证思考,体现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真正理解与运用。

由《白毛女》开启的新中国歌舞电影提出了两个原则性的问题:其一是媒介问题。舞台与电影分属两种不同的媒介,在新中国电影的发展中,逐渐分化出倾向于实景表现和倾向于舞台表现两种不同风格的歌舞电影。倾向于实景的又可以分两支,一支为了与影像媒介匹配而尽量减少歌唱,变成了插曲电影,如《陕北牧歌》《柳堡的故事》等影片;另一支则尽量寻找适合日常生活歌唱的题材,如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五朵金花》,表现音乐家生活的《聂耳》等影片。倾向于舞台表现的也分出了两支,一支趋向于实景,如《柯山红日》《洪湖赤卫队》等影片;另一支则趋向人工景和程式化表演,如《红霞》《阿诗玛》等影片。
其二是观众接受的问题。歌舞电影中的歌唱能够带来参与感和情动,与叙事表达的思考性对立统一。为了吸引观众,叙事的传奇性需要与音乐彼此配合,形成具有类型化特征的电影作品,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创作环境下,大部分作品都顾此失彼,情节雷同相似的情况严重,只有少数作品能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研究新中国时期的歌舞电影能够为今天的创作提供有益借鉴。

在对中国电影史学研究梳理中,中国早期电影人不仅拍摄了大量的影像作品,也同时作了很多学术梳理,其中包括大量的教材、史学著述、艺术评论和理论构建,形成了中国早期电影研究的学术基础。
陈犀禾教授在《中国电影研究学术发展史纲》中将电影学术史划分了三类,即电影史学研究、电影批评和电影理论。以此为据,本论题将中国早期电影学术史的研究也置于“史学史”“批评史”“理论史”三部分来检视,以电影学术本体的内在理路为本,注重电影学术与社会历史、人文和学术语境交互研究,以期探寻中国电影的文化基因。
在对电影史学的探寻过程中,发现这些早期电影史学记述中,既有通史研究,也有“年鉴”式记录,更多的是微观层面的电影史记录。体现出电影史研究中“论从史出”的理性态度,电影批评实践的历史几乎与电影自身发展历史同步,不仅有来自影迷和专业电影评论者的电影批评文章,对于电影批评标准、理论与方法的讨论与批评观的构建也是始终摆在电影人面前的重要课题。中国电影理论由初发到稳定发展的历程是在文学性、影戏观、电影化之间相互解构与同构中生成的。
总之,从学术史的视角反观早期电影观的形成,系统化考察早期电影学术的内在理路、主要贡献以及在整体电影学术进展中的历史定位,以呼应国家对本土电影文化传统和文化基因探寻的时代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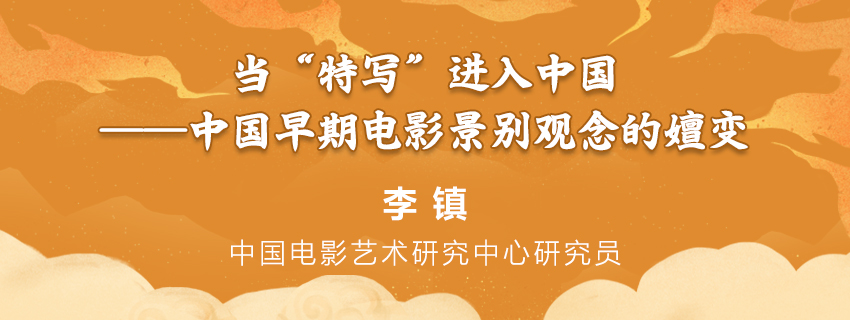
中国人面对景别问题的时候,不仅是认识一种拍摄的基本技术和方法,而是历史进程、精神境遇和文化抉择。中国传统观念非常重视距离感,崇尚间接性,中国画一般不会直接描绘人。中国古代的人物画不发达。在中国视觉艺术中,景别是一种20世纪后开始发展出的现代性观念。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存在过一段热衷于“特写”的历史。
上世纪20-3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的“特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1925年的鸳鸯蝴蝶派电影《风雨之夜》中近景和特写多达713个镜头,占全片镜头数的65%以上。上世纪30-40年代,“特写”作为一个时髦的现代词汇,被影迷奉为电影的妙笔。特写因为具有科学时代特有的机器特性被中国人视为理性工具的象征,人们赋予特写以科学的光环,影评人侯枫将特写镜头和“显微镜”的发明相提并论。特写被中国电影人看做是走向理性、科学、现代、艺术的必经之路。
上世纪30年代后期,特写被滥用,遭到质疑。郑应时认为,“特写”是一件危险的事,它会告诉人这是一种戏剧。西方理性主义的影像表达得不到中国人共鸣。在中国文化看来,真实不在于一定要贴近对象,对于人的真实揭示不必通过靠近人脸的方式。特写把物象和环境剥离,但是中国人的艺术表达向来离不开环境。中国文化本来就有“远”的自觉。远有助于审美意蕴的升华。从精神心里的角度来说,中国人对于远景的内在精神,是放大的,是当做特写来看的。中景最平和,能使人无意识投入,也最符合中国人内在仪式心态的需求,这是它成为主流的基础。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的长镜头很有特色,以中景为主的场面调度镜头增多且变得复杂。虽然一个长镜头的起始景别不是中景,但是从整体来看是以中景为中心设计场面调度的。
从热衷特写,到回归“远”和“中”,中国早期电影的景别倾向映现出国人文化选择的路径,其中包括了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和质疑,也有对传统文化的重拾、再理解与深挖。

在谈到《野叟曝言》或者《文素臣》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多种文本:是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稿》中专章论述的康乾时期古典小说,曾在清末报纸上连载,胡适、沈从文等先生都考证过其版本;也是“孤岛”时期红极一时的连本戏和系列电影。但今天我们不断向传统中寻求电影故事时,却鲜少提及。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异?《野叟曝言》中文素臣是绝对核心人物,但在改编时,文素臣与女性的纠葛却为人津津乐道,戏曲表演中实际处理成了类似疯癫喜剧中性格偏执的男女爱情故事。“孤岛”时期的电影尤其注重女性形象,以女英雄、女性牺牲者等女性命运的展示完成对于时代的隐喻。与之相应的是男性角色的降维。小说中的文素臣可以素手屠龙,天文地理无所不知。改编后去除了“神迹”和大段才学演讲,文素臣成了一个狷狂书生,情感纠葛是连缀故事的主要情节线索。
《野叟曝言》在小说时期屡遭禁毁。“孤岛”时期,文素臣故事的创作意图也不能被真正理解,因此受到抵制。小说本身带有众多局限性,如果进行当代改编,需要大幅度的重读重写。
阿英先生说,历史题材创作的意义就在于使其具有启发当代思考的作用。从这一角度看,对《野叟曝言》改编的考查具有多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