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主流经济学界,一种高度同质化的研究范式已占据主导:数学建模成为衡量学术价值近乎唯一的标准。无论是在顶尖期刊发表论文、经济学专业学生的训练,还是教职的聘任与晋升中,展示数学模型的复杂性,例如严密的定理证明、复杂的计量分析、精巧的模拟算法都被视为“科学”与“严谨”的体现。相比之下,那些致力于理解真实世界经济运行规律,如通过案例研究或访谈,但未能大量运用数学工具的研究,则常被边缘化。这种“建模至上”的文化已让经济学与现实严重脱节,也大大削弱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多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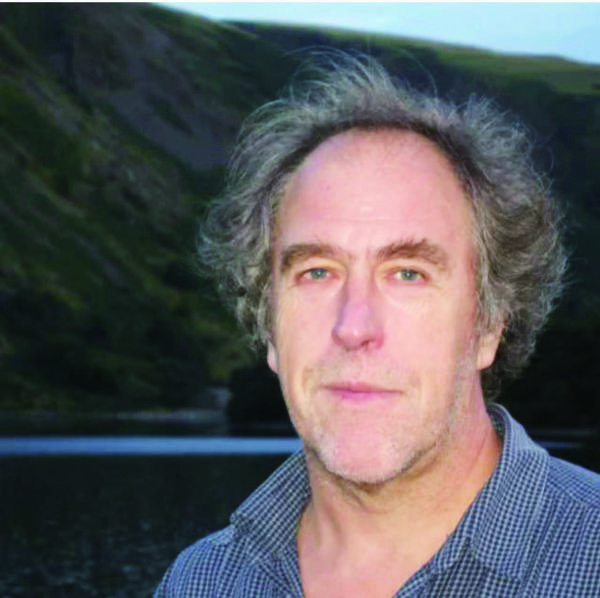
■托尼·劳森 受访者/供图
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与哲学荣休教授托尼·劳森(Tony Lawson)对主流经济学过度模型化的批判,已持续近50年。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他揭示了经济学如何因对精致模型的迷恋而脱离社会现实,并呼吁进行一场从“社会本体论”出发的彻底变革。
对经济学建模的批判
应立足于本体论层面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对主流经济学过度依赖数学工具的批评日益增多。在您看来,当前经济学研究在“数学严谨性”与“现实关联性”之间是否已经失衡?哪些方面最令您担忧?
劳森:经济学过度模型化至少可追溯至二战结束初期。当时面对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畏首畏尾的大学管理者和资助方将资源分配给那些数学建模者,这些人既不解决现实问题,更不批判当时的经济体制。出于诸多原因,数学建模者自此一直掌握着权力与影响力。
自那时起,“非主流”经济学界为寻求现实关联性曾进行过不同规模的尝试,成果时好时坏。但由于长期以来大部分经济学家接受的是数学建模的训练,而且通常只有建模者能在多数经济院系获得教职,唯有建模类论文才能被权威期刊收录,所以那些最终得以在学术界生存的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家,其本身也大多属于建模者。这些所谓的“非主流”经济学家错误地认为经济学缺乏现实关联性的根源在于建模方法的选择,并非过度模型化倾向本身。因此,他们通过采用基于代理的建模替代计量经济学,或得出某些特定政策结论等方式标榜自己的“非主流”身份。但建模的根本问题在于本体论层面——从本体论视角出发,经济学的建模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假设或结论,都难以摆脱与现实脱节的宿命。
为何对经济学建模的批判应立足于本体论层面,即基于社会存在的本质。我已反复阐明,社会现实在特定意义上是开放的、具有深度、本质上是关系性的且处于过程之中,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特征。然而,经济学家所采用的各类方法却预设:社会现实是封闭的,即由各种事件的规律性系统构成,并且处处都是由孤立的原子组成的系统。这些原子在相同条件X下,总会以相同方式Y行动,正如建立“只要X则Y”形式的数学关系所必需的那样。
显然,这种孤立性的前提与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在现实世界中具有的关系性本质是截然对立的;而固定原子假设也与社会现象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这一事实完全相悖。因此,经济建模不仅从未提供过真正的洞见,而且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永远也不会提供真正的洞见。
基于上述本体论层面的原因,我认为当前经济学研究中的“数学严谨性”与“现实关联性”本质上是无法兼顾的。同时,不但数学要追求严谨性,而且现实关联同样需要严谨。我认为,严谨性关乎逻辑的自洽、清晰且缜密的推理,而经济学建模活动恰恰是为了回避这种真正的严谨。
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状况,与其说是由某些当下的“驱动力”所导致,不如说是一种固化的“路径锁定”。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严谨的或科学的研究本质上必须是数学化的。
问题在于,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已深陷于建模的范式之中。这个圈子完全由经济建模者构成,而其中大多数人对建模项目持续未能提供真知灼见感到极度不安。正因如此,出于防御心态,他们难以容忍任何非建模的替代方法,生怕它们的成功会动摇建模范式的支配地位。然而,真正成功的学术研究应始终对挑战持开放态度。
因此,往往只有那些具备建模导向或倾向的新人才会受到鼓励和筛选。与此同时,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更倾向于选择其他领域,而学术界坚信建模必不可少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几乎堵死了批判者进入的大门。所以,正如我所说,经济学界已经陷入了与真实世界无关性的封闭状态。
总之,过度模型化的经济学已脱离现实,无法对宏观经济体系提出切中要害或有力的批判。建模者自身似乎也颇为满足于因展示数学能力而从同行那里获得的赞誉,因此,对他们来说,缺乏现实关联性似乎已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所必须面对的事实。
所以,除了少数仍对现实关联性抱有期望而勉强挤进这个圈子的经济学家之外,几乎没什么人真正在意这门学科的现状。这一现状的所有表现,无论被视为一种趋势还是其他原因,都令人感到担忧,因为经济学已经被禁锢在与现实脱节的境地,分配给它的资源实际上被浪费了。这些资源原本可用于造福社会,既可用于支持那些旨在提供真知灼见的项目,也能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提供更有意义的教育。
与现实关联的起点
在于厘清研究对象的本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行为经济学、复杂性科学、代理基模型、演化经济学或基于访谈/案例的定性等新兴或非主流的研究范式有可能弥补经济学中过度模型化的缺陷吗?
劳森:行为经济学、复杂性科学、基于代理的建模以及大多数演化经济学,本质上仍以建模为导向,因此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即将一个开放的、关系性的、处于过程中的世界简化成由孤立原子构成的封闭系统。案例研究、访谈等方法虽具有现实相关性,但通常远不足以独立支撑研究。
经济学家所使用的各类数学建模方法,其根本问题在于:鉴于社会现实的本质,那些方法根本不适合用于社会分析。运用那些方法就好比是用锤子去割草或清理洒出的牛奶,工具与任务完全错配。与现实关联的起点,在于厘清研究对象的本质,即待考察的社会实在的基本性质,这需要从社会本体论入手,并据此选择与之相匹配的研究方法。
因此,那些以明确、系统且持续的方式致力于社会本体论研究的经济学进路,最有可能实现与现实世界的关联,这也是剑桥社会本体论小组(Cambridge Social Ontology Group)的鲜明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学术界日益强调跨学科研究的背景下,您认为经济学如何从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生态学甚至物理学中汲取养分,以构建更贴近现实、更人性化的分析框架?
劳森:心理学、物理学等学科所研究的对象与社会现象具有本质区别,并各自拥有与之相匹配的方法。当然,如果我们像物理学、心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那样,让所研究对象的本质来决定学科边界,那么我们实际上只需要一门社会科学就足够了。
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生态学、政治学、人文地理学等,至多只是一门统一连贯的社会科学内部的“分支”,其主要区别在于所探究问题的类型不同。所有这些“分支”研究的都是同一种性质的对象,即那些具有深度、关系性、过程性并发生于开放系统之中的社会现象。它们都存在于时间与空间之中。
然而,现代学院派经济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通过坚持在研究中普遍采用数学建模的方法,从而人为且武断地将自己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区分开来。
增强方法论的多样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数据、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兴起,是加剧了“技术至上”的模型竞赛,还是为我们理解复杂经济系统提供了一种更有效的全新工具?
劳森:任何工具,只要与研究对象的本性相契合,便有用武之地。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确实为那些纯粹追求数学形式主义的人提供了更多机会。但是,对于那些优先考虑现实相关性的研究者而言,只要有充分的本体论理由相信某种工具是相关的,他们就可以使用任何可用的工具。
本体论的应用,其目的并非要将某些工具排除在工具箱之外。所有方法都可以被纳入工具箱。关键在于,本体论的立场要求我们始终致力于选择或打造与任务本身相匹配的工具或方法,而不是固执地坚持无论何种情境都必须使用数学工具,甚至在我们尚未了解任务或研究对象的本质之前。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果要鼓励更多元化的高质量研究,学术界的评价体系,如期刊审稿标准、职称评定、项目资助需要进行哪些根本性的变革?
劳森:我认为,整个学术界的体制都需要进行重构。目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大多数学院派经济学家,都只懂得如何建模。如果将现实相关性设为硬性要求,他们将会变得无所适从。因此,我认为,如果改革要体现包容与关怀,过程需要循序渐进;但若想取得实效,变革很可能需要从外部强化。最重要的是,必须彻底变革研究评估体系。至少在英国,这类评估是由一个几乎全是数学建模者组成的经济学家团队执行的,他们只给数学化的成果或研究者打“高分”。这样一来,在大多数经济院系中,实现方法论上的多样性几乎是天方夜谭。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陈密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