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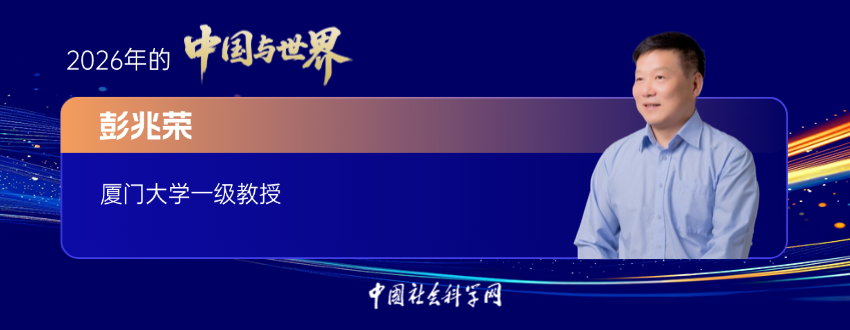
今天,全球出现了生态危机、生物多样性危机,这是联合国发出的警告。其实,造成困境的原因已经非常清楚:人类是危机的主要制造者,同时也是责任的承担者。生态危机的问题主要在于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的使用已经到了需要进行“自我调控—自我治理”的时候了。因此,保护生态也已经成了人类共识,全球各地提倡“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这个概念早在1980年《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中就已提出;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然而,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定义,窃以为是有问题的,原因是只考虑到人类的生存,而生态和生物问题并不是只满足“人类”这一物种,还要保证生物共生共存关系。众所周知,与生态最为相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人类对生态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的耗损加剧,致使生态链出现断裂的风险,生态系统遭受不可逆破坏;二是出现了严重“生物多样性”问题,许多物种处于灭绝和濒临灭绝的危境中。英文中的“生态”(ecology),从语词的溯源看,是从希腊移植而来,原先的意思指某个地方的特性,包括自然、生物、物种等。与“生态”概念联系得最为紧密的是“环境”(environment)。虽然这些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被赋予不同的语义,但“自然—生态—环境”交错使用,“生态—生物—生命”共生共存的关系却是一致的。
美国生态人类学家怀特(Leslie A. White)曾以“能量”的方式看待生态与社会的关系,他提出一个文化进化公式:C=E×T,在这里,C=文化(culture),E=能量(energy),T=技术(technology)。在这个公式中,能量与技术成为文化决定性的因素。虽然不同的生态人类学家对公式的观点存在差异,比如著名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就对这一公式提出了质疑。换之,简单的C—E—T的“线性进化论”已成为人类自我反思的概念,但文化对生态起到了重大作用的认知却一直未变:即有什么样的自然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反过来,特定的文化又在生态保护中起到关键作用。我们可以将这一原型简述为:生态具有自然的能量,文化具备自在的能力。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文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自然能量的耗损成为生态问题的重要切入点,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在《极简人类史:从宇宙大爆炸到21世纪》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参考数据:采集狩猎时代,每人平均每天可以支配3000多千卡的能量;农耕时代,每人平均每天可以支配12000千卡的能量;到了近现代,平均每人每天可以支配230000千卡的能量。人类对能源的采用和对能量消耗的“平均数”或许并非绝对准确,但以历史的演化趋势而言,人类对能量使用的增加和耗损却无异议:即我们一方面在越来越多地消耗自然能量,另一方面生态却越来越陷入危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同的文明体系对能量的耗损上存在差异。
中华文化中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三位一体,和谐相处,既是哲学上的本体论,又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同时包含中式生态智慧和大国责任。这也是我国提出生态优先战略的要旨。
(作者系厦门大学一级教授,联合国《人与生物圈》(MAB)中国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