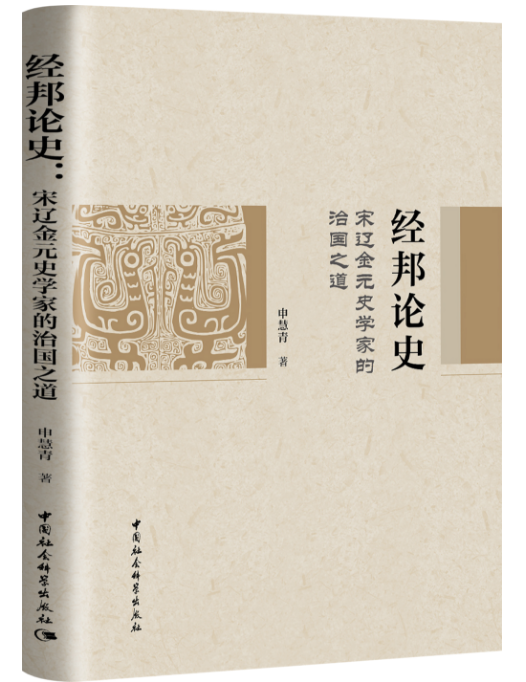《经邦论史:宋辽金元史学家的治国之道》书影
关于宋辽金元史学发展的特点,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指出,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主要特点是“史家的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更加趋于深化”,且有“史学之民族内容的进一步丰富”。从史学发展的阶段来看,瞿先生将宋辽金与元划分为两个部分展开讨论,以突出元代史学的多民族特性。而于《经邦论史:宋辽金元史学家的治国之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5月版)一书,申慧青教授则在“新的阶段”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史家的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是如何深化的,以宋辽金元的治国之论为聚焦点,从史学史发展的角度考察这一极具历史延续性的时期,观察宋辽金元所表现出的“史学家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的总结、归纳与思考”。可以说,本书是将宋辽金元的治国之论作为“历史理论”加以展开并作深入探讨的作品。
顾炎武云,“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所谓“史笔”,即史学家在叙事中所采用的写作方式,或秉笔直书,或有笔削褒贬。“法”之义,许慎谓“㓝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之,“㓝者,罚辠也。易曰:利用㓝人,以正法也。引伸为凡模笵之偁”。由此来看,史笔有法之“法”,在本书宋辽金元史学的语境下,即史家撰著中具有规范性的“义理”,具体来说则是史家对君主“内圣外王”之道德品评。申慧青教授在本书中,从影响史学家治国之道的思潮、治国之论的形成、理想化人君形象的再塑造这三个层面,对这一长时段、多民族融合时期的历史书写进行分析,以展现当时史家著述之“法”形成的背景、内容与影响。
首先,本书描摹了士大夫群体对“以史为鉴”的重视和对“得君行道”的期望,以及在这两种思潮影响下史学的变化。
一方面,在对唐五代盛衰转换的忧患意识下,宋代以来越来越重视编年体“通史”在历史借鉴中的优势,随着《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通志》《文献通考》的问世,“会通”之义愈显,“以史为鉴”的观念与史著、史论之间形成互为促进的关系,推动了宋辽金元史学家着眼于历史规律与经验的总结。
另一方面,宋代理学的流行与“内圣外王”说的兴发,推动了士大夫政治主体性的发展,“义理”亦成为治国理政的中心思想,在对君主的要求上,也形成了“治心”与“治国”的统一。因此,在宋代以后的史学发展中,“义理史学”成为主流,关于“正统论”的探讨以及对帝王个人修养的要求成为重要内容。“所谓义理史学,即以史著和史论传儒学尤其是理学中的‘天’‘性’‘道’‘理’等概念,用历史著述凸显道德性的行为准则”,范祖禹的《唐鉴》、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可为代表。在此思潮下,宋代以后史学家对“君德”的评判主要依据道德和功业两个维度,对君主的要求则以内心修养作为国家政治的起点。在“以史为鉴”与“内圣外王”观念的双重驱动下,宋辽金元之士大夫亦依托经筵制度将治国理论贯彻于君主的教育之中,并以之作为“得君行道”的重要途径。
其次,深刻的“忧患意识”也是宋人治国之论中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在此精神影响下,改革与变法成为两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申慧青教授指出,“居安思危”意识,源于宋代激荡的社会局势,也是传统儒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发展与深化。“变法”的进程促进着宋代史学的发展,《资治通鉴》《稽古录》成为“资政”史学的突出代表,堪称中国古代的“帝王学百科全书”。
历史实境是培植思想的土壤,思想本身不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本书从思想跃动切入史学脉络,犹如透过皮肤观察毛细血管,是对史学发展内在肌理的深入剖析,展现了宋代以来历史书写主体的精神世界,这无疑是作者深入宋辽金元政治社会、文化与史著史论的体现。
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核心命题,历史书写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无疑也是“思想史”发展的一个侧面。本书通过不同史家的论述,不仅详细讨论了宋代以来“正统论”“君主论”的衍变,还展现了各时代中“人君”形象的戏剧性转变,以及这种“思想”维度的力量是如何通过史著史论影响人们对历史人物的态度和看法。
总之,本书深入探讨了宋辽金元历史书写的形成过程、价值判断与形象塑造,呈现了宋辽金元的政治文化、社会变迁与史学发展的脉络,为读者创造了一个多维度立体的史学世界。《经邦论史:宋辽金元史学家的治国之道》是一部值得细细品味、研读的力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