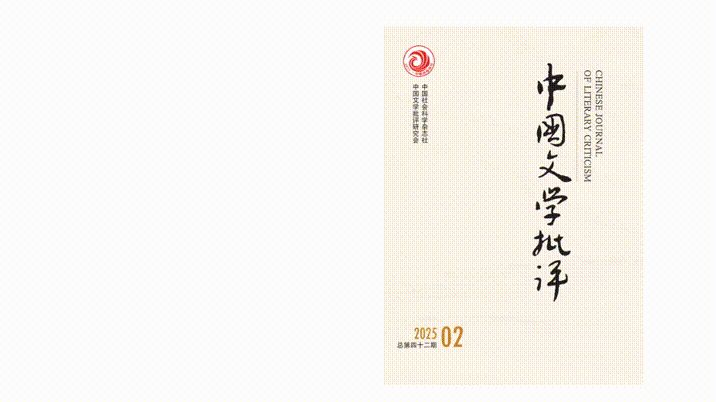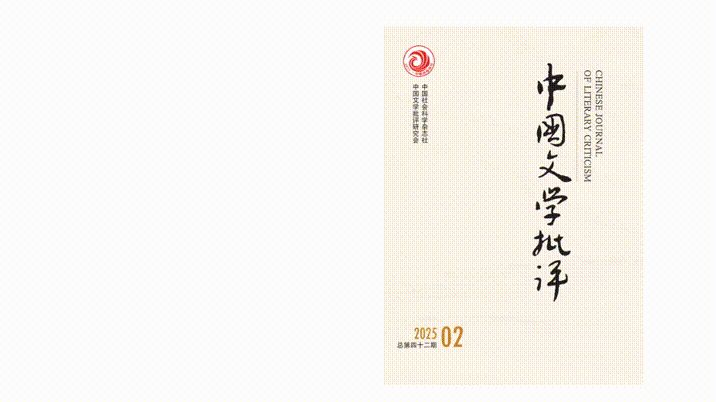
《云落》的主人公万樱是一位“异常”的女性,也是整个作品的核心,同时,我认为她身上隐藏着理解张楚作品的密码。张楚对“万樱”这个人物情有独钟,在中短篇小说《樱桃记》《刹那记》里已经写过,却意犹未尽,又在《云落》中为其建造了一个更大的可以尽情表演的舞台。所以,万樱不是突然出现在《云落》中的,而是在张楚的艺术空间中反复发酵,最终在《云落》中“完整”呈现出来的(“完整”是相对的,不排除以后张楚还会写她)。评判一部长篇小说有很多标准,其中之一是它贡献了一个“典型人物”,即与众不同的“这一个”。万樱是张楚的“这一个”,也是当代文学现场之中的“这一个”;读懂张楚的密码,就在于对万樱的诠释。这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万樱这个人物看似“日常”,实则高度隐喻化,承载着张楚诸多关于世界/人生的独特认识,以及小说表达中呈现出的当下书写的可能与限度。万樱不是来自生活(现实)的,是被“建构”出来的,易言之,万樱与“原型”差别很大,是作家根据想象和需要“设置”的人物。这并不是说作家过度使用了虚构的权力,而是说人物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作家叙述的目的——在这里作家必须要强有力地掌控人物及其周边状况,否则就会让人觉得“脱离现实”。这对作家来说固然是冒险的,但一旦“达成”就会反转,人物会自动生成作家未必可以控制的内容,自我链接到“谱系”之中,可以永久地“活下去”。这是本文打算分析《云落》中万樱人物形象复杂性的理由。
一、异常的“安全感”
如果把万樱的简历和基本生活状况做成表格,只看“资料”,读者的直观感受可能是“普通”。小说中的万樱是北方某县城云落(张楚的故乡滦南是其原型)的本地人,大概39岁,已婚。万樱长相并不出众,小说多次借助别人的视角,说她胖、粗笨。这对一位女主角来说是天生劣势,因为未曾登场就失去了大众文化所通行的“颜值即正义”。她高中肄业,无正式职业。万樱一天很忙碌,早上的工作是清扫马路,上午到窗帘店打杂,中午到一个老太太那里做保姆,傍晚到按摩院做按摩工;晚上回家接替婆婆(曾在农贸市场卖活禽)照料植物人丈夫华万春——可以说,她是茫茫人海中毫不起眼的一滴水。万樱的母亲是个裁缝,父亲死后,有个煤矿工人经常来她家,侵犯过少年时的万樱,某一天忽然失踪了;后来搬到她家与母亲同居的是一个鞋匠。现在,母亲、鞋匠和弟弟草莓,到安徽养螃蟹去了,与万樱几乎没有联络。她虽然已婚,但丈夫是植物人,相当于不存在。万樱学历低,所以只能依托同学、熟人关系,靠打几份工获得微薄报酬。从上述基本信息可以知道,万樱的人物设置是:一位地位不高,经济不佳,挣扎着生活于县城的中年女性。她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也乏善可陈,没有“亮点”。
万樱的这种“出厂设置”并不是她的全部。对于长篇小说来说,女主人公如果是“普通”的,那她一定有“额外”的内部力量加以弥补。易言之,这个女性最大的看点正是她的超越他人、“异常”的行动和理念——“普通”不过是为了让“异常”不那么明显的背景。《简·爱》中的主人公就是相貌普通的,但正是如此,才使她“征服”罗切斯特的道路变得更为艰难,当然,也因此变得更为“纯粹”。这种“普通”中的“异常”,与她熟识的罗小军的感受是:“她像只披着斗篷的刺猬攥着生锈的剑在月光下行进,斗篷腌臜寒酸,布满了窟窿,可她仍以为自己是个骄傲的女王。她不知道,此时的她,比别的女人都美。”如是,张楚没有把万樱写成一个毫无特点的“普通”女性,而是特别写了她的“异常”,这是第一眼看不到,通过仔细观察才可以发现的——只不过没有人如此做罢了。很明显,张楚在这里动用了作者的“特权”,赋予观察者发达的洞察力,让他们“发现”了“异常”的万樱。
所以,按照逻辑,万樱是小人物,别人看她的时候,应该如同看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祝福》),唯一可以拿出的是同情的眼光,但《云落》中的万樱却有一种特殊光环,让观察者感觉她与众不同。张楚对万樱的这个人设是“不合常理”的,也是小说的看点之一。
小说中,罗小军是少女万樱的暗恋对象,是云落知名企业家,事业有成,却一直珍藏着少年时万樱匿名写给他的信件。中年之后,罗小军见到她就“有种想抱揽入怀的冲动”,却“不晓得为何有如此古怪的念头”(第152页)。他体会到,万樱带给他的是一种“可疑的、莫名其妙的安全感”(第153页)。所谓“安全感”,是拥有心理上的依靠和慰藉之后才有的体验,是一种可以把人从焦虑和恐惧中解救出来,从而通往救赎、幸福的力量。罗小军认为万樱带来的“安全感”是“可疑的、莫名其妙”的,与其说他不擅长总结,不如说是《云落》的叙述策略——不可能有毫无来由的安全感,只是体味和分析不到位。
这种“安全感”首先来自万樱的“利他”特质。她给罗小军做的虾皮萝卜馅的蒸饺,是他在任何高级饭店都吃不到的口味,而万樱却不要求甚至讨厌他的回报。这让处于尔虞我诈商战中身心俱疲的罗小军耳目一新。不仅对罗小军如此,万樱的“利他”是普惠的、平等的。她时刻都在围绕别人转,为他们分忧解难,这是打工的必要,更是不计报酬的情感陪伴和支出。绝大多数人是把自己作为中心的,所谓“自私”是普遍的人性。那么,能够“反向”而行的万樱,虽然相貌、身世和工作都很“普通”,却是“异常”的。万樱的“利他”中有熟人社会相互扶助的因素,但她对陌生人同样如此,这使她有别于常人,这就有了精神层面的讨论度。难得的是,万樱对此一无所知,她的“利他”并非刻意的慈善和布施,而是出自朴素的本心。万樱对她周边的来素芸、蒋明芳和城里来的老太太同样是毫无私心地付出。即便万樱想寻短见时,看到一个同样想自杀的老太太,还不忘劝她继续生活,为此还搭上了别人刚送给自己的排骨。“利他”意识是人本性中都有的,区别在于多少——万樱是少有的充沛者,所以她才会显得很“异常”。
万樱与几位男性之间的关系,堪称神奇,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女性,却很有“异性缘”。她以柔克刚,用包容和宽容化解了他们的苦难和仇恨。常云泽是被收养的流浪儿,受到继母虐待,在无爱和仇恨的环境中长大,后来又从事长途货运工作,性情粗犷,“这是一个没有原则、铁石心肠的恶棍,没有什么能真正地撼动他,让他的心脏柔软片刻,如果有,可能就是万樱了吧……”(第351页)万樱对丈夫华万春的照顾更不用说。丈夫车祸后就成了植物人,晚上全靠万樱伺候,他们的关系,类似大人与儿童。还有上述的感受到强烈“安全感”却无法知晓原因的罗小军。常云泽、罗小军、华万春三个男人年龄不同,身份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受到万樱的照顾和呵护——他们寻找母性带来的“安全感”的心理,在万樱这里得到了满足。
万樱能够带来“安全感”的另一个原因是“忍耐”。面对生活的各种不如意、困难乃至苦难,万樱照单全收,极少怨恨和抗争。万樱在丈夫华万春成为植物人后,对他照顾有加,但仅是尽义务,因为他们的感情之前已经破裂。华万春创造了医学奇迹,竟然在成为植物人的六年后恢复正常,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含辛茹苦照顾自己的万樱离婚。万樱对此却没有“怨恨”,而是接受了离婚协议。当万樱准备把怀孕的事情告诉常云泽时,常云泽却先说了自己准备与他人结婚,于是,万樱按下不表,仍然选择“忍耐”。作为对比,来素芸是一个“怨恨”型的人物,她心比天高,因为生病考云落电视台未果,没有当成主持人,开了窗帘店。她的感情生活一塌糊涂,不断换身边男性,却找不到靠谱的;还因为参与集资,差点损失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因为万樱随叫随到,才使来素芸的“怨恨”只是停留在摔手机、砸电视和骂员工层面,并未形成实质性的心理创伤。她每天都在抱怨生活不公,与万樱的从来不说“不”形成反差,正好注释了万樱的“安全感”——对来素芸来说有求必应。
那么,生活中只是“利他”和“忍耐”的万樱该不该由此而产生“怨恨”呢?按照舍勒的论述,“怨恨”是现代伦理结构中很重要的内容。如果是个“普通”人,如来素芸、常云泽、华万春,“怨恨”当然应该有,也是确实有的,但是由于万樱的人设,所以她的“异常”才是“正常”。小说中她的“自杀”是一次对生命的拒绝,但很快她就“想开”了。因此,万樱是个情绪稳定的、不断为身边人提供“安全感”的人,她自己生活虽然很艰辛,却具有超常的“忍耐”力,丝毫没有“怨恨”,这使她的“异常”不那么简单了——是需要进一步解释的。
二、“地母”的当下版本
很容易联想到,万樱是一个“原型”人物,有文化史上经常出现的地母(或曰大母神)形象的影子。所谓“原型”,就是经常在文艺作品中出现的一类人物形象,通常来自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地母是一个系列,源远流长,形态各异,是人类文化中最基本的崇拜对象之一。圣母、希腊女神、女娲、妈祖等,在世界各地都有信徒,这种现象本身说明,地母是人类潜意识中的“本质”性形象。具体到文学作品,地母类的女性形象屡见不鲜。地母的特征就是由己及人的“利他”,还有由人及己的“忍耐”,她们生活在底层,在丈夫缺席的情况下(往往是死亡、失踪或不负责任),忍辱负重,含辛茹苦,以宽阔的心胸包容儿女和一切。她们具有生育本能和强大生存欲望,携带着无差别的奉献,以此抚慰人生暗夜中的孤苦灵魂。当然,不同作家对此有不同理解和表现。关于地母和地母崇拜问题,女性作家涉足得较多,但男性作家也不遑多让。莫言的《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是生活于晚清、民国的山东农村普通妇女,没有文化,生育了八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与不同男人所生),把他们全部抚养成人,承受了强奸、饥饿等各种不幸和苦难,却丝毫没有抱怨,只因她有着坚强而朴素的、部分来自宗教的“忍耐”的意志。之所以说《云落》中的万樱也可以从这个参照系理解,盖因万樱的“利他”“忍耐”气质与地母精神是相通的。
《云落》中有一座娘娘庙,香火很旺,虽然作品有意没有多做联系,但还是让人有所联想。另外,作品中数次有意无意做出暗示。作品描述万樱说,“在她看来,她生来便是欠着人家的,钱也好,物也好,情分也好,统统是她的错处”(第304页)。万樱的“赎罪”心理,虽然她并未意识到,但却是慧根所在。万樱的长相被称为“一副菩萨相貌”,虽然来自路人的恭维,却有旁敲侧击的效果。来素芸说万樱,“你还真是王母娘娘,天上地下没你不管的”(第377页)。因此,将万樱置于地母形象系列中,并非突兀之论。对比一下可知,《云落》中的来素芸、罗小军、常云泽等人物是“普通”的,因为他们总是在做出“正确”的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但万樱的选择则是利他的。她欲望低,无所求,愿意奉献,护佑他人,特别能忍耐,是地母的《云落》版本。
在张楚这里,万樱也是逐步“生长”起来的。读《云落》时,熟悉张楚的读者会发现,其中的个别人物和情节似曾相识,来自他此前的作品《樱桃记》(2004年《中国作家》)和《刹那记》(2008年《收获》)。当然,张楚对其做了大幅度改写。对照几个版本可以了解,万樱是在张楚的雕刻下逐渐成形的。万樱这个人物,在短篇小说《樱桃记》中就出现了。作品中樱桃矮胖腿短,右手只长了三根手指,是同学们(包括罗小军)嘲笑的对象,却对爱收集地图的罗小军产生了恋情,为得到地图还受到了继父性侵。这段少女的创痛不被罗小军知晓,只能由她默默承受。《刹那记》是樱桃的前传,为《云落》提供了诸多万樱的基本设定,如生活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小镇(根据小说中的流行歌曲可以判断)、家庭成员和父母的职业等。小说的主干情节是樱桃与继父的关系受到母亲怀疑,她的良性肿瘤被误解为怀孕,闹了乌龙事件。《刹那记》中的樱桃遭到不明身份青年的强暴,却得到了家人的关爱;虽然不敢把情书投递给罗小军,却拥有一个青春期女孩卑微而美好的梦想。《刹那记》中的樱桃已经有很多《云落》的影子,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最大的不同是,万樱在《云落》中虽然仍很卑微,但却成为一个施动者,不但可以忍受所有苦难,还以旺盛的生命力和饱满的情感,润泽周边所有人,与《刹那记》中那个心怀梦想、等待救助的女孩相比,这个变化是颠覆性的。也就是说,是到了《云落》中,“樱桃”才脱胎换骨,变成了“万樱”。
为何张楚这么写万樱?其实,存在主义者视角中的“樱桃”和地母“万樱”,是一个人物的两个面相。2016年的时候,张楚用不确定的口气说到自己小说的特质:“那群内敛的人,始终是群孤寒的边缘者,他们孑孑地走在微暗夜色中,连梦俱为黑沉。只有在黑暗中,他们才能各得其所。这是件真正细思恐极之事。”这是存在主义视角,表现出黑色、悲观的调子。逐步地,张楚叙述的调子变暖。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其实我一直在构思一个长篇。我想写樱桃长大之后的故事,想以她从青春期到成年之后的成长史为线索,写一个县城和一个女孩子心灵的变迁,写一个笨拙、卑微的生命在历史长河中如何固守自己的位置。”在此理念下,虽然还是关注小人物,但张楚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尤其到了《云落》,集中了张楚对弱势群体的理解和关怀,这也使《云落》更具有层次感,提出的问题也更为复杂化,不是那种直接的“反映”式的单骑突进了。
回顾张楚此前的创作可以发现,他“打造”万樱的行动没有停止过——卑微、笨拙,但是坚韧不移,这类地母类人物一直在张楚的小说中若隐若现。《野象小姐》中,“野象小姐”名为鲁叶香,长得很胖,在医院做清洁工,穿44码的鞋子,没有结婚,带着一个智障儿子。她白天到医院做工,晚上兼职到酒吧跳钢管舞。虽然生活很拮据,却如同溺水者,顽强扑腾,保留着生的希望。与此同时,“野象小姐”身份神秘,智障儿子来源成谜,但她乐观、勇毅,感染了周边的癌症患者,给了他们抗争命运的力量。《良宵》中,一个到村里居住的老太太(此前是著名戏剧演员)离家出走,顶住儿子、村干部的压力,寻找、关心谁也不敢靠近的得了艾滋病的男孩,“当孩子冰凉的小手紧攥住她榆树皮似的掌心时,老太太身上忽就有了气力,手脚在瞬间都热了起来。有那么片刻,老太太确信双腿其实就踏在棉花般洁净干燥的云朵里,每向上微微跨一小步,就离天空和星辰更近了半尺”。这段描写中的老太太,显然是超越的、带有神性色彩的。张楚喜欢把人物设置在一个极端状态,让他们面对生和死的问题——至少也是徘徊在这个主题的边缘——用浪漫主义文学的方式,展开他对生命问题的思考。因此,他的笔下出现“地母”类的人物万樱,可能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三、文学史中“活着”哲学新解
重要的是,张楚给万樱这个地母类形象增加了很多“当下”和“自我”的内容,这使她成为具有相当“个人意志”的形象。
《云落》中的万樱,是张楚对文学史中弱势群体问题的“当下”的回复。弱势群体概念比较复杂,人群所指也不同,且因为不同历史语境而多变,具体是指为了生存而挣扎的社会分层中的群体,如农民、矿工、农民工、下岗工人、失足女、快递员、保安等,都曾经是文学叙述中的弱势群体。现代文学中,鲁迅对祥林嫂、闰土、阿Q的关注和书写,就是对弱势群体关注的开端。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底层人物虽然有同情,但更多是批判,希望通过“呐喊”,惊醒睡梦中的他们,逃离“铁屋子”,试过后感到无能为力,“荷戟独彷徨”。这个工作“当下”仍处于“未完成”状态。21世纪以来,曹征路的《那儿》、谈歌的《大厂》、刘庆邦的《神木》等,展示出弱势群体面对的尖锐的苦难。晚近,“东北文艺复兴”,班宇、双雪涛、郑执以小人物为主人公的一批作品横扫文坛,使弱势群体的问题再度成为焦点。
万樱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关注弱势群体的线索在当下的延续。此前曾交代,她少年时遭受性侵,早恋无果,成年后下岗,每日辛苦打工,生活条件不好,因为容貌和身材被身边人调侃,并成了顶着巨大道德压力的单亲母亲——按照常理,她应该有因为“不公”累积的强烈“怨恨”,但是,万樱却对此安之若素,予以全部接受。小说中,罗小军看到万樱生活困难,问她“这些年……你是咋扛过来的?”普通人可能怨天尤人,但是万樱却出人意料,以“不挺好的吗?能有啥不好的呢”(第38页)来应对。关于万樱的反应,可以有诸般解释,而张楚赋予她地母般异常的“忍耐”,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面对不公,其实万樱也不是完全照单全收,没有任何抗争。当她知道自己怀孕后,精神压力巨大,跑到涑河边打算自杀——正是对“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的回应。“但是这不过是一瞬间的冲动,因为万樱的自杀念头并非“生活毫无意义”,而是“怀孕会带来道德指责”,后者显然不足以压垮万樱,所以她很快平复,放弃了轻生想法。在万樱的哲学中,道德规范从来不是占首位的,对她约束力很小,因此她才能够有博大、宽容的心胸,包括面对“苦难”。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普通人无法忍受的“苦难”,在万樱这里似乎没那么严重,甚至还有点麻木和无所谓。因此,万樱是一个生活在苦难中且对苦难不加辨别、照单全收的底层女性。她处于黑暗中,身上带有久远的“劣根性”传统,不得不令人想到鲁迅的批判。“利他”“忍耐”带来的负面问题,张楚没有发挥,目的是使万樱的选择更为“纯粹”。也正是在这里,对相同的问题——万樱或者沉默,或者反抗——张楚展现出不同的洞察力和处理方式。万樱虽然是底层小人物,但由于身处地母的谱系,对“苦难”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承受能力,不仅如此,如上所述,她还以“利他”和“忍耐”做出回报。
将万樱形象置于当下,可以看到,她体现出当代作家关于“活着”哲学的新的思考,这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的。关于“活着”问题,新时期以来,很少有作家正面强攻,处于“失语”状态。其实这个问题并非不言自明,也并非作家不感兴趣,而是具有相当的难度,何况从选题上说并不讨喜,因此受到冷遇很正常。余华和史铁生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所建树的。余华在《活着》中,借用福贵的故事,剥离掉了“活着”的意义,使其裸露出存在主义的荒谬却真实的肌肤;史铁生的作品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叩问命运,个人化地逼视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70后”作家中,张楚是少有对“活着”问题持续做出探讨的。他的主人公往往批判现实,“生活在别处”,渴望“逃离”,并进行徒劳的努力——《中年妇女恋爱史》中的茉莉、《简买丽决定要疯掉》中的简买丽,都是不断“逃离”、折腾不止的人物。万樱的独特性在于,她实践了另一种对待“活着”的态度。万樱发现自己怀孕,担心不伦之恋被发现,准备结束生命,一了百了。就此来看,她并非对现实很满意,也曾在生命“意义”问题上徘徊。万樱准备投河自尽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也打算寻死的老太太,计划发生了“延宕”,结果改变。这个延宕其实是万樱自己,也是张楚对“活着”意义的认识和阐释。《云落》中的人物都不去思考为何“活着”,这种态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如余华《活着》的主题)。但是万樱的不同在于,她“活着”是因为“惦记”。她想,“这么死了,省心,再也不用做牛马,膝下没有儿女,囊中没有钱财,房产证上写的名字是华万春,裁缝草莓在安徽养螃蟹,好坏有鞋匠照顾……”(第246页)自杀前,她“惦记”的还是父母、弟弟和丈夫,凡尘俗事、亲朋故交一个不少。而那个神秘的老太太,如同河神,知晓万樱从小到大发生在河边的故事,也是从“惦记”的角度说的:“这世上,总要有让你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的糟心事,日日磨着你,月月吊着你,年年熬着你,你才活得有心劲,在人世的那口气,才吊得长些。”(第250页)也就是说,作品借助“神谕”(老太太说完消失不见,作品暗示违反常理),阐释了关于“活着”的问题,主张把“糟心事”作为吊着自己的“心劲”——这个道理颇类似佛教所谓“即烦恼而菩提”。二人相约都不寻死,明年再见。老太太承诺送给万樱一只汉代玉器,可以用来喝酒,万樱打算送老太太她心目中最重要的礼物——一只猪背腿(“热爱凡俗生活”的象征,也是“惦记”)。“惦记”在这里不仅是一种想法,还是本体性的概念,与“放下”“四大皆空”等超离的选择是相对的,是万樱在哲学的角度对生命意义的确认。万樱的自杀及其被“治愈”,其实是《云落》对万樱定位的必然延续。于是,与此前关注弱势群体的作品不同,作为承受苦难者的万樱面对现实时,心态不是崩溃、反抗和逃离,而是选择“平静接受、乐观面对”。
可以说,万樱对待“活着”的态度,是理想化的,也是“张楚化”的。我们可以从身边找出《云落》中的其他人物,但是找不到万樱,或者很难;我们绝大多数人不想成为万樱,但渴望身边有个万樱——就这一点来说,万樱是一个“高概念”的人设——不是主题先行,而是从不同角度认识一个常见的概念。对于这位底层女性,张楚选择了不同以往的处理方法。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结尾“他们在苦熬”曾让张楚心有戚戚,写作的时候不断盘桓于脑海,但他又向前迈了一步,这个理念被印在《中年妇女恋爱史》的腰封:“她从失败中来,再到失败中去/她从来没有放弃,也从来没有收获/她那么美好,犹如春天夜风中的蒲公英。”这几句话已经透露出,张楚不准备像此前的作家一样,用“知识分子”的眼光来看待他笔下人物的“失败”,而是更为注重“过程”,并对其坚韧的生命力做出肯定和赞美。只有从更为宏大的悲悯视角,才可以理解万樱的选择。考察《云落》中的所有人,罗小军、来素芸、常云泽以及各个配角,似乎都有各种“失败”和“不如意”。有的死亡、有的入狱、有的出走,但活着的,仍旧在路上。面对这一切,万樱改变不了什么,但不“怨恨”,而是更能接受,甚至“以德报怨”,回报给生活——天地不仁、众生皆苦是必然的,所以欣然接受也是正常的。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女性,就是在这样的哲学境遇中,呈现出了“这一个”自我。
也许有人会说,万樱的“状态”与现实不符,安于现状就失去了批判现实的力度。其实,只要细读《云落》,就能从万樱及周边人物的遭际中找到很多类似问题的蛛丝马迹,作品并没有回避这些问题。《云落》的独特性在于,并不打算刻意强调万樱的下岗女工的苦难(这是明摆着的),写成一个《秋菊打官司》或《我不是潘金莲》式的反抗的主人公,这并不困难,而把万樱写成现在的“状态”,还可以取信于读者,才是困难的。就此来看,张楚做此选择,不是突发奇想,而是在对万樱类人物做了充分了解后,做出的不一样的探索。
结语
万樱是在《云落》中“诞生”的新的人物,但她却有着古老的“地母”基因,因此她尽管有普通小人物的人设,却是个带有悲悯情怀的理想化形象。在张楚笔下,万樱并不是一个可供学习的“标杆”式人物,他也没有把万樱的态度作为面对现实的“良方”,有时还故意解构,让她接点“地气”。万樱的以德报怨,本身就是超越的,也并非不可尝试,这其实是更符合宗教意识的——对于张楚处理的题材来说,从酷烈的个人惨剧到忍耐和救赎,本来就是硬币的两面。此前他关注第一面的“是什么”,写了不少因为恶产生的罪案和死亡;但也没有忽视第二面,即“如何解决”第一面的问题,并在《云落》做了深入讨论。万樱对待“活着”的态度,是地母形象的当下版本,也是带有“异常”的“正常”。二者之间的无缝切换是张楚的功力所在,因为稍有偏差,人物就会让读者产生“不真实”(试想主人公是个普济天下贫苦人的女神)的反应,但张楚用万樱“正常”的一面让这个人物立了起来:她是云落的芸芸众生的一员。因为有强大的细节支撑(这不是本文讨论范围故而从略),万樱并不显得“观念”。由此可知,万樱是有“来路”的——她身上扭结着地母谱系和弱势群体书写两个传统,回答了当下“活着”的问题。这是张楚的写作中必然要解决的,同时也是当代文学中关于“活着”哲学的新的讨论。张楚赋予万樱“安全感”的举动并非简单化地展示爱与和平的“媚俗”,而是在悲悯的视角下,让万樱代表他对现实的具有张力的和解(忍耐),并特别强调去“改造”的意义(利他)。这个观点躁动在张楚作品里很久,终于借助对万樱的书写完成了一跃,由小人物的“被动”接受转换为地母般“施予”——尽管只是精神上的。万樱的意义在于,世界仍然是那个世界,但是有了她的存在,就不再是存在主义的“他人即地狱”的世界,而是烟火蒸腾、有情有义、充满“活气”;她的态度和影响,正是人类赖以抵御困苦的宗教般的慰藉和希望(安全感)。因此,万樱的出场和张楚的选择,是经过淬炼后的看世界的角度,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之后,与现实保持着既冷又热、恰如其分的温度的境界。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