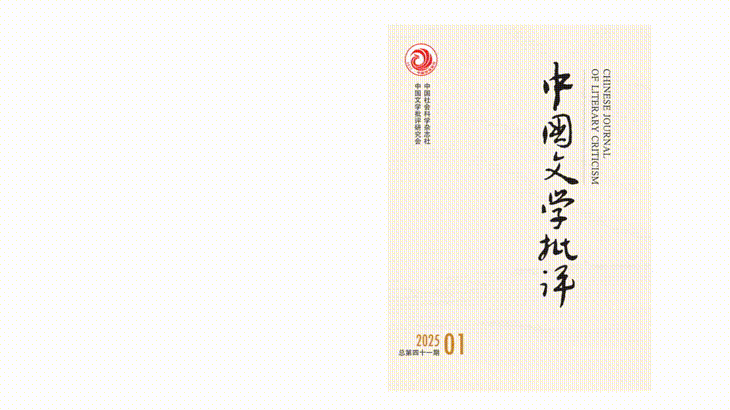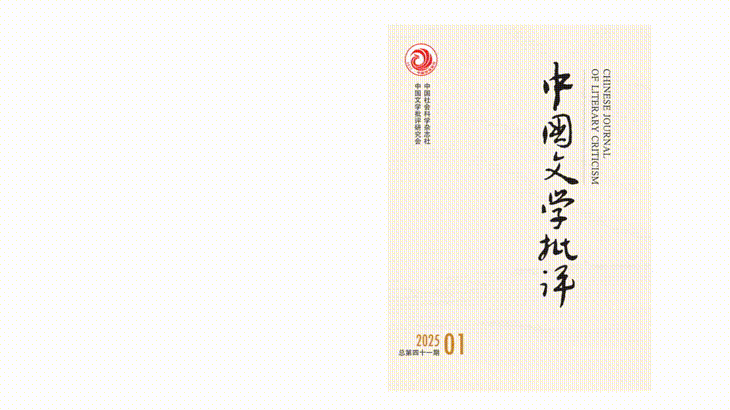
在中国美学史上,王国维曾使用“壮美”“优美”这一对概念来分别形容使人意志破裂和与人无利害关系的自然之物或艺术描绘。不过,王国维并非最早注意到壮美、优美之间的区别并进行详细阐释者。往前追溯,学术界提到清代桐城派文论家姚鼐的颇多,但往往忽略“早在姚鼐之先,魏禧对于壮美和优美就曾经有过很好的论述。” 叶朗甚至认为,王国维把“壮美”定为“有我之境”,把“优美”看作“无我之境”即是受到魏禧思想的影响。
魏禧为明末清初著名散文家,与侯方域、汪琬并列为清初“古文三大家”,被尊为“易堂九子”之首。综观其生平创作,不仅以散文作品著称于世,而且在文艺理论方面也颇有创见,其壮美观即是显著一例。
魏禧关于壮美的论述主要见于《魏叔子文集》卷十《文漱叙》一文。该文是他为无锡钱子础的文集《文漱》所作的叙。在该叙中,他对壮美的理解是基于对自然万物的观察,并引申至文章创作与品评。“‘风水相遭而成文。’然其势有强弱。故其遭有轻重,而文有大小。” 因此,在魏禧笔下,壮美来自自然的雄伟壮阔,“洪波巨浪,山立而汹涌者,遭之重者也”,和“沦涟漪激,皴蹙而密理” 的优美形成对比;亦来自昂扬的道德文章,“有忠臣孝子义士节妇之文,足以震动天地,摇撼山岳”。在《文漱叙》中,魏禧实际上以自然壮美为铺垫,比拟自己对“忠臣、孝子、义士、节妇之文”的赞赏。抛开他受时代局限的道德标准不谈,他的壮美感是和文章的内容紧密结合的。表现道德高义的文学作品成为激荡人心、撼人心魄的壮美感的主要来源。
审美客体或恢弘强大,或道德大义高扬,文风犀利磅礴、气势充沛、情感真挚,引发了审美主体的“惊而快之,发豪士之气,有鞭笞四海之心”。可见魏禧对壮美的阐发并未止步于对壮美来源的观照,而是进一步点明壮美产生的心理情感:豪迈激昂。但“惊而快之”则暗示这种情感并非一蹴而就的单维度存在。为了阐明自己对壮美的多重感受,魏禧讲述了泛舟于江上的经历。“吾尝泛大江,往返十余适。当其解维鼓枻,清风扬波,细激微澜,如抽如织,乐而玩之,几忘其有身。”风平浪静时,微风轻扬、水波不兴,人乐而忘返;但“及夫天风怒号,帆不得辄下,楫不得暂止,水矢舟立,舟中皆无人色,而吾方倚舷而望,且怖且快,揽其奇险雄莽之状,以自壮其志气。”魏禧描述的惊惧来自与自然的对抗,但快感却来自超越了对抗,经气为媒,由此而上升到与宇宙合一的境界。并且,他进一步把壮美、优美的审美感受做了对比,“轻者人乐而玩之,有遗世自得之慕”。
显然,相比优美触发的怡然自得,壮美涉及的心理更为曲折丰富。无怪乎叶朗评价魏禧对美感心理的分析在中国美学史上前未有之。从魏禧对壮美的细致描绘,层层深入可以看出,虽然赞同两者不可偏废,但壮美仍是他更为向往的审美境界。总之,如叶朗所言,“魏禧关于壮美和优美的论述,特别是他对于壮美和优美所引起的不同的美感心理的分析,是很有价值的”。他的壮美观关注到了壮美与优美的不同,比西方美学对崇高与优美引发的美感心理分析早了一个世纪,既总结了审美客体在文与质方面的特征,也涵盖了主体的审美感受:惊惧、恐怖与振奋、喜悦的交叠递进,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对“壮美”这一重要美学范畴的可贵探索。
虽然有学者指出,魏禧的文艺美学思想“在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清初的文风与文论水准”。但遗憾的是,迄今在对魏禧美学思想的探讨中,少有专文提及其对壮美的创新之解。在积极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当下,这笔宝贵的文艺遗产却在历史的长河中面临湮没,在新时代文艺理论自主创新中受到忽略。对魏禧壮美观的发掘恰恰可以为美学界、文艺理论界提供立足民族文化,借鉴西方理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良好契机。这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加以努力:首先探究魏禧壮美观之根源,重访民族历史、地理文化语境,凸显本土美学发展的独特性;其次以西方对应的美学范畴为镜,厘清国内魏禧壮美观与西方崇高论对比研究中的偏差,在跨文化美学的视野中,更加清晰准确地认识魏禧壮美观与西方伯克、康德代表的崇高感之差异;最后考察其当下的状况,以西方崇高感之当代发展脉络为鉴,吸收魏禧壮美观的思想遗产,从而为构建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作出新探索。
一、形塑魏禧壮美观的历史与文化语境
魏禧之所以会形成极具个性的壮美观,其背后交织着中国地理、历史和文化的复杂因素。首先,魏禧成年后所处独特的地理环境给他的人生境界、文艺思想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魏禧青年时遭逢国变,遂和父兄一起迁至金精山翠微峰隐居。《魏禧年谱》中记载其“年二十一,明亡,遂弃诸生,从父隐居,与兄魏际瑞、弟魏礼及李腾蛟、彭士望、林时益、邱维屏、曾灿、彭任结庐金精翠微峰,砥砺人格,研讨经学,切磋诗文”。其所居翠微峰,奇拔千尺,这无疑加深魏禧对雄浑大自然的体认,开阔其胸襟。魏禧曾作《翠微峰记》,描述“此峰迤逦竞里,旁无援辅,自下仰之,如孤剑削空,从天而仆”。与友人相会时,居所周围“壑风千尺,倒上吹墙屋,汹汹有声,雨雪杂下”。主动选择这样险峻的地方,即可见其对地理环境的偏好,期望环境磨砺自身人格。他认为,“文章视人好尚,与风土所渐被。古之能文者,多游历山川名都大邑,以补风土之不足,而变化其天质。”年近四十时,魏禧担心自己长期偏居一地,固步自封,眼界变得狭窄,特意出游,足迹遍布江淮吴越。魏禧本人十分看重自然环境对个人性情的熏陶作用及对阅历、眼界和创作风格的潜移默化作用,进而影响他的文风。这种与自然贴近的观念反映在其对壮美的讨论中,则是其从自然山水着手,以自身对自然险峻骇人、变幻莫测的亲身见证为例来说明壮美之来源和主体的感知、心理转变。
魏禧把个体的修养和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的认识源于中国儒家的养气说与天人合一说。养气说的首创者是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嫌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叶朗则把它理解为纯粹精神性力量,“是一种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主观心理状态”。气具有物质性,否则何谈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它是生理之气,故谭嗣同说:“夫浩然之气,非有异气,即鼻息出入之气,理气此气,血气亦此气,圣贤庸众皆此气。”它被道德理义所规导充实,则变成精神性力量,是感性与道德的交融,作为精神和物质的复合体存在。它也存在于自然之中,如魏禧所说,“地悬于天中,万物毕载,然上下无所附,终古而不坠,所以举之者,气也。”孟子的养气说把主体的道德人格、精神超越与大自然以及整个宇宙联系统一起来,可以与天地宇宙相交通,而达到天人同一。孟子养气说的实质是强调道德主体的壮美,关注的是道德主体与宇宙万物的呼应,路径是由人而天,但却忽略了也可以由天而人,人并不仅仅是因为道德主体性而与天齐,也可以因为与天交融而扩大自己的道德主体。身内身外之气不仅仅是呼应的关系,而且是能够融会贯通,实现彼此生命力量的壮大合一。正如文天祥在《正气歌》所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魏禧对壮美的激越振奋式审美心态有着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乾卦》)的底色,其壮美观是一种主客先分离而后合一产生的大我对小我的本体的超越,不仅是对“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发扬,亦是对儒家“参天地”“赞化育”思想的继承,具有浓厚的天人合一特质。《中庸》里谈到至诚“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达到了至诚的境界,则可以辅助天地化育万物,与天地合一。《易传》进一步论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乾·文言》)。人积极进取,才能遵循天道,与天地合一。
不过早期儒学的天,是赋予了人格的天,是有道德品质的,所以人与天同。但到了宋明道学,受老庄影响,天的含义中也包含了自然性。而魏禧在《文漱叙》描写道:“水生于天而流于地,风发于地而行于天。生于天而流于地者,阳下济而阴受之也。发于地而行于天者,阴上升而阳蓄之也。”其中的天明显是指自然的天,承袭了宋理学思想,有更多道家的成分,不过天人合一的思想根本是不变的。魏禧深受儒家思想熏染,把天人合一的思想运用到审美体验和艺术创作中。隐居生活既使他可以潜心研习儒家经典,又使他有充沛精力游览名山大川,养胸中沛然正气,感悟天人合一的思想。所以魏禧认为惊涛巨浪壮人志气,使观者发豪士之气,这其中既有养气说蕴含的个体浩然之气至刚至大的昂扬雄健之感,又有天人同感、圆融壮阔之意。
魏禧壮美观中对主体超越性的激赏根植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土壤,也是对明清朝代更迭之际个体的责任做出的回应。朝代更迭给魏禧人生带去巨大的变故,促使他放弃了生员身份,转而以布衣之士立身于世。据记载:甲申以后,魏禧“故善病,谢弃诸生服,隐居山中,岁惟清明祭祀一入城而已。因屏去时艺,专古学,教授弟子”。魏禧在崇祯十一年(1638)就已取得县学生员资格。顺治四年(1647),地方官员召集诸生重新入学,参加考试。为保全气节,魏禧主动放弃了通过考试入仕的机会,选择教书著文。这种选择使他不必趋附时文,反而得以专研古文。曾灿说:魏禧“乃甲申、乙酉来,自以病放废山中,尽弃去其时文,为古文辞,而其所自修立与设施之方皆不获用”。隐居山林,远离科举体制,他得以保留真性情,崇尚洒脱不拘的个性,喜畅所欲言,曾在《内篇二集自叙》中自言其在山中,“以养谷气,遂得优游放论,快生平之所欲言”。同时弃诸生的决定让他不习八股,专古文,思想相对自由,也更为推崇文章情感表达的慷慨激昂。他说:“古人法度犹工师规矩,不可叛也。而兴会所至,感慨悲愤愉乐之激发,得意疾书,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时也,虽劝以爵禄不能移,惧以斧钺不肯止,又安有左氏、司马迁、韩、柳、欧阳、苏在其意中哉?”因此雄浑磅礴、气势充沛、发人之所未发的道德文章便成了壮美感的来源之一。
不入仕,深受儒家教诲的魏禧选择了立言以传世。他把立言、立功、立德视为一体:“文之至者,当如稻粱可以食天下之饥,布帛可以衣天下之寒,下为来学所禀承,上为兴王所取法,则一立言之间,而德与功已具。”郭英德认为,“从顺治四年起,魏禧已经明确地想要以既有‘意识议论’、又富‘超逸独绝’的‘古文’,‘足与古人并立’而且‘传后世’,并自认为‘其精神所到,当有一段不可磨灭之处’。这正是一种‘立言’以‘不朽’的生命意识,当然也是一种‘立言’以‘不朽’的人生选择。” 他的立言选择依然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虽为布衣之士,但不随波逐流,坚守君子的自强不息,以一种不放弃气节的形式实现主体的价值。魏禧在《郑礼部集序》中写道:“夫君子立言,必取其关于世道民生,虽伏处岩穴,犹将任天下之责,而况其为士大夫者乎?” 由此可见,他虽然拒绝入仕,但不忘身为布衣之责,胸怀天下事,渴望用文章来匡扶正义,反映世道民生。这也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他的壮美观中会涉及文章的道德内容。
二、再谈魏禧壮美观与西方崇高论的异同
鉴于“崇高”是西方美学中类似于中国美学中“壮美”的重要审美范畴,有国内学者以魏禧的壮美观为主要参照,将两者进行比较辨析,但结论多大同小异。在论述壮美与崇高的相似和区别时,国内代表性的观点是:壮美与崇高的审美实质都在揭示人类生命的超越性;西方的崇高感包含恐惧、压抑的痛感,而壮美“属于和谐的审美形态”,“壮美感不包含否定性的情感体验,没有崇高体验的由痛感向快感的转换过程而是一种较纯粹的积极向上的快感体验”。
以上观点,笔者认为值得商榷。首先,魏禧对壮美体验的论述充满了气壮山河之势,“惊而快之,发豪士之气,有鞭笞四海之心”,确实体现了人作为宇宙生灵的主体能动性和对生命局限性的超越,但把中西之同归纳为对人类生命超越性的体现则泛化、简单化了西方的“崇高”这一概念,忽视了其作为核心美学概念的生发性、建构性的特点。实际上这一概念随着时代的不同被不断地重新阐释,与时代精神、社会现实紧密相关。从古希腊的朗吉努斯开始,直至当代的利奥塔,西方崇高论并没有统一的观点,而是各有针对,后人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地批判、超越。
以西方崇高论奠基人物、18世纪的伯克为例,他的崇高论展现的不是康德所称颂的主体的超越性,而是主体的被压制和臣服性。在伯克眼中,绝大部分崇高事物是力量的变体,“力量无可置疑是崇高的一个首要来源”。绝对的力量带给人的是占据情感反应主导地位的惊惧。因此,伯克崇高感的首要成分是超出人类感知能力之物带来的恐惧感。他说,“凡是能够以某种方式激发我们的痛苦和危险观念的东西。也就是说,那些以某种表现令人恐惧的,或者那些与恐怖的事物相关的,又或者以类似恐怖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事物,都是崇高的来源;换言之,崇高来源于心灵所能感知到的最强烈情感……如果危险或者痛苦太过迫近我们,那它就不能给我们任何愉悦,而只是恐惧;但是如果保持一定的距离,再加上一些变化,它们或许就会令人愉悦,这正是我们日常生活所经历过的。” 伯克对力量的崇拜、对崇高引发的恐惧的强调招致了后世理论家的批驳。伊格尔顿就曾批评伯克的崇高和优美概念都为维护巩固旧有秩序服务,“优美以软性手法建构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愿景,满足共同体建构的身份认同。但仅有优美,无法培养对法与权力的敬畏感。为此,伯克调入崇高论来赋予它恐怖的威慑感。”
启蒙时代的康德抛弃了伯克基于感官的路径,不再强调崇高带来的否定性情绪,转而宣扬崇高“只针对理性的理念”,带有崇高特征的客体激发起“人的内在性的崇高”。高扬着理性的旗帜,康德声称:“我们作为自然的存在物看来在物理上是无能为力的,但却同时也揭示了一种能力,能把我们评价为独立于自然界的,并揭示了一种胜过自然界的优越性。”
仅从伯克突出主体受威慑感的崇高美学到康德弘扬主体优越性的崇高美学,便可呈现出西方崇高论的复杂多元。因此,从跨文化角度探讨本土美学思想时,需要注意观点的流动性,注意明确具体的比较对象。唯有在对比魏禧代表的壮美观和康德代表的崇高论时,我们才可以说两者都展现了主体超越性。
其次,虽然魏禧的壮美和康德的崇高都指向了对人类主体超越性的肯定,但超越的根源不同。康德的崇高论弘扬了主体的超越性,但是凭借的是理性,而魏禧壮美观展现的超越来源于自然的元气内化为个体本身的真气。无论是魏禧的自述“发豪士之气,有鞭笞四海之心”,“揽其奇险雄莽之状,以自壮其志气”,还是他对司马迁的评价“纵游江南沅湘彭蠡之汇,故其文奇恣荡轶,得南界江海烟云草木之气为多也”,都证实了这一点。魏禧赞赏的是从自然造化中汲取天地之气,以化为内在的浩然正气,从而实现气壮山河的豪迈之情。也正是因为体内志气受山川之气激荡而来,两者体现了一种互通融合性。魏禧的壮美感的确体现出一种积极振奋的精神和天人合一的雄浑境界。
魏禧的壮美观不仅涉及自然对象,也包含了艺术作品,这一点和伯克的崇高感所涉及对象是一致的。魏禧在评论同时代文章大家侯朝宗时不无批评:“吾闻朝宗高气雄辩,凌厉一世人,独与王谷深相引重。朝宗之人与文则甚相似,予每读朝宗文,如当勍敌,惊心动色,目睛不及瞬。其后细求之,疑其本领浅薄,少有当于古立言之义。又是非多,爱憎失情实,而才气奔逸,时有往而不返之处。”文章形式固然重要,但是彰显大义的文章内容才是维持壮美感持久性的基石。因此,在面对艺术作品时,魏禧更注重作品体现的道德气概、大义担当,由此令读者有气壮山河之感。他自己即是这种壮美观的践行者。邓之诚在《清诗纪事初编》中对魏禧的描述是“为文学三苏,喜传节义事,尤善持议论,多人所未发。世以并侯朝宗、汪琬为三家,不唯志节非禧之比,琬笔嫌弱,而朝宗略无渟洄,视禧坚卓不移,气象万千”。他豪迈的文章风骨不仅源自其酣畅淋漓的笔触,更来自充沛振奋的道德情感。但是不是仅凭借内容就能够激发壮美感呢?魏禧的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在《文漱叙》中魏禧并未阐明忠孝节义的内容如何震动山河,但结合他在《论世堂文集叙》的阐述,可以看出内容依然要凭借“气”才得以彰显。“土石至实,气绝而朽壤,则山崩。夫得其气则泯小大,易强弱,禽兽木石可以相为制,而况载道之文乎?”那么什么是“气”呢?魏禧先提出普遍看法:“而世之言气,则惟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穷,动而不止者当之。” 然后又进行自己的辨析:“气之静也,必资于理,理不实则气馁,其动也,挟才以行,才不大则气狭隘,然而才与理者,气之所冯,而不可以言气,才与气为尤近,能知乎才与气者之为异者,则知文矣。”
可见,气是统摄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元素,蕴涵旺盛的生命力和浩荡的气势。而文章之气来源于作者之气,但这气不能等同于个人才气,虽然其发挥需要以才气为基础。创作者的气是个体蓬勃的生命力。徐复观在解释中国文论中的“气”时说:“切就人身而言气,则自《孟子》‘养气’章的‘气’字开始,指的只是一个人的生理地综合作用,或可称之为‘生理地生命力’。若就文学艺术而言气,则指的只是一个人的生理地综合作用所及于作品上的影响。” 他的观点可以看作对魏禧的“气”说的很好注解。魏禧在《论世堂文集叙》文末引苏轼作总结:“理非气不充,事非气不立,文非气不雄,以气发论,真得作者深处。” 归根结底,作者之气灌注于文章,文章也因之有了生气,推动内容得到更好表达,即作者的所思所感才能够更为深刻地影响读者,才最有可能生发壮美感。无论审美客体是自然事物还是艺术作品,在魏禧的壮美观中,对审美主体的超越起核心作用的是气。
“气”作为关键词汇出现在魏禧对壮美的表达中并非偶然。它不仅支撑了魏禧的壮美观,而且被魏禧发展为真气论,成为其文艺思想的核心概念。魏禧将有无“真气”作为作品的衡量标准:“吾尝谓今天下之文最患于无真气,有真气者或无特识高论,又或不合古人之法;合古法者,或拘牵摹拟,不能自变化。是以能者虽多,瑰玮魁杰沈深峻削之文所在而有,求其足自成立,庶几古作者立言之义,则不少概见。”他所说的“真气”类似于前面提到的“气”,高于特识和法度。一味追求法度,文章会拘泥呆板,只注重特识,可能会忽略法度。好的文章,应该是真气总领下的特识和法度的统一。他用真气说来褒扬宜兴隐士任王谷的文章,认为“其人易直淳古,故其文多真气而又深于古人之法”。可见,他的“真气”最终落在了主体的个性、才情。创作主体的真气塑造了作品,这是对中国文论中“文如其人”观点的继承。朱泽宝把魏禧的“真气”说的内涵总结为三层:其一指创作主体应该拥有鲜明个性,其二是鼓励主体“挥洒性情”,其三是倡导多元化的文风。他的观点基本上是令人信服的,特别是第一和第二层涵义较为恰当地点出了魏禧“真气”的要义:个性和性情。
但需要补充的是,真气还体现在主体的品格、气节上。有坚毅品格、坚持气节,才会不拘性情,才敢于挥洒自如,形成有力度的壮美文章。所以,魏禧对文风是有偏好的,并非大力提倡多元化,“其为文主识议,凌厉雄健,不屑屑抚拟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节烈事,则益感慨激昂,摹画淋漓。”凌然于众的雄健之风正是魏禧所追求的。可以说,“真气”论是魏禧“气”论的具体化,展现了从自然的壮美转入艺术之美中,从自然元气到主体生命力再到主体的品性、气概的一步步融会、升华。
反观西方,在康德式崇高中,我们“被扔出了自我感官的局限”,并且抓住了“自己内心的理性的崇高性”,这是一种凭借理性超越自然,确立人类主体性的崇高,反映了西方启蒙时代对理性的高扬。康德认为,虽然在自然的强力面前,人力显得渺小,但是这种强力却会激发人内心的勇气和人的能力,凭借理性,人能够意识到自我作为独立于自然之外的独特存在,因而战胜最初的恐惧感,产生智力或道德上的优越感。所以崇高感的产生媒介是理性,正如他说,“真正的崇高不能包含在任何感性的形式中,而只针对理性的理念:这些理念虽然不可能有与之相适合的任何表现,却正是通过这种可以在感性上表现出来的不适合性而被激发起来、并召唤到内心中来的。”人因为理性而彰显崇高,这在康德的时代成为一种普遍的信念。德国浪漫主义画家弗里德里希创作的《雾海上的漫游者》正是继承这种理念的产物:俯瞰脚下云雾缭绕的崇山峻岭,在大自然的强力面前陷入理性反省的个体作为世界的对立面孤独骄傲地屹立。西方的崇高感有痛苦悲厉的感受,因而更富于生命的强度和力量,而中国的崇高感则具有天人合一特征,强调和谐圆融,缺乏斗争和冲突。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革新发展的命题在当今依然是学术界面临的重要使命。
再者,认为壮美感不包含否定性的情感体验的观点,忽略了不同文化中审美情感的共通性。从经验主义角度出发,面对超出日常感官体验之物,人皆有畏惧惊恐之心,尤其是当生命受到威胁之际。“他(伯克)的崇高美学是建立在感官刺激和生理反应之上的,以个人的、直接的、感觉的经验为基础,却能反映普遍的人类共通感。” 从《文漱叙》中所写“舟中皆无人色……然且登舟之初,风水所遭遽若是,则必不敢解维鼓楫蹈危险以自快”来看,魏禧描述的壮美观和伯克分析的崇高感在生命直观体验中的复杂性上是一致的,两者都体现了对情感的重视,有恐惧、有快感,不过如果知道生命会受到威胁,不会有崇高感。但魏禧的最终点落在了乐,是惧之后的升华,是振奋昂扬之情。而伯克坚守住了怖,并于自保原则中发现了欣喜快慰。魏禧对壮美的审美心理描写其实和康德的描述有共通之处:“后者(崇高的情感)却是一种仅仅间接产生的愉快,因而它是通过对生命力的瞬间阻碍、及紧跟而来的生命力的更为强烈的涌流之感而产生的”。叶朗指出魏禧对壮美的论述表明:“壮美的对象和审美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对抗的关系,使审美主体产生惊怖的情绪,但同时又在审美主体内心激起一种摆脱琐细平庸的境界而上升到更广阔更有作为的境界的豪壮之气,因而感到兴奋。” 所以,魏禧壮美观对审美心理较为全面的认识难能可贵,细致地传达了人类情感的共通性。当代学者在分析其成就时不应该因为他对负面情绪的渲染就加以否认。中国人在面对超出感官把控之物时,难道不会害怕、恐惧?一味否定负面情感的存在会使我们的美学在面对生活中的痛苦、可怖之事时无所适从,进而失声。
综上所述,在跨文化美学的语境中可以发现,魏禧的壮美观从个体的感官、心理体验着手,揭示人类情感共通性的同时,又突出了中国文化系统内对气的推崇,在突破个体的局限性中,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实现超越。
三、反思魏禧壮美观的当下性
对于惊怖的反复提及,魏禧的壮美观表现出相类于伯克的崇高说。它利用经验主义模式,揭示了人类情感的共通性。然终以快意豪气涤荡惊怖,以天地浩然之气充塞主体内在,实现超越式的主客融合,展现了中国地理、历史和文化的底色。可以说,无论是对审美主体心理和感官反应的描述,还是对审美对象的分析,魏禧的壮美观比之伯克的崇高论都毫不逊色。
但是,文艺理论的活力取决于其当下性,即唯有不断发展、创新,才能够与时俱进,解决时代问题。就当下性而言,西方的崇高论给予了中国壮美观以很好的启迪。伯克的崇高论在不同的时代被包括康德、席勒、利奥塔、伊格尔顿、齐泽克等在内的一系列思想家不断地改写,形成了不断被构建的西方崇高美学。而在此过程中,推动思想家、美学家们重新阐释崇高概念的原因在于与当下社会如何发生关联。例如,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为了分析当代先锋艺术,反思了康德崇高论中的唯理主义,质疑其排除异质的宏大叙事,重新回归了伯克崇高美学遵循的感官路径。与伯克不同的是,利奥塔的焦点并不在崇高客体引发的恐怖与屈服。针对先锋艺术在受资本和科技操控的后现代社会的功用问题,他提出了后现代崇高的颠覆性。利奥塔的美学中,崇高、非人和事件三个概念是缠绕联动的。“非人”概念并非利奥塔首创,但是他根据时代的特征发展了这个概念的内涵。他用“非人”概念来描述工具理性主义塑造下,后现代社会的人缺乏生命力,沦为科学技术控制对象的异化状态。“走向前面的机器后面拖着人性尾巴,为的是将人性非人化”,“人类不再具有让人惊讶或惊奇的能力,他/她被削减为仅仅只是资本主义(……)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但利奥塔也认为人类存在另外一种非人状态:“思想被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客人纠缠而感到痛苦,这个客人让思想不安、亢奋,同时促使它思考”,这种非人是对第一种非人的抵抗。他强调以极简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先锋艺术通过唤起崇高感,激发了这种反异化的非人性,实质上是对机器化的非人状态的撼动。
伯克在谈及崇高感的来源时,其中一项是客体具有模糊不清、难以辨认的特征。如果艺术作品让主体难以理解,使其产生模糊、不确定感,进而感到焦虑、恐惧,这是一种由“知性匮乏”引发的崇高感。利奥塔利用了伯克这一观点,并看到了其革命性。他以后现代先锋画家纽曼为例,指出纽曼的画不再企图再现什么,画面中纯粹的大幅色块令观者不知所措,旧有的经验、感知模式已无法应对,“面对抽象主义的极简性,我们的体验和伯克式崇高论中‘如临深渊’的体验很相似。人们在认知受阻时,积极调动感官和智性,振奋了被平庸生活磨得麻木的灵魂”。“知性匮乏”带来的崇高感在激发挑战性的非人状态时,也指向了事件的发生:“这种让我们感到面对一种不确定事物的崇高的体验,就是这样一种匮乏的状态,惊恐与愉快矛盾地混合在一起。纽曼的作品拒绝了我们熟悉的事物,在其中引入了休止,干扰了思维的顺畅流动,因而让一种吸收式(甚至侵吞式的)理解产生了偏移,因而引发了正在发生什么的问题,以及发生了什么的问题。”在观看的瞬间,观者感到不安、困扰,他意识到事件发生了,却无法说明发生了什么,但事件需要回应。也正因为如此,事件的发生能够激发亲历者打破旧的范式,尝试新思维、新话语,而这也回到了利奥塔的初衷,即对非人的挑战。“对于利奥塔,资本主义的思想结构‘将人类主体(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经验及经验的独特性溶解进盈利的算计中’,而艺术与事件的关系正是要挑战这样的结构。”让人不再臣服于工具理性,以效益来计算一切,找回自己不带预设和目的的感受能力。最终,崇高感、非人、事件一起打开了改变现实之路。利奥塔的贡献在于,通过借鉴和反思伯克和康德关于崇高的论述,创造性地和贴近时代的新的哲学、美学概念发生关联,他充分利用了传统美学概念来阐释当代的文学艺术现象,并发掘其背后的挑战传统的力量。
以西方崇高概念的演进为观照不难发现,在魏禧的壮美观里并未出现类似的生发性和当下性,其中一些重要的论述反而被忽略了。清代的姚鼐和刘熙载都谈到了壮美,但是他们的讨论均以艺术作品为主,并未关注审美主体的心理。例如,刘熙载对艺术风格的论述:“书要兼备阴阳二气。大凡沉着屈郁,阴也;奇拔豪达,阳也。”(《书概》)他注重的是壮美和优美的和谐统一,两者不可偏颇:“书,阴阳刚柔不可偏陂,大抵以合于《虞书》九德为尚。”(《书概》)“孙过庭草书,在唐为善宗晋法。其所书《书谱》,用笔破而愈完,纷而愈治,飘逸愈沉著,婀娜愈刚健。”(《书概》)“文之快者每不沉,沉者每不快,《国策》乃沉而快。文之隽者每不雄,雄者每不隽,《国策》乃雄而隽。”(《文概》)“词,淡语要有味,壮语要有韵,秀语要有骨。”(《词曲概》)在他看来,无论书法、词曲、文章,都遵循相同的审美准则,皆以雄浑俊逸的统一为典范。可见,在刘熙载的理论体系中,壮美已经丧失了作为单独的审美范畴的重要性。王国维虽然重新开始详细区分壮美和优美,而且与魏禧相仿,对审美的主客体都有分析,但他受了康德和叔本华的影响,论述集中在壮美客体和人的冲突。“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为独立之作用。” 壮美置人于危险境地,则主体的生活意志受到打击,这和叔本华的哲学隐隐相合。而“艺术之美使人超然于利害之外,忘物我之关系”。主体在面对引发壮美感的艺术作品时,其审美快感来源于超脱于利害关系之外的审美观照,这无疑打上了康德美学的烙印。由此可见,王国维的壮美观是西体中用的产物,并没有很好地发扬魏禧壮美观中有价值的方面。更令人遗憾的是,在王国维之后,除了在一些美学汇编中被概括提及外,国内美学界并未将魏禧的壮美观加以发扬,如何在前人基础上针对新的文化语境对壮美这一中国特有的美学范畴加以阐发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通过比较崇高论和壮美说的当下状况不难发现,对美学的构建需要良好的继承传统,需要不同时代的美学家、思想家和批评家结合时代的社会、文艺新问题、新现象,对传统美学中的核心范畴加以改造,同时与当代哲学、美学概念相联系,从而形成系统的阐释并开掘传统美学思想的当下性,保持其生命力。
在审视自身文化传统时,需要不断地指涉、映照他者。从跨文化美学视域下对魏禧壮美观的重新辨析和其当下性反思中可见,在中国的传统美学中存在与西方比肩、兼具文化共通性和独特性的思想结晶,是具体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语境的产物,但是它们与当下现实的关联性的缺失,导致了未能充分参与中国当代美学的建构,需要在重塑中激发新的生命力。以西方为镜,这就在跨文化的视域里重新审视传统美学思想,厘清其与西方美学的异同,发现其特质,同时借鉴西方经验,寻求其古为今用途径,使中国的美学思想置于不断地阐释、批判、重构之下,与本土的现实问题相呼应,与当下发生关联。唯此,才能实现本土美学的继承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的结合,才能构建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的自主性。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姜子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