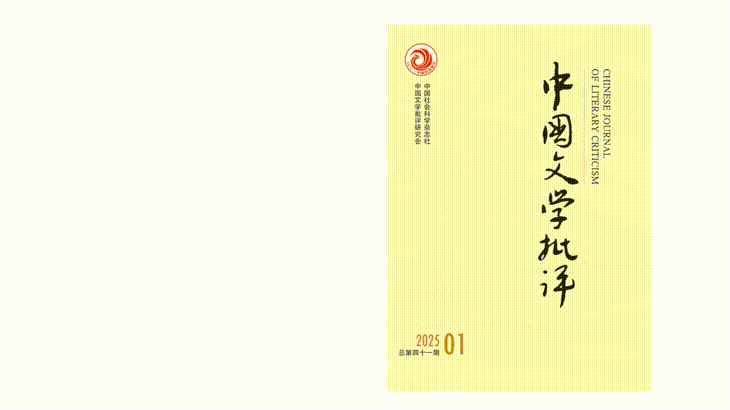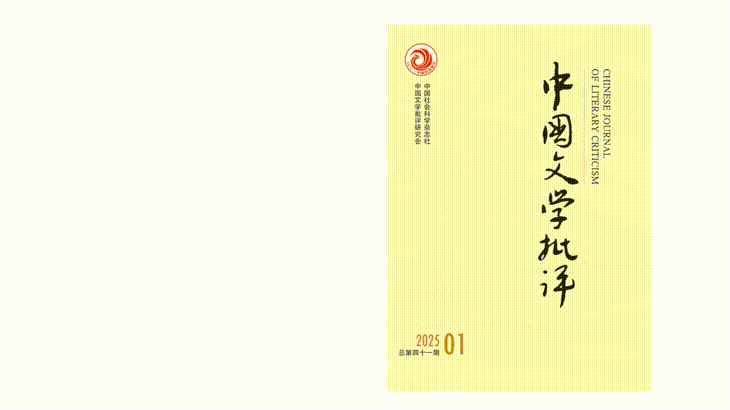
詹姆斯·伍德论及福楼拜时曾说:好的小说家,“能保持一种不多情的沉稳,如男仆一样知道何时从多余的评论中抽身而退”——假如我早点读到这段话,也许,早在近二十年前,我的小说创作生涯仍然能持续下去:那时的我,在写完两部长篇小说以后,突然间对自己是否还能够完整地讲完一个故事充满了怀疑。对,我一边将自己所置身的时代愣生生拽进古典戏曲式的装置之中,将身边的人们视作了许仙、白素贞和张生、崔莺莺去书写,一边又能深切地感受到,当时的生活绝非只是一座戏台,它们早已和过去的生活发生了深深的割裂,我其实是在一种不沉稳的多情中左右为难。如果我是诚实的,我就应当承认,世界早已不是那座戏台,相反,人们正在冲破戏台,走向更宽广、暧昧也更加平常的世界。像当初的福楼拜写下的那些人物一样,他们只是作者的替身,是作者渗透到小说里的侦查员,又“无可奈何地被各种印象淹没”。就此意义上说,我所写下的许仙、白素贞和张生、崔莺莺,也许只是我对这个世界多余的评论。
是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未能听见那些真正的“众声”,写作也由此陷入漫长的停滞之中,只好作为一个失败的编剧去这世上游荡,却意外地靠近了一张张我从未认识过的脸孔:戈壁滩上的修路工、宵夜摊上卖唱的前黄梅戏演员、失明之后用想象给自己虚构了一座崭新人世的盲人,等等等等。在他们身上,有人苦修不止,有人则梦中做梦,用虚构出的崭新人世收纳了自己;有人在追问和审判着自己,也有人却在不停地原谅着自己和世界。看哪,他们其实是多么像福楼拜、契诃夫乃至卡夫卡写下的那些人啊!而我,尽管早已被他们唤醒,甚至想在他们的激发之中重新写下一部小说,但是我也知道,那些众声,仍在被我强制性的审美与想象之中,就像我对《猛虎下山》的起心动念之时——那时候,我在剧组里,听一个场工兄弟说起了他的遭遇:当初,为了不让自己下岗,为了让厂里的改制小组吃上老虎肉,他曾经孤身犯险,一个人在工厂背后的深山老林里转悠了一个多月。这个故事,在十多年里,一直折磨着我,我反复地去写,又反复地承认自己终究写不出来,现在想起来,不过是因为,在这些废弃的书写里,充满了我自己的声音,但就是没有别人的声音。
有一年的三月初三,我曾经在黄河岸边目睹过一场盲人的歌会:当持续了一整天的歌会行将结束,盲人们陆续踏上自己的回返之途,漫长的挤满过盲人的河滩重新变得空荡荡,像是一场约定,最后一阵歌声漫天响了起来。但是,盲人们唱的却并不是同一首歌,唱信天游的,唱花儿的,唱山曲的,各自唱起的都是自己会唱的曲调。尽管如此,当那些歌声汇聚在一起,某种盛大与慈悲之感,还是凭空降临在了满目河山里:说它们慈悲,是因为那些各自响起的歌声并未被对方淹没,仍能被我一一辨认,就像那些盲人在这世上的辗转与指望,也仍能透过这些歌声被我一一辨认出来。随后的许多年里,我跟随着不同的剧组,踏足过不同省份里的那些早已废弃的三线工厂。有一回,在一片高耸而破败的车间里,我看见过在此打洞的狐狸们,到了此时,杜甫的声音便幽幽响了起来:“四山多风溪水急,寒雨飒飒枯树湿。黄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狐立。”还有一回,当我在贵州的一家三线炼钢厂里,穿过了半人高的荒草,来到当年的一号高炉之下,看见散落了一地的钢钎和夹钳。必须承认,在我的耳边,霎时便出现了许多早已消失的声音:钢水涌动的声音,钢块被敲击的声音,甚至还有从工厂背后的山间传来的隐隐的虎啸声,这些声音来自早已过去的年代。但是我也知道,它们可能来自一本还未被我写出来的名叫《猛虎下山》的小说之中。
我也在《聊斋志异》和更多的志怪小说里听到了那么多“出于幻域,顿入人间”的声音——聂小倩生怕宁采臣不记得自己的葬处,一再对其叮咛:“但记白杨之上,有乌巢者是也。”还有王六郎,对着远来看望自己的许姓兄弟说:“远劳顾问,喜泪交并。但任微职,不便会面,咫尺河山,甚怆于怀。居人薄有所赠,聊酬夙好。归如有期,尚当走送。”许姓兄弟便回答他:“六郎珍重!勿劳远涉。君心仁爱,自能造福一方,无庸故人嘱也。”这些声音,如鲁迅先生所言:“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实际上,伴随着多年的行走,在莽荡山河的各处皱褶和犄角里,我都听见过类似的声音:那些荒废工厂里不断响起的狗吠声,听上去就像狼嚎,莫不是,在对早已抛弃它们的主人日复一日的眺望中,它们已经异变成了一只只的狼?还有那些工厂背后的群山里,一阵阵隐约响起的低吼,莫不是,我在剧组里碰到的场工兄弟其实一直未曾下山,而是在群山与密林里化身为虎了?正是在这样的狂想中,那部名叫《猛虎下山》的小说在我的想象中一点点显露出了清晰的模样。再看《聊斋志异》之时,它和我所经受的现实已经互相敞开:时至今日,蒲松龄的道路对于如何言说我们的今日生活依然是有效的,而广阔的现实在古典传统的映照之下,也被激发出了之前一直被我想象的崭新的书写可能。
必须承认,在写作《猛虎下山》的日子里,犹如神启一般,我也似乎异变为了小说里的那只老虎,听觉异常灵敏,就连鸟雀们啄食草籽的声音,狐狸们出洞的声音,积雪压断树枝的声音,全都被我一一听得分明。但是,最令我难以忘怀的,还是写作时不停在我耳边莫名响起的一阵阵急促的鼓点声,这鼓点声,是被我在多年的辗转与浮沉中所遇到的那些无名氏们敲响的。在鼓点声中,世界重新变作了一座戏台。由此,我一边写,一边看见一代代的人,可爱人,可怜人,纷纷被催促,撩起了戏袍,再登上戏台,投入到无尽的热情与徒劳之中。有时候,我和他们一样剑拔弩张;有时候,我又和他们一起痛断肝肠。到了这时候,我才真正确信,那些在我的生活与体验中消失了太久的“众声”,它们回来了,并且要求我忠诚。就像当初,我在刚刚写作散文之时,当我跟随着剧组来到那些从未踏足过的地方:贫瘠的山丘,荒凉的戈壁,简陋的工棚,冷风呼啸的小旅馆,等等等等。在写作停止了许多年以后,面对它们,我突然萌发了不可抑制的写作愿望,原因无非是,我只想用写下它们,来忠诚于自己在彼时彼刻所感受到的艰险。说不定,我忠诚于了自己,也就是忠诚于了更加广大的河山和无名氏。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