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比较西方社会学的“情境论”“交换论”与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点的“絜矩论”,能够透视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解释的微妙差异。“絜矩论”的基本观点是:一个行动者理解和回应另一个行动者的关键,在内而不在外、在己而不在人、在心而不在物;外力的影响固然不可忽视,但唯有心有所感、心有所动,才更易于推己及人,实现感通和引发后续行动。“絜矩论”以儒家仁义观为思想基础,可用于解释社会行动的情感动因和情理逻辑。重返社会学的中西文化比较视野,挖掘和凝练中国思想传统中体现中国人行动取向和精神气质的概念,有助于更适切地认识中国社会和把握中国人的行动伦理。
关键词:絜矩论;情境论;交换论;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作者王建民,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教授(北京1000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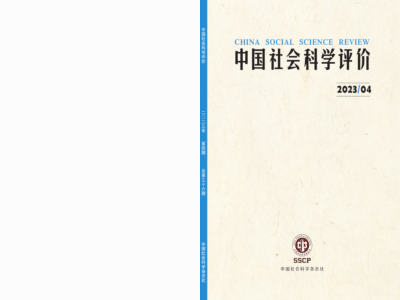
1895年3月4日至9日,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原强》一文,引介了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如果以此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学的起点,那么这门学问在中国已有近130年的历史。彼时,严复译介和阐释西学,并以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探究中国社会的问题及出路,这也是当时处在历史大变局和古今中西交汇处的众多中国学人的共同特点。而后,一些社会学家提出或阐发的概念,往往带有中西社会与文化比较的色彩,如潘光旦的“中和位育”、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梁漱溟的“伦理本位”。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学的中西文化比较视野渐趋淡化,而流行的是以西方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认识中国社会。尽管这种知识的移译和借用在现代中国学术的建立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如对一些概念和理论的内涵缺少反思,甚至削足适履,以牺牲现实的丰富性和经验的完整性为代价来佐证舶来概念和理论的适用性。
时至今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大势,但这不意味着学术上的“闭关锁国”,相反,恰恰需要在中外历史文化的宏观背景下审视和反思我们自身的传统,其路径之一是以能够反映中国人行动取向和精神气质的概念比照西方的概念,既尝试提炼具有现代社会科学特点的概念工具,又寻求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生命体验更适切的理解。中国社会学重建40余年来,在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如对“关系”“人情”“面子”等的研究,也取得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这些概念揭示了中国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一些重要特征,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不过,对这些概念的使用却往往是以西方社会和西方社会学理论为基质的,如以“普遍主义”的视角审视“特殊主义”的关系与人情,甚至将后者视为公共规则的对立面而加以批判。
从表面上看,以西方社会和西方社会学理论为基质审视“关系”“人情”等现象,体现了中西社会与文化比较的视野,但实际上,这种比较或多或少带有“西方现代化范式”的特点,即将中国视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将“关系”“人情”等视为与“现代社会”相龃龉的“传统社会”的特征,与其说这是一种双向的“比较”,不如说是单向的“度量”。如此一来,一方面,“关系”的往来往往被简化为工具性的“社会交换”,人情的情境化特征往往被简化为“情境定义”。另一方面,“关系”“人情”等概念背后的传统思想资源往往少有问津,因而对其丰富内涵的挖掘便也相对较少。基于这一状况,本文拟以和“关系”“人情”密切相关的两个故事为例,尝试对西方社会学的情境定义理论(以下简称“情境论”)、社会交换理论(以下简称“交换论”)与具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点的“絜矩论”进行初步比较,以辨识不同概念和理论的微妙差异。
一、“情境论”与“絜矩论”
孙立平和郭于华在论文《“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中谈到一个案例: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农,分到的交粮任务是50斤花生,他已经交了35斤,但拒绝交剩下的15斤,镇干部S将交纳订购粮的种种道理反复讲述后,老人还是坚持不交,镇干部甚是无奈。不过,老农最后交了那15斤花生。使老农转变态度的关键点是,镇干部S说:“这样吧,您也别把我们当成收订购粮的,您干脆就当我们是要饭的,就当我们现在是向您要15斤花生,您说您能不给吗?”
对于老农转变态度的原因,孙立平和郭于华运用了西方社会学中的情境定义概念和常人方法学的相关观点进行分析。他们指出,镇干部S在和老农的互动中构造出三个情境:一是最表面的乞讨者与被乞讨者的关系(“您干脆就当我们是要饭的”);二是在虚拟关系中力图表现的恩赐性的平等关系(镇干部S自降身份为“要饭的”,拉近了和老农的距离);三是真实存在的征收者与被征收者的关系(有收粮任务的镇干部S和有交粮任务的老农)。“尊贵的”官员已将自己比喻为乞讨者,将征收的对象比喻为施舍者,等于是给足了老农面子。在这种情况下,便对老人形成一种情与理的逼迫:在你不占理的情况下给了你很大的面子,如果你不接受这个面子,不用交纳花生的方式还给对方面子,就会使自己陷于不通情理的地步,就会失去人们的同情。这种解释,我们姑且称为“情境论”的解释。
作者将镇干部S自降身份、把自己比作乞丐,看作基层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指出了镇干部S行使权力的“高明”之处,这是在“权力技术”的意义上讲的。问题是,这种所谓的“软技术”为什么会发挥作用?显然,老农一开始就明白镇干部S的来意,也知道他说的“当我们是要饭的”只是一种说辞而已,其用意还是为了完成收订购粮的任务。老农的态度发生变化,不是理智的作用,而是情感的作用。现实的镇干部S和老农的关系带有博弈色彩——催交与不交,而镇干部S自比乞丐的策略,是使征收者和被征收者的关系“还原”为更朴素的、容易引发情感体验的乞讨者和施舍者的关系。“要饭”是为了活命,是走投无路时的无奈之举,通常情况下人们都会对“要饭的”救济一二,起码会产生一丝同情,这种同情往往是自然而然的内心反应,而不是理智考量的结果。
老农态度转变的关键在于:“外在的”镇干部S的言辞和态度激发了老农“内在的”情感体验,老农心有所感、心有所动,进而改变了对待“外在的”镇干部S的态度。我们不妨做一个合理的想象:当镇干部S说出自比为“要饭的”那句话时,一定表现出非常“为难”甚至“可怜”的表情和语气,这使老农的注意力由交订购粮的“外在任务”转向“内在感受”。真正让老农动心的不是作为“施舍者”的难为情,而是作为“乞讨者”的可怜处境;不是“我”感到如果“你”是乞丐“你”多么可怜,而是如果“我”是乞丐“我”会多么可怜。虽然老农本人未必有过“乞讨”的经历,但一定经历过生活中的种种困难,有过类似的困苦体验。当老农的内心感受被“外在的”力量激发后,才能进一步由内向外“推”出去,考虑并在意镇干部S的处境和难处。这个过程,就是以己心“比”人心的过程,所谓“将心比心”。这一解释,我们姑且称为“絜矩论”的解释。所谓“絜矩”,出自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的“絜矩之道”,简单地说,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地忖度和处理人伦关系的方法。
在前面的案例中,镇干部S的“高明”之处是,不用高高在上的姿态施压,而是“退一步”“说软话”,在单纯地晓之以理(交粮是完成国家的任务)不起作用时,动之以情(以弱者姿态相求)。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往往不意味着退缩和怯懦,而是暂时将“理”搁置一旁,使对方看到自己的低姿态,感受到自己的委屈和不易,使“理”有了“情”的基础,甚至情理交融,进而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由此来看,镇干部S自降身份为乞讨者的那句话,与其说是情与理的“逼迫”,不如说是情与感的“激发”。以“权力运作”的观点看,镇干部S自降身份是一种“权力技术”,即在情理上“逼迫”老农,进而“换取”老农交粮的结果。但如果从“絜矩”的角度看,镇干部S把自己比作乞丐,是真实而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工作中的难处,以和老农相感通。和“以官压人”的姿态比,这是一种较为柔和的工作方式,而若以“权力技术”来理解,实际上是将镇干部S和老农看作对立的关系,这种理解的背后,或多或少隐含着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预设。
根据威廉·托马斯的情境定义(definition of situation)概念(也被称为“托马斯定理”),“如果认定某些情形为真,结果它们就会成为真的”。通俗地说,个人对社会情境的解释不同,其行动的方向和表现便会不同。据此看,老农转变态度是因为他对镇干部S和双方关系的“定义”发生了变化,这似乎能说得通。不过,“情境论”主要指向“外在的”情境,而难以解释老农内心的变化。其中的道理在于,“将心比心”的关键不是一个主体直接“向外”去理解另一个主体(或环境),而是主体萌发自我感受(心动),先有“心之所感”,才能由己心而推及人心。往往是和“我”有关、令“我”心有所感(而不是用外在规范说教)的人或事,“我”才更有内在动力作出积极的回应,否则,事不关己,便可能“高高挂起”。
如果根据儒家思想解读的话,案例中老农“心”动,既是“仁者,人也”,对他人产生了恻隐之心,也体现了“义者,宜也”,对合适与否进行了拿捏掂量。“仁”“义”皆与心之所感有关,而不是对抽象的外在“规范”的认知。老农对外在制度规范的要求一清二楚,否则最初也不会交那35斤花生,但交不交剩下的15斤花生,其实与镇干部S的态度和行为有关,“时机”没到,双方僵持不下,老农没动心,就会坚持“不交”的态度。“仁心”的生发或“流溢”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或路径,而是和对象是谁以及双方的情感到了“哪一步”有关,同样的人,同样的事,沟通的方式和“火候”不同,效果就会有差异。镇干部S和老农已经就交粮的事打了几次交道,直到老农“心动”,态度才最终转变。
二、“絜矩论”与“交换论”
前文的例子,似乎也可以用社会交换论来解释:镇干部S以屈尊之态“换”了老农补交15斤花生,或者说,老农用补交15斤花生“换”了镇干部给的面子。乍一看,这似乎很有道理,但问题是,“姿态”和“花生”的“分量”如何度量呢?“花生”和“面子”属不同的事物,二者“交换”的尺度何在呢?其实,镇干部和老农的关系,不单是收粮者和交粮者的关系,二者还共享一套伦理文化。实际上,这个例子表明,如果背离了共享的伦理文化而只以表面的权力关系行事,常常是难以奏效的。
这里尝试以小说《三国演义》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的故事为例,说明“絜矩论”和“交换论”的一些微妙差异。这个故事说的是,曹操为统一全国南下征战,刘备兵败长坂坡,派诸葛亮前往东吴,拟与孙权结盟、联合抗曹。在东吴大都督周瑜的指挥下,吴军以火攻的方式击败曹操。曹操败走华容道,关羽奉军师诸葛亮的将令前去拦截,并在行前立下了军令状。在华容道,曹操以弱者之态、君子之言相求,希望关羽能顾念往日恩情,放自己一条生路。最终,关羽冒着被军法处死的危险,放走了曹操。如果仅就华容道的场景理解“释曹”,往往只能得出曹操深藏心机,而关羽心慈手软以致草率地“以私废公”的结论。不过,关羽作为一员武将可谓“杀人无数”,称其对敌方心软并非“事实”,他对军师将令的威严和违反将令的后果也心知肚明。要完整地理解“释曹”何以发生,需要对双方的往来过程进行充分了解和体会。
关羽和曹操的往来是小说《三国演义》中非常值得玩味的一段关系。在关羽默默无闻之时,曹操能打破身份等级的成见,看到关羽身上的不凡气质,给他创造了立功的机会(温酒斩华雄);关羽暂降曹营时,曹操又多次施予厚恩,试图将其留在帐下;在关羽准备离开去寻找刘备之时,曹操也未对其暗下毒手,而是成全了他的忠义。关羽和曹操在政治立场上是对立的,但在私人关系上却积淀了深厚的恩情。
关羽在华容道的态度变化是由具体情境引发的,既包括目之所见的当下情境,也包括心之所感的过往情境。在华容道,曹操以英雄末路的情状向关羽重提旧恩,又有故旧张辽落魄地纵马而至,再加上曹军兵卒皆欲泪垂,激发了关羽的仁义之心——对曹操往日恩情的感念,对生死之交张辽的同情,对曹军受苦兵卒的怜悯。关羽本来声称“岂敢以私废公”,怀有对刘备乃至天下人之“公义”;但在与曹操言语往来的过程中,其态度发生了变化。我们理解关羽的行为,不能脱离情境带给他的内心触动而空谈抽象的道德原则。
如果将“义”视为外在的客观原则,那么无论在许田还是在华容,关羽都该阻截甚至诛杀曹操。但“义”和人伦关系中具体的人和事有关,而不是一般性的客观原则。曹操常被骂为“汉贼”,无数人欲除之而后快。如果关羽在华容道擒曹,当会获得无数激赏,但于关羽则为不义,因为曹操对关羽有旧恩,如果在曹操兵败势危之际擒杀之,会被认为是“乘人之危”“忘恩负义”。如果不顾往来恩情而以客观原则行事,可能是既不仁也不义:对恩情心无感念,是为不仁;不仁,就难以由己心推及他心,来而不往、置身事外,是为不义。毛纶、毛宗岗父子对“关云长义释曹操”的点评可谓恰如其分:“或疑关公之于操,何以欲杀之于许田,而不杀之于华容?曰:许田之欲杀,忠也;华容之不杀,义也。顺逆不分,不可以为忠;恩怨不明,不可以为义。”“使关公当日以公义灭私恩,曰:吾为朝廷斩贼!吾为天下除凶!其谁曰不宜?而公之心,以为他人杀之则义,独我杀之则不义,故宁死而有所不忍耳。”这正体现了“絜矩论”所强调的“心有所感”和“心有所动”(而非抽象规范)的意义。
关羽和曹操的施恩回报过程使我们容易想到西方社会学的“交换论”。根据理查德·埃默森的概括,该理论关注的焦点是人们在社会互动中的成本和收益,认为人们会(经常或一直)理性地行动,以求收益(商品、货币、称颂、尊重、认可以及关注)的最大化。以“交换”的观点看,关羽放走曹操是在报其旧恩,而他自己则获得了情感(心安理得)和声望(“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的“收益”。但问题是,关羽违背了军师将令,深感不安和愧疚,而如果擒拿甚至诛杀“汉贼”以利于匡扶汉室,其声望回报岂不更大?“成本—收益”模式难以解释关羽“擒曹”还是“放曹”的选择。
这种看似矛盾的转变,实际上遵循了儒家伦理的“絜矩之道”。关羽之所以“公私转化”,并非因为他公私不分,而是因为公私乃与恩义连在一起。如果出于“公义”,维护蜀汉正统、遵守军师将令,关羽当擒曹操。问题在于,关羽尚有余恩未报(五关斩将仍被放行),知恩不报、来而不往,非君子所为。对关羽来说,在华容道公私尚可区分,但恩情却不能无视,如果余恩未报又乘恩人之危,便是不义之举。因此,关羽“华容释曹”的行为,被称为知恩图报的“义举”。
和前文“收订购粮”的例子类似,“释曹”发生的关键点,不是关羽“向外”看到曹操(以及张辽和兵卒)的困境和可怜,而是“向内”感受到自己曾经身处绝境时的难处,并以此与无路可走的曹操及其将士相感通。倘若换做张飞在此,定会大骂“曹贼”并径直擒之,因为张曹之间并没有施恩回报的情义。如果只将关羽“擒曹”视为超越于个人的匡扶汉室大业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以外在的客观标准评判其内心感受,那样就不会发生“义释”之举了。相较而言,如果说“絜矩论”之权度的特点在己、在内、在心,“交换论”之权度的特点则在人、在外、在物,即一般性的客观原则或所谓的“上帝之眼”指引着互动双方的权衡取舍。
三、“絜矩论”的要义及思想基础
在《礼记·大学》中,有两句话表达了“絜矩之道”的大体意思。
其一,“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此所谓絜矩之道也”。根据《说文》,“絜”意为“麻一耑也”,段玉裁注曰:“一耑犹一束也。耑、头也,束之必齐其首,故曰耑……束之必围之,故引申之围度曰絜。”郑玄注“絜矩之道”曰:“絜,犹结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谓当执而行之,动作不失之。”。《说文》释“挈”为“悬持也”,段注曰:“则提与挈皆谓悬而持之也。”孔颖达疏大体从郑注之意:“絜,犹结也。矩,法也。言君子有执结持矩法之道,动而无失,以此加物,物皆从之也。”朱子注则有所不同:“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是以君子必当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间各得分愿,则上下四旁均齐方正,而天下平矣。”相较而言,郑注侧重动作举措,朱子注则偏人心推度。“因其所同”即由“人心之所同”出发,“所谓絜矩者,矩者,心也,我心之所欲,即他人之所欲也。我欲孝弟而慈,必欲他人皆如我之孝弟而慈”。如此,则“各得分愿”“上下四旁均齐方正”,大体说的是人人各安其位、各得其宜的理想状态。
其二,“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这句话更具体地解释了“絜矩”在于使“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也表明“絜矩”的关键是“己心”对“他心”的忖度,如果心无所感、心无所动,便难以发挥“人心之所同”、推己及人地体会他人的好恶趋避。关于对上下四旁的忖度,朱子注曰:“如不欲上之无礼于我,则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无礼使之。不欲下之不忠于我,则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朱子还明确将“前后”“左右”的推度归结为“将心比心”:“左右,如东邻西邻。以邻国为壑,是所恶于左而以交于右也。俗语所谓‘将心比心’,如此,则各得其平矣。”朱子的阐释可谓点出了“絜矩”最核心的意思,那就是“将心比心”。根据朱子的阐发,如果能做到“将心比心”,便会“各得其平”,消融可能的误解或怨恨。
在《四书训义》中,王夫之对“絜矩”的阐释与朱子类似,认为“理有同然而可通,心有同然而必感也”,“物之不齐,而各有所应得者,犹之矩也;君察乎理而审乎情,以各与所应得者,此心之絜度也”。不过,在《读四书大全说》中,王夫之认为:“君子以絜矩之道治民,而非自絜矩以施之民也。”称朱子等人是“就絜矩上体认学问,故取一人之身以显絜矩之义,而非以论絜矩之道。”他认为:“国之于家,人地既殊,理势自别,则情不相侔,道须别建。虽其心理之同,固可类通,而终不能如家之人,可以尽知其美恶以因势而利导之。”相比之下,朱子的理论重心落在推度人心与兴起民众共通的道德意识上,而王夫之则以政治的角度去探求絜矩之道的实现方式;前者的阐发更贴合《大学》的文本脉络,后者则更关注絜矩作为一种政治原理何以能建立可靠的政治秩序。
基于以上的简要梳理可以发现,郑玄与孔颖达的注疏主要点出“絜矩”的“度量”之意,朱子侧重强调“人心之推度”,王夫之在心之推度的基础上着重谈论政制路径。基于“絜矩之道”的意涵,本文侧重在“社会”层面理解和运用“絜矩”概念:一方面,将“絜矩之道”从“治国者”引申到一般的社会行动者,其相通之处在于“人心之同然”;另一方面,在“德性情感”与“政制路径”之间理解“絜矩”,即将其定位于社会行动及人际往来层面。“絜矩”既有内心权度、将心比心的意思,也有行动层面使上下左右前后多方社会关系各得其宜的意味,是一个能够同时包含内与外、人与我、情感与行动等多重维度的概念。
我们大体可将“絜矩论”的基本观点概括为:一个行动者理解和回应另一个行动者的关键,在内而不在外、在己不在人、在心不在物;外力的影响固然不可忽视,但唯有心有所感、心有所动,才更易于推己及人,实现感通和引发后续行动。“絜矩论”侧重关注“伦理本位”社会的社会行动,其特点往往体现为:
首先,社会行动以“己”为中心。这里的“己”并非原子化个体,而是处在社会连带关系中的行动主体,“心”的作用体现了主体的情感力量。《朱子语类》中讲道:“絜,度也。不是真把那矩去量度,只是自家心里暗度那个长那个短。”以己心比人心的关键是“我”的内在情感体验的激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诗经·豳风·伐柯》)说的便是絜矩的关键在“己心”的道理:斧柄的尺寸无需外求,而取决于斧头的孔,斧头的孔便是人心中的“尺度”。
其次,社会行动具有注重感受与体会、情理合一的特点。在人际关联的意义上,以心权度是达至理解的关键,正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所言:“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夫之曾将“能絜与不能絜”看作“人情得失之枢”:“夫絜之以矩而去所恶矣,去所恶,则必全所好矣,故能絜矩者,能公好恶者也,好恶公,则民情以得”。这里的“公好恶”显然不是推行一般性的客观原则,而是以己心之好恶去感受他人之好恶,这时,能否动心动情、推己及人,便至为重要。
最后,社会行动过程的“内外合一”。如前所述,人对外在的他人和事物作出反应,关键在内心的反应,“心动”后进一步引发对他人和事物的态度与行为的变化,或可称此过程为“外—内—外”的过程,具有“内外合一”的特点。絜矩的“标准”不同于一般性的规则,而是和心与外物的接触及其引发的感受密切相关。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絜矩的关键是内心感受的变化,即“心动”,但这不意味着“絜矩论”只是重视个人的内心世界,而是注重内—外、人—我、情感—行动的融通合一。根据儒家社会思想,由己心向外推,可由亲亲而仁民,由仁民而爱物,这是一种更为广泛的“内外合一”。
“絜矩论”与“情境论”和“交换论”的差异,究其根本,是其背后的关于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预设不同。潘光旦曾论及:“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个人与社会并不是两个对峙的东西……群己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推广’与‘扩充’的关系,即从自我扩充与推广至于众人”。费孝通晚年重提“差序格局”概念时也提出类似的观点:“传统意义的中国人,对于‘人’、‘社会’、‘历史’的认知框架……中国的世界观,更像是一种基于‘内’、‘外’这个维度而构建的世界图景:一切事物,都在‘由内到外’或‘由表及里’的一层层递增或递减的‘差序格局’中体现出来。”相较而言,“情境论”关于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预设带有主客二分的色彩,而“交换论”则隐含着个体行动与一般原则的分立。
追本溯源,“絜矩论”的思想基础是儒家的仁义观,其核心关注点是推己及人的情感与行动过程。在传统儒家思想中,“仁”是人与生俱来的特质,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但“仁”不只是一种内在的情感,而且需要在日常生活的人伦关系中实践,如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人伦关系分亲疏远近和上下尊卑,仁心之外推亦有差等,合宜的差别便是“义”。
仁义的重要特点在于,其生发往往与目之所见、心力所及的事物密切相关。“见牛未见羊”的典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即以羊代牛衅钟不在于牲畜的贵贱和节约的考虑,而是因为目见牛之觳觫激发了人的怵惕恻隐之心,所以孟子认为易之以羊“乃仁术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仁者,人心也。义者,人路也。”(《孟子·告子章句上》)当仁心外推时,便涉及“义”。朱子有云:“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心之制’,亦是就义之全体处说。‘事之宜’,是就千条万绪各有所宜处说。‘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说。看甚么事来,这里面便有个宜处,这便是义。”所谓“看甚么事来”,就涉及人和人之间的具体关联,特别是情感的关联,如果“一刀切地”以一般原则评判,所谓“对事不对人”,可能恰恰为“不义”。
在人伦关系的意义上,仁义与亲亲尊尊之道相呼应。《礼记·中庸》有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大体意思是,所谓仁,就是爱人的意思,亲爱双亲是为大仁;所谓义,就是合宜的意思,尊重贤人是为大义。这句话,王夫之给出了精辟的诠释:
仁者,即夫人之生理,而与人类相为一体者也。相为一体,故相爱焉。而爱之所施,惟亲亲为大;一本之恩,为吾仁发见之不容已者,而民之仁,物之爱,皆是心之所函也。乃仁者人也,而立人之道,则又有义矣。义者,即吾心之衡量,而于事物酌其宜然者也。酌其宜然,必有尊焉。而尊之所施,惟尊贤为大;尚尊贤之义,行为而又自有其条理者,则亲亲之杀出焉。推而上之以及乎远祖,推而下之以及乎庶支,厚薄各有其则,尊贤之等出焉。
亲亲与尊尊是最基本的人伦之道,在根本上,体现这两种关系的制度规范并非外在的,只是顺应人的自然禀赋而已。亲亲之杀与尊贤之等,是顺应自然人性而出的人伦秩序和行动伦理,有研究指出,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在根本上便源于此。在这种社会结构中,若要形成和谐融洽的社会关系,便需“酌其宜然”,懂得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根据梁漱溟的说法,传统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所谓“伦理”,并非指一般性原则,而是指不同的“伦”有相应的不同的“理”,和谐的人伦关系往往体现为“伦理相宜”;而如果以一般性原则度量不同的人伦关系,则可能带来“伦理相悖”的结果。
以絜矩的视角看,无论行仁义,还是尽孝道,虽然会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但“作主”的,还是看“己”和“心”。我们不妨引入朱子关于父责子、君责臣的观点来讨论。“‘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每常人责子,必欲其孝于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果孝否?以我责子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则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常人责臣,必欲其忠于我,然不知我之事君者尽忠否?以我责臣之心,而反求之于我,则其则在此矣。”大体意思是,父亲希望儿子如何对待自己,并不取决于父亲是如何对待儿子的,而取决于父亲如何对待自己的父亲,儿子参照父亲对待祖父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父亲;上级希望下级如何对待自己,并不取决于上级是如何对待下级的,而取决于上级如何对待更高的上级。也就是说,在祖孙之间或上下级之间,“我”是关键,“我”是否尽己之心事父事君,会影响子代对父辈、下级对上级的态度。
“父责子”“君责臣”背后的道理和传统中国社会人伦关系的特点有关。在传统中国社会,父子是家庭关系的主轴,父子之伦核心的行动伦理是慈和孝,这种伦理的主要内容通过至少三人的关系框架得以实现。周飞舟的研究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一体本位”而非“个体本位”,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是以“祖—父—子”三代关系为基本单元,而不是父子之间的对子关系,这种家内的关系和思想行为方式是理解整个社会的底色。如果以“对子”关系审视父子关系以及君臣关系,便可能得出“你不慈,则我不孝”“你不仁,则我不忠”的结论,将具体的人伦和情理关系简化为一种抽象的、工具性的交换关系。
余论
相较于“情境论”和“交换论”,以儒家社会思想为底色的“絜矩论”,适用于理解社会行动的情感动因和情理逻辑,在社会行动何以发生和演进上具有一定解释力。
首先,越是和行动者本身有直接关联,特别是触动其情感体验的人和事,越容易引发社会行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说的“和我有什么关系”就是这个意思,与己有关、心有所感,才易于形成推己及人的情感力量和实际行动。特别是在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如果仅从外在规则出发或以旁观者的观念评判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常常会造成误解或错判。
其次,絜矩论有助于理解公共规则和个体行动之间的“张力”与“合力”。众所周知,公共规则不会自动实现,其实施并产生良好效果往往需要一系列社会过程。一般而言,公共规则及其落实越是关注人的切身体验,越可能得到认可和遵守,否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可能会带来漠视规则或阳奉阴违的后果。絜矩之道注重心与心的沟通,这也适用于公共规则的落实和执行。公共规则的施行,并不是时刻以超然物外的冷面孔在公私之间划线定界,而是要在公私之间留出质朴而适切的情感空间。
再次,絜矩论有助于辨识和判断社会行动的合理性。很多社会行动仅就结果看是“不合理”的,而就其过程看又是“合理”的,因为判断一个人的行动合理与否,需要考虑其前因后果,将心比心地体会其中的往来过程和情感积淀。如果以后果推测原因,实际上是将一种“理论逻辑”或“旁观者立场”置于行动过程之上,往往难以把握行动过程的丰富性特别是情理逻辑。
最后,絜矩论有助于揭示和感知中国的“社会底蕴”。传统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人生哲学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它作为一种“社会底蕴”,渗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意识结构里,表现在社会的风俗习惯和成员的行为规范中,并参与建构当下的社会。对于深受儒家思想濡染的中国社会,欲真正理解社会行动,固然需要深入田野进行观察和理解,但光有“田野饱和”也是不够的,还需要把握行动伦理的思想根源。在理解社会行动的动机和意义时,往往需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地感受和体会,如周飞舟所言,研究者以自己开放、包容、变化和成长的心态去触摸、感通研究对象的心态,这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从实求知”。
本文对“絜矩论”及其与“情境论”和“交换论”之比较的初步讨论,无意于在一些概念和理论上刻意区分本土的或西方的,而是重在强调,概念和理论的背后往往是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如果对这些深层因素缺少辨识,便可能对概念和理论的表面意涵视若当然,如此一来,用来解释现实的概念和理论就可能成为对思维和现实的“遮蔽”。对于探索中国社会理论而言,我们需要“重返宏观”,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中挖掘传统思想资源中能够体现中国人行动取向和精神气质的概念,以更适切地认识中国社会和把握中国人的行动伦理。毫无疑问,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关于“絜矩论”的理论内涵、知识基础和学理脉络等,尚需深入研究。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文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