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外交政策经历从“大陆扩张”向“海外扩张”的战略转型。面对在东亚相对弱势的竞争格局,美国摒弃了欧洲列强瓜分领土的传统殖民模式,转而诉诸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为核心特征的“新殖民主义”策略。美国政府表面上高举“保全中国”与“机会均等”的旗帜,暗中嵌入独占未来中国庞大市场的战略野心,通过将门户开放政策包装成“反对领土占有”的所谓“进步”方案,博取虚誉,争取广泛支持。因此,门户开放政策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新殖民主义”话语。它巧妙利用“反对旧殖民主义”的国际法话语,服务于美国的经济扩张与区域主导权诉求。
关键词:门罗主义;门户开放政策;《辛丑条约》;自由主义霸权;新殖民主义
作者马建标,复旦大学外交学系教授(上海200433);徐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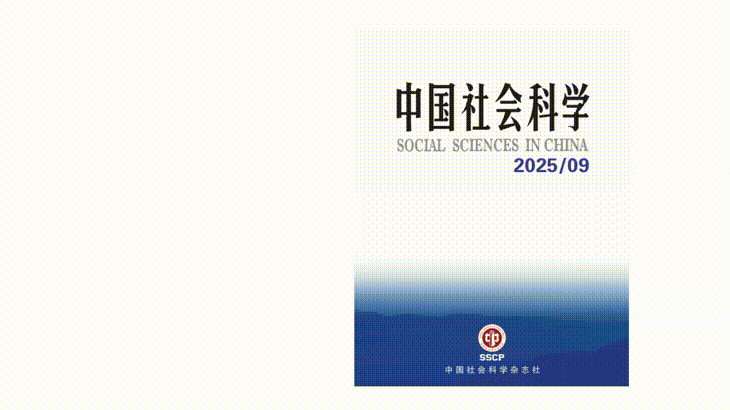
引言
一、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历史逻辑及其话语设计
门罗主义既是美国19世纪在美洲大陆进行扩张的外交基石,也是其后门户开放政策赖以存在的历史逻辑。尽管门罗主义常被认为是“封闭”和“孤立”的代名词,但它真正的核心宗旨可以被概括为:“所有美洲国家的独立、在这一区域不存在殖民地、非美洲国家不得干涉这一空间。”尽管它也在历史变化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但发生变化的是其适用范围,从美洲推广到全球其他区域。这个变化的标志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伴随着对菲律宾的占有,美国的地缘政治版图越出西半球,向亚太地区延伸。
1900年春,美国扩张主义的精神领袖马汉(A.T. Mahan)指出,美国需要重新界定“门罗主义范围”。他说:“门罗主义是为了防止欧洲势力进入美洲大陆”,但是美国现在占有了菲律宾,由此带来诸多机遇,美国政府不应固守“过去式的”门罗主义,有必要重新予以解释。同时,这也是为了摆脱美国国会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的牵绊,以说服反对者为目标的政治压力促使美国政府形成了强烈的外交话语权意识。具体而言,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及其智囊们将目光投向了帝国主义领土占有之外的其他扩张方式,采取文化、经济、宗教等隐形的新殖民控制方式。
与此同时,19世纪末期的国际形势也呈现出帝国主义逐渐衰落的趋势,美国政府由此找到关联门户开放的新政策与门罗主义的历史逻辑的“钥匙”,即以“门罗主义”的名义反对列强在美洲和东亚推行以瓜分领土为目标的“旧殖民政策”。 门罗主义不仅主张美国对欧洲的孤立,还追求整个美洲的集体孤立,在美欧之间筑起一道藩篱。门罗主义在美洲的推行以美国军事武力为后盾,而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的推行依靠的是国际法武器,试图以最小的代价确保美国在华利益的最大化,即由美国主导中国未来的市场。正如美国学者裴斐(Nathaniel Peffer)所言,美国“竭力阻止某一国家来独占中国,自1905年日本把俄国威胁消灭了,她就专门对付日本。这并不是因为她尊重凯洛格非战公约的不可侵犯,而是由于她不让任何国家把中国占为己有的政策”。
1899年初,贝思福在回国途中来到美国,他试图游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1898年8月,英国议会对“门户开放”政策展开辩论,引起时任美国驻英大使海约翰的兴趣。1898年11月29日,贝思福在赴美前夕致信海约翰,提议英美两国缔结“商业联盟”,共同推进对中国的“门户开放”。他抵达华盛顿后,受到美国亚洲协会的热烈欢迎,成为海约翰国务卿的座上宾。在访美期间,贝思福的英国同胞、中国海关职员贺璧理(Alfred E. Hippisley)也通过柔克义接近美国外交决策圈。随后,贺璧理起草的备忘录经过柔克义的修改后被海约翰采纳。1899年9月6日,海约翰签署了以“在华贸易机会均等”为核心内容的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该照会于同年11月至12月间正式递交各国使馆。但这次照会只单方面表明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立场,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政策并无本质不同。
中国时局变化凸显美国的“与众不同”。1900年,义和团运动给了列强干预和侵入中国的“借口”,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这时,来自上海的一封电报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轨迹,美国从此走向“新殖民主义”扩张的历史道路。1900年7月初,美国驻沪总领事古纳(John Goodnow)给海约翰发送紧急电报,介绍了6月26日上海道台余联沅与各国驻沪领事签署的《中外互保章程》,章程规定东南督抚负责“保境安民”,列强不对东南动武,不干涉中国事务,史称“东南互保”。这封电报引起了海约翰的高度重视,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趁机联络其他列强支持中国的“东南互保”。
海约翰最终采纳摩尔的建议,采取蕴含解释空间的政策措辞。摩尔参照美国之前对华政策的某些表述,重新设计门户开放照会文本。7月3日,美国政府向相关列强发布了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主张“保全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实体,维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的一切权利,并保护全世界在中华帝国境内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此即“保全中国”原则的由来,它一方面高举门罗主义的旗帜,反对列强武力侵略中国的“旧殖民政策”;另一方面又以国际法为幌子对中国采取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新殖民政策”。可以说,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完成了门罗主义与门户开放政策的“历史衔接”。值得注意的是,海约翰发出门户开放照会前,并未就此问题向美国国会咨询,以避免国会中孤立主义势力的阻挠,引起美国是否应向海外扩张的新争议。
除了摩尔,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芮恩施、美国陆军部部长罗脱等代表的美国政治精英都是门罗主义的信奉者,他们用美国公众熟悉的门罗主义话语对门户开放政策进行话语设计,将美国外交政策和自由主义价值观捆绑在一起。正如芮恩施自称的:“从安德鲁·怀特(Andrew D. White)到罗脱,美国的国际主义者一直在与世界争论应将法律和司法手段运用于国际事务”,换言之,“将门罗主义原则推广到全世界,是过去三十年来美国政治家的理想”。1903年,罗脱支持芮恩施等人创建了美国政治学会,汇聚政学两界的人脉资源;他建立的跨界精英联盟为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推动美国法律的国际化。在东亚地区利用国际法推行美国主导的“新殖民主义”,实现了美国在中国建立“自由商业市场秩序”的梦想。
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意味着门罗主义从一种不干涉和抵御外部势力干涉的美洲原则,演变成以“新殖民主义”策略干涉东亚事务的自由主义霸权,将不干涉他国的国际法原则转变成“全球理念”,在人道主义的掩盖下插手东亚事务,甚至成为一种泛干涉主义的意识形态。《辛丑条约》谈判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新殖民主义”话语实践提供了一个实验场。
二、门户开放政策话语在《辛丑条约》谈判中的运用
门户开放政策诞生在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时刻,尤其是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因中外多重势力的影响,麦金利政府要把外交观念转化为外交实践,显然会面临诸多挑战。在此过程中,门户开放政策必然会因应局势的变化而做出某种调整。但是,门罗主义作为门户开放政策的观念基础并没有发生改变。美国代表柔克义在《辛丑条约》谈判中将门户开放政策具体化为一种“话语实践”,通过强化“新殖民主义”话语,实现了从外交政策到外交话语的关键转换。在此过程中,柔克义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执行人”角色,负责将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落实到具体细节上。诚如论者所言,柔克义在此期间“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实施产生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大的影响力”。
与其他列强相比,美国在东亚的政治军事影响力极为有限。在钢铁巨头卡内基看来,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截至1898年,美国军舰数量还不及英国的七分之一。硬实力的严重不足,更是凸显了美国“软实力”即门户开放政策话语在《辛丑条约》谈判中的重要性。美国政府需要通过在谈判中与英法日德俄等列强代表进行有效的协商,制定一套符合门户开放政策的条约规则,在承认列强在华既有势力范围的前提下凝聚门户开放政策的共识,以“机会均等”的名义暗中嵌入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霸权逻辑。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形成的中外条约体系和“最惠国待遇原则”作为列强默认的历史共识,依然在发挥着惯性作用。这是麦金利政府在《辛丑条约》谈判中得以贯彻门户开放政策的历史基础。值得注意的是,门户开放政策理念在谈判中的落实,首要障碍并不是列强代表,而是在华美商群体。尽管门户开放政策符合美国在华利益集团的诉求,但是在“惩凶”“归政”等涉及清政府尊严的问题上,在华美商群体与麦金利政府存在严重分歧。换言之,在华美商群体对待清政府的态度仍然停留在旧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而麦金利政府倾向于在“惩凶”问题上大事化小,贯彻门户开放政策。
围绕所谓“惩凶”问题,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理念在《辛丑条约》谈判落实过程中的主要阻力来自在华美商群体,英俄两国与美国政府表现默契。其间,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多次要求列强尊重两宫:“现东南各省极力弹压,遵旨保护洋人,然假使各国不尊敬我皇太后、皇上,薄海臣民必然不服,以后事机实难逆料”;受此影响,英俄等国代表也主张宽待慈禧:“如果把皇太后牵入这件事情以内,人们将冒着废弃中国整个国家组织的危险,这也是对于欧洲不利。”作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实际执行人,柔克义的首要任务是与列强和清政府协商,尽快在谈判中落实门户开放政策。如果在“惩凶”问题上纠缠不休,只会导致谈判延宕不已。故而,柔克义倾向于不追究慈禧的罪责。
在赔款问题上,各国代表意见存在分歧,美国公使康格起初笼统的“降低赔偿总额,各国按比例缩减各自要求”的调和建议也未获赞同。在柔克义接手谈判后,国务卿海约翰发来两点指示:一是由各国联合向中国提出一项包括各种性质的赔偿诉求总额;二是将赔款数额降低到中国支付能力范围以内。各国代表委托德国、比利时、荷兰公使和柔克义组成“赔款委员会”,负责制订中国的赔款原则。赔款委员会坚持两个原则:第一,保证受损害者得到公正赔偿;第二,防止在任何情况下以义和团运动为借口,取得非法收益。
在赔款方法的讨论过程中,柔克义不失时机地利用门户开放政策,维护美国在华通商利益。一些列强代表极力提倡中国“应当借外债支付赔款”,柔克义认为这样虽然是偿付赔款最快的方法,但是会导致建立某种形式的“国际财政管制”,影响中国“行政主权的完整”,违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最后,英国公使萨道义(Ernest Satow)建议“按照中国的岁入分期偿付赔款”。柔克义认为这种办法“对中国非常有利”,因为这会有助于促使清政府加快行政改革,更好地确保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的运行。在《辛丑条约》谈判期间,美国政府还试图在条约中规定北京开放为“商埠”,强行要求清政府外交官员必须说“洋话”,实施语言殖民。1900年11月16日,海约翰致电康格公使,要求中国的外交人员“必须能讲某种外国语”。
在提高中国关税问题上,柔克义设法阻挠,意欲通过关税将门户开放政策转化为控制中国的新型经济武器,迫使清政府在经济层面对美国和列强全面开放。这种以“商业机会均等”为幌子的话语策略,标志着美国政府将“新殖民主义”话语深度嵌入《辛丑条约》。
美国所谓的“通商利益”着眼于中国未来的庞大市场预期,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无限的可能性,而不必像其他列强那样被具体细微的“蝇头小利”所束缚。因此在《辛丑条约》谈判中,柔克义假意保持超然的立场,用其“新殖民主义”的“话语霸权”主导列强对华谈判进程。诚如柔克义所言:“我们在保持完全独立的同时,能与各国协调一致地行动,这种协调一致对于迅速、和平地解决争端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为了全世界与中华帝国各地进行平等和公平的贸易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在《辛丑条约》谈判期间,美国麦金利政府采纳摩尔的国际法建议,海约翰与柔克义电报往返,柔克义贯彻了门户开放政策谈判原则,在谈判中表面上尽量维护清政府的行政主权尊严,甚至赢得了清政府官员的好感。柔克义践行了麦金利政府利用国际法作为谈判武器的策略,形成以门户开放政策为标志的“新殖民主义”话语。
三、清政府对门户开放政策话语的认知偏误
门户开放政策的政治功能是为美国向亚太扩张提供一种“基本话语”或“主导叙事”,借此确定美国在东亚世界的国际地位,规范美国与在华列强的国际关系,由此彰显美国与众不同的国家身份。门户开放政策旨在拓展美国在东亚世界的自由市场秩序,作为一个霸权性话语,它不仅主导着美国扩张主义者的自我认知,而且影响了其他国家对美国国家身份的认知。门户开放政策把美国塑造成一个不同于欧洲列强的“利他主义国家”,这种主导性叙事话语深刻影响了清政府官员对美国的认知。
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确属一种“新帝国主义”,它不以领土占有为目的,而是着眼于市场控制,这种典型的“新殖民主义”体系主要依靠本地精英的支持来维护其政治商业利益,而这些精英也从中获利。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就是美国政府看中的此类代表。1901年12月6日,柔克义致信祝贺袁世凯:“你的任命对美国国务卿来说则是一件令人满意和愉快的事情。我经常向国务卿和总统谈论有关你的情况。”美国政府通过亲美的袁世凯成功地对清政府进行间接的政治影响。据日本外务省观察,在袁世凯主持晚清外交的那几年,清朝高官普遍认为,中国的命运“掌握在美国手里”。例如,庆亲王奕劻就是一位对美国有好感的高官,他曾聘请耶鲁大学毕业的唐国安担任其秘书,而唐国安与美国社会各界有着密切的往来。美国人也会通过唐国安了解袁世凯和清政府高层的政治动态。
面对日本在东亚地缘政治上的空间挤压,清政府希冀联合被日本排斥在外的美国、德国,共同抵制日本的侵略。清政府反制日本的战略构想逐渐清晰起来。1907年8月14日,两江总督端方在给朝廷的电报中建议:“如能派亲贵重臣游历欧美,密与德美两国设立协约,以互换利益为主,尤足为无形之抵制。”两广总督张人骏的“联美”主张表达得最直接,他认为,“独美国所处僻远,而在中国商务最盛……彼为保商计,岂能不竭力维持”。张人骏的看法,不仅体现出传统中国“以夷制夷”的政治思维,还带有“美国例外论”的意味。张人骏并无留美背景,他对美国格外青睐,与他的姻亲袁世凯同声相应,更反映出当时清政府重臣普遍的认知偏差:他们对美国的观察和认识基本停留在门户开放政策的表面,并没有意识到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的全方面、深层次的侵略性。
以袁世凯为首的清政府外务部官员,仍然把美国与英法德等列强等量齐观,视为可以外交结盟的对象。1908年6月1日,袁世凯对德国驻华公使雷克斯(Arthur Alexander Kaspar von Rex)说,中国与德美两国接近是“既定路线”,并表达了他的“不安之情”。袁世凯的不安,显示出清政府高层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理解尚存诸多不确定性。这一时期,清政府高层的“联美”呼声不断,一项旨在改变东亚地缘政治秩序的“联美制日”计划呼之欲出。
四、门户开放政策话语对东亚空间秩序的影响
门户开放政策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新殖民主义”方案,通过取代传统军事外交政策的旧殖民主义,在东亚建立一个基于自由主义霸权理念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其显著特征是减少对军事武力的依赖,以“机会均等”破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束缚,以开放性的“合作模式”代替赤裸裸的殖民掠夺,通过条约体系来维持列强在华均势格局,逐步建立基于门户开放政策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这套国际秩序是服务于美国的商业帝国构想。然而,美国倡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与日本以武力为依托在东亚建构的旧帝国主义秩序是格格不入的。这两种秩序理念的博弈,集中表现为美国的“新殖民主义”话语霸权与日本的政治军事霸权的较量,对其后东亚空间秩序构建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罗斯福政府呼吁“机会均等”,号召列强支持共同投资和“开发”中国市场,使门户开放政策成为美国对华开展金元外交的指导方针。门罗主义从此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地缘秩序,转向为帝国主义扩张服务的普遍原则,在东亚地区实现美国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秩序。美国银行团代表司戴德(W.Straight)认为,“如果外国资本家要在中国投资发展经济,就必须以合作替代竞争,并为此组成一国际联合的银行团”;在美国倡导下,银行团从最初的三国发展成由英美法日德俄组成的“六国银行团”。国际银行团在中国的投资,本质上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经济体系,建立了一个单方面有利于资本帝国主义的不平等贸易体系,其对中国的破坏性影响无法估量。
其次,门户开放政策充满“利他主义”的迷惑性话语,这也激发了清政府推动“中德美联盟”计划的主观愿望,为这一时期东亚国际秩序的构建描绘了新的愿景。但是,清政府对门户开放政策的理解存在很大的认知鸿沟。这是由于中美两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标和关切点不同,也与门户开放政策话语的迷惑性有关。门户开放政策表面上是在保障中国的主权,实际上却让中国门户大开,使外国商品更为便利地倾销到中国,中国资金不断外流,本国工业难有起色。这就是梁启超所谓的“灭国新法”,就是通过金融、借债、修筑铁路、派遣顾问等方式实现对中国的新殖民控制。故而,梁启超才是清末真正理解美国“新殖民主义”话语本质的有识之士。
门户开放政策暗藏着美国的“新殖民主义”霸权野心,以新兴的世界经济强国姿态对东亚秩序实施战略干预,激化了美日冲突,更为数十年后的美日战争埋下伏笔。长远看来,清政府联美制日的战略构想,符合美国东亚政策的核心关切:预防和牵制日本的殖民扩张。但是,就罗斯福总统而言,其东亚政策仍然是坚持对日本妥协的原则,让日本成为美国门罗主义在亚洲发挥效力的重要支点。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罗斯福总统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利益来换取日本政府的妥协。然而,对此浑然不觉的清政府为制衡日本的侵略,急于寻求美国的支持,此即1908年唐绍仪使美与联美活动之意图。
结语
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实现海外扩张的战略目标,已经显露出利用国际法增强外交话语权的意识。比如,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摩尔的帮助下,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开凿巴拿马运河是为了人类“集体文明”利益,反对巴拿马政府的阻挠,并以此说服美国国会内部的反对派。在1900—1901年间,摩尔作为国际法顾问密切参与了美国政府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制定,他成功地说服麦金利总统,将国际法理论作为美国参与《辛丑条约》谈判的指导思想,由此形成一套以门户开放政策为准则的“新殖民主义”话语系统。
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要建立一套由其主导的自由主义霸权,以及由此生成的国际法体系,其实质是非平等性的。19世纪、20世纪之交,门罗主义远渡重洋,摇身变为“门户开放”,在看似“机会均等”“主权平等”的自由主义国际法体系之下,隐藏着美国的新殖民帝国野心。从这个意义上说,门户开放政策的历史价值,在于让原本局限于美洲的门罗主义,成为超越单一国界和美亚洲际边界的“新国际法”。传统国际法以“国”为单位,门户开放政策则是以跨地域“大空间”为单位的“美式国际法”,服务于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战略,维护其自由主义霸权。
在20世纪初,美国围绕门户开放政策提出的“新殖民主义”话语,是在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博弈中形成的。美国政府凭借其外交话语的“软实力”意图弥补在东亚地区政治军事上“硬实力”的不足。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真实用意是把中国最终变成由它独占的经济市场,事实上,美国政府通过与国民政府签署的1946年《中美商约》几乎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理解,如果放在二百余年来美国对华活动的历史脉络中予以考察,就可以看出其“新殖民主义”的本质。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武雪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