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探讨友谊在公共政治领域的作用。友谊在雅各宾派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雅各宾派将友谊理想化为一种自然美德,但拒绝将其视为庇护、腐败和任人唯亲等古代政权政治风格的象征。将行政职位交给私人朋友的革命政治家冒着违反政治美德意识形态的风险,即不应该对特定公民给予优待。随着政治局势的日益紧张,友谊变得愈发可疑,充满派系斗争甚至阴谋的味道。本文探讨了在这种政治生活中,由友谊造成的不安和模糊如何影响了雅各宾俱乐部中的两个派别:吉伦特派和罗伯斯庇尔派。
关键词:雅各宾派;吉伦特派;友谊;政治
玛丽莎·林顿(Marisa Linton),英国金斯顿大学荣休教授、大学学术委员会成员,著有《启蒙法国时期的美德政治》《法国革命中的阴谋》等。Email:linton@kingston.ac.u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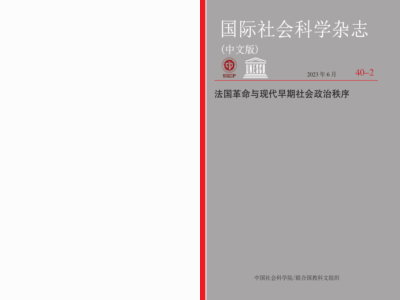
1794年春,激进记者卡米耶·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在卢森堡的监狱里待了几日。大革命伊始,他便是狂热支持者。此时,他在等待被转移到巴黎古监狱。那里是囚犯在等待革命法庭审判期间被关押的地方。与恐怖统治的许多受害者不同,德穆兰与指控他的人有私交。他和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从在路易大帝中学做同学起就是朋友。如今,罗伯斯庇尔已经签署了逮捕他的朋友的命令。对德穆兰而言,这种否定以往的信任与友谊的行为,是尤为个人的背叛。面对这一反转,他瞠目结舌、心如死灰。在牢房里,他给他挚爱的妻子露西尔写了几封信。在信中,他为自己的命运而哭泣,并尝试理解这一切何以发生在自己身上:
如果是皮特或科堡如此苛责于我的话,我无话可说!但这个人偏偏是我的战友!是罗伯斯庇尔签署了监禁我的命令!是我为之殚精竭虑的共和国!这就是我的美德和牺牲所换来的回报!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为共和国披荆斩棘,我在革命时仍箪食瓢饮……我亲爱的洛洛特(Lolotte)……那些自称是我的朋友、是共和派的人,把我扔进了牢房,仿佛我是一个阴谋家!
他到底做了什么才会遭受如此对待?在他能想起的事情中,有两件事几乎是确凿无疑的:他在著作中对革命领袖的嘲弄、他与罗伯斯庇尔的对手丹东的友谊。“我可以毫不掩饰地说,几句玩笑话以及与丹东的友谊,导致我受害而死。”
这种声称他是由于考虑不周的玩笑和友谊,而不是由于任何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而死亡的说法,至少在第一眼看来,是奇怪的、微不足道的,也不是他被捕的主要原因。德穆兰是《老科德利埃报》(Le vieux Cordelier)的创办者,他在这份报纸上发表批评执政委员会恐怖政策(尤其是反对缺乏言论自由)的言论。这是一个大胆而危险的立场。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是不会容忍如此公开的威胁的。在3月30—31日的晚上,其中的大多数成员,包括罗伯斯庇尔,都签署了逮捕德穆兰和其他丹东派的命令。此外,我们也看到,德穆兰自己通过全然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一事件。他认为,这属于涉及个人恩怨和忠诚度的问题:一段忠诚的友谊(他与丹东的友谊),以及一段背叛的友谊(罗伯斯庇尔与他的友谊)。这种对事件的个人论断,并不能排除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语境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应重视德穆兰自己的话语,特别是因为他写下这些话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动摇观众或读者的想法,而是为了写给他的妻子看的。他正试图向自己、向她解释所发生的事情,至少在当时,这就是他的理解。
德穆兰对友谊在他被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个人看法,让我们对在恐怖时期起主导作用的革命者(无论是恐怖统治的拥护者还是受害者,或者有时是兼具两者身份的人)的政治有了新的认识。德穆兰的解释说明了革命政治的公众形象与革命者的私人生活、友谊、忠诚、猜忌、背叛是如此密不可分。这种解释揭示了革命身份和革命政治的本质。它提出了一种有说服力的观点:对于共和二年的雅各宾派而言,友谊可能会带来致命的结果。
近年来,伴随着对情感史的更为广泛的关注,作为情感史组成部分的友谊史也日渐引起了研究者更多的兴趣。艾伦·布雷和其他人关于友谊的研究丰富了英国史的研究,也有关于18世纪法国男性友谊的重要学术著作。关于革命者的心理和情感的文献也与日俱增。革命博爱的主题引发了一些学者的深入思考。历史学家以各自的方式对以下假设提出质疑: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寓居于一个客观且理性的世界当中,并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那些经历和参与革命的人们的私人生活。然而,他们尚未研究过大革命中的友谊政治。
友谊是革命政治的核心。它一直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经常被低估)。但是,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建立的友谊往往比在“正常”情况下建立的友谊更为紧密。大革命裹挟而来的剧烈变动,打破了旧制度下固化的社会习俗,把原本在不同圈子里活动的人聚集到一起。对于德穆兰以及与他志同道合的激进分子而言,早期的大革命意味着个体和政治上的解放:存在一种目标一致、情感联结的感受。共有的同情心可能会催生亲密的友谊。然而,也会出现截然相反的情况:革命者的敌人至少和他们结交的朋友是一样多的,正如德穆兰所意识到的,曾经的朋友可以成为最可怕的敌人。
在雅各宾派中,这些冲突的情感所发挥的作用最为强烈。他们共享了许多关于友谊的文化预设,这在他们那一代人中是很常见的。但雅各宾派对友谊的态度是特别有启发性的,不仅因为他们的崛起以及随后的衰落构成了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时刻之一,还因为雅各宾派试图创造一种基于美德共和国的模式的新的政治形式。友谊是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因此,雅各宾派的友谊观向我们讲述了许多东西,包括他们关于美德共和国的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对他们实际政治生活行为的重要影响。这篇文章将论证,友谊在雅各宾派的意识形态中有着复杂的作用,他们对友谊的暧昧态度让我们看到了在大革命最为激进的阶段,他们对革命身份和政治生活本质的焦虑。
如果我们纯粹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这段时期的政治史,我们就有可能忽视很多对革命者自身而言至关重要的事情。无论革命者是否公开承认过,他们和所有政治家一样,认为私人生活和个人关系是举足轻重的。不过,我们要审慎对待公共和私人的概念是如何构建此时期政治参与这一问题的,不能使用过于僵化的概念。事实上,关于18世纪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近期研究,倾向于强调公共和私人在18世纪的话语中表现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表明两者的互动比两者的界限更重要。在这种语境中,友谊跨越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人为鸿沟,从而帮助我们重新评估这两个范畴。
雅各宾派的友谊观
雅各宾派的友谊观若非自相矛盾,也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雅各宾派将友谊视为珍宝,认为它是人类联系的理想形式;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它是可疑的。雅各宾派沉浸于古典传统当中。在这些传统中,友谊被讴歌成一种类似于美德的品质。为朋友牺牲自己被看作一种崇高的道德行为。西塞罗的著作《论友谊》(On Friendship)就详述了友谊是美德之人的一个特征。“是美德,是的,让我再重复一遍,只有美德才能创造友谊、增进友谊、使友谊永恒。”西塞罗进而论证,“真正的”友谊建立在美德之上。正因如此,友谊不能被视为犯罪(包括背叛祖国的政治罪行)的正当理由。一个拥有美德的人是不会愿意教唆他的朋友做出这样令人发指的行为的。路易·德·圣茹斯特(Louis de Saint-Just)表达了友谊是构成美德共和国的核心的观点。他在《共和体制散论》(Fragments d’institutions r épublicaines)中认为,友谊可以将人们作为一个统一的祖国的成员聚集起来,并通过他们自己选择的、相互的社会纽带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圣茹斯特认为友谊是社会粘合剂,并希望友谊能有助于抵御公民社会的崩溃、确保祖国的安全。事实上,在理想的共和国中,所有人都深信真挚友谊的存在。“谁说他不相信友谊,谁就会被驱逐。”
18世纪后期的思想对雅各宾派的友谊概念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尤其是认为友谊毫无保留地呈现了自然美德、真诚情感、同情他者的卢梭主义。对让-雅克·卢梭而言,真正的友谊是发自内心的,是感情的外露。它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让人们为朋友许愿美好的未来。对卢梭而言,友谊担任了道德指南的角色,提供了一条通往美德的道路。他的小说《新爱洛漪丝》(La nouvelle Hélo?se)中的核心人物,特别是克莱尔与朱莉、圣普乐与爱德华勋爵,分享了一种美德的友谊。但卢梭也关注到友谊的黑暗面,即“假友谊”。“假朋友”是指滥用他人的信任和自然情感的人。一些雅各宾派也同样忧虑于虚假的友谊。它模仿美德,实际上却与美德背道而驰。
卢梭主义的自然美德思想,在博爱的革命原则中得到了延续。但友谊是私人的和个人的,是两人之间的关系;而博爱则是由普遍的仁慈所激发,且不偏不倚地赐予祖国的所有成员。革命者在公开提到“朋友”时,所引用的正是这种抽象的博爱品质,例如“宪政之友”(friends of the constitution,雅各宾派的正式名称)。雅各宾政府在1793年秋采用的“革命的你”(tu révolutionnaire)也象征着博爱、平等、仁慈。
此外,雅各宾派出于务实的考量,把友谊放在了首位。大革命始于突然爆发的自发性融合。在对革命的赞美和对革命进程的自豪感中,人们感受到了与他人的联系。在攻克巴士底狱一周年庆的联盟节上,这种与群体的联系感达到顶峰。但到了1793年,在战争、内战、恐怖统治的压力下,个体之间的信任开始瓦解。在这种状况下,关键要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国民公会成员马尔索(Antoine-Fran?ois Sergent Marceau)证明,真正的友谊从未像恐怖时期那样重要。他观察到,一个人不可能既是狎邪小人,又是所有人的莫逆之交。因为一旦横生枝节,没有美德的人就会对他所谓的朋友落井下石。人们早就注意到,在地方层面,雅各宾派的组织和恐怖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友谊网络。在国家层面上,友谊也在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对雅各宾派而言,友谊也有负面的涵义。第一,友谊可能会让人联想到旧制度下的庇护关系(patronage and clientage)。朋友们可能会利用彼此来提高社会地位。17、18世纪法国的宫廷文化与友谊中自私自利的方面尤为吻合。友谊是一种为参与者的共同利益服务的制度,这一理念是社会准则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相互的友谊、恩惠的交换构成了赞助制度的基石。
革命者发现这样的友谊存在悖论。这使得它很难与革命政治的理论兼容,却又无法与政治实践相分离。革命被有意识地描述成旧制度及其所代表的一切的对立面。然而随着革命者的掌权,有一些职位,尤其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位置需要填充。在某些程度上,革命本身成为一种职业发展道路,而拥有能够提供帮助的朋友成了“上位”的一种手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友谊可能被敌对者视为腐败和满足个人野心的手段,而这与革命原则是相悖的。
还有第二个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原因,即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友谊。对个体而言,友谊的排他性可以说是破坏了最高的革命理想:美德。对雅各宾派而言,沿着18世纪思想所铺设的路,政治美德是对公共利益的奉献。这不仅意味着将所有人的利益置于私人的自我利益与自我进步之上,还意味着那些希望在革命政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人应当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们的伙伴,甚至以牺牲个人与家庭、朋友的关系为代价。最高境界的爱不单单是针对亲密的人:它是针对整个祖国的。因此,私人关系与公共关系可能并不相容。显然,这给政治领袖带来了忠诚冲突的问题。这是一个经典的两难困境:虽然古人认为私人友谊是一种美德,但他们也认为最高的美德是爱自己的祖国。如果他的朋友背弃美德,那么他作为好公民就有责任反对这个朋友,从而保持对祖国的信仰。这种思想似乎支撑着罗伯斯庇尔为他抛弃德穆兰的行为进行自我辩护。当他在国民公会上发言,阻止丹东、德穆兰等人在国民公会上为自己辩护时,他把他们称为“为个人利益……牺牲祖国利益的人”。革命者必须把正直置于特定的友谊之前。罗伯斯庇尔自己,正是以这样的原则在友谊和革命之间作了选择。“我是佩蒂翁的朋友。当他被揭穿时,我抛弃了他。我与罗兰也有私交。他变成了叛徒,而我谴责了他。丹东想取代他们的位置,而现在,他在我眼里不过是祖国的敌人罢了。”国民公会的议员们在惊惧的沉默中听完他的发言,经过投票决定不经听证就把丹东派送入监狱。
还有第三个更为不妙的原因,即友谊在政治上是危险的。这指的是友谊与政治阴谋之间的联系。排他性的友谊网络与私人的聚会,可以成为反革命阴谋的遮羞布。在共和二年,对革命派别的所有重大审判,都大肆渲染朋友网络、非法派别、政治阴谋之间的所谓联系。政治派别的存在被视为不利于展现革命的公开透明。对雅各宾派而言,正如对所有革命者而言,不存在合法的政治反对派这一回事。从组织一个派别到发动一场阴谋,不过一步之遥。然而事实上,在共和二年,各派之间的分歧很小:革命领导者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大革命的前几年曾一同密切参与革命集会和俱乐部的活动。
显然,雅各宾派认为可疑的友谊实际上是通过私人渠道开展的政治事务。实施革命政治的合法场所是所有公民都可以进入的地方:革命集会、部门、委员会,以及至少在理论上对每个能够支付费用的人开放的俱乐部。相较之,友谊是通过个人关系和私人约定进行的,比如革命沙龙、私人晚宴、邀请家中、个人通信。例如,接受专设的晚餐邀请具有政治意义,因为这代表着一个融入某一派别的过程已然开始。因此,私人友谊对于政治网络或派别的形成和运作是不可或缺的。
吉伦特派与友谊
到了1792年秋天,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等人已经与雅各宾俱乐部断绝来往,转而彻底反对它(尽管布里索和罗伯斯庇尔之间的分歧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即1791年冬天在战争问题上的辩论)。他们成为被称为布里索派或吉伦特派(更为常见)的领导人。在1793年10月对他们中的21人的审判中,他们之间的联系受到了密切的审查。他们遭到指控,并不是因为他们吉伦特派的身份,而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友谊。所有被指控的人,无论对错,都被怀疑采取了反对雅各宾派的政治行动。但这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宣判一个人死亡的理由。在推行战争政策方面的难有作为或愚蠢无能,也不是判定一个人犯了叛国罪的理由。因此,雅各宾派发现,如果说吉伦特派的政治行动掩盖了反革命意图,能够更易于他们的辩证。雅各宾派利用吉伦特派友谊联系的证据支持自身论点,即吉伦特派实际上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反叛者联盟。据此,吉伦特派的友谊网络表明他们组建了一个政治派别或政党。指控他们的雅各宾派,继而用最虚无缥缈的论据,把这种友谊关系与吉伦特派是结党聚群的反革命分子、反对大革命的阴谋家的观点联系起来。这个问题就此引发了争议。历史学家迈克尔·J.西登纳姆(Michael J. Sydenham)在他那本有点讽刺意味的名为《吉伦特派》(The Girondins)的书中,否认了吉伦特派的存在(至少是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政党)。他的观点是,是雅各宾派回顾性地制造了关于吉伦特派的神话,即存在一个统一的政治派别,以便雅各宾派更易于非难吉伦特派是一个阴谋集团。卢纳(Frederick A. de Luna)反对西登纳姆的观点。他认为,在雅各宾派取胜之前,就存在一个吉伦特派的派系观念。在1792年4月战争爆发和“吉伦特派内阁”成立之后,人们就不时地提及这个派别团体的成员。从国民公会第一次会议开始,就有几个术语被相当普遍地用来指代这个团体。它的成员们被不同程度地称为“吉伦特派”(the Girondins)、“布里索派”(the Brissotins)、“罗兰派”(the Rolandins)、“政府成员”(the men of state),以及最常见的“此派别”(the faction)。
因此,到1792年9月,关于吉伦特派的派系联系观念已经确立。但是,友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吉伦特派之间政治联系的形成(既包括团体内部,也包括外界对吉伦特派身份的看法)?仔细研究过吉伦特派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友谊网络对他们的政治活动至关重要。由此,西登纳姆总结道:“从证据中得出的唯一合理的结论是,在缺乏有组织的政党时,个人友谊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的政治联系形式。”加里·凯特(Gary Kates)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同时阐述了这种友谊文化的政治内涵:18世纪末,派系的核心不在国家立法机构,而是在立法机构之外的友谊网络和个人联盟当中。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政治,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与旧制度类似,因为它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在国民公会之外,有一个不太正式的机构的网络,包括沙龙和俱乐部,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们在这里建立了对其职业生涯至关重要的个人关系。历史学家至少能够在布里索及其朋友的联系中找到吉伦特派的中心。
我们能够确定几个友谊“圈子”:一个是吉伦特派的代表们之间的“圈子”,一个是罗兰派与里昂派的代表们之间的“圈子”,一个是那些来自马赛的代表们之间的“圈子”,还有一个是与布里索的关系不太密切的另一个“圈子”,即围绕着亨利·格雷古瓦神父和孔多塞侯爵的团体。这些友谊圈子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与布里索有所联系。吉伦特派的朋友和敌人都承认,若是吉伦特派有领袖的话,那个人就是布里索。据说,布里索是吉伦特派参与的社交聚会的生命和灵魂。绝大多数证据表明,布里索充分利用友谊来拓展他的政治影响。他自己在《回忆录》中坦言:“我总是喜欢把我的朋友聚在一起。”
似乎从1792年春“吉伦特派内阁”或“爱国派内阁”成立开始,人们就开始怀疑吉伦特派之间的友谊关系为不法行动提供了便利。让-玛丽·罗兰(Jean-Marie Roland)和艾蒂安·克拉维埃(Etienne Clavière)从未在革命政治中担任公职,却被任命为部长。罗伯斯庇尔等人认为,这是他们共同的朋友布里索干预的结果。革命组织的职务任命似乎让人联想到旧制度的庇护策略。这加剧了雅各宾俱乐部在战争辩论中已经出现的分裂。显然,罗伯斯庇尔、让-保罗·马拉(Jean-Paul Marat)等人觉得布里索派已经“售完”了职位。怒火中烧的罗伯斯庇尔斥责布里索利用他的《法兰西爱国者报》(Le patriote fran?ais)为其朋友在新部门中争取职务,从而规避了宪法,因为宪法规定布里索作为代表不能以本人名义获得部长职务。罗伯斯庇尔谴责此种做法是腐败行径。
早在大革命前,布里索就与罗兰先生、罗兰夫人结下友谊。布里索在雅各宾派中的政敌,怀疑他利用与罗兰(现为内政部长)的友谊来操纵政治决策和赞助,并为其他朋友争取职位。罗兰和他的妻子在盖内戈街的住所被认为是吉伦特派的重要基地。1791年,罗兰夫人就是在这里举办了她的政治沙龙。在沙龙上,受邀者都被她迷人而强大的个性所吸引。罗伯斯庇尔本人也曾是这些聚会的常客,是罗兰夫人和布里索的朋友。但吉伦特派政府成立后,他就断绝了这些私人联系,拒绝了罗兰夫人的进一步邀请。一旦罗兰成为部长,这些聚会的政治性质就发生了改变,与罗兰一家人的友谊也便有了新的意义。因为现在罗兰夫妇能够提供赞助,这让人想起旧制度的政治的方式。
一些雅各宾派似乎希望借助与罗兰夫妇的忠诚友谊而得到晋升。罗兰夫人曾讲述当时还未熟识的弗朗索瓦·罗贝尔和他的妻子如何与新部长攀交情。她说,在罗兰被任命为部长后不到24小时,罗贝尔夫人就出现在她家门口,并对她说:“你丈夫被任命为部长了;爱国者们必须互帮互助,我希望你不要忘记我丈夫的职位。”罗贝尔并不满足于一个小职员的职位,他想要君士坦丁堡大使的位置。外交部长迪穆里埃(Charles-Fran?ois Du Perrier Dumouriez)认为罗贝尔完全无法胜任这个职务。但罗贝尔感到十分沮丧,后来与跟随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派结盟,并背叛了他曾经的吉伦特派的朋友们。
作为部长的妻子,罗兰夫人每周都会举行晚宴,邀请其他部长和选定的代表们参加。她对这些晚宴的描述表明,其目的是扩大围绕罗兰和布里索的网络的力量。为了鼓励男性社交和政治网络的发展,她自己尽可能地避免发言。
迪穆里埃对这些晚宴的看法则截然不同。他声称,其他部长(即除了吉伦特派的部长克拉维埃和罗兰本人之外)对被束缚于吉伦特派的网络中感到不满:“周五的部长晚宴变成了派系的晚宴。在晚宴上,吉伦特派的成员想强迫部长们接受他们对政策的建议和指导。”他断言,其他部长心照不宣地不会把他们的部长简报带到这些晚宴上讨论。他还声称,当他提醒罗兰注意他与朋友的政治联系时,这位内政部长“宣称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委员会里,如果没有他的朋友们的建议,他什么都做不了”。
我们应谨慎对待迪穆里埃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写于事件发生很久之后,而且作者急切地想否认与吉伦特派的任何纠葛。但其他证据显示,迪穆里埃和吉伦特派之间的关系在部长任命后不久就疏远了。吉伦特派认为迪穆里埃对罗兰辞职负有责任,此后两者之间的敌意彻底爆发。布里索的回应是给迪穆里埃写了一封特殊的公开信,发表在1792年6月的《法兰西爱国者报》上,信中否定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在他的信中,他使用了卢梭主义的语言,即轻信他人的美德之人被虚假的友谊所背叛。他知道这种语言是他的听众所熟悉的,并希望这样的描述能支撑起他作为一个有美德之人的形象,并使他与迪穆里埃保持距离。
1793年春,与迪穆里埃(时任法国的主力将军)的友谊已经成为对吉伦特派最不利的指控。3月,迪穆里埃试图带领自己的部队进攻巴黎;当进攻失败后,他逃到了奥地利人那里。这次背叛对几乎一直在支持他的吉伦特派而言是致命的。当他的背叛行为被揭露时,这些吉伦特派争辩说,他们和许多雅各宾派一样被迪穆里埃欺骗了。这并不能打动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决意把与迪穆里埃共谋的罪名扣在吉伦特派的头上。但他没有办法佐证这项阴谋——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罗伯斯庇尔和其他雅各宾派给吉伦特派安上莫须有的罪名,根据美德语言的政治逻辑,指控迪穆里埃和吉伦特派之间的友谊(这种友谊在本质上是私人和个人的)存在阴谋的联系。
虽然布里索与迪穆里埃之间的友谊受到了雅各宾派的审查,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两者间存在真正的温情。不过到了1792年10月,当迪穆里埃重登将军之位时,大概是出于政治上的便利,双方又恢复了合乎情理的友好关系。这之后,布里索给将军写了至少三封私人信件。布里索用友谊的语言来拉拢迪穆里埃,使得迪穆里埃在布里索寻求帮助时更难拒绝他。但这些信的存在足以进一步损害布里索的声誉,正如布里索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几个月后,布里索在被捕后坚持说,自从1792年6月他们的友谊公开破裂后,他与迪穆里埃“没有任何通信,没有任何特殊关系”。
1793年3月31日晚,迪穆里埃被证实叛国的消息传到了巴黎。4月3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中起身,不仅指斥迪穆里埃,还斥责他的“帮凶”。他利用这个机会把布里索牵扯到将军的背叛行为中,把友谊当作连带责任的标志。
布里索随即否认与“迪穆里埃的罪行”有任何串谋,否认与迪穆里埃有任何个人关系,否认在他被任命为部长时对迪穆里埃有任何帮衬。随后,布里索以书面形式否认他的友谊与他的野心之间存在任何联系。他的部分辩护旨在反驳他利用友谊为自己或朋友谋取利益的指控。
布里索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卢梭主义的“孤独者”,与国民公会中的少数人相识。这并不符合他的社交能力及其广泛的政治友谊网络。这也不符合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喜欢互相介绍他的朋友们认识。显然,这是为了抵制对他利用友谊谋求政治地位的指控。
1793年5月17日,德穆兰发表了一篇题为《大革命秘史散论》(Fragment de l’histoire secrète de la Révolution,后来被称为《布里索派的历史》,L’histoire des Brissotins)的文章,对布里索及其朋友们造成毁灭性打击。在文章中,他把大革命的历史改写成一场布里索派筹谋已久的阴谋。德穆兰对布里索虚伪地宣称他只让不到6个朋友担任过公职的说辞不屑一顾。他抓住布里索在8月10日之后写给罗兰夫人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在罗兰的文件中发现的密封文件,随后被移交给公安委员会。在信中,布里索为错过晚餐而道歉,但他给她(转告她的丈夫和弗朗索瓦·伦特纳斯)寄来了“一份爱国者的职位的名单”。雅各宾派非常重视这一指控:布里索被捕后,这封定罪的信被用于审讯他。布里索被问及他是否曾向罗兰提供过一份由他安排职位的个人名单。他承认他提供过,但试图为自己开脱,声称是罗兰要求提供的。
在信件、回忆录、审判中,吉伦特派的领袖们试图否认他们组建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派别,更不用说筹划一个阴谋了。他们声称,他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仅仅是基于美德。如果他们相互之间建立了友谊,那是因为他们钦佩彼此的正直,而不是因为他们寻求晋升或渴望推动一个阴谋。维尼奥(Pierre-Victurnien Vergniaud)做了记录,试图在自己的审判中为自己及其朋友辩护。关于他是否是一个派别的一分子,以及“是否存在一个阴谋”的问题,他写到,曾经存在“基于尊敬而形成的关系,但从未有过意见一致的联盟”。布里索、罗兰夫人、比佐(Fran?ois-Nicolas-Léonard Buzot)、卢韦(Jean-Baptiste Louvet)等人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认为是友谊和美德将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描绘了一幅卢梭主义的画像,即一个与美德之爱、同胞之情、献身革命相联系的群体。克洛德·福谢(Claude Fauchet)和卢韦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同样,布里索在他的《回忆录》中否认在他努力提拔朋友的过程中有任何物质利益或晋升期望。他对他们的慷慨大方恰恰证明了他的情感和美德。他说,像卢梭一样,他只希望做有益的事。
因为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证据证明吉伦特派是反革命分子,所以诬陷他们的友谊在指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这是一场政治审判,在招致雅各宾派的敌意方面,政治介入将是一个比友谊更为严重的因素。因此,布里索的朋友苏克一直支持他并与他一起逃到穆兰,在那里,他们一起被捕。尽管苏克被监禁到热月政变之后,但他逃过了一劫。
罗伯斯庇尔派与友谊
在一定程度上,罗伯斯庇尔本人因为攻击布里索在政治生活中利用友谊的行为而赢得了“不可腐蚀者”(Incorruptible)的名声。但是,当罗伯斯庇尔与簇拥着他的团体掌权后,他们面临着与吉伦特派同样的问题:友谊的政治利用与革命美德如何兼容?在将个人友谊与政治责任相联系的问题上,罗伯斯庇尔比吉伦特派要谨慎得多,他也担心被人发现他这样做。毫无疑问,他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将自己和山岳派与吉伦特派的政治方法区分开来。但是,调和私人友谊与公共美德的内在矛盾实际上是无法克服的。
早在1791年,罗伯斯庇尔就有很多密友来拜访他在迪普莱(Maurice Duplay)的住处。但自从他进入救国委员会之后,这个圈子就大大缩小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就更加谨小慎微了。许多评论家指出,此时要联络罗伯斯庇尔是非常困难的。除了在国民公会、救国委员会或参与雅各宾派活动之外,罗伯斯庇尔几乎一直窝在家里,不与外界接触。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周,除非是为了试图修补与其他委员会成员的关系(这些关系在热月政变中行将崩溃),他不再出席委员会组织的活动。只有菲利普·勒巴(Philippe Le Bas)、路易·德·圣茹斯特、乔治-奥古斯特·库通(Georges-Auguste Couthon)、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和菲利普-米歇尔·博那罗蒂(Filippo-Michele Buonarotti)还经常去他家拜访。
缺乏可信赖的朋友造成了相当大的政治困难。罗伯斯庇尔派的问题可以用圣茹斯特的实用主义的观点来概括:“无朋友,无治国。”这种想法违背了美德的信条,却反映了政治现实。在罗伯斯庇尔派下台后,为了寻找他们的罪证,库尔图瓦(Edmé-Bonaventure Courtois)查阅了他们的个人文件,抓住了圣茹斯特的这句话作为控诉罗伯斯庇尔派政治不道德和阴谋本质的证据。
在私人笔记中,罗伯斯庇尔写了一份“拥有或多或少才能的爱国者”的名单。这些人都是他信任的人,可以担任政治职务。他们在行政部门里任职,尤其是在军队管理部门、战争部门、国民公会(在清除埃贝尔派之后,国民公会和革命法庭的职位主要由罗伯斯庇尔派提名的人担任)、革命法庭。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与罗伯斯庇尔或多或少有私交的人(不过不是密友,因为罗伯斯庇尔没必要把他们的名字写在这样一份名单上)。少数人是由罗伯斯庇尔信任的人推荐的,比如“圣茹斯特的姐夫、精力旺盛的爱国者、纯粹的、进步的”。成为公社的公职人员的帕扬(Claude-Fran?ois Payan)(罗伯斯庇尔派)也向罗伯斯庇尔做了推荐。名单上的一些人反过来又推荐了其他的人。一些来自里昂的爱国者也进入罗伯斯庇尔的网络。
其他人则成为救国委员会的一员,据称其中一些人取代了人数更多的丹东主义者,因此这些人也是被怀疑的对象。也有一些人成了警察局的一员。警察局在救国委员会的支持下运作,但它的存在造成了两个委员会之间的分歧,因为罗伯斯庇尔利用它接管了一些被视为公安委员会特权的监视职能。后来,警察局被攻讦为罗伯斯庇尔派“阴谋”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热月党人操纵了这种充满敌意的说法。历史学家阿纳·奥丁(Arne Ording)指出,警察局的活动对救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开放,他们也签署了授予警察局职务的命令。但警察局是罗伯斯庇尔派的特殊产物。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毕竟警察局的一些职员与罗伯斯庇尔派有私交。这些职员得到了来自不同省份的任命。他们的职责包括调查旧贵族,告发那些涉嫌腐败、参与密谋、尸位素餐的公职人员,传递关于公共精神的信息。
在某些方面,罗伯斯庇尔的爱国者名单看起来就像旧制度下的被赞助者的名单。但这些人并不是从通常意义而言的社会精英中选拔出来的。一些人几乎可以说是目不识丁,比如朗贝尔,他是埃托格(Etoges)的一个羊倌。名单上的另一个小人物是吉兰·维勒(Guilain Villers)。维勒在热月政变中强调,他只是圣茹斯特的仆人,不过他似乎也在政治上受雇于圣茹斯特。库尔托瓦后来在介绍罗伯斯庇尔的名单时,提到了这些人在社会上的平庸,并称这些爱国者是“无知的人,腐败的人,霸占公职”。
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似乎都选择了他们认为是两袖清风的人。对他们两个人而言,这是政治任命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这一政策不仅仅是将他们与吉伦特派区分开来的一种策略——尽管这些策略在此是一个问题,而且两人都意识到革命给政治领袖的公众形象带来的重要性。不过,脂膏不润也是他们认定自己是有德行的革命者的核心。他们任命的一些人确实把拒绝贿赂作为一种荣誉。例如,军队管理人员加托和图里耶,谴责了一个向他们提供5万欧元贿赂的店主。但并非所有的罗伯斯庇尔派都如此恪守道德。
进入名单的关键因素是罗伯斯庇尔(或圣茹斯特)是否信任他。向罗伯斯庇尔核心圈介绍和推荐成员似乎在消除罗伯斯庇尔的戒心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这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因为在雅各宾俱乐部或巴黎的政治生活中,不乏有人自称爱国者。但是,怎么能仅仅因为一个人在适当的政治时机说着充满美德和爱国主义的话,就相信他是正直的呢?雅各宾派不断提到面具、欺骗、“爱国主义的伪君子”。
在革命政治的迷宫里,只有知根知底的人才能被认为是有美德的人。罗伯斯庇尔在制定一份亲信名单时,采用了他所厌恶的旧制度下大臣们的政治策略。结果证实,这一手段行之有效。但问题是,他没有足够多的朋友来填补所有职务空缺。事实上,在最后几个月里,罗伯斯庇尔派成员所担任的职位数量增加了一倍或两倍。的确,罗伯斯庇尔曾痛苦地抱怨,很难找到可靠的政治管理者。他希望这些人的实际的美德(在献身于公共利益和抵制金融或政治腐败的意义上)与他们精通的修辞一样完美。
并非所有罗伯斯庇尔信任的人都是政治美德的典范,比如维兰·德奥比尼(Vilain d’Aubigny)。他是圣茹斯特在布莱朗库尔的一个朋友。不过他比圣茹斯特更早出现在国家政治的舞台上。他曾于1792年8月10日被公开指控从王家仓库偷窃东西。多亏了罗伯斯庇尔,德奥比尼才被任命为战争部长布硕(Jean-Baptiste-No?l Bouchotte)的第二助理。但瓦兹的波登(Fran?ois-Louis Bourdon de l’Oise)和比约-瓦伦(Jacques-Nicolas Billaud-Varenne)重新提起了对他的指控,反对罗伯斯庇尔提名他担任这一职务。9月30日,圣茹斯特都在国民公会上为他们的保护对象(protégé)说情。圣茹斯特形容德奥比尼是“一个好人。他是我的同乡。我曾经目睹他变卖财产来赡养他的母亲,他已经供养了她十五年……他是我认识的最好的朋友、最热情的爱国者、最可敬的公民”。国民公会回应了这些热烈赞扬的证词,确认德奥比尼为布硕的助手。但是,德奥比尼一踏入战争部,就卷入了埃贝尔派和丹东派之间争夺主导权的斗争。在之前,他曾经是丹东和代格朗蒂纳(Philippe-Fran?ois-Nazaire Fabre d’Eglantine)的朋友。现在他改变了立场,投靠文森特(Fran?ois-Nicolas Vincent)和龙森(Charles-Philippe Ronsin)。但是在埃贝尔派被逮捕时,他又一次转换了阵营。他对龙森的求助保持沉默,并最终决定他是“罗伯斯庇尔的人”。几个月后,有人对德奥比尼提出了新的指控,这次是说他参与欺诈军队合同的行动。波登要求将他送上革命法庭。罗伯斯庇尔再次为他公开陈情,避免他被送上法庭。然而,德奥比尼并没有回报这份恩情。热月政变后,他谴责了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否认自己曾是他们的朋友,就像他以前采取的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即与垮台的雅各宾派的伙伴撇清关系一样。一些罗伯斯庇尔曾经的追随者也跟着否认与堕落的“不可腐蚀者”及其朋友存在任何关系。
但也有人坚守这份友谊,比如加托。他在热月政变时被捕,在监狱里呆了一年,等待正式指控。当他被允许用一句话来解释他的监禁时,他感到非常愤怒:“阴谋家圣茹斯特的朋友。”虽然这不可能缩短他的监禁时间,但加托还是给他的指控者写了一份慷慨激昂的文章,为他童年时期的朋友辩护。他把圣茹斯特描绘成一个有美德且感性的人。他并不认为圣茹斯特是指挥雅各宾派恐怖活动的主要领导人物。加托不思悔改。他也否认了指控圣茹斯特是阴谋家的说法。加托抗议说,是因为他与圣茹斯特的友谊,他才被认定是阴谋家。这体现了笔者最初的看法:德穆兰感到困惑的是,他忠于朋友是如何导致他自己因阴谋的指控而濒临死亡的。对于大革命中承上启下的各个派别而言,这就是友谊最终的结果:在忠诚和背叛之间的孤独选择,无论哪种选择都有可以预见的后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共和二年的雅各宾派友谊的含义,与传统意义上的友谊观(一种自我提升的手段)截然不同。实际上,正如1793年夏天与布里索的友谊、1794年春天德穆兰与丹东的友谊是通往断头台的捷径一样,1794年夏天与罗伯斯庇尔的友谊,也不是通往类似于旧制度特权的手段——它是极其危险的。罗伯斯庇尔的很多朋友为他们的忠诚最终付出了代价。他的一百多个朋友、同事、伙伴,包括巴黎公社委员会的成员,在热月的10日、11日、12日被处死。在雅各宾派的统治下,友谊可能是致命的。
结 语
研究雅各宾派之间的友谊网络,带来了对其政治运作的新认识。友谊在革命政治中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它的影响是复杂的,且跨越了革命政治的私人和公共层面。友谊的观念被革命的意识形态所唤醒,但它也在日常政治领域发挥着实际的社会功能。通过研究雅各宾派交往的真实情况及其对友谊的观念,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革命政治的运作方式。
首先,我们意识到友谊是幕后的政治交易、网络、赞助、职位分配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吉伦特派和罗伯斯庇尔派(更多表现为不情愿)都热衷于用朋友来填补政治和行政职位。但是,革命者之间的个人友谊与政治美德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个人的友谊是私人的、排外的,通常对个人有利。这与革命政治理应是公开透明、促进所有公民利益的思想背道而驰。革命派系的成员间确实有友谊关系,尽管这种关系的程度被夸大了,而且在对各派的审判中被赋予了邪恶色彩。吉伦特派的内部圈子因友谊关系(特别是与布里索的关系)而团结在一起。这并没有使吉伦特派成为阴谋家,但却使他们更容易受到敌人的指控。
在对主要派别的指控中,友谊网络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人们不仅仅因为他们与主要政治人物(如布里索)的友谊而遭到指控,更多时候是因其政治行动而遭到指控。但是,对友谊的指控把不同的人群打造成一个统一的政治派别,进而建构出一个阴谋团体。友谊可以被怀疑,因为它占据了私人生活的领域,因此不受革命透明度的影响,且始终抵制将其纳入革命意识形态的做法。
最后,友谊不仅仅是一种说辞或一种话语。在共和二年,政治的选择生死攸关:选择站队哪个派别?选择忠诚于谁?选择背叛谁?友谊在所有这些选择中都发挥了作用。意识形态并不是决定政治阵营的唯一因素。对革命友谊的研究有助于我们重构个人动机的复杂性,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雅各宾政治中剑拔弩张的关系。虽然友谊网络无益于革命政治的理论,但对革命政治的实践却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舒建军 马毓鸿
译 者:李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