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精英主义决策模式是民主理论和区域一体化理论的补充。
关键词:移民政策;移民危机;德国;匈牙利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匈牙利和德国的移民政策,尤其关注2015—2017年间精英主义政策议程制定和实施的法律、事实和话语层面的精英作用。从理论上讲,精英主义决策模式是民主理论和区域一体化理论的补充。在方法论上,本文呈现了一项比较分析,旨在解释处理移民方法相反的两个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差异。确实,虽然匈牙利和德国通常被对立为两个完全不同的移民政策范例,但以精英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在这两个案例研究中显示出令人费解的差异对称性。虽然政策结果各不相同,但行为和叙事模式却有明显的凝聚力,表明政治精英是移民政策形成和实施的主要驱动力。在建立理论基础后,本文比较了匈牙利和德国政府的国家立法、接受的移民配额以及官方叙事。通过案例分析,可以重新解释看似矛盾的移民政策,从而为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解决此问题提供新的方案。〔李光辉译〕
作者:莫妮卡·加布里埃拉·巴托谢维奇(Monika Gabriela Bartoszewicz)在捷克共和国布尔诺马萨里克大学政治科学系从事社会科学教学工作。她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课程,研究重点是欧洲人皈依伊斯兰教的潜在恐怖主义威胁。她的研究于2009年获得了罗素信托奖(Russell Trust Award)。2011—2013年,她被任命为意大利威尼斯欧洲校际中心国际关系研究员。详情见其个人网站(www.bartoszewicz.mg)。Email:mgbartoszewicz@gmail.com
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1年第4期P29—P45
欧洲移民危机
由于前所未有的非欧盟国家非正规移民的大量涌入(Greenhill 2016),对于欧洲联盟(欧盟)及其成员国而言,2015年是决定性的一年。欧盟无法形成和维护共同移民政策的事实,是决定其外部和内部动态的现象之一(Andersson 2016; Bojadzijev and Mezzadra 2015; Scipioni 2018)。可以说,不同成员国的民粹主义浪潮,欧洲人的欧盟怀疑论情绪空前高涨,以及英国脱欧公投的意外结果等事件,可以用所谓欧洲移民危机的影响来解释(Brubaker 2017; Kneuer 2019)。事实上,可以说这种现象是最近欧盟历史上最起作用的工具性和宪制性因素之一(Birchfield and Harris 2018)。
为什么尽管欧盟委员会提出了解决方案,欧盟各成员国却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尽管在国际框架同质的情况下,各国移民政策有时竟会有根本性的不同,如何解释这些差异?为了理解有关这种令人惊讶的多样性的争论和逻辑,本文提议通过精英制定政策模式(elite model of policy-making)的视角来探究这一问题。精英模式假设社会被划分为拥有权力的少数人和没有权力的很多人,所以,政策与其说反映了人民的需求,不如说是反映了精英们的利益、价值观和偏好。相应地,在塑造大众对有关政策问题的舆论方面,这种模式将核心因果引力赋予了精英。因此,政策并没有反映群众的需要,而是反映了精英集团无处不在的利益(Dye 2013)。
虽然本文没有试图建立理论,但对理论适用性的探索旨在突出精英阶层与政策制定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精英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发挥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它来理解移民政策结果的格局。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以精英为中心的政策制定进行解释,增进对当前有关欧盟成员国移民政策争论的理解。为此,本研究明确聚焦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的角色,并涵盖了从2015年上半年欧洲难民危机开始到2018年3月第四届默克尔内阁宣誓就职(Deutscher Bundestag 2018)和第三届欧尔班内阁任期将满(Mischke 2018)这段时间。从方法论上讲,以下分析是“最相似而结果不同”(MSDO)项目的研究设计(Berg-Schlosser and De Meur 2009),旨在解释两个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差异,尽管它们有义务保持统一战线,但它们在处理移民和边境政策方面的做法却截然不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匈牙利是本研究的主要分析对象,因为在欧盟总体移民政策的背景下,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对待移民方式。选择德国,是因为其激进的亲移民立场,而匈牙利入选,是因为其坚定的反移民政策。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与话题相关的关键术语在政治和大众话语中均被歪曲或不恰当地概括。出于这一原因,我努力保持概念的有效性,在下文中将采用国际移民组织(IOM 2018)对“移民”和“难民”的定义。最后,“第三国”指既非欧盟成员国也非申根区成员国的国家。
本文结合了两种方法:比较案例分析和因果过程追溯。后者主要被认为是一种单一案例研究方法,之所以使用它,是因为它可以更好地理解单个案例中因果关系的性质(Beach and Pedersen 2013, p.5),从而有助于建立用于比较的共同证据基础。随之,比较分析可以将推论并置,澄清不同案例的变量之间的关系,以确定所研究的变化的关键因素。选择这些案例的具体目标,是使结果(Y)呈现较大差异,同时使它们的起始位置(X)彼此尽可能接近。
比奇和佩德森(Beach and Pedersen 2013, p.11)所述的以案例为中心解释结果的过程追踪法,被用来作为解释“特别令人困惑的历史结局”的最有用工具。以案例为中心的方法,其雄心是“对某种特定结局进行最低限度充分的解释,这种充分性被定义为解释了结局的所有重要的方面,而不存在多余的部分”(Mackie 1965; 参见Beach and Pedersen 2013, p.18)。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种方法的因果机制是在比通常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因此将产生所讨论结局的因果机制中的系统性部分和(随案例而不同的)非系统性部分结合在一起,从而可以采用双聚焦的(bifocal)观点来解释“内部”和“之间”的观察结果(Reuchamps 2015, p.4)。这种比较也可以作为对隐含因果关系的一种合理性探究,因为系统的、结构的和文化背景对最终的政策决定有着相当大的影响(Bemelmans-Videc, Rist and Vedung 2011, p.13)。
接下来,在简要的理论概述之后,本文从比较的角度对政策制定进行了精英论的解释。在分析精英在精英主义政策议程设定和政策实施的法律、事实和话语方面的作用时,为了指引有关分析,本文探讨了三个标准:(1)在其与欧盟共同政策保持内在一致性的背景下,将德国和匈牙利的国家立法进行比较;(2)着眼于欧盟重新安置计划,将德国和匈牙利接受的移民配额并置分析;(3)针对所采取的政治解决方案的理由,仔细考察匈牙利和德国政府的官方叙述。欧盟以及德国和匈牙利政府的当前政策文件,包括各种报告和分析、政策论文、工作文件、当前立法、法案、官方统计数据、声明和公报等,被用作分析的主要资料来源。媒体和非政府人士的讲述用作支持这些分析的资料。从三个方面将这两个案例研究并列,可以通过将国家政治精英确定为两国移民政策形成背后的主要推手,解释国家移民政策的差异和特质。随之,本文在最后一部分表明,在这两个案例中所使用的手段和机制的相似之处是惊人的,这确实互相反映出两种情况下的差异之间存在着令人震惊的对称性。
精英需要
最近的欧洲移民危机重新唤醒了对政治和社会的原有精英主义解读,特别是在反移民民粹主义言论突然盛行的背景之下。因此,本文采用由维尔弗雷多·帕雷托(Pareto 1916)和加埃塔诺·莫斯卡(Mosca 1939)提出的被称之为“精英理论”的思想体系作为分析的主要基础。同时,我们还辅之以区域一体化理论。精英理论的关注重点,是作为主要政治行为体的精英,这套理论后来经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 1971, 1989)、乔瓦尼·萨托里(Sartori 1987)、G.洛维尔·菲尔德和约翰·希格利(Field and John Higley 1980)等人的发展,被置于民主理论的更广大背景(特别是通过竞争性选举选拔和约束国家领导人和精英的语境)之下(Schumpeter 1942)。这三种成分,构成了本文的理论三角的三个关键点。
正如T.B.波托摩尔(Bottomore 1993)指出的,“精英”一词起初说的是一种特别好的商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发展成为用来指一个界限清晰的社会群体,由“凭借其在强大的组织和运动中的战略地位,能够定期和实质性地影响政治结局的人士”(Higley and Burton 2006, p.7) 组成。精英可以以类别划分,也可以以层次划分,这意味着他们还可以分成不同的群体(例如,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并在不同(例如地方、国家、国际)的层面上形成独特的网络。因此,精英一词首先让人想到的是高层政治人物、国家机构负责人、商业大亨和管理者、有组织的劳工领导人、媒体大亨和相关群众运动领导人,还包括政府、商业和军事领导人,以及政党、专业协会、工会、媒体集团、主要利益集团和著名的宗教、教育和文化组织的领导人(Best and Higley 2010)。不过,为了在理论丰富性与分析清晰度之间保持均衡,本文将“精英”等同于个人,而不是群体。此外,还将“精英”等同于在权力结构中处于关键地位的个人,以及塑造国家政策总体方向和目标(而不是具体细节和具体目的)的能力。
在当下,国家政治精英只是被定义为“具有重大决策权的个人和相对有凝聚力和稳定的小群体”(Higley 2018, p.27)或“由具有重大决策权的个人和小型、相对有凝聚力和稳定的群体组成的网络”(Pakulski 2018, p.12)的众多精英群体之一。国家一级的当代政治精英拥有选举产生的授权,在其人口当中具有相对的多元性和代表性,即便是在民主制度内,他们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尽管不具有决定性,但也仍然是相当大的。安德拉斯·科洛申尼( 2018, p.41)认为,根据精英主义决策模式,“大型组织和民族国家总是会产生陡峭的权力等级和政治精英——个人和较小的、相对团结、稳定的群体,他们拥有不成比例的权力,可以影响组织或国家的结局”。那些认可新精英主义(neo-elitist)对政治的理解的人,遵循了前面提到的维尔弗雷多·帕雷托提出并由罗伯特·米歇尔斯(Michels 1962)详细阐述的论点,即被理解为由人民来统治的民主,是一种虚幻的幻觉。新精英主义认可的是一种程序性民主,它将民主的形式与基本上自主的政治领导人和大部分自选产生的精英调和起来,演变成一套间接民主的理论,承认这种不对称性,同时减少了经典民主学说与经典精英理论之间的截然对立。
2018, p.41)认为,根据精英主义决策模式,“大型组织和民族国家总是会产生陡峭的权力等级和政治精英——个人和较小的、相对团结、稳定的群体,他们拥有不成比例的权力,可以影响组织或国家的结局”。那些认可新精英主义(neo-elitist)对政治的理解的人,遵循了前面提到的维尔弗雷多·帕雷托提出并由罗伯特·米歇尔斯(Michels 1962)详细阐述的论点,即被理解为由人民来统治的民主,是一种虚幻的幻觉。新精英主义认可的是一种程序性民主,它将民主的形式与基本上自主的政治领导人和大部分自选产生的精英调和起来,演变成一套间接民主的理论,承认这种不对称性,同时减少了经典民主学说与经典精英理论之间的截然对立。
最重要的是,与新古典主义民主理论中关于政治过程的自下而上讲述不同,民主精英主义将政策设定、制定和执行的过程描绘为由政治领袖激励和指导。政策不是由公民提出,不是通过选民的偏好传递自主民众的意志并由他们的代表转化为政治实践,而是由领导人提出,并通过说服(包括煽动和形象操纵)强加于公众,这种做法已经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套用一句俗语就是:塑造政策的是精英,而不是民众要求。这就是精英论研究方法能够把握政策制定关键方面之所在,而其他研究方法却看不到。
这种对以政治领袖和精英为主要行为体的有组织权力结构的阴暗理解,一方面对民主在面对煽动性民粹主义时的可行性提出质疑,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更加仔细地审视政治话语,即构思、解释和证明所选择的政治行动路线的言语行为(Buzan,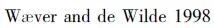 )。这些言语行为(speech-acts)可以被概念化为隐藏在不同话语框架中的论点。如果我们同意政治现实是以话语方式建构的,那么具体的结构就构成了这种话语中的意义生产(meaning production)的关键部分,并在文本中得以实现(参见Wodak 2008)。
)。这些言语行为(speech-acts)可以被概念化为隐藏在不同话语框架中的论点。如果我们同意政治现实是以话语方式建构的,那么具体的结构就构成了这种话语中的意义生产(meaning production)的关键部分,并在文本中得以实现(参见Wodak 2008)。
戴维·扎里夫斯基将论证(arguments)理解为话语情境中“试图影响他人而推动的主张”和“为支持主张而提出的理由”(Zarefsky 2014, p.2)。论证是“说话和写作的形式,我们首先要将其与叙事分开,但其中的叙事结构却是固有的”(Hofmann,Renner and Teich 2014, p.2)。以此方式定义的论证,也许可以纳入政治叙事理论(参见Czarniawska 2004; Fischer 1984; Hofmann,Renner and Teich 2014),作为从话语上建构的政治现实的一种基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在利益冲突的政治舞台上,论证具有解释、辩护、说服不同政策选项或使之合法化的威力。叙述和论证与其他的选择相竞争,“总是与要作出的一般决定或判断的视角相竞争”(Llanque 2014, p.14)。对于隐藏在叙事框架之内的论证的建构性威力,最普遍的反对意见来自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哪个政治单元(某个国家)是如此单一和同质,以至于“合理的故事剧目”中的局外人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不过,沙尔尼亚夫斯卡断言,而且我也认为,尤其是在代议制民主的背景下,情况就是这样:“出于解释目的,在任何时候都用一种占主导地位或普遍的……主流……叙事风格讲话,是有意义的”(Czarniawska 2014, p.6)。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说,就以精英为中心的移民政策研究方法而论,所分析的两个国家的政府叙述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如此,眼前的问题还存在有待考察的第三个方面,即区域一体化理论。韦伯和熊彼特曾致力于在精英人士的存在与民主的实际运作之间建立一种理论上的调和(Pakulski 2018, p.11),但问题是如何解释像欧盟这样复杂的国际参与者的多层次治理。欧洲一体化进程过去和现在都是基于欧洲精英阶层的高度欧洲化并由其推动的(Best, Lengyel and Verzichelli 2013, p.9)。确实,正如我在其他场合所论述的那样(Bartoszewicz 2014),欧洲化是一个精英驱动的工程。尽管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国家精英们倾向于欧洲统一的政策,以及支持将主权要素移交给更高级别的欧洲多级治理,但这又让读者想知道,为什么国家精英们会奉行不同的战略,特别是在移民政策这种关键的领域。在此背景下,胡格和马克斯(Hooghe and Marks 2009)提出了一个聚焦于精英与更广大的公众之间的关系的论点,并认为由于欧洲问题的冲突性政治化,非精英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与描述欧洲一体化对精英有利的经典功能整合理论(Schmitter 2004)相反,这种方法将欧洲一体化的持续过程主要视为国内(或国家)精英作出的自觉且往往有争议的决定的结果,他们要对其选民负责,因此受到他们的制约。本文通过整合欧盟政策制定的三个构成要素,再次主张对多层次治理体系中的政治作出一种以精英为中心的解释。因此,无论自下而上的非精英态度和自上而下的超国家精英的影响如何,国家精英在政治上都是有效且自主的存在,所以,当涉及理解决定欧盟成员国当前移民政策的形成和方向的主要驱动因素时,这一点也至关重要。最后的免责声明,涉及一种与政治过程精英研究方法有关的常见误解。人们经常争辩说,精英模式贬低大众,暗示他们很容易被操纵或忽视,而希格利(Higley 2018, pp.31-32)清楚地表明,精英在寻求和行使权力时必须争取民众的支持。同样,不能说以精英为中心的解释意味着为精英政策辩护和辩解;相反,所提议的研究方法认识到,无论他们的议程如何,精英们都可能是极其有效的,并促进了人们对欧盟成员国当前有关移民政策的政治争议和危机的解释性理解。
德国和匈牙利:案例概述
当代德国处理移民方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时在战后重建的背景下,大规模招聘所谓的客工是必要的。随后的历届政府逐渐减少了这一招聘程序,并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完全停止。政策制定者认为这是一种暂时现象,可以通过分隔模式来解决(Konle-Seidl 2018, p.44)。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因为客工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离开,而且由于家庭团聚,移民人数进一步增加。2015年,德国走在了边境开放政策的前列。就其历史遗产而言,德国的欢迎立场似乎是独特的和可以理解的,但这种立场的形成也考虑到了经济利益。德国人口的老龄化,导致曾预计到2020年将短缺多达240万工人(Statistisches Bundesamt 2018)。因此,德国就业市场的严峻形势促使人们试图吸引受过教育的移民,并为他们提供有竞争力的条件。目前,德国仍然是欧盟避难申请者的首要目的地(到2017年,占所有申请者的31%),移民主要来自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伊朗、厄立特里亚、土耳其和尼日利亚(Eurostat 2018)。
另一方面,匈牙利是一个相对同质的国家,没有有组织移民迁入的历史。作为“铁幕”背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一个国家,匈牙利在1989年之前一直与苏联集团的其他国家隔绝。然而自2015年初以来,匈牙利就成了移民过境国,因此受到移民危机的巨大影响。虽然德国在2015年的庇护申请最多,但根据欧盟的统计数据,匈牙利“在2015年收到了创纪录的首次庇护申请(占欧盟总数的14%)”,按其人口比例计算,这是最高数值(每10万当地人口中有1799人)的庇护申请(Samek Lodovici et al. 2017, p.18)。与德国维持基于欧盟成员国责任分担概念的欢迎政策相反,匈牙利代表着一种基于保护主义、严格的边境控制和严格的准入限制的限制性意识形态(Higgins 2015)。
立法背景
2015年移民危机的升级,促使欧盟领导人重新考虑他们的政策(当危机开始时,欧洲层面并没有真正单一的移民政策1),这不仅是因为入境个人的数量太多,还因为当时有四五个欧盟成员国接收了大约70%的跨越欧盟外部边境的难民。2015年4月,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了一种新的配额制度,将非欧盟寻求庇护者分配到欧盟成员国。默克尔是边境开放政策和“欢迎文化”(Willkommenskulture)的坚定支持者。根据欧盟委员会重新安置寻求庇护者的紧急制度,28个成员国将被要求根据其经济规模、失业率和人口比例接收寻求庇护者。拟议的方案,即所谓的“柯尼希施泰因方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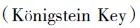 ,是基于一个分配指数,该指数赋予人口规模40%的权重,40%基于经济增长,10%基于失业,10%基于以前与寻求庇护者的接触(European Commission 2015a)。事实上,2015年9月22日,欧盟内政部长在司法和内政理事会举行会议,批准了一项在两年内重新安置12万名寻求庇护者的计划(European Commission 2015b)。
,是基于一个分配指数,该指数赋予人口规模40%的权重,40%基于经济增长,10%基于失业,10%基于以前与寻求庇护者的接触(European Commission 2015a)。事实上,2015年9月22日,欧盟内政部长在司法和内政理事会举行会议,批准了一项在两年内重新安置12万名寻求庇护者的计划(European Commission 2015b)。
在欧盟内部,有关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事项按“欧盟庇护资格指令”(Directive 2011/95/EU)管理。然而,在大多数欧盟国家,还有其他的国内立法,允许成员国以自己的方式控制移民政策。德国是欧盟的重要大国之一,这一点也体现在其对移民危机和欧盟移民政策的总体态度上。有鉴于此,德国希望不仅遵守欧盟法律,体现团结精神,而且积极塑造整个政策。正如布莱尔(Blair 2016, p.73)所言:
2015年夏之前,德国仍然是欧盟立法政策各个方面的坚定支持者,并要求所有国家直接遵循欧盟政策,以此作为增强凝聚力的措施。事实上,德国对希腊和意大利在利用这些政策解决非正常移民流动方面的无能和失败越来越感到沮丧。
德国在执行欧盟关于移民的指导方针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直到最近还鼓励更多的外国人进入德国。对于普通移民来说,存在着一个强劲的劳动力市场,为受过教育的个人提供许多机会。关于寻求庇护者,德国发挥了保护处于危险当中的人士的作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项官方政策假定大量寻求庇护者重新进入其原籍国(Goetzke and Rave 2011)。
在移民危机开始时,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匈牙利一直是受影响最大的欧盟成员国之一。根据欧盟边境管理局(FRONTEX)绘制的迁徙路线,匈牙利是西巴尔干路线的一部分,这条路线成为进入申根地区的热门通道。仅在2015年,这条路线上的非法越境数量就达到764038次(FRONTEX 2018)。为了限制非正常移民的流动,匈牙利政府发起了几项法律行动。从2015年开始,与政府主导的话语相配合,制定了限制性的法律框架。在匈牙利,自2010年以来,执政党青民盟在议会拥有绝对多数席位,这意味着即使是修改宪法,也可以在没有议会任何其他政党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简单地说,在匈牙利,政党政策体现了国家政策。更何况,欧尔班正是该党的领袖。
匈牙利当局修订了庇护法,并加强了边境管制。虽然这些限制已于2013年7月收紧,但2015年6月仍引入了新的限制,当时匈牙利政府下令在与塞尔维亚接壤的边界上建造一道175公里长、4米高的隔离栏。而政府则已于2015年2月在议会举办了一次特别讨论日,讨论那些只想以牺牲欧洲社会为代价(Dull 2015)来换取生活的谋生移民(subsistence migrants,匈牙利语为megélhetési migráns)问题,并于4月举行了一次有关移民与恐怖主义的全国协商(Hungarian Government 2015)。匈牙利国会也通过了关于移民和临时边界屏障的“第T / 5416号法案”,因此,实际上先前的政府命令已被批准为正式法律(Hungarian National Assembly 2015)。最后,匈牙利政府于当年7月21日发布了一项决定,其中提供了安全原籍国和安全第三国的清单。在此基础上,议会对《庇护法》进行了新的修正,其中规定,来自“安全原籍国”的申请人将得到加速处理。相比之下,通过“安全第三国”到达的寻求庇护者提交的申请将不被接受。该修正案于2015年8月1日生效(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5)。到8月底,与塞尔维亚的边界隔离栏的建设已经完成。然而,匈牙利的移民危机在2015年9月达到顶峰,当时移民从罗什凯 的一个登记营逃出,并与警察部队和反恐特别部队发生冲突(BBC 2015a)。作为回应,匈牙利关闭了与塞尔维亚的边界,并宣布南部两个县处于“移民造成的紧急状态”。同时,另一项修正案生效,规定非法越境或破坏匈牙利与塞尔维亚边界沿线围栏为犯罪行为(B r s g 2015)。另外,边界隔离栏的建设进入下一阶段,并在匈牙利与克罗地亚边界沿线建立了类似的围栏,政府关闭了克罗地亚的过境点(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015)。
的一个登记营逃出,并与警察部队和反恐特别部队发生冲突(BBC 2015a)。作为回应,匈牙利关闭了与塞尔维亚的边界,并宣布南部两个县处于“移民造成的紧急状态”。同时,另一项修正案生效,规定非法越境或破坏匈牙利与塞尔维亚边界沿线围栏为犯罪行为(B r s g 2015)。另外,边界隔离栏的建设进入下一阶段,并在匈牙利与克罗地亚边界沿线建立了类似的围栏,政府关闭了克罗地亚的过境点(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015)。
2016年,法律诉讼较少,但影响重大。最重要的是2016年2月发布的加强边境壁垒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定(Sullivan 2016)。根据延期,紧急状态生效至2018年9月(Government Decree No.21/2018)。此外,2016年,匈牙利议会通过了几项法案,加快了边境的庇护申请流程(Hungarian National Assembly 2016)。不过,最重要的变化与匈牙利宪法有关,旨在应对恐怖袭击威胁的新规定被接受,从而赋予政府寻求临时额外权力的权利(BBC 2016),“以打击可能的恐怖袭击,包括加强公共监视和更广泛使用军队”(Dunai 2016)。同样是在2016年,作为对欧盟重新安置计划的回应,匈牙利政府宣布了一项“配额公投”,于2016年10月2日举行(Reuters 2016b)。
根据欧盟重新安置计划接受的移民配额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欧盟共收到了1321560份庇护申请,创下了纪录;其中,德国收到了476510份。尽管申请数量众多,但德国只批准了140910份(Blair 2016, p.26)。然而,德国当局承认,在此期间,另有11.5万名移民从官方雷达上消失(Huggler 2016a),可能是转移到了申根区的其他成员国。同时,德国作出了各种承诺,接收的人数远远高于配额所显示的人数。这种更具包容性的政策立场是由默克尔发起的,随后得到了德国政治精英的认可。2016年,德国收到28.05万份申请,占当年欧盟申请总数的60%。2017年,首次申请19.83万份,占总数的31%。
根据欧盟批准的在全欧盟范围内重新安置16万难民的计划,匈牙利将接收1294人(BBC 2015b)。匈牙利政府拒绝了该计划,并在理事会上投票反对。如果接受,该计划将使16万寻求庇护者中的5.4万人从匈牙利重新安置到其他成员国。矛盾的是,配额制度对匈牙利是有利的,因为该制度也将重新安置其移民,但在匈牙利拒绝之后,这些问题自然也就没有被考虑在内(Botos 2016)。根据匈牙利移民和庇护办公室的统计,仅2017年,就有1291人获得匈牙利当局的国际保护,从而达到了配额要求。其中大多数是阿富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公民(Immigration and Asylum Office 2018)。2016年接受的申请数量为432件,2015年为508件。2018年1月,政府(Hungarian Government 2018)也发布了这些数据。
政策论证:政府叙述
2015年,默克尔承诺向任何寻求免受暴力和战争伤害的人提供庇护。她还宣称,对有需要的人关闭大门的邦域不是她的邦域,对难民怀有敌意的国家不是她的国家(Der Spiegel 2015)。因此,德国承担了欧洲欢迎移民政策的主角角色。政府精英采取了欧洲持续共同对待移民的路线,德国国内的政治文化增强了这一立场。德国社会亲难民的热情应对证明,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价值观居主导地位的国家,似乎“在吸纳移民的时候,较少受到本地居民的反对和抱怨”(Schmidt-Catran and Spies 2016, p.257)。
2015年下半年,移民显然是一个不易解决的严重问题,德国被迫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大量移民流入带来的挑战。第一步是对奥地利实行临时边境管制。值得注意的是,这尽管违反了申根协定原则,却为其他欧洲国家效仿树立了先例。除了这一挫折,德国继续实行开放边界政策,并呼吁继续在移民问题上保持团结。这种议程上最有力的例子,是总理默克尔的竞选活动口号“Wir schaffen das”(我们可以做到),目的是使民众放心,政府拥有应对这种情况的必要能力,德国将获得成功。这场竞选运动要求人们理解和采取宽容的态度,并伴随不断地宣称此次危机并非德国欢迎政策之错,而是南欧国家无力确保其边界并对大量非洲移民流动的控制。德国接受了《都柏林协定》规定的配额,同意根据《柯尼希施泰因方案》在整个联邦各州之间分配移民。在这些事件之后,政治反对派提出了要求采取更具限制性的政策,并在公民中获得了一些支持,但日益增长的反移民抗议并未导致德国移民政策发生任何重大变化。尽管如此,这些事态发展引发了一场关于德国国内(内部挑战)和欧盟背景下(关于配额的非建设性讨论)的移民政策的公开讨论。
尽管有着共同的欧洲框架,但从这次欧洲移民危机开始,匈牙利政府的立场就与德国的做法截然相反。这一差异在匈牙利政治和民众辩论中关于移民的负面话语框架中可见一斑。最初的负面说法早在2015年2月议会讨论经济移民时就已出现,这些经济移民被比作寄生虫(Dull 2015)。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政府发起广告牌宣传活动支持“全国协商”时也使用了这个比喻,口号是“如果您来到匈牙利,就必须尊重我们的文化和法律!”(Német 2015)。而且,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将欧洲移民政策描述为“德国的问题”(Colmain 2016)。此外,官方声明提出欧洲共同移民政策是不可接受的,侵犯了国家主权。大规模移民被认为是对匈牙利身份认同的威胁,也会危及信仰基督教的欧洲。除了对社会和文化安全的威胁外,移民还被描绘成潜在的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的代理人。其中暗含的意思是,这场危机绝非自发发生,事实上它是由全球性势力精心策划,最引人注目的策划者当属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
差异的对称性
2015年春,几个欧盟成员国已经在呼吁修改共同移民政策。瑞典和德国是这方面的领导者,德国利用其领导地位来处理这些问题。德国积极支持统一的重新安置和定居计划,并倡导对寻求庇护者采取更迅速、更人道的处理程序。它努力保持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凝聚力,并为欧洲的团结辩护,声称欧盟成员国的限制性移民政策有使欧盟四分五裂的危险。相比之下,匈牙利对德国领导层持强烈批评态度,并带头大声反对开放边境政策。匈牙利投票反对通过重新安置计划,甚至在欧盟法院对这一决定提出了质疑(Guild 2017, p.29)。
当默克尔试图就来自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进行固定配额交换,以换取土耳其帮助减少移民流向欧洲时,两极分化的立场进一步加剧,匈牙利政府开始在与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边境建立隔离栏,并加强边境管制(Huggler 2016b)。当德国采取促进移民融合的立法措施并优化其庇护政策时,匈牙利则对其政策作了限制,使驱逐流程更容易,并修改了宪法。当德国呼吁开放边境时,匈牙利正在修建围栏。当德国支持基层运动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以加强一体化进程时,匈牙利采取了一项名为“制止索罗斯”的议案,旨在控制和限制支持移民的组织。
然而,这些措施之间存在着某种令人困惑的对称性,差异也存在某种惊人的相似性。一方面,德国是重新安置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其重新安置数量位居第二(1349人),这一点并不奇怪。然而,对重新安置总数的关注掩盖了成员国的相对承诺。从相对份额来看,德国只重新安置了其4.9%的份额(Guild 2017, p.27)。为使重新安置工作顺利进行,欧盟成员国应承诺迅速重新安置。它们被要求按月作出实质性承诺,以达到重新安置目标,比如每月接收来自希腊的2000名寻求庇护者,来自意大利的1000名寻求庇护者。这样,意大利和希腊当局就可以按照这些承诺采取行动,向潜在的重新安置候选者提供建议。因此,接收国在此过程的一开始就作出了正式承诺。在这方面,德国的承诺不到其份额的20%,与匈牙利并列前十位承诺国(见下表),匈牙利官方没有重新安置任何寻求避难者,也没有作出任何承诺(Guild 2017, pp.27-28)。

有趣的是,尽管匈牙利精英人士在公开场合口头上极力反对移民,但人们怀疑他们在重新安置过程中“秘密”接纳了约2200名难民。匈牙利副国务部长克里斯托夫·阿尔图斯(Kristóf Altusz)在《马耳他时报》(Times of Malta)的一次采访中提到了这一点。阿尔图斯说,欧尔班政府在2017年接纳了1294名难民,但并未将这一决定公之于众图片。政府的官方网站也支持了这一说法,该网站称匈牙利在2017年期间接收了1294名寻求庇护者,但解释说这些人是正规移民,不是欧盟希望通过配额制度重新安置的人员。所采取措施的合法性也可能受到质疑。匈牙利的解决方案曾受到广泛批评。较少关注的事实是,在德国总理府办公室的档案中,找不到关于2015年9月开放边界的决定的文件。德国报纸《明镜》(Der Spiegel)的一项调查(Amann et al. 2015)使人们承认德国总理的决定是非法的。在德国,开放边界的命令应由联邦议院下达。但是,可以说在这两个国家,移民已经被安全化,也就是说,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一种需要采取非常措施的威胁(Bartoszewicz 2017)。
在寻求国际合作方面,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模式。虽然人们普遍承认,德国呼吁欧洲团结,特别是通过欧盟机构开展工作,但也应该指出,匈牙利并非单独行动。匈牙利与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其他成员国(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达成共同立场。根据官方声明,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将基于有效、负责任和可执行的外部边界保护原则为正在进行的有关综合性移民政策的辩论作出贡献(Visegrad Group 2018)。事实上,可以说匈牙利在确保多边合作方面更成功,因为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形成了统一战线,而不能说支持移民的阵营因内部分歧而四分五裂。
从国内来看,公众舆论对移民和融合政策越来越敏感,这一点在关于该问题的全国性辩论中得到了体现。在匈牙利,欧尔班曾表现出强烈的反难民和欧元怀疑论态度,从一开始就反对重新安置计划。自2015年夏季以来,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已经成为新闻媒体的日常话题,尤其是公共媒体(公共服务电视频道M1),它们将这一话题主要描述为一种安全威胁,暗示需要维持紧急状态。此外,一场官方宣传运动还传播了有关德国主导的欧盟配额制度的信息,将重新安置计划描述为将会“增加恐怖威胁”的“强制安置”,并以巴黎、布鲁塞尔和尼斯袭击事件为例作为支持证据。如果说默克尔的口号试图说服德国人“我们能做到”,那么欧尔班竞选宣传的中心信息就是“我们决不能做”。实际上,这两个政治人物都成了自己的负面形象;而且,两个国家的辩论框架也可以从对方那里看到自己的影子。
可以说,在这两个国家中,媒体和政治精英携手合作来操纵舆论。实际上,官方叙述中使用的论点是相互依存的。从中可以确定四组主要的论点:关于法治、团结问题、威胁以及移民益处的论点。在第一组论点中,在德国受雇的那些人强调了具有约束力的欧盟法律,规定其成员国有义务接受重新安置制度和分配的配额。在匈牙利,国家主权被置于突出地位,并强调了国家立法的优先性。关于欧盟政治人物和机构(特别是欧盟边境管理局)无效性的论点,也为人们所引用。
德国的团结呼吁,是基于将国际性关注问题置于自私的国家利益之上。因此,(与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内部团结以及(与来自第三国的受苦受难人民的)外部团结,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匈牙利的叙述指出了德国人的双重标准。据称,德国在移民政策方面要求团结,同时在不同领域(例如能源政策)却在回避团结。匈牙利确保边境安全的企图,随之被作为欧洲团结的证据提出。在这种叙述中,修建边境围栏是为了保卫欧洲,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德国不受更多难民涌入的影响。此外,呼吁加强与中东的团结和向冲突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防止强迫迁移的呼声,也很普遍。
在德国,移民潮被视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无法阻止,拒绝接收移民被认为是欧洲共同体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反移民的立场还将助长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心理和伊斯兰恐惧症的幽灵,这些都被视为最突出的危险。反之,在匈牙利,主要的威胁具有某种安全(恐怖主义)、文化(身份认同)和社会(社会凝聚力、犯罪、经济压力)的性质。在匈牙利人的话语中,大规模移民迁入根本没有好处。匈牙利反驳了德国人关于预期经济利益的所有论点,指出大多数入境者并非难民或寻求庇护者,而是经济移民,欧盟经济体系并不需要几十万无技术劳工,将来也不会需要。还有人提出了关于融合成本和福利制度被滥用的论点。
虽然匈牙利媒体的偏见毋庸置疑,但研究表明,在德国,这方面的话语同样也是既不平衡也不客观。由迈克尔·哈勒(Michael Haller)领导的汉堡媒体学院和莱比锡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分析了2015年2月至2016年3月间发表在德国四大报纸——《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世界报》和《图片报》上的新闻文章。他们写的报告指出,德国媒体的行为就像是道德说教者和教师爷,感性的理想主义压倒了事实。这些调查结果证实,媒体成了政府的宣传渠道,无视以不偏不倚的公正方式报道事件的义务。在2017年年中之前,缺乏批评的情况,说教的语气,以及将好客文化强加给公众,很大程度上是德国媒体话语的特征(详见Butzke 2016)。这清楚地表明,两国的官方叙述都被强加给了媒体,几乎主导了这方面的辩论。
在匈牙利,反移民、反欧盟、反配额、反索罗斯的论点仍然出现在公共媒体、青年民主联盟的通信和政府声明当中。只有政治上独立和左翼的媒体提供了不同的讲述,但这些讲述明显属于少数。不过,匈牙利的反政府示威证明,社会远非达成一致。同样在德国,人们的态度也各不相同,尽管存在着上述主导话语。最好的证明就是反移民的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的崛起,该党在2017年9月的大选中凭借民族和民族主义情绪赢得了13%的选票(Konle-Seidl 2018, p.24)。他们的主要论点包括犯罪活动的大幅增长、新移民令人担忧的失业率、恐怖主义袭击的危险、融合问题以及极端主义的蔓延。在选举之前,默克尔的执政党基民盟/基社盟改变了其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在其竞选活动中,它承诺将加大对被拒绝庇护寻求者的驱逐力度,收紧关于被拒绝庇护寻求者的规定。然而,总的来说,默克尔支持其内阁先前的决定,同时也承认德国需要一部新的移民法(Bierbach 2017)。
毋庸赘言,两国的情况都并非乍看上去那么泾渭分明。也可以这样说:德国和匈牙利都是极端的案例,因此不能说具有代表性。不过,还有一个国家证明了政治精英在塑造移民政策方面的关键作用。2015年,波兰执政的公民平台党(Civic Platform)赞成接收难民。政府发言人塞扎里·托姆丘克(Cezary Tomczyk)表示,“我们(政府)已经准备好接收任何数量的难民”(Malinowski 2015)。当时的波兰反对派与匈牙利人一起,坚持要封锁边界。当欧盟反对这一想法时,匈牙利人采取了单独行动,为此他们遭到了波兰人的批评。到2015年9月,欧盟仍未能就应对这场危机制定统一的措施。然而,拒绝强制配额的中东欧国家所受到的压力却在不断增加(PAP 2015),包括欧洲理事会主席(也是波兰前总理)唐纳德·图斯克在内的欧盟官员也言语毫不吝啬地谴责这种不情愿的态度。当波兰内政部长特雷莎·皮奥特洛夫斯卡(Teresa Piotrowska)前去谈判强制性配额时,她没有确认华沙与布鲁塞尔双边谈判中早先商定的2000人,而是承诺最多接收1万人,打破了维诺格拉德四国集团投票支持重新安置计划的内部投票纪律(TVN24 2015a)。该文件是在政府换届前签订的。甚至在竞选期间,总理埃娃·科帕奇(Eva Kopacz)就表示,波兰既愿意也准备接收尽可能多的难民(TVN24 2015b)。法律与正义党赢得了选举,该党与公民平台党的亲移民立场截然相反。法律与正义党无可争议的领导人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将欧尔班视为盟友,早在2011年就承诺成为“华沙的布达佩斯”(TVN24 2011)。因此,在2015年11月巴黎袭击事件发生后,波兰的欧洲事务候任部长康拉德·齐曼斯基(Konrad Szymański)抓住第一个选择退出的机会,表示由于安全原因,他认为没有可能实行皮奥特罗夫斯卡部长早先同意的欧盟难民重新安置方案,这一点并不奇怪。因此,波兰新的政治精英不顾内外压力,坚持其严格的反移民政策。这样一来,波兰的案例重复了上述模式,并证实了精英是移民政策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类似的因果逻辑在2018年后的意大利也可以观察到,当时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宣誓就任副总理兼内政部长,直到2019年8月辞职。
结 论
以上呈现的比较案例研究的主要优点,是证明在当前移民危机的背景下重新回到精英研究方法可以就政治过程的模型为人们提供新的理解,并因此为似乎不可能解决的局面提供新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这种方法论框架不仅大致划定了研究的范围和选择的案例,而且排除了也许可以提供的其他可能的解释。毫无疑问,精英模型只是几个政策制定模型(过程、制度、递增、理性、群体、公共选择和博弈论)之一,这些模型强调研究现象的不同方式,提供了看待政治生活的不同聚焦点。不过,考虑到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案例研究的设计,精英模型已经被人们选定为最适当的模型(Anderson 2014),因为它为人们了解现有研究看不到或忽视的问题(精英的作用)带来启示。尤其是,除了其他方面之外,集中于媒体报道、角色、叙述和话语、责任和影响的分析最为常见(Chouliaraki and Zaborowski 2017; Greussing and Boomgaarden 2017; Nikunen 2016; Triandafyllidou 2018等)。这些途径也指出了本文的局限性,因为可以这样说:锚定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论,可以突出的不是精英话语本身,而是强调两种鲜明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制度的意识形态根源,集中关注不同的变量,如政治领导人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或所研究的两个国家的欧盟成员资格时间长短和地位差异。
尽管有其他的解释,但本文证明,以精英为中心的解读,为解释看似矛盾的移民政策提供了一个补充的方法,使人们能够以相对复杂的方式研究这些政策,以解释政治和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和细微差别。在大多数分析中,德国和匈牙利通常被对立起来,作为移民政策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事实上,当我们审视政策结果时,研究这一主题的方式就可以有较大的不同。德国以支持移民的立场著称,而匈牙利则是反移民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然而,以精英为中心的分析,使我们能够发现有关政策制定的新细节。托马斯·代伊(Thomas R.Dye)对政策的定义简洁而有力,即“政策,就是政府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这使得种种变量可以灵活操作。因此,我的分析仔细审视了三个关键问题。当我们比较匈牙利和德国政府的国家立法、接受的移民配额和官方叙述时,可以明显看出,目标的不同与手段上令人费解的相似之处是同时存在的。
从欧洲移民危机开始,德国就是主要的目的国之一,而匈牙利是主要的过境国之一。匈牙利严厉批评德国领导层,并带头大声反对开放边境政策。两国的领导人都是具有长期经验、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默克尔已任四届,欧尔班已任三届)。在这两种情况下,领导人都在积极塑造应对移民危机的措施:默克尔将自己的愿景强加于整个欧洲共同体,欧尔班则强烈地破坏任何一致行动的尝试。结果,这两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都受到批评,并受到某种孤立。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单独行动。当默克尔寻求与布鲁塞尔和巴黎建立伙伴关系时,欧尔班则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平台,形成了一个稳固的集团。还有,这两个国家都采取了非常措施来应对移民问题,而这些措施的合法性在国家和欧洲的立法背景下都可以提出质疑。最后,可以说,在这两个国家,媒体和政治精英携手合作,操纵公众舆论。在一个国家,对移民友好的话语占主导地位,而在另一个国家,反移民的话语占主导地位,但在法治、团结问题、威胁以及移民的好处等方面,在两国也有人提出了类似的论点。
这两种情况通常被并列成完美的对立面。确实,当我们分析政策结果时,情况可能看似如此。然而,当对所采取的手段进行探讨,并对行为模式以及话语框架进行调研时,就会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均表明,政治精英是政策过程背后的推动力。因此,政策制定的精英模型解释了这些差异,但也指出了这些差异有些流于肤浅的事实。简单来说,匈牙利与欧盟政策的分歧,是因为其精英认为欧盟无权要求其接受寻求庇护者,声称德国和西方的多元文化处理方式行不通。在国际环境的语境下,这是一场为了主权的斗争。对内,匈牙利的精英希望通过利用对移民的恐惧和反欧盟的态度作为控制舆论的工具,从而作为政策合法化的工具来增强自己在国内的地位。而德国则与欧盟共同的移民政策保持着凝聚力,只是因为它曾帮助形成了欧盟的移民政策。作为欧盟层面的关键政策制定者之一,德国的精英利用国际框架来推进自己的议程。然而,即便是德国人,在按照对意大利和希腊的承诺安置寻求庇护者方面也存在问题,其内部应对大规模移民的能力也在不断萎缩。这种政治上的头脑简单导致了国际上的批评和国内反对之声的反弹,因为反移民势力在国内获得了令人惊讶的人气。不可否认的是,欧盟精英们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介入并采取更为果断的行动,以确保一种真正的欧洲共同移民政策的形成和实施。
原文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南茜
扫码在手机上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