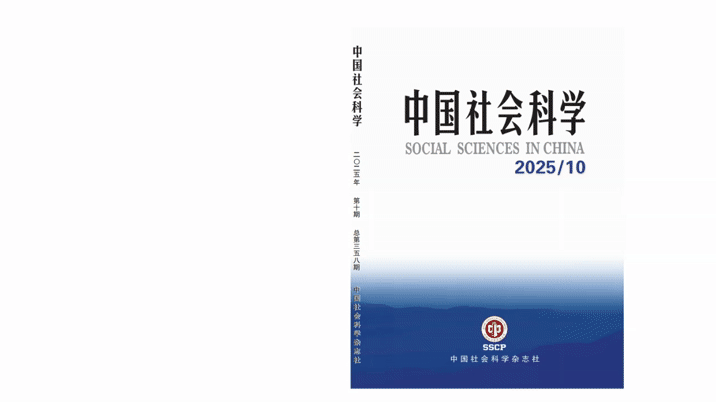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聚落形态考古的开展以及多学科手段的广泛应用,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重心逐渐由文化史转向社会史领域。以往由文献史学主导的商王朝国家形式研究这一重大课题,也陆续积累起一些可资讨论的考古材料。本文通过梳理相关考古材料,结合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对这一课题进行尝试性探讨,以促进相关问题的继续深入研究。
一、以往相关认识
《诗经》等先秦文献中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经·商颂·玄鸟》)等相关记述,在汉代以降的传统史观中,夏商周三代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圣王治下的泱泱大国,与秦汉以下的专制王朝国家别无二致。
伴随20世纪初西方史学观念的传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学者们开始对包括商王朝在内的三代国家形式等进行重新思考。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指出商代的“国家形式”属于“以王为首的贵族政体”,成为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史学界对商王朝国家政体形式认识的主流观点。此后,不少学者依据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或与考古资料相结合,陆续对商王朝的国家形式作出不同视角的解读。先后产生了军事部落联盟,城市国家(城邦),以商本土为核心的方国联盟,君主专制的集权王朝或集权国家,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体制,中央王国和地方族邦的组合体,统治范围很大的地域国家,分割式国家(segmentary state),共主支配下的广域王权国家(以下简称“广域王权国家”),复合制王朝国家,军权、王权、宗教祭祀等神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和政治关系松散的霸权式邑制国家(以下简称“邑制国家”)等认识。其中,“广域王权国家”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用来指称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形态。
需要指出,在以考古资料为主探索商代国家形式及其形成与演进机制的研究中,宋新潮较早提出,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安阳殷墟都邑为中心的区域,与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地区基本一致,而商王通过官吏或侯伯间接统治的四土范围与王畿之外的商文化亚区虽大体相当,但实际上却可能要大于商文化分布区。孙华由二里岗文化周边城邑的规模、建筑朝向、大型建筑的规制、高级别墓葬的葬俗与中心都邑的比较,论证了二里岗文化属于商前期文化,周边城邑上层人士的族属为商人,中心都邑对周边城邑具有控制权。他与宋新潮观点接近,认为商王朝的实际控辖范围不仅覆盖了商文化的分布区域,甚至和吴城文化类似的与商文化有密切关系的非商文化区,可能都属于商王朝“四土”的范围。刘莉、陈星灿等从聚落形态与金属、盐业等资源控制的视角探讨了包括商在内的中国早期国家的政治格局及其变化。他们认为二里头与二里岗时期,早期国家呈现出地域集权的特征。黄陂盘龙城等城址是以郑州地区为中心的商人向周边扩张和控制重要资源而设立的区域中心。中商时期集权衰落,多个政治中心并存。商代晚期商王室的政治影响力复苏,但始终无法重获二里岗文化时期那样的霸权地位。王立新从选址、布局与功能视角分析,认为早商时期黄陂盘龙城、垣曲商城等城址是商王朝为控制重要资源产地或交通要道而设立的军事重镇,只见“官署类”建筑而无宗庙类建筑,可称“直辖邑”。通过直辖邑的分布及控制范围,可看出早商时期商王朝控制着很大区域。此外,近年亦有研究涉及商王朝的政治地理结构及其对周边区域的经略与控制方式等。如方辉的《商王朝经略东方的考古学观察》、韦心滢的《殷代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研究》 、豆海锋的《冲击与调适:长江中游商代文化与社会演进的考古学观察》等,也都讨论了与商王朝国家形式相关的问题。
综上,伴随商文化编年体系的逐渐确立,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商文化的聚落形态、技术—经济网络、对周边区域的经略方式等研究不断深入,结合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重新解读,对商王朝国家形式的探索已取得长足进展。不少学者认识到,以二里岗—殷墟商文化为代表的政体控制着广阔的地域范围。夏商王朝均属“广域王权国家”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看法。然而,解读商王朝国家形式这一颇具历史学意义的重大课题,单纯依据考古资料显然是不够的。以往从对甲骨文这类第一手史料的研究得出的商王朝实系以商王为实力盟主的方国联合体的看法,仍然是值得重视的学术认识。更重要的是,商王朝是以何种社会组织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政体?考古学上如何判断商王朝的直接控制区域?商文化分布区与商王朝疆域究竟是何种关系?商王朝前后期对周边区域的经略方式与国家结构是否发生过重大变化?如何从考古学视角推导商王朝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些无疑均是关涉商王朝国家形式的关键性问题,需要凭借多元史料的结合尝试予以解答。
二、商王朝赖以建立的社会组织基础
夏商之交,中原地区出现了一批文化面貌处于非稳定状态的遗存。已辨识出来的有郑州南关外下层遗存、化工三厂遗存、洛达庙三期遗存、偃师商城第一期第一段遗存、二里头第四期晚段遗存等。这些遗存都或多或少呈现出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因素初步混合的特征,但均缺乏稳定的器物组合。若将它们分别与代表夏人集团的二里头文化、代表东夷集团的岳石文化和代表商人集团的下七垣文化相比,面貌特征虽有不同程度的接近,但其间的变化却十分明显。而与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早商文化相比,又尚未具备二里岗下层早段之后形成的稳定的基本陶器组合,也难以归入早商文化。这一时期,正是中原地区由原有的二里头文化与下七垣文化隔沁水对峙转向早商文化一统格局的关键阶段。
郑洛地区原属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分布区,被多数学者视作夏王朝中晚期统治的腹心地带。上述各类遗存中出现的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因素都系外来文化因素。由这两类遗存成组出现的现象看,已非之前各文化之间的普通交流,反映了两种人群势力的进入。其间必有更深层次的历史动因。其实,这种巨变恰恰源自豫东地区。杞县鹿台岗等遗址发现的成组的、特征鲜明的漳河型晚期陶器与岳石文化因素共出的现象即是明证。已有迹象显示,以河北中南部为主要分布区的下七垣文化漳河型遗存,在夏商之际正是沿豫东濮阳—杞县这一夹在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辉卫型之间的狭长“通道”南下,在今商丘、周口一带与东方的岳石文化碰撞、整合,继而逐步西进,最终出现于郑洛地区。在传世文献中,仍然保留灭夏之前商夷结盟的记录。《楚辞·天问》云:“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所指即成汤通过与东方的有莘氏联姻而得到贤臣伊尹之事。《吕氏春秋·慎大览·慎大》亦有“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的记载,将商汤与伊尹所在的有莘氏结盟的目的说得更清楚。今豫东的开封、陈留一带,直到春秋时还被称为“有莘之虚”。可见,商汤在伐夏之前首选向东南方向发展,很可能即有与东夷势力结盟而壮大自身实力的战略意图。史载商汤有“景亳之命”,所指即商汤以会盟的形式组成军事联盟的重大战略举措。景亳所在,虽有不同看法,然均不出豫东、鲁西的范围。商夷势力正是在豫东及邻近地区形成强大的军事联合体之后,才进一步西向进军灭夏的。所谓“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诗经·商颂·长发》),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反映了此后灭夏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考古发现所显示的时段、遗存内涵特征及分布区域,与文献记载若合符节。
至于下七垣文化的南下,以往学者多关注豫东地区这条路线。我们曾指出,郑州南关外下层遗存中以矮平裆鼓腹鬲为代表的因素,其实来源于下七垣文化辉卫型。而且这组因素自豫北地区南下到达郑州地区之后,并未在当地持续发展,而是很快继续向南,到达长江之滨的黄陂盘龙城一带,在那里与当地文化因素结合,形成了早商文化的盘龙城类型。辉卫型所代表的人群南下,虽与漳河型人群南下的路线不同,但时间节点大体一致,相关性十分明显,很可能也是服务于商汤灭夏的总体战略意图,只不过具体的战略目标有所不同。无论是漳河型与岳石文化因素,还是辉卫型因素,成组出现于郑洛地区,甚至出现于被认为是夏王朝中晚期都邑的二里头遗址及被认为是商汤所建西亳或别都的偃师商城,应当就是以成汤为盟主的联合体实施对夏王朝故土军事占领的结果。这一重大政治变革,导致中原及邻近地区出现文化格局的重大变化。随着商、夷、夏人群的穿插流动,文化因素由碰撞走向交融,稍晚阶段即形成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早商文化一统中原的历史局面。
商汤灭夏,以汤为盟主的人群不仅占据夏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即夏国的范围,甚至对夏王朝曾予以重点经营的周边地区先后占领(详见后文)。我们认为,这体现了以商汤为核心的军事联盟夺取和继承夏王朝疆域的战略意图。历史上,新兴的政治势力灭掉敌对国家或其联合体之后,多是要占据前朝的故土,从而拥有对前朝民众和资源的管辖权。《吕氏春秋·似顺论·分职》云:“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民,尽有夏商之地,尽有夏商之财。”谢维扬认为,占有并支配前朝的地域、民众和财产,是在古代中国政治传统中始终存在的一种王朝正统观念,是维护新政权正统地位和彰显自身权力合法性的首要之举,很有道理。由此看来,夏商之际中原及邻近地区出现的文化格局的重大变化,正是缘于以商汤为核心的军事联盟对夏王朝原有控制地域的占领,而新兴的商王朝就是以此军事联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政体。
三、从早商文化分布看王朝疆域及资源控制
早商文化在郑洛地区的形成始于二里岗下层一期。此期出现了以鬲、甗、鬲式斝、大口尊等为代表的稳定器物组合。这一时期早商文化的遗址不仅遍布“有夏之居”,而且形成了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两个都邑。表明商王朝初立时期即将经营夏王朝原有统治核心区作为重点。在选址区位、规模、布局、功能分区等方面,两大商都均体现出其作为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的地位。不仅如此,此期商文化向西、西北、南三个方向扩展到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
在西面,商文化在西安、商州一线以东地区取代了东龙山文化。东龙山文化因有较多带耳陶器而被认为是齐家文化东向发展的一支。《诗经·商颂·殷武》中有后人歌颂成汤的诗句:“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近世学者多将其视为不实的夸耀之辞。不过,《后汉书·西羌传》中对此事却保留较具体的说法:“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稳定王朝的西部边域,占据肥沃的关中平原,很可能是新兴的商王朝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老牛坡遗址所见本期遗存正是商王朝势力在其建国之初即已深入渭河平原的证明。从商州东龙山遗址的早期遗存看,陕南东部一带也是二里头文化因素强势渗入的地区,这一地区应当是二里头夏都绿松石原料的重要来源地。不仅如此,从西安老牛坡、赤栏桥、蓝田怀珍坊等地点陆续发现的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的冶铜作坊遗址看,早商文化进入关中与陕南东部,很可能亦与接续获得该区域绿松石与铜矿资源有关。不过,这一区域铜矿料的具体产地尚待确定。
夏王朝曾将晋西南地区河东盐池与中条山铜矿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已成学术界一致看法。商人在郑洛地区立足不久,旋即进入晋西南地区。至晚到二里岗下层二期,在靠近河东盐池的夏县东下冯和靠近中条山铜矿的垣曲古城镇分别出现了城邑这种区域控制中心。同时,在城邑附近的夏县辕村、绛县西吴壁等地点还发现随葬青铜礼器的高级别墓葬,体现出商王朝对盐业、铜矿资源的高度重视。中条山千斤耙等遗址开采的铜矿料,首先运送到山下绛县西吴壁等聚落进行冶炼,除了在当地铸造少量青铜工具之外,生产的铜锭主要运送到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都邑进行铸造。从铜料的生产到铜器的铸造,已形成中央王朝严格控制的完整产业链。
较二里岗下层一期稍早的南关外期遗存已到达鄂东北的盘龙城遗址。这一区域在二里头文化阶段的文化面貌尚不清楚,很可能是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一类土著遗存。《吕氏春秋·孟冬纪·异用》云:“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此说或许有夸大成分,但成汤之时商人势力已抵长江中游,有盘龙城遗址等相关发现可证。以盘龙城遗址为据点,商文化因素向西南渗透到湘北澧水流域,向东南渗透到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其中,鄂东北与赣北的长江以北地区至少在二里岗上层一期阶段已纳入商文化的分布区。豆海锋在鄂东、赣北地区区分出的意生寺类型、龙王岭类型,属于商文化盘龙城类型之下的次级类型。早商文化分布所抵近的鄂东、赣北地区,即传统所谓的“吴头楚尾”地区,是我国已探明铜矿资源分布最集中的区域。在江西瑞昌铜岭、湖北大冶铜绿山等遗址均发现早至二里岗上层阶段的铜矿开采或冶炼遗迹。而在黄陂盘龙城、郭元咀、九江荞麦岭等地点则发现二里岗上层一期至殷墟一期早段前后的冶铜遗址。这表明早商文化向南方的拓展很可能亦是缘于攫取重要资源的战略意图。
二里岗下层二期,商文化着力于向东南方向发展。沿淮河诸支流而下,在淮北与江淮地区中西部取代斗鸡台文化,形成了柘城孟庄、含山大城墩、阜南台家寺等重要据点。不仅如此,含成组商文化因素的遗址点还向南布及了皖南地区,与以土著遗存为主体的薛家岗遗存形成交错分布的态势。皖南铜陵一带亦是铜矿资源富集之地。从铜陵师姑墩遗址已发现夏时期冶铜遗存的迹象看,该遗址所见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遗存,也有可能与经营或管理铜矿料的生产行为有关。
大致从二里岗上层一期开始,商文化分布区向周边的扩展步入高峰。在西边,商文化聚落布及关中西部的岐山、扶风一带,与郑家坡文化交错分布。在北方,商文化不仅到达晋东南长治盆地,甚至沿太行山东麓北上,长驱直入大坨头文化分布区的西部,远达张家口蔚县一带。由此往西,含成组商文化因素的遗址点还出现在忻定盆地,甚至更远到达鄂尔多斯的朱开沟遗址。我们曾推测,这一文化扩张态势可能与商王朝防御晋陕黄土高原地区业已强大起来的土著势力有关。现在看来,也不能排除商人攫取该区域土地、人口、矿产等资源的战略意图。刘莉等即曾推测,此时商文化向河套及周围地区的发展,可能与商人获取阴山山地的铜矿资源有关。
二里岗上层一期,商文化可能已进入鲁西,最远或已至济南大辛庄。不过,目前迹象尚不明显。二里岗上层二期,商文化聚落已沿南北两条路线深入海岱地区。在泰沂山脉北侧推进到淄 流域,大辛庄遗址已成为此期的区域性中心聚落。而在泰沂山脉以南,商文化则至少已占据汶泗流域。此期商文化向东方拓展,控制了海岱地区水热条件优越的地区,并将岳石文化不断向东部沿海压缩。一般认为,这一阶段正值商王仲丁、外壬以隞为都的时期前后,是传统认为的“九世之乱”的开始阶段。商文化尽管在其他区域的拓展趋于停滞,但仍然显示了强势东进的势头。古本《竹书纪年》所记仲丁即位,“征于蓝夷”;河亶甲即位,“征蓝夷,再征班方”,可能为理解此期商文化的东进提供依据。前已述及,在成汤灭夏的过程中,至少部分东夷部族已成为商族盟友。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一军事联盟在最初几个阶段的拓疆,并未向东方发展。而这一阶段商人与部分东方传统盟友关系破裂,是其东向拓展势力的直接诱因。深层动因很可能仍与对资源的争夺有关。
流域,大辛庄遗址已成为此期的区域性中心聚落。而在泰沂山脉以南,商文化则至少已占据汶泗流域。此期商文化向东方拓展,控制了海岱地区水热条件优越的地区,并将岳石文化不断向东部沿海压缩。一般认为,这一阶段正值商王仲丁、外壬以隞为都的时期前后,是传统认为的“九世之乱”的开始阶段。商文化尽管在其他区域的拓展趋于停滞,但仍然显示了强势东进的势头。古本《竹书纪年》所记仲丁即位,“征于蓝夷”;河亶甲即位,“征蓝夷,再征班方”,可能为理解此期商文化的东进提供依据。前已述及,在成汤灭夏的过程中,至少部分东夷部族已成为商族盟友。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一军事联盟在最初几个阶段的拓疆,并未向东方发展。而这一阶段商人与部分东方传统盟友关系破裂,是其东向拓展势力的直接诱因。深层动因很可能仍与对资源的争夺有关。
可见,早商文化在郑洛地区形成之后,如波浪般逐次向周边地区拓展。至二里岗上层二期,其分布区域已西至宝鸡周原,东达淄 与汶泗流域,北起冀西北桑干河谷,南届鄂东、赣北与皖南一线。涵盖地域之广,远超此前中国境内任何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其间,在重要的资源产地或交通要道上,还发现东下冯商城、垣曲商城、盘龙城商城、府城商城等直辖邑。此外,也出现了一批如老牛坡、大辛庄、台西等区域性中心聚落。早商文化分布范围的不断扩展,与以商王为核心的军事联盟不断向周边扩张,以获取土地、人口、矿产等各类资源的战略意图密切相关。在一定意义上说,早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大致代表了商王朝依靠军事实力实际控制的区域,亦即早商王朝的实际疆域。早商王朝在其强盛之际控辖的地域范围已相当广阔。仅由西北面的山西夏县东下冯到南面的湖北黄陂盘龙城,两座直辖邑之间的直线距离就达550公里左右,确有千里之遥。由此亦可说明,进入王朝时期之后,文化的分布范围与军事势力的扩展和被占区域的稳定控制息息相关。
与汶泗流域,北起冀西北桑干河谷,南届鄂东、赣北与皖南一线。涵盖地域之广,远超此前中国境内任何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其间,在重要的资源产地或交通要道上,还发现东下冯商城、垣曲商城、盘龙城商城、府城商城等直辖邑。此外,也出现了一批如老牛坡、大辛庄、台西等区域性中心聚落。早商文化分布范围的不断扩展,与以商王为核心的军事联盟不断向周边扩张,以获取土地、人口、矿产等各类资源的战略意图密切相关。在一定意义上说,早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大致代表了商王朝依靠军事实力实际控制的区域,亦即早商王朝的实际疆域。早商王朝在其强盛之际控辖的地域范围已相当广阔。仅由西北面的山西夏县东下冯到南面的湖北黄陂盘龙城,两座直辖邑之间的直线距离就达550公里左右,确有千里之遥。由此亦可说明,进入王朝时期之后,文化的分布范围与军事势力的扩展和被占区域的稳定控制息息相关。
早商时期,商王朝向周边区域的开拓并非一帆风顺,也曾出现对部分区域资源争夺的失利。大致在商王祖乙以邢为都的时期前后,即商文化东先贤期,伴随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都邑的废弃,商都迁离郑洛地区。与此同时,分设于晋西南的东下冯商城、垣曲商城两座直辖邑遭到废弃,晋西南地区亦不见这一时段其他的一般性聚落,表明商王朝不得不放弃对该区域铜、盐等资源的控制。曾经一度突入到桑干河流域的商王朝势力,已退据拒马河以南地区。与此相应的是,此阶段或稍晚,以陕晋间黄河两岸为重心的李家崖文化聚落已南下至吕梁山南部与临汾盆地交界的洪洞上村一带。而以鄂尔多斯地区朱开沟文化为主源的李大人庄遗存,出现在宣化一带。这一文化格局的伸缩变化,凸显了不同人群势力对资源的争夺和较量。
四、由晚商文化的分布看商王朝疆域与经略方式的变化
殷墟一期晚段及稍晚阶段,约当商王武丁时期,商文化分布范围出现了又一波明显的伸缩变化。在西方,商文化的分布由岐山、扶风一带回缩到铜川—西安以东的关中东部地区。在北方,商文化在太行山东麓地区进一步退缩至唐河—大清河一线。在南方,商文化则由鄂东、赣北回缩到桐柏山、大别山以北。在东南方向,商文化则退出长期占据的皖中北地区。与此不同的是,商文化在西北与东方仍显示出强势发展的态势。在西北方,商文化聚落重新进入晋西南地区,由北向南出现了洪洞坊堆—永凝堡、杨岳、浮山桥北、临汾庞杜、曲沃西周、绛县周家庄、乔野寨、闻喜酒务头等一系列遗址,它们大都居于河汾之东,靠近山地的盆地边缘地区。在东方,商文化聚落在泰沂山脉以北,向东北方向的分布直抵渤海湾南岸。在泰沂山脉以南,聚落分布曾一度到达鲁南苏北的近海区域。
结合周边地区文化的兴衰变化、重要资源的开发及相关文献记载,方能为上述商文化分布范围的伸缩现象提供合理解释。伴随商文化退出关中西部,来自宝鸡以西的刘家文化、泾水中上游的碾子坡文化、泾水中游及邻近区域的郑家坡文化相继进入周原地区。大致在商末周初时期,上述三种文化在关中西部地区趋于高度融合,区域聚落逐渐形成以周原为中心,以周公庙、孔头沟等为次级中心的庞大聚落体系,标志着区域政治秩序的建立,即以周国为核心的强大军事联盟势力的形成。在华北平原北部,兴起了已出现明显社会分层现象的围坊三期文化。在南方,盘龙城等重要据点被放弃,商文化聚落亦撤离长江中游与皖南地区的重要铜矿产地。吴城文化、大路铺文化、费家河文化等土著文化纷纷进入繁荣发展阶段。江西新干大洋洲、湖南宁乡黄材等地陆续出现具有本地风格的青铜器群。商文化在上述区域的收缩,无疑与地方土著势力的雄起密切相关。
在北方,大致在殷墟一期前后,陕晋间黄河两岸陆续崛起了流行北方系青铜兵器与工具的李家崖文化、西岔文化、西坬渠遗存等。其中,李家崖文化与西岔文化均发现石砌防御围墙和高级别建筑的大型城堡,代表的是一类武装化程度很高的人群。有学者认为,晋西南地区出现的一系列晚商时期聚落,恰恰形成了抵御西北面敌对势力的防线。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有大量与西北方敌对势力发生军事冲突的记录。《易·既济》爻辞等传世文献中也保留了“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等相关记载。恰在这一阶段,由文化分布所见的商王朝势力重返晋西南,表明其目的除了巩固边防之外,很可能意在重新强化对本地区铜、盐等资源的攫取与控制。近二十多年来,在鲁北近海区域陆续发现大量晚商时期与盐业生产相关的遗址。其中既有沾化杨家、利津洋江等制盐作坊遗址,又有内陆一侧靠近制盐遗址的沾化陈家、滨州兰家等与盐业相关的定居点或管理中心。这表明商王朝势力向鲁北沿海区域的发展,与控制那里丰富的浅表卤水资源有直接关系。由此可见,晚商时期商文化在各个方向的伸缩变化,实际上也是商王朝实际控制区域即王朝疆域的盈损变化,其深层动因,仍与对各类资源的争夺和控制密切相关。
晚商阶段商王朝向周边开拓的势头虽然总体上趋于减弱,但是安阳殷都的规模及聚落发展程度却远超商代早期的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自殷墟一期晚段至殷墟四期,除了自身人口的增长之外,还有源源不断的外来人口持续进入殷都。在其周边区域先后出现了陶家营、辛店等不同等级的“卫星城”及众多中小型聚落,从而使“大邑商”始终保持了对周边政治势力的强大威慑力。文化面貌与“大邑商”高度一致的豫北冀南地区的商代晚期文化,被称为“殷墟类型”,应该就是商王室重要的直接管理区域,即商王国本土。这一区域,大致与吴起所说“殷纣之国”的范围相当,是商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这一区域之外,也有商王朝的直系势力活动。虽然伴随商文化在南方与东南方的退缩,商王朝可能已丧失对鄂东、赣北与皖南铜矿资源的直接控制,但是晚商时期青铜器的生产规模、技术与质量却达到了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高峰,中原风格青铜礼器的传播范围亦远远超出了商文化的分布区,从而形成了一个范围更广大的“青铜礼器文化圈”,表明商王朝礼制文化浸润区域的进一步扩大。这些都不是简单用商王朝明显衰落所能解释的。
有迹象表明,晚商时期商王朝针对不同区域、不同资源可能采用了不同的经略模式。晋西南与鲁北地区,不仅有丰富的盐业、土地等资源,而且分别面临强大敌对势力的威胁,这一时期的聚落分布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既有利于对重要资源的直接掌控,也有利于对敌对势力的战略防御。商王朝对这两个区域的经略,仍与早商时期类同。盘龙城、意生寺、师姑墩等据点的放弃和商文化的撤出,表明商王朝已失去对鄂东、赣北、皖南铜矿资源的直接控制。然而,原产于安阳一带的青铜礼器与有领玉璧等高级别物品却成批流入长江中游地区。从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群中有地方风格的铜礼器来看,不排除商王朝对外有技术输出的可能。豆海锋指出,晚商时期商王朝可能采用了安抚政策保持与长江中游地区精英阶层的交流,通过贸易或贡赋等手段获得安阳殷都铸造青铜器所需原料,而反馈给当地部分产品乃至制作技术。通过这一途径,青铜器的制作技术与部分产品流传到中国南部更广阔的区域。浙江湖州毘山遗址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分析表明,其所使用的铜料和制作技术与安阳一致。广汉三星堆青铜器泥芯成分的分析则显示,其中非容器类青铜器是以中原地区的范铸法制作,容器类青铜器则很可能是长江中游地区流入的产品。
大兴安岭西南端是中国北方地区已探明铜锡矿资源分布最集中的地区。近十多年来,通过调查和发掘,已确认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喜鹊沟、伊和沃门特、哈巴其拉、翁牛特旗尖山子等4处晚商时期的铜锡矿开采和冶炼遗址。由铜锡矿产地向南,在克什克腾旗、巴林左旗、翁牛特旗、赤峰松山区、朝阳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北京平谷等地陆续发现殷墟一、二期的青铜器窖藏或高级别墓葬。这些地点连接起来,明显指向商文化分布区的交通要道。在翁牛特旗头牌子地点发现的铜器窖藏中出土了3鼎1甗,出土时2件铜鼎中盛满了含锡量达50%的锡矿砂,足证在商代晚期大兴安岭西南端一带的铜、锡矿料已被纳入商王朝主导的青铜工业采、冶、铸分离的产业格局,处于这一产业链的上游环节。尤为重要的是,在头牌子铜甗上带有“ ”字铭文。此字李学勤、裘锡圭力主释为“贾”,即商贾之“贾”。此铭文很可能系标识职事一类的族徽,表明大兴安岭西南端的铜锡矿料及邻近地区发现的青铜器成品,应是通过贸易手段在当地与安阳殷都之间流通的。这种流通的主导者应是商王朝。由此可见,正是通过经略方式的调整,晚商时期商王朝获取铜锡矿料等资源的区域甚至可以远达此前的实控区之外。
”字铭文。此字李学勤、裘锡圭力主释为“贾”,即商贾之“贾”。此铭文很可能系标识职事一类的族徽,表明大兴安岭西南端的铜锡矿料及邻近地区发现的青铜器成品,应是通过贸易手段在当地与安阳殷都之间流通的。这种流通的主导者应是商王朝。由此可见,正是通过经略方式的调整,晚商时期商王朝获取铜锡矿料等资源的区域甚至可以远达此前的实控区之外。
五、考古视野下的商王朝国家形式
早商时期,商王朝依靠建立直辖邑及其他区域性中心聚落等手段实现对广大辖域内各类资源的稳定控制,其凭借的主要力量是灭夏前夕形成的以商人为核心的军事联盟。随着占领区域的逐步扩大,各地臣服人群的不断增多,这一联盟的整体势力也在不断扩大。从聚落形态特点及其与商都之间的关系来看,疆域内政治势力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设于资源富集之地或交通要道上的直辖邑为代表,伴随商都迁离郑洛地区,这些重要据点及周边附属聚落也纷纷被放弃。这些据点的人群很可能是与商都居民一同迁徙并重新安置。另一类则如西安老牛坡、济南大辛庄等区域性中心聚落为代表的势力,这类聚落并未随商都的迁徙而发生重大变化。在晚商时期,它们在文化面貌上的自身特色愈发凸显,表明其独立性不断增强。
目前,虽没有甲骨卜辞等出土文献资料可资说明上述现象,然而,传世的《尚书·盘庚》篇中却保留了相关记录。《尚书·盘庚》篇下所记盘庚迁殷时诰谕的对象有“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其中的“邦伯”是指诸邦方的首领。与商都一起完成迁徙重任的邦方,无疑是商王倚重的结盟势力。“师长”为军事首领,“百执事之人”为各类王朝职官,历来的注疏几无异词。由此可见,在商代早期的王朝政体中,包含两类政治势力。一类是商王可以直接控制的“师长、百执事之人”及其辖众,另一类则是具有一定自主权力的“邦伯”及其辖众。这显然与我们从考古材料分析中所得的认识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晚商时期,商文化重新进入晋西南地区,聚落形态也呈现出面向西北方黄土高原的分布态势,表明这里的政治势力完全服务于商王朝的整体战略。闻喜酒务头、浮山桥北、灵石旌介等地点发现的高级别贵族墓,从葬式、葬俗到随葬品组合,均与安阳殷都的贵族墓高度一致。东方地区亦是商王朝重点经略的区域,晚商时期聚落数量激增。桓台史家、青州苏埠屯、滕州前掌大等成为维护统治秩序的中心性聚落。晚商时期泰沂山脉南北两翼地区的文化面貌虽与中心区有一定差异,但是从数量众多的高级别墓葬来看,其形制结构、葬俗、用器规制等也大多与安阳殷都的贵族墓高度一致,显示出对“殷礼”的遵从。出土多件带“亚醜”族徽青铜器的苏埠屯M1的墓主人,多被认为是商王朝派驻东土的武官,而苏埠屯遗址应当就是商王朝在东方拓展的一个据点。董珊将“亚醜”之“醜”改释为“酌”,认为该族氏源于族长小臣酌的私名。据帝乙时期卜辞,商王曾派小臣酌率族人在东方建立疆垂,抵御东夷的人方。出土“戍宁觚”的桓台史家遗址,亦被视为商王朝派员戍守的一处军事重镇。
晚商时期也有如罗山天湖墓地、西安老牛坡遗址所代表的人群,他们在葬具、随葬品形制及组合等方面与殷墟地区有较大差异,独立性逐渐增强。天湖墓地因有多例铜器铭文,可断为息国墓地。甲骨卜辞中有“妇息”之名,表明该方国与商王室存在通婚关系。由其所处位置看,息国可能还承担着商王朝南方藩屏及保障各类资源向安阳殷都输送的重任。但是,文化面貌上的变异,仍然透露出其与中心区离心力的逐渐加大。此外,寿光古城遗址发现一批带有上“己”下“並”族徽的青铜器。何景成认为该族徽系商末由“並”族一支受封“纪侯”而新立的族氏。寿光在春秋时期仍为纪国国都,而纪为东夷古国已明。以寿光古城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反映了在鲁北地区商王朝直系势力与臣服土著势力的并存状态。显然,由上述现象可推知,晚商时期商王朝尽管因周边势力的崛起,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有明显收缩,对周边区域资源的经略模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但其国家结构特征并未发生质的改变,仍然属于以商王国为核心的邦方或族的联合体。其中包含了两类政治势力,即直接附属于商王国的政治势力和与商王国处于联盟状态的政治势力。而这类与国家形式相关的信息,无论是在出土文献还是传世西周早期文献中均能得到印证。
甲骨卜辞中,参与王朝事务的人员,既有单称妇某、子某、亚某及统称多子、多工、多马、多尹、小臣等名目繁多的各类执事,又有常常以“比”即联合的方式参与商王组织的军事行动的方国首领。前一类是商王室倚重的直系势力,后一类则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尚书·酒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大盂鼎》铭中也有:“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 殷正百辟,率肆于酒。”从中可看出,甲骨卜辞所见两类政治力量也见于西周早期金文与诰辞之中,被称为“内服”与“外服”。其中的内服即“殷正百辟”,包括“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等各类官员及“百姓”“里君”等宗氏贵族。外服即“殷边侯甸”,则系尊号为“侯”“甸”“男”“卫”等的邦方首领。这种内外服制,无疑是商王朝基本的管理架构。那么,以这种内外服制为基本管理体制的国家,自然就是包含了两种政治力量在内的以商王国为核心的邦方或族的联合体。
殷正百辟,率肆于酒。”从中可看出,甲骨卜辞所见两类政治力量也见于西周早期金文与诰辞之中,被称为“内服”与“外服”。其中的内服即“殷正百辟”,包括“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等各类官员及“百姓”“里君”等宗氏贵族。外服即“殷边侯甸”,则系尊号为“侯”“甸”“男”“卫”等的邦方首领。这种内外服制,无疑是商王朝基本的管理架构。那么,以这种内外服制为基本管理体制的国家,自然就是包含了两种政治力量在内的以商王国为核心的邦方或族的联合体。
以往学者对商代国家的定性,视角颇不相同。所谓“领土国家”“分割式国家”无疑强调的是地域特征。前者将商的统治地域视为完整的版块,后者则强调在商的疆域中尚有许多非商的“孔洞”。王权、军权与神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之说,则属于从权力结构角度的解读,至于集权制国家的说法亦属此类。目前广泛流行的“广域王权国家”,则集中考虑了地域与权力两大特征。郭沫若提出的“以王为首的贵族政体”,实际上强调的仍然是统治阶层的特征,而并没有涉及国家结构的形式。而城市国家(城邦)、邑制国家与以商本土为核心的方国联盟等则确系从国家结构形式角度给出的定性。其中城市国家(城邦)与邑制国家着重概括早期国家政体的基本结构,而以商本土为核心的方国联盟则点明了这类基本结构之上还存在着国与国的联合体这类更高层次的政体结构。至于“中央王国和地方族邦的组合体”等说,实质上与“以商本土为核心的方国联盟”说类似,只是关于王权、疆域、管理体制以及商王国与方国之间关系等方面的理解或有不同。前文我们由考古材料出发,结合出土与传世文献,推导出来的商王朝的国家形式亦与方国联盟说接近。
林沄论证商代方国联盟,主要基于甲骨卜辞中常见商王以“比”的方式与盟友一同开展军事行动,反映了联盟对象与商王之间的“一种地位上的对等性”。他还强调各方国在自己所辖的“都鄙”之内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实际上都是相对独立的政体。这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认识,已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不过,甲骨文中不仅有商王对雀、妇好、多子族等直系势力的军事活动采用“呼”和“令”的辞例,而且也不乏对沚、望乘等方国势力的活动使用“令”这一指挥行为的例子。再者,与商王结盟的方国首领只称侯、伯、任等而不称王,这显示出王与联盟成员之间具有上下等级之别,而非完全平等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晚商时期盟友方国的产生途径看,有些应是很早加入商王军事联盟的传统盟友,跟随商王不断开疆拓土,承担王室分派的职事。其中有些可能被赐以具有一定等级意义的尊称。裘锡圭指出,侯、卫之类在边域担任斥候保卫工作的职官,以及田(甸)、牧之类被商王派驻到商都以外从事农垦、放牧的职官,在商代晚期可能已经大量发展成诸侯。这些方国,自然仍会保持与商王的臣属关系。不过,亦不能排除有些同盟势力的首领仍以族氏之长的身份参与商王室的各类事务,而并未被商王视为方国之长赐以尊号的可能。另一类联盟方国,则是由被征服的敌对势力转变而来,如沚、犬、望乘等。结合传世文献看,鬼方、周方等也应属此类。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鬼方与周方都是商文化分布范围之外的盟友。文献记载显示,即使对这种在商王朝实控区之外的盟友,商王仍然对其有管控或干预的权力,甚至可以对其首领采用极端的惩罚方式。这也是导致周人逐渐结成自己的同盟势力,最终东向灭商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我们倾向认为,传统史学观中的“商王朝”概念,仍然可以用来指称“以商王国为核心的邦方或族的联合体”这种国家形式。
尚需说明的是,以往对于商王朝内外服制的解读,多是基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视角,而我们所辨识出来的商王朝疆域范围内存在的两类政治势力,则是以考古材料为中心实证了商王朝内外服的管理体制。而且,以往学者多认为商王朝的王畿或“商本土”主要是由内服职官管理,四土及边域则主要是由各类邦伯实施管理,两类不同的管理者或有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流动。而我们更倾向于认为,为了控制周边区域的各类资源与交通要道,商王朝不仅在以都邑为核心的商王国之内会任命各类职官管理各类事务,甚至在周边相当大的范围内都会设置直辖邑或疆垂予以实际控制。这类王朝直属势力向地方的派驻,除了控制资源的目的之外,或许还与监督、管控其他结盟势力的战略目的有关。我们认为,王震中首倡的商王朝是以商王国为核心的、与四土邦国相结合的一种“复合制国家形态”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所不同的是,他着重强调在这一国家结构形式中,商王国属于“国上之国”,而四土的邦国是从属性的政治力量,而我们则认为这一政体中的各邦方实际上都是有相对独立性的,故而仍以联合体称之。这种独立性是由参盟的任何一方均由一个或多个都鄙群所构成这一基本结构特点决定的。因为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任何一个都鄙群都是可以自给自足的、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单位。
总之,夏商之际中原地区文化格局的变化,缘于以商汤为盟主的军事联盟对夏王朝实际控制区域的占领,新兴的商王朝即是以此军事联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种国家政体。早商时期,商文化呈波次向周边区域的分布扩展,是由以商王国为核心的联合体攫取和控制周边各类资源的战略所导致。因此,商文化的分布区域与商王朝的实控区域即疆域范围大体一致。商文化在东先贤期和殷墟一期晚段先后两次出现分布范围的收缩,而商式礼器的分布范围却不断扩大,表明商王朝可能已由之前的向外不断开疆拓土,转变为以贸易或贡赋手段获取部分地区的资源,但国家结构的联盟性质并未发生质的变化。由考古学上两类政治势力的逐渐辨识可以印证,周初文献中记录的商的内外服制,应当就是商代国家真实存在过的管理制度。商王朝就是以内外服制为管理体制、以商王国为核心的邦方或族的联合体。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武雪彬 责任编审:晁天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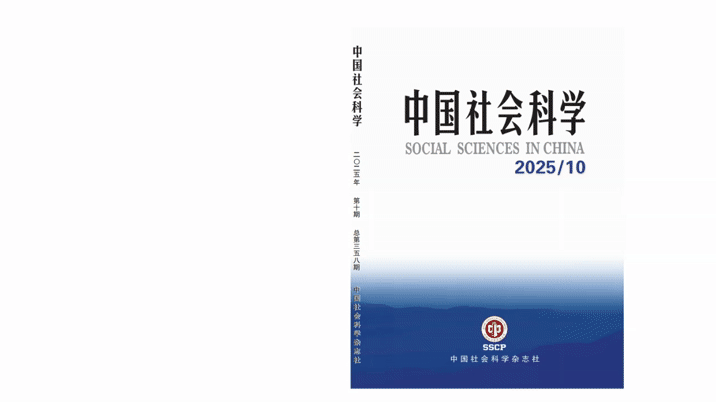


 ”字铭文。此字李学勤、裘锡圭力主释为“贾”,即商贾之“贾”。此铭文很可能系标识职事一类的族徽,表明大兴安岭西南端的铜锡矿料及邻近地区发现的青铜器成品,应是通过贸易手段在当地与安阳殷都之间流通的。这种流通的主导者应是商王朝。由此可见,正是通过经略方式的调整,晚商时期商王朝获取铜锡矿料等资源的区域甚至可以远达此前的实控区之外。
”字铭文。此字李学勤、裘锡圭力主释为“贾”,即商贾之“贾”。此铭文很可能系标识职事一类的族徽,表明大兴安岭西南端的铜锡矿料及邻近地区发现的青铜器成品,应是通过贸易手段在当地与安阳殷都之间流通的。这种流通的主导者应是商王朝。由此可见,正是通过经略方式的调整,晚商时期商王朝获取铜锡矿料等资源的区域甚至可以远达此前的实控区之外。 殷正百辟,率肆于酒。”从中可看出,甲骨卜辞所见两类政治力量也见于西周早期金文与诰辞之中,被称为“内服”与“外服”。其中的内服即“殷正百辟”,包括“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等各类官员及“百姓”“里君”等宗氏贵族。外服即“殷边侯甸”,则系尊号为“侯”“甸”“男”“卫”等的邦方首领。这种内外服制,无疑是商王朝基本的管理架构。那么,以这种内外服制为基本管理体制的国家,自然就是包含了两种政治力量在内的以商王国为核心的邦方或族的联合体。
殷正百辟,率肆于酒。”从中可看出,甲骨卜辞所见两类政治力量也见于西周早期金文与诰辞之中,被称为“内服”与“外服”。其中的内服即“殷正百辟”,包括“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等各类官员及“百姓”“里君”等宗氏贵族。外服即“殷边侯甸”,则系尊号为“侯”“甸”“男”“卫”等的邦方首领。这种内外服制,无疑是商王朝基本的管理架构。那么,以这种内外服制为基本管理体制的国家,自然就是包含了两种政治力量在内的以商王国为核心的邦方或族的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