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开罗宣言》锁定同盟国必将顽强战斗,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这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法宝,也是奠定东京审判管辖权的基础。极端人士杜撰日本享有“不变更天皇统治大权”,鼓吹日本有条件投降,意在否定东京审判管辖权,然而历史事实足以揭露其谎言。日本辩护律师虚构开战法规和交战法规的差异性,以此诟病《巴黎非战公约》缺乏惩治性规范,但传统习惯国际法实践表明,只要严重违反对整个国际社会应承担的义务,必然招致国际社会的反措施。“破坏和平罪”列入《东京宪章》的权力来自日本投降书;“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不具有强行法性质。无论在管辖权还是法律适用方面,东京审判完全符合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
关键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管辖权;无条件投降;法不溯及既往
作者管建强,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上海 201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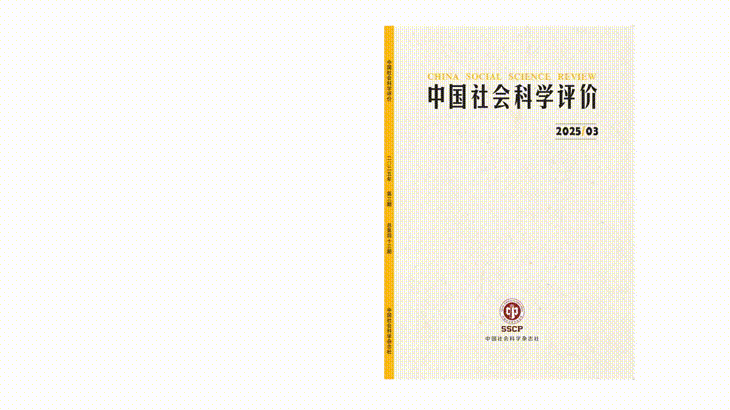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然而,至今仍有日本极端人士以管辖权、法律适用等为由头,诟病甚至抹黑东京审判。这类看似颇具学术色彩之质难,实乃包藏断章取义、歪曲史实之伎俩,其意乃在欺瞒日本国民和
一、东京审判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争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同盟国为惩治纳粹德国与日本帝国战犯的战争罪行,根据国际法原理,设立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严重违反战争法规的罪犯予以依法制裁。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至1948年11月12日宣判判决,前后持续两年多。
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以下简称《东京宪章》)第5条(对被告与罪行之管辖权)的规定:
本法庭有权审判及惩罚被控以个人身份或团体成员身份犯有各种罪行包括破坏和平罪之远东战争罪犯。
下列行为,或其中任何一项,均构成犯罪行为,本法庭有管辖之权,犯罪者个人并应单独负其责任:
(甲)破坏和平罪指策划、准备、发动或执行一种经宣战或不经宣战之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或保证之战争,或参与上述任何罪行之共同计划或阴谋。
(乙)惯例战争犯罪指违反战争法规或战争惯例之犯罪行为。
(丙)违反人道罪指战争发生前或战争进行中对任何平民之杀害、灭种、奴役、强迫迁徙,以及其他不人道行为,或基于政治上的或种族上的理由而进行旨在实现或有关本法庭管辖范围内任何罪行之迫害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否违反行为地国家的国内法。凡参与上述任何罪行之共同计划或阴谋之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与共谋者,对于任何人为实现此种计划而做出之一切行为,均应负责。
东京审判开庭当日,日本律师辩护团向法庭提出七项动议(以下简称“辩护团动议”):
(一)同盟国没有权能通过同盟国最高司令官将“破坏和平罪”列入《东京宪章》(第五条第1款),并对其进行审判。
(二)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的本质只是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手段,既没有拓展战争犯罪的含义,也没有将战争本身定性为犯罪。
(三)战争中作为国家的一员而采取行动的人,在国际法上没有个人责任。
(四)《东京宪章》之规定属“事后法”,故属非法。
(五)规定实施《波茨坦公告》的投降书所载战争罪,仅指违反本公告发布当时国际法所承认的惯例战争法规的行为,本法庭不能对其他事项作为战争犯罪进行审判。
(六)交战中的杀人行为,除构成违反交战法规或惯例战争法规的情况外,是战争通常伴随的行为,不是杀人。
(七)被告中有数人是俘虏,根据1929年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可以由军法会议审判,但不能由本法庭审判。
其中(一)(二)(四)(五)项内容,主要针对管辖权和法律适用问题。其余辩护团动议经法庭检察官的反驳,辩护方已不再纠缠,故不展开讨论。
就辩护律师对法庭管辖权以及法律适用问题的抗辩,东京审判法庭于1948年11月12日对被告作出判决时,援用并重申了1946年10月1日在纽伦堡判决书的判决依据,概要如下:
《巴黎非战公约》无条件斥责以战争作为政策工具,庄严地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其中必然包含承认战争在国际法上是非法的原则。凡是从事计划和实施这类产生不可避免的可怕结果的战争者,都应当被视为从事犯罪行为。……保护国家代表者的国际法原则是不能适用于那些在国际法上被视为非法行为的犯罪者的……他们不能以公职为庇护……逃避惩治。法无规定不为罪(Nulla poena sine lege)原则,并不是对主权加以限制,而是一般的正义原则……如果对他的非法行为容许放任,不加惩罚,那才真正是不公道的。法庭宪章明确规定……被告依照本国政府或上级命令所作的事实,并不能使被告免除责任……真正的标准,不是命令的存在,而是事实上有没有作道德选择的可能。
东京审判法庭完全同意纽伦堡法庭的上述见解及推论,对辩方的抗辩作出了有力的驳回。
东京审判的管辖权依据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书》无条件承认了包含《开罗宣言》在内的《波茨坦公告》;东京审判的实体法基础是《巴黎非战公约》。本质上而言,国际法效力依据来自当事国的意愿(同意),只要不违背国际强行法,缔约国之间当然有权缔结和开创造法性的国际规范。因此,东京审判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的正当性是理所当然的。
一些日本极端人士将日本无条件投降解释成“日本有条件投降”,将《巴黎非战公约》诟病成仅有禁止性规范、缺乏惩罚性规范,将“法无规定不为罪”包装成国际法基本规范。这类貌似具有学术性的质疑,实则以歪曲历史事实和断章取义为手段,目的则是欺骗国际舆论。为此,有必要就东京审判管辖权和法律适用所遭受的不实质疑,进行学术上的解析和反驳,以微观视角结合国际法基本原理,进一步说明东京审判在管辖权程序和实体法适用上的合法性。
二、管辖权的程序性依据是日本无条件投降
(一)管辖权与无条件投降的关系
管辖权是指主权国家通过立法、行政法令或法院判决而影响人们权利的权力。它与主权和领土的概念密不可分,在域内,管辖权几乎是排他的,而在域外,只有经其他国家允许才能行使。概言之,域内司法管辖是基于权威,而无须被管辖对象明示同意,而在国际层面,如果管辖对象系代表他国家主权地位时,未经其国籍国的同意无权行使管辖权。东京审判的管辖权是国际法上的管辖权。
国际法学界经常引用“平等者之间不存在支配权”这一法哲学格言,从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推导出主权司法豁免原则,因此一国的行为或财产不受另一国支配。例如,代表主权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在接受国享有特权与豁免权。他们在国际社会中,同样享有排除外国任何管辖的豁免权。同理,军队是国家的公器,也不受外国司法管辖。
然而,在战时,任何一方战斗员放下武器向敌方屈服的投降行为,意味着放弃司法豁免权。在国际法实践中,俘获战俘一方的军事机构对违反交战惯例的战俘进行司法审查及军事审判,已成为国际习惯法的重要部分。虽然二战前,审判战犯的实例不是很多,但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亦即犯有暴行罪)的人在战时或战后受到法律制裁却是常有和惯见之事。
同样地,当整个国家无条件投降时,意味着这个国家毫无保留地放弃主权国家地位。因此,战胜国对战败国任何涉嫌违反战争法规的人或事物,可以行使司法管辖权。这里的“人”,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任何参与了计划、准备和实施破坏和平罪行为的人员。对“事物”的管辖,通常伴随着对武器装备和军事设施的限制、移交,还涉及对领土主权限制等方面的事项。
二战后期的国际法实践表明,无条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的本质是指胜利方不允许或不接受投降方提出任何保留条件和要求,投降方必须完全接受胜利方的意志,包括领土处置、战争赔偿、战犯审判等各方面的事项。东京审判管辖权的法律基础,来自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日本投降文书》,以及同盟国对《日本乞降照会》的复函等文件。
(二)《开罗宣言》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达成《开罗宣言》,同年12月1日对外公布。《开罗宣言》聚焦日本,强调了三大使命:第一,此次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第二,剥夺、归还以及驱逐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非固有土地;第三,重申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此后,1945年7月26日,同盟国的最后通牒《波茨坦公告》全文共13款,明确包含《开罗宣言》所有内容。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全面接受了《波茨坦公告》。
1949年 11月 26日(美军占领日本时期),在日本第 6届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首相吉田茂在对国会的答复中解释说,“日本国家已经无条件投降”。然而,1978年,文艺评论家本多秋五与江藤淳之间展开了“无条件投降论争”。此后,东京大学国际法教授高野雄一在《朝日新闻》报纸上进行解说,认为日本投降与德国不同,承认了日本政府的存续,因此,江藤淳主张的日本投降并非无条件投降,是正确的。此外,一些极端人士总是一厢情愿地将《波茨坦公告》第5款“以下为吾人之条款(Following are our terms)……”篡改成“以下为吾人之条件(Following are our condition)……”。其逻辑是,既然同盟国对日本国提出了投降条件,那么,这也属于“日本有条件投降”。这类言论将同盟国在《波茨坦公告》中向日本下达的命令或要求,视为同盟国与日本的协议,殊为牵强附会。
鼓吹“有条件投降论”的动机在于,依据《波茨坦公告》第13款“吾人劝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主张法庭管辖权所涉对象仅限于审判日本武装部队成员,从而否定法庭审判日本国和政府领导人的权限。但是,“有条件投降论”无视一个重要的史实,即《波茨坦公告》第8款规定:“开罗宣言诸条款必将实施……”,而《开罗宣言》第三项目标就是必将这场反侵略战争进行至日本国无条件投降为止。无论是《开罗宣言》还是《波茨坦公告》,其针对的义务主体都是日本国,不单是日本军队。
战败国日本理应知道,既然日本无条件承认了包括《开罗宣言》在内的所有条款,惩罚侵略的对象当然涵盖包括组织、策划和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国家和政府领导人,这是无可争辩的。《波茨坦公告》第13款的表述,恰恰反映了日本军队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主体,故而同盟国给日本过渡政府下达通牒,要求日本过渡政府必须将无条件投降命令全面落实到日本军队。因此,从逻辑上讲,落实无条件投降的义务主体是代表日本国的日本政府。
到了2007年2月9日,安倍首相在众议院,就议员铃木宗男提出的关于无条件投降定义的质问时,称:很难对无条件投降的定义作出一般性陈述,并且(关于日本是否无条件投降)存在各种观点。安倍的言论,无疑是在给日本学术界极端势力全面否定东京审判的言论保驾护航。受日本学术界“日本有条件投降论”的影响,中国国内也有学者主张,1945年9月2日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由天皇和政府代表重光葵、武装部队代表梅津美治郎签署的投降书,亦不能理解为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其理由是投降书的用词为:“我们兹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及在日本控制下驻扎各地的日本武装部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可是,“日本有条件投降论”鼓吹者全然罔顾以下事实:这份投降书冒头言明,代表日本天皇、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接受《波茨坦公告》和苏联附署的公告各条款。况且,所谓的“日本大本营”,其最高统帅是日本天皇。而且,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举行受降仪式时,日本陆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递交给中国的《日本投降书》冒头言明:“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已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此外,劳特派特(Lauterpacht)就战争概念指出:战争是国家之间为着彼此制服的宗旨而进行的武力争斗。同理,同盟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也是国家之间武装冲突的法律状态。因此,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当然指向日本国国家。
三、“不变更天皇统治大权说”的虚假性
(一)极端人士杜撰日本对《波茨坦公告》的保留
有国内学者甚至对日本无条件投降进行全盘否定,宣扬:这是美国经过反复辩论和利益权衡后作出的政策抉择,并对日本最终提出以“不变更天皇统治大权”为前提接受《波茨坦公告》,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日本则利用这一考虑,“不仅成功地护持了国体,而且还成功地使天皇制国家的内核保留至战后”。因此,认为“日本无条件投降”,是一个“错误常识”。
所谓“日本最终提出以‘不变更天皇统治大权’为前提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说辞,是指日本乞降照会。1945年7月26日,同盟国发布《波茨坦公告》后,同年8月10日瑞士将日本乞降照会转发给美国国务卿。其中,日本言明,日本政府准备接受1945年7月26日由美国、英国以及中国政府,以及后来由苏联政府签字的在波茨坦发表的联合宣言中所列举的条款,但应取得如下谅解,即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有损于陛下作为至高统治者之特权的要求。日本政府真诚盼望这一谅解能得到保证,并迫切希望能很快地获得对上述谅解的明确指示。
该照会强调日本在接受《波茨坦公告》时,提出了“不变更天皇统治大权”之“保留”。该“保留”是否成立,不仅关系到历史事实还涉及国际条约法中保留的基本概念。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条规定:所称“保留”者,谓一国于签署、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条约时所作之片面声明,不论措辞或名称如何,其目的在摒除或更改条约中若干规定对该国适用时之法律效果。换言之,即使日本国对通牒日本的《波茨坦公告》提出“保留”,也须同盟国接受其“摒除或更改条约中若干规定对该国适用”时,才具有法律效力。
四大国委托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F. Byrnes)于8月11日给出答复:天皇与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利,即须听命于盟国最高司令官,该司令官将采取其所认为适当之各项步骤,以实施投降条款……依照《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的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事实上,复文丝毫没有改变《波茨坦公告》任何条款的内涵,俱与《波茨坦公告》精神一致。以“天皇与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利,即须听命于盟国最高司令官”作为回复,实际上已明确地将日本的国家元首置于同盟国主权之下,完全没有顾及日本提出的“不包含任何有损于陛下作为至高统治者之特权”的保留愿望。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正式签署投降书,由天皇与政府代表重光葵以及大本营代表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国履行签署义务,标志着日本毫无保留地承认了包括《开罗宣言》之条件在内的《波茨坦公告》。日本国接受无条件投降,当然包含接受同盟国对任何发动侵略战争的罪犯绳之以法的惩治手段。日本天皇裕仁也是这样理解的。日本宣布投降后,裕仁天皇首次拜会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时曾表示“我是作为对我国人进行战争时,在政治上和军事方面所作出的一切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负责任的人来到这里的,是向你所代表的那些国家投案并接受审判的。”显然,根据《波茨坦公告》《同盟国回复日本乞降书》以及《日本投降书》,同盟国完全有权处罚天皇、消灭天皇制。
同盟国最终没有审判日本天皇甚至保留天皇的外在形式,不是基于任何国际法上的义务,而是出于自身利益的综合考虑。这与日本单方面提出的保留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换言之,权利主体有权放弃权利,但义务主体无权不履行义务,这是一项基本的法理原则。同盟国没有审判日本天皇,属于对权利的放弃。
(二)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同盟国对其体制的改造
1945年8月30日,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抵达战败的日本后,命令日本成立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希望日本能制定防止帝国主义复活的新宪法。但日方提交的草案依然规定,天皇享有国家最高权力。美国人看到新宪法修改草案后,彻底失去了对日本临时政府的信心。
麦克阿瑟的意图是既要在形式上保留天皇制度, 又要推行对天皇制度的民主改造。美国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 认为保留天皇制有助于建立一个稳定的服从于美国统治的日本, 最终采取了对战前天皇制度实行民主改造的方案。1946年2月3日, 麦克阿瑟向占领军民政局局长惠特尼(Whitney)出示了史称“麦克阿瑟笔记”的宪法修改三原则:(1)天皇为国家元首。皇位世袭。天皇依据宪法行使其职责和权力。(2)废除国权发动的战争。日本放弃以战争手段解决国际纠纷、维护自己的安全。日本的防卫和保护将委托给世界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崇高理想。将来日本也不应拥有陆海空军,日本军队没有交战权。(3)废除日本的封建制度。
日本政府试图抵抗麦克阿瑟草案,但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还是接受了,并于3月6日公布了几乎是麦克阿瑟草案翻版的《修改宪法草案纲要》。该纲要经过第十九届帝国议会修改审定, 于10月7日获贵族院和众议院通过, 11月3日向全国颁布。1947年5月3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和平宪法最终面世。战后日本宪法是在同盟国最高司令官的监控之下起草的,将日本由君主政体改变成人民主权的国家,政府听命于人民创建的国会,剥夺了天皇实际掌控国家的权力。虽然同盟国没有彻底废除天皇,但日本帝国的天皇制度已经被消除。如今的日本天皇仅是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不再是三军统帅。根据战后日本的实践,所谓日本“不变更天皇统治大权”的说辞与事实严重不符。
四、《巴黎非战公约》禁止性规范构建惩治侵略罪行的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于1920年建立了第一个全球性国际政治组织——国际联盟,并对于诉诸武力解决争端,规定了强制性调解的程序性规定。在国际社会禁止侵略、维护主权的强烈愿望之下,1923年国际联盟还制定了侵略定义的草案。1928年制定的《巴黎非战公约》,明确地禁止缔约国行使武力解决争端。二战爆发之前,《巴黎非战公约》的加入国已有63个,未参加的国家有阿根廷、玻利维亚、萨尔瓦多、乌拉圭四国。国际社会于1933年缔结了与《巴黎非战公约》内容大致相同的《拉丁美洲非战条约》,有20个国家参加,包括上述四国。因此,《巴黎非战公约》的原则已经获得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承认。《巴黎非战公约》开创的禁止诉诸武力原则,是在全世界谴责侵略、视其为罪恶行为的背景下创立的。
传统的战争法规的主要内容是交战法规,即在国际武装冲突中规范交战各方行为的法律规则和原则。这些规范战争手段、方法以及对非战斗员进行保护的法律规范以人道为基础,又称国际人道主义法。《巴黎非战公约》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后,意味着战争法规中增添了以“禁止诉诸战争权”为内容的开战法规。概言之,“惯例战争罪”属于违反交战法规之行为,而破坏和平罪则属于违反开战法规之行为。
辩护团动议(第五项)声称:规定实施《波茨坦公告》的投降书所载战争罪,仅指违反本公告发布当时国际法所承认的惯例战争法规的行为,本法庭不能对其他事项作为战争犯罪进行审判。这意味着,日本律师辩护团认可法庭享有对武装人员违反“惯例战争罪”进行审理的管辖权,而否定依据《东京宪章》授权法庭管辖的破坏和平罪。其理由是,《巴黎非战公约》仅禁止诉诸武力解决争端,实施武力将被认定为非法而应受到谴责,但是它没有涉及犯罪和惩罚问题。因此,法庭审判日本国家领导人是缺乏管辖权的,也是非法的。
法庭上辩护律师仅认同法庭对战争罪的管辖权,其逻辑为交战法规与开战法规的结构不同:二战前,交战法规不仅有禁止性规范,还有明确的惩罚性规范;而作为开战法规的《巴黎非战公约》,止步于禁止性规范而缺乏惩罚性规范。因此,法庭对破坏和平罪无权管辖。事实上,在二战前,无论是交战法规还是开战法规,两者的构造并无差异,均为禁止性规范并无惩罚性规范。即使是相对成熟的交战法规《海牙第四公约(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也不含有惩罚性规范。因此,辩护团动议(第二项)鼓吹的《巴黎非战公约》既没有扩大战争犯罪的含义,也没有把战争本身定性为犯罪的观点,完全违反逻辑的同一律。国际法的实践表明,传统国际法中的战争法规只要有禁止性规范,就暗含惩罚性。只承认法庭对惯例战争罪的审判,而排斥法庭对破坏和平罪和反人道罪的管辖,毫无逻辑可言。
此外,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形成的国家责任制度表明,违反国际义务的国家须承担国家责任。因此,受害国有权行使各类反措施。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开始编撰国家责任条款草案,1979年拟定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将国际不法行为分为“国际罪行”和“一般国际不法行为”两类。由于一些国家的反对,2001年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修正草案以“严重的国际不法行为”取代了“国际罪行”,理由是国际社会缺乏对集体的权威。即便如此,也不妨碍归纳出习惯国际法中长期形成的共识,任何国家只要严重违反了国际义务,就必然遭到反措施的处理。事实上,同盟国的权威来自日本无条件投降。可见,在传统国际法中,对于严重违反国际法禁止性规范的国际不法行为,受害国始终有权利采取反措施,无须依赖惩罚性规定。只是,反措施不得违反比例原则。
《波茨坦公告》第10条规定:“吾人无意奴役日本人民,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其审判的对象不限于战场上违反交战法规的行为人,也包含组织、策划、发动侵略的领导人。从《波茨坦公告》使用的“战犯”或“战罪人犯”(war criminals)来看,它与(狭义的)战争罪表述和内涵都不同。战罪人犯是指违反开战法规或交战法规的犯罪行为人。而战争罪是违反交战法规的罪名。实际上,以战争罪之罪名惩治违反惯例战争规范的军人,也是首创于《纽伦堡宪章》和《东京宪章》。因为,一战结束后的莱比锡法庭,对于违反惯例战争规范的军人,判决书中没有使用“战争罪”,而是以“暴行罪”为后缀的罪名施以判决的。可见,《波茨坦公告》中审判战争犯罪的内涵,不仅包括违反交战法规的战争犯罪,也必然涵盖违反开战法规的战争犯罪。
五、“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不具强行法性质
辩护团动议(第四项)主张,“《东京宪章》之规定属‘事后法’,故属非法。”对此,日本国际法学者大沼保昭在其著作《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中认为:如果仅以当时存在的国际法为判断基准的话,不能认定“破坏和平罪”就是国际法上的犯罪。罪刑法定主义在保护个人的权利方面是人们所希望的,是正确的原则——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而且,罪刑法定主义正在当时的国际法上逐渐确立。这样,以“破坏和平罪”给予个人以重罚,不能不说是有问题的。实际上,这一观点并不成立。
法不溯及既往,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是现代西方的法律格言,主张只有在行为发生时明确确定了犯罪本身和相应的惩罚,行为才能受到惩罚。可以说,现代民主国家的国内法都明确规定禁止溯及既往原则。但需要澄清的是,该原则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并非如此。强行法(jus cogens),又称绝对法或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意为必须绝对服从和执行的法律规范,是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在国际法领域不具有强行法性质。
事实上,二战前,“罪刑法定原则”尚不属于国际法范畴,只是一些国家国内法的司法原则。同时,罪刑法定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规定差异甚大。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实行成文法制度,罪刑法定原则通常明确体现在宪法与刑法之中,并在刑罚设定方面具有清晰具体的法律依据。相比之下,英美法系国家虽亦存在成文立法,但整体上更依赖习惯法与判例法的发展与积累。法律适用过程在英美法系中更侧重于司法解释,其法律运行机制体现出强烈的解释性与实践性。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卡多佐所指出的,普通法不是从普世预设的真理和不可改变的确信出发,推导出的结论。它的方法是归纳的,它从细节中得出结论。
国际法的效力依据来自国家之间的协调意志。换言之,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可以依据既有的禁止性规范,追索严重违反禁止性规范所应承担的国家责任,而不受“法不溯及既往”的羁绊。关于“条约不溯既往”的格言,《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8条作出了有例外的一般规定:“除条约表示不同意思,或另经确定外,关于条约对一当事国生效之日以前所发生之任何行为或事实或已不存在之任何情势,条约之规定不对该当事国发生拘束力。”其中所谓“例外”,是指在缔约国之间另有约定的情况下,条约的效力可以溯及缔约国以前所发生之任何行为或事实或已经不存在之任何情势。可见,法律不溯及既往在国际法领域中不是一项强行法。从法律效力的依据来看,破坏和平罪是在同盟国与战败国日本的共同意志之下创立的。
况且,“法无规定不为罪”的格言并非对主权的限制,而是关于正义的一般原则。“罪刑法定”的基本要求是国民能够根据刑法规范预测自己行为的后果,从而明确地知道何种行为被刑法所禁止而慎行。侵略行为在被告人实施之前就已经被禁止。被告人既然应当知道,违反交战法规禁止性规范者要被处以惩罚,也就应当预见违反《巴黎非战公约》禁止性规范者也将会受到惩处。此时,惩处被告并非远离公正,如果允许其逍遥法外,才是不公正的。
二战后,审判战争罪犯和法西斯分子的实践,使各国刑法学界对法不溯及既往的局限性有了充分认识,法不溯及既往必须服从更高的人道主义原则,这在一些战后签订的人权公约中有所体现。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之行为或不行为,于发生当时依内国法及国际法均不成罪者,不为罪。”但该条第2款紧接着规定:“任何人之行为或不行为,于发生当时依各国公认之一般法律原则为有罪者,其审判与刑罚不受本条规定之影响。”可见,极端人士鼓噪的“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丝毫无损于东京审判的合法性基础。
余论
回看辩护团动议(第一项)的鼓吹,其无视了以下史实,日本国签署的投降书第8项明确承认:“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利,应置于为实施投降条款而采取其所认为适当步骤之同盟国最高司令官之下。”毋庸置疑,《东京宪章》的效力依据源自四大同盟国与日本国达成的共同意愿。
“东京审判”的本质是以国际法制裁日本军国主义。因此,对于抹黑东京审判的谬论,应当直面其所谓法理依据,以国际法基本原理和习惯国际法的实践,全面论述国际法制裁日本侵略行为和反人道暴行的正当性,彰显法庭管辖权的程序性正义和法庭判决的实体性公正。
当然,东京审判并非十全十美,一些严重的反人道暴行未得到清算。例如,日军在中国实施化学武器作战、细菌武器作战、细菌活体实验、实施随军“慰安妇”性奴役制度、强掳中国“劳工”等暴行,均未被纳入清算门槛。但是,东京审判无论在司法程序性管辖权还是在法律适用方面,都具备坚实的法律基础,完全符合程序正义或实体正义。东京审判不仅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在推动国际刑法处理战争犯罪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外,与东京审判密切关联的《开罗宣言》,其原则立场表明:即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战败后,同盟国也不会剥夺日本固有的领土。这一确保战败国固有领土主权完整原则,标志着以武力吞并他国领土的时代已经结束。因此,日本是东京审判的受益者。从长远来看,东京审判也是日本人民从日本军国主义禁锢的思想中获得解放的开始。东京审判从源头上震慑了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为推动实现世界和平创造了新规范,这是值得人类世代铭记的伟业。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王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