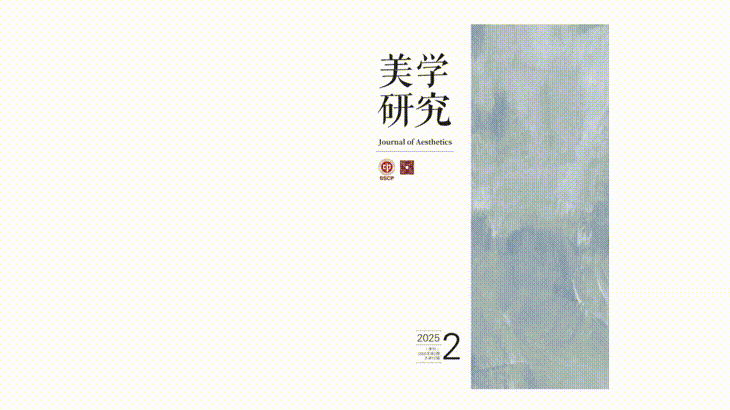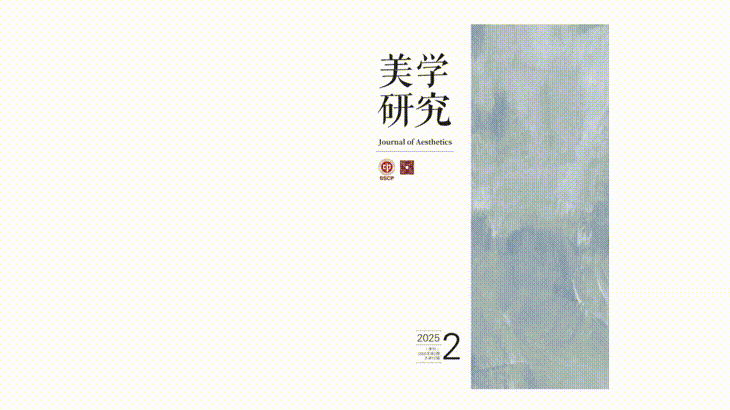
晋宋之际,荆州名士宗炳(375—443)遍览长江中游山水,晚年因疾返回家乡江陵,图画所游荆、巫、庐、衡山水于室壁之上,慨叹“澄怀观道,卧以游之”,是为“卧游”。此后,唐代张彦远作《历代名画记》,书中引宗炳“卧游”典故,且全文收录后者的《画山水序》,对其深远高洁之思想品格大力推崇。自此以降,宗炳与“卧游”逐渐绑定,成为宋元明清文人诗画的经典意象。20世纪以来,学术界围绕宗炳及《画山水序》的思想背景做了大量研究,但对“卧游”观念来源的关注不足,尤其是在“以佛解《序》”已成为主流看法的当下,“卧游”愈发面临难以定位的窘境。已有论者指出,《画山水序》与“卧游”是和宗炳所属庐山慧远僧团的教义、禅法存在矛盾的,继而提出“卧游”应解为道教的“存思术”。而荷兰学者许理和(Eric Zürcher)在论及慧远时早已提醒,“寺庙与山林(尤其是名山)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中国佛教的特色,这“无疑”受到了道家或道教的影响。据此,宗炳的山水观及“卧游”观念探源理应回归中土视域。就“卧游”来讲,完全从道教“存思术”解读并不妥当,这忽略了宗炳本人的知识背景与时代思想语境的复杂性。晋末宋初尚处于玄学兴盛之时。结合《画山水序》相关文段释读,可以认为,“卧游”隐含“庄子—嵇康—宗炳”的玄学观念线索。基于此,本文首先对宗炳的道教徒身份进行辨析,然后缘“养生”观念考察宗炳与嵇康的思想关联,进而析明“卧游”与庄子“逍遥游”的遥契关系。
一、自“尚平之志”说起:宗炳的道教徒身份辨析
按《宋书·隐逸列传》,宗炳“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美国学者谢柏柯(Jerome Silbergeld)据此点明宗炳存在道教思想倾向,因为“衡山”是道教圣山,“尚平”乃2世纪的道士向子平。以此为背景,有论者把“卧游”解为“存思术”,即内视冥想的修炼方法,依据有三点:一是宗炳的“道教徒”身份背景,二是认为《画山水序》与道教“五岳真形图”的文献用语相似,三是提出“卧游”观念最早出现于道教经典《太平经》。实际上,除宗炳的“道教徒”身份存在一定模糊性外,其他两点皆难以成立。澄清这三点,是引入嵇康玄学之“养生”论解读“卧游”的必要前提。
首先,《宋书》所谓“尚平之志”,在晋宋时代多用来指隐逸理想,而非道教信仰的标志。按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逸民列传》,“尚平”即东汉“向长”,“子平”是其字,本传没有提及他的道教徒身份,但可以知晓此人隐居不仕、精研《老》《易》、好游山水。这三点也是宗炳本人的毕生写照。更值得关注的是,此前嵇康(223—262)作《与山巨源书》已坦言“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尚、台两人俱为东汉时的山居隐士;《晋书·嵇康传》载叔夜“撰上古以来高士为之传赞,欲友其人于千载也”,此《圣贤高士传赞》更是专列“尚长”一条,为其所立传记盖为现存最早版本:
尚长字子平,禽庆字子夏,二人相善,隐避,不仕王莽。长通《易》《老子》,安贫乐道。好事者更馈遗,辄受之,自足还余,如有不取也,举措必于中和。司空王邑辟之连年,乃欲荐之于莽,固辞乃止,遂求退。读《易》至损、益卦,喟然叹曰:“吾知富贵不如贫贱,未知存何如亡尔!”为子嫁娶毕,敕:“家事断之,勿复相关,当如我死矣。”是后肆意,与同好游五岳名山,遂不知所在。
史载宗炳曾作《嵇中散白画》《尚子平图》,推知嵇康的“尚子平”传记乃其“尚平之志”的重要知识来源,且有效仿叔夜“欲友其人于千载”之意。在宗炳的时代,陶渊明(约365—427年)作《尚长禽庆赞》:“尚子昔薄宦,妻孥共早晚。贫贱与富贵,读《易》悟益损。禽生善周遊,周遊日已远。去矣寻名山,上山岂知反。”谢灵运(385—433)《初去郡诗》亦讲“毕娶类尚子,薄游似邴生。”可见《后汉书》之“向子平”在晋宋士人文中常作“尚子平”。鉴于嵇康的思想地位自东晋以来得到了巨大的抬升与弘扬,晋宋士人多言尚子平应与叔夜不无关联。可以说,“尚子平”乃魏晋士人普遍认可的隐逸高士,“尚平之志”即隐逸不仕、山水逍遥之志,这是嵇康、陶渊明、谢灵运、宗炳等人的共同理想。但又如《宋书》所载,宗炳本“欲怀尚平之志”,继而因“有疾还江陵”戛然而止,一个“欲”字表明他终究未能达至尚子平遁入山水“不知所在”的境界。不过相比之下,唯独宗炳提出“卧以游之”的新途径,足以彰显此命题的珍贵。
至于“结宇衡山”虽说明宗炳特重衡山,却不能作为道教信仰的证据。魏斌指出,“衡山”自魏晋已有道教活动,但道教馆舍诞生于刘宋后期,而佛教迟至南朝末年才入此山。宗炳卒于443年,即刘宋中期,“结宇衡山”之“宇”并非道宇。与炳同时的刘凝之亦“隐居衡山之阳。登高岭,绝人迹,为小屋居之,采药服食”。宗炳之“宇”应类似刘凝之的“小屋”,即山中隐居的普通屋宇。这也佐证“尚平之志”确指山水隐逸理想,与道教信仰无关联。不过,宗炳家族先后有宗繇之(炳父)、宗彧之(堂弟),以及宗尚之、宗高之、宗珍之等。按陈寅恪,六朝天师道信众常以“之”字为名。可知宗氏家族的确存在道教信仰传统。然而,宗炳虽难免受此家风浸染,却非全然的道教信徒,如炳之五子分别名为朔、绮、昭、说、繁,无一“之”字。其孙宗测继承祖风,《南齐书·高逸传》载其遍游衡山且著《衡山记》。 魏斌指出宗测此文不直接与修道相关,其知识来源应为山民或隐居者。这也佐证宗炳一支并不具有明显的道教信仰。更何况,宗炳追随庐山慧远学习佛理众所周知,且有名篇《明佛论》流传至今,此乃前述“以佛解《序》”论者的核心依据。因此,宗炳不能被贸然归为“道教徒”,这就为解构所谓《画山水序》与“五岳真形图”存在关联的看法提供了基本依据。
接着先要点明,有论者之所以将《画山水序》(以下简称《序》)联系道教“五岳真形图”解读,旨在完善“存思”与“卧游”的关联论证:宗炳面对此类山水道图,存思修炼,冥想成仙。但这个思路很牵强。具体来看,此论者一是提出《序》主要沿袭比例缩尺的地图绘制技法,而“没有表现出特殊的绘画思想”,所以与地图性的“五岳真形图”存在交集;二是把“五岳真形图”文献中的“昆仑”“阆风”与《序》的“昆仑山”“昆阆”对应,强调后者“应不是无心之言”;三是认为宗炳的“山水”与《五岳真形图序》(以下简称《图序》)的“山水”相似,后者表述为“五岳真形者,山水之象也”。第一,本文赞同《序》沿袭了地图绘制技法,但此文的重点是讨论山水绘画的哲学性质,这是学术界常将其称作“玄论”的原因。第二,用词匹配至多表明宗炳可能受道教观念影响,而不能过度推论成他在讨论“五岳真形图”,更何况宗炳并非道教徒。第三,《图序》引文的逻辑不是“等于”,而是“包含”:“山水之象”包含“五岳真形”,即“五岳真形”是“山水之象”中的一种;宗炳的“山水质有而趣灵”则是对“山水”本身的定义。并且,《图序》约创作于南朝宋末,所用“山水”义同“山川”,“象”指一般形象,与《序》之兼有审美与哲学属性的“山水”“象”不同。
实际上,“五岳真形图”非常独特:一是“绝对俯视状”或鸟瞰式的平面图,二是形状似怪异文字,即融合“半抽象图像和文本”的“复合文字图”,区别于写实性的地形图。相比之下,《序》既讲“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且未提及文字入画,可知宗炳所论山水图像的画面呈现为平行远视,区别于“五岳真形图”的绝对俯视和“复合文字图”形式。法国学者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虽曾论及中国早期山水画论和道教真形图的相似性,但他明确强调此非断言两者存在直接关联,而是旨在点明一种“共同观念语境”。这种开放性的自觉意识很重要。此外,论者断定“卧游”最早见于东汉的《太平经》。其实,成书于西汉的《文子》已经言及“卧游”:“故通于大和者,暗若醇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谓大通。”就中国古代的美与艺术现象及观念研究来讲,艺术史愈发重视的宗教进路值得肯定,美学史秉持的哲学视角亦不可或缺,囿于任何一极都可能得出不周全的结论。至此,既然宗炳不能归为道教徒,《序》与“五岳真形图”无关,“卧游”也非最早见于《太平经》,那么接下来亟待追问,“卧游”若非道教“存思术”的冥想修炼,那它的观念来源究竟在哪里?
二、“凝气怡身”与“闲居理气”:从嵇康“养生”看“卧游”之缘起
若要回答这个问题,也须从道教谈起。本文虽不赞同完全从道教视角解读“卧游”,但学者们的论述已经触碰到重要的学术生长点,这就是“养生”。如谢柏柯点明《序》之“凝气怡身”“闲居理气”与道教“长生”(Life-prolonging)工夫有关,并指出宗炳的此种观念在其时代有普遍性。陈铮明确言及“作为道教养生术的‘卧游’”,且联系“凝气怡身”强调宗炳“卧游”说蕴含“主动接受养生技术”之意。陈传席把“凝气”“理气”解为“调养气息”“调理呼吸”,且拈出《明佛论》之“松乔列真之术”,提醒关注赤松子、王乔之神仙观念,并点明好慕神仙是汉末晋宋以来的流行士风。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刘纲纪虽坚持“以佛解《序》”,但也肯定“凝气怡身”“和道家与神仙家的养生之术相联”,并将此溯源至葛洪《抱朴子》与嵇康“养生论”。据此可知,“卧游”是与“养生”存在关联的,《序》之“凝气怡身”“闲居理气”是理解这种关联的切入点,魏晋时代的思想语境则是基本参照系。为了析明此论,且将《宋书》与《序》的相关文段援引如下:
《宋书》:(炳)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
《序》: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愧不能凝气怡身,伤跕石门之流。于是画象布色,构兹云岭……又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藂,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峣嶷,云林森眇,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
对读可以发现,《序》可谓“卧游”说的具体展开,或者说,《序》之写作宗旨在于论证“‘卧游’何以可能?”在此,“凝气怡身”涉及山水实地游览,“闲居理气”关乎山水图像鉴赏,自前者向后者的转换类同于从“实游”转向“卧游”。此种移换的现实动因固然是“老”,但更内在的机缘在于“气”。“气”乃“卧游”得以成立的基础。实际上,“气”也是魏晋南朝文艺理论建构的重要元素,如刘勰《文心雕龙》专作《养气》篇探讨“调畅其气”对于作文的重要性,且在开篇处就彰明东汉王充的《论衡》是其依据。同样,《序》之“感类”即“气类感应”亦与《论衡》相关。鉴于《论衡》作为魏晋玄学“首要思想来源”的地位,以及宗炳的荆州名士与《易》学名家身份,“凝气”“理气”及“卧游”诸说理应来源于玄学语境。但按蜂屋邦夫等人的研究,“气”作为中华本有的思想传统,魏晋玄学家如王弼、郭象并不特重“气”,唯阮籍、嵇康、葛洪等人把“气”作为自身理论建构的关键元素,其中又以颇富道教色彩的嵇康之“养生论”最具代表性。在美学史领域,叶朗在论及王充气论哲学与魏晋南北朝气论美学的关联时,也特别举例嵇康与阮籍。
如前文所述,宗炳是服膺嵇康的。但在传统的魏晋玄学话语体系中,嵇康因强调元气自然论以至于难以合理定位,这与他在历史上的典范地位并不匹配,学术界对此已多有论述。与此相应,对嵇康思想的讨论也多偏重道教视角,只是其人毕竟区别于以葛洪为代表的“神仙道教”,所以有学者将其解为“文士道教”的创始人。辨析嵇康、玄学、道教的关联非本文力所能逮,这里是想说明,宗炳及《序》的观念背景争论,以及“卧游”的定位窘境,可以从嵇康身份与思想定位的游移境况中找到“影子”,这侧面反映出嵇康对宗炳等晋宋名士学问旨趣的重大影响。从思想史看,嵇康发明“养生”思想极精、影响极大。按《世说新语·文学》:“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汤一介、王葆玹皆已指出,所谓“言尽意”应作“言不尽意”,所以“三理”不仅俱出自嵇康,更因王导的宣扬而成为东晋以降士人论学的纲领命题。又《晋书·嵇康传》载:
(嵇康)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
作为宗炳之景仰对象,嵇康亦为怀有隐逸理想的玄学名士,故能凭玄思辨理素养将原属神仙方术的“养生”观念发明甚精。概言之,嵇康论述“养生”主要涉及三点:一是肯定神仙存在,凡人无法学得;二是认为凡人通过呼吸、服食的养生方法可以益寿延年;三是将“养生”观念应用于玄论、艺论,乃至山水。需要强调,嵇康否定凡人“成仙”的可能性,表明立场近于玄学先导之王充,远于道教信徒之葛洪。牟宗三就此认为叔夜“已开出成仙之‘限制原则’”。嵇康又以“导养得理”为“养生”基点,主张“内视反听”“遗世坐忘”等,进而将“养生”引至不为外物所累的“君子”境界,《释私论》谓“君子”乃“气静神虚”“体亮心达”,正合乎《养生》二篇之“清虚静泰,少私寡欲”“明白四达,无执无为”。其中体现出以《老子》《庄子》玄理中和道教方术的玄智自觉,或可称为“玄化养生论”。并且,嵇康将“养生”引入“山水”,除“采药游山泽”外,《幽愤诗》自陈:“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又《与山巨源书》:“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小尾郊一认为以葛洪为代表的采药必入名山之道教观念推动了东晋山水游览风气。但确切地讲,嵇康的“玄化养生”与“山水养生”观念及身体力行,对东晋士人产生了直接的范导效应。典例如王羲之“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服食养生”本为养生道术,却因化入山水之游隐然不彰。宗炳本人亦浸润于此种“山水养生”氛围之中,所以会因“老疾”慨叹“愧不能凝气怡身”,进而提出“卧以游之”。
当然,就“卧游”与“养生”的关联讲,“气”是关键元素。嵇康论“养生”尤其重视“气”:“神仙”乃“特受异气”,“人”亦禀“元气”化生,“人”虽无法“成仙”,但经“呼吸吐纳”之“行气”,以及“食气”“易气”达至“体气和平”,益寿延年。相应地,宗炳的“凝气怡身”“闲居理气”之“气”,亦应解为嵇康的这种“具有养生倾向的体内之气”。宗炳《明佛论》又讲:“老子庄周之道,松乔列真之术,信可以洗心养身。”陈传席点明其中的赤松子与王乔神仙术端倪是合理的,但认为宗炳“以不能成仙而自愧”则不尽然。一方面,王乔与赤松子属神仙家之“行气”派,此派自古最显,晚周时已盛行于楚地,《庄子》《楚辞》皆有记录,魏晋之世亦普遍流行。宗炳成长于楚地荆州,“凝气”“理气”的确彰显“行气养生”的观念痕迹。但另一方面,“洗心养身”并非昭明企图“成仙”,而是旨近嵇康《养生论》之“有老可却,有年可延”。此外,戴琏璋认为嵇康养生思想中的“气”接引了汉代的气化宇宙论。杨儒宾则以宗炳《画山水序》为例提出晋宋山水观乃“玄化山水”或“气化山水”,“山水”与“观者”皆由“气”化成,山水鉴赏为“气化共振共游”,进而将此观念来源归为以“有、无、气化”为核心的“玄学本体论”。但在玄学家中,惟嵇康经“养生”把“气”与“山水”作初步关联,此种“玄化气论”应为晋宋山水观的重要思想依据。在此意义上,“凝气”“理气”之“气”便须解为经玄风洗礼而涤除汉代元气论之神秘色彩的新鲜之“气”。“人”唯有秉此新鲜之“气”,方能在一片“山水”气化场域中得新鲜之体验,此即王羲之于会稽山水所得之“适我无非新”(《兰亭诗》)、谢灵运于永嘉山水所得之“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
但与会稽、永嘉所处的浙东丘陵不同,宗炳所登之荆巫山水因险峻而呈现为“萦回盘礴,千变万态”,“或极天高峙,崒焉不群,气胜势飞,合沓相属;或修江耿耿,万里无波,欻出高深重复之状”。此类奇壮山水气势更能启人幽思,故《画山水序》特标“千仞之高”“百里之迥”,且强调“自然之势”:唯“千变万态”之“山水”方能合乎“阴阳变化”之“大象”,唯“高深重复”之“山水”方能于“天尊地卑”之间撕开一道“裂缝”,涌动出刚健不已之“气势”。“人”既由“气”化成,便可缘这股“气势”汇入“山水”,“养生”之“呼吸吐纳”便是“行气”“导气”与“凝气”“理气”,根本上是回还生生不息的“气化共振”原初之际,人既感通于“道”,自然益寿延年。可以说,“养生”在“山水”即气化流行之天然场域中方能完满实现,“山水”可谓“养生”的最佳处所。然而,凡人即便浸润山水,终究也会“老”。宗炳坦陈“老之将至”,表明其深知“成仙”虚妄,故叹“愧不能凝气怡身,伤跕石门之流”。这里的“石门之流”,指古今山水隐逸高士,《画山水序》之“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之流”是也;“伤跕”,“跕”为“跕跕”之省,语出《东观汉记·马援传》之“仰视乌鸢跕跕堕水中”。“跕跕”即坠落之貌,马援见飞鸟坠落联想人生亦如此,引申为黯然退场之义。有鉴于此,宗炳之叹,亦是为不得已从山水养生的隐逸高士之流退出而伤感、遗憾。
宗炳既非神仙圣人,生发此种遗憾伤感当属人之常情。但他作为“善养生者”,能够自伤感中醒觉,“于是画象布色,构兹云岭”,即进入新的“养生”之境,这便是“卧游”。毕竟,“养生”之“无执无为”不等于无所作为,而是“泊然无感”于生老病死,“体亮心达”,慷慨生活。甚而言之,宗炳之“叹”不仅是叹息,更是赞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此乃对人生的热情礼赞。于是,宗炳澄怀以观赏“山水图像”,从“实游”之“凝气怡身”转入“卧游”之“闲居理气”。所谓“闲居”,阮籍《达庄论》已讲“平昼闲居,隐几而弹琴”。“理气”,潘岳《笙赋》:“援鸣笙而将吹,先嗢哕以理气。”唐李善注:“嗢哕,或为温秽,谓先温煖去其垢秽,调理其气也。”又李周翰注:“嗢哕,吐饮之貌。”《庄子·齐物论》之“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此句亦有“行气”的思想痕迹。可知从宗炳之“理气”至阮籍之“隐几”与潘岳之“嗢哕”,皆其来有自。以“行气养生”为基点,“闲居理气”便成为“凝气怡身”的复现,此乃依据“山水养生”发明的“绘画养生”新论。在宗炳看来,“画山水”乃“画象”,“山水图像”与“山水”皆属“象”而契合无间,前者是对后者的完满“拟象”,“人”不仅能经由作为图像的“山水绘画”气化感通“山水”乃至“道”,更可以通过坐卧朝向“画中山水”还原“实地山水”的养生功效,“凝气”即“理气”,“理气”即“凝气”。如此,“山水实游”圆融移至“山水卧游”。
三、“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卧游”与庄子“逍遥游”之遥契
基于前文讨论,魏晋玄学不仅存在由王弼开启的偏重抽象的论理线索,而且包含以嵇康为代表的侧重感性的抒理脉络。宗炳的“卧游”更多处在后者的观念延长线上。倘若进一步讲,“卧游”不仅关乎“玄化养生”的观念背景,而且受到嵇康“游心太玄”之艺术哲学的重要启发,并由此接引庄子“逍遥游”之根源精神。关于嵇康玄学尤其是“养生”论与庄子哲学的关联,学术界已多有论述。相应地,刘纲纪、罗宗强、萧驰等学者指出了嵇康“养生”论与其音乐思想的密切交集,并强调叔夜正是由此充分体认庄子“逍遥游”的精神,继而将庄子与玄学引入现实,“从纯哲学的境界,变为一种实有的境界,把它从道的境界,变成诗的境界”。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宗炳的“卧游”说并非限于纯然的图像观看或绘画鉴赏,而是本然涵摄音乐的维度,因为他讲出“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后,紧接着便是“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序》则将此“卧游”场景具体呈现为“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藂,独应无人之野”。其中,一条隐微的“庄子—嵇康—宗炳”观念理路呼之欲出。
具体来看,《画山水序》并列的“理气”“拂觞”“鸣琴”,已皆为嵇康所重。典例如《养生论》结尾强调“晞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琴艺”不仅是“养生”的重要阶段,更是境界升华的关键。嵇康诗文也常谈及“琴酒交汇”的情境,如“临觞奏九韶”“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并有《酒会诗》七首,其一曰:“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山水之间,风气流动,琴酒与诗歌交相辉映。《闲夜肃清》诗云:“闲夜肃清,明月照轩。微风动袿,组帐高褰。旨酒盈尊,莫与交欢。瑟琴在御,谁与鼓弹。仰慕同趣,其馨若兰。佳人不存,能不永叹。”这里的“闲夜”“旨酒”“瑟琴”,与宗炳的“闲居”“拂觞”“鸣琴”可谓相契。嵇康虽然发明“善养生者”极精,此诗却颇流露伤感之意,其人毕竟是不企成仙的凡俗,这又可与前述宗炳之“愧”“伤”情感参映。据此可知,“琴”与“酒”自魏晋之际已成为山水之游的重要元素,而嵇康更强调“奏琴”应入“山水”,如《琴赋》云:“若夫三春之初……涉兰圃,登重基,背长林,翳华芝,临清流,赋新诗,嘉鱼龙之逸豫,乐百卉之荣滋,理重华之遗操,慨远慕而长思”,最终,在山水琴音共同营造的境界中,“感天地以致和”。此外,嵇康还以“山水”论“琴”,如制琴之木为“惟椅梧之所生兮,托峻岳之崇冈”“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梧桐生于山水之中,饮吸山泽之气,故“琴”与“道”通“气”为一;故琴声也呈“山川形势”,即“状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汤汤,郁兮峨峨”,它因“气激”产生,所以能“感人动物”“导养神气”;制琴者如荣子期、绮里季须飞入山水取材;奏琴者则“若乃高轩飞观,广夏闲房,冬夜肃清,朗月垂光”“器冷弦调,心闲手敏”,这与宗炳之“闲居”“鸣琴”之境界仿佛;听琴者应有“旷远”“渊静”“放达”“至精”的心胸,如《声无哀乐论》总结:“琴瑟之体,间辽而音埤,变希而声清,以埤音御希变,不虚心静听,则不尽清和之极。是以体静而心闲也”。
嵇康关于“琴”之材质、创制、演奏、鉴赏,乃至于琴声本质的哲学探讨,都对宗炳论“画”具有启发意义。基于此,宗炳以“理气”“拂觞”“鸣琴”烘托引出“披图幽对”,旨在创造以“山水图像”为鉴赏主题的气感与养生整体氛围,故而有“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此句不能仅仅理解为宗炳琴技出神入化之效果。琴声之所以使图中山水“皆响”,在于“气化感通”的观念前提:“琴”源自通“气”之“山水”,“琴声”又为“气激”而成;“山水图像”乃“山水”之“拟象”,故呈现为一片“气象”;“人”亦“秉气”化生,故能与“琴声”“山水图像”感通。关于“琴”与“山水”的气化共游场景,南朝齐梁时的一处“商山四皓”画像砖提供了生动参照:在曲动连绵的整体山水之间,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四位或抚琴、或吹笙、或展卷、或濯足。这正是“卧游”之人的期待图景。若更进一步讲,音乐的媒介即“声波”本为“气”,所以“琴声”可以使“气”荡漾流动,“气”因相摩所生之“势”得以更加刚健有力,再配合“酒”之饮用使“人”血气涌动,以至“人”“山水”“山水图像”共融、共化、共游于整体气场中,此即“卧游”之境,亦可谓“逍遥游”。
于是,宗炳的“卧游”终又复归庄子。所谓“坐究四荒”,后接“不违天励之藂,独应无人之野”,此句遥契庄子美学的“独成其天”之旨。“无人之野”是关键入手处,语出《庄子·山木》:“吾愿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游于无人之野。”郭象注为“任其自化”。又《在宥》有“游无极之野”。嵇康《圣贤高士传赞》记楚人“市南宜僚”亦自陈“游无人之野”。但在根源上,“无人之野”源出《庄子·逍遥游》: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
宗炳的“卧游”正旨归庄子的“逍遥乎寝卧其下”。他的“无人之野”通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的“逍遥之境”,所谓“独应无人之野”乃遥契庄子的“独成其天”“以游无穷”“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由此再看“坐究四荒”。需要提及,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宗炳面对山水图画乃“坐卧向之”。这既可与“坐究四荒”参看,更提醒“卧以游之”并不限于躺卧的姿态,而是坐卧皆可,换言之,“卧游”是不拘泥身体动作的,它的重点是鉴赏山水图像通达“游”的境界。“四荒”,《楚辞》已有《离骚》之“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远游》之“经营四荒兮,周流六漠”;又按《尔雅·释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西晋郭璞注:“觚竹在北,北户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东,皆四方昏荒之国,次四极者。”不过,《序》之“四荒”或非四处明确地点的有限指称,而是对四极远方之地的无限想象。进而言之,“坐究四荒”既秉承《离骚》《远游》之遥望“四荒”的诗性理想,更通往庄子之“游乎四海之外”“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的“游心于澹,合气于莫”,以至于“游乎天地之一气”。这在嵇康那里,则是“游心太玄”以及“游心大象”“栖心于玄冥之崖,含气于莫大之涘”的超拔精神。
至于“不违天励之藂”,刘纲纪、朱良志皆将“天励”解为“天厉”,即天之威严。福永光司认为,“天励”原作“夭厉”,指灾害,并引《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之“盗贼公行,而夭厉不戒”,以及《汉书·严安传》之“民不夭厉,和之至也”为据。按杜预注,《左传》之“厉”确指“灾”;又阮元校勘“夭厉”应作“天疠”,但“夭疠”亦可。而颜师古注《汉书》之“厉”为“病也”。综而论之,《画山水序》之“天励”或原作“天疠”,含义姑且解为:天不假年,因病夭折。宗炳既自陈“老疾俱至”,且“不救所病”,表明其深知生老病死的自然道理不可违背,所以有“不违天励”之说。这也是嵇康谓“善养生者”的“无执无为”境界,并在根本上契合庄子的“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郭象注为“任理之必然”。可见宗炳“不违天励”人生态度的观念渊源。“藂”通“丛”,指聚集或群体。那么,“不违天励之藂”应解为:顺应生老病死的自然道理。当然若从艺术哲学角度看,所谓“不违天励之藂,独应无人之野”一句更贴近于嵇康:“琴诗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怡志养神。”唯宗炳把诗里的“琴”“诗”移至“画”,且论及“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与“贤者通”,进而强调山水绘画能够使人“畅神”,故其“卧游”说显出的境界,终究是比嵇康此诗更加开阔了。
至此总结,宗炳的“卧游”指“人”通过鉴赏“山水图像”或“山水绘画”,并配以“养生”之呼吸吐纳与琴酒渲染推荡,气化共振感通于“道”的“逍遥”之境。萧驰曾提及嵇康的“养生实践在‘清虚静泰’之余,须‘绥以五弦’,更直接是艺术成全‘至乐’生命的表白”。相应地,宗炳的“养生”亦在“澄怀”“理气”之余,须“画象”“披图幽对”以效仿嵇康,并用“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化叔夜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之“人在天地之间一个最美的姿势”进入“卧游”:庄子与嵇康是我的老师,当鸿阵嘹喉着自天穹下缓缓掠过,当藐姑射神人乘云气御飞龙逍遥游过,画家凝睇间蓦然会意,手指亦不自主地挥毫布色成云岭——这是以绘画的心灵,亦是以音乐、以嵇康、以庄子的心灵,去感悟天人之间的律动;在画家盘桓身目恋眷山水之际,是一片新鲜氤氲气象,是心灵放开,任山水自去归、人自去挥兹的活泼泼空间;此灵动的空间是庄子与嵇康对宗炳、对绘画的大赠与,是心灵逍遥游的无限境域,故而画家“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跃入宇宙自然的节奏中,感受其中难言的“大音”;《序》文末更以“圣贤”一词前承“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即“石门之流”,后启“万趣融其神思”,并设问“余复何为哉?”且自答“畅神”,暗示这晴明中的恍然憬悟,“图像”之“峰岫峣嶷,云林森眇”就是“大象”之“庐、衡、荆、巫”;至于“神之所畅,孰有先焉?”一句再行自我设问,上接“山水养生”的古今高士,同时扣住“画山水”的文章标题,彰明“画中山水”与“实地山水”完满契合,所以“畅神”之功,无有高下。在这里,“畅神”应看作对“卧游”的升华表达,如嵇康诗云:“思与王乔,乘云游八极。思与王乔,乘云游八极。凌厉五岳,忽行万亿。授我神药,自生羽翼。呼吸太和,练形易色。歌以言之,思行游八极。”琴画殊途,“游”旨同归。宗炳关于“畅神”的感慨与重复设问,正与嵇康对“游八极”的复叙契合,皆是对逍遥游乎无限天地的吟咏与向往。
徐复观曾点明,“庄子的逍遥游只能寄托于可望而不可即的‘藐姑射之山’;而宗炳则当下寄托于现世的名山胜水,并把它消纳于自己的绘画之中”。若就本文来讲,宗炳的这种“消纳”,正体现在将庄子的“逍遥游”落实为“卧游”。进而言之,“卧游”说旨在将山水绘画接通“逍遥游”的万化无极境界,所以可看作一个绘画或图像哲学论题。倘若从更加广远的山水美感之文艺表述视域考量,正如萧驰所言:“中国诗人在山水中至高的精神体验,是一种冥契,即在感应山水时倏然体验到与宇宙终极性的合一状态,这一刹那之间发生的感受是愉悦甚而神圣的,而诗人却难以述说。”诚然,所谓“冥契”“感应”“终极性的合一”等话语固然可用来描述山水美感,但皆不如“游乎天地之一气”或者“卧以游之”来得更加妥帖。更何况,山水美感既然为诗人所难以述说,画家的登场便成为应有之义,故而自晚唐五代以降,山水诗文式微,山水绘画却愈发兴盛。至于千年以后,作为读者与观者的我们,依旧能从山水诗文与山水绘画中体会到那股天地生意,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卧游”?
结语
可以说,宗炳的山水思想深深扎根于玄学语境。正如叶朗指出:“魏晋玄学是魏晋南北朝艺术的灵魂,也是魏晋南北朝美学的灵魂。”本文可谓按此种美学史研究法做的个案尝试,没有玄学视角的引入,就无法洞悉“卧游”关涉的“庄子—嵇康—宗炳”观念演进线索。在魏晋玄学领域,杨立华已提出有必要挣脱玄学话语束缚以更深入地把握魏晋思想。胡海忠亦接引强调突破既有玄学研究范式以重构魏晋思想的解释框架。有鉴于此,美学史论者理应关注魏晋玄学的新进展,以期在具体论题上开启对话,毕竟,士人玄谈并不限于“言意之辨”,“声无哀乐”与“养生”同样重要,此类论题本就体现出玄学和美与艺术的互渗交融。以宗炳的“卧游”说为切入点,重思嵇康玄学及其山水实践对晋宋南朝文艺理论乃至山水诗画革新的范导影响,便是值得考量的思路之一。如西晋陆机以“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论文章创作,李善与包咸皆注为“不视不听”。其实,“收视反听”通达嵇康《养生论》之“内视反听,爱气啬精”,不是“不视不听”,而是“视返于听”,亦即庄子的“听之以气”以至“虚而待物”,如此方能“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继而在刘勰《文心雕龙》化为“视通万里”“神与物游”。此中真意,正是宗炳《画山水序》的“披图幽对”“万趣融其神思”之理,“幽对”乃“内视反听”,返于“听之以气”才能“卧以游之”,感通万物生趣或一片气化生意,即“游乎天地之一气”的庄子精神。又王微《叙画》讲“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风”与“云”皆“气”,“气”通“神”与“思”,如此卓然拥抱大化的心胸是庄子的心胸,也是嵇康、陆机、宗炳、刘勰的心胸,亦即一团生气活泼的“游的心胸”。如果说庄子“由工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本无心于艺术,却不期然而然地会归于今日之所谓艺术精神之上”,那么魏晋南朝士人已是“有心于艺术”,正因为“有心”,才能自觉援引庄子“游”的哲学论述美感与文艺体验中最玄妙的道理,最终成就了“中国美学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胡海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