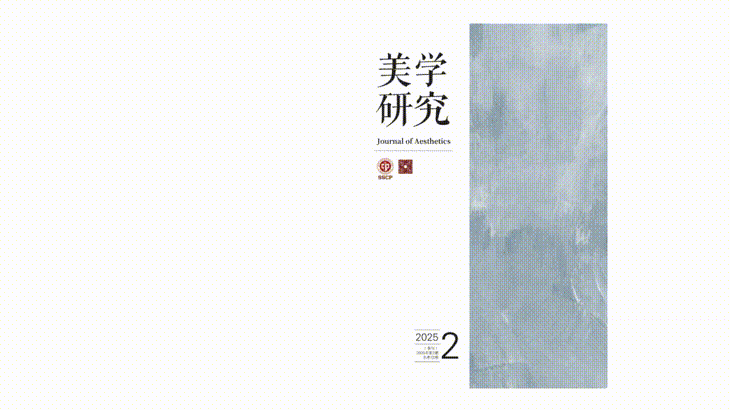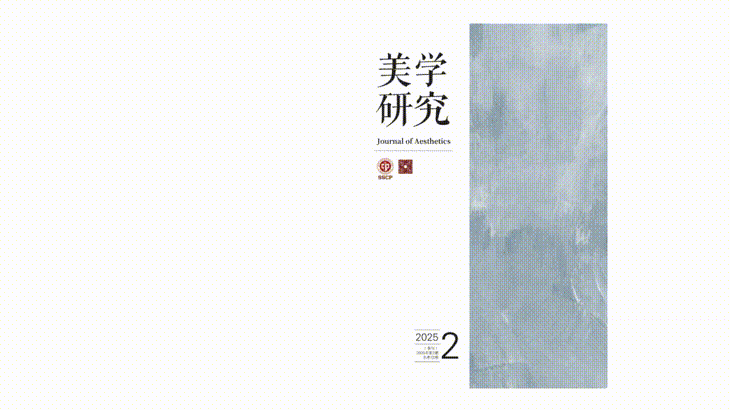
在现代学术视野下,传统的“阴阳五行”思想就是一种“被拒绝的知识”,其无所不包的类比思维将宇宙万物囊括进一种平面秩序,构筑了恢宏富丽的宇宙政治论秩序,并朝向天人合一的目的论视野。然而,这一仰赖天人感应的存在秩序早已褪尽光环,成了前科学时代“原始思维”的遗迹。“到了二十世纪以后,五行论在漫天遍野的‘科学主义’的压迫下,它基本上被贬放到理性之光照耀不到的黑暗角落。但五行论的命运一定要如此凄凉吗?”在《五行原论:先秦思想的太初存有论》(以下简称《五行原论》)这本著作中,杨儒宾如此发问,这一忧思指向了勘探五行原貌的决心。于是,这本著作以“物”立论,以此追溯五行的源初力量。具体而言,五行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儒家的政教模式、阴阳家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模式以及传统科学中畴人运用的认知模式,该书的探究重心是第三种知识论的用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五行具备认知功能,但其绝非中立透明的知识结构,其知识论价值只有与主体转化问题放在一起才是有意义的。该书对五行范畴的探讨,并非要重启其奠基于万物类比基础上的认识功能,而是要探究五行认知范型的主体根源和依据。本文以《五行原论》为起点,从神话和象思维角度探讨五行物象论的认识和思想潜能。
一、神话经验与工夫论传统
尽管《五行原论》以五行范畴为论述对象,读上去却更像是一部中国神话学专论。杨儒宾给予了华夏上古神话充分信任,既追溯了五行观念背后源远流长的华夏上古神话土壤,也援引了西方神话理论范畴,更关注神话经验在主体转化方面的重要意义。在横跨古今中西的学术视野中,五行的鲜活与庄重感扑面而来。神话为何在这部著作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实际上,《五行原论》与杨儒宾的另外两部著作(《原儒:从帝尧到孔子》《道家与古之道术》)共同构成了一个思想整体,分别从原型象征、儒家和道家三个角度探索了诸子百家兴起之前古代中国的源初义理,其核心思想议题都延续着他对“天人鬼神交通”的持续性关切。这一思想图景可置于“从神话到哲学”的议题之下,构成了理解古代中国思想演变的途径之一。不过,古代中国有神话之实而无神话之名,能够与神话对应的思想形态,可名之为“古之道术”。
“古之道术”应指哲学之前的原始宗教,可笼统地称呼为巫教。巫教的实践面向是仪式,或可以旧名“礼仪”称呼之;它的叙述面向也就是教义面向,可称作神话。杨儒宾认为:“从‘古之道术’到东周时期的‘天下方术’,可以简化地说即是从神话到哲学的历程,也可以说是从前哲学到哲学的历程。”
就认识论层面而言,从“古之道术”到“天下方术”的转化的确类似于“从神话到哲学”的变迁,都是人类认知意志从存在整体中脱身而出的结果,源自神或一的权威逐渐让位给人类主体的理性构造。但在价值取向上,两者却截然不同,从神话到哲学的演变是“希腊奇迹”的光荣,是逻各斯战胜秘索斯,是理性对非理性的胜利,更是人类认知史的巨大进步。在先秦诸子思想视野中,从道术到方术的演变绝不是进步,反而会导致“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可悲局面。作为知识形态,道术“皆原于一”,关联于人在世的源初整全姿态,方术却是“一曲之士”的知见,致力于辨名析理的智性活动,有着走向形式逻辑,并以名相和逻辑去对象化和奴役万物的趋势。
以“古之道术”观之,能够与“从神话到哲学”构成呼应的思想范式其实是古代中国的巫史传统,即从巫教时代向人文理性的过渡。就儒家传统而言,这一思想迁移呈现为从神话意识向经学意识的转化,即“灵魂论的、情念性的、脱体论的文化表现凝聚于肃穆的主体性意识中”。然而,无论是从巫教到人文理性的转化,还是从古之道术向天下方术的变化,都不能被“从神话到哲学”的思想范式所涵盖,因为神话与哲学的分立和进化原则并不适用于解释古代中国的思想演进,由巫入史的理性化进程并没有切断巫教保存的集体性神话体验,这一体验经历了连续性和创造性转化,反而构成了主体转化的重要精神资源。杨儒宾对神话的兴趣亦在于此,即“神话意象与工夫论的主体经验关联甚深”。
儒家经学意识可溯源至上古巫教,这种精神转换在《原儒》一书中得到了充分论述,巫教中蕴含的恍惚伦理绝非怪力乱神之物,反而是儒家工夫论的精神源头。依此思想脉络,杨儒宾将五行认识范型的主体根源定位于性命之学的工夫论传统之中。在心学工夫论传统中,“物”的意识也历经变迁,“近世的第三系儒学与先秦的原始儒家都能赋予‘物’本体论的意义,关键的因素在先秦时期是‘圣感’所致,其理论建立在神圣的辩证上面;在北宋与晚明则是道体之下贯,其理论建立在体用论的基础上”。从先秦圣显之物到道体论哲学的格物之思,五行物论处于中间阶段,标志着神圣的物感意识逐渐转变为蕴含着自然原型的认知范型,就此而言,依托于五行的认知实践,既非圣物崇拜的拜物意识,也非得意忘象的自我证悟,而是与物象流转密不可分的体认过程。除心学工夫论外,还存在物学工夫论,即“物学的工夫论和性命之学的工夫论极为相关,没有心的转化即没有真正的物之呈显”。心学工夫论和物学工夫论是心物交接的一体两面,凸显了心物交接的物象中介。
五行之“物”朝向“物象”的转化是该书的理论焦点,这种转化依赖双重思想资源,一是西方宗教与神话学的理论资源,二是从先秦至宋明儒学的工夫论传统。这一双重脉络也彰显了在当代学术视野下重释儒家工夫论传统的意义所在,即“不能由于现代西方学术分类的限制而幻想在与西方现代学术绝缘的情况下以回到‘旧学’的方式实现,只能积极主动地在与西方现代学术深度互动与交融的过程中达成”。在这一双向阐发过程中,杨儒宾将工夫论的心学维度引向物学维度,试图让物学工夫论成为与心学工夫论并驾齐驱的一极,这一另辟蹊径的划分并不导向心物二分,而是对心物交接之源初感通状态的绝对肯定,从而抗衡超越性的道德主体,并为“气化主体”重新定位。
简言之,五行认知范式的主体根源就在心物交接的工夫论体验之中,在这一源初心物关系之中,既不是主体占有物,也不是物湮没主体,而是气化感通与世共化的状态,即“不是认识,不是利用,甚至也不是美感的欣赏,而是一种气感的流通。在此气感的流通中,一种尚未明文化的‘理’已酝酿其中”。这一状态指向了“气化主体”的生成。在杨儒宾的论述中,气化主体是理解庄子思想的密钥,是心性论与本体宇宙论的共同展开。气化主体绝非孤立存在,而始终与世共在,“始源的实相就在气化主体的框架本身”。作为始源实相的主体性框架,将心物共化的源初境遇作为世界的伦理根基。气化主体也是新儒家哲学的落脚所在,并成为五行认知范型的主体依据。不过,对“气化主体”的探讨仍偏重于心学工夫论的面向,该书的核心则在于对物学工夫论的阐发。
二、五行创世神话的物象剧场
《五行原论》的起点与重心都聚焦于“物”,“物”不能脱离心学立论,五行之“物”并不是纯粹的自然客体或物质元素,而是经由心之构造生成的物象,从物到物象的转化是理解五行范畴的一个基本前提。借助于伊利亚德的“神显”(hierophany)和“力显”(kratophany)范畴,五行从金木水火土之“物”转化成了神圣的“物象”,依此构筑了化生万物的物象系统。在学术界,圣显有诸多译名,其内涵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圣显物”,类似于拜物教意义上的“物神”,指向物的客体或偶像面向;二是“神显”或“圣显”,这一译名强调“显现”的意味,凸显物在意识乃至视觉中的显现方式。五行之物同时包含了这两个方面,即五行“既是那个时代在自然界中存在的‘圣显’之物,也是与人的意识构造结合在一起的神圣意象”。作为一种圣显物,五行物象突破了“形式想象”的范畴规约,是带有物性色彩的自然原型,具体化在构筑世界的元素本源之中。除“圣显”外,“力显”亦是理解五行的一个重要范畴,它彰显了五行转化的内在动力,这一活力是物之活性的体现,也是质料能动性及其沟通转化的活力,构成了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内在动力。“圣显”揭示了五行的自然原型,“力显”揭示了五行生克转化的动力原则,这两个范畴共同激活了五行的神圣性。神圣的来源并非一神教式的超验权威,而是周流不息的自然。自然声光氤氲之中,物象脱离并逾越了主体表象规则,蔓延生长,这是相似的交织与共生。一言以蔽之,物象的生成流转建立了关系的可能性,以及诸种差异性关系的神圣空间。五行物象的认知潜能就是师法自然的必然结果,是道行之而成的绽现。金木水火土之元素性转化成了神圣的“物象”,依此构筑了化生万物的物象符号系统,这应和着“观物取象”的思想进程,并激活了这一观念的宗教之维。“物”从客观对象性的存在,进入物象生成的神圣空间之中,万物一体的原初信念得以确立。
神圣物象的动力转化机制构成了五行物象的核心,即“五行的位阶是作为从始源的太初之道与芸芸万物之间的转化地带”。这一中间状态是由“物象”的中介地位决定的,“物象”既是形而上之道进入世界并散化于万物之中的媒介,也是沟通心物的媒介。这种转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元素性的自然转化,金木水火土的生克与化生,构成了畅然无滞的自然气化宇宙论;二是心物交接之间的主体转化,主体转化始终不离其气化本源。
论及五行物象的自然转化之时,该书直接参照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从无极到太极再到阴阳的衍化过程,是乾坤未定、阴阳始分之际的宇宙生成,这一过程应和着从浑沌(宇宙卵)到气(风,玛纳)再到阴阳(明暗)的化生历程,构成了太初存有论的创世神话学版本,亦是进入五行世界的前厅。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气化宇宙论”占据着主导性的创世范式,该书却以浑沌神话为创世始基,既是对气化宇宙论的神话学转译,也为其添加了物的前身。作为浑沌的物质性分化,金木水火土诸元素历经从物到物象的转化,构成了自然转化的中介物象,道体论的宇宙生成与五行创世的神话剧场彼此呼应,哲理与神思交相辉映。
在创世神话体系中,浑沌与巨卵共属宇宙蛋类型,代表着原始未分化的质料本源,浑沌开辟则是分化与创造的开端。作者对浑沌创世的重述,尤其强调其内在生成性理论,以区别于外在的形式创世。浑沌的自力开辟也构成了一种气化过程,风是气的自然意象,“风—气”构成了内在交缠的心息相依之力,是内在于浑沌又形塑浑沌的柔和之力。简言之,浑沌是创世的质料性原则,风—气是创世的形式原则,其交互涵化带来了源初的宇宙—时空制式,物之物性在起源处是敞开的,构成了大化流行的抟转进程。经过对无极(浑沌)、太极(风—气—玛纳)以及阴阳(明暗)互根的神话学阐释之后,就进入了五行化生万物的氤氲天地,即“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的创世进程,这也是太初之道的原型散化至万物的显现。以金木水火土的元素性和德性象征为引导,杨儒宾将原始宗教意识、五帝传说、时空秩序、政教愿景以及通神体验等都汇聚至五行的自然原型之下。
就五行的认知结构而言,依托于万物类比的分类模式构成了基本的认知图示,杨儒宾对五行神话的重述并未过多地依赖已成定势的分类范畴,而是深入五行范畴之天人感应的内在机制之中,其中包含着天地神人之源初关系的自然外化,既体现了宇宙政治论秩序的自然根基,也为主体人格修炼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具体而言,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五行的自然原型具备的集体性祭仪的宗教特质;二是五行原型在主体转化与性命修炼方面的象征作用。在此,神话与五行是彼此成全的,五行范畴成为理解中国神话体系的元结构,神话意识也让五行认知范式的主体根基得以彰显。
金象征着刑法、冶炼与永固不朽,其悠久与坚固意识体现在三代的青铜器具之上,成为凝聚历史意识的不朽之力。此外,金还是中国道教炼丹术的重要象征,从外丹到内丹的转化,也是从药性锤炼到心性修养的转化。五行之木与遍及世界的宇宙轴(Axis Mundi)神话紧密相关,宇宙轴可以具体化为圣山或神树,沟通天地人神,是人世向超越界的通道。颛顼绝地天通之后,天人通道被垄断,带有祭祀功能的社木则成了公共空间的通天圣物,这株上古神树经过了身体性转化,也是《逍遥游》中那棵“树之于无何有之乡”的参天巨木。五行之水象征着创生、深奥与消融。就神话意象而言,水与女性意象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大母神神话的中国变体。水与大母神意象都具有意识底层的混融特质,是一种内敛回光之状态,这一特质也贯穿在先秦儒道两家的意识基层之中。火与光并蒂而生,光源于天界日月星。同样,火之天界原型就包含了太阳和大火星心宿二。火与天道的关联,就在于太阳和大火星度量时间的礼仪要素中。此外,各类祭祀仪式都以香火达成,火亦是沟通神人的重要通道。火之精神就是大化流行中的精气元素,既是天道之彰显,亦是个人修行的生命动能。黄帝位居中央土位,象征着至高权威;女娲也居于土位,以大母神位格展现了土地孕生万物的绵延生命力。初春举行的籍田仪式与岁暮举行的蜡祭都与农业相关,包含着巩固王权的政治效用,也带有生殖与求取丰产的象征意义,更是一种原始的生命庆典。仪式成为有关生命延续的神圣记忆,其中包含着感通生命、沟通生死的宗教意识。
以引譬连类的象思维为引导,经典生成之前的神话世界与五行物象的元素特质关联了起来,聚集并升华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象征。由物质想象延伸出来的五行物象,成了道德意识周行遍布的自然基石。金之不朽、火之仪礼、土之厚德、水之渊奥、木之通天正直——自然与道德的衔接点就在心物交流的微妙缝隙之中,道德与自然具备了同构性。如何理解这种物性元素与感性经验乃至道德意识的耦合?杨儒宾提出了几条思想路径来阐释这种结合,比如认知隐喻说、汉字原型说、“物质想象”说,以及言—气—志的传统解释模式等。这些解释路径从不同方面通达了自然与精神的衔接,然而,物性与感性、自然与道德的耦合,很难以知识论的语言阐发清楚,其核心都存在着一种难以言传的“目击道存”之体验,其中蕴含着心物交接、与世共化的过程,会将认知主体引领至心物交接的源初气化感通之中。
三、象思维与神圣的转化中介
《五行原论》对五行认知范型的探讨具备鲜明的中西汇通视野,同时绾和了两条思想线索,一是从神话到哲学的思想范式,二是巫史传统的人文转化。该书对神话经验的重视,亦是对“从神话到哲学”这一思想议题的中国式回应。在古代中国思想经验中,神话经验就是巫教中的通神体验,这一体验构成了儒家工夫论的源头,也是气化主体乃至五行认知范型的根基。尽管神话体验是通达巫教与儒家工夫论体验的重要途径,五行认知范型的运作机制和思想潜能却远非神话思维所能涵盖,实际上更为根本地体现了中国传统“象思维”的特质。“象思维”源自“观物取象”的思维传统,中国传统思维向来强调圆融无碍,体用不分,象思维并未被视为独立的认识范式。近代西学东渐以来,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学术界也意识到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进行提炼的紧迫要求,并试图以此突破西方概念性认识范畴的文化框架。近年来,很多学者论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时,都关注到了“象”的中介作用,不约而同地采纳了“象思维”这一术语,系统化地探究了中国传统思维的深层意蕴及其阐释空间。
象思维与神话思维存在诸多叠合之处,都试图超越概念式认知并克服主客二分的认知方式,其差异也显而易见。神话思维源自西方神话学传统,内在地包含了一个从神话到哲学的进化路径,神话思维的积极作用尽管得到了肯定,却带有非理性意蕴以及不真实的语义特质,似乎摆脱不了一种虚假、迷思或意识形态的彗星尾巴,是终将被理性和科学思维超越和扬弃的存在。这亦是卡西尔对神话的看法,即“可以把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哲学史看成为实现与神话的分离和解脱而展开的延续一贯的斗争。这种斗争的形态由于理论性自我意识的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普遍趋势清晰可见”。将神话视为非理性的偶像,也许是启蒙意识最傲慢的迷信,尽管神话一直潜隐在理性的根源处,但尚未得到完全的辨认和接纳,直至启蒙再次沦为神话。对神话的排斥是人类理性的一种本能恐惧,是对自然无名之力的恐惧,恐惧驱使人们以文化自保,将自然暗面和质料性卑贱化,使之成为低级存在。弗莱就将神话称之为“受到意识形态表面上承认,实际却予以排斥的能动性(excluded initiative)”。相对于人类理性主体的规范性权力,神话思维总是一种野性思维,包含着去主体化的非人力量,这一力量不会屈从于主体意志的裁决,而是与生命、质料以及必然性相伴而行的势能。“从神话到哲学”的进化范式制造了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无尽冲突,神话思维因而会陷落在真假之辨以及排斥—接纳的困境之中,其合法性需要辩护。象思维则不然,作为物之活力的肯定表象,它是自然势能的表现以及神话力量的现象学传达,构成了心物交接的媒介界面,也为冲突力量的辩证转化提供了通道。思维并不透明,其根基处总有惟恍惟惚之象在盘旋,有形之象与无形之象的错综转化共同构成了思维的内在进程。有形之象来自万物自然现象,构成了思维的象符化中介,是思维不可排除的图像—质料性因素;无形之象则是有形之象的深层动态结构,是道法自然的运作势能,指向了不可见的原象之思。
《五行原论》以大量篇幅绘制了金木水火土的物象变迁及其神话背景,其思想重心却落脚在心物交接以及主体转化之上,神话经验实施的主体转化功能,正是由象思维践行的。五行物象的转化就是“象”的生成、流动与化生的进程,“依照五行的观点理解和认识世界,与阴阳学说一样,正是要选取世界万物之‘象’”。五行物象构成了象思维的自然语法,这一语法体系绝非抽象的形式规则,而是融汇了神话事件、图像产生以及心物转化的创造性言说。五行物象从自然物象升华为仁义礼智信的德性象征时,已经包含了自然与主体的双重转化,象思维就是这一双重转化的动力机制以及无主体的媒介,自然从物变成了物象,主体也在沟通心物过程中成就了“与天地合德”的德性存在,这种双重转化是对心物交接之绝对性的肯定,即“不存在彻底赤裸的物,也不存在完全孤立的心”。五行物象的媒介性使心物一体,回转自如,其神圣又充满活力的转化,是力与时间的显现,也代表着创造性本源的传达。
不过,杨儒宾并未将物象提炼为一个理论话题,只有在讨论道德意识与自然原型的衔接时,物象才上升为亟须直面的问题。他既关心道德与自然的衔接,也关心道德与自然何时分离的问题。依此问题意识,精神展现了直接性和中介性两个维度,道德与自然的衔接,构成了主体精神传达的中介性,五行物象就是衔接两者的中介物象;而道德与自然的分离,则导向了精神传达的直接性,物象中介消失了,主体意识具备了当下即是的直接性。不过,若以象思维的视野观之,即使在中介消失的精神传达中,依然有无形之“象”的运作,精神转化的直接性即使不依赖于有形物象,也不离无形之象,无形之象亦是精神活动的原发特征,且会通于儒释道三教心源,“在《周易》中就是卦爻之象,在道家那里就是‘无物之象’的道象,在禅宗那里就是回归‘心性’的开悟之象”。
有关精神转化之直接性的表述,也暗含着一些隐忧:伴随着脱离物象中介的超越性主体的兴起,是否会使道德意识形式化,从而远离了“气化主体”这一心物交接的始源实相?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理性主体的确立就伴随着实践理性的形式主义规定,逐渐远离了自然和生活世界。气化主体范式以自然物象流转为媒介,始终向心物共化的感通之境敞开,为启蒙理性主体提供了向自然软着陆的契机和路径。五行物象的核心价值在于使精神自然化,为道德重返自然提供了路标,其认知范型是自然原型而非逻辑形式,彰显的道德意识并非主体意志的伦理规定,而是道法自然的结果。每一次运作都将我们带回心物交接的源初经验状态,感受万物并生的悠游超迈,直抵天人合一的存在理想。
结语
近代以来,尽管五行思想遭遇了诸多激烈批判,但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思想律”的地位还是不容撼动的。如今,五行思想依然活跃在中医、传统建筑、占卜命理等领域,但其知识论潜能仍在尘封之中。在诸多有关五行范畴及其起源的研究中,《五行原论》的意义就在于对五行认知潜能的“活化”研究,以神话和五行物象激发心物源初境域,构成了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认知溯源研究,凸显了五行物象沟通心物的媒介特质。以物象为始基的五行认知范型构成了存在本身的自然—符号环境,心与物于其中不可偏废。神话对经学阐释的重要意义以及为气化主体重新定位的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重要议题。受学养所限,笔者主要从认知视野来理解五行范畴的运作机制,对深受科学世界观洗礼的现代心灵而言,源初气化感通的存在姿态已不可追忆,象思维给予了一种非对象化的认识方式,提供了再次迈入心物交接之源初体验的途径。
作为象思维的认知语法之一,五行物象关涉着人类经验的象征过程本身,既破除了主客对峙的思维方式,又激发了心物交接的气化感通,促进了自然意识向道德意识的转进与突变,从而使道德与自然获得同一。在对中国技术问题的探讨中,许煜曾将“宇宙技术”(cosmotechnics)理解为通过技术活动使道德秩序与自然秩序达到同一。依此观念,以五行物象为媒介的象思维就是宇宙技术,实则构成了一种“去技术化的技术”,兼具批判性与建构性。其批判锋芒直指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结构以及由此生成的装置化技术视角,因此象思维并不追求物象语法的普遍化,反而不断超克自身的物象固化图示,让认识轨迹向自然之生气保持开放。就此而言,象思维是让万物得以传达的信息技术,这一信息化的技术视野涵纳着观物取象、立象尽意以及运象通变的动态性体认过程,体现了关联主义的特征,主体以感通之姿成为万物的连接者和沟通者。概而言之,以物象为始基的象思维并不朝向占有和把握万物,从未在客体化万物的轨道上狂奔,而是始终关联于主体状态的过程性体认,这一过程本身就包含着价值之维,不断返回相契于天地自然的道术整体之中。正所谓“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认知总是自反性地关联于主体与万物交接的源初姿势,由此彰显了身体与世界交织的物象根基,以及华夏文明的自然教化和养生之源。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莫斌 常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