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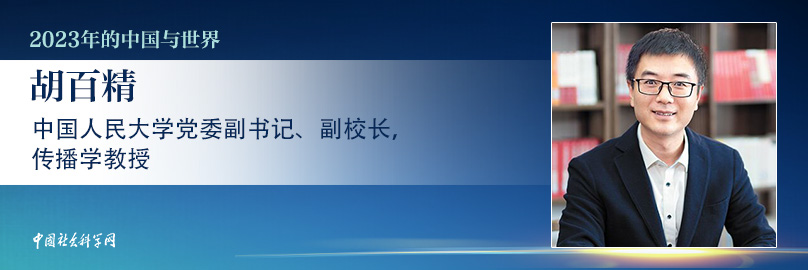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而人非独存的个体,交往的现代化或人在交往中使自身现代化,乃现代化应有之义。马克思指出,历史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实因个人、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普遍交往。在《哲学的贫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交往关系视为生产关系的重要形式,交往与生产力同为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范畴。正是在交往革命与生产力革命的互构中,民族史、世界史得以发生和迁转。从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社会、历史、技术和伦理主题看,马克思的论断非但不过时,而且提示我们更加重视现代化进路中人的交往境况。
西方现代化理论也注意到了交往革命问题,但长期受困于三种交往危机话语:一是主体哲学危机话语,启蒙思想“意外”造成了片面的主体性,现代人据于单一主体性和主客二元论,溺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持续冲突之中,犹如要么不交往、要么交往即斗争的孤立原子;二是理性危机话语,工具理性受到系统批判而其替代方案也并不高明,如哈贝马斯、罗尔斯等提出的交往理性、公共理性仍停留于程序或工具之维,人只是对程序理性负责的抽象的交往者——处于无思、非思或均质状态,交往主体的生命意志、价值选择和特殊尊严被遮蔽了;三是民主危机话语,现代性许诺了大众社会的神话,而当个体汇聚为群体——以大众的面目进入公共舆论和集体行动空间,则将产生勒庞、李普曼等精英主义者宣称的“乌合之众”或“幻影公众”效应,陷入非理性的迷思、暴躁和癫狂。
孤立的个体、非思的对话者和迷思的群集,制造并承受了现代交往危机。即使新科技革命创造了空前便利,交往的时空和工具革命不断爆破,前述交往危机亦未得到根本改善。这就要以人自身为主题和目的,重思交往革命,重申交往现代化。若无人及其交往现代化的撑持,经济、政治、社会和科技现代化未免僵硬而虚弱,或将遭逢空心化危机。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亦应在交往现代化上破题,产出在地思想、知识和经验,并持续增进其世界意义。中国传统人文思想有一重要的方法论:返本开新。若将交往理解为人之在世方式——个体安身立命、我他共在和族群共同体存续的根本机制,那么中华文化于此早已积存悠远、厚实的思想遗产。我们的任务是重振传统的优秀成分,使之与马克思主义交往观和当下的交往境况相结合,为交往现代化补给历史资源。
钱穆将中国传统学术划分为“两大纲”:心性之学和治平之学。前者关怀由内而外的人生问题,尤重“人类所共同并可能的一种交往感应的心理”;后者旨在解决个人“欲投入人群中去实践”的问题,即何以基于心性之学——修身齐家,推扩至治国平天下。在此“两大纲”之外,实有另一纲——天人之学,即搭建人天交往的阶梯,建立人生、社会同存在之理的联系。心性、治平、天人无非人学,亦为关系之学、交往之学。三学会通一处,便是关怀人群中的人——共在者的命运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包括人何以行于天地、修己安人,健全生存网络,构建融贯人生、社会、宇宙的和谐秩序。
在何以理性或曰有德性地交往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思想对天下国家整体秩序的追求,并未压倒或湮没个体之安身立命,交往之道恰始自修己安人而达于治平。个体内由仁义,外依礼法,在自我与家国天下的相遇、交往中成就人生意义,参与公共生活。譬如《论语》对宇宙人生、社会历史问题的求索,是从“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等当下心、眼前人、寻常事谈起的。具体的人在日常生活和生命实践的铺展中,成为交往着的历史行动者。
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个人的存在不能被抽象地讨论,历史的行动者只能是“现实的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在写给《科隆日报》的一篇社论中,马克思强调“使个人以整体的生活为乐事,整体则以个人的信念为乐事”。此一理想,也正是交往革命的宗旨所在,需要一场人学或曰人文主义的复造和更新来成就,而非仅在程序、工具或技术层面的修补运施。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传播学教授)
扫码在手机上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