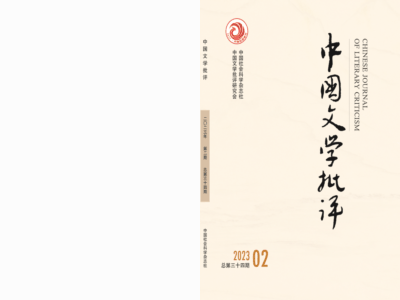一、“象喻”与阐释的诗性魅力
钟嵘在《诗品》中详尽地评述了由汉至梁的123位五言诗创作者,以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精准地概括了不同诗人的语体风格,其充满形象和鲜活灵动的言说方式使阐释过程呈现诗性魅力。《诗品》中不时以自然物象来喻示审美感受,如评价梁诗人范云和丘迟的诗歌道:
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
评价谢灵运诗歌的创作特征道:
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
谢诗如芙蓉出水。
当然,也有以人工物象来比拟的例子,如提到潘岳作品的佳词妙语道:
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
描述颜延之作品的“体裁绮密”,则道:
颜诗如错彩镂金。
以象来揭示一个诗人的整体风格,在钟嵘笔下发展为论诗的一种经典范式。从思想上溯源,中国哲学的起点便为“观物”,无论是自然现象或人事变迁,都可通过图像的形式来传达。上古圣王伏羲所作八卦,是用八种抽象图式指代天地间的万千物象,“由这八种图式组成的整体图案,就成了宇宙的整体模型”。为确保可以承载复杂的现象世界,史载文王将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周易·系辞》中载: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从中已可见相对于语言之局限,“象”有着彰显形上之道的先天优势。后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又进一步强调“象”在意义传达上的辅助功能:
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者所以明象,得象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言之不能尽意,一方面由于语言系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建构,名与实之间的对应以公共经验为基础,而个体的思想和体验有众多尚未形成概念的幽微之所,远非语言所能覆盖;另一方面则由于语言的抽象性,使得其在描述生动丰富的现象世界时往往存在遗漏,造成简单化、片面化的结果。“立象”有效地避免了“言”和“意”之间的隔阂,通过将世界万物进行象征化处理,构建起一个意义宽泛的框架。因为越过了语言的界定和归纳,“意”被折叠在“象”中,保留了广阔的阐释空间,通过观者的理解和领悟,意义不断得到揭示并无限生发。“象”的完满性在于用诉诸视觉的外部形式构筑了一条通向意义的无尽道路,暗示意义而不固定意义,从而真正实现了对意的贯通。
钟嵘所运用的“象喻式”阐释方法,因为仍属于批评话语,故不完全等同于“立象尽意”之“象”,而是介于语言和图像之间的“语象”。与实有的图像相比,“语象”虽然只在精神世界中存在,但同样鲜活生动。形象的生成与阐释者的生活经验有密切的联系,源于阅读体验与脑海中生活原象产生的连接,在此过程中,主体需同时调动理解力、感受力和想象力。“语象”可随时生成和变化,且带有深刻的个人烙印,可视为另一种形式的文学创作。一般意义上,一个批评家本身应当兼具创作经验,否则无法深刻地理解文本,也难以提出对作品的真知灼见。如严羽作为卓越的诗论家,诗歌创作数量颇丰。唐代诗人留下了辉煌的诗篇,他们对诗歌的精辟见解也令后人叹服。钟嵘除了有《诗品》流传于世,创作才能也多受称赞,如其所作《瑞室颂》,被史书评价为“辞甚典丽”,这为象喻阐释的成功运用提供了良好的支持。在引入喻象时,无论是词语的选择、形象的勾勒还是修辞技巧的使用,都显示出《诗品》清雅优美的言说风格和卓越的文采,与概括诗人风格的抽象短语相互配合,使得阐释既通俗明晰,又诗意盎然、摇曳生姿,彰显了六朝文人对阐释语言审美性的推崇。
以对谢灵运的品评为例,为形容谢诗“有句无篇”的创作风格,钟嵘以“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的组合喻象来传达。谢灵运的山水诗受到当时社会文学思潮的影响,诸多作品显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外观,即风格的矛盾杂糅,如“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等句,真切自然,天趣流动,如神来之笔,在佳句之外却多富丽繁芜、雕琢滞涩之句,使得全篇呈现出一种类似反衬的美学效果。钟嵘在《诗品》中较早地指出了这一点,为呈现对谢诗的阅读感受,仅凭“名章迥句,处处间起”的概括难以引起读者的注意,跳出诗歌之外,依据“相似性”的原则选择“灌木”“尘沙”的形象形容“繁芜”之弊,又以“青松”“白玉”喻指作品中的清俊佳句,便增强了反差感,且巧妙地寄寓了阐释者的褒贬,这种迂回的表意模式反而使诗歌的风格特征澄澈无隔地显露出来,给读者鲜明的印象。
这一方法在钟嵘笔下得到了初步的运用,经过后世论者的发展,逐渐蔚为大观,众多的文学批评家开始通过象喻将作品内在的风神转化为直观生动的形象,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以特定的诗境表现不同的诗歌类型,严羽的《沧浪诗话》构造了种种超凡拔俗、孤寂静穆的虚静幻象等,不仅有助于克服逻辑论证给阐释带来的疏离感和枯燥感,也能够体现审美经验的完整性,避免因条分缕析带来支离破碎之感。从功能上看,喻象并未提供确定性的结论,而是为读者提供了联想的方向,辅助读者审美直觉的生成,有利于实现诗人、阐释者与读者之间的有效沟通。
二、“滋味”与文藻之美的发现
《诗品》受到历代文论家的重视,不仅因其借助对五言诗人的逐一述评提出了众多新颖的审美范型,如“雅”“怨”“清”“奇”等,还引入了一些涉及诗歌文体特殊性的概念范畴,“滋味”即是其中一种。在开篇的序言中,钟嵘将“滋味”作为五言诗较四言诗的一大优势加以关注,指出: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
“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是诗歌表达的内容,“有滋味”的成因则在于“详切”,可知钟嵘将语言表达的环节作为是否具有“滋味”的判定依据。随后又进一步展开,从诗之三义“赋”“比”“兴”的安排入手来讨论“滋味”生成的修辞因素:
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咏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在现代诗歌理论里,将语言形式作为文学本体加以剖析的代表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如雅各布森的语言诗学便对文学性作出了语言学层面的探讨,指出文学性存在的关键是作者对待语言的态度。在实用语言中,语言被看作交流的工具,以传达情感或知识为目的,关注的是语言的内容。而在诗歌中,语言构成了目的和本体,词语自身的形式(语音、拼写、组合等)和词语表述形式(词法、句法)使诗歌区别于日常语言,获得了“诗性”。基于此,雅各布森认为诗歌文本是一个相对自足的、充满自在价值的语言系统,并用“语法肌质”来指称诗歌的语言本体。于是诗学的主要任务便为寻找诗歌的“语法”,即揭示语法范畴的分布及韵律的、分节的相关要素间的关系。钟嵘对五言诗创作的评议,也是从语言的构造手段方面言之,他指出“赋”“比”“兴”三者各有所长,若仅用单一的手段,必然会走向极端,或趋向“词踬”,或趋向“文散”,须经合理的斟酌和调配,才能发挥出形式技巧的最大效用,达到最佳的审美效果。
“味”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在先秦时代便已多次出现。在儒家传统中,“大羹遗味”用于体现对礼乐的至敬之情,“和味”指向由多样统一带来的生命和谐感。道家文化中,“味无味”则用于描述对于“道”的一种精神体验。除本土文化典籍之外,外来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钟嵘之前,不少佛教中典籍频繁出现“以味论文”的现象,呈现出一种“重文尚味”的观念倾向。如东晋僧肇在《百论序》中有一段“风味”论:
论有百偈,故以百为名。理致渊玄,统群籍之要。文旨婉约,穷制作之美。然至趣幽简,鲜得其门。有婆薮开士者,明慧内融,妙思奇拔,远契玄踪,为之训释。使沈隐之义,彰于徽翰;风味宣流,被于来叶;文藻焕然,宗涂易晓。
“风味”在此处是对文藻之美的一种肯定,《高僧传·鸠摩罗什传》中称“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为“失味”,也是将“味”的概念与文辞的美感相连,这二者都早于钟嵘约百年的时间。加之在当时的佛教典籍中,大量赞美说法言辞之美的记载与“味”相关,如“妙音清彻,句味辩证”“言辞美妙,犹如甘露”等,可以推知佛教中的“味论”对钟嵘“滋味说”不无影响。
在具体的评述中,钟嵘一以贯之地显示出对文辞美感的推崇,在评价永嘉时期玄言诗时说:“永嘉时,贵黄、老,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其时文人将诗歌作为谈玄明道的工具,竞相追逐理趣,强调遗貌取神、得意忘言,自然会削弱在语言文采方面所费精力,正如《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说:“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其正面肯定的两例,一为张协之诗:“词彩葱蒨,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一为应璩之诗:“至于‘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二者都可以看作“有滋味”的代表。《诗品》虽然屡屡用“味”来概括对作品的理解过程和品赏结果,但并未直接界定“味”的内涵,有观点认为,这根源于“滋味”之无法言说,像宇宙本体“道”一样,能说出的“味”只是“味”的现象而不是本体,所谓“大味无呈”正是此意。从另一个角度看,“味”的无法定义还在于其内涵的丰富和复杂性,就《诗品》中的几处表述来看,“味”已涉及叙事容量、修辞、气势、词藻、音律、节奏等多维度的构造,是由形式的多样性统一带来的综合性美感,故给概念的界定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如果说“象喻”尚有具体的形态可依托,“体味”则触及精神世界更深处的运思,具有更为空灵的特征。如后世《景德传灯录》中记傅大士《心王铭》所说:“水中盐味,色里胶清,决定是有,不见其形。”基于这一属性,“味”在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常常成为对诗歌语言的最高赞誉。诗味的生成需要接受者反复讽诵涵泳,在沉浸式的精神体验中不断辨析和自得,作品的形式要素组织得越高妙,越能契合主体的审美“先结构”,越容易激发接受者持续的审美快感,故会出现阅读品赏“亹亹不倦”的现象。
三、“吟咏情性”与抒情传统的深化
对于诗歌表达的对象,钟嵘已有简明全面的概述,即“指事造形,穷情写物”,其中情的维度得到了极大的关注,“摇荡性情”甚至被视为诗歌创作的唯一契机。虽然陆机在《文赋》中已将情文结合的过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但主要还是一种理论上的想象和推衍。到了《诗品》中,对创作者情感世界的考察开始大量地出现在具体的阐释实践中,如在谈论曹植的诗歌风格时道:
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评论惠休上人的诗歌语言失之浮浅时道:
惠休淫靡,情过其才。
也有多处评述细致地区分了“情”的具体类型,如在上卷之中,涉及多位诗人传达出的生命悲切,包括评古诗的“意悲而远”,李陵的“文多悽怆”,班婕妤的“怨深文绮”,王粲的“愀怆之词”,左思的“文典以怨”等,可知钟嵘承续了汉魏时期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将“悲”视为上品诗歌最为突出的审美共性。
在理论的部分,钟嵘也对“情性说”作出了详细的说明,其一云: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礼记·乐记》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诗品》中梳理的传递链条与《乐记》一脉相承,将音乐领域的感物理论引入到诗学领域,并将“人心”明确为“情”,强调了诗人情性的摇荡是诗歌创作发生的直接动力。
其二云:
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释其情?
从功能上看,《毛诗序》强调诗歌为国为政而作,对圣王君子而言,可正得失,“风”“雅”“颂”三义无一不带有治世的价值导向。《诗品》对此进行了删改,不仅删除了“正得失”一条,也将诗之六义缩减为三义,只保留了“赋”“比”“兴”三种形式技巧,带有强烈政教意味的话语被悉数省略,通过这一方式,儒家传统诗论中诗乐“为国为政而作”的价值目标被弱化,诗歌的功能沉降为抒泄一己之悲喜。钟嵘将之概括为“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并列举了包括“楚臣去境,汉妾辞宫”在内的种种感荡心灵的人生境遇,填补了诗人为何而作的意义空白地带,从而完成了诗歌价值在个体意义上的重构。
其三云:
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此处在肯定诗歌以抒发情性为本体的基础上,将“直寻”与“用事”视为诗歌创作的不同路径加以取舍,“用事”更多的是借助概念来表达情感,可以增加作品的意义含量,“直寻”则更多借助具体可感的形象来表情达意,钟嵘推崇“直寻”,正是看到了审美直观在抒情性文本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从先秦时代起,中国哲学中就存在着一条高度重视“人心”和“人情”的尚情主义传统,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就通过一系列论述高度称扬了“情”的价值,如称“道始于情,情生于性。使者近情,终者近义”“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君子美其情,贵其义,善其节,好其容,乐其道,悦其教,是以敬焉”,在儒家学派重视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之外,又推出了一个与之并列的、认识人类精神运行的重要范畴,“这一段历史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心理学,它和亚里士多德建立心理学的时间相当”。在相近的时代,还可看到屈原在《惜诵》中提出的“发愤以抒情”,被学界视为古代美学传统中“抒情说”的正式登场,到了《毛诗序》中,有“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文赋》中有“诗缘情而绮靡”,《文心雕龙》中也提出“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凸显了“情”在诗文创作中的根本性意义。钟嵘的《诗品》无疑遵循并深化了这一传统。
从阐释过程上看,对“情”的感知和辨识是依赖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的心灵共振完成的。情感作为诗歌作品意义的重要构成,投射在整个作品之中,浑然而不可分割,任何推理与分析的手段均难以有效地达到对情感的体认。审美主体需将自身代入诗歌的情境,保持思虑的清明和精神的专一,才能完成心灵共振与情感传递的过程,这一获得意义的途径可视为一种“共情”,是诗歌阐释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思维活动。
四、直觉思维的主导和“自然论”土壤
从跨文化的角度观之,《诗品》的阐释方式与西方哲学中的“直觉”概念有着诸多相通之处。“直觉”(intuition)是一种不经逻辑推理而直达对象本质的思维形式,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其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受到关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便主张直觉是一种高级的理性能力,因为它能够直接把握真正的存在。近代的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理性主义者也主张知识的最高原理都是通过清楚明白的直观被把握到的。康德之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沿用了智性直观这一范畴,接续了古老的理性传统。《诗品》之中,无论是以“象”喻示诗人风格、以“味”形容品赏诗歌语言的过程还是以“情”统摄作品的整体氛围,均以直观的认知方式为主导,反映了主体对诗歌语言形式和内在意蕴的智性把握,这一思维活动贯穿于理解与阐释的全过程,可以“直觉阐释”的范畴来概括。
纵观前代的诗文阐释,主要受到实证思维的支配,一方面是通过对文字的训释来确定经典的原意,以东汉的古文经学为代表;另一方面是结合经世致用的现实关怀来阐发经典中的政教伦理大义,以西汉的今文经学为代表,二者都具有明确的规则和逻辑框架,对阐释者有较高的知识训练上的要求。文学文本更多的是作为政教观念的载体而存在,需通过对章句的条分缕析来获得意义,在这一阐释机制中,文本的艺术属性是极为淡薄的。虽然《诗品》中并无对儒家微言大义式阐释路径的质疑和否定,在实践中仍然以新的关注点完成了对传统阐释方法的突破。在思维过程方面,变推求、考证为体悟、涵泳;在思维成果方面,不再重视对文字内涵的确证和建构,转向对语言形式意义的发掘,着重揭示诗人创作前后的心灵轨迹,也关注读者接受作品时的审美触动,两相对照,可以见出政教与艺术、实证与悟证、逻辑与直观之间的巨大差异。
从思想史上追溯,直觉阐释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反复讨论的“自然”范畴有着密切的联系。对“自然”的推崇最初源于《老子》和《庄子》,代表一种自然而然、取消外力干预的状态。“自然”首先是万物生成的内在法则,也是“道”的天性和本体。老子言: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自然”的本意接近“自己如此”“本来如此”,是一种自足的形态,也是地、天、道的本质。地、天、道作为人之外的存在,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律和内在的规定性,无需外力改变,也不会发动意志来改变万物。基于此,地、天、道呈现出一种素朴的状态。“素朴”对物而言指未加纹饰,保存原有之貌,对人而言则指真纯之本性。老子认为赤子、婴儿富有朴性,正是自然的象征。对地、天、道之自然的言说,最终是为了指引人的行为,老子通过一组递进关系提出了人法自然的观念,实际是为了防范等级名教对民性的异化,是一种对礼乐文化的超越。谈到治国路径时,老子指出圣人当“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将执政者置于服务者的位置,反对为了实现统治秩序而实行严苛繁琐的干涉和制约,以不扰民为原则。
作为老子的后继者,庄子将“自然”视为以自由为核心的理想人生境界,强调尊重人的自然天性,追求人的精神自由。这一境界可通过“游心”的方式实现,本质上是对现实人生一切问题的精神超越。通过顺应自然的心灵之游,人方能感受到充盈天地的“至美”与“至乐”,这一追求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形成影响深远。
到了竹林玄学时代,嵇康同样以现实人生为出发点,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及“越名任心”的人生追求,主张通过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的方式来养生延年。尤其重要的是,他将“自然论”作为审美理想引入了艺术的场域,在《声无哀乐论》中将“乐生于自然”作为理论起点,并将“声若自然”“自然之和”“清和自然”作为音乐的理想形态。在嵇康看来,“自然”兼容了真与善,且是审美的本体,真正完成了“自然论”从哲学向艺术理论的转换。
钟嵘的《诗品》沿着这一理论脉络,将“自然主义”引入了诗学场域。《诗品序》中有言:“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已将自然之美视为一种极高的评价标准,以此为前提,钟嵘在创作方法上反对典故繁复、刻意雕琢声律辞藻的做法,提倡即景会心、率性而作,确保诗人情感的自由表达。
崇尚自然的倾向同样贯穿在钟嵘的阐释过程中。象喻的运用须由批评者首先获得审美体验,后通过想象与联想的方式捕捉对应的艺术形象,并以精心营构的语言加以传达。其中关键的环节皆通过“直寻”完成,即向内挖掘欣赏者自然生发的视觉联想,不再向外求索经史的论证。滋味的获得则需接受者通过涵泳和讽诵的方法,激发和强化对诗歌文采与声韵的细腻感知,需要鉴赏者内在的审美机制经历一系列复杂的反应产生,更多地依赖感官与身体的参与而非冥思苦索。“共情”的阐释路径依赖审美主体因作品的感染和震撼而引发的情绪共振,本质上也是心灵在外物触发下的自然冲动。钟嵘对“情”的态度同样不可忽视。在儒家的诗论传统中,人的感物之情长期被视为对社会秩序的威胁,荀子在《乐论》中曾言“乐出于人情”,是“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他接受音乐源于内心情感的涌动,同时又对充满生命能量的情绪振荡保持高度的警惕,认为放任情感的发展而不加干涉,可能造成失控的局面,故提出通过“礼节乐和”的手段来为情感制定框架。“雅乐”便是圣王所制引导万民避恶趋善的工具,《乐论》中言“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可知情感与礼乐教化构成了一种对立关系。在《毛诗序》中也可看到对此的继承,如其虽然认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指出了“抒情言志”是诗歌普遍的发生机制,但接着即言“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仍然是站在整个社会和谐统一的出发点上,以“善”的要求来规范“真”。《诗品》作为六朝时期诗论的代表,将“摇荡性情”置于“物感”的自然序列之中,使得“情性”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同时肯定“情性”为诗人珍贵的创作资源而非被压抑的对象,面对人心因境遇的变化而激起的种种悲欢,钟嵘的态度是通过“长歌”来“释其情”,以顺应生命能量的自然宣泄,而不强硬地将之引向“中正平和”。在玄学的影响下,与钟嵘同一时代的士人在社会各个领域都显现出超越纲常礼法、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如通过追求物我合一的无我之境来达到“任心”的目的,重视个体自我的审美想象力和创造性,崇尚个人的姿态和风采,等等。对于情绪的解放也是魏晋士人走向生命自由的重要步骤,在这个意义上,《诗品》在启发士人自我觉醒的维度上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