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网络文学批评”包含两重含义:发表于网络的文学批评与对于网络文学的批评。发表于网络的文学批评由于特殊的传播速度形成相互激荡的狂欢气氛,并且导致答辩机制的消失。这种状况再度诱发由来已久的专家、精英主义与大众喜闻乐见的辩论。网络文学的批评表明,类型化的网络文学屏蔽了历史逻辑之后,细读式的文学批评基本失效。但是,“数字人文”开拓了崭新的研究空间,同时也带来另一些必须考虑的问题。
关键词:网络文学批评;文学批评谱系;精英主义;大众;数字人文
作者南帆,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福州35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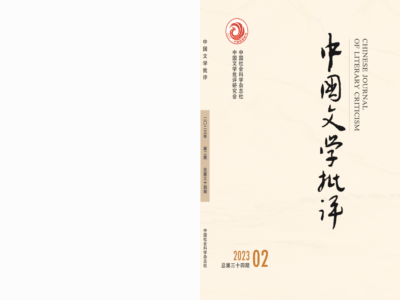
一
作为一个稳定的术语,“网络文学批评”愈来愈频繁出现于不同的理论场合,充当主导各种论述的关键词。既然如此,人们就没有理由持久地混淆这个术语包含的两重含义:第一,“网络文学批评”指的是发表于网络的文学批评,既可能论述《水浒传》《红楼梦》或者金庸小说,也可以围观《盗墓笔记》《甄嬛传》以及众多网络电影,长则宏论滔滔,下笔千言,短则只有一个句子,甚至一个词,例如称之为“弹幕”的批评形式;第二,“网络文学批评”指的是对于网络文学的批评,批评家秉持各种观念评判发表于网络的小说、诗歌或者戏剧。尽管网络文学的批评多数发表于网络,然而,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可能栖身于不同的传播媒介。口头文学的批评文章可能见诸纸质的报刊,戏剧的文学批评多半并非展示于表演舞台。
澄清“网络文学批评”术语的时候,人们必须完整列举两重含义背后隐藏的多种逻辑可能:发表于网络的文学批评既可能考察网络文学,也可能考察纸质文学;考察网络文学的批评话语既可能发表于网络,也可能发表于纸质的报刊。这不是玩弄繁琐的文字游戏,而是指出两条不同的理论线索。换言之,两重含义的混淆可能重叠不同的理论焦点,无法进入问题的纵深。
“网络”一词显然是造成两重含义混淆的主要原因——哪一种批评话语都不可能绕开网络。这种错觉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网络”一词的强势。“互联网+”成为时髦的观念之后,“网络”始终充当统领的中心词。尽管各个行业拥有传统的谱系,但是,网络的加入极大开拓了延展的空间。从网购、网站、网银、网管到网友、网恋、网红、网课,这些项目幸运地获得网络的垂青之后,奇迹般的效果屡屡发生。作为普遍的仿效,更多的行业正在向网络汇聚,力图赢得一个浴火重生的机遇。发表于网络的文学批评与批评网络文学共享“网络”概念。网络的特殊性质如此强大,以至于批评话语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古老区别很快显得无足轻重。
“网络”的出现首先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通信革命。通信速度产生不可思议的飞跃,同时,线性结构进化为立体的网状。这一场通信革命正在许多领域显示巨大的成效,例如经济领域的国际金融结算系统,或者军事领域的精确制导技术。相对来说,网络赋予文学批评的特殊性质不如想象的那么突出,从而构造出一个显眼的历史阶段。文学批评史保存了古今各种形态的文学批评范本,发表于网络的文学批评并非面目一新,无论涉及的是文学观念还是技术分析模式。多数文学批评并未因为发表于纸质或者网络而发生颠覆性变化。必要的时候,二者可以轻而易举地相互转移。的确,人们可以从发表于网络的文学批评看到某些独特的术语,例如“扑街”“太监”“烂尾”“金手指”“崩”“坑”,如此等等。这些术语多半来自口语表述,通俗风趣、犀利尖锐,同时缺乏足够的思想含量。批评家简明的语言平面背后不存在进一步的理论启迪。言及“新学语言输入”的时候,王国维提出的标准是形成新的思想格局:“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显而易见,网络文学批评并未显示出达标的意愿。相反,理论的深奥、晦涩往往被斥为迂腐的学究式卖弄。
目前为止,网络的介入并未向文学批评提供新型的文本解读理论。文本解读并非仅仅表现为单纯而直观的反应,而是涉及基本的文学观念,譬如文学构成、文学功能、文学传统等,甚至涉及哲学理念、历史的理解或者社会理想。孔子以“思无邪”解读“诗三百”,儒家的道德思想渗透于文学批评之中;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共同肯定白话文学,启蒙大众的思想充当了文学褒贬的基础;“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或者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这些批评学派无不涉及语言哲学,“陌生化”、文本结构、叙事学、话语分析等概念或显或隐地进入文本解读;接受美学对于“读者”的重视源自现代阐释学的转向,海德格尔等一批哲学家的思想重新设定了文本与阐释的相互关系。相形之下,发表于网络的文学批评很少显示出相似的理论雄心。彼此投缘,击节称赏;一言不合,一拍两散,没有什么引经据典的高头讲章,也没有什么委婉周详的辩解。即景会心,我手写我口,不必到哪一本哲学著作布置的迷魂阵里绕一个圈子,也不想为哪一篇标新立异的文学宣言摇旗呐喊。不设门槛,出入自由,人人可以发言,学术权威丧失了居高临下的中心位置,狂欢的气氛成为最为显眼的标识。这将为文学批评谱系增添什么?
二
返回文学批评谱系,发表于网络的文学批评更想重现文学批评的早期状态。一种分析将网络内外的文学批评区别为“线上”与“线下”。“线下”多为熟悉学术训练的专业批评家:“专业批评家评价一部作品时难免会有一种‘思辨冲动’,即通过自己的批评行为完成一次有意义的‘学术旅行’,用批评对象的价值判断印证某种文学观念的正确性与有效性”;相对而言,“线上”文学批评的“持论主要是个人立场而不是他者式理论立场,他们言为心声,袒露性情,面对阅读的网文,忠于自己的感受,不虚美、不隐恶、说真话、讲实情,针砭对象不留情面,三言两语却直击要害”,这些批评可能由于尖锐直率而迅速获得作家的关注。尽管这种概括泾渭分明,可是,后者并非网络的独特产物。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之中,一时一地即兴的文学批评比比皆是。快人快语,切中肯綮,坦然不羁,直抒胸臆。金圣叹称《西厢记》为“天地妙文”、赞叹《水浒传》作者的“非常之才”“非常之笔”“非常之力”,或者,脂砚斋评《红楼梦》“如此叙法方是至情至理之妙文”,“其囫囵不解之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这些精粹的评点批语保存于纸质的典籍。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蔚为大观,批评家多半要言不繁,精简的风格与学术式的“掉书袋”大相径庭。“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大众的好恶不言自明。村夫野老街谈巷议,三五文友推敲切磋,古代民间的文学批评与现今网络上的众声喧哗相差无几。回溯文学批评的初始状态,即兴、明快犹如童言无忌,“言必有据”的学术规范是后来的事情。现今的文学批评之中,批评家对于作家的反馈亦非网络的专利。一些报纸杂志设有“读者来信”栏目,读者可以在信件之中坦陈自己的作品观感。这些意见可能不同程度地影响作家,甚至对于作品后续的修改产生重要作用。20世纪50年代,杨沫《青春之歌》的修改即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总之,通俗、活跃乃至泼辣率真的文学批评并非始于网络,而是古已有之,并且长期寄存于纸质传媒。
如果总结发表于网络的文学批评带来了什么,传播速度显然是令人瞩目的特征。这是纸质传媒不可比拟的。当然,“文以气为主”的命题或者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不会因为传播速度的加快而有所改变。尽管如此,传播速度并非仅仅充当外在因素。许多人记得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媒介即是讯息”。麦克卢汉解释说:“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譬如,铁路运输的货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铁路带来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和新型的闲暇。相同的理由,网络的传播速度可能改变批评家、文本、解读方式的传统关系,甚至转换为“内容”的组成部分。
网络的“弹幕”评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弹幕”评论的对象通常是网络播放的电影或者电视连续剧,任何一个观众均可充当批评家,即时将自己的观感借助键盘与鼠标同步上传到屏幕。“弹幕”评论亦步亦趋紧跟剧情,评论的对象可能是剧情之中的一个场面、一个桥段、一个人物的出场或者几句对白,评论的语言往往是一个短句,甚至是一个感叹词。“弹幕”评论的传播速度不能低于剧情的演变。剧情结束之后,这些评论文字同时冷却,迅速丧失意义。事后搜集那些“弹幕”的评论文字,诸如“前方高能反应”“美爆了”“劝你善良”等,不知所云。然而,跟随剧情起伏的时候,诸多“弹幕”评论文字相互激荡,一路飙升的点击率显示出不可遏止的狂欢热度,不进入这个场合发出几声呐喊就像一个可笑的落伍者。对于许多人来说,说出什么或者看到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手疾眼快,迅速汇入浩浩荡荡的文字洪流。企图在“弹幕”评论之中追求思想观念的严肃表达肯定是走错了门,可是,狂欢本身就是另一种表达。屏幕之中的剧情悲欢离合,屏幕上方无数字符络绎不绝地驰过,这个画面已经构成另一种导演始料不及的奇特屏幕形象。
对于网络经济来说,传播速度与流量密切相关。单位时间之内,愈来愈多的点击量表明网站愈来愈大的营业额。巨大的点击量迅速产生滚雪球效应,网站声望的提高将形成进一步吸附力。尽管纸质传媒,例如报纸或者杂志的发行量同样是利润的表征,但是,传统的编辑、出版、配送给分散订户与网络传播速度、点击上网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钢笔纸张书写的文字与电脑的键盘敲击仍然相差无几,那么,印刷、出版、发行与网络传播之间完全是两套迥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印刷文化与读者之间的衔接犹如古老的手工作坊,电子信号瞬息之间的发射与接收决定了网络即时传播。文学批评荣幸地纳入这个体系的时候,纸质媒介保存的某些特征无形地消失了。
首先,网络制造的相互激荡气氛逐渐取消了深思熟虑的分析模式。竞相表述彼此的观感,层层递进的逻辑悄然成为主宰。张三的机灵不能比李四的俏皮逊色,王五的夸张必须换来赵六的戏谑,即兴的感想你追我赶越滚越快,一本正经的分析反而如同不识时务的愚蠢。浮光掠影带来轻捷的快意。既然可以充当一个舒适的乘客,人们不再愿意像机械师检查发动机那样费神拆解作品的内部结构,衡量各种成败得失,继而联系悠久的文学史背景,阐述成败得失的意义以及文化根源。
其次,网络之中喧闹的狂欢很大程度抑制了答辩机制。正如波普的“证伪”思想所认为的那样,严肃的理论观点必须接受严格的检验,答辩机制往往是检验的重要形式。然而,狂欢是喧闹式的同声相应而不是深入的思想对话。调侃、挖苦、嘲弄或者故作惊诧、装疯卖傻,嬉笑怒骂无法负担严密的理论辨析。即使存在不同的倾向与观点,没有多少人愿意瞻前顾后,为之进行冷静的思辨。喜剧性哄笑或者尖刻的反唇相讥很快就会冲垮丝丝入扣的论辩。迄今为止,印刷文化与思想的速度构成稳定的联系:意识的感知、鉴别、判断与漫长的印刷文化历史相互适应;书写、编辑、印刷、发行,诸多环节的衔接之间保留必要的反思空间。然而,报纸、刊物、书籍遭到网络传播速度的全面碾压。一念闪动,敲击键盘,鼠标一点,这些文字已经进入公共空间。从思想的生产到传播,前所未有的快车道出其不意地敞开。这时,网络的文学批评显现出令人惊异的快节奏。
可是,“令人惊异的快节奏”能否带来更有质量的思想?文学批评并非跑步竞赛。社会已经摆脱“文学饥渴症”多时,没有必要因为更高的产量追求从而加快生产线的运转。的确,网络敞开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空间,许多人一拥而入,七嘴八舌、众说纷纭。然而,如同常言所说的那样:如果是对的,一个人就够了。
这时,网络的文学批评又把这个争端抛出来了——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大众还是专家?
三
如果是对的,一个人就够了。真理追求并非依赖“人海战术”。一个人真正拥有标准答案的时候,多数人起哄式褒贬没有多少意义。然而,这种自信仅仅适合简明的自然科学领域。对于人文学科以及相当一部分社会科学来说,“大众”本身就内在地镶嵌在“标准答案”内部。换言之,“大众”人数的大幅度上升可能改变标准答案。譬如,对于文学来说,大众的喜闻乐见始终是一个重要指标,尽管这个指标可能以不同的理论语言显现。更为复杂的是,“大众”的各种需求并非如同自然规律始终如一,而是作为变数与历史运动之中众多因素积极互动。这种状况必将导致专家与大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如同许多学科一样,文学批评领域的专家首先表现出雄厚的文学知识积累。从文学史的演变脉络、文学经典的稔熟到各种文学理论命题,文学专业训练是从事文学批评的前提。如果说批评家较之普通读者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良好的专业训练是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所谓的专业训练可能滋长精英主义的文化姿态。精英主义往往认为,文学史确立的经典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文学经典不仅是文学知识的核心,提供审美遵循的圭臬;更高的意义上,文学经典可以代表文化传统。无论纸质传媒还是网络空间,文学经典的追随将有效地保持文化的深邃、典雅、厚重、源远流长。许多时候,精英主义不知不觉地流露出厚古薄今的倾向,热衷于将现今的文学作为古代典范的证明材料。另一些批评家甚至将传统的典雅与文化阶层联系起来。渊博显示的良好教育与文化修养仿佛带有贵族出身的意味,生气勃勃的世俗气息乃至俚俗风格则是来自底层的乌合之众。
另一些批评家并未如此公开地主张精英主义。大众必须成为文化的受益者——认可这种前提之后,批评家力图委婉指出问题的另一面:那些貌似赢得大众的通俗作品是否真的代表大众的利益?武功盖世的大侠及时除暴安良,“穿越”到另一个时空摆脱令人窒息的现实环境,或者,主人公无缘无故地赢得霸道总裁的欢心而幸福地嫁入豪门——这些“白日梦”是解放大众还是麻醉大众?由于文化教育的限制,大众时常被称为“沉默的大多数”;底层人民无法创造独特的形式表述自己。多数时候,他们只能沉溺于各种古老的文化形式及其封建主题,从社戏、说书、连环画、西洋景到侠客、神仙、花妖狐魅、青天大老爷。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一批进步知识分子的启蒙使命包含了对封建主题愚民毒素的严厉批判。然而,即使批评家的理性分析拆穿了曲折情节制造的美学骗局,通俗作品的“白日梦”仍然拥有巨大的市场。许多时候,批评家的观点并未获得大众的响应。
文学史表明了更为复杂的情况:一批以“通俗”面目出现的作品最终入选文学史经典名单并且传诸后世,例如一些词、曲以及话本小说。不论入选依赖哪些历史条件,这种状况至少显现出通俗作品摆脱众口一词的贬损而突围的一个缺口:通俗作品与文学经典之间存在转换通道。对于精英主义来说,通俗作品赢得市场与文学史的双重待遇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理论挑战。
发表于网络的文学批评向学院与专业隐含的精英主义权威展开反击。驰骋于网络的批评家高度信任自己的感性直觉,并且认定大众之中普遍存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础。喜欢就行,何必拖出一大堆权威站台。许多时候,这种反击可能扩展为对于传统文学知识的蔑视。修辞、叙事分析犹如繁琐哲学,结构形式的考察毋宁自寻烦恼,学院派炫技式的理论铺排令人厌倦。网络之间的一个观点呼之欲出:大众要将文学批评的话语权从精英主义手里夺回来。
不言而喻,这时的批评家与大众融为一体。然而,什么“大众”?所谓的“大众”并非一个抽象名词,而是带有不可代替的历史时空标记。换言之,大众通常是根据历史提供的某种组织机制汇合起来的。“普罗大众”“工农兵大众”或者“消费者大众”,这些称呼无不显示出清晰的时代烙印。作为精英主义的对手,各种“大众”提出的质疑不尽相同。“普罗大众”的通俗化涉及阶级动员,“消费者大众”的通俗化着眼于娱乐市场的扩大。网络上指谓的大众往往等同于“网友”。事实上,根据网络出现的时间,围绕网络组织起来的大众大约只有20来年的历史。尽管如此,网络文学的碎片化阅读、高度类型化、功德圆满的结局与巨大的体量均已成为“网友”的强烈期待。而且,“网友”时常以“下线退出阅读”作为要挟,要求作家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情节设计,譬如男一号必须娶女一号,或者决不可赋予主角道德污点,更不能不幸逝世。发表于网络的文学批评是否照单全收,忠实执行这些标准?
四
“网络文学批评”指的是对于网络文学的批评——转入这个术语的第二重含义之前,必须明确人们的某些模糊共识:纸质传媒的文学批评流传于高深的学术圈子,强调各种理论命题和文学经典的范本,并且由一批学识渊博的专家把持;网络文学需要的批评话语直观、率真、坦言无忌,批评家与大众联袂狂欢。前者围绕传统的纸质文学,后者与网络文学共生共荣。这些观念仿佛认定:网络文学无法纳入学术的视野,犹如唐诗宋词或者巴金、茅盾不会在活跃于网络的批评家心目中形成多大波澜。
的确,纸质传媒的文学批评未曾对网络文学表示足够的重视。网络文学的字数业已成为空前庞大的存在,可是,遵从学院标准的批评家视而不见。这种自以为是时常被形容为文学批评的缺席与失职。在我看来,批评家的傲慢或许是次要原因;更为常见的理由是,批评家仿佛无从下手。文学史生态表明,众多文学作品并非平均接待文学批评的惠顾。少数情况下,一部文学作品可能吸引一千篇研究论文;多数情况下,一千部文学作品无法吸引一篇研究论文。前者体现出文学经典享有的待遇。文学经典通常精深广博、结构繁杂,文学经典考察的基本方式是文本的细读。从文字训诂、修辞分布、叙事视角到人物形象、意境氛围以及微妙的节奏掌控,文学批评借助细读论证文学经典的宏大精妙。然而,网络文学,尤其是网络小说,几乎无法承受文本分析:
那些倾泻而下的文字一览无余,没有庞大的象征系统,没有远古的神话原型,没有深邃的哲学主题,也没有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许多文字粗糙的作品段落甚至缺少可供分析的修辞现象。从人物、结构、主题到意象、无意识、叙事模式,文学批评的众多术语只能空转。必须承认,相当多网络小说的情节设置极为出彩,漫长的故事悬念丛生,欲罢不能;遗憾的是,文学批评从来不肯对情节和悬念给予过高的评价。相反,许多作家和批评家的共识是,过分离奇的情节夺人耳目,以至于真正的主题可能陷落在眼花缭乱之中,这犹如荣华富贵的温柔乡将会消磨一个人的雄心壮志。所以,作为一个旁证,传统的文学史通常不愿意将经典的荣誉授予侦探小说。
我想补充的是,大部分网络文学并没有兴趣追求结构、无意识、叙事模式等等晦涩的话题。为了投合普遍的“碎片化阅读”,写手的意图就是浅白,通俗,甚至让读者可以一目十行地囫囵吞枣。他们心目中,艾略特的《荒原》也好,乔依斯的《尤利西斯》也好,这些深刻的玩意还是留给学院派享受吧,简单和好玩才是后现代的至高原则。
网络文学之所以单纯、浅显,负责提供强烈而清澈的快感,很大程度上源于“白日梦”对于欲望的代偿性满足。欲望没有历史。然而,欲望的实现机制始终诉诸历史。饥渴制造的欲望世代相同,但是,满足欲望的食物与饮料必须由历史指定。苞谷、田间野菜还是丰盛的满汉全席,米酒、普洱茶还是牛奶、咖啡,历史决定分配的内容与形式。一个终身劳碌于田间的农夫无法想象皇亲国戚如何果腹,正如一个帝王会惊奇地询问“何不食肉糜”。文学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来自作家的虚构,文学批评时常鉴定这些虚构是否吻合历史逻辑。虚构古代的一个武侠利用互联网刺探宫廷里的情报,历史逻辑就会提出抗议。
事实上,文学批评的历史分析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从社会历史批评学派、新历史主义到后殖民理论,历史逻辑始终是批评家衡量文学的一个准则。故事情节的社会背景、人物性格的形成、叙事之中的民族或者性别观念以及一段对白、一个战争场面无不接受历史的检验。无论悲欢离合,每一个人物只能栖身于历史赋予的社会关系;因此,作家与批评家默契地共享一个前提:认可历史逻辑的限制。文学虚构不是任意捏造,缺乏“历史真实”的保障可能严重干扰文学的审美效果。某些文学虚构利用幻想——无论是神话幻想还是科学幻想——摆脱历史重力,但是,神话或者科幻文学的魅力恰恰是相对于后者的存在。换言之,文学虚构与历史重力之间的复杂博弈以及彼此衡量同时是文学批评反复谈论的话题。然而,当文学虚构放弃历史逻辑的互动而仅仅遵循欲望逻辑的时候,文学内容迅速简化,以至于文学批评同时丧失了大部分话题。每一个主人公肯定吉人天相、心想事成、恶棍必死、善人善终,美人嫁给了白马王子,遭受世俗鄙视的穷小子终将因为挡不住的横财而青云直上,傲视人间,这时还需要文学批评补充什么呢?欲望没有历史,可是,如果同时将实现欲望的社会背景销毁,文学漫画只剩下简单的曲线:从欲望的启动到欲望的完成。个人成为没有历史的欲望主体。当然,网络文学同时设计了若干摆脱历史重力的文学策略,这些文学策略的反复执行形成了文学类型,例如“武侠”“穿越”“玄幻”,如此等等。“武侠”以常人无法获得的盖世武功摆脱历史,“穿越”干脆抛开物理限制奔赴另一个时空,批评家曾经详细概括出“玄幻”类型的坚硬框架:“主角模板”,“主角光环”,始终采用主角视角,不能“虐主”——主角不存在各种缺陷,必须无与伦比地强大:
表现主角的什么呢?表现主角的“强”。具体来说,就是“成为强者”,这是玄幻小说句法模式的核心谓语。在网络上,不计其数的小说都在书写一个关于强大的故事,主角最后总是成王、成神、成仙、成尊、成宇宙之主、成各种业界领袖……用17k小说网主编血酬的话来说,网络文学的核心与特质就是“成功学”。“主角成为强者”,这就是当下玄幻小说句法模式最为核心的部分。
对于玄幻小说作家来说,文学虚构与历史之间的联系已经切断,重要的是读者形成的主角“代入感”。社会历史批评学派的分析被精神分析学取代:强大的幸福幻象恰恰是众多失意者的内心寄托:
小说就应该一直采用主角视角,不宜随意切换,不断地营造“主角光环”、不断编织主角强大的故事,这是读者能够持续“代入”、小说获得良好黏着度的重要保证。显然,“代入感”在根本上强调的就是能让读者代入到主角身上实行角色扮演的可能,而这也正是个体在网络空间的虚拟体验形式,换句话说,玄幻小说“主角成为强者”的叙事模式与网络空间中个体凭借虚拟自我而幻想自身强大的行为在本质上是合一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网络玄幻小说成了数字时代个体角色扮演的文学形式。
网络文学之中的类型如同以平均值为基准压缩的粗糙模块。各种情节与人物大同小异,文学批评的细读如同浪费精力。然而,抛开围绕文学经典形成的专业训练,能否从网络文学拥有的海量字数发现另一些问题?至少在目前,这些问题的深度以及复杂关系更适合诉诸纸质传媒的文学批评模式。
事实上,由于“数字人文”的带动,网络、网络文学与文学批评正在展示出一种新型的结合方式。
五
将网络文学的海量字数纳入考察视野,这是“数字人文”研究出现之后形成的可能。大规模的统计、计算、数据库等伴随计算机出现的研究方法是“数字人文”的必要条件。相对发表于网络的文学批评,我更愿意认可的是,“数字人文”开启了文学批评谱系的崭新空间,许多研究课题以及考察路径闻所未闻。例如,分析7000个英国小说的标题叙事;统计200年间的英国小说,区分为“菜园派”“新妇女小说”“帝国哥特”等44种亚文类并且建立可视模型;搜索、统计某一个词在特定阶段文学史之中出现的频次以及出现的位置;计量某一个作家在参考文献数据库中被提及的次数;如此等等。“数字人文”为许多长时段或者大范围的文学特征描述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批评家对于爆炸式增长的网络文学望洋兴叹的时候,“数字人文”轻而易举地证实了许多猜测与假说。
当然,许多人已经意识到“数字人文”存在的盲区。例如,计算机可以获知18世纪以来“浪漫主义”或者“现实主义”出现于理论文献之中的频次,但是,统计通常无法显示,哪一个理论权威的哪些论述赋予这些概念稳固的理论地位并且引起使用的激增,或者,哪些论述导致这个概念出现转义,以至于扩大了使用范围。对于网络文学来说,“数字人文”的启用至少要考虑到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字人文”提供的结论可能远离传统的作品、作家范畴——不再是文学经典的示范,也不再介入个别作家如何获取题材、构思、写作等具体事项。根据许多网络写手的自述,他们大约每日不辍地上传八千字左右,甚至连错别字也无暇仔细订正。对于这些粗制滥造的文本字斟句酌、钩沉索隐有些可笑,但是,“数字人文”仍然可能获取某些有趣的信息。类型的总结始终是一个引人瞩目的课题。大量网络文学面目相似,所谓的“个性”或者“风格”必须从作品扩展至类型。无论是侦探、武侠、宫斗还是探险、盗墓、寻宝,概括一个类型的构成因素甚至比分析一部文学经典还要简单。当欲望、无意识与文学虚构的关系将社会历史条件完全挤压出去之后,所谓的类型仅仅剩下某种风格的表象加悬念制造。当然,“数字人文”还可以利用数据协助某些小型课题的完成,例如众多“穿越”小说分别选择哪些朝代作为落脚点——各个朝代的不同比例说明什么?或者,古往今来“武侠”小说对于内家拳与外家拳的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说明这种变化的原因之前,数据可以显示不同时期的演变曲线。总之,“数字人文”开设的各种课题并非证明传统的文学理解,而是扩大文学意义的延展范围。
第二,“数字人文”必须发现新的问题,而不是证实不变的结论——没有人愿意增添更多的数据证实人类的面孔上具有两只眼睛。新的问题产生于数据统计之前还是统计之后?如果说,“数字人文”领域与作品、作家范畴缺乏交集,那么,新的问题通常不是源于二者的自然积累,而是来自研究者的设置。无论是假设某些问题之后收集数据给予证明,还是数据的增加使之察觉问题的存在,“问题意识”不可或缺。能否从民间故事之中发现叙事结构的胚胎?“问题意识”促使普洛普收集100个俄罗斯民间故事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31种功能项,他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从而成为叙事学的奠基之作。中国古典诗词之中“月亮”意象如此之多,“月亮”在古人的理想生活之中扮演什么?古典诗词之中“月亮”意象的统计、分类与阐释可能带来新的发现。可以从各个层面描述一个对象的数据,“问题意识”才能决定数据使用有的放矢。研究者想知道什么?面对一座山峰的时候,高度、动物种类、植物种类、树木或者花卉的分布、季节与温度或者湿度的关系、地貌构造等无不可以转换为数据形式,然而,数据的意义必须由考察的问题确认。
第三,“数字人文”的大规模统计往往展开一个宏观视野,同时,庞大数据堆积的数字模型祛除了不可复制的个别特征而留存共性的规律,抽象的数字不再依附于具象与个性。这时可以发现,无论是情节波澜的起伏设计还是类型的总体概貌,网络文学的规律远比文学经典清晰明快,以至于“数字人文”可以得心应手:
研究者认为,算法已经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主导了网文评价并渗透到创作之中,形成了各种“套路”或“模式”,不仅有“升级流”“废柴流”“重生流”“退婚流”等桥段套路,也存在金手指、掐高潮等反复使用的具体应用技巧,甚至开篇和高潮都有精确的设计。与传统文学的类型或模式不同,网络小说的套路存在着高度的重复或规律性,显示出极强的量化可行性 ,即研究者所认为的算法基因,这使得数字人文方法的融入更为便利。
然而,这种结论同时表明,遵从或者拒绝“套路”“模式”恰恰是网络文学与文学经典的重要分界。独创是文学经典的重要指标,雷同的构思或者表述意味着缺乏历史的独到发现。正如“影响的焦虑”这个命题所表示的那样,许多经典作家竭力回避前辈既有的成功。对于他们来说,“重复”——无论是重复他人还是重复自己——是包含很大耻辱成分的评语,甚至无法完成文学乃至美学的基本预设。可是,网络文学不再重视这个指标。网络写手的共识是尽量投合读者的口味。双方的相互肯定迅速导致“套路”“模式”以及类型的固化,貌似五彩斑斓的想象仅仅流动在几个简单的槽模内部。由于可观的经济收益,网络写手不会如同经典作家那样为之沮丧或者自责。读者欣然吞食手机屏幕上的文学读物,种种曲折离奇的情节远比文学教授唠叨的《红楼梦》或者鲁迅有趣得多。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愈来愈稳定的回环之中,巨大的“信息茧房”如期而至。听到的恰恰是自己想听的内容,熟悉的快乐一次又一次定期重现。当“数字人文”将海量字数化简为一目了然的图表时,人们仿佛更加了解自己——的确,如此庞大的文学版图只有若干“白日梦”的集聚点。这时,作家与读者至少有必要重新反思一个基本的问题:机械的单向度快乐就是文学热衷的目标吗?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