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水乳大地》算起,范稳迄今共发表了7部长篇小说,其结构形式丰富多样,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增添了浓重的一笔。《水乳大地》是“合拢式”的结构,时间跨度长达百年,像大江筑堤坝,从两岸起笔,向中间合拢;《吾血吾土》是“展开式”的结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中间起笔,向两端展开;《重庆之眼》以一个叙事单元的线索为主,交织起其余叙事的内容,形成了小说的艺术整体;最新的《太阳转身》则又回归了朴素的线性结构。从范稳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流变,可以看出其对长篇小说的结构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在叙事的空间与时间处理、叙事单元的组合等方面做了多种探索。
关键词:小说结构;合拢式;展开式;叙事单元
作者宋家宏,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昆明6500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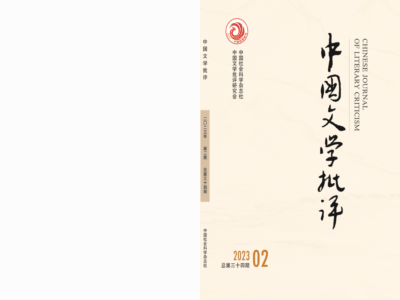
一个小说家在动意写作一部长篇小说时,必然已经拥有了丰富的材料,包括小说的题旨、语言、故事、细节等。怎样把这些材料组织为一个艺术整体?这是一个长篇小说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即使写作中根据情节与人物性格逻辑,或者主题深化的实际有所修改,也只能在不影响整体结构功能的情况下,做局部的调整。因此,结构是长篇小说艺术的第一要素。
文学作品的结构有多种说法,叙事文学的结构是叙事内容在一部作品中的存在形态。它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表层结构,也就是叙事的布局,时间与空间、情节的安排、材料的剪裁、开头与结尾等;这个表层结构受到第二个层面的支配,即作家所要完成的总体存在形态,这是它的深层结构。它隐含着作家在这部作品中要传达的最重要的价值指向、要形成的整体审美感受,这往往是由叙事单元之间的关系来完成。一部作品的整体性,由不同的叙事单元组合构成。
范稳的长篇小说,主要还是吸收了19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营养,他并没有在结构艺术上吸收过多以“意识流”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现代主义小说那种无结构的、碎片式的、忽视整体性的结构艺术被范稳跨过去,他直接承续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即使“魔幻”,也仍然是“现实主义”,都强调整体性,有完整的叙事结构,对人、对世界有整体的理解,人物与故事皆有始有终,小说中要实现艺术的完整性。但是范稳在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上对现代小说又有所吸收,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规范,特别是在叙事的空间与时间的处理、叙事单元的组合等方面做了多种探索。除去《骚宅》《冬日言情》《山城教父》《清官海瑞》这几部通俗小说色彩更为明显的长篇小说,从《水乳大地》算起,迄今为止,范稳发表了7部长篇小说,7部长篇的结构丰富多样,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水乳大地》是范稳花了十多年时间,关注民族历史、文化交融、宗教信仰等问题,大量阅读典籍,无数次往返滇藏大地采风,并在那里“挂职”一年,长时间与当地的民众生活在一起,实实在在地考察、学习、体验,最终完成的作品。素材的积累难以计数,怎样修建这一座雄伟的“大厦”,范稳也经过了精心的构思,在结构上别出心裁。
小说以滇西北地区一个世纪以来的风云变幻为背景,书写以宗教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卡瓦格博雪山之下,澜沧江大峡谷之中,多民族聚居,多种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涉及藏传佛教、基督教、纳西东巴教以及西藏土著宗教苯教,头绪纷繁,人物众多,时间的跨度长达百年。如果按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方式,以线性结构为基础,按时间顺序,推进故事发展,也能完成这部小说,那可能就是一部平庸之作。小说共十章,开头是20世纪初两个法国传教士进入澜沧江峡谷,他们想把上帝的福音传遍雪域高原,掀开了故事的帷幕。之后作者将一个世纪的时间以十年为一个时间段,每章一个时间段,从时间的两端向中间合拢。第一章为“世纪初”,第二章即“世纪末”,“第一个十年”则与“八十年代”对应,结束在第十章“五十年代”。作者在一次访谈中将这一结构称为“向心结构”,笔者认为不甚准确,“向心”可以是一个圆心,是一个点。《水乳大地》可不是以一个圆心点展开的蛛网式结构(蛛网式结构是现代小说的一种方式),而像大江筑坝,从两岸起笔,向中间合拢,故可称其为“合拢式结构”。
作家选择这一结构,基于对这一地区的百年历史、社会变迁、宗教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整体的思考和深入的理解。叙事的表层结构打乱了时间的线性发展方式,空间又随时间变化,时间与空间的折叠式交错,这一表层结构是由小说叙事的深层结构决定的。这部小说中作家要传达的最重要的价值指向是什么?范稳在接受《青年作家》编辑卢一萍的访谈时明确说过:“我不就是写的在藏区大地上一段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交融与砥砺吗?过去是不同宗教和民族血与火的争杀,现在是相互尊重和包容,‘水乳大地’这个书名就像瓜熟蒂落般脱颖而出了。”作家要表达的就是不同家族、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文明,经过百年的冲突与融合,终于走向相互尊重与包容,水乳一般地融合了。神父与喇嘛,野贡家族与泽仁达娃家族,以及纳西族长和万祥等人延续了三代的爱恨情仇,各叙事单元的内涵都指向这一总体价值。之所以以20世纪50年代为时空的中段,从两端向其合拢,是因为50年代,尤其1950年,这一地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各种冲突与矛盾发生了质的根本变化。按十年为一个时间段,折叠起来看,形成了更加鲜明的对比。这只需阅读第一章及第二章就可明白。在20世纪初,宗教信仰的尖锐冲突,引发“教案”,即使同一民族的家族之间也会发生仇杀。在20世纪末,有教案世仇的法国少女像天使一般降临藏区,藏传佛教的转世灵童竟出生于信仰耶稣基督的家庭,并得到了认可。之后的各章两两对应,各叙事单元的矛盾冲突是各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的反映。它们共同昭示着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水乳般融合的大地,来之不易!
然而,这种“水乳般融合”,既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又在一定程度上是作家范稳的良好愿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滇藏地区迎来了安宁祥和、经济快速发展、各民族团结友爱、多种信仰的宗教相互尊重与包容的美好时期。云南在努力建设“民族团结示范区”,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是不同信仰的人们相互尊重与包容。在滇西地区,笔者也亲眼目睹了一个家庭里共同生活着宗教信仰全然不同的人,深感震惊。范稳同样是目睹了这一现象,激发了他创作《水乳大地》的动意,藏地近百年的仇杀、动乱,在新的政策引导下,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归为安宁与祥和。但是,不可回避的是,宗教信仰没有逻辑可以遵守。不同的宗教信仰,既有共同的起点,比如对“爱”的重视,又在具体地更深入地阐述时,有了区别。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出发点是绝然不同的,正如无神论与有神论只能相互理解,却难以融合。
范稳《水乳大地》隐形结构中的价值指向非常明确,也影响着小说各叙事单元中的取舍,他特别强调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中的共同性,而对差异性、不可调和性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更不去追问和谐相处的不同信仰的人们,他们在各自信仰的根本问题理解上有无变异?今天的僧侣、教徒与过去的僧侣、修士有无不同?不同宗教在这一过程中精神价值是否发生了重要变化?丧失了什么?有无伤痛?也许,这些问题对小说写作来说更难深入,从各叙事单元的文本中看,皆较为浅表。文明的冲突,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水乳大地》给了我们不同的感受,不同文明是如何走向交融与谐和的。一部长篇小说的隐形结构必须具有恒定的价值指向,否则无法形成作品的整体性,但是价值指向过于清晰、明了,会让读者没有更多的思考空间。《水乳大地》叙事单元的一些内容与过于清晰的价值指向构不成张力关系,反而显得累赘。结构不仅是先讲与后讲的问题,还有多讲与少讲的问题。《水乳大地》被研究者更多地从民族性、地域性来解读,而不是从总体价值指向来深化理解,正是这一问题的结果。
或许范稳在完成《水乳大地》的过程中,对文明的冲突也有更深入的理解,但是由于小说创作隐形结构价值指向的需要,而不能把自己的理解完全纳入其中,几年之后创作《碧色寨》时,他才完成了对文明的冲突的完整思考。
《碧色寨》在范稳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艺术结构属较为简单的线性结构,个别叙事单元中的冲突与解决方式也不尽合理。故事的主要情节,围绕中西文明的冲突,以及由此衍生的悲剧而展开。《水乳大地》写的是不同文明之间在新的意识形态统领之下走向交融与谐和,而《碧色寨》写的是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不和谐,更无法融合,可以说这是与《水乳大地》不同层面的反向思考。作家巧妙地把故事结束的时间设定在1950年之前,以彝族纪年的方式写了十章。从碧色寨修通铁路到铁路毁弃,围绕卡洛斯兄弟的命运,讲述了以铁路为中心的碧色寨数十年的兴衰史。以铁路、火车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明以强力的方式进入云南准农耕时代的碧色寨,开始缓慢地、静悄悄地影响当地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但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了,仍然“桥归桥,路归路”。西方的绅士、淑女们在碧色寨享受着在欧洲一样的生活,一箭之遥的彝家山寨仍然过着他们传统的生活,毕摩仍然坚守他的信仰,至死与“地上的恶龙”战斗。铁路、火车,这些西方现代文明的象征物,被同样是西方现代文明的飞机(毕摩称之为“天上的恶龙”)以残酷的方式摧毁,证明了现代文明的脆弱。无论是胸怀理想的弗朗索瓦、露易丝,还是胸怀野心的大卡洛斯,最终都归于失败甚至搭进了自己的生命,小卡洛斯充满西式特征的爱情最终也毁于一旦。而普田虎土司和他的百姓仍然过着既往的日子,虽然多少有了一些改变。信奉祖先崇拜的毕摩从自己的信仰中获得力量,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和信仰,维护着自己民族的宗教传统。
如果说范稳在《水乳大地》中表达的是他所见到的在主流意识形态政策的引导下的安宁与祥和,对不同文明冲突走向和谐、包容与融合寄予希望和热情的赞颂;那么,《碧色寨》所表达的是西方现代文明强力进入,迅速绽放又迅速地凋零之后的荒凉感。这是许多人进入碧色寨这个现实中的真实场景所产生过的心理感受,范稳用他小说家的方式,对这个“荒凉感”做了深度的思考。《碧色寨》所表达的“文明的冲突”的难以谐和,补充了《水乳大地》的遗留问题。
《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被研究者合称为“藏地三部曲”,其实,称这三部作品为“三部曲”是非常勉强的。《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没有统一的构思,《水乳大地》获得成功之后,作家受到鼓舞才开始构思创作后两部作品,三部作品之间没有构成“正反合”的关系,甚至三部作品的情节与人物都没有延续性。三部作品的结构也各不相同,《水乳大地》如前所述,《悲悯大地》采取两大叙事单元的平行交叉结构,《大地雅歌》不断变换叙事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完成对信仰与爱情的诠释。
《悲悯大地》以时间的自然流逝为序,以阿拉西、达波多杰两个人物的不同人生道路为中心,形成两大叙事单元,采取平行交叉的结构,其中穿插了作家行走在藏地的六篇田野调查笔记和三篇读书笔记,在相互对比、映照中表达作家的价值指向,也诠释作家范稳所理解的藏传佛教。阿拉西即洛桑丹增喇嘛,为摆脱世俗仇恨选择了一条充满苦难而虔诚的精神道路,一心向佛,他求得的“藏三宝”是“佛、法、僧”,最终涅槃成佛。达波多杰选择的则是充满世俗快乐的冒险之路,试图实现自己的英雄梦,他所认为的“藏三宝”,是“快刀、快马、快枪”。洛桑丹增喇嘛用他的生命和精神唤醒了藏族人的悲悯之心,化解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也让达波多杰明白了怎样才是真正的英雄。
《大地雅歌》围绕央金玛(玛丽亚)、扎西嘉措(史蒂文)、格桑多吉(奥古斯丁)三个人之间的曲折爱情展开情节。虽然仍然以时间的自然流逝为序,但小说不断变换叙事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完成对信仰与爱情的诠释。全书分上下两部,第一部《大地》,第二部《雅歌》,共52节。扎西嘉措与格桑多吉,一个是令人迷醉的流浪歌手,一个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强盗,一文一武,形成对比。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他们因对玛丽亚的爱,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也改变了自己的性格与命运。作家把人间的真爱提升到了信仰的高度,与宗教具有同样的精神价值。小说的表层结构写他们在对玛丽亚始终不渝的爱情追求中完成生命的意义,而深层结构的总体价值指向则是具有宗教情怀的“苦难—救赎”。小说写人物的生命历程中经历诸多苦难,最后获得灵魂的救赎。小说的三个人物,都经历了人生苦难的折磨,在苦难中坚韧执着,忍辱负重,宽容与奉献,信仰与爱情交融,人的灵魂获得救赎。这是小说的一些小标题具有的《圣经》色彩的原因。
范稳是以一位汉族作家的文化背景进入藏地的,他不是以猎奇的心态来书写藏地,而是对藏地充满虔诚与敬畏之心。他不是停留在对藏地文化的浅层表达上,而是深入这个民族厚重的宗教、历史及文化之中,完成了他对宗教、文化与人的生命意义的思考。
二
《吾血吾土》是范稳又一部耗费了巨大心血创作的作品,小说于2014年10月推出。众所周知,2015 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此时上架这部作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小说写一个中国远征军老兵的人生命运以及他在抗战中的英雄事迹。因此这部小说被当作“抗战小说”来评说,合乎时代语境。然而,我们如果分析这部小说的结构就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一部“抗战小说”。
小说的叙事时间从20世纪50年代起笔,向后,延伸至抗战烽起主人公投笔从戎,直至其家世背景的展开;向前,延伸到20世纪80年代,主人公迎战友魂归故里。《水乳大地》是从时间的两端起笔,向中间合拢,《吾血吾土》则是从中间起笔,向两端展开。因此,笔者将《吾血吾土》称为“展开式”结构,尽管这一称谓也不甚准确。《水乳大地》以一个叙事章节为一个时间段,很规范地两两对应;《吾血吾土》则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1951年、1957年、1967年、1975年、1985年,向前推进,但这只是故事的表层时间,每个部分都饱含着抗战老兵赵广陵的个人历史,配以往事回忆“交待材料”“书信”“刑事裁定书”“墓志铭”等,形成卷宗,伴随着时间推移,他的“罪恶”也不断地被“揭露”出来,他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所作所为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完成了一个民族英雄的悲剧史。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与侵略者的大决战,无论前方后方,无论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抗战中产生的一些英雄是被遗忘的英雄,直到抗战胜利60周年后才掀开新的一页。范稳将《吾血吾土》的“后记”明确命名为“拒绝遗忘”,他要还原被遗忘的历史真实,重塑赵广陵抗战老兵的英雄形象,这是这部小说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从这一角度说这部作品是一部“抗战小说”,没问题。
但是,如果范稳仅仅是写一部“抗战小说”来还原历史,不必采用这一结构。将小说的叙事集中于抗战时期,可以更深入、更细致、更具历史的真实性。这类文学作品已经有很多。早在20世纪90年代,云南文学中,彭荆风完成长篇小说《孤城日落》之后,又创作了长篇纪实文学《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这部长达54万字的作品依照战争的进程,全景式地展现了抗战期间中国远征军从组建、出征、进攻、败退、再进攻直到最后夺取胜利的完整过程,它与彭荆风的另一部长篇纪实作品《挥戈落日: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构成姊妹篇,完整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远征军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征战历程。小说对史实的考证极为详尽,是可以当作“信史”来读的作品。用小说来重现历史,还原历史的真实,与纪实文学相比,自有其短。
范稳在《吾血吾土》中,显然有他更丰富的整体价值指向,这是小说的深层结构决定的。小说从中间起笔的五个部分,选择了极具代表性的时间点作为标志,在向时间的两端展开的过程中,赵广陵通过交待其“罪行”,还原一个悲剧英雄的生命历程。时间的一端从他创办迎春剧艺社,向前追溯至内战时期、抗战时期,再到他就读西南联大,报考黄埔军校,直至追述他的父兄亲族与家世。另一端则是赵广陵为可以融入新时代而兴奋,不料却卷入政治事件的漩涡,家破人亡,最后终于回归抗战老兵的面目。在同一个部分里向两端展开的内容,“过去”与“现在”形成巨大世事反差,强烈的对比使读者更清楚地看到,时代风云笼罩着他的命运变迁,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时代风云中的艰难沉浮,令人唏嘘怅惘。近半个世纪,赵广陵经历了命运浮沉,怀着报国救民的雄心,赴汤蹈火作出的卓越贡献被遮蔽和遗忘,而莫名的“罪名”却伴随了他数十年,带来人生的磨难,家破人亡,在苟活中挣扎。书写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这是对《吾血吾土》作整体观并分析其结构,应该得到的认知。
这一结构还隐含着个人在被时代左右的命运面前何其渺小!赵广陵的悲剧,是命运的悲剧,他先后使用了五个名字,每一次姓名的更换都隐藏着一段身不由己的历史。他只想报效国家,不涉政治,政治却非找上他不可。身不由己卷入内战,在战场上大败,作为营长的他差点被军法处置,之后走上了漫长的赎罪之路。抗战中他为国家为民族舍生忘死,伤残成为“无脸人”,英勇的事迹却被强迫性遗忘,连自己都不敢想起。在时代的巨浪中他始终在挣扎,却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连姓甚名谁都难以确定。小说写出了个人在命运重压之下的无力,刻画出了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
范稳写得相当纯粹的抗战小说,是《重庆之眼》,无论取材还是主题,都紧紧围绕重庆在抗战期间遭遇的大轰炸进行。重庆,在抗战期间,经历了日本人长达六年的无差别轰炸,依然傲然挺立,粉碎了侵略者试图摧毁这个中国抗战时期的“陪都”,进而摧毁中国人民抗战意志的战略意图。范稳在小说的“后记”中写道:“这是一部向一座勇敢顽强的城市致敬的小说,是向一段不屈的光辉历史致敬的颂歌。”分析作家如何将一段真实的历史转化为长篇小说,结构仍然是我们首先应该进入的问题。
小说并未仅仅局限于重庆大轰炸,叙事时间从抗战初起,延续至新世纪以后,长达七十余年。重庆这座英雄的城市所遭遇的狂轰滥炸,重庆人民如何面对敌人的大轰炸,构成了小说的第一叙事单元;战后幸存者向日本政府的艰难索赔,构成了小说的第二叙事单元。这两个叙事单元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叙事时间,如何把它们自然地连接起来?作家巧妙地设计了发生在蔺佩瑶、邓子儒和刘云翔三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作为第三个叙事单元,以这一叙事单元的线索为主,交织起另外两个叙事单元的内容,形成了小说的艺术整体。小说的这一艺术整体的结构,也就是这些丰富内容的存在形态,拓展了向英雄城市、向光辉历史致敬的意义和价值。小说中歌颂了重庆人民坚不可摧的生存意志,也歌颂了中国人民威武不屈、永远不可征服的志气,描写了重庆人乐观、开朗、豁达的性格特征。但是,仅有歌颂又是不够的。反思历史、思考战争,成为这部小说重要的价值指向。重庆所面临的大轰炸已经过去七十多年,战争也已经结束七十多年,反思那一场战争,文学是重要形式。《重庆之眼》让读者看到日本人是如何看待那一场他们发起的侵略战争,一些日本人在淡化它,为他们的残暴辩护,进而试图美化它。中国民间的索赔,就是要为历史留下证言,不能忘却了侵略者的残暴。同时,小说也在反思大轰炸期间一些国人所暴露出来的怯懦,让人警醒。这就超越了致敬与歌颂,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因为它应该有超越的东西。小说中三个人之间的爱情,也有出人意料超越通常“三角”关系描写的价值指向,这就是在面临生死灾难时的忠贞不渝和牺牲与奉献。
三
范稳的《太阳转身》是他新世纪后推出的第7部长篇小说,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可以用“朴素而自然”来概括这部作品的总体风格。这部小说的一些章节写得惊心动魄,但整篇作品无论叙事笔调还是结构、人物塑造都是朴素而自然的。
老英雄卓世民重出江湖解救被拐女孩,是小说的主要叙事单元,卓世民的故事构成贯穿作品始终的线索。小说开篇就是主人公卓世民被告知身染沉疴,他的生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他如何对待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牵挂的被拐女孩还未找到,人贩子未抓获,这是他的内心隐痛。他能解除这一内心之痛吗?他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这成为整部小说的悬念。卓世民英雄般地再度出山,奔赴破案战场,破案前得知被误诊的消息,最后却又牺牲在现场,人物的命运跌宕起伏。
南山村老村长12年来带领村民在山崖上修路,只为了改变贫困的命运,是小说又一重要的叙事单元。南山村人最终在新的时代,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在有识之士的帮助下,修通了路,也完成了脱贫攻坚的艰巨任务。评论家们把这一小说称为书写脱贫攻坚主题创作的作品,源于这个叙事单元的内容。
作家如何把老英雄卓世民重出江湖与南山村的故事融合起来,是作品结构要解决的问题。作家巧妙地把人贩子设计为南山村人,正是南山村的贫困导致一些人因贫穷而走向犯罪;再把卓世民与老村长设计为一个是当年的支前民兵连长,一个是奔赴战场的连长,两人结下了战火中的友谊,也令卓世民对南山村始终难以忘怀。被拐女孩也是南山村人,这是令卓世民牵肠挂肚的重要原因。
作家把脱贫攻坚等生活中正在发生的重要内容与一个英雄故事自然而完美地融为一体,让读者在被英雄的壮举深深吸引的同时,又被南山村人为改变贫困的顽强精神而振奋,为社会与时代的变迁而欣喜。以此为基础,融合进侬建光、韦小玉的爱情与婚姻,他们逃离山乡又重回山村;禇志与林芳个人生活和创办企业过程中的矛盾以及他们的犯罪与悔过;卓婉玉对壮族历史与民间文化的研究几个叙事单元,以及曹前贵、杨翠华、魏老虎、马洪琪等各自走向犯罪道路的故事,自然地因南山村而融合为一体,让读者身临其境,似乎不是在读一部虚构的小说,而是亲眼目睹了云南边地的现实人生百态。这样朴素而自然的阅读感受,证明作家有强大的写实能力和结构能力。
范稳的小说历来重视历史与现实的交织,在历史的背景上看现实,《太阳转身》也一样,南山村的今天与40年前那一场自卫反击战有密切关系,今天卓世民舍生忘死重出江湖,与他和南山村鲜血凝成的友谊密不可分。作家也重视把一部长篇小说写得丰富多彩,使读者阅读时产生一个地方百科全书式的阅读感受。但对一部作品主题意蕴的理解,不能只抓住某个叙事单元的内容来理解,而要从这部作品的结构、各叙事单元的关系,以及是什么贯穿小说的始终来分析。把《太阳转身》仅仅当作“脱贫攻坚”的主题创作,显然是不恰当的。这部作品贯穿始终的叙事单元是老英雄卓世民重出江湖解救被拐女孩的故事,说这部小说是书写英雄的故事,似乎更为合理。
许多作家的创作经验证明,要解决好长篇小说创作的结构问题,深入研究类型化的作品,吸收所谓“通俗小说”的经验,非常重要。范稳对通俗小说并不排斥,他还创作过比较纯粹的通俗小说。在《太阳转身》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类型小说对范稳小说创作的影响。电影中常有因各种原因退出江湖又重出江湖,再创辉煌的英雄故事。范稳的《太阳转身》主体结构是这一类型故事的洐化,但是范稳把它写成了一部纯文学的作品、一部边地世相的百科全书。这就与好莱坞的类型故事有了根本不同,又与其他同样写脱贫攻坚题材的“主题创作”小说有了鲜明的区别。《太阳转身》成为一部雅俗共赏的作品,像生活一样的朴素而丰富,有了多种解读的可能,极大地拓展了这部小说的阅读空间,这正是一部优秀长篇小说的特征。
从1994年出版《骚宅》这部通俗小说色彩明显的长篇小说开始,范稳对长篇小说艺术结构的探索已近20年。2004年《水乳大地》出版,标志着范稳对长篇小说结构艺术的探索翻开了新的一页。从时间的两端向中间合拢的“合拢式”他写过,从中间向两端展开的“展开式”他也写过,还对三个叙事单元并置的结构做过探索。如果把范稳先前的《骚宅》《山城教父》这类通俗小说色彩更明显的小说,与2022年出版的《太阳转身》进行比较,会发现它们都属更为常见的线性结构,但是,后者与前者相比,其叙事单元的丰富性、各叙事单元组合的多样化,是前者无法比拟的。从范稳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流变,可以看出他对长篇小说的结构问题有过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写长篇小说的作家很多,但像范稳这样认真研究过长篇小说结构问题的并不多。因为长篇小说结构的变化很难,而创作长篇小说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结构问题。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