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艺创作和改编中的经典化问题,既是文学家、艺术家在文艺创作和改编中要思考、解决的问题,也是评论家和学者需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白毛女》的改编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它从民间传说到报告文学和短篇小说,再到逐步被改编成歌剧、电影和芭蕾舞剧,最终成为文艺经典。以《白毛女》的经典化为中心,结合百余年来文艺史上其他作品经典化的经验,可总结出文艺创作和改编的经典化路径:凝炼主题,表达时代精神;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依托现实生活,反映人民心声。此外,文学家、艺术家还需走出书斋,从生活中发现典型人物和典型故事;超越自我,用集体智慧提高艺术水平;克服小众视野,用改编促进大众化传播。只有这样才可创作出饱含时代精神,具有中国气派,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
关键词:《白毛女》;改编;经典化;时代精神;典型形象
作者徐兆寿,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兰州730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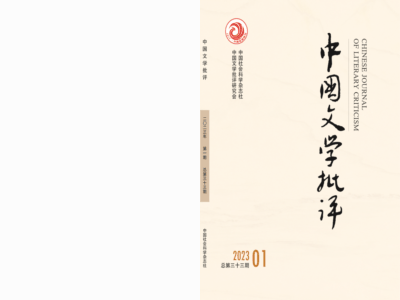
近年来,对当下中国文艺“有高原无高峰”现象的持续讨论凸显出一个长久以来的学术议题,即文艺作品的经典化问题。一部作品的经典化,需经历作品传播、读者接受、批评家阐释的漫长过程。文艺改编既是拓宽作品传播途径的一种方式,也包含了对作品的阐释和解读。从百余年来的文艺改编史来看,成功的改编在作品经典化过程中可起到关键性作用。在众多改编案例中,20世纪40—60年代《白毛女》从民间故事到歌剧再到电影及芭蕾舞剧的改编和经典化过程极具典型意义,其中涉及从民间自然流传到文艺工作者集体创作的文本生产机制转变、政治话语的介入、大众化的社会接受和传播基础等,取得了政治性、大众性、艺术性的完美统一,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也对当下的文艺创作和改编有重要启示意义。日本学者清水正夫说:“《白毛女》是任何时代都令人难忘的故事。”细致梳理《白毛女》歌剧、电影和芭蕾舞剧改编前的报告文学、短篇小说及相关资料,结合时代背景分析比较民间传说、文学文本、歌剧表演、电影拍摄、舞蹈呈现的异同,不但可全面认识《白毛女》经典化的过程,也可由此总结文艺创作和改编中锻造经典的路径,推动当下的文艺创作和改编更好地向前发展。
一、时代精神、主题凝炼与经典创作
一部文艺作品能成为经典之作,首要因素是凝炼主题。每个时代都有其面临的时代问题,也有各自的时代精神,所以每个时代的文艺经典都在集中表现并试图回答它所处时代的问题,并与时代精神相呼应,以此来凝炼主题。“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理论主张随时代发展不断变化,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价值导向。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代语境下,《白毛女》应时而生。
《白毛女》的故事最初是一个民间传说,后被记录下来成为报告文学,然后又被创作为短篇小说《白毛女人》,20世纪40年代中期被改编成歌剧《白毛女》,取得巨大成功,新中国成立后被改编为电影、芭蕾舞剧及各种地方戏曲,成为文艺改编中的经典之作。经过多次改编,《白毛女》的主题被一步步凝炼和升华,与时代的关联更为紧密,成为号召广大工农兵反抗地主压迫、凝聚时代激情和理想的典范作品。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创世神话不同,白毛女并非英雄,而是弱者,但正是这样的弱者需要被拯救、被同情,所以,她的控诉便成为对旧世界的控诉,而拯救她的英雄便成为被时代歌颂的英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作品通过塑造这样一个普通女子的形象,揭示出旧社会一定会灭亡、新社会一定会来临的历史必然性。这是该作品的特色和取得成功的原因。白毛女这样的女性形象是当时中国千千万万被压迫和被损害的女性的代表,很容易在广大贫苦百姓中引起情感共鸣,激发起人们对压迫者的仇恨,进而走上革命道路。《白毛女》创作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的主要内容和主题是反封建,这是它要表达的时代精神和主题内涵,而对它的改编则一步步实现了这样的政治追求和艺术表达。
白毛女的故事最早来自民间传说,主要来源于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第三分区西部山区。李成瑞曾回忆说家乡河北有“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每年三月春暖花开之时,家乡淑闾村的乡亲们便会去附近的青虚山庙会烧香拜佛。因为有人看到山上有个“白毛仙姑”,每天晚上会来庙里偷吃供品。她一旦发现有人出现时,便像一阵风似的不见了。后来,人们又说那白毛女原来是一个受恶霸地主欺辱而逃进深山的农家女,长期没有盐吃导致头发全白。这是原始故事。作家周而复、剧作家任萍、歌剧《白毛女》导演之一的王滨、电影《白毛女》编剧之一的杨润身等人后来也都谈到过当时存在不同版本的“白毛仙姑”故事。通过他们讲述的故事,可概括出民间“白毛仙姑”传说的一些共同特征:一是“白毛仙姑”的故事在多个地方流传;二是这些传说反映出地主欺辱农家女在当时颇为普遍;三是农家女不堪忍受地主压迫,但无处可去,只好逃往深山;四是“白毛仙姑”由于常年吃不到带盐的食物,所以头发全部变白。
由于这个故事在多地流传,所以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成为认识当时社会的一个切入点。作为《晋察冀日报》的记者,李满天(笔名林漫)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故事的重要性。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有了新的方向。于是,李满天采访传播这些故事的人,写成了报告文学,之后又深入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山区采访了更多人,写出了一篇1万多字的短篇小说《白毛女人》。李满天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提炼了主题,加入了八路军这一集体形象。在长期的采访和写作中,他认识到这个故事和人物的典型特征及其反映的时代精神,是当时革命斗争所需要的,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得有更好的传播,方可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他于1944年秋天请去延安的交通员把小说带给周扬。周扬看过后,立刻感受到了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内涵,并有了进一步的思考。
当时,周扬正在为党的七大准备献礼节目。他决定将这部作品改编为歌剧,重新凝炼主题内涵,进一步塑造人物形象,以此激发广大工农兵的情感。于是,由贺敬之、丁毅执笔,汇集集体智慧创作出歌剧《白毛女》。歌剧《白毛女》在延安多次上演,广受欢迎。随着群众的热烈关注与反馈,歌剧《白毛女》剧本历经多次修改。最终,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白毛女》,此书被列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该版本成为此后供文学欣赏和舞台演出《白毛女》的定本和保留本。歌剧《白毛女》在保留小说《白毛女人》主要情节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这些修改均与凝炼主题有关,以便更好地表达时代精神,激发人们的斗争精神。
第一,进一步提炼了主题。“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没有明确的主题预设,只是一个猎奇式的故事,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除了故事的细节被“添油加醋”或“以讹传讹”使不同人讲出的故事内容千变万化之外,未能产生明确的有价值的主题。小说《白毛女人》虽在民间故事基础上增加了八路军的形象,提升了故事内涵,但只是将一个民间传说以小说形式表现出来,其主题仍停留在破除封建迷信层面。而在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和改编中,周扬事先确定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并要求改编者围绕这一主题开展创作,作品的人物、故事、情节都要与这个主题相符。这一主题有双层内涵,一方面是“旧社会把人逼成鬼”,即主要表现旧社会底层农民在以地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压迫下的悲惨命运;另一方面要表现“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即主要表现解放后农民的新生活。这一主题使作品具有了更为广阔和立体的表现空间,比如,为表现这一主题,歌剧《白毛女》重新设置了八路军的出场方式。八路军来之前人们的期盼和八路军来之后帮助农民推翻地主的压迫、建设新社会,是歌剧《白毛女》在小说《白毛女人》基础上改编的重要故事情节,表达了新的主题内涵。在歌剧《白毛女》的创作改编中,这一“主题先行”的做法表面上看似与文学艺术生产的规律相悖,但实质上却体现出创作者对时代精神的精准把握,契合了时代需求,表达了当时广大农民群众的强烈诉求,极大激发了人们推翻旧世界、创造新社会的热情。
第二,强化了对主题的表现力度。歌剧《白毛女》用大量细节表现了主人公喜儿与父亲的深厚亲情、与王大春的坚贞爱情以及与乡亲们朝夕相处的邻里情,使整个故事的情感叙述更加充分。例如,在外躲债的杨白劳偷偷带着卖豆腐赚回的二斤面,在除夕夜贸然回家,只为让喜儿吃上饺子,还给女儿买了两尺红头绳;王大春在去西北寻找红军前,托二婶给喜儿带话“无论多苦,要等着他,他会回来”。这些细节使歌剧更为具体可感,更具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同时,它们也是为表现时代精神服务的。造成杨白劳不敢回家的原因是地主压迫,致使王大春离家的因由也是地主欺压,而红军则是他们的希望。这些动人的细节并非只是出于增强艺术表现力的考虑,也是为了表现主题,在激起观众对喜儿、杨白劳不幸命运同情的同时,也激起了他们对地主的痛恨,进而表达出对党和人民军队的渴望。此外,歌剧还增添了几位次要人物,如杨白劳的好兄弟赵大叔,他能在关键时刻为王大春指明方向“去西北,找红军”,对强化主题表现很有助益。
歌剧《白毛女》自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首演成功后,受到党的领导人和群众一致好评。丁玲这样描写延安群众观看歌剧《白毛女》的场景:“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屋顶上是人,墙头上是人,树杈上是人,草垛上是人。”1953年,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将歌剧《白毛女》写入文学史,充分肯定了其历史价值,称它是“新歌剧的进步与发展的一座里程碑”。歌剧《白毛女》的改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除了艺术上的大胆创新和积极尝试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抓住了当时最鲜明的时代精神,并在作品中加以艺术化的表达,提炼出反抗地主压迫、只有党和人民军队才能拯救老百姓的主题。由此可见,表达时代精神、凝炼密切呼应时代发展的主题对作品改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白毛女》被改编成电影。这是“白毛女人”故事继小说、歌剧之后的又一次改编。因为歌剧的巨大成功,电影《白毛女》在主题、内容的呈现上基本是按照歌剧《白毛女》进行的,在表现形式上也保留了歌剧中的经典唱段,但电影《白毛女》绝非对歌剧《白毛女》的简单复制和影像化再现,而是在主题表达上又前进了一步。
首先,从个体复仇到阶级革命的主题演进。电影《白毛女》表现的已不是被压迫的农民个体对地主的复仇故事,而是代表着被压迫农民的影像符号杨白劳、喜儿、王大春等反抗压迫阶级的影像符号黄世仁的革命叙事。在电影中,杨白劳、喜儿、王大春三个影像符号分别代表逆来顺受者、觉醒者、反抗者,三者潜在构成了“革命”发生的时间序列;黄世仁则被塑造为一个丧失人性的残暴压迫者形象,尽管这一形象显得单一和扁平,但因为电影要呈现农民和地主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同时呼应当时的农村土地改革,所以这样的设置有其时代合理性。
其次,从个人小爱到阶级同志的大爱。小说和歌剧都没有对未来生活做更多展望,这与作品创作的年代有关,但电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改编的,此时人们过上了新生活,并开始进一步探索新的制度、伦理和价值观。因此,电影对主人公的爱情进行了特别呈现,以此表达新社会男女平等、自由追求幸福与美好生活的主题,在“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拓展。歌剧《白毛女》中,王大春是作为即将与喜儿成亲的对象突然出现的,电影则对喜儿与王大春的情感进行了细致展现,如两人一起在田间劳作、嬉戏,两家人平时相互照料,王大春和喜儿一起努力干活帮杨白劳还债等,塑造出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形象。这些改编一方面增强了电影的艺术观赏性,另一方面也展现出新的社会风尚。自由与平等在旧社会无法得到,但这正是新社会的重要价值观念。电影最后喜儿和大春在田间收割麦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展望着未来。喜儿顺手取下头上包裹的毛巾擦汗,无意间露出了乌黑的头发。重新变黑的头发,与之前在深山居住时一头苍白的枯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暗示着农民阶级被压迫、受侮辱的时代已过去,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迎来了幸福的新生活。在此,个人化的男女之爱在一系列革命化影像符号之下得到升华,成为包含新社会阶级同志之间革命情感的大爱。
1964年,《白毛女》在小说、歌剧、电影的基础上又被改编成芭蕾舞剧。该剧剧本由贺敬之、丁毅编创,马可等作曲,上演后成为芭蕾舞和中国民族舞结合的典范。1970年,上海电视台、上海市电影摄制组将芭蕾舞剧《白毛女》摄制成黑白电视屏幕复制片。
与歌剧和电影相比,芭蕾舞剧《白毛女》在人物外形特征、主题思想、时代精神方面又有了很大变化。首先,在人物外形特征方面,芭蕾舞剧《白毛女》利用舞剧的独特表现力,对人物造型进行了更新。在剧中,喜儿的大长辫子和红色棉袄极具视觉效果,凸显出农村少女的青春气息和活力。大春则头戴羊肚手巾,体现出一种质朴敦厚的北方农村青年气质。同时,喜儿和大春的造型都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该剧将民族化的造型和具有“国际范”的芭蕾舞形式完美结合,在中外文化的交融创新中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这种艺术创作方式和思路对当下的文艺创作仍有借鉴意义。
其次,在主题思想方面,芭蕾舞剧《白毛女》对歌剧和电影中的阶级革命主题作了进一步的强调和渲染,而与此相关的阶级和革命符号也更加突出,全剧贯穿着一种激昂的政治和革命情绪。在芭蕾舞剧中,杨白劳一出场就已经是一个敢于反抗压迫的形象,身上已具有了革命者的潜质。喜儿则由原来的“成长型”人物变成了一个美丽、聪明、勇敢、革命意识非常强烈的人物,原来的各种复杂情绪和心理成长过程皆被作了简化处理。大春的被迫逃离家乡被改成了主动参加革命。这一从“被动”到“主动”的改变让全剧的革命主题更加突出,强化了人物的斗争与反抗精神,凸显了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最后,芭蕾舞剧《白毛女》所彰显的时代精神与歌剧、电影有所不同。《白毛女》从小说、歌剧、电影,再到芭蕾舞剧的主题嬗变,反映了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时代精神变迁。从20世纪40年代到1964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新的文艺创作需求开始出现,那就是要以一种新的话语、符号和精神来实现文艺的政治诉求。
可以说,从民间传说到报告文学、小说文本,再到歌剧、电影和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每一次改编都在提炼更贴合时代的主题,这是促成它在改编中逐步实现经典化的重要因素。
与《白毛女》的改编相似的有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刘文韶在海南军区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时,经过多方采访,发掘了娘子军连的事迹,写成了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发表在1957年8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后来又根据该题材撰写了电影和歌剧的剧本。与此同时,梁信也写成了《琼岛英雄花》的电影剧本,后更名为《红色娘子军》。该剧本由谢晋拍成电影,他因此获得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1964年,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红色娘子军》由中国国家芭蕾舞团改编为芭蕾舞剧并首演成功。此后,该剧在国内外演出超过3000场,被誉为“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作品”。从民间传说到报告文学,再到电影,最后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走过的经典化历程与《白毛女》几乎完全相同,区别在于《白毛女》有小说文本,而且是先改编为歌剧后改编为电影,但它们在依托时代凝炼主题方面有相似之处。
由此可见,创作文艺经典,需要文艺工作者站在时代前沿,思考所处时代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回答时代之问,将时代精神凝炼成作品主题,并加以艺术化展现。这是创作和改编文艺经典的重要路径之一。
二、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与经典形成的关系
形象是我们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符号,作家艺术家要表达深刻的思想,呼应时代精神,创作文艺经典,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是不可或缺的手段。
白毛女是经过一番苦难后,最终拥有了自由、平等和爱情的农民女性形象。她虽有痛苦的过去,但解放后是幸福的。歌剧和电影《白毛女》中的白毛女是一个新人,一个被从压迫中拯救过来的新人,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的白毛女则是一个勇于反抗的革命者,“她们”都是新的女性形象,也是中国现当代文艺中的典型形象。
白毛女的形象是被一步步塑造出来的。从最初的报告文学和小说,到后来的歌剧、电影、芭蕾舞剧,白毛女是一个经历了长达20余年的不断塑造才最终完成的典型形象。白毛女的形象塑造主要经过了“鬼—人—社会主义新人—革命者”四个阶段:在民间故事中,她是一个受苦的、无法得到拯救的农村女性,在这样的环境中,她从人变成“鬼”,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在李满天的小说《白毛女人》中,由于八路军的出现,她从“鬼”变回了人;在歌剧和电影中,她不仅觉醒,而且勇于反抗,最终成为自由的人、平等的人,还拥有了爱情,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在芭蕾舞剧中,她是一个始终如一的反抗者和革命者。最终,她成为一个独特的典型形象。这一文学形象体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革命理念。
王大春是另一个典型形象。他也是一个新人,是白毛女这一新形象的伴生者,甚至也可说是拯救者。如果没有他的出现,喜儿就不可能得到解放,不可能获得自由、平等和爱情。尽管王大春在歌剧和电影中属于次要角色,但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典型性。王大春这一形象是艺术家基于当时的社会生活进行创造性建构的结果,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与喜儿一样,王大春也是从底层农民中走出的新人,他不同于之前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也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形象。他是八路军的代表,生活在底层,被迫走上革命道路。在加入八路军之前,王大春像杨白劳一样,是一个老实憨厚、不敢反抗地主,甚至有些懦弱的农民。但当他身穿军装带着八路军队伍归来时,他成了革命力量的代表。王大春是来终结地主压迫和开启新的时代的人,不仅仅是革命力量的代表者,更是土地的重新分配者,代表着新的伦理价值、社会秩序,是新生活的缔造者。如果说歌剧和电影中王大春的角色还略显次要的话,那么在芭蕾舞剧中,主动参加革命这一行为设置让王大春的角色更具标识意义,因为他代表了广大农村青年在特定时代的人生选择,也代表了整部芭蕾舞剧的革命基调。可以说,不论在歌剧、电影还是芭蕾舞剧中,王大春这个人物形象都被赋予了深刻的历史内涵。
在歌剧中,因为舞台限制,王大春带着八路军肩背步枪,直接回到杨各庄。而电影可以更加丰富地渲染,特意在王大春归来之前用八路军打败日本鬼子的激战场面和八路军高举红旗渡过河流等壮观场景做铺垫,突出八路军英勇善战的形象。当八路军到达杨各庄时,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他们高呼“遭罪的日子到头了”。八路军立刻号召村民团结抗日,帮助他们减租减息。黄世仁试图利用村民对白毛仙姑的敬畏阻止减租减息,不料,却刚好促成了王大春和喜儿的相遇。由此,白毛仙姑作为保佑杨各庄村民的封建迷信被八路军打破。最后,黄世仁和穆仁智被八路军押解到全村公审大会。八路军尽全力帮助农民获得合法权益、时刻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真实行动,最终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心。旧的历史被王大春代表的力量终结了,新的历史时代被开启。这就使集体形象与典型人物高度融合,并有机统一到一起。在这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行动。
与代表新人形象的白毛女相联系,她的父亲杨白劳也具有典型意义,是无数受苦受难农民的代表。歌剧中杨白劳的出现不过短短一幕,展现出对女儿的疼爱与唯唯诺诺的软弱形象,是传统逆来顺受的农民形象。但在电影改编时,创作者运用电影的艺术手段,强化了一系列典型环境。电影中,佃户们在田间辛苦劳作,他们与杨白劳一样都失去了土地,靠租用地主的土地生活;杨白劳家徒四壁,没钱过年,因为欠债被迫卖女儿,最后被逼自杀;而地主黄世仁则为富不仁,对农民没有丝毫怜悯之心,黄家大厅里供奉的佛像、木鱼、佛经、佛珠,以及黄世仁成亲时特写镜头凸显的“德贯千顷”“大慈大悲”“积善堂”等牌匾都与黄世仁的残暴冷血构成了巨大的反讽,而杨白劳的自杀则是社会秩序崩坏的象征。
从文学史角度来看,如同喜儿这一形象的产生是经过很多思想和革命实践得来的一样,王大春、杨白劳这些底层农民的典型形象也是社会思潮和革命实践深入发展的产物。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后,为广大工农兵服务成为新的文艺方向,农民成为很多文艺作品的主角。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诞生了《白毛女》,也诞生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创业史》等作品。这些作品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在后世引起人们广泛而持久的共鸣,成为文艺经典。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是这些作品实现经典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当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创造新的典型形象,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应思考的重大问题。
三、个体经验、集体创作与经典生成的关系
通过梳理《白毛女》经典化的成功经验,结合不同时期的经典创作和改编,可以发现,除上面总结的两条经验外,还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和关注。
第一,摆脱狭隘的个人经验,到广阔的时代生活中去发现典型人物和典型故事。这是古今中外经典作品创作的一个基本方法。只有如此,才能摆脱个人偏见,真实写出一个时代的细节和精神面貌。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作家、艺术家摆脱狭隘的个人经验,到群众中去。很多作家纷纷走进工农兵的生活中,以工农兵为主人公来写作,《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作品就是在这样的创作方针指引下完成的。这种创作方法影响了一大批作家,例如,周立波在1946年10月前往东北参加土地改革,1947年7月携《暴风骤雨》上卷初稿到五常县周家岗继续深入生活,历时4个月,一边工作,一边对《暴风骤雨》上卷初稿进行了较大修改。1956年1月,周立波返回桃花仑故里,投身农业合作化运动,并担任了益阳桃花仑乡党委副书记,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创作了《山乡巨变》。柳青也一样,1952年8月,他到陕西省长安县任县委副书记,主管农业互助合作工作,同时深入生活开展调查研究。到1953年3月,他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一职,保留常委职务,到皇甫村定居,住在破庙里,一方面继续深入生活做调查研究,另一方面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创业史》。这些良好的传统一直被继承下来,很多作家都有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经历。但毋庸讳言,也有些作家是以自己的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他们基本上过的是书斋生活,其自身的生活经验又总是有限的,因而也就难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也因为他们局限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也很难去思考时代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难以有“国之大者”的胸怀与视野,自然也无法凝炼出宏大的主题。因此,继承和发扬深入生活的优良传统,是创作文艺经典的必然要求,也是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要表现一个时代的风貌,表现一个时代人民的悲欢、喜怒和心声,就需要走进人民的生活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他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白毛女》的创作和改编,正是深入生活的结果,其成功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第二,超越自我,用集体智慧提高艺术水平。《白毛女》从民间传说到小说,再到歌剧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电影《白毛女》的创作又是在歌剧基础上进行的另一次集体创作,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创作也是如此。其中,从小说到歌剧这一过程值得特别重视。小说创作者只是感受到了一种时代精神的召唤,而歌剧的改编则准确把握到了时代精神,并据此凝炼主题和塑造形象,才打造出了这部经典之作。集体智慧能使作品超越单个作者在识见、胸怀和情感等方面的局限,也可使作品中的人物关系更为严密妥帖、情节上的呼应更加丝丝入扣。当下,有些作家过分强调个人写作的重要性,强调个体修辞的独特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集体智慧的力量,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现象。在文艺创作中,个体有个体的优势,集体有集体的长处,应将这两种创作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文艺工作者也应借鉴集体创作的成功经验,创作出新时代的文艺经典。
第三,克服小众视野,用改编促进大众化传播。从歌剧到电影是《白毛女》传播的一次巨大提升。如果仅仅是歌剧,那么它只能给有限的人群观看,广大的老百姓很难看到,如此一来,这部歌剧的传播效果就会受到很大局限。但当它被改编为电影,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观看时,一个时代的情绪就被调动起来,文艺的效用也因此真正显示出来。从众多经典文艺作品的大众化改编可看出,大众化并非经典的敌人,而是经典传承的重要途径,而影视改编和传播则是其中最为方便的方法之一。因此,为扩大经典文艺作品的传播面,可将其改编为大家乐于接受的影视作品。同时,传播媒介的变化也要求文艺工作者转变心态,积极面对影视改编,创作出能反映时代风貌和人民心声的作品。这些都是《白毛女》和众多经典文艺作品创作和改编带给我们的启示。
歌剧、电影、芭蕾舞剧《白毛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产生的经典力作,是体现中国气派、中国美学风格的典型艺术文本。以《白毛女》为中心,结合百余年来中国文艺作品的创作和改编实践,考察其中的得失,总结创作经典的经验与方法,可为新时代的文艺创作提供借鉴和参照,促进文艺工作者创造出新的艺术高峰。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范利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