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作家中,艾伟非常关注女性主体意识与性别身份、时代情感经验、社会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显示出他对女性主体意识整体性经验的敏锐洞察。他的小说《爱人有罪》《爱人同志》《妇女简史》及《镜中》,具象地描述了女性主体意识和时代整体性经验之间的密切勾连,展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女性形象的嬗变。艾伟对女性主体意识流变的深刻剖析与摹写,极大地拓展了现代女性生命体验的丰满度、情感认知的复杂性和人性维度的多面相。
关键词:艾伟;女性主体意识;时代情感经验
作者郭艳,鲁迅文学院研究员(北京1000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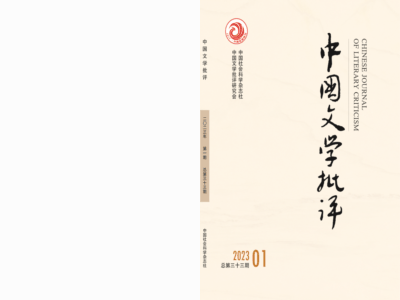
近现代女性日渐获得更多政治、经济、情感乃至人格的独立和自由,然而唯一不变的是女性主体性表达的模糊、暧昧和艰难。经历了极端女权主义、温和女性主义等一系列的运动之后,女性却日益被欲望化、符号化和刻板印象化。由此女性主体性在意义纷呈的同时,又再次陷入芜杂和迷失。很多作家都曾关注女性个体生命体验的觉醒,比如写少女的意识流动,女性欲望的觉醒,大历史景深中女性的命运等。更为先锋的女性写作中,世界与“她者”之间始终充满着紧张与错位,女性欲望化象征符码被放大,女性主体意识反而在精神情感维度上后撤。在倾诉性的话语情境中,这些文本表达了男权意识和观念下被压抑的女性的觉醒和抗争。然而,庸常现实中女性主体意识更多呈现出蒙昧状态,很多女性处在主体意识尚未觉醒或刚刚觉醒的阶段,而更多女性的主体意识可能处于混乱无序的模糊状态之中。女性主体意识一旦和现实联系在一起,就会被各种因素所左右,女性往往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现代女性清晰而确定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往往以观念的形式存在。
当代作家中,艾伟非常关注女性主体意识与性别身份、时代情感经验、社会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显示出对于女性主体意识整体性经验的敏锐洞察。他对这些命题的叙述和摹写也独具面目,深刻揭示出女性主体性经验的流变。女性生存时常是被动的、不自知的、盲目的,被抛入的生活往往是她们生活的常态。艾伟耐心地呈现出了这一被抛入的过程,叙述她们如何被动地进入莫测的生活和命运,以及这一过程中女性自身所呈现出的蒙昧、纠结、挣扎和撕裂。他深入描写了女性在主体意识缺失状态下的进退失据,以及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后,面对灵肉两端的挣扎乃至沉溺。他的小说《爱人有罪》、《爱人同志》、《妇女简史》和《镜中》,集中体现了对女性主体性经验的深切洞察。这些文本中的女性主人公都具有主动性的人生选择,在时代主流价值观念影响下,主动投入到时代流行和推崇的价值观念与伦理体系中,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塑型,如成为英雄的妻子、小街美人、城市尤物等。而在被时代所裹挟的生活流中,义无反顾地追求或者说实践自己认定的观念和标准,恰恰是不确定和危险的。文本叙述了她们将自己交付给莫测的情感和命运,体现出特定时代女性主体性的集体无意识,以及集体无意识中呈现出女性主体意识的日渐觉醒和嬗变。
四部小说提供了近半个世纪中国当代女性自我认知的三个阶段:内化的道德律令与女性献祭的自我迷失;个体意识觉醒的欲望情感表达与自我的救赎;物质主义豢养中主体意识的沉沦与后撤。
一、内化的道德律令与女性献祭的自我迷失
《爱人同志》讲述了残疾英雄刘亚军和普通女孩张小影的婚姻情感生活。小说独特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日渐繁荣的社会语境中,文本着力刻画了英雄和献身英雄的善行被逐渐遗忘,而英雄和献祭的女性依然背负着过去踟躇而行。小说讲述了刘亚军英雄形象背后对于自身残疾的自卑和对于现实生活的绝望,女孩张小影献身英雄之后对于公众人物身份的痴迷与沉溺。张小影是当时一个普通的女孩,具有善良柔顺的性格和纯洁无私的品性。她的人生原本是寻常的戏剧脚本,但却因为张小影自身对于道德主义(实质上更多虚荣成分)的追求而发生了改变,或者说在残疾英雄的光环效应中,张小影对刘亚军产生了超乎寻常的怜悯、关注,甚至于爱情。张小影从单纯的看护女孩,到嫁给残疾英雄成为献祭的“圣母”,最终因时代价值更迭和自身的改变,沦为和残疾人刘亚军相生相杀的匹夫匹妇。文本对于时代集体无意识悉心体会和揣摩,尤其对于女性集体潜意识有着非常精准的把握。崇拜英雄是那个时代的风尚,女青年献身英雄更是为人称道的善举。在这种影响下,无数女青年幻想着嫁给英雄,哪怕是残疾英雄都拥有着很强的魅力。这种内在道德律令对于当时女性的主体意识的影响是强大的。小说通过张小影的人生选择,非常具象地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对于英雄如痴如狂的膜拜,又通过对二人婚后情感生命体验的摹写,描述了在这种英雄崇拜和道德崇高感笼罩之下,张小影人性真实本质的荒谬和虚无。小说让人深思的是:张小影的纯洁、善良、爱以及宽容、忍耐、坚强是真实的,是内在道德律令产生的真实品质。这样的女性却在自我献祭中迷失,显出某种令人心酸的反讽和荒诞。虚荣心仅仅是表面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她完全没有最基本的女性主体意识,终其一生,都没有对自己的生活有过自省和凝视。相对于张小影这种极端非我的选择,她周围的人物其实都具有明显的自我意识和个人化选择。男主人公刘亚军是个“另类”的英雄,作者没有描写一个从战场回归日常生活之后依然充满道德感和崇高感的军人,而是通过描述这个英雄内心的地狱图景,讲述伤残的身心和这种身心所带来的自卑、屈辱和变态,以及这些人性之幽暗面对生活的败坏、对人性的扭曲和对灵魂的摧残。
文本貌似是从新闻报道的轰动事件进入小说叙事,实际上则是通过张小影非我的自我选择,讲述一个极具道德感的女孩对整体性生活经验完全无知,对于基本的人性维度毫无省察,对于平庸生活缺乏常识认知……与此同时,又被时代表面流行的观念所裹挟,即便她向往崇高伟大的情感,又具备宽容忍耐和坚韧的品性,当然也有着对于名利的虚荣,她的人生选择依然会带着极大的盲目性和伤害性,尤其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致命的伤害。张小影那个饱经人世沧桑的老父亲,站在幕后暗影中,眼看着女儿一步步迷失自我,陷入人生的困境。
文本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日常生活的精神情感以及性心理的深度刻画,多维度重新阐释了张小影和刘亚军这对英模夫妻之于时代、社会、大众以及熟人社会种种关系的复杂意味。自我献祭的“圣母”和圣母般的道德牺牲曾经是一种风行的价值选择和道德律令,文本阐释了这种选择之于人性本质真实的虚妄。与此同时,女性主体意识的蒙昧是这种献祭的根源,在一个缺乏女性自我认知的时代,年轻女性的善良单纯是美好的,然而女性主体意识匮乏带来的对性、情感、婚姻乃至生活本身的盲目无知却是致命的。
二、个体意识觉醒的情感欲望表达与自我的救赎
《爱人有罪》的题目耐人寻味:这个爱人是有罪的,爱这个人是有罪的,这两种解读都暗合文本内蕴的反讽和揶揄。文本对普通人的特殊经历进行想象和重组,在虚构的文本中透视人性与生活的本质真实,尤其侧重于摹写女性个体心理情感和生命体验。小说女主人公俞智丽身份的设置独具匠心,作者将附加在女性身上的诸多社会身份一一从她身上剥离:俞智丽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女儿,甚至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女人;她曾经被强暴,是受害者;她告错了人,又是诬告者。俞智丽不具备通常伦理道德标准的女性身份符码,然而正是这些伦理标签的剥离,俞智丽的人生经历才更为清晰地呈现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性主体意识三个层面的觉醒。
俞智丽女性主体意识第一次觉醒是成为小街美人。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以身体和外表之美的觉醒为标志的。对流行时尚的追求往往被看成不务正业,而这种追新逐异的风气又深深吸引着众多年轻人,且成为街谈巷议的资料。身体之美和外表之美往往引起大众集体无意识的羡慕与嫉妒,时常和不良品性联系在一起。由此俞智丽被强暴的事件,一方面追究罪犯的责任,一方面社会舆论依然有因美致祸的推断,以至于俞智丽也认为是自己过于追求时尚外表之美而招致不幸。由此她迅速嫁人生女,穿着保守,到处做善事,俨然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忏悔和救赎。事情吊诡之处在于:鲁建正是因为小街美人而深深迷恋着她,甚至于出狱之后,依然在爱恨交织中和俞智丽纠缠不清。
第二次主体意识觉醒是身体和情感的安放。欲望和身体是女性主体意识表达的焦点,这个文本最为深刻的地方在于:俞智丽是个受到过性伤害的女性,但她并没有因为这种伤害自暴自弃,沉沦放荡。在遍地流言蜚语的时候,她很快地结婚生女,丈夫也温存善良,俞智丽无法体验到幸福,不是因为自己曾被强暴,而是因为她没有爱情。即便没有爱,她也尽量活成应该有的样子,温良恭俭,俨然从小街美人转换成为良家妇女。可是作为主体意识很强的女性,她的情感和身体是沉睡的,一旦遇到真正灵魂相契合的人,身心就会从沉睡中醒来。鲁建就是那个她命中错过、伤害过又时时在等待的人。由此她遵从自己的内心,和鲁建生活在一起,让自己的身心得以在救赎之爱中安放。
俞智丽第三次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对母爱和亲情的眷念。俞智丽并非没有伦理亲情,只是在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中,这些情感是微弱的,毕竟她不会被固有的道德伦理规训所束缚。但是当她从生命体验的角度感受到对女儿的爱时,发自内心的亲情是如此浓烈,这种亲子之情就像爱情、欲望和精神救赎一样,让俞智丽从自己非母亲的状态中惊醒。这种对于母爱和亲情的眷顾并非道德或者伦理规约的,而是发乎内心的自然而真挚的情感。
俞智丽的人生更多是自我选择的结果,由此层层展现出她的女性主体意识和命运之间的关联。这三次觉醒带给她的既有觉醒的快乐,更有不顾一切带来的巨大伤害。俞智丽女性主体意识呈现出当代文学罕见的忏悔意识及救赎精神,深切表达了普通人爱欲、道德、伦理与日常性之间的矛盾,以及主人公在救赎行为中对自我的不断审视、打量与内省。
三、物质主义与女性主体意识的沉沦与后撤
20世纪90年代现代性进程加剧,物质主义开始影响人们的身体、情感与婚姻,娱乐至死的价值观念开始广泛传播。身体和欲望从自卑的、私密的与可耻的,进而转换成为自信的、公开的甚至于享乐的,且以流行时尚的面目出现。在这种社会价值伦理风尚中,女性主体意识在身体和欲望方面也开始有所反映,部分表现为和男性一样追逐婚外情或者多重性关系的身体体验。
《妇女简史》如果不放在艾伟小说的整体性框架中,它可能会被认为是一本关于出轨的小说,然而当它和《爱人同志》《爱人有罪》《镜中》一起出现的时候,就能够清晰地看出作家对于女性主体意识整体性经验的持续关注与思考。文本通过女主人公小项的婚姻情感经历,阐释了当代女性对于性自由、性解放价值观念的无法抗拒又无所适从。和以前时代女性被偷窥、被欲望化及被社会身份符码化不同,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体觉醒恰恰是以身体和欲望的个体性表达为特征的。所以文本中描述了小项从对周菲作为有夫之妇婚外性关系的排斥,到自己婚后因为性和情感生活的无趣而出轨,表达了女性个体对于平淡婚姻和情感的厌倦和逃离。相比较《爱人同志》中张小影非我的选择,《爱人有罪》中俞智丽对于身体和欲望满足的忏悔,小项是在更为宽容和开放的伦理环境中面对自身真实欲求的主动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小项面对婚姻情感的态度是当时伦理观的映射:婚内出轨、小三等词汇的高频率出现,是现代人面对身心更高自由度的反映。现代女性身心欲求更多个人化的选择和感官的满足,这种女性主体意识现状使得女性灵肉两端得以很大程度的释放,但同时也带来了灵肉两端异常混乱的局面。由此文本中的小项是可爱的,又是迷惘的。她想要一个身心契合的人生伴侣,却在身体出轨的同时遭遇精神情感的危机。婚姻的潘多拉之盒一旦打开,就会遭遇始料不及的各种心魔。当一个女性以欲望身心来面对男性同样的欲望和身体的时候,她既看清了自己曾经看不清的世界,也陷入了对于这个世界的迷失和无能为力。毕竟一直作为被动存在的女性及其身体和心灵,并没有做好应对真实的身体和欲望的诸多准备。由此小项在打开身体和欲望的时候,遭遇到的并非理想中的灵肉契合,而是各种接踵而至的身心创伤,以至于最终只能从情感婚姻(包括身体欲望)中抽身而去。
《镜中》是对现代婚姻和伦理的一次幽暗探寻,是艾伟对于现代人身心更为彻底的一次叩问。这部小说是《妇女简史》文本的延伸,从俗世的烟火向心理的、观念的、哲学的区域探寻,从俗世伦理的层面去透视人性幽深地带的复杂图景,探讨人性趋向可能的超越性追求。文本通过女主人公易蓉与丈夫润生和情人世平的感情纠葛,在不同镜像中呈现了人性不同维度的真实以及虚妄。两位男性主人公都是当下理性、精明、体面而文雅的成功人士,富足安逸的人生图景中,他们的情感和婚姻生活依然千疮百孔。在朦胧的面纱之下,肉身的沉重、爱情的歧义、友情的背叛连同巨大的虚无,这些命运的黑洞不断吞噬生命的力量。在死亡的阴影中,艺术和宗教闪现着救赎的光亮,让现世众生相偶或凝神缄默,内省和反观爱恨贪嗔痴的庸常人世。
《镜中》对两位男性主人公着墨甚多,然而易蓉却是从容驾驭两个男人的大女主。本文也更多从女性主体意识整体经验表达的角度阐释这部小说的内涵和意蕴。小说非常真实地再现了社会物质日渐丰裕之后,接受良好教育的现代女性对于生命深度的内在体验,以及对于爱情婚姻更为精细和复杂的欲念。易蓉养母纵情声色、沉溺酒精与艺术的一生,给易蓉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物质享乐主义的认知背景。现实生存的物质主义认知尽管程度不同,但是对于每一个现代人而言都是真实存在的,易蓉是更能代表现代性复杂特质的女性。易蓉不喜欢这种阴郁而颓靡的生活,所以她嫁给了阳光而清新的润生。对于易蓉来说,母性的、端庄的、镇定的和阳光的品性,这些仅仅是她大家闺秀的一面;她更有着来自物质主义所豢养的任性、享乐、阴霾和虚无的一面。人性阴面和阳面交织在易蓉的灵肉生存中,她的纠结、挣扎和分裂都源自于此——这也是所有“无根现代人”的精神分裂症候。易蓉在文本中文字的分量并不是最多,然而她却是最重要的核心人物。两个男人对于这个女性的爱、恨与痛恰恰因为易蓉身上背负着这个时代女性主体意识幽深的裂变和浓烈的悲情。有深度的、痛感的、精致的且美丽的女性及其灵魂,正是这些让男性着迷沉溺又痛不欲生。
这个文本探讨了人性幽微处爱与欲的表达。当下,一些人日渐远离传统道德伦理价值观念,情感伦理生活呈现出无序混乱的状态。他们在情感、婚姻乃至精神生活的道路上奔跑,往往呈现出加速度的裸奔状态,且无法刹车,故而在快餐情感和短暂婚姻中彷徨于无地。人性之幽微暗黑处有着猎奇的惊险刺激,也有着无法辨识的陷阱和壕沟,让人身陷迷局或者粉身碎骨。由此《镜中》一再让宗教、艺术和大自然成为救赎的某种方式,富有寓意的动画短片《致人间的情书》也有着四面佛的设计。然而《金刚经》云:无法相,亦无非法相。所以《致人间的情书》即便有四面佛,依然是在婆娑世界。或许人类正因其无法清静的六根六识,才有人世间弥漫的烟火气和种族繁衍旺盛的生命力。
结语
艾伟的文本一直有着一个非常稳定的世俗生活逻辑和价值体系,与此同时,他的叙事逻辑又是对于现行世俗生活及其流变的虚构变形与重塑,在重构的文本世界中阐释生存的本质真实。他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但却不是和女性对立的他者。通过这种冷静旁观者视角,他可以从容地去“看”。这种“看”带着对于女性理解之同情,深入到女性日常又能够从日常中剥离出女性和时代情绪、情感乃至伦理价值之间的纠缠与张力,从而更加理性、客观却体贴地叙述中国女性在近半个世纪时光中跋涉的场景和状态,从现代性视角去阐释女性主体意识所呈现出的独特性。
总而言之,中国人尽管深植于传统,但是近现代以来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尤其市场经济模式下社会的高速度发展,使得现代人开始受到现代文明和伦理价值观的冲击与浸润。这些尚未完全消化或者完全无法消化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本土文化根性一起,逐渐汇聚为新的传统和风尚。现代性以双刃剑的方式影响人的身心,人性、人心和世情百态进入一个新的现代社会语境,姑且不论这种嬗变的优劣,只是从现代性自身的复杂度和多面相来说,当下对于“人”的理解从简到繁,从疏到密,从浅入深……艾伟的作品突出呈现了当下时代女性形象的嬗变,具象地描述了女性主体意识和时代整体性经验之间的密切勾连。四个文本中刻画的四位女性都是特定时代独特的象征性符码,清晰传递了特定时代的风俗伦理风尚,敏锐地折射了处于时代秘史中的幽微人性。在体恤的观察中,他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流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摹写,极大地拓展了现代女性生命体验的丰满度、情感认知的复杂性和人性维度的多面相。由此,为更多人打开了通过文学所敞亮的世界更为本质地了解人性的本质真实的路径,以期在这种更为本真的内省和反思中,有更多现代女性从魔镜中出走,完成女性主体意识的真正成长与成熟。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
扫码在手机上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