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艾伟已有超过二十年的长篇小说创作经验。通过对其小说叙述主线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出艾伟的创作思想由先锋主义意识向现实主义精神不断转化和推进的过程。其近期的创作通过更接近真实的生活描写、生活故事以及有血有肉的人物性格塑造,来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生活本质,表明了艾伟使作品融入社会现实的文化自觉。
关键词:艾伟;;现实主义;;先锋文学;;长篇小说
作者张陵,作家出版社编审(北京100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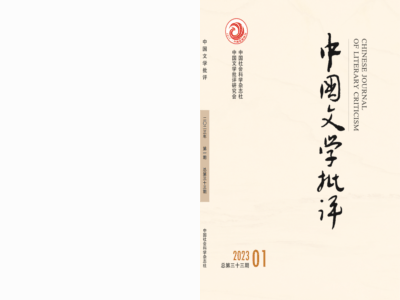
艾伟是一个写作勤奋的实力派作家。他的作品得到读者的积极反响,也得到评论家们的充分关注。从2001年第一部长篇小说《越野赛跑》开始,艾伟先后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爱人同志》《爱人有罪》《风和日丽》《盛夏》《南方》《镜中》,以及相当数量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随笔。《镜中》完稿于2022年1月,是艾伟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由此,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历史超过了二十年。
一
艾伟长篇小说处女作《越野赛跑》即使不是一部纯粹的先锋派作品,也是一部深受先锋派意识影响的作品。作家显然非常娴熟地运用“第一人称”叙述,自然而然就把历史现实经过心理逻辑“消解”,化为“个人化”视野中的事件——一个可以理性评说的历史现实,变成了“我们村庄” 荒诞不经的场景。小说把叙事的重心放在两个时期,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们村庄”许多人被一个叫“常华”的复员军人带着守仁、小老虎等打手,随心所欲地欺凌。作品主人公冯步年因为养了一匹当地罕见的马,也被不断施暴, 打得死去活来。实在受不了,他只能把自己变成了马,在世人面前学着马的样子走路,发出马叫的声音,总算能够熬过了那些苦难的日子。这样一匹马,很容易让人想到卡夫卡笔下的那只甲壳虫。另一个则发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天柱山”里的一种生生不息、似乎永远在成群飞舞的虫子,实际上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高级绿色食材。城里人都来这里吃虫子,一夜之间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吃成了灯红酒绿、光怪陆离的富裕小镇。人们富得流油,物欲无法节制,人性也开始变态。主人公冯步年曾经在“天柱山”和虫子们生活过很长时间,也因此成为“我们村庄”最先富起来人当中的首富。然而,和他患难与共的妻子小荷花却变成了一匹马,而且是被父亲关在笼子里的一匹马。
《爱人同志》和《爱人有罪》通常会被误解为姐妹篇,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意识走向的故事。唯一相同的是,这两部作品已经注意到要控制以往的“先锋性”,转向更真实更深层的“人性”的展示与开掘。前者展开了一个前线负伤、光荣归来的英雄刘亚军与他的妻子张小影的关系描写。人们实际上并不关心靠轮椅生活的刘亚军的侦察兵战争经历,而更醉心于嫁给刘亚军的张小影的社会演说效果。张小影渐渐成了两人关系的主角,而刘亚军则被不断边缘化。由此产生了相当扭曲的“人性”后果,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生活悲剧。后者则讲述一个被误判为强奸犯的鲁建,出狱后寻找那个曾经指认他犯罪的女人俞智丽复仇。故事发展却出人意料,两人有了情感关系。也许更多为了赎罪,工会干部俞智丽爱上了刑满释放人员鲁建,不顾一切离了婚,打破安定生活,和鲁建一起离开。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不幸的结局正在远远地向他们招手。
尽管这两部小说很受读者的喜爱,但这个时期,艾伟最为厚重的作品,应该是长篇小说《风和日丽》。当主人公杨小翼少女时代知道自己的生父在北京为官的时候,她内心中就建立起强烈的“寻父”念头。她作为军人保送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也开始了她真正的“寻父”历程。然而,由于当时政治的、家庭的种种原因,父女俩虽然相见,却无法相认。一个曾经身经百战的将军,在自己的妻儿面前,始终没能承认年轻时的一次情感经历。杨小翼决心让将军认下自己,反而惹怒了将军。她被发配到四川的军工厂,经历了复杂的生活,也有了自己的婚姻。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意外地救了流落到四川的将军。后来杨小翼回到北京继续完成学业,成为一个历史研究专家,设专题研究将军的革命史。她个人生活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与被判刑入狱的丈夫伍思岷离婚后,带着儿子一起在北京生活,同时,与青梅竹马但已是有妇之夫的刘世军激活了埋藏心里多年的情感。然而刘世军却因参战被俘,杨小翼也因儿子离家出走云南,死于车祸而陷入了深深的苦痛之中。这个时候,风烛残年的将军托人带话,想要认她。杨小翼说,我已经老了,不需要一个父亲了,以此拒绝。她和将军再也没有见面。不过,她得知,将军临死前好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但还记得当年,她救过自己。这部作品容量巨大,时间跨度也很大,几乎涵盖了一个女人一生的坎坷命运。如果选择用三部曲的结构去叙事,那么思想艺术效果一定会非常理想。而我们现在不得不接受作品后半部材料有些拥挤,叙事节奏有些急促的结果。
由于《风和日丽》的厚重,反衬出《盛夏》的斤两不足。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怀疑《盛夏》的文学品质成色。事实上,这是一部构思精心、故事张力极强的优秀小说。大叔级的法律界精英柯译予爱上了美女小晖,而这时的小晖却因为至少两个以上的男孩子的追求,和柯译予的关系显得若即若离。与此同时,刑警丁成来正在秘密调查一起开车肇事逃逸案。这个恶性交通事故造成了小晖的原男朋友也就是丁成来的儿子丁家明虽然抢救过来,却要一辈子过着轮椅上的生活。所有的证据,慢慢都指向了柯译予。当然,这还只是一个犯罪小说的结构。柯译予律师因得罪了维权事件中的极端人士被绑架在埋有炸弹的水塔上,是丁成来把他救下,而丁成来却在炸药爆炸中牺牲。柯译予良心发现,以自杀谢罪。
犯罪小说的模式延伸到了《南方》。作品用人称不断转换的方式,多视角地讲述一个杀人案件七天的破获过程,使一对双胞胎姐妹三十年的人生命运故事变得扑朔迷离,神秘莫测。这部作品再度显示了艾伟超常的讲故事能力,也不时流露出对他的“先锋文学”挥之不去的流连。当死者罗忆苦居然用第一人称参与讲述时,读者一定会惊讶地发现,不是死人复活了,而是“现代派”复活了。罗忆苦找到了一个好人家,嫁给了公安局政委的儿子肖俊杰。妹妹罗思甜则爱上了她们共同的朋友夏小恽。肖俊杰因杀了须南国的妻子,被父亲肖长春枪毙。从此,罗忆苦过起了失魂落魄、随波逐流的生活。夏小恽带着罗思甜私奔闯边防线,要去香港找母亲。结果夏小恽被捕判了刑。罗思甜则未婚生下一个儿子,被母亲杨美丽、姐姐罗忆苦、傻子杜天宝放在一只水桶里,沿江流去,希望好人能够捡到抚养。多年以后,罗忆苦与出狱后的夏小恽混在一起,在广东一带行骗,骗了须南国二万元,使他无力救活自己的孩子。精神变态者须南国跟踪罗忆苦,把她杀死,扔在护城河里。而这时,罗思甜的儿子在广东成了歌手,并爱上了杜天宝的女儿杜银杏。
《镜中》从故事到主题突然与艾伟以往的小说完全不同,有一种全新之感。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不仅使身居杭州的作品主人公庄润生的家庭完全支离破碎,还使作为国际知名建筑设计师的他,失去了原有的佛系品质与节奏。本来,他的犯罪感来自以为自己的偷情导致妻子、孩子发生车祸。很快,他发现情况并非这样。妻子易蓉爱他的时间加起来并没有超过一个星期,她之所以嫁给他,是因为要离开自己的演员母亲。更为令他精神崩溃的是,平时一派贤妻良母模样的易蓉,实际上是一个酒鬼和放浪之女。这样的打击,逼迫着他不得不离开繁华大都市的中产阶层生活,在中缅边境的战争难民营充当志愿者,看到了另外一种人生。庄润生在缅甸地方武装的拘留营里,深切体验到无法掌握自己命运,无助无望的普通人的苦难,内心升华出超越“自我”的崇高境界,并在后来承接的道场设计中,化为悲悯的人类情怀。这部作品的创新意识和主题深度,表明艾伟长篇小说创作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思想飞跃。
二
梳理了艾伟长篇小说故事叙述主线,就足以使艾伟小说创作思想变得清晰起来:由先锋主义意识向现实主义精神转化和推进。从文学史的角度说,批判现实主义走向现代主义,也许是文学思想的发展与进步,但对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当代作家来说,选择走向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思想落后与退步,更多表明使作品融入社会现实的文化自觉。事实上,艾伟在创作《越野赛跑》时,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思潮已进入低谷,现实主义“复归”的呼声则日益高涨。
先锋色彩较为鲜明的作品通常选择“第一人称”叙述,把“说什么”的重心放在“谁在说”。这意味着小说叙事者不再“全知全能”,而作为一个叙事“自我”体现出观察现实的个人自由,也有意表现出个人视角的局限。《越野赛跑》中的第一人称只是“我们村庄”,有点像莫言著名的“我奶奶”视角。正是这个视角的存在,小说中的历史关系、现实关系、社会关系、人际关系才能发生合理变形,才能被“心理现实”合理解构,才会出现“非理性”的合理倾向。例如作品重点描写表现的我们村庄不同时期的“人性”欲望灾难,仔细读来,之间并没有理性逻辑的关系,倒是更像两大历史碎片随意放在那里。冯步年与冯步青兄弟之间、与小荷花之间、与“我们村庄”所有人之间,关系似乎都很松散随意,之间关系的必然性仿佛被偶然性更多替代了。
“第一人称”小说并不是没有反映现实,而是以多种方式去反映现实,其中一种方式就是“荒诞”。《越野赛跑》就是“荒诞”地反映历史和现实,揭示生活的这种“荒诞”性,讲述的就是把丑恶的现实转化为“荒诞”的人性故事。一旦把现实“荒诞”化,现实矛盾冲突的关系就可以被解构,显示出非深度、非力度的特质。小说“荒诞”自有“荒诞”的意义和魅力。没有“荒诞”,小说中那匹如此重要的白马就不会那样牵动人心。艾伟自己说:“在现实的村庄里,我决定用夸张而变形的手法演绎1965年以来我们生活的变迁;而那匹白马则联系着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没有“荒诞”,冯步年就无法变成一匹马,用马的形态、用马的语言、用马的眼睛去生存,去看世界,去思考世界,去抗争世界。没有“荒诞”,就不会出现冯步年与小荷花在天柱山野无拘无束、田园自由生活的华彩桥段。
实际上,艾伟不光曾对先锋文学有重要贡献,也是当前最具实力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不光是解构故事“关系”的高手,更是组合故事关系的行家。从《爱人同志》《爱人有罪》以后,艾伟开始选择第三人称叙事方式,把重心从表现“自我”转向反映“他者”,也因此不再“荒诞”化,而是理性化、接近真实地描写揭示历史现实关系以及人际关系。从小说叙事层面看,作品正在有效地拓展现实视野,打开思想的空间,升华精神的格局。
如果说,《爱人同志》《爱人有罪》还只是“永城”故事,人物关系还比较单纯的话,那么《风和日丽》则是一部从“永城”走向四方的故事,人物关系与由此丰富复杂起来了。故事至少形成了三条线索。一条自然是女主人公杨小翼几十年“寻父”的过程。评论家们显然对这条线索更有心得。评论家王春林细腻地分析了这个过程的“思父”“寻父”“仇父”“识父”四个阶段,认为这“正是整部《风和日丽》的主题叙事线索”。贺绍俊说:“杨小翼寻找父亲的过程虽然非常艰难,但更艰难的是得到父亲的承认。”孟繁华认为:“神秘的个人身世是杨小翼内心焦虑紧张的根源。”第二条线索是杨小翼与伍思岷从相遇、结婚、生子到婚姻破裂的过程。第三条线索是杨小翼与刘世军从小到大的情感纠葛关系。这三条线索交织在一起,相互碰撞、相互作用,构成了小说中重大主题、深沉情感、复杂性格、宏大格局的融合。事实上,在巨大的历史力量面前,杨小翼的人生命运要比“寻父”复杂得多,丰富得多,重要得多。这部作品考验了艾伟驾驭现实主义小说重大题材的魄力和能力。当杨小翼这个人物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艾伟现实主义之路走通了并无限宽广。
就小说故事而言,《盛夏》是艾伟小说中最为精致、品相最好的一部。小说并不长,却能够把复杂的人物关系安排得井井有条、丝丝入扣。也可能过于精致,使这部作品更接近推理小说,导致陷入了“类型”的困局里。《南方》可能因为多人称——“你我他”的叙事者组合,以及小说时空的调配,显示出小说探索实验形式的美感。这部小说的人物关系,比艾伟任何一部小说都更突出“艾伟式”叙事风格,却也能发现,“真实”与“荒诞”的相互渗透,会让人感觉到叙事正向以往的“先锋”习惯滑行,如果作家失去控制力的话。
三
现实主义文学是对历史现实的认识把握,思想深度、批判精神、哲理意义,需要通过人物形象塑造来传递,通过富有典型性格意义的“这一个”来实现。一部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内涵和思想力量,在“这一个”的塑造里充分体现。
严格地说,《越野赛跑》由于“荒诞”内涵渗透于人物关系之中,很难看出塑造人物形象的意识,很难分析主人公冯步年的性格内涵。或者说,冯步年并不是一个理性的现实主义的小说人物,尽管他经历了恐怖的生活磨难,变成了一匹不可思议的白马。与其分析这个人物,不如分析“第一人称”叙述者。但是,这并不妨碍更深度去认识理解“变形”的思想含义和哲学意义,更不妨碍作品才华出众地写出“白马”令人神奇的魅力。小说中关于“白马”的描写,带着诗一样的情感,充满祈求敬畏的神圣感。事实上,“白马”形象象征着一个至暗年代“上苍”之光、生存的勇气和抗争的力量。这一点,它与冯步年之间有着神秘的沟通。所以步年只有把自己变成马,才能生存、才会思考、才有灵魂。白马是冯步年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能量的源泉。而其他人,变不了马,只能是没有灵魂行尸走肉,被一种几近疯狂的现实力量所吞噬。
进入较充分的写实以后,艾伟的作品人物反而没有如此鲜明的哲理气质。作品显然更自觉地使人物更加接近现实生活的“真实”,通过更接近真实的生活描写、生活故事以及有血有肉的人物性格塑造,来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自然也带着哲理的意味。显然,艾伟更愿意写普通人的故事,塑造普通人的形象。多数评论家都用“小人物”来定位这些更可能“受损害受污辱”的形象,其实,用“普通人”更为准确。《爱人同志》中的刘亚军,虽然被当作一个英雄,其实他并没有“英雄”的底气。他明白自己是在战场上意外看到敌人女兵裸体,失去警惕,才被地雷炸伤。这样的“英雄”经历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报告会上几乎无法讲述。为了配合现实的需要,他只能有意识地让妻子走到社会聚光灯下,大讲如何爱“英雄”的故事,自己自觉退到幕后。实在退不了,他也有意识回避真相,以讲述抽象的“战争人性”观,掩饰还带着一丝人性良知的道德心虚与羞愧。然而,生活的发展加深了他内心的矛盾冲突:一方面,作为小学教师的妻子,成了政协委员,社会地位越来越高,人越来越强势,夫妻关系之间的距离正在拉大;另一方面不仅自己的“英雄”光环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渐渐退去,而且还因残疾正在变为根本无力参与社会生活的弱势群体。他想用自己“英雄”的影响,帮助生活的弱者,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才知道自己是真正的生活弱者。他过去自愿帮助妻子成为社会的“圣母”,而如今,他内心却对“圣母”深恶痛绝。可是,只有当妻子是“圣母”时,社会才能让他们持续这样的“好”日子。他的心理越来越矛盾,精神压力也越来越大,不断折磨着他一直很脆弱的心灵。他也想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放下“英雄”的身段去捡垃圾,结果家里闹得鸡飞狗跳,自己内心更为矛盾。最后,他选择把自己封闭在黑屋里不出门,在黑暗之中,心灵得以平静,人性得以复归。这个人物形象与其说表现了人性的挣扎,不如说反映了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困窘与无奈。
另外一个与之相似的人物,就是《风和日丽》中的刘世军。他出身高级干部家庭,从小在部队里,前途一片光明,更像生活的宠儿。他可以和女主人公杨小翼的闺密保持夫妻关系,而又跑到北京与杨小翼同居。然而与刘亚军共同经历的那场战争,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他从敌人战俘营逃回来,受到最严格的组织审查,也沦为社会底层人士。他选择了当一个灯塔管理人,每天伴着无尽的寂寞。回归普通人生活后,他找到了“自我”,非常乐观充实,表现出军人的“英雄”品质。从刘亚军形象到刘世军形象,我们看到艾伟小说中的普通人正在驱散悲观的阴霾,见到乐观的阳光,也能感知人物形象塑造的不断深化。
先锋派小说通常对“傻瓜”形象颇有心得。《越野赛跑》中的小荷花就是这样的人物。她略有些智障,“人性”则相当完整美好,才有可能和冯步年一样变成“马”。到了《南方》,就成了男人杜天宝。他没有变成“马”,却作为弱者真实顽强地生活着。他是永城西门街有名的“傻瓜”,和西门街最放浪的女人杨美丽的两个女儿罗忆苦、罗思甜一起长大。这两个女孩后来也成为这一带的风流女性,搅出了许许多多悲欢离合的故事。所有人都变了,只有杜天宝还是一个“傻瓜”。他一直都是两姐妹的异性知己和避风港。罗思甜未婚怀孕,就躲在他家里。罗思甜儿子被放到桶里漂走了,是他带着沿江寻找。他每天用三轮车送罗忆苦上班,任劳任怨。罗忆苦受对象肖俊杰欺负,杜天宝愤怒地把肖俊杰的一只耳朵咬下来,自己去坐牢不后悔。他其实是一个有特殊禀赋的人。抓苍蝇有一手绝活,而且,在服刑三年里就学成了一名优秀的小偷。人们利用他的傻劲,利用他的绝技去干各种好事,也干各种坏事。可他永远傻傻面对人生,无怨无悔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他的婚姻生活也非常怪异。老婆比他还傻,一辈子傻笑。他们俩生下的女儿则聪明伶俐,长大后也是个美人。谁也没有想到,多年以后,这个傻瓜的女儿与罗思甜失踪的儿子恋爱,书写了西门街一段美丽的爱情童话。作品没有深度挖掘杜天宝的个性,却写出了杜天宝善良仁义的人性。在那个非人的年代,在那个人心险恶、道德沦丧的西门街,杜天宝象征着暖意、亮色、信任、诗意、美好。作品通过这个有点“钟楼怪人”品质的人物,表明了作家批判现实的鲜明态度,也赞美了普通人的人性,突出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品质。
《镜中》的主人公庄润生是个新人物。艾伟的长篇小说第一次把笔触伸入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描写社会精英的生活,就塑造出一个有新意的人物形象。艾伟说:“我愿意把这部小说当作我写给杭州的一首赞美诗。”实际上,当庄润生形象完成后,读者会发现,作者是对一座精英之城的反思。
主人公庄润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著名建筑设计家。他财富自由,有美丽的妻子、有可爱的孩子,还有情人,过着时尚精致的而又超然脱俗的佛系生活,是时代的宠儿。他的设计代表作飞来寺禅院正是他现代时尚理念和宗教意识融为一体的产物。他对记者说,我研习佛经,思考生命,想做成一座经由生命矛盾性抵达信仰的建筑,让禅院不仅仅是禅院本身,而是我们心中的那道光。这是一段相当标准的东西方文化混搭的精英话语,透着他不知天高地厚的优越感。如果不是突然的家庭变故,他应该很顺利地接受日本山口洋子“原爆道场”的设计委托。然而,这场变故的持续效应迫使他深入经受战争和生活苦难的老百姓生活,看清了人生的真相,迫使他终于有时间反思他长期以来不真实的虚幻精英生活,认清了他自己在时代繁华奢迷的物质基础上形成的“佛系”思想和时尚理念的浅薄,最终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他来到仰光,在佛塔前,才知道什么是宗教佛学,才找到“那道光”。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有接受“原爆道场”的勇气和信心。而他的设计思想,虽然还有待于付诸实施,但整个思想倾向和内涵,已经远远高出他一直引以为豪的飞来寺禅院。
此前,庄润生这个形象,在艾伟的长篇小说中,从未出现过。在中国当代小说中,这样的人物也极为鲜见。作品真实反映了中国精英群体的现状,深刻揭示了精英生活的内在矛盾,体现出道德批判的现实主义精神,突出了作品的思想主题。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将在以后的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进程中,接受更多的检验,得到更有力的证实。
四
艾伟小说的女性形象很值得一说。
《越野赛跑》中的小荷花,虽然不是现实主义小说人物,却有着突出的传奇色彩。她因为与表兄一起到水库时游过泳,为“我们村庄”的人所不齿。因为脑子不太灵光,所以这些人格污辱并不会造成她多大的痛苦,阻碍她继续和男人打情骂俏。她被投机分子冯步青抛弃后,与“马人”冯步年结成了患难夫妻,一起到天柱山中,过起无忧无虑的好日子。冯步年也因此不用变为马,可以直立走路了。然而后来小荷花却变得更傻了,冯步年不得不关掉生意,背着她到处求医,仍不见好。这回轮到她变成了一匹马,关在笼子里。这个女性形象颇有些象征意义:人性历经磨难,不泯不灭。她在过去的苦难岁月中还能找到一块净土,而当资本过度膨胀的时候,她只能被关在笼子里。在这里,作家的批判态度非常鲜明。
另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人物,则是《南方》中的女主人公罗忆苦。这个“艾思米拉达”式的女性打破了平庸无奇的西门街世俗生活的平静,挑战式地把世俗男女间传统的偷情苟且变为爱恨情仇的浪漫传奇。她先是和夏小恽谈恋爱,却选择了与公安局政委之子肖俊杰结婚,打发妹妹罗思甜去爱夏小恽。她并不爱肖俊杰,所以有意无意和须南国保持了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导致肖俊杰因为吃醋枪杀了须南国之妻。结果是公安局政委肖长春不得不批准儿子的死刑。从此,这个权势之家支离破碎。后来她又与从监狱出来的夏小恽恢复了情感关系,两人一起闯广东,到处行骗,居然骗了旧情人须南国两万救儿子命的钱。夏小恽发现了当年婴儿漂流事件的真相,愤恨离开了她。而她回到永城后,被须南国跟踪杀害,扔进护城河里。这个人物内涵相当复杂,折射出当时社会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无序与混乱状态,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作者对社会矛盾现实一度困惑茫然。
实际上,《爱人同志》女主人公的张小影,《爱人有罪》的女主人公俞智丽更接现实生活的地气。她们身上已经少有传奇性,而多了许多普通人的烟火气。因此,她们与现实关系所体现的人性冲突更具有现实主义的思想内涵。张小影本是一个纯朴的姑娘,崇拜“英雄”因而违背家长的意愿嫁给了刘亚军。在不断做报告的过程中,自己也萌生起英雄的“情结”。不知不觉,报告的内容不是在讲“英雄”故事,而是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英雄”已不是主角,她才是主角,是牺牲自己的“圣母”。更为扭曲的是,她乐此不疲叙述着故事,跟着宣传的功利需要,不断修正,不断调整,已经与他们家庭生活的真实状况越来越远,越来越显现出虚假编造的本质。而这个时候的张小影也由纯朴的姑娘渐渐变成了谎话的制造者,也成了这个普通人家庭悲剧的无形的推动者。作品由此写出了普通人生活潜在的危机,进而揭示了人性与现实那种脆弱的关系。俞智丽内心的冲突性显然比张小影更为强烈,也更受折磨。因为,她是当事人,知道“强奸”的真相,又没有站出来说明真相,导致了鲁建的冤案。虽然生活平淡无奇,其实她内心一直存在罪恶感。鲁建的复仇反而激活了她内心的良知,才促使她和鲁建发生感情,痛下决心打破现有家庭和稳定的世俗生活,去抚平鲁建的伤痛。这种善恶交织的矛盾冲突,奠定了俞智丽的性格基调。当她保持恶的时候,一定会遭受鲁建强烈的复仇,生活悲剧一定发生;当她变为善的时候,就得接受道德的惩罚,性格悲剧就产生了。而俞智丽选择了后者,让这个性格的悲剧焕发出“人性”“自我”的光辉。俞智丽形象典型表现出现实主义文学的“人性”的深刻内涵,也多少暴露了现实主义“善恶”道德冲突观存在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
毫无疑问,艾伟女性形象塑造得最好的是《风和日丽》的女主人公杨小翼。她最初的朴素动机也许就是“寻父”,弄清自己的身世。正赶上新中国历史发展处于最动荡、最复杂,矛盾冲突最激化的时期,接受历史学系统教育的她,其实很自然会把“寻父”加入探索历史问题的因素,或者,提升到一种理性的高度看待与父亲的关系。她的这种历史观,并不是完全靠读书做学问来实现的,而是亲身参加历史运动,接受历史力量的冲击以及个人命运沉浮中获得的。应该说,四川军工厂生活是她思想积淀、性格打造的一个非常重要时期。从这里回到北京的杨小翼,经历了生活的严酷的洗礼,浑身都是伤痕,但她没有沉湎于历史的伤痛,而是很快走出了生活的阴影。她和伍思岷的分手正是她走向新的生活的开始,也是她与思想解放时代共鸣的开始。正是在这样一个实际上比新中国任何时代更复杂更矛盾的年代,杨小翼才更深刻地意识到,父女相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身上所承载的历史。所以她拒绝了再次去见将军,却热心寻找父亲当年的足迹,认真写出了研究将军经历的具有学术价值的历史学论文。
《风和日丽》的写作年代,正是社会上历史虚无主义比较盛行的时期,文学创作中的虚无主义倾向也不鲜见。有意思的是,杨小翼并不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更不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她完全有可能和许多人一样,把历史虚无化、碎片化、解构化,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她个人选择了放弃“寻父”,却承认了父亲的历史并自觉捍卫“父亲”的历史,正确地认识把握个人命运与历史伟力的理性关系,更加深刻地阐释历史,与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形成自己独有的历史批判态度。这个女性人物形象内涵的历史精神,使之站到了时代思想的制高点,也使人物形象的现实主义思想品格超越了艾伟笔下的所有女性形象,从而开阔了作品的视野、拓展了作品的格局,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五
受过现代派文学熏陶过的作家,作品几乎都会染上一些悲观主义颜色。艾伟也是这样。他会在一些看上去对死亡、暴力、恐怖场景敏感细腻的描写中,隐隐约约表达这种情绪。比如《爱人同志》中对齐亚军躲藏的密不透风的黑屋子的描写,《爱人有罪》中对俞智丽闻到死亡味道的描写,更为典型的是《南方》中对火葬场、《镜中》对车祸惨状和殡仪馆氛围入木三分的描写。
事实上,类似的描写大量存在。把它们集合在一起,不难看出,作家的情绪,不仅悲观,而且流淌一种悲悯之情。是命运无常,抑或生命脆弱?是历史无情,抑或人性无力?是世界之大,抑或人之渺小?是世纪末情绪的延续,抑或对人类前景的怀疑?很多时候,这些情绪会化为作品的叙事基调与情怀。贺绍俊认为艾伟是一个“温情的怀疑主义者”,悲观情感与怀疑情感在作品里总是连在一起,很难分清彼此。不过,如果说,艾伟以往的长篇小说包括《风和日丽》的诗意还来自宿命感、忧郁感的话,那么在《镜中》这部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里,不再来自个人的感伤,而是来自对真实世界历史变迁的忧患。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
本文注释内容略
扫码在手机上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