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欧亚草原乌拉尔南部牧民所培育的DOM2马种,加速了驯马术、马车和骑马术由乌拉尔山脉向东西方的传播和普及。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由欧亚草原东部南下的族群活动于今中国北方地区并与北方列国发生接触。随着公元前5世纪巴泽雷克文化兴起,中国北疆地区与骑马族群有了贸易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及至公元前4世纪末以赵国为代表的华夏诸国开始正视新的军事格局,一改前期忽视骑兵的传统而进行“胡服骑射”之类的军事改革。骑射技术的普及加速了交通路线的开拓以及列国深入边疆地域的进度,为国家和文化的统一奠定了必要基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骑马术向中国的传播是中华文明多元汇聚、兼收并蓄、开放交流的一个重要例证。
关键词:骑马术;阿尔然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巴泽雷克文化;;胡服骑射
作者黎婉欣,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北京100871)。

骑马术(horse-riding)的出现极大改变了古代社会的发展轨迹,是促进人类历史多种文明交流十分重要的因素。通过骑马,古代族群迅速地向外扩张,打通了陆路交通,接触并获得了日常活动范围以外的资源,扩展疆域与自己的军事势力范围。骑马术也使各族群与邻近社会接触的机会增加了,各种贸易商旅开始出现,因争夺疆土而出现的军事冲突亦随之变得愈加频繁。公元前4世纪末,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是中国史上极其重要的军事改革举措。从近年的考古发现及典籍记载可知,在赵国推行这一军事改革之前,骑马术即已零星出现于中国北方、东北等与草原文化密切接触的区域。有关骑马术在欧亚草原的流行及其向中国传播的问题,学术界过去虽曾有过研究,但不够深入,而近年来国外学者对于骑马术起源的广泛讨论亦尚未在国内得到相应关注。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考证欧亚草原东西两大区域与骑马术起源相关的考古遗存资料,对骑马术在欧亚草原起源、发展及其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兴起的路径与缘由作进一步探讨。
一、驯马术和骑马术在欧亚草原中西部的起源
(一)公元前四千纪至前两千纪间的马匹驯化
近年来,欧亚草原中西部地区的多处遗址中均发现了马的骸骨,学术界对驯马术和骑马术的起源问题十分关注。哈萨克斯坦草原北部的博泰(Botai)遗址(约前3700—前3100)所发现的动物骸骨逾30万块,马骨占其中90%,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马骨堆积。学者桑德拉·奥尔森(Sandra Olsen)、阿伦·乌特勒姆(Alan Outram)、大卫·安东尼(David Anthony)分别通过骨骼鉴定、陶器残留物分析和马牙微痕分析等方法,认为博泰牧民已开始畜马且有可能已驯马和骑马。然而,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对以上观点持保留甚至相反意见,玛莎·莱文(Marsha Levine)、威廉·泰勒(William Taylor)、尼古拉·勃克温克(Nikolai A. Bokovenko)、 皮塔·凯勒娜(Pita Kelekna) 等人分别从博泰马骨形态分析、马牙微痕分析、历史学与民族学等角度对“骑马早起说”提出质疑, 认为骑马术甚至家马于公元前三千纪以前皆尚未出现, 他们的意见相对来说比较严谨。
马的移动能力强且速度快,有了马的协助,人类的畜牧规模(亦即所能放养的牛或羊的数量)必然会有所扩大,聚落的大小、位置以及聚落间的距离也都会随之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位于乌拉尔山脉西麓的阿巴舍沃文化(Abashevo Culture,约前2300—前1850)遗址多位于森林和草原的交错地带,分布范围明显较前期的颜那亚文化(Yamnaya Culture,约前3500—前2600)广阔。阿巴舍沃聚落遗址中所发现马骨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并发现了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圆饼形骨马镳。这些发现说明家马培育较有可能出现于公元前三千纪中叶至末叶之间。考古学家诺伯特·贝内克(Norbert Benecke)曾分析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发现的与阿巴舍沃文化年代相当的马骨,发现青铜时代中期(约前2600—前1900)的马在体型上明显较前期小,估计曾经过人工培育。贝内克由此推断家马的驯化大约始于公元前2600年,而骑马习俗的出现估计不会早于公元前2500年。这项发现十分重要,与以上阿巴舍沃文化所揭示的信息以及近年早期家马DNA分析数据所见的分析结果都十分吻合,也应是骑马术于欧亚草原最早出现的可靠证据。
(二)辛塔什塔文化遗址的车马葬与DOM2马种的传播
位于乌拉尔山脉南麓的辛塔什塔文化 (Sintashta Culture,约前2050—前1850)遗址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该遗址出土了目前所见最早的马车,墓葬中随葬的马匹数量也很多。 驯马术于此时已发展成熟, 但迄今尚未于辛塔什塔文化遗址中发现与骑马术直接相关的材料。
2021年10月,法国和俄罗斯的古DNA研究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有关辛塔什塔家马的重要发现,为研究骑马术起源提供了十分有用的线索。这个团队对比了283组古代马骨的DNA样本,将其分为4组,其中以第4组的年代最晚(前2200年以后),与现代家马接近,二者同样拥有DOM2基因,亦即具备能负重、有耐力、能适应压力等特征。辛塔什塔文化的家马几乎都属于DOM2马,也是第4组研究样本中年代最早的;DOM2马种在当时应有较明显的优越性,很快便零星出现于今土耳其、摩尔多瓦和捷克等地并随即取代了各地的马种。因此, 这个研究团队推断现代家马源自辛塔什塔文化所在地区,亦即乌拉尔山脉南麓,估计带DOM2基因的马种是由当地牧民于公元前2200年前后成功培育出来的。参与这项研究的学者也论及,目前虽仍没有关于骑马术出现的直接证据,但辛塔什塔的DOM2马同时拥有稳定情绪的ZEPMI基因和扺抗脊骨疼痛的GSDMC基因,这表明它们具备被用于骑乘的条件。这项重要研究成果明确了辛塔什塔文化的家马与后世家马的传承关系,进一步肯定了马以及驾马术是从欧亚草原中部分别向东、西方向传播的认识。骑马习俗兴起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即牧民从草原往外地运马,通常会以骑乘头马、让其余马匹跟随的方式进行,因此,在公元前两千纪末,骑马术很有可能已伴随着DOM2马匹贸易而出现。
有必要提及的是,俄罗斯考古团队于2020年在乌拉尔山脉东沿、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利萨科夫斯克城(Lisakovsk)东北16公里外发现了新伊利因斯基2号墓冢(Novoil’invskiy 2 cemetery),其碳14年代是公元前1890年—前1774年。冢内的殉牲坑内埋有两匹高龄马,一公(18—20岁)一母(16—18岁),均是E. callabus家马,属于DOM2马种。这项发现反映了DOM2马向东传播的现象,而两匹马的年龄和从骨骼所反映的健康状况也说明当时的牧民已掌握了较好的养马技术。此外,发掘者还着重指出这两匹马的牙出现了非自然磨损,马的腰椎骨骼也有病变特征,故有可能是用于骑乘的马。
在欧亚草原地区发现的有关马的考古材料十分零散,且地域跨度很大。马车发展较骑马术早,但牧民在驯马时使用骑行的方式控制马也是有可能的。驯马术和骑马术在欧亚草原地区出现的年代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差距不太大。事实上,两河流域地区于此时已出现了一些骑马图像,可证草原地区的牧民在这个时期已经流行骑马了。
(三)马匹传入西亚的过程与骑马术、骑兵的出现
在苏美尔时期的滚筒泥章上曾发现目前确知年代最早的骑马图像, 骑手身材瘦长,单手执鞭,技术熟练,据其上的楔形文字可知其为公元前2030年的遗物。 大英博物馆所藏陶模板(22958)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800年,属于古巴比伦时期。陶模板上的男童只穿短裤、短靴,策骑动作娴熟,但马头的比例十分不协调,显示出巴比伦地区的陶工已见到了骑马,但并不熟悉马这种外来的动物的特征,而骑马的男童也很有可能并不是西亚本地人。
骑马现象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以后逐渐出现于西亚地区。在古赫梯文书中首次称骑手为pithallu,其原意为“通讯员”,应与早期骑马人的身份有关。大英博物馆藏的古埃及青铜木柄斧(EA36766)据传发现于底比斯神庙遗址(约前1550—前1295)。铜斧上的透雕骑马图,图案线条简单,骑手单手执缰,策马奔驰。埃及学家一般认为这是在描绘神庙人员或使者。综合上述材料可见,骑马术于公元前两千纪上半叶已零星出现于西亚和埃及等地,但仍未得到普及。
赫梯王都哈图沙(Hattusa)遗址位于今土耳其波格兹卡雷城,遗址中发现的楔形文字泥板包括一份珍贵的养马文书,详细记录了养马和驯马的技巧。这部养马文书,由自称来自米坦尼的驯马人吉古里口述并由赫梯书吏笔录而成。彼得·劳文(Peter Raulwing)考证养马文书中的词源,指出其中关于驯马场、马毛发颜色等的专业名词都是直接采自吉古里所说方言, 属古印度—雅利安语系。劳文又发现这份文书虽写成于新赫梯王国时期(约前1400—前1190),但由于它使用了较为古老的字形和用语,可知它只是抄本,其原稿的年代至迟可追溯至公元前15世纪的中赫梯王国时期(约前1500—前1400),亦即与上述骑马图像的年代相当。这项发现说明,西亚文明在引入马、马车甚至是骑马术的初期也曾伴随着部分有草原文化背景族群的迁入。
东欧大草原位于今黑海、里海以北,南行穿过两海之间的高加索地区便抵两河流域。马匹由高加索地区向南传播主要可循东西两条路线,西线是沿托罗斯山脉进入赫梯所在的安纳托尼亚,也即养马文书所流传的区域;东线则是沿西北至东南走向的扎格罗斯山脉南下,经过米坦尼及其以东的伊朗高原。骑马术的发展与骑兵的出现应在这些地区寻找遗存。
乌拉尔图(Urartu)是亚述文献中经常提及的北方族群,其疆域曾一度从土耳其东部的凡湖(The Van Lake)往北延伸至今亚美尼亚一带,占据着西亚前往草原地区的交通要道,这片地带也是十分重要的马匹养殖场地。乌拉尔图最早见于亚述王萨尔玛那萨尔一世(King Shalmaneser Ⅰ,前1274—前1245年在位)时期的文书中,是亚述的马匹供应源之一。至公元前9世纪中叶,乌拉尔图势力突起,建立了王国,经常与亚述交战。有关骑马的材料也于同时期大量出现,乌拉尔图的三环钮青铜马镳是当时十分先进的设计,其形制方便于骑者通过缰绳前后摆动,以向马传递指令。马具的优化与马上作战技术应该是同步发展的,下文讨论的阿尔然1号墓冢的年代与乌拉尔图王国相当,同样出现了优化马具的过程,反映出骑马和骑兵战术在这个时期已流行于整个欧亚草原地区。据同时期的西亚文献记载,乌拉尔图王曼努亚(Menua,约前810—前785年在位)曾调配9174名骑兵与1600辆战车迎战亚述军队,反映出乌拉尔图的军队拥有大量的马,骑兵的设置也较亚述军队优越。
亚述皇宫中的浮雕壁画有不少早期骑兵的图像,其中一幅描绘了被亚述军队追赶的乌拉尔图骑手(大英博物馆118905)。亚述的出土文献中亦曾多次提到亚述军俘虏乌拉尔图、叙利亚等地的马和骑手回国的事迹,有学者推测亚述的这些举措既是为了削弱对方军力,也有可能是因为亚述需要他们的马甚至骑马术以提升自身骑兵的战斗力。不过,骑兵这种兵种虽在公元前9世纪间已出现在亚述军队,但一直未成为军中的主力。直到公元前7世纪亚述巴尼拔三世(King Ashurbanipal Ⅲ,前669—前631年在位)登基并向外大规模扩张时,亚述王首次在壁画(大英博物馆124877)上展示自己在马上使用长矛和拉弓的雄姿,骑兵自此才在西亚受到高度重视。亚述帝国虽然很早已接触骑马,但前后经历了至少两百年才将骑兵大规模地纳入常规的军制。吸收过程之长应不仅是因为西亚人歧视骑马这项活动,更与马匹供应量和骑手、骑术的发展有限的情况有关。
关于骑马术的问题,必须关注伊朗高原北部的卢里斯坦(Luristan)文化。该文化围绕今伊朗哈桑鲁丘(Teppe Hasanlu)地区发展,活跃于公元前9世纪—前7世纪之间,与乌拉尔图王国的发展年代相近。卢里斯坦青铜器主要都是兵器、车器、马具和宗教用器,其中以骑手为造型的马镳(大英博物馆134927)是其经典设计,反映出骑手在这个区域的重要性。哈佛大学博物馆藏的卢里斯坦马衔(1992256125)采用“一”字形设计,两端往上下方向卷曲,这种形制未曾见于其他地区,有可能是为了方便骑手单手拉动缰绳以增加摆动幅度的动作而设计的。研究骑马术起源的学者布莱恩·斯科特(Brian Scott)曾指出,马匹的高度一般是马衔长度的10倍。卢里斯坦的马衔是同类型器物中较大者,上述哈佛大学博物馆藏的卢里斯坦马衔总长208厘米,如扣除两侧马镳的宽度,约可得18厘米,适合高约16—18米的马匹使用。这种马即使在今天也是体型较大的马种,可见当时的卢里斯坦牧民已有着十分先进的养马技术,成功培育出体型较大而适用于骑乘的马匹。
综上所述可知,乌拉尔图和卢里斯坦等地早期骑马民族既熟悉农耕社会的需求,又有熟练的畜牧技巧,他们曾有效地提高马的产量,使之更能适应西亚地区的生存环境。这些族群在供应马、传播骑马术和骑射战术等方面都曾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新亚述帝国以及后来的新巴比伦帝国之所以能建立起强大的骑兵军团,在很大程度上是间接受益于这些位于草原腹地和两河流域之间的王国。
二、公元前两千纪间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骑马术遗存
(一)卡拉苏克文化的兴起与马匹东向的传播路径
从乌拉尔山脉往东行,通过哈萨克斯坦北部广阔的草原地带,溯额尔齐斯河而上,即可通过西西伯利亚进入阿尔泰山脉地区,抵达今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四国的边境接壤处。受内陆性气候影响,欧亚草原东部的草木资源远不如中、西部地区丰富,该地区的青铜社会发展步伐亦略晚于西部地区。
卡拉苏克文化起源于公元前14世纪的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至今虽未见马车的遗迹,但库尔根纳(Kyurghenner)、贝斯卡娅(Beyskaya)和拜诺夫斯克(Bainovsk)等墓冢已出土多件男性墓主佩于腰间的弓形器,表明马车在该文化中已相当重要。克雷斯特-卡亚 (Krest-Khaja) 遗址曾出土一块绘有骑马人图案的墓石,同遗址中亦发现有三孔骨质镳。由于卡拉苏克文化式的弓形器、环首削刀、蘑菇形首短剑和三凸钮环首短剑也曾见于蒙古外贝加尔地区、商后期的晋西与陕东北山地以及辽东地区,所以可以肯定卡拉苏克文化的驾马传统和铸造工艺在欧亚草原东部有着一定影响力。
卡拉苏克文化的年代延续至约公元前9世纪,与已确切出现骑马遗存的阿尔然文化年代相接,可以推断卡拉苏克文化除了使用马车并曾推动周边地区使用马车外,也应曾推动了骑马术在蒙古高原的发展与东传。埃斯特·雅各布森特普弗(Esther JacobsonTepfer)观察到在阿尔泰山脉地区于公元前一千纪前后始见执弓箭的骑手追逐动物的岩画,生动地展现了骑马、打猎和放牧的场景。 自骑马流行以后,岩画也改变了前期呆板的描绘风格。
(二)蒙古的积石冢文化、石板墓文化提供的骑马信息
蒙古地区对于探讨马匹传入中国的路线十分重要。迄今已先后有多个国际考古团队在蒙古西北部的乌布苏省(Uvs)、北部的库苏古尔省(Khovsgol)和后杭爱省(Arkhangi)进行调查和发掘,确认了上述地区于公元前两千纪初已开始饲养马匹。蒙古中北部地区发现的岩画也证实了卡拉苏克文化马车的东传,而传入的时间在分布于此地域的积石冢文化(Deer Stone-Khirigsuur Culture,约前15世纪—约前8世纪)年代区间。 弗朗西斯·阿拉德(Francis Allard)团队在呼尼河谷发掘的Urt Balagyn积石冢群年代属于公元前一千纪上半叶,曾发现马头多达1700个,均向东整齐排列,应属于积石冢文化一种祭祀活动的遗存。但该文化目前仍未发现高级别的墓葬。
关于积石冢文化是否已发展出骑马术的问题,马修·福卡(Matthew Fuka)曾试图从人骨遗存中找证据。他分析了蒙古国家博物馆藏的53副积石冢文化人骨上所见的病理特征,发现男性的左肩、左肘和盆骨有较明显的骨质病变,说明身体的左侧经常发力、胯部长期受压,他认为这些特征很有可能是由无鞍具骑乘的身体动作所致。 威廉·泰勒也通过对考古出土的积石冢文化的马骨、人牙进行检测,认为蒙古地区在约公元前1300年已流行骑马。他提出的证据包括:第一,通过对人牙进行的蛋白分析,发现蒙古中北部地区青铜时代晚期的牧民已普遍不再食用马肉,这反映出马在当地被赋予了新的社会功能。第二,马鼻梁骨的中脊多出现突沿或一定程度的骨硬化,上颚前臼齿也有明显磨损,应是马匹长期服劳役所致。第三,部分马骨鼻腔向左倾斜,疑是骑手习惯用左手牵拉马缰所留下来的迹象,而且马匹的蹄足普遍增厚,反映出其行动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第四,积石冢文化的覆盖范围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出现较大规模的扩张,这一变化应与骑马术的出现有关。
泰勒推算的骑马术出现于蒙古的年代实际上是参考了安阳殷墟遗址(约前14世纪—前11世纪中叶)出土马车的年代。但即使如此,泰勒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仍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尤其是他尝试测算缰绳的拉力和角度并据此区分驾马和骑马的动作,又观察到用于驾车的马一般在肩骨与前肢上都会留下较为明显的劳损等情况。这些发现都可能成为日后研究中国境内商周遗址中所发现马骨的重要借鉴。
蒙古中南部、东部地区属于石板墓文化(约前1100—前400/300)范围,其分布向南延伸至中国内蒙古北部。自2009年起,宫本一夫团队分别在属于特布希文化(Tevsh Culture,约前1400—前1000)的特布希、勃鲁敖包(Bor Ovoo)和哈尔哈拉其(Khyar Kharaach)三处墓冢进行发掘,重点分析人骨病理特征,尝试找出骑马所留下的痕迹。宫本团队的发现是,特布希M1女墓主的锁骨、肋骨均有骨折愈合的痕迹;M3男墓主高171厘米,鼻骨、左前臂均有骨折愈合痕迹,下胸椎有骨变,其上肢发达,右大腿骨内侧的肌腱附着位点明显,这些现象可能与骑马、拉弓等动作有关。勃鲁敖包M13女墓主约20岁,左锁骨曾有骨折,右上臂肌肉发达,盆骨、右大腿骨内侧也有明显的肌腱附着位点,小腿胫骨近脚踝处弯张,似有长期骑马的习惯。哈尔哈拉其M20男墓主约40岁,身高164厘米,鼻骨曾有骨折,右肱骨、右前臂和右大腿骨的肌腱附着位点明显,颈椎至腰椎间有不同程度的变形与损伤。以上三处遗址同位于阿尔泰山脉地带,碳14年代均是公元前14世纪初至前13世纪中叶。宫本团队指出,上述各墓主骸骨上发现的创伤多是由高处坠下的意外造成,有可能与驾马甚至是骑马有关。
国外的体质人类学者十分关心骑马活动在人骨上相关部位所留下的痕迹,曾指出大腿骨、脚踝和髋骨臼的形态以及人骨损伤的位置等都有助于判断墓主有无骑马的习惯, 只是目前仍无法严格区分这些痕迹是由肢体冲突、意外、劳损还是由骑马所留下的。宫本团队的工作为石板墓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线索,尤其是发现了女性也有类似的骨折和损伤,目前虽仍似难以为骑马术流行与否立下确切的定论, 但上述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多可以借鉴。假如能对中国内蒙古地区甚至是安阳殷墟遗址所发现的人骸骨与马骨进行同类型的研究,或能有更多新的启示。
(三)商王国后期马的使用与骑马活动的有无
在商后期以前,即公元前三千纪至前两千纪中叶,家马曾零星出现于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宁夏隆德县沙塘北塬齐家文化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和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等。这些遗址的家马数量极少,且有与野马骨骼同时出土的例子,国内基因检测团队研究结果证明这个时候的家马未必是本地培育的牲畜,很可能是从草原地区引入的。在商前期的遗址中(如郑州商城遗址等)并没有发现有关用马或马车的遗存。及至商后期即殷墟文化时期,情况发生重大改变,马已大量输入中国北方甚至中原地区。这种现象首先与气候因素有关,“商代晚期已进入全新世大暖期的最后阶段,气候开始向干冷化转变”,为华北地区引入马匹与牧马技术创造了有利的自然条件。 殷墟西北冈大墓M1001号属于殷墟文化二期早段,在墓坑东南角尚存有马车舆底及其铜饰件。 小屯北地乙七基址南边的M20、M40也已见年代较早的车马坑, 亦属于殷墟文化二期早段,由此可以推断商人自迁都于安阳后即开始使用马车。马车与马的引进应与约自商前期末叶至商后期偏早时期商王国和北方族群的冲突、交流有关。大量卜辞记载了商王武丁时期北方族群曾东进、南下,商王朝西土与北土区域受到多重骚扰的情形。在此之后,商王国通过军事行动将西疆拓展至今山西晋中盆地、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与聚居于晋西和陕东北高原以及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北方族群形成军事上对峙的局面。自此,殷墟甲骨卜辞中便也记载了有关商王养马、要求下属贡纳马、使用双轮幅式马车等内容。马匹贸易与育马的技能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乃至贸易交流而传入。由于青海、甘肃等地尚未发现商时期的马匹、马车,似乎可以排除其从新疆进入中原的可能性。马与驾马术应是从今蒙古、内蒙古地区传入中原地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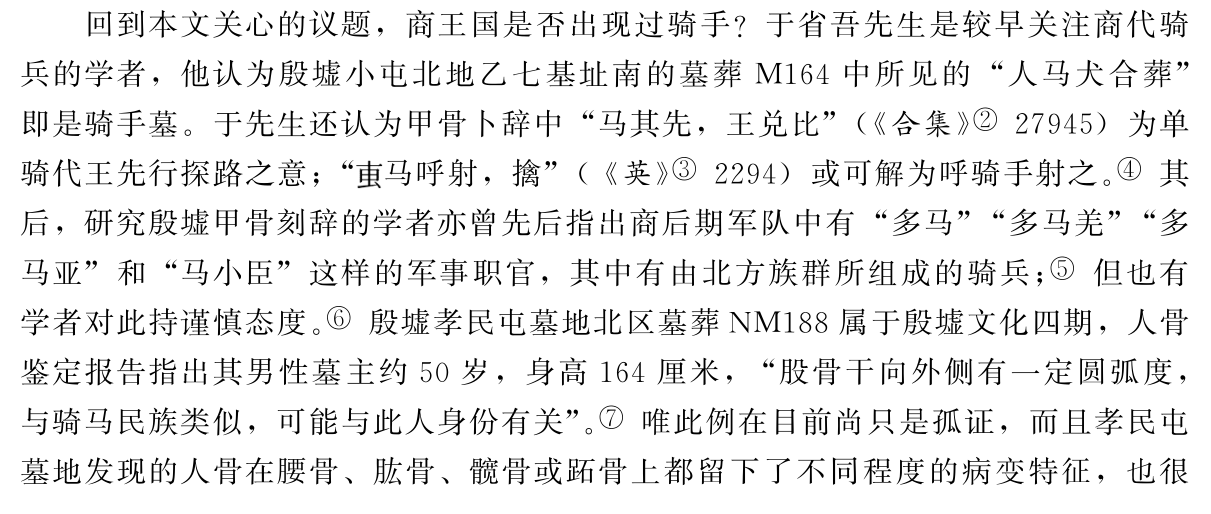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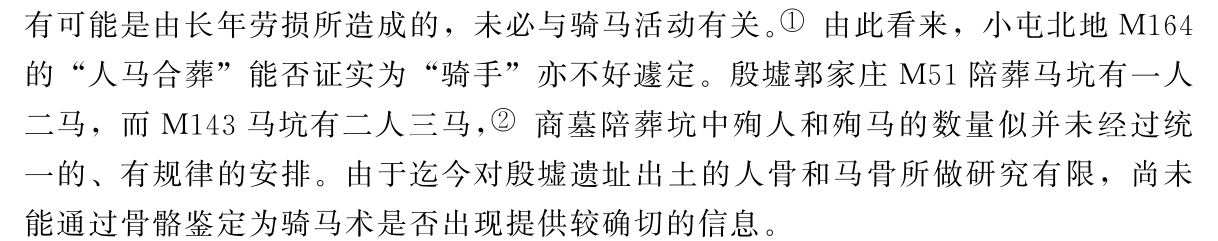
但是,在殷墟发现的车马坑内随葬的驭者、杀殉(或杀祭)坑内的死者,常同时随葬有北方式的兵器和工具,联系上引卜辞所见的“多马羌”,可以认为有草原背景的北方族群应曾参与商后期的军事活动,并为商人贵族养马和驭车。事实上,养马和驯马需要十分丰富的牧马经验和技巧,商王朝于后期才使用马,必然需要北方族群协助养马、驯马、管理马和驾马车,这一点与赫梯养马文书上所反映的情况应是一致的。武丁时期卜辞中提及“获羌刍五十”(《合集》32043),又有要求下属贡纳“刍”、追捕逃脱了的“刍”等记载,“刍”应是为商人贵族服务的来自北方族群的牧人(相关卜辞参见《合集》93正、94正、136正)。商王国从北方族群引入的有养马技术的人群应当会利用骑马的方式为商人放牧马,但是骑马术显然并没有被商王与商人贵族重视并大力发展。
三、骑马术传入中国的时间与可能的路径
(一)斯基泰文化兴起与骑马术在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发展
进入公元前一千纪后,欧亚草原东西各地出现多个大型墓冢,出土被学术界称为“草原文化三要素”的马具、兵器和动物形饰件,成为极具特色的文化特征,学术界常统称这些墓冢为斯基泰文化遗存。斯基泰(Scythia)一词源自古希腊语,含有“牧民”的意思。斯基泰人于公元前9世纪至前2世纪活跃于今黑海、咸海北部至阿尔泰山山脉和外贝加尔湖地区,生产生活方式是养马、骑马与放牧。在欧亚草原东部发现的阿尔然墓冢群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斯基泰文化墓冢,它们的发现确立了游牧文化出现的年代。
阿尔然墓冢群位于今图瓦共和国境内的乌尤克河谷(Uyuk Valley),经遥感勘探可知河谷内共有大小墓冢约150座。20世纪70年代格里亚兹诺夫(M. P. Gryaznov)发掘的阿尔然1号墓,属于公元前9世纪至前8世纪间,墓堆直径120米,覆盖由松科树干堆叠而成的弧形木建筑。树干围绕着正中央的方形“主墓室”辐射铺开,形成多个不规则的梯形陪葬室,随葬了不同数量的殉人和殉马,但头骨皆向着主墓室,布局严谨。主墓室内发现8名配有短剑和箭镞的青年男性以及6匹公马骸骨。出土殉马最多的是3号陪葬室和2号陪葬室,各有马30匹和殉人若干。全墓共出土马160匹,皆配备马具。对殉葬的马所做的毛发分析数据显示,这些马应有不同产地。发掘者特别指出,各墓室出土的马镳、马衔彼此间形制皆不同,反映出各个牧马群体都有着独立的马具铸造坊。格里亚兹诺夫认为,带有“马镫形”外环的马衔和带小蘑菇头顶的三孔镳是阿尔然本地铸造的,其余如直杆三孔镳、野猪獠牙镳、圆形外环马镳等都应是阿尔然周边的游牧部落在献送陪葬品时被带到出土地点的。这些发现说明当时的阿尔泰—萨彦山脉地区散居着多个彼此有联络的游牧群体,他们通过军事、祭祀等活动已联结成一个较大的政治集团。综合以上情况,基本可以肯定阿尔然地区已出现有相当规模和政治组织能力的游牧王国,且阿尔然1号墓主已拥有十分精良的骑兵部队。
约翰·辛普森(St John Simpson)曾指出,马衔的形制对于骑马术十分重要,必须具备轻巧、灵活和适应马的骨骼结构这三个条件,马衔与马镳配合而产生的摆动幅度能影响到马的灵敏度。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间,欧亚草原东部各地出土的马衔形制之不同,反映出这个时段内草原上各个马具铸造坊,包括前述乌拉尔图、卢里斯坦文化在内,都在钻研和优化马衔的设计。阿尔然1号墓出土的马衔外环呈“马镫形”,沿用时间长,应属于比较成功的设计,周边地区出土了不少仿效的这种设计的马衔。阿尔泰共和国艾里塔什1号(AyryTash1)墓冢内近年发现了一座属于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的石板墓,为目前所知年代较早、最为完整的一人一骑“骑手墓”。墓主屈肢左卧,头向西,脚边随葬骨质箭镞,而其身后的马仍套着阿尔然式的马衔,马背上发现了疑为鞍布的痕迹。马埋于墓主身后较高的台面上,正对着墓主。这是后世草原民族埋葬骑手及其坐骑的常用葬式。
1998年德俄考古团队发现了阿尔然2号墓冢,墓堆直径约100米,残高2米,年代为公元前7世纪中叶。 2号墓冢规模较小但未曾被盗,出土黄金饰件共5600件,几乎全是墓主衣服、兵器和马具上的配饰,以马、鹿、羊和鸟的造型为主。2号陪葬坑内的是男墓主的坐骑,墓冢内另有埋葬了14匹公马的马坑,经鉴定这些马应是来自10个不同的产地。马头骨出土时仍佩戴着马镳和马衔,其中12副应是由同一块模具所铸造的。 这种弧形马镳与带方形外环的马衔较阿尔然1号墓冢中所见的更为先进。2号墓冢的发现显示出阿尔然王国在公元前7世纪仍控制着南西伯利亚地区周边的资源和冶金技术。
骑马术的兴起对草原地区产生了极大影响。阿尔然文化改变了过去游牧部落分散聚居的形态,通过建造大型墓冢、举行大型祭祀活动等方式发展出有组织的族群网络,又发展出与马和骑手相关的宗教观念。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改变了殉马的方式,马在墓葬中的角色变得十分重要。上述阿尔泰共和国艾里塔什1号墓冢内发现的骑手墓正好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变化,骑手已成为族群中十分重要的群体。
新疆于田流水墓地M10、M55等墓葬也曾出土阿尔然式的青铜马镳、马衔,阿尔然文化圈的影响力虽曾一度向南进展,但似未能深入。 蒙古中东部地区迄今尚未发现与骑马密切相关的遗存,但在欧亚草原最东端、年代与阿尔然文化相当的属中国东北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则出土了不少与阿尔然文化相似的器物(详见下文),说明欧亚草原东部区域内的文化交流活动是存在的,阿尔然的骑马文化和部分相关的宗教观念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当已沿着中国北疆区域传布了。
著名的巴泽雷克墓地是欧亚草原东部晚期斯基泰文化的一处重要发现,年代约在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之间。巴泽雷克墓冢位于今阿尔泰共和国南部海拔2500米的乌科克高原(Ukok Plateau),1948年由谢尔盖·鲁登科(Sergei Rudenko)主持发掘。巴泽雷克墓葬长年被冰土围封,墓内的有机物都得到很好的保存,各墓椁室呈东西向,以落叶松木板砌成,葬具使用独木棺,墓室与墓坑之间以碎石填满。殉马多被置于椁室旁或椁室上侧,各马仍披戴马鞍、马镳、马衔与各类木质马具,造型考究。领头的马还佩戴仿鹿角的木雕刻,这应与斯基泰人认为马可以将墓主安全地带到永生世界的宗教思想有关。
巴泽雷克文化所属族群凭借着骑马的便利,已与周边各地的文化建立起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墓冢中不少器物都是从古波斯即伊朗地区以及中国楚地引入的,如6号墓冢出土了流行于楚地的山字纹铜镜;5号墓冢发现了古波斯毛毡马鞍褥以及由楚地丝帛改制而成的马鞍布和楚式的髹漆马套头等, 而3号墓冢出土的髹漆马鞍饰件则很有可能是直接从中国订制的。 这些发现说明晚期斯基泰人(有学者称他们为“原匈奴人”)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前已与中国内地有较深入的接触。巴泽雷克式的动物形牌饰等也大量发现于中国的内蒙古以及甘青地区,可证两地的商贸和文化交流业已有年。晚期斯基泰人利用中国生产的丝绸和漆器制作马具是极其重要的发现,如果相关器物真的曾直接在中国订制,则表明包括楚国在内的列国很可能于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之际已知悉骑马的习俗。这方面的研究在未来似值得注意。
(二)西周至春秋时期中国北部和东北部地区马的使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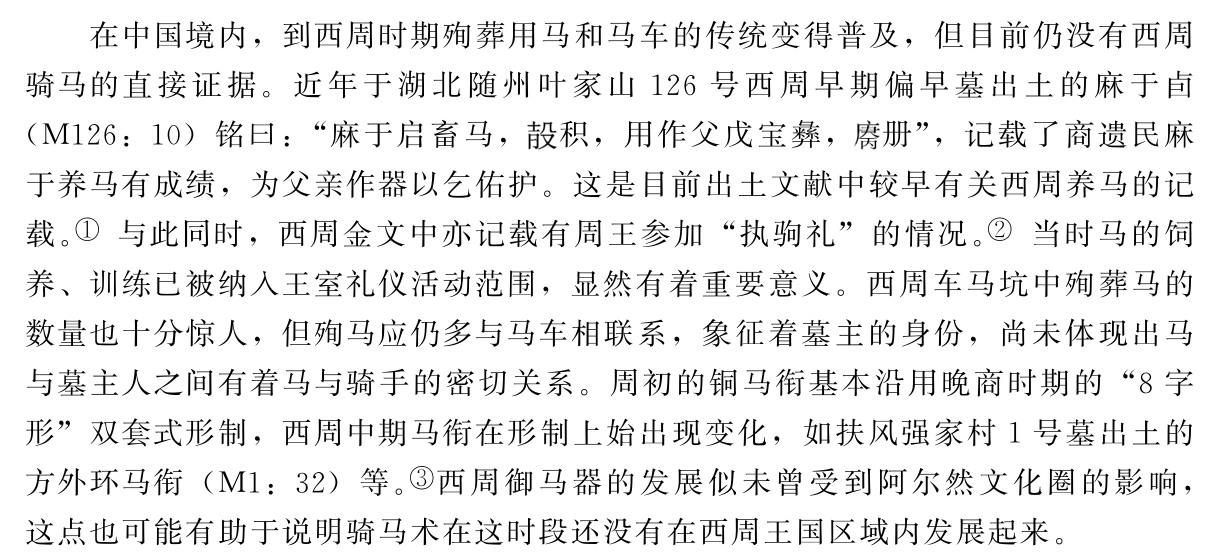
进入公元前8世纪中叶即春秋早期以后,中国北部陆续出现多个由半农耕、半畜牧的北方族群所形成的文化圈。1958—1980年间已先后清理了9批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墓葬,主要分布于今内蒙古与辽宁西南交界的宁城和建平县。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墓葬采用石椁墓、木椁墓,也有石板墓,以侧身或仰身直肢为葬式。墓中出土青铜器较多,包括内地列国铸造的青铜容器,也有仿造燕或改造中原形制的器物。根据出土青铜容器的形制可将墓葬的年代推断为春秋早期,较晚的不过春秋中期,即主要分布于公元前770年至前670年之间。此年代区间与阿尔然1号、2号墓冢年代大致同期。马具中小黑石沟11号墓还发现具“马镫形”外环的马衔和直干双孔马镳(92NDXAⅡM11:25、26)。宁城南山根和小黑石沟发现的青铜曲背刀刀首上的动物造型、金箔饰和活动环扣等装饰风格几乎都能在南西伯利亚地区与蒙古东部石板墓文化墓葬中找到对应的器物。此外,带动物首的青铜锥形器(小黑石沟1993ⅢM17:3、1993ⅡM7:4)与阿尔然2号墓冢内发现的铜锥也近同, 其他如鸟形饰件、马形牌饰等也很相似,可以肯定斯基泰文化在此时已伸延至中国东北地区。
目前中国最早的骑马实证见于1961年宁城南山根3号墓出土的青铜环扣, 同区域内的小黑石沟遗址也曾征集得一形制相似的半开口青铜环扣(75ZJ:23),环扣上的骑手形象已脱落,只剩马背上的双腿。 类似的造型设计与出土于南山根101号墓残缺较严重的一件青铜环扣及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铜环扣(2002.201.14)均相近同。艾玛·邦克(Emma Bunker)观察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的一件环扣,指出镂空铜铃内装有一粒小石,草原族群一般认为石头有着护佑人的宗教力量。南山根3号墓出土的这一件环扣,两名骑手往不同方向骑行,其中一个正做奔驰状追逐兔子。“骑手猎兔”的纹饰虽罕见于中国境内出土的器物,但在欧亚草原文化中却有着十分重要的寓意。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斯基泰骑手喜爱猎兔,认为能带来好运和胜利。黑海北部库尔奥巴(Kul’Oba)墓冢(约为前5世纪—前4世纪)出土的金牌饰(艾尔米塔什博物馆KO.48)便以骑手猎兔为吉祥纹饰。
在冀北地区发现的玉皇庙文化墓葬群,保存较好,对于研究北方骑马文化的起源亦有帮助。玉皇庙文化兴起的时间略晚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盛行于春秋中、晚期,延续到战国中期。延庆军都山玉皇庙墓地出土墓葬逾400座,玉皇庙文化遗址、墓地分布于今河北怀来、涿鹿、滦平等地, 覆盖着太行山东北麓、燕山南麓;其南部估计能与春秋时期燕国北境和晋北代地的西北境相接。玉皇庙文化的大型墓葬M2、M250均随葬了马牲,其余的中、小型墓葬仅用牛、羊和狗作为祭牲。男性墓主多随葬带有不同剑首与纹饰的青铜直刃扁茎短剑和铜带扣等,而玉皇庙墓葬M18和M250(均男性墓)出土了草原地区常见的青铜鍑。以上情况反映出玉皇庙文化有较浓厚的草原文化背景,对畜牧经济有较高的依赖性,而且十分重视男性的武装战斗能力。何嘉宁研究玉皇庙墓地出土的人骨,指出男性上肢十分发达,应与长期打猎或游牧的生活习惯有关, 这与上述墓地所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
玉皇庙墓地出土的铜马衔共18件,均出自9座规模较大的墓葬。马衔多数置于墓主胫骨侧,估计与同出的铜泡原系在皮质的马辔上。 属于春秋中期中、晚叶的M2和春秋中期的M300出土马衔的外环呈马镫形、内环为圆形,形制基本同于阿尔然1号墓冢中所见的马衔;而属于春秋中期晚叶的M250则有与阿尔然2号墓相似的一体式设计(M250:19—1),马镳成微弧状,两头有凸起马头饰,这种形制可以使人联想到阿尔然1号墓中出土的两头凸起的蘑菇头三孔马镳。而年代稍晚的M156和M230中的马衔外环已被拉长成一凸孔以增加与马缰的接触点,可借此加大摆动马镳的幅度,应是为方便骑者向马传递指令而设计的。这种设计有可能是玉皇庙文化自身的改造,但因同时代的哈萨克斯坦塔斯莫拉文化(Tasmola Culture)也曾发现相似的马镳,所以亦不排除玉皇庙文化也曾吸收了其他草原文化的因素。 玉皇庙文化拥有较先进的马具,同类型的双孔式马镳(见怀来甘子堡M5:8、M1:13、M5:9)也见于年代略晚、属春秋战国之际的辽东郑家洼子墓地和固原杨郎马庄墓地。玉皇庙文化出土的马衔、马镳在中国北部似不见于较早的遗存。需要注意的是,玉皇庙文化墓葬的马衔皆是成对出土,考虑到马具形制的先进性,双马衔的配制是代表着马车还是有别的含义自然仍有讨论空间,但玉皇庙文化的特征与草原地区所见骑马的北方族群文化墓中只随葬马具的习俗多有重合,其族属仍宜归入骑马族群中。
进入战国时期以后,拥有草原特色的文化圈已比较集中地出现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在呼和浩特和凉城一带发现的毛庆沟文化(公元前4世纪—前3世纪)遗址出土了很多动物造型的青铜饰件、牌饰、扣饰以及鹤嘴镐、削刀和短剑等兵器;但墓葬形制与习俗显然异于玉皇庙文化,采用了常见于草原地区的头蹄葬。 与此同时,桃红巴拉文化在鄂尔多斯地区兴起,在伊金霍洛旗明安独木村发现的一座战国时期墓葬,其中便随葬了一副马骨和两副马衔,形制与玉皇庙M230:19近同。 杭锦旗桃红巴拉战国早期墓M1随葬了9个马头,其中两个出土时仍套着木质马镳与青铜马衔,很有可能即是墓主人的坐骑。从内蒙古南部和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葬式和随葬品内容可见,阴山南北两地于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之间应曾出现一批新的有草原背景的族群,其进驻的地点即秦、赵北境之所在。
综上所言,骑马现象自春秋早期开始已出现于中国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之中,骑马习俗有可能是先后通过辽西、冀北、鄂尔多斯、岱海地区传入燕地、晋北和陕东北地区,并进而影响到中原腹地。这几条南下与西行的路线应是通过贸易甚至战争的形式打通,成为中原出现骑马人甚或小规模骑手群体的原因。
在今辽西南、冀北和内蒙古中南部发现的东周时期半游牧社会虽已畜马、骑马,但遗址出土马的数量并不多。玉皇庙文化的延续年代和活动范围是比较清晰的,只是其发展似未达到大规模威胁各中原诸侯国的高度。后来兴起于内蒙古的毛庆沟文化和桃红巴拉文化中也尚未发现高规格的墓葬。目前看来这些区域中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虽未曾出现巨大的军事势力,但大规模的半农半牧族群南迁已出现。毛庆沟文化和桃红巴拉文化所在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正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前后吞并且训练骑兵的区域。在此之前,秦、赵和燕三国的北境便已出现林胡、楼烦、东胡等族,而巴泽雷克文化于南西伯利亚崛起,其黄金工艺、动物相争的纹饰也已在中国北方地区流行。秦、赵和燕三国似都有机会接触到骑射,但可能出于文化抗拒等原因,骑马术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直到赵国积极向晋北和内蒙古地区扩张,与已以骑兵为兵种的胡人直接交锋后才下决心进行军事改革。
(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背景与功效
由上文论及的巴泽雷克墓中的丝绸、铜镜和漆器可知中国北方至南西伯利亚地区之间在公元前4世纪时即已存在商旅交流,赵国以拥有昆仑(新疆)玉、代地马和胡犬而闻名六国, 可见赵国应是在此种贸易中扮演较为重要的角色,亦因而较易与北方族群产生联系。
自晋文公(前636—前628年在位)即位以来,晋国赵氏便一直活跃于北方政治舞台。及至赵鞅(赵简子,前476年卒)一代,赵氏家族的势力已稳守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并开始往太行山以东的邯郸、柏人(今河北隆尧)等地拓展。据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吴问》篇所载,赵氏曾优化土地税制政策以吸引移民开拓荒土,渐渐充实了太行山以东地区的经济实力,邯郸遂成为北方重要的贸易枢纽。此举为赵襄子(赵无恤,前475—前443年在位)继位后往北方的军事扩张打下了十分重要的经济基础。
代地出产的马闻名于列国。苏秦(前284年卒)曾谓秦国四境之优势言:“南有巴蜀,北有代马。”《史记·苏秦列传》索隐:“代马,谓代郡马邑也。《地理志》代郡又有马城县。一云代马,谓代郡兼有胡马之利。” 代地产马,按索隐所注亦是胡马的集散地。代国为狄族,建立于春秋时期,史书对之记载甚少,只知其活跃于今河北怀安、蔚县至山西阳高、浑源一带,其南与中山接壤,其北则是楼烦、林胡,是十分重要的军事战略区域。赵襄子即位不久,便首先吞并代国,改设代郡,使之成为重要的军事前线。
实际上,在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之前,在北方列国中,骑兵应已经出现。 《战国策·齐策一》记公元前353年田忌、孙膑于桂陵之战中击败魏军,归齐时遇阻,孙膑教田忌曰:“使轻车锐骑冲雍门。”据此可知当时齐军已有骑兵。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之《八阵》篇讲骑兵之用道:“车骑与战者,分以为三,一在于右,一在于左,一在于后。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 苏秦游说六国,多次论述各国兵备,曾向赵肃侯(赵武灵王之父,前326年卒)分析当时赵国的形势曰:“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赵地方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如依此说,赵肃侯在位年间赵国骑兵的数量已是六国之冠。曾有说法指上述的“骑”是指战马,而非骑兵,但同卷提及秦攻齐时,途经韩、魏之地,路径险窄,“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可见“骑”应还是指一人一骑,只是当时的骑兵仅负责执行探险、做先锋开路的任务, 未必已形成大的兵种。
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25年即位,列国形势已有所变化,中山国变得强大,秦兵犯吕梁,取赵邑蔺、离石。公元前318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五国联军却被败于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这是匈奴首次被著录且以援助部队的身份加入列国军务。此战后,在外来威胁下,赵武灵王首先考察北境,访九门(今河北藁城西北)、房子(今河北高邑西),观中山边界;再经代地前往西北至无穷(今河北蔚县北),西向转到黄河,此行必然经过今乌兰察布、呼和浩特与黄河边上的包头一带。所以,赵武灵王此行已深入楼烦、林胡势力范围内,并应已接触到上述毛庆沟文化和桃红巴拉文化区域。他回到邯郸后即论当时不利于赵国的军事形势,曰:“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战国策·赵策二》) 可知赵武灵王通过此行已深入观察到骑射于战事之重要作用,尤其是深刻感受到只有胡服才有助于马上使用兵器,特别是射箭。
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推行胡服骑射,赵国也很快体会到骑兵的优势,“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又曰:“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此时赵国骑兵锋芒无两,迅速兼并内蒙古南部。在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假装使者经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南)南下入秦见秦王后的第二年,曾从代地出发往西与楼烦王会面(地点不详,疑为今阴山山脉中段大青山一带)并得其兵。赵国骑兵所需的马匹已直接从楼烦、林胡等地引进,训练骑兵的地点也设于新占领的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以为骑邑。(《战国策·赵策二》)这个布置很有可能是请了楼烦人教授骑射。《史记·匈奴列传》记述赵国控制胡地的情况,曰:“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 沈长云整合了不同年代所进行的赵长城实地勘查资料,指出“赵武灵王所筑的长城,在内蒙古自治区内,由兴和往西,经卓资县、旗下营,沿大青山南麓过呼和浩特市北、包头市的石拐矿区、兴胜公社、越昆都仑沟口,断续延伸到白彦花公社北面的山脚下”。这些举措都反映出林胡、楼烦在后来的时段已非赵国的战略重心,在阴山南部新修筑的长城很有可能是针对新兴起的、善于骑射的匈奴族。
结语
马是十分特别的动物,体型大,奔跑速度快且有极强的耐力,又有着群居和服从的天性。在马进入人类社会以后,曾多次改变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公元前7世纪以前赫梯、两河流域和古代埃及有关马和骑马的图像与文献记录虽多有存藏,但缺乏马骨遗存,无法为马的引入和利用提供完整的信息。及至20世纪在欧亚草原上先后发现了辛塔什塔、阿尔然和巴泽雷克等文化遗址,马的研究才迎来重要突破。欧亚草原乌拉尔南部的牧民率先培育出DOM2马,使之往东西两地传播并推动了家马和马车的普及,然而骑马术并未能很快在农耕文明中传开。直到乌拉尔图、卢里斯坦等文化在公元前两千纪末至前一千纪初兴起,积极培育良马, 骑马术才正式用于作战,骑兵成为乌拉尔图、卢里斯坦军队中的主力。经过长时间与他们的作战接触后,亚述的军队才意识到骑马的优势,方于公元前7世纪中叶大力发展骑兵。
通过追溯骑马术和骑兵在西亚传播的过程,可以看出骑马术在农耕社会被大规模传播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其一,邻近的牧马族群需要拥有较好的养马和驯马技术,保证马的供应量与性能的稳定;其二,马匹的交易需要达到一定规模,包括有经营大型牧场的能力、稳定的运输路线和马匹集散地等;其三,农耕社会之所以接受骑马,并非仅出于交通与经济活动的需求,往往是缘于外来重大军事威胁才大规模学习骑马和马上作战技术。
在欧亚草原东部地区,马车虽于公元前14世纪中晚叶已出现于中国商文化圈,但目前对于商人的马的来源、流布以及驯马人的族属等问题的研究仍存在很多空白。今图瓦阿尔然墓群所属的政治实体是目前年代最早的大型牧马王国,应当也是位于欧亚草原东端中国东北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骑马术的来源。从公元前8世纪始,已有较大规模从欧亚草原东部南下的族群活动于今中国北方地区并与北方列国产生过小规模冲突。但在较长时间内,欧亚草原腹地(阴山以北至蒙古一带)和华夏文明区域之间的半农半牧地带(辽西地区、燕山南北、岱海流域及长城地带乃至宁夏南部地区)没有发展出拥有较强大军事力量的势力。直到公元前5世纪末至前4世纪初,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文化兴起,迅速成为新的军事力量,财富和文化均攀升至前所未见的高度,并与中国内地有着较密切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巴泽雷克式的牌饰在中国北方区域流行,中国内地取其黄金工艺,代马也屡见于战国时代文献中,情势出现改变,华夏列国不得不正视所面临的新的军事格局,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考量后才一改前期忽视骑兵的态度,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开端,骑兵才在列国迅速发展。骑兵移动速度快,又有较强的致远能力,促使列国得以迅速开拓交通路线,深入各处边疆地域,为统一国家的出现打下必要的基础。
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多种文明与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中华文明发展演变的历史就是一部多元文化不断汇聚融合、交流互鉴的历史。近二三十年以来,中国学者与欧美学者均十分关注欧亚草原地区的考古发现。由于草原通道开阔而平坦,牧民长期迁移的生活习惯推动了欧、亚两地间的接触。欧亚草原地区的考古发现不仅深化了过去对于文明发展方式的认识,也让中国这样的传统文明古国重新省视草原民族在其文明发展过程中曾作出的贡献。目前,中国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遗存中与马相关的考古资料日渐丰富,通过马骨DNA研究、人骨鉴定、马具形制的精细分析、牧马群体与马匹贸易的研究,可以为考察古代中国骑马术的起源与发展进程提供更多信息,为深入揭示中华文明多元汇聚、兼收并蓄、开放交流的特性,为人类文明互鉴研究作出更多的学术贡献。
原文责任编辑:晁天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