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行动不仅是简单的行为,没有信念、欲望和意志(信欲志)作为理由,行动不成其为行动,这是当代行动哲学的中心思想。那么,以信欲志为原因来解释行动的根源何在?心智因果状态与脑神经的动力因果状态作为行动的原因,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心智哲学的研究文献对此类问题众说纷纭。以最小自由能原理为核心的能动推理理论,为动物和人类的心智因果解释提供了新资源。行动的物理解释仅为动力因果解释,戴维森和塞尔强调的基于意向性的心智因果解释恰恰是自然目的因果在动物和人类身上“内在化”的结果。这种内在化遵循自组织系统的最小自由能原理,并经由长期复杂的演化博弈过程演变而来。最小自由能原理为心智意向性解释提供了科学基础的自然规律。通过自然博弈与选择而涌现的能动推理功能,遵循的是一种二阶自然规律(最小自由能原理),它为化解如反常一元论这样的身心问题提供了自然机制。
关键词:目的因果;动力因果;演化博弈;贝叶斯大脑;能动推理
作者刘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2004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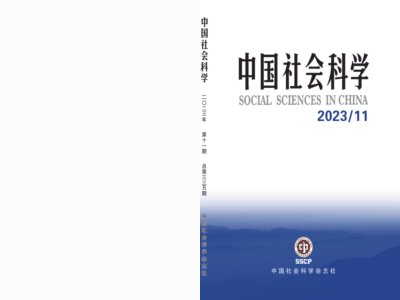
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有时行动的目的对自己以及他人都是一目了然的,但很多时候你为什么采取某个行动,你自己也不知道,周围的人也感到困惑,可是那并不等于该行动没有目的,而只是目的未知而已。我们有时会说做某件事不为什么,没有目的,但那仍然还是不能说明你的行动是没有目的的。大多数情况下的行动类型具有社会性目的标签,而你做它不是为了那个社会性目的,所以说“行动没有目的”,其实是说不是为了它习惯界定的那个目的而已。如果真是“没有目的”的,那么所说的“行动”很可能不是行动而仅仅是“行为”。行动(action)和行为(behavior)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有理由来解释,而目的是理由的重要成分,信念是另一个重要成分。一般来说,行动必须是有理由的动作行为,而理由则包括信念(belief)、欲望(desire)或意志(will),欲望或意志是行动的目的,信念是引导行动以达到满足欲望的目的的工具。一整套源于休谟的行动哲学就是从这个简单框架启始的。
没有理由的动作行为当然并非没有原因,宏观物体的运动一般来说都是有充足原因的,不过物理原因一般都是所谓的“动力因”(efficient cause)或者“近因”(proximate cause),而不是“目的因”(ultimate or teleological cause)。对于人的肌体自然反应导致的动作行为,当代哲学认为只有动力因果,无所谓目的因果;只有受了欲望或意志的驱使、在信念的指引下产生的行为才算是有目的、有理由的行动。但这个观点并非历来如此,无意识、无意志的物体运动在古代哲学中不但有动力因果解释,同时也具有目的因果解释。比如科学史上亚里士多德认为重物下落的目的因是重物为了回到地球中心(它们的归宿地)而落向地球表面。当然,就算是在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宇宙观中,重物的目的与人们行动的目的也截然不同,前者归于宇宙的目的因果结构,而后者为人的内在秉性。重物的“目的”外在于其自身,而人的欲望和意志则是内在的。欲望和意志赋予行动以目的性,但是因为发生在行动之前,它又是一种“动力因”。如果万物有灵,重物之落回到地球表面也可以说是受了它想回到地球中心(它的归宿)的欲望所致。那么相反,如果万物“无灵”,要么不存在人的行动这回事情,要么人的行动(有目的的行为)也是外部目的因的结果。
从科学史的角度,亚里士多德式的目的因果解释,在近当代科学文明中几乎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动力因果以及与之匹配的动力学定律(dynamic laws)。要解释某事件的发生,只要找到初始事件和环境条件,援用适应的自然规律(往往是以微分方程的形式出现),便能从原则上解释该事件为何发生。动力因果解释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知道了它,便可以制定预防或促进同类事件发生或发展的措施。
目的因果解释在当代自然科学中也存有一席地位。比如在演化生物学中,某器官由于具有某种功能,它为肌体在自然选择的生存竞争中获得优势,从而与肌体一同存活下来;这种解释器官或其他生物体的生存与演化的理念,乃是目的因果解释的典范。然而问题在于,演化生物学是否最终会被分子生物学所替代,动力因果解释模式是否会在生物学领域全面取代带有目的论思想的演化解释模式,这本来就是生物哲学中一个争论的焦点。演化论解释模式不但需要面对目的论解释的历史性诘难,同时它确实是一种非充分性解释模式。演化论解释这类目的因果思维模式似乎并不能为人们提供从“因”到“果”的预测推理,它能提供的更多是对已经存在的事物的某种历史性理解,它是一种“可能的因果故事”,而不是原因(大概率)导致结果的解释模式。
如上所述,自然科学中的这种现象,在心智科学与哲学中是不存在的。心智因果解释(mental or agent causation)作为“理性的”或“给理由的” 解释,既是目的因果又是动力因果,但它与物理的动力因果又非常不同,而且有与物理的动力因果解释相互竞争的可能性。那么,如何化解心智因果与动力因果的矛盾呢?首先,物理的动力因果解释虽然完整,但它对解释行动似乎“不得要领”。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心智因果解释,也就是意向性解释。
其次,为了反驳心智因果解释的冗余性,当代行动哲学中的意向主义方案,一方面解决了心智因果与行动之间的逻辑关系,另一方面试图以心智因果可由物理动力因果过程来“实现”,或者可被“还原”于其中的方案来解决问题。但下文将解释为何这条进路不可行。戴维森(D.Davidson)提出的心智因果解释之“反常性”仍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对这些经典问题提出新的解答。第一,回答心智因果是如何从动力因果的世界中涌现出来的。 第二,回答为什么心智因果有意向性、目的性、规范性(遵循原则而不仅仅是受自然律约制)。 第三,回答为什么行动的心智因果解释不是冗余的。第四,回答心智因果是否有规律可循,它们的规律是什么。
一、心智因果与意向性解释的哲学问题
戴维森认为用人们的心智作为原因或理由来解释他们的行动既无可非议,也是不可或缺的解释模式;可是他同时又认为每一个行动作为自然事件,又必然存在充分的物理或自然解释。而且,自然因果链加起来必然是完备的,因为原则上说,世上只有自然事件,而自然事件只可能被自然事件和自然规律所解释,不可能有超自然的解释因素,心智因果当然也不例外。那么,心智解释是怎么一回事呢?用心智因果解释行动虽无可非议,但戴维森也意识到,与自然解释不同,心智因果解释并无严格的规律可循。在常见心智因果解释的大众心理学中,很少能见到像物理、化学、生物学领域中的那种严格的自然规律;某个解释是否成立,并非看它是否可以从某个自然规律(以及信念、欲望等前件条件)中推导出来,而是要看它是否“符合”解释所需的“理由”,而理由包括诸如对人的理性与基本需求的假设。因此,心智因果产生物理效果,但又不遵循严格的规律,常常是一例一判,即便有某种规律可循,也可以随意找到例外。基于这样的情况,同时又无理否认心智因果与物理或自然因果是个体同一的 (token identical),那么,一元论必定成立,心智因果则只能是“另类”或“反常”的了。就行动的充足解释而论,心智解释似乎是冗余的,但又是合情合理的。这就是戴维森所谓的“反常一元论”的中心思想。一元论是指大自然中的动力因果解释的充分性,反常是指心智解释既合理又不必要的“反常”处境。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比如某人干了某件事情,问他为什么那么做,他给出行动的理由,大家认可是这个理由使得他做了这件事情,那么,解释的需求就满足了。如果有人反驳说,那是“目的因果”解释,不算数,要解释该人的行为,必须给出他处在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中,他的肌体(包括大脑)在做这件事之前发生了哪些物理、化学、生物的变化,然后是哪一组物理、化学、生物的自然规律使得那些自然条件充分地导致了他做了这件事,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此人的要求“不合理”。我们并不是说这样的动力因果解释不可能或不存在,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我们知道从原则上说,大自然中必然存在这样一条动力因果链(也许仅仅是大概率的因果链),但是,我们既不可能找到这条因果链,也不需要去找它;没有人会在知道了该行为的心智因果解释之后,还会想到要求知道这条因果链(某些专业的科学家除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形呢?以下这个演化生物学中的例子似乎能够给我们一点启发。
宾莫尔(Ken Binmore)在评论动力因果解释与目的因果解释的关系时,用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自己为“目的论”解释辩护的观点。自然中的鸣禽类在早春时节会不停地引吭鸣唱,歌声十分悦耳,是大自然在春天里复苏的象征之一。但鸣禽为什么在早春不停地引吭鸣唱呢?苦苦追寻其动力因是没有希望的。即便我们知道了所有鸣禽在早春时节体内的分子排列、化学反应、环境因素等,我们仍然不会觉得回答了问题。可是该现象的目的因果解释却非常简单,鸣禽为了在繁殖季节保护自己的地盘,用长期演化出来的“歌喉”向其他鸣禽“宣布”它的所有权,用以防止不必要的直接争斗。当然,这里的目的是以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为条件的目的,并非鸣禽类个体自身的目的行为。这样的例子在演化生物学中比比皆是。为什么雄性鸟类通常拥有比雌性更艳丽的羽毛?为什么动物体内有诸如心脏或者肝脏或者血管这样的器官?与宾莫尔的例子相同,用来回答这类问题的科学解释,不是像物理学、化学,甚至普通生物学里给出那种解释,即找到产生需要解释的现象的初始和边界条件,再找到该现象所遵循的自然规律,然后用它们来推演出需要解释的现象。熟悉科学解释的科学哲学理论的读者都知道,这是亨普尔(C.Hempel)的DN解释模型。而根据上述的讨论,这是典型的动力因果解释;使用的自然规律多半是由微分方程表达的动力学定律。而适用于回答上述生物学问题的解释模型大多则属于目的因果解释。演化生物学中的“目的因果”并不一定要理解为亚里士多德自然体系中的目的论解释。现代演化论或者演化博弈论中的解释模型是在以下意义上作为目的因果解释的。
鸣禽早春引吭鸣唱,是为了保卫其交配地盘,防止直接冲突。这样的行为模式在多代际漫长的生存竞争中,由于高出其他与之竞争的物种或策略,被自然所“选中”。因此,早春鸣唱因为是保护鸣禽交配地盘的有效手段而为其存在提供了理由。存在或出现的理由是行为的目的,而此目的并非隐含在早春鸣唱的动力因果之中(并不能在任何鸣禽早春鸣唱行为的初始和边界物理生化条件中找到)。这就是所谓的演化博弈论解释。当然,这里的目的是以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为条件的目的,并非鸣禽类个体自身的目的行为,至少当代演化生物学还不具备解释非人类动物个体的自身目的意向性的理论框架。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戴维森的反常一元论在演化生物学中有类似的情况。两种不同的解释模式对同一个现象均能给出充分的解释,一类解释为动力因果解释,另一类则是某种目的因果解释,其解释的理由不是初始和边界条件如何“导致”或“产生”了需要解释的现象,而是什么目的或意向(有指称的信念和有目的的欲望或意志)为现象的存在或出现提供了理由。同样地,动力因果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第一”解释,每个可解释的现象都必定存在一个完整的动力因果解释(是否可能找到该解释则另当别论);而目的因果解释的“合法性”始终存在疑问,即便是在如演化博弈论解释这样的“科学解释”领域内也是如此。
要解决心智因果解释与动力因果解释之间的矛盾,首先必须对前者有一个更完整深入的理论认识。塞尔(John Searle)关于意向与行动哲学的理论是一整套近乎“意向主义”的理论。虽然塞尔并未试图直接“解决”上述的戴维森“反常一元论”困境,但其理念框架似乎足以解决该困境;塞尔一方面试图提供心智状态足以为行动提供理由的逻辑关系,另一方面试图说明心智因果解释如何在物理动力因果解释中得到实现或还原。
塞尔意向论的基本单元是心智状态或心智事件(mental state or event),心智状态的本质,或者说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它的“有所指”性。心智状态的“内容”为命题内容,作为内容的命题表达该状态呈现或表征的事实。你说看到了一只鸟,当时的知觉心智状态的内容其实是一个“知觉命题”:“我面前有一只鸟”,而且这只鸟导致我看到一只鸟在我面前。后一句是前一句的真值条件,它是一个因果判断。信念心智状态命题内容的例子更常见,而欲望和意志心智状态的意向性与知觉的情况颇为相似。人们通常以为想要的是物,但其实是想要拥有所欲之物的事态的实现。
其次,塞尔进一步认为,心智状态的本质决定了它被“满足”的条件。意向性就是有所指的性质,而“所指”则有“成”“败”之分。成败的条件就是所谓满足心智状态意向的条件。条件在现实中兑现,意向性得到满足,否则是不满足或“所指者为误”。塞尔的这一意向性理论对于知觉、信念、意义以及欲望的意向性本质的阐述,具有统一性、简明性和实在论方面的优势,如若为真,显然是可以用来回应戴维森问题的。“意向因果”应该是说行动中意向或动机如何导致作为行动结果的行为以及为其提供理由的范畴。与知觉、信念和欲望相同,行为中意向的命题内容就包含了该意向的目的以及意向与目的的因果关系。塞尔强调说,意向因果属于“具体因果关系”的类型,不应该被视为体现因果规律的那种休谟式的因果关系。而且,意向与其产生的行为(如口渴与因口渴而喝水)之间是一种“逻辑”关系,意向的内容就意味着行为的发生。当然,和其他意向性范畴一样,这些条件是否得到满足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
最后,与戴维森问题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意向因果与物理因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反常一元论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在塞尔看来,意向因果解释与大脑神经过程的动力因果解释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心灵过程中的意向因果与大脑神经过程的动力因果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不同“现象层次”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实现”(realization)关系:高层次的意向原因和结果分别在低层次中得到实现,而在不同层次上,各自又有各自的因果关系,比如大脑神经层次的过程为动力因果解释,心灵意向与行动层次为意向因果解释。这样的架构不单单是在心灵与大脑之间存在,在自然现象的其他部门也十分常见。比如在流体力学领域,说液体是“湿的”,并不能说是因为组成该液体的分子是湿的。应该说液体的“湿”在组成它的分子中得到实现,或者说液体的湿度由组成它的分子的总体结构和运动因果地决定。再则,火焰的灼热实现于分子的剧烈运动,而火焰烧焦木材是高层因果过程,它实现于低层的火焰系统与木材系统之间分子运动的相互作用。
可是,在笔者看来,塞尔的这套现象层次间的“实现”机制似乎并不能帮助他的整个意向论有效地回答戴维森问题。在液体的湿度和火焰的灼热的例子中,说现象层面的因果解释可以被分子层面的因果解释完全取代,在科学解释的语境里是不成问题的。不可能说,现象层面有任何因果过程在分子层面得不到解释。但是,在具有意向的心灵现象层面,戴维森问题恰恰是在说:(1)意向因果解释无法还原于底层的大脑神经动力因果解释;(2)每一个行动的原因均存在完整的大脑神经解释;(3)意向因果解释似乎不遵循自然规律。
上面说到,塞尔应对(3)的思想是,虽然意向因果的确不受休谟类型的自然规律的管辖,每一个意向因果过程都似乎是具体的、独特的,但是,由于行动的意向或动机的命题内容包含了实现该意向的行动和条件,即所谓的“自指性”(self-referentiality),因此意向因果解释具有属于现象层面的“逻辑”自主性。可正是由于意向因果的这种自主性,塞尔用“实现”的关系来解决不同层次还原的问题便显得薄弱,因此无法回应(1)。心智状态的意向性与大脑神经元的结构与活动之间的关系似乎完全不像液体的湿度与分子的结构与运动之间的关系。最明显的不同就是物质现象层面的状态都不具有心智状态那样的自指性。某事物导致另一事物的存在或发生也不具有所谓的“逻辑地”隐含其满足条件这么回事。当然,塞尔也不会否认(2),因为他反对身心二元论。
二、演化博弈与目的和理性的涌现
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的认知和行动是有目的和理性的。毫无理由(reason)地相信是盲从,毫无理由地行动是鲁莽,两者都是违反理性(rationality)的行为。那么什么是“理性”呢?在浩瀚的哲学书卷中,对理性的探讨众说纷纭。按照诺齐克(R.Nozick)的理论,理性体现在对原则的运用与坚持,而运用原则使得人类摆脱了盲从自然规律的束缚,人类理性是生物与社会演化过程的产物。
人类理性的最显著特点应该说是懂得遵循原则(principle)来办事。也许可以说这是人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动物行动亦遵循规则,但那是自然规则;动物自身并不懂得,也无从建立或取消自身遵循的行为规则。一般来说,人类理性有三大功能,一是求索(inquiry),二是审慎(prudence),三是道德(morality)。一个依靠证据来认识事物,靠权衡利弊与证据来行动,用道德原则来约束自己和他人的人,就是一个理性的人。而在这三个方面,人们不是仅仅凭借直觉或本能来对付证据或利弊的,一般动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能力;具有通过建立与修改原则来应对这种能力才是理性的特征。知道自己和他人都是理性动物,我们才会对人类的行为要求解释的理由以及依据原则做道德判断。对动物或婴儿做同样的评判之不合理也就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运用原则来认知、办事、赏罚比通过本能或凭直觉行事更好,以至于这样做成为理性的标准、人类有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呢?诺齐克称原则为“目的论工具”:“要想为原则辩护,你得说明它的功能,然后证明它有效地实现了它的功能,并且在损耗、限制等条件等同的情况下,比任何其他的东西更有效。”如果说动物在以上所说的三个方面都能做出直观或自然的选择和评判,这种选择和评判只能是不自觉的、因物因时而异的,不可能也不可以被复制和普及的。有了原则,不同类型的选择和评判便可以通过对照原则来进行;这样做不但有可能被学习和普及,同时也给评判行动的优劣或善恶提供了标准。人类社会文明的诸多成就都是与人类能够建立、运用和反思行动原则分不开的。
虽然坚守原则的理性在诺齐克看来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准,但人类理性并不像欧洲启蒙时期的哲人标榜的那样,是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理性的缺点不止一个,与本文有关的是过于固执于原则以及过高要求其普遍性。信念需要理由或证据充足才能相信,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此道理要具有普遍性则必须建立“充足理由或证据”的标准;而要求逻辑上完美自洽的充足理由,使人们(如笛卡尔或休谟)意识到人类所有可能得到的经验知识都是可怀疑的。怀疑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执着于完美理性的结果。这是认知维度上的困境。在审慎维度上,坚守原则最有名的例子也许要算是“囚徒悖论”。自顾(或自利)(self-interested)与理性的人类,在遇到囚徒选择矩阵的情况下,只能选择非理性的行动策略,这就导致了悖论。在道德维度上,“电车难题”也许是最有名的例子之一。
诺齐克认为,无论认知抑或行动都是心智状态与外部环境的协调契合的过程。正如上述塞尔的观点,认知的适应方向(direction of fit)是心智状态适应环境,而行动的适应方向则相反。可是诺齐克认为,无论是哪个适应方向,适应的成功(适应度的最大化)不应该也不可能是纯粹内在的过程。也就是说,不是像康德所期望并论证的那样,认知与行动的成功是由理性内在地界定的。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将事物本身(物自体)关在了知识与理性行为(或审慎与道德的行为)的范畴之外,真信念或明智的行动只能是现象领域之内符合理性融贯性的东西,与事物本身无关。诺齐克这样说道:“康德说,如果理由和事实是相互独立的变量,那么理性主义者便无法为它们为何会契合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因此他提出了(经验)事实不是独立变量的方案;事实之依赖于理性解释了它们之间的对应与契合。但是还有第三种可能性:理性才是非独立的变量,它受事实的塑造,而且它的这种对事实的依赖解释了两者之间的对应与契合。这正是我们的演化假说所提供的可能性。理性(理由)之所以能告诉我们世界(reality)是什么样的,是因为世界塑造了理性,选择了它看上去‘无可怀疑’的东西[为真]。”
正是因为厘清了笛卡尔以降、由休谟补充的怀疑论困境,以及康德为解决怀疑论而做出的哲学发明,诺齐克认识到,演化论的思想能够为自然化人类理性的原则和功能提供明确的道路。无论是笛卡尔所谓的“清晰分明”的感知与思想还是休谟的长期自然形成的“习惯性”的因果判断,这些“合情合理”的心智状态之所以为真,并非外部环境决定了意识或者理性意识决定了“现象化”了的外部环境,而是大自然通过漫长的演化博弈过程,造就了人类这样的依靠理性来连接心智状态与外部环境的动物。显然,运用原则或原理来判断信念和规范行为的理性,之所以在演化博弈的选择过程中胜出了,正是因为理性是上文提到的目的工具。
事物的“功能”及其存在的“目的”和事物在其环境中的“适应度”的关系是通过“稳定态”(homeostasis)来连接的。从演化博弈的角度来看,大自然可以被视为一个不断地从一个稳定态过渡到另一个稳定态的演变过程,而所谓自然的稳定态就是在其中的各种系统处于相互适应的状态,而使得各系统适应的功能便是系统及其部分所追寻的目的或目标。生物体从理论上看都是复制子(replicator),它们通过自身的机制,比如动物体内的基因,不断随机地产生变异;变异的复制和为生存相互的竞争便是自然选择的资源。系统的不同部分为生存而各自具有的功能是系统的目的,而系统生存的大环境可被抽象地模拟为所谓的“适应度地形”,系统的变异和复制可被视为在该地形中的运动,在自然选择中的生存竞争,可以用微分方程(比如复制子方程)来刻画为向着适应度地形的局域高峰攀登的行为。诺齐克援引演化论来解释理性的自然演化是下文将讨论的理论的粗浅原型。
那么人类的演化过程为什么选择了理性而不是其他的生存策略?以上提到的诸如怀疑论、囚徒悖论以及电车难题,的确让人怀疑理性是否比其他生存策略具有更高的适应度。可是,演化博弈自然地产生的理性并不完全是必然会引出各种悖论和困境的理性,它同时也是实用理性、默会理性,甚至无意向的、贝叶斯大脑自然而然地运用了千万年的预测加工理性。按照诺齐克的看法,演化过程产生了人类对真理和理由的积极反应,能够依照原则来索取近似为真的信念并以它为理由作决策。语言以及其他高级知行功能的产生强化了理性的功能,使其有超越自然演化结果的可能。另外,文化演化(cultural evolution)是在生物演化之外的新型演化过程,是人类社会独有的演化过程。它的科学性一直是学术争论的焦点。但如果文化演化为实,以语言和原则为主的思辨理性的演化发展就不再令人费解了。
探究自然化理性的起源与本质的哲学家还有很多,比如吉巴德(A.Gibbard)关于伦理道德规范的演化起源的论述。然而,这些论述均过于笼统,无法真正回答演化过程如何产生了人类理性或伦理道德;不但没有能说明理性或道德这样的“目的工具”的生物神经机制是什么,也未能说明具有某种目的的大脑神经机制是如何通过演化博弈,在长期的自然选择过程中被选中的。只有弄清了回答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则和进路,我们才能说对理性(或者道德)的起源和本质问题有了令人满意的解答。当然,许多经验细节还有待实验生物学、脑神经科学以及演化心理学方面的成果验证。
奥卡萨(S.Okasha)的近作深入探讨了演化生物学中关于目的、策略和“能动体”(agent)等概念的理论及应用。有研究表明,贯穿始终的是在两种或两层意义上这些概念的交织运用。“能动体思维”的原始形态是隐喻生物体亦具有意向性,比如工蚁吃掉其他工蚁的卵好似因为它们有意捍卫蚁后的后代;而演化生物学里的概念则是生存竞争中生物体为提高种群的适应度演化出来的功能,而且这种适应性功能通常是由生物体体内的化学机制维持的,似乎与意向性无关。然而,自然化了的能动体思维从两个维度与“适应度最大化”相关联。一个维度是生物体演化出来的特征使得它比有其他特征的个体适应度高;另一个维度是自然环境会选择能最大化适应度的特征。前者是关于个体特征适应度的维度,而后者则是大自然择优保留的维度。如果说能动体思维在演化生物学中引入了目的或意向这种类似“理性”的概念,那么前一维度是用来衡量个体对最大适应度这个目标的追求,而后一维度则是用来表征大自然追求最佳适应体目的的属性。有趣的是,能动体思维的原本意义与它在生物种群中的意义之间的内在关系,似乎可以在“演化博弈论”的发展历史中找到。
博弈论属于经济学或类似的学科,是理性人之间博弈决策的数学模型理论。这类学科的基本方法为“理想化”建模,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对模型做“去理想化”地应用来解决实际问题。演化博弈论源于发现生物世界中博弈现象处处可见:比如动物之间为争配偶或领地,为避免直接争斗,靠诈唬对方来试图取胜的行为。为了移植博弈论,创始人梅纳斯密斯(John Maynard-Smith)发现,只要将博弈论中的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转变为演化生物学中的适应度函数 (fitness function),由“理性选择”决定胜负的一次性博弈便转变成了由“自然选择”决定胜负的多代演化博弈。博弈者并不需要做理性决策,它们的策略也不需要有意识地来做选择,甲壳虫头上的角的长短之分就可以是在生存博弈中的不同策略。自然选择长角甲壳虫的过程就是演化博弈的过程中因为长角甲壳虫的策略具有比短角甲壳虫的策略更高的适应度而取胜的过程。
更加有趣的是,这个通过“祛魅”理性而获得的生物演化博弈理论,很快又被博弈论学者重新引回到了有意向有选择的人类博弈过程中,成为解决各种博弈论悖论的利器,比如用演化博弈的方法解释著名的“囚徒困境”悖论的例子。“博弈”概念,就这样经过“祛魅”和“复魅”的两次转变,开辟了生物演化博弈论与理性决策论中的演化论两大领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可以说是硕果累累。结合上文的讨论,笔者对博弈论做一个实质性的阐释。高度理想化理性的博弈数学模型,严重误解了人类理性。生物体的演化博弈论揭示了大自然中“理性”的根源。所谓的能动体思维有两个维度:(1)大自然有目的地选择适应度最大化的种群的维度;(2)生物个体为生存最大化自身的适应度的维度。二者分别体现了意向性或目的性在作为整体的自然和作为个体在自然中的存在形式。笔者认为在能动体思维的这两个维度之间存在着内在和有机的联系。那就是说,生物个体追求最大适应度的内在目的,恰恰是“内化”了大自然选择适应度最大化者(maximizers)生存的这样一种“理性”举措。打个比方说,小王庄东头住着王大姐一家,家里有三个女儿,老大从小喜欢习字数数,老二喜欢自己动手敲敲打打,而老三喜欢跟着大人理论是非。王大姐和老公都是知书达理的人,精心培育助长孩子们各自的特长,结果她们长大成人之后,老大做了村里的文书兼会计,老二做了木匠,而老三当了村干部。三人各自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得有条不紊,成为王家的骄傲,也是村里人的骄傲。王家三个女儿优秀的表现是她们各自的理性发挥了作用,而这种理性的存在与发扬,则是她们父母明智选择(培育助长)的结果。理性从外在的自然目的性或意向性到个体内在的目的或意向性的转化,乃是生物与文化演化博弈的结晶。
三、能动推理与心智因果的起源
心智因果是一种目的因果,因为解释行动的心智状态(即信欲志)都具有意向性或目的性;为行动提供解释的理由正是其目的性,而不是因为其出现于行动之前;这就是心智因果与动力因果的根本区别。正如上文鸣禽早春引吭的例子所示,在生物演化博弈的现象中,生物体的某类功能是为了具有更好的竞争和生存优势而存在的。为了更好地竞争,被自然选中,就是一种目的。心智因果的机制也是这样一种有目的地演化的产物。包括诺齐克、丹尼特(D.C.Dennett)与奥卡萨在内的哲学家均认为,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人类理性或意向性或目的性(不少动物亦有这种功能的低级版本)是长期演化博弈的结果。
奥卡萨的工作比其他哲学家更高明就在于他不但讨论了理性的不同种类以及它们的相似性,而且还讨论了演化博弈与理性涌现的汇合与分道扬镳的不同可能情况。奥卡萨关于演化论与理性之关系的讨论,是从演化过程中如何出现“行为可塑性”或“反应灵活性”入手的。对环境非理性、纯反应式的适应是一种特殊功能与特定环境的一一对应关系,比如鹿的敏捷反应和飞快速度就是用来对付环境中凶猛的捕食者的特殊技能。而所谓理性的特征,如诺齐克所说的,则是对应不同的环境或生存需要做出相应的反应的能力。因此,演化博弈过程中非理性到理性的演化就是一个从简单直接的功能环境适应到可塑的或灵活的适应的演化。后者便是理性、意向性或心智因果原型的出现。而生物个体从非理性到原始理性的演化就是通过个体提高其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行为变得越来越可塑和灵活来实现的。随着集体社会性生存的扩大、原始语言的出现等,大型哺乳动物个体的可塑性和灵活度变得更高,同时出现了诺齐克所谓的以原则对应变化的现象,也就是人类理性的涌现。
奥卡萨进一步认为,理性的两个维度(即理性的演化与演化的理性)似乎可以从以下的类似平行现象中得到印证。动物和人类从生到死的发展过程,至少前半段是从弱理性到强理性的发展过程。人从婴儿到成年的发展就是一个思维判断发展得越来越可塑和灵活的过程。这个过程对应了动物由于环境的复杂多样化,在生存竞争中逐步变得更加可塑和灵活的过程。作为思想实验,奥卡萨还建构了一个贝叶斯理性(以贝叶斯定律作为推理原则的理性)如何在演化博弈过程产生出来的例子。通过对一个合理的理想化的演化博弈过程的演算,贝叶斯理性的确是演化博弈中的演化稳定态。当然,贝叶斯理性应该不是演化博弈的直接产物,而贝叶斯大脑里的贝叶斯(亚)理性倒很可能是。那么,理性有可能完全被自然化吗? 奥卡萨的回答是不大可能,其原因十分明显:不但实验心理学告诉我们非理性行为比比皆是,经济学或哲学家也普遍承认,人并非完全理性的动物。可是,原始理性则无疑是自然化了的。人类心理学实验发现的诸多非理性行为多半是原始理性的例子。而后续出现更为高级的理性则是文化演化或其他非演化过程的产物。
那么,演化博弈、自然选择在地球上长期生物演化的过程中到底是如何演化出理性或心智因果的呢? 它是以何种具体的机制演化出了心智因果的呢?为何具有如此机制和功能的动物和人类心智因果会是演化博弈的结果?
回答了这些问题就聚焦了本文的中心论断:理性或心智因果是自然目的因果的内在化,而和其他自然目的因果一样,心智因果也遵循一种极值原理。也就是说,心智因果的意向性或目的性是为了使得内部状态倾向于某种极值稳定态而涌现出来的性质。那么,什么内部机制能够作为通过演化博弈过程“内化”自然的目的因果呢?笔者认为,回答这些问题可以借鉴以弗里斯顿(K.Friston)、克拉克(A.Clark)、霍威(J.Hohwy)等人为先驱的动物感知以及低等认知的能动推理理论。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有着细节各不相同的感认知模型,比如“预测加工”“贝叶斯大脑或贝叶斯机器”以及“马尔可夫毯(Markov blanket)—能动推理模型”。与回答以上问题直接相关的,实际上是贝叶斯大脑和演化博弈论相结合的产物。通过推测自然中自组织系统由简单到复杂系统结构的演化,马尔可夫毯的出现以及贝叶斯推理机制的出现等可能演化历史,可以说我们已经看到,动物和人类心智因果如何由演化博弈的目的因果转化而来。
这是一个与奥卡萨虚构的贝叶斯理性的演化完全不同的过程。奥卡萨的贝叶斯理性是高度发展的、人类有意识有原则地进行的思考推理活动,这与贝叶斯大脑亚个人(sub-personal)或无意识和潜意识层面的准理性活动截然不同。人类高级理性的出现应该与诸如文化演化以及语言的出现密切相关。
设想在自组织系统出现之前的原始海洋,不同规格的分子按照物理化学原理运动和相互作用,局域性的非平衡态出现了消失,消失了又出现;描述这种现象有热力学也许就足够了。之后海洋里出现了能够较长期的保证非平衡态的系统。这种系统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往往是因为产生或获得了某种膜或壁,将系统的内部与外部隔离开。外部的能量和信息只能通过这种的膜或壁与内部交流。这就是马尔可夫毯的原型。具备了马尔可夫毯的系统即成为所谓的自组织系统。出现了内外分离但又依赖与外部的交流生存的状态,自组织系统的内部便开始产生出不同的“对付”外部环境的机构或机制。系统由极为简单的(如雪花),逐渐进化到复杂的(如单细胞生物);内部的机制也开始持续分工。“感知”外界的部分似乎与“行动”的部分出现分离。由于马尔可夫毯的高度隔离保护作用,感知机制不可能像依靠处理大数据的深度学习AI机制那样,通过直接处理和学习外部提供的信息来感知其环境。
我们可以借用深度学习的AI系统作为对照,虚拟地解释贝叶斯大脑的起源“故事”(所谓的most likely story)。设想在原始海洋中的简单系统,它们用不同的机制与外部的大环境互动。一类系统不受马尔可夫毯的隔离和保护,但具有快速处理海量信息数据的能力,就如今天深度学习的AI系统。这种系统的感知或低级认知功能可以是特殊功能对应处理特定类型信息的直接简单、非可塑非灵活功能。并且系统控制自身行为的是另外一套机制,也是一类信息指令控制一类行为、非灵活变通的机制。此类生物依靠着快速直接的学习机制和控制机制的分工合作来生存繁衍。这类生物所处理和产生的东西无须具有意向性,或者仅需要最低级的意向性。另一类生物则是受到马尔可夫毯的保护与隔离的。由于隔离,无法直接处理海量信息(大数据),它们需要产生一种感知外界和指导自身行动的带有高度“预测”性和“自护”性的内部机制。不同的机缘产生出不同机制,而其中在演化博弈的环境中最有竞争力的就是贝叶斯机器的原型。
从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动物感知(以及低级认知)的贝叶斯机器模型乃是赫尔姆霍兹机器的现代版本。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动物感知不是被动地吸收和处理消化感官摄入的外部信息的产物,也不是仅仅为高层认知与行动提供感知材料的大脑机构。相反,动物感知是主动的、有推理和验证的、与行动同时进行密切相关的“能动推理”机构。而贝叶斯机器或贝叶斯大脑模型,顾名思义,就是说动物大脑感知和低级认知所遵循的自然规律是贝叶斯定律。贝叶斯大脑是近年一个备受关注的关于动物大脑或心灵预测感知外部世界、策划执行策略,以及感知和行动互动互补的理论。其核心部分是贝叶斯概率更新定理,定理给出某系统在给定了某信念或类信念状态的先验概率和似然之后,如何求得后验概率的公式。设想动物大脑就是非意识性地按照贝叶斯定理来更新后验概率的;非但如此,大脑还是一台主动预测其感知材料的外界因的机器;它一方面自上而下地推送自己带着某种先验概率的预测,同时又自下而上地反馈预测与感知数据“对照”产生的不可化小化无的预测误差。此循环在大脑不同层级之间依照贝叶斯算法重复,上一次(层)的后验概率帮助修改预测和更新下一次(层)预测的先验概率。因此,根据这个模型,动物知觉即为贝叶斯式的误差最小化条件下的预测。预测所依据的即为外部因的模型,是大脑主动“想象”或假设是什么事物在外部导致了它会遇到的感知数据,比如视网膜上录下的光线频率与强度的数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是猫或狗而不是它们在我们视网膜上留下的数据。
预测加工理论同样也可以应用到对行动策略的选择上。假设被选中的行动策略改变了你的外部环境,使得你感知该环境的预测误差得以降低,在这样多次多方面的循环操作后,你的感知环境会得到改善,你会体验到近似想见的能见到,不想见的不会见到的怡人氛围 。另外,学习也是通过能动推理完成的;这样一来,学习、审度、 决策和行动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最小化预测感知的误差,它们都以不同形式被统一在贝叶斯大脑或预测加工理论的旗帜之下。这也就是弗里斯顿、克拉克和霍威等人所推崇的口号:知觉就是行动,行动就是知觉。同时,这个学说也改变了心灵哲学中一个非常传统的观念,那就是心灵与世界之间有着两种相反的配合方向(directions of fit)。知觉的方向是心灵配合世界,而行动的方向则是世界配合心灵。但根据贝叶斯大脑学说,心灵与世界只有一个关系,那就是相互配合的关系。
回到上面的故事,可以想象以AI处理外来数据信息、不受马尔可夫毯保护的系统,在其初级阶段只能处理有限数量和方面的信息,因此对外部环境的“感知”和“认知”只能处于原始状态,而受到马尔可夫毯保护的原型贝叶斯机器,却可以通过对外部环境的“假说猜测”和“假说验证”,不需要处理大数据的能力就能逐步形成越来越复杂和高明的感知和认知。由于原始海洋中维持自组织系统的特殊环境要求,以马尔可夫毯和贝叶斯机器为机制的生物系统在与AI式深度学习机制的生物系统的生存竞争中取胜,得以繁衍至今,成为动物和人类的感知或认知的模式。只有到了计算机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才有可能构建复杂高明的深度学习AI系统,在不受也不需要马尔可夫毯保护的情况下,依赖于充足的能量供应和高速的运算能力,直接处理外部的大量数据信息以获得类似动物感知和认知的效果,甚至在很多方面远远超过动物和人类的能力。
假如某些人工智能系统的确有感知、认知和行动功能的话,它们的这些功能完全可以和本文讨论的理性、意向性,以及心智因果没有关系。心灵哲学家如塞尔和德雷福斯等人所谓的计算机不可能像人类那样说有意义的话,做有意义的事,给出有规范性的判断,就是这个意思。对这个结论,不同的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理由。比如塞尔曾经提出著名的“中文屋”论证来说明计算机系统不可能懂语义。
回顾上文的诸多理由,特别是上述虚拟的演化博弈故事,不难看出为什么AI直接处理大数据的系统不会产生,也不需要产生类似人脑的意向性和规范性,因为它们可以直截了当地处理所有外部信息(大数据)。这也是工匠做产品与AI机器做产品的根本区别所在。工匠的贝叶斯大脑是依靠推测、计划、小数据验证等,在受马尔可夫毯的信息机制限制下工作的。而AI控制的机器可以直接处理大数据、直接做归纳推理,因此它们的做法是与工匠截然不同的。
以上的论证必须结合前面关于理性和目的的演化博弈根源的讨论才会有力。虽然消失了的竞争策略不会如消失的物种的肢体和器官那样留下化石标本,但是策略的曾经存在和器官功能的存在一样,可以通过对环境条件的认识来推测。某个策略应该出现过,因为生物系统需要它的环境条件曾经出现过。当然,推断只能是可能性很强,不是直接做结论说一定出现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最为可能的故事”来表述这类推理。
结语:极值原理与二阶自然律
人类的心智因果是真实、自然的因果解释关系,它是大自然的目的因果通过内在化,在大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因果关系,它是超乎物理的动力因果过程之上的一种“二阶”因果过程,它的“意向性”或“目的”就体现在对“最小值”或“极值”原理的遵循。贝叶斯大脑是依靠贝叶斯定律来最小化预测误差,从而保护了自身的完整性,得以在漫长的自然选择过程中博弈演化而来的。通过弗里斯顿团队的探索,这种预测误差最小化是系统内自由能最小化的一种表现。因此,自由能(最小化)原理与能动推理理论是上述讨论的贝叶斯大脑模型的理论基础。动物和人类心智行为的意向性解释之所以“反常”,是因为它不是直接从非意向性基本物理化学过程与原理中涌现出来的,它是自组织系统在地球上长期演化博弈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大自然体现在演化博弈过程中的理性选择(自然选择),正是贝叶斯大脑理性机制的原始模型。而戴维森提出的心智因果无法还原于动力因果,以及行动的心智因果解释中不可能找到自然规律的责难,到此本文也有了一个回应。
心智因果解释的确不能还原为物理的因果(动力因果)解释,因为心智因果属于一类全然不同的因果关系,它是大自然中的一种目的因果内化的结果;因此行动的心智因果解释似乎超乎动力(物理)因果之上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塞尔提出的还原或实现关系,在本文的框架下则是不可取的。另外,戴维森的所谓心智因果没有自然规律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们的自然规律不同于动力因果的规律,比如牛顿定律或孟德尔定律。这些是所谓的“一阶自然律”。心智因果遵循的是极值原理,是“二阶自然律”。预测误差最小化或者自由能最小化,这样的自然律以某种“目的”来“统治”各类不同的动力因果过程。正如宾莫尔在鸣禽早春引吭的例子中强调的那样,虽然产生该现象的每一个物理化学生物的动力因果过程都遵循它们各自的自然规律,它们的总和充分地产生和解释了现象的出现,但现象的演化博弈解释既不能被无遗地还原为这些过程,也不遵循它们的规律。因为演化博弈解释是目的因果的解释,而这种因果解释遵循的规律是演化博弈论的规律,是鸣禽最大化它们与环境和其他个体之间博弈以达到最大适应度的规律。心智因果是目的因果的一类,是成功地内在化于动物大脑(和身体)的目的因果,因此,同样的理由也适用于心智因果。
意向性解释和心智因果不受类似动力因果的自然规律约制,另一个理由是,一阶自然律是在事件之间的稳定联系(constant conjunction)的基础上,加上动力因果联系而生成的规律。常见的物理、化学和(非演化论的)生物学定律都属于这一类。然而目的因果的规律不是从事件之间前后出现的稳定联系开始的,它们是以某个目的如何组织或统领某种类型的自然过程,个体在其约制下如何趋近该目的这样一种思维解释进路开始的。这是在动力因果的一阶科学解释进路之外或之上存在的一种二阶解释进路。这种一阶和二阶的关系在物理学中展示得最完美,那就是各个特殊力学系统的一阶动力因果律与二阶的最小作用量原理之间的关系。在那里,从二阶原理可以通过变分法推导出各个不同系统的一阶力学定律。
限于篇幅,许多相关的重要概念与问题无法展开讨论。比如所谓的贝叶斯理性与贝叶斯大脑的准理性是什么关系?本文试图论证的贝叶斯大脑类型的心智因果的演化与人类高级理性(如科技、法律、政治等领域的理性)存在是什么关系?在哲学上心智因果的存在一直是个争议颇大的概念,本文以何种理由默认它的存在?引入极值原理作为心智因果过程的自然规律,如何可以解决戴维森等哲学家提出的那些特殊的、展示反常一元论的例子?
简单回应一下的话,最后一个问题的解答在于,戴维森在寻找心智因果过程的自然规律时,显然是找错了方向。他所想要找到的是心智因果过程中的动力因果律。通过本文的论证,在那个方向上是找不到的。至于心智因果的本体论问题,哲学文献中有着诸多讨论,在此无法开启。感知或低级认知与高级认知之间,从演化博弈的角度存在什么关系,这个问题诺齐克与奥卡萨均有讨论。语言的出现与之后的文化演化博弈应该是从低级到高级认知转化的重要机制。另外,贝叶斯定律同时为动物和人类大脑执行能动推理、最小化预测误差的“自然规律”,同时又是人类认知、有系统地更新自己知识体系中各信念的概率权重的基本方法(贝叶斯主义乃科学哲学中关于科学方法论的一大分支),这是大自然中纯粹的机缘巧合吗?演化博弈通过自然选择到底是选择了理性还是准理性或非理性,对这个问题本文这样看待,演化博弈所产生的动物和人类感知或认知系统,是一种近乎卡尼曼(D.kahneman)所谓的“快思维”的系统。这种系统的机制和行为与所谓的“慢思维”系统的机制和行为同时存在于每个个体的大脑中。
一般可以认为,快思维系统是更加原始的系统,而慢思维系统是后来发展出来的高级认知系统。那么问题是快思维系统可以算作“理性”系统吗? 在传统的知识论与心灵哲学理论框架里,它应该不能算,因为系统产生的判断往往经不起(慢思维系统)推敲而不为真知,以及快速和便利的推理方法也常常出错。笔者认为动物和人类理性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近乎快思维那样的系统,而另一类则是慢思维系统那样的。第一类之所以可以被视为“理性I”系统,是因为它所用的低级认知方法和结果均为“近似真”和“近似正确”。它们对动物和人类的生存和繁荣起着不低于第二类“理性II”系统的作用。称“理性I”为准理性也可以,或者,如果相信贝叶斯主义,那么贝叶斯大脑赖以运转的贝叶斯原理(自然规律)是“理性I”的基本原理,而人们做科学研究所用的贝叶斯定理(科学方法)则是“理性II”的基本原理。但是,“理性I”与非理性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因为非理性是有损于个体与种群的生存和繁荣。过去哲学文献中所谓的理性与非理性之分,现在看来是粗略的。在它们之间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带,那就是“理性I”的地盘,或者说是贝叶斯大脑运行的领域。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莫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