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城市化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祖先的祭祀活动在其物质形态、功能与意义生产上的存续都面临挑战。本文基于宗教学物质性转向的视野,引入示能性理论考察闽南一个拆迁乡镇重建祭祀空间的实践。狮峰镇乡民在集体拆迁安置的过程中,经历了从乡村生活到城镇生活的剧烈转换,家庭中的祭祀活动在新的生活环境下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这种变异与物质空间示能性的变化密切相关,传统住宅与现代住宅以不同的空间示能性参与了不同形态祭祀活动的生成。鼓浪村乡民重建祖厝的个案表明,行动者受空间示能性限制、引导的同时,仍能自主性对示能性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基于更大范围空间的示能性展开,并以其为限度。同时,新示能性的显现以特定的文化为背景。当空间示能性的调整不能完全满足传统祭祀活动向现代空间的嵌入时,新的象征与诠释就被调用充当中介。在现代住宅空间内调整示能性重建祖厝的过程,也是列斐伏尔意义上“抽象的空间”出现裂隙、“差异性的空间”显现的过程,这有助于我们反思近些年来集体拆迁安置中标准化实践对于物质空间与伦理生活维系内在联系的忽视。
关键词:神安兹宅;示能性理论;闽南;祖厝
作者:洪哲泓,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宗教人类学、礼学,尤其关注身体经验参与宗教生活的意义生产并受到塑造的过程,目前正在开展一项有关本土基督教教会信仰生活的田野工作。Email:Philosophiahzh@pku.edu.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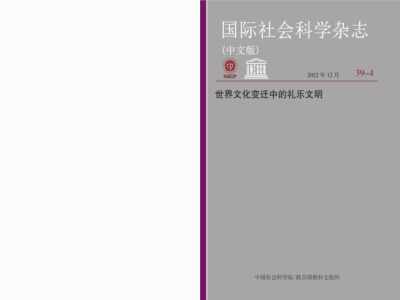
引言:社会变迁中的传统祭祀空间
本文讨论的祭祀空间指的是中国社会中围绕祖先祭祀建立的空间设施以及与之关联的一系列活动与社会关系,主要包括但不仅限于祠堂、祖厝、坟地等。这类空间大多经历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变迁并存续至今,其关联的意义与实践和前现代保持着某种连续性的关系。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社会关系与物质空间的形态都经历着快速变迁。在这一背景下,祭祀活动在其物质形态、功能与意义生产上的存续都面临挑战。对此,学者们围绕传统祭祀空间在现代变迁中的处境、反应与调试展开了研究。现有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针对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镇拆迁改造中祠堂的存续、整合与重构(陈壁生2014;焦长权等2015;袁振杰等2016;吴正运等2017;王杰等2020);另一种则关注“乡村振兴”背景下对农村祠堂等传统空间的现代改造,比较典型的是在政府推动下将农村祠堂改建为“文化礼堂”的实践(孙秀林2011;林敏霞等2016;靳浩辉2018;靳永广等2020;方菲等2022)。这些研究在地方语境下,以不同的程度生动地展示了作为传统祭祀空间的祠堂与行政权力、意识形态话语、资本以及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张力与互动。相当一部分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政府权力在传统祭祀空间重构中的主导性存在(焦长权等2015;林敏霞等2016;吴正运等2017;靳浩辉2018;王杰等2020;靳永广等2020;方菲等2022),政府权力首先是发展主义话语下空间变迁的规划者与推动者,在变迁过程中,它扮演了民众与资本间的中介者、部分改造项目的资金提供者、改造后空间的象征符号调用者与意义诠释者等角色。一些学者将政府主导下的空间改造视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理手段,尤其是在城乡间人口流动性增强、价值缺失、关系离散等情况下,起到整合秩序、纯化道德的效果(焦长权等2015;吴正运等2017;靳浩辉2018;靳永广等2020;方菲等2022)。应该说,这一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政府权力尝试结合传统社会文化资源开展社会治理的实效,但必须指出,该叙事很容易遮蔽传统空间中真正生活者所面临的“失语”危险。尽管在一些语境中,研究者采用“存续策略”(靳永广等2020)、“双名制”(靳浩辉2018)等术语描述民众与政府权力带着各自目的建立的共谋关系,但这一基于特定语境的情势并不能涵盖空间改造中的诸种权力关系形态。林敏霞和颜玲云(2016)的研究就注意到了官员与学者在“文化遗产”的建构过程中对于村民营造、阐释与使用空间的主体性的刻意忽视乃至压制。在一定的语境下,忽视与压制有可能导向各方围绕空间的物质形态、功能与意义展开的冲突,冲突未必以直接的、剧烈的形式表达出来,更可能是个人性的、偶发的“战术性抵抗”(袁振杰等2016;德赛图2009)。这表明,政府权力与资本所规划的“空间的表征”与个体感知生活其中的、活生生的“表现的空间”(列斐伏尔2021)之间存在着矛盾与裂隙。囿于田野场景的特殊性,有关村民“抵抗”的书写中(袁振杰2016),民众的行动更多是被迫的反应,而非主动建构。陈壁生(2014)对于潮阳县“城市祠堂”的考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力量之外的民间行动者从现代城市生活的特点出发调整祠堂空间与宗族祭祀的主体性,但在其田野场景中,通过建筑文物性质的确定、法人身份的申请等细节依然能够辨识出政府权力的强势在场。此外,在宗祠复兴的过程中,主导的力量也是掌握了较多社会资本与话语权力的精英,宗族中的“庶民”主要以被排除或纳入的形象示人。
上述研究中的有待商榷之处,极有可能是田野场景的限定造成的。研究者们对传统祭祀空间的关注,往往集中于祠堂、家庙这类较大的宗族性的祭祀空间。由于这类祭祀空间较大的建筑规模与所涵摄较广的社会关系范围,更容易在政府的治理活动中成为优先关注的对象。同时,在宗族关系中处于中心、集中了较多社会资本与话语资源的行动者在其中的活动也更为显著。然而,传统上除了这类大宗族的“庙祭”,也存在五服之内的规模较小的“家祭”,这就为本文的研究留出了空间。弗里德曼(2000,pp. 104-121)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中区分了祠堂内的祭祀和家户内的祭祀,从规范上说,后者不包括主祭家长五代以上的亡者,且不在家户之外专门另辟祭祀空间。作为祭祀场所的家户,在闽南语中又被称为“祖厝”。本文所关注的正是这类对象。
本文采用民族志的方法,针对闽南某镇集体拆迁安置中的传统祭祀空间开展研究。通过引入示能性的概念,描述并分析家户祭祀在搬迁前后遭遇的断裂、嵌入与再生,我将展示作为物质存在的空间如何参与宗教经验与社会关系的生成,以及个体如何调用观念与实践资源在空间的重塑中调整权力关系。我将首先基于对宗教学传统中的空间研究和晚近“物质性转向”的简要梳理,说明本文采用的问题视角与分析工具。随后,我将通过对于拆迁历史的简介描画田野场景的基本轮廓,在此基础上,进入到民族志的个案深描。最后,我尝试从田野案例出发,提出结合示能性理论与其他空间分析进路的可能。
“示能性”作为分析祭祀空间的概念工具
传统祭祀空间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神圣空间构成了宗教学的研究对象。早在宗教学的经典理论家那里,空间就已经是分析理解宗教现象的一个重要维度。这些主张具体各异,但都倾向于将空间视为某种更次级的存在:空间要么是特定生活方式的容器、要么是深层秩序的表征、要么是圣俗秩序的象征,空间实在性被还原到另一个层次上才能得到理解,实存的物质空间反而在有关论述中消融了。宗教学理论传统中这种将宗教视为某种精神存在从而不太关注其物质层面的倾向在晚近的研究中受到了诸多批评,研究者们提出应当将宗教视为某种同身体以及诸感官密切相连的物质性实存,由此激发了宗教研究中的“物质性转向”(Material Turn)。在宗教研究的物质性转向中,不同的理论从权力关系、现象学等角度重新考察宗教空间、图像、圣物等对象(Hazard 2013)。其中,受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等当代“物活论”(Vital Materialism)思潮影响,在物质性转向中又兴起了对其他进路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反思,进而强调关注在人类感官经验与意义诠释之外的物本身以及作为能动存在者的物在人类实践与意义生成中扮演的角色(Vásquez 2011, pp. 83-84; Hazard 2013; Morgan 2016, pp. 277-278)。本文针对祭祀空间的考察主要借助于这一思潮的视角,但并不排斥其他可能有益于增进理解田野事实的分析进路。
鉴于相当一部分针对传统祭祀空间的研究借助了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展开分析(王杰等2020;靳永广等2020;方菲等2022),我们有必要在此对其方法论资源作出澄清与检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所借助的理论资源同其的区别与联系。事实上,宗教学中物质性转向的思潮与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都可以视为20世纪后半叶针对主体哲学反思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两个“转向”共享了一些相近的立场与旨趣。在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中,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提出了空间的“三重性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生产进行分析:即“空间性实践”“空间的表征”与“表现的空间”,三者在实际中是彼此涵摄的辩证关系。应当承认,研究者们对于“三元结构”的套用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我们对于田野场景中具体经验的理解。然而,这种对于“三元结构”的套用很大程度上是以剥离列斐伏尔文本的语境为代价的,林叶(2018)基于对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整体脉络的把握和细节的梳理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重大误解。因此,本文并不主张直接使用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结构对祭祀空间进行分析,但列斐伏尔的有关论述依然对本文的思考具有重要启发,他提醒我们注意特定空间场所本身生产社会空间、社会关系的力量,而非将空间仅仅视为资本、权力与关系的容器(林叶2018,p. 135)。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与宗教学的物质性转向可以说旨趣相当。澄清了列斐伏尔思想资源的启发意义,我们得以引出构成了本文分析祭祀空间的关键概念:示能性。
现代学术语境中的示能性(affordances)概念可以追溯到心理学家吉布森(Gibson 1979),他提出这一概念用以刻画具有智能的生物同环境间的关系。在他看来,物质环境之于生物既不是容器,也不是完全起到决定的作用,而是“示能”,即特定的物质环境构成了生物以特定方式行动的可能性。吉布森意图通过这一概念在认识论上拓展某种克服主客二元对立的可能性。其后,示能性概念溢出了生态心理学的领域,在建筑学(Koutamanis 2006)、设计学(Kannengiesser and Gero 2012)、语言学(吴炳章2013)等领域得到了运用。在人类学研究中,示能性概念较早由英格尔顿(Ingold 2018)引入,他将示能性的刻画对象严格限定于客观的物理环境,意图为跨文化间的理解与互动提供一个实在的基础。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同样在人类学研究中引入示能性概念的基恩(Keane)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参见 Ingold 2018;Keane 2018)。基恩拓展了示能性概念所刻画的范围,他主张“不仅仅是物理对象,任何能为人们所经验的事物,诸如情感、认知偏见、身体运动、饮食方式、语言形式、传统教训或习俗实践等”(Keane 2014)都具有示能性。英格尔顿(Ingold 2018)则激烈地批判了这一拓展,他从概念史的角度质疑基恩拓展示能性概念的合法性。本文无意在此卷入两人有关示能性概念适用范围的争论,只是借助二人的讨论,对本文这一概念的运用进行界说。首先,本文对于“示能性”概念的使用并不限定于物理意义上的物质空间,而是在民族志书写中强调地方性的宇宙论知识等文化背景之于示能性显现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的立场更接近于基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祭祀空间中,这些非物理性的实存和物理空间一样,它们与行动者之间不是强迫与被强迫的关系,而是与行动者的选择密切相关。其次,本文试图在书写中展示示能性生成的情境性,意即示能性并不是现成自在的,而是在特定的关系中生成的。从而,在一个具体语境中,示能性所指涉的内容具有流动性。
因此,在问题视角上,本文承接了宗教学研究中的物质性转向,引入示能性的概念,考察拆迁安置中的祭祀活动,着重关注空间等要素的示能性如何作用于祭祀活动。有关祭祀活动在现代居住空间中遭遇阻碍的讨论,与列斐伏尔理论的批判意图相近,而行动者与空间在特定语境中的互动所产生的示能性则指向了列斐伏尔所期待的“差异性的空间”。
安居到流离:狮峰镇的基本情况与拆迁再安置简史
为方便下文论述的展开,我们在此先简单介绍这个搬迁乡镇的基本情况。狮峰镇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的漳浦县。在漳浦县南部的沿海地带,一条狭长的半岛向南延伸入海。半岛南端与铜山岛及其附属列屿隔海相望,构成海门,海门以北为铜山湾内海。从半岛北端南行,地势平坦开阔,行约十余公里可见一座山拔地而起,当地人将这一景观称为“平海出高山”,这就是狮峰山。狮峰镇以山得名,占据半岛大部,全镇下辖13个行政村,共计35个自然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农耕与渔业是狮峰镇乡民主要的经济来源。狮峰镇的耕地以沙质土壤为主,主要的粮食作物是甘薯,也大量种植花生。市场经济恢复后,芦笋、萝卜等蔬菜的种植得到发展。渔业方面,以海水养殖为主,捕捞次之。大约2003年前后,有外地资本到狮峰镇投资建立鲍鱼养殖厂,但连年亏损,之后撤资。直到拆迁之前,除少数外出务工者外,狮峰镇乡民的生活基本上围绕山与海展开。在这里,山海田园的安逸景象与其说是自然的赐予,不如说是祖辈肇基创业的成果。根据地方志记载,狮峰半岛旧时环境恶劣,植被稀少。风沙问题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十分严重,后通过在沿海地区大量种植木麻黄防护林才获得改观。由于半岛地表缺乏河流,生活与灌溉用水需要通过打井解决。因此,对于狮峰镇乡民来说,狮峰镇的地理空间并不是单纯的自然环境,而是凝聚了祖辈同环境磨合的艰辛历史,与乡民的自我认同密切相关。
表面上看,在这样一个远离县城与市区的偏僻小镇,安居生活似乎能一直持续下去。但剧变的种子早已埋在这片土地之中。狮峰镇半岛南部西岸是天然的深水良港,天然航道港口可供万吨级船舶通过停泊。这一自然资源并不能为乡民的生产生活直接利用,但在现代化的发展话语中却意义重大。早在20世纪80年代,地方政府就在港口建设的国家立项上做了大量工作,使这一资源进入到发展规划者的视野中。2000年后,地方政府开始了一系列运作,最终在2006年由省政府批准成立了“福建狮峰港口经济开发区”,后经国家发改委公告确认。2003年前后,厦门市海沧区一个规划中的XP石化项目由于遭到市民团体的激进反对,最终未能落地。迫切需要发展工业调整经济结构的地方政府承接了这一项目。该项目最终决定在狮峰镇开工建设,拉开了狮峰镇集体搬迁的序幕。最初落地的只有一家台资企业,拆迁村舍也仅涉及杏花村和附近的几个自然村。然而,港口经济开发区很快又被规划为石化炼化一体的工业区,大规模引入石油化学工业。自此,全镇皆被纳入拆迁范围。随着通知的下达和前期工作的展开,狮峰镇乡民似乎很快地接受了这一事实。虽然发生过几次群体性事件(狮峰镇乡民到县政府门前静坐),但主要诉求也是涉及赔偿方案的问题。乡民关注的焦点不是搬与不搬,而是如何在搬迁中最大程度获得利益。占地、抢建、搭盖开始逐渐占据狮峰镇乡民生活的中心。由于先前的许多家产、族产、承包的土地滩涂与海洋资源的划分并不明晰,拆迁赔偿却明确要求进行产权意义上的分割,短时间内也引发了大量的家庭、家族矛盾。
赔偿协议基本签订后,狮峰镇乡民逐步获得赔付,并准备迁入新居。在紧邻狮峰镇的南浔镇,一片高层住宅楼群拔地而起,作为狮峰镇居民的集体安置社区,该社区被命名为新港城,配有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乡民所获赔偿,主要包括购置新港城住房的产权指标和一次性支付的现金。对于很多人来说,拆迁可谓是“一夜暴富”。与巨额的财产增长相伴随的是背离传统道德伦理的失范现象。大约在2014年到2016年,漳浦县开始流传起一个名称标签与所指群体——“峰哥”:一些获赔巨额现金的狮峰镇男性开始频繁出入夜场等娱乐场所,进行娱乐与色情消费,为县城与集镇的餐饮业和灰色产业贡献了大量流量。部分女性由于无法承受丈夫或儿子违背传统道德、抛弃家庭,选择自杀。“峰哥”的标签多少有污名化的色彩,但这一时期许多狮峰镇人缺少节制的消费却是事实,新港城与南浔镇上的KTV与洗浴场所也是在这段时间内扩张增长的。也是同一时期,非法集资与金融诈骗在狮峰镇时有发生。一方面,传统用以耕作和生产的滩涂已经被征用,狮峰镇乡民失去了原有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政府在安置上没有对乡民的就业问题予以充分的关注,新港城缺少配套的产业承接狮峰镇的劳动力,也没有组织合适的职业技能培训;再者,从乡民的主观态度上看,不少人认为劳苦多年,今后不愿意再从事劳动,用当时很常见的一句话说:“这世人再也不用做了(这辈子再也不用干活了)!” 手握资金的狮峰镇乡民希望过上食利者的生活,一时各种“投资产品”风起,各路“理财专家”涌入新港城。事后证明,其中绝大部分是非法集资与诈骗。参与的乡民不仅本钱无归,有的还背负债务。鼓浪村有一位村医,拆迁前通过经营卫生所过上了殷实的生活,拆迁中也获赔巨额款项,但在之后的“投资”中,却被卷走款项一千余万,并欠下债务。如今,这位医生重操旧业,从头再来。类似的例子在狮峰镇还有很多。2015年到2017年间,新港城的街道上到处悬挂着警惕非法集资、防范金融诈骗的标语,相关情况引起了执法部门的关注。这些失去资产的人,或外出务工,或到临近乡镇做养殖工人,作为劳动力重新进入了市场。
总之,集体搬迁使狮峰镇在短时间内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迁。传统的宗族、家庭关系在财产分割的过程中遭遇撕裂,旧有的道德观念在财产的急剧增长和消费黑洞中瓦解,个体从以家庭为中心的劳动经营中剥离出来成为个体化的劳力,独自面对市场与资本。我们无法全面展示或细节剖析狮峰镇社会变迁的方方面面,只是在此略加刻画,将其作为我们理解祭祀空间演变的基本背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意义上祭祀空间的重建,都不仅仅是一种惯例的移置或恢复,而应理解为伦理关系拉扯、断裂、再连结与重构的一部分。
魂归何处:现代居住空间中的祭祀活动
如上所述,狮峰镇在相当短的时间内遭遇了剧烈的社会变迁。在居住空间上,变迁集中体现为从传统乡居转向密集的高层住宅社区。下面我们通过分析作为建筑空间的祖厝与现代高层住宅所具有的不同的示能性,来考察这一变化对狮峰镇祭祖活动带来的影响。
除个别大宗族外,祖厝(而非通常意义上的祠堂)才是狮峰镇乡民祭祖活动的空间。祖厝在最初建立时并不是专门的祭祀空间,它通常是各家共同祭祀的祖先遗留的家居,一般由肇基祖先的嫡子一脉继承。在春节、清明、中元、冬至、忌日、春秋二祭(四月初一、十月初一)这几个节点,各家代表会聚集到祖厝进行祭祀。在集体迁入商品房的过程中,出现了祖厝较远祖先牌位被遗弃的现象。根据鼓浪村退休教师洪穆的观察:“近一些父母、祖父母辈的牌位还有人要,祖父母辈以上的就少有人要了。” (访谈,2022年5月7日)在农村家屋中安然供奉的远祖牌位,在现代楼房中却失去了立足之处。除了拆迁过程中由于财产纷争而引起的家庭矛盾以及观念淡漠等潜在的原因,现代住宅空间不同于传统家屋的示能性就与祭祀活动构成了紧张关系。
我们从那些进入楼房的牌位与香炉的情况,可以一窥祭祀活动在现代住宅空间遭遇的阻碍。这首先体现在空间整体的几何结构上。在传统家屋中,厅堂的正中处要么放置近一人高的供案,要么放置高度相当的橱柜,祖先牌位或遗像安立其上,电视等家电、茶几桌椅等一般靠厅堂两侧摆放,从牌位前到厅门、中庭与院门中间留下了相对空旷的空间与通透的视野,子孙仰视牌位,牌位俯视子孙的饮食作息,其在场构成了家屋空间的神圣中心。现代楼房的设计与建筑结构使得传统上安放祖先牌位的方式无以为继,牌位“不知道怎么放”:传统家屋中,厅堂与家屋整体朝向一致,“三间两伸手”左右对称的布局以及从院门到厅堂贯通的中轴,使得厅堂几何中心的位置十分明确,同时,厅堂的几何中心也构成了整个家屋的中心,家屋也在传统风水知识的指导下与建筑外的自然人文空间连接在整体的秩序格局下;而在现代高层住宅中,虽然房型的设计也有相对固定的版式,但客厅与房中其他空间的组合方式与楼房的整体朝向并没有确定一贯的关系,客厅与门户、客厅与其他空间缺乏一贯的轴线或对称关系,客厅并不像传统的厅堂那样能够在整体的建筑空间中得到明确的中心定位,客厅的中心并不构成整体住宅的中心,家庭住宅内部各别空间、家庭住宅整体的秩序与家庭住宅外的世界之间并不构成一个秩序上的连续体。其次,现代住宅空间中,客厅的空间示能性指向一个核心家庭在劳动生产之外私人的“休闲”(消费)活动。搁置客厅在整体房中的位置不谈,现代住宅客厅的空间示能性也并不导向放置祖先牌位的行动:预先铺设的电视闭路线与网线确定了客厅内的空间定位,有线路铺设的一侧被设定为前方,其正中将为电视所占据。这一线路铺设引导居住者在相对的位置上放置沙发、茶几,从而将客厅呈现为现代人的私人休闲时空,区隔于工作身份的休闲消费行为在其中得到鼓励。因此,在乡民与现代住宅空间遭遇时,后者并不直接提供重建一个传统上人神共居宇宙的示能性。在搬迁后现代住宅的客厅中,搬迁后的乡民很难像在传统家屋中那样通过放置供案或橱柜将祖先安顿在居高临下的正中位置。对此,不同的家庭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妥协方案:有的家庭中,牌位或遗像就委身于电视下方不及膝盖高的柜子一侧;稍不敢怠慢者,会购置大一些的神龛放置在过渡厅或餐厅,在供奉神明附近的位置安置先祖;更重视的家庭则会在家中专设一室用来供奉牌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家中有兄弟数人的家庭共同祭祀祖先,由于另辟祭祀空间实际上压缩了专室所在家庭的居住生活空间,同时也可能是为了表明于祭有份,那么几个家庭会就专室面积相当的房价进行分摊。无论是哪种方案,在楼房之中,祖先牌位都不再处于空间的中心。或放置在电视侧下方,或并置于他处(譬如厅侧、餐厅)的神龛,祖先牌位都趋于边缘。设立专室的做法虽然没有直接削弱祖先牌位的神圣性,甚至看起来还表达了对祖先更高程度的崇敬,却将祖先与子孙的生活空间相分离,使祖先从子孙饮食起居的生活视野中淡出,在日用作息、饮茶闲叙的活动中,祖先不再始终在场。
在传统家屋中,牌位等祭祀时的敬拜对象在空间上并不是一个与生活其他领域相分离的部分,在搬迁进入现代住宅后,祭祀对象在生活空间上的分离以及分离后同住宅中其他生活空间的组合关系所呈现的示能性,限制乃至阻碍了家户祭祀的开展。由于祖厝的祭祀至少包含两代(父—子),上可至五代(高祖—玄孙),在惯习的作用下还可能溢出这一范围,加之计划生育之前较大的生育规模,每一次祖厝中的祭祀就意味着多个核心家庭的聚集与共同活动,这就要求空间能够容纳相当规模人群和共同活动的展开,同时还不能对家庭空间内的正常生活产生过多干扰。在搬迁前的狮峰镇,这并不是太大问题。一是存在部分祖厝由于年代久远,生者迁出另建居所,旧居辟为专门祭祀空间而无人居住的情况,祭祀活动并不对家庭生活的环境和家庭成员的日常活动造成直接影响;二是即便祖厝有人居住,祖厝相对开阔的厅堂、中庭也能够容纳多个家庭聚集和活动(通常是各家的妇女和晚辈将各自带来的成叠纸钱拆分成张,以便焚化,印有银箔的成叠银纸则要用拳头按压住中心旋转,最终呈现为圆形),传统闽南民居中“两伸手”的布局使得居住者能够在厅堂中庭人群聚集的同时,相对不受影响地从厨房、餐厅一侧的通道出入住宅;三是群聚的祭祀活动可能给家庭生活带来的直接困扰是卫生问题,因为金银纸钱的焚化、鞭炮的燃放会带来纸灰纸屑,而在中庭焚烧、门前燃放基本能够避免纸灰纸屑大量飞入室内。并且,在拆迁前的农村,并没有城市居住空间意义上的清洁观念与实践,由于农具或收获物的堆放、下地下海劳动等原因将泥沙水渍带入住宅内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因此,焚烧金银纸钱产生的纸灰与尘土在传统家屋中并不如现代房屋的居住者看来那样异质。除了观念的因素,农村住宅中常用的土砖和整体较为昏暗的采光与照明也是原因之一。用红土烧制的土砖表面粗糙、吸水良好,这使得灰土和污渍不像在现代住宅中常用的大理石地砖、木地板上那样显眼,相对昏暗的采光与照明更强化了这一点。铺设材料与屋内光亮度的示能性指向的是一种相对有限度的清洁观念与实践,从而削弱了祭祀活动中人员聚集、出入踩踏与金银纸钱焚化给生活环境和家务负担的负面影响。在现代楼房住宅中,情况则大为不同,搁置主人的清洁观念不论,高层楼房难以为大规模聚集的祭祀活动提供场所,十几人、二十几人同时进入其中,准备放置供品、拆解纸钱就会占据很大的空间,在阳台上焚烧银箔纸钱除了可能造成的大量纸灰涌入屋内,还会给上下楼层的邻里带来同样的困扰。现代住宅空间的光线明亮度和室内装修材料表面的光洁度带来与传统家屋不同的示能性,原本不起眼的灰尘与污渍会变得十分突兀,从而导向另一种清洁观念与家务劳动实践,焚化的纸灰也就构成了困扰。而在一年之中,除了除夕、春节、正月初二、清明、中元、冬至等节令之外,另有忌日与春秋两祭,如有乔迁、嫁娶、升学之事,亦需祭祖。因而,安放曾高以上牌位的家庭将在搬迁后面临较大的压力。由于这种潜在的压力,加上拆迁前后基于财产分割产生的家内矛盾,一些家族在搬迁之后不再祭祀或不再共同祭祀曾高及以上祖先。就我在田野中的了解,不愿共同祭祀的家族,一般有如下两种处理方式:(1)牌位保存在嫡长家中,旁支不再祭祀,或以钱款委托的方式“交代”祭祀;(2)兄弟、族人以瓜分祭祀相关物品的方式,分开各自祭祀:例如港尾村,有一家兄弟三口因拆迁赔偿中地产分配不睦,不愿共祭,分别取父祖的牌位、香炉、遗像回家各自祭祀,还有的情况是,模仿民间信仰从神明香炉中分香灰以示分灵的做法,从祖先香炉中捻取香灰回家各自祭祀。
从乡村进入到现代社区,祭祖传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断裂,但也没有被彻底抹去。传统存留的部分,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到新的空间之中,祭祀活动的样态以及社会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异。通过对新旧空间不同示能性的描述与分析可以看出,不应仅仅将祭祀样态的变化视为拆迁过程中社会关系变化自然而然的“表征”,现代空间的示能性参与引导了变异的发生。同时,尽管本文侧重于分析新旧空间示能对于祭祀活动的引导,但必须指出,祭祀活动在现代空间中的延续,就表明了牌位、香炉等物件引导“放置”的示能性。搬迁后的祭祀活动不是现代住宅空间示能性单方面引导的结果,而是行动者在多种示能性下情境性的实践。而对现代住宅与传统家屋的分析也表明,示能性并不是一个客观自在的物理属性,它在特定的权力关系与文化语境中显现,从而包含了实践的历史性维度。现代住宅的空间布局与管线设置引导现代个体休闲消费行为的示能性,是资本与规划者想象与设置的结果,这一示能性在生活场所与劳动场所分离、家计与社会劳动分离的社会场景中才显示并具有意义,而传统家屋示能性的显现则与传统乡村的生产生活、习俗观念密不可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示能性并不如英格尔顿所主张的那样纯然限定于客观物理的环境,示能性在特定语境中显现的过程就已经将异于物理的内容囊括于自身之中了。因而,示能性也是一个可能在不同文化语境的实践中得到调适的范畴。
下面我们通过对狮峰镇鼓浪村一个在楼房中重建祖厝案例的深描,更为细节地展示狮峰镇乡民在祭祖传统嵌入现代社区过程中,在实践中调适空间示能性的努力。
神安兹宅:现代居住空间中的祖厝重建个案
2014年初,狮峰镇的拆迁赔偿工作进入收尾阶段。除了少部分乡民拒绝搬迁,大多数人都签署了搬迁赔偿协议。按照计划,第一批次的狮峰镇乡民已经迁入了“新港城”的一期“福晟”社区。鼓浪村的大部分居民则是在第二批次迁入新港城的。在临近搬迁日期的前些日子,鼓浪村退休教师洪穆家中开始就搬迁后的祭祖问题进行商讨,讨论在兄弟、族亲四散居住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安放牌位,如何进行祭祀。兄弟姊妹七人中,洪穆为长兄。兄弟之中有三人在体制内工作,洪穆是鼓浪村的小学教师,退休前任校长职位,二弟洪仁、四弟洪昭分别在县城的机关、国企任职。三弟洪愍早年曾外出务工,后来回本地从事零工,五弟洪瑞在拆迁前一直从事渔业养殖,六弟洪茂多年经营海鲜生意,妹妹洪敏在家务农。其中,洪瑞十分热心于村中的真武庙祭祀以及与外地洪氏宗亲的联络。洪穆兄弟一家是鼓浪村中较为重视祭祖并十分强调祭祀“慎重追远”礼义的家庭,洪穆曾经多次在祭祀当日的聚餐和子孙聚集扫墓的场合,向在场的晚辈不厌其烦地讲述先人肇基创业的历史,强调祭祀重要的不是求取福佑,而是子孙饮水思源的本分。讲述先人劳作艰辛,同样也是其他兄弟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内容。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与受教育水平有关,例如洪穆、洪仁、洪昭三人就更乐于也更擅长在家人晚辈聚集的场合进行说教。不过,三人的学历不应仅仅被视为他们个体努力的偶然成果。在鼓浪村,像洪穆兄弟这样,有多达一半子女通过高考完成社会跃迁的农民家庭并不多。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洪穆父亲承欢公的教育观念和艰辛持家。承欢公为家中独子,自幼体弱,但十分好学。由洪穆家中承欢公遗留的私塾课本、书画作品以及笔记述作可以推想,承欢公早年在旧式私塾打下教育基础,其后仍孜孜自学不倦。据洪穆回忆,承欢公的教育经历使其在鼓浪村中经常担任礼生的角色,婚丧嫁娶等场合,多需要他来主持安排仪节,撰写请帖祭文。谨于礼,大抵也构成了洪穆兄弟成长背景的重要底色。承欢公的经历使他特别重视子女教育。无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前还是之后,只要中断孩子们的教育,让他们参与生产队计算公分或发展养殖,家庭经济情况都会大为改观。但他坚持让6个儿子都接受教育,为此夫妻二人独自劳作,较其他家庭辛苦数倍。直到后来洪仁、洪昭到另一镇上念高中,且复读多次,家中经济难以为继,才被迫中断了洪瑞、洪茂的学业。洪穆兄弟在讲述“慎重追远”的意义时,习惯通过回忆父辈的这段历史加以说明阐释。承欢公留下的记忆,既是洪穆兄弟重视祭祖、向晚辈讲述祭祀意义的动力,也是他们所讲述礼义的注解。在面对剧烈变动的环境时,承欢公以身行遗留的教训,构成了洪穆兄弟主动应对变迁的信念基础。同时,洪穆兄弟通过教育完成的社会跃迁也为他们在家族中赢得更多的话语权,使得他们能够将这一信念贯彻推展到对高祖的祭祀上,从而在众人搬迁散居的境况下做到“收族”。
从宗族关系上说,洪穆兄弟一支若从其曾祖数算,并不是曾祖嫡传,但他们却在推动新祖厝的建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根据承欢公晚年遗留的家谱笔记以及洪穆后来的补充整理,我们在此简单梳理一下洪穆兄弟家族的情况。现今洪穆家谱中行状可考且坟茔可寻的,是洪穆兄弟的曾祖马成,曾祖马成是洪穆兄弟高祖“六世祖”之长子。曾祖马成与曾祖母林氏育有六子,按长幼分别为万谨、大略、万字、万宝、万寿、万忠。承欢公为次子大略之独子,故而洪穆兄弟一家实为曾祖马成之次房。此外,曾祖马成有一弟,为曾叔祖乌房,乌房育有一女本月,招南昭入赘为后,膝下五子,又各育五子。在搬迁之前,洪穆兄弟一支需要祭祀的祖厝共有三处:一处为洪穆兄弟六人的祖厝,供奉祖父母、父承欢公;一处为万谨一系后人居住,厝中供奉高祖“六世祖”、曾祖马成、伯祖父万谨、堂伯甘顺;一处为南昭一系后人管理,供奉曾叔祖乌房及其后诸族叔。如果严格按照宗法原则,万谨一系才是嫡传,在祭祀的问题上理应主持大局。但在实际生活中,基于宗族原则的话语权可能在一些情况下变得相对有限,而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文化程度等其他因素则会产生影响,加之教育的不同使得他们对于祭祀活动的理解与重视程度也存在差异。由于明确地意识到搬迁后四处散居、分开祭祀的情况可能对家族团结带来冲击,洪穆兄弟与南昭一支同辈的洪明经过讨论提出,应当在搬迁后专门购置一套房产作为祖厝。并且,祖厝所安放的神主不仅限于本支,还应联络另外各支族人,将诸祖合于一处共祭。最终,由洪瑞出面进行联络,提倡共同物色房屋作为祖厝,将各家祖宗集中到堂中祭拜,以起到敬宗收族、联络感情的作用。
提议很快获得了响应,大多数家庭同意购置祖厝,并将具体事务交托洪瑞办理。对众人来说,合处共祭可能是一个新处境下比较妥当的解决方案。洪穆一族中,曾高两辈祖先的祭祀最多时有二十二个家庭一同参加。如上文所述,如果在单个家庭的住宅中进行祭祀,就将给这个家庭的生活带来较大的影响。事实上,在开始时,南昭一系也有族人不愿其他族人登门祭祀,想通过分炉灰的方式解决问题。对此,洪瑞和洪明坚决反对,南昭一系的其他家庭也很不满,因为分炉灰的做法通常适用于神明祭祀,却不适用于祖先祭祀。在众人的压力下,这位族人最终勉强同意了新祖厝的计划(访谈,洪瑞、洪明,2022年5月27日)。
其时,第一批搬迁安置已经完成,除部分乡民未签约搬迁协议或未接受集体安置房、以钱款的形式取得赔偿外,第二批搬迁安置的乡民基本选定了新的住所。故而,可供选择的空房比较有限。洪瑞和洪明走访多处,都没有找到满意的处所。事实上,如果仅仅是购置一处空间安置牌位,新港城内还有一些48平米的小户型能够满足需求。但是,洪瑞和洪明认为,既然要共立祖厝,就应当秉持重视的态度,尽可能地使新祖厝合乎规制,不可随意敷衍。在他们看来,多数48平米户型的商品房存在太多问题:(1)这些房屋楼上楼下都有他人居住,是“上无天,下无地”,上无天显得压抑,下无地则是“虚”,两者对祖先都不够恭敬;(2)大多东西南北通透,而祖厝中供奉祖先的位置“要阴”,背后和左右两面不能有窗户,对这些窗户进行封堵工程量太大;(3)房屋的平面格局左右不对称,安放牌位的主位、朝向和门户的相对方位关系很难处理;此外,还存在焚化金银纸钱的问题,除了前文提及在阳台焚烧的卫生问题与安全隐患外,如果移到楼下小区空地上焚烧,既麻烦,又有误祭孤魂的嫌疑——传统上,焚化给家内祖先的金银纸钱都要在家屋范围内进行,中元对于孤魂的济度由于在家户外进行,又叫“拜门口”。在洪瑞和洪明寻找新祖厝的过程中,现代商品房空间的示能性构成了阻力。农村中以祖先神灵为中心的祖厝空间观念,在试图嵌入这个围绕私人生活(“私”,通过与家计分离的生产活动相对立而得到界定)建构的物质空间时,表现出了种种“不适”,物质空间一再引导着观念与实践的变异。
几经寻访,洪瑞和洪明最终在较早完工的“福晟”一期找到了较为合适的房子。在洪穆兄弟看来,这里的房子用作祖厝算是比较合适的:安置房内的其他房型,一般开门就是楼梯间或狭窄的走廊,正对他人门户,这套房子则在进入楼梯间之前的过渡露台上,正门前是宽敞的露台空间,这可以为族人聚集、焚化金纸提供空间;房屋的平面是一个规正的矩形,前后左右对称,便于神主位置和方位的确定;更关键的是,房子坐东朝西,露台之下直到小区的边界都是绿化用地,没有高楼遮挡,远处的梁山主峰在视野中通畅可见。梁山是漳浦县境内的主要山脉,位于漳浦县城西南方向。洪仁就认为,祖厝开门可见梁山,“气场很通透,不会闷得慌,而且梁山看起来就和笔架一样(对子孙后代读书好)。”(访谈,洪仁,2022年5月25日)。在安置住宅的空间规划中,远处的梁山本来和住宅空间内的活动没有什么关系,但在洪穆一家寻找祖厝的过程中,梁山山峰的物理形态在行动者的感知中得以凸显,通过象征化,原本与地方性宇宙割裂的现代建筑空间又被重新建立起了关联,这种接入与家族整体生命的轨迹息息相关。同时,这间房又属于小户型,面积约50平方米,复式构造,恰好能够满足祭祀活动的需要,又不显得过于铺张。不足之处在于,它仍旧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上有天下着地”,对此洪明自己提出了一个解释试图化解这一问题:(1)经过阶梯直通露台,不用经过楼下的店面门口,也算着地;(2)楼上虽然住人,但门前露台开门见天,也算有天。此外,这套房子整体较为低矮,且一层在建设时已经分割为厨房、客厅、洗手间三个空间,如做祖厝,仍需要进行改造。
之后,洪瑞说明了这处房产的情况,众人基本没有异议。但到涉及购房问题时,却出现了一些风波。拆迁赔偿中,原先的三处祖厝都获赔相应的产权指标,这些指标可以在新港城用更便宜的价格购置房产。原先,洪瑞和洪明倡议,从祖厝赔偿的指标中划出一部分购置新祖厝。但万谨与南昭两处祖厝的实际居住管理者都默不作声,因为如果以指标进行赔偿,并用指标购买新祖厝,那么他们就少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他们独自签署了以现金赔偿的协议,用产权指标共同购买的计划不了了之。新祖厝的计划陷入了僵局。
最后,洪瑞用自家迁入安置房后剩余的产权指标购置了房产,再由众人平摊支付。房头按照与洪穆兄弟同辈的男性族人数算,除万寿一系出后他人不愿共祭之外,共十五个房头,每个房头2.6万元人民币,用以支付房产和装修的费用(访谈,洪明,2022年5月27日)。对于洪瑞来说,这一决定并不合乎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因为这部分指标既可以用来扩大居住面积、改善居住条件,也可以用以购置店铺投资,用来购置祖厝实际上牺牲了相当可观的潜在收入。并且,他用产权预先购置,也面临着一部分人不愿支付的风险。如果洪瑞不愿做出牺牲,新祖厝的计划很可能就此搁置,因为不使用安置的产权指标购房将使各个房头的支出大为增加,而并不是每个家庭都愿意在祭祀和家族的延续上付出不菲的开销。但是洪瑞坚持父亲承欢公身行的遗训,他的兄弟们和其他族亲对传统观念的持守也给了他决断的底气。在嵌入现代社区的关键时刻,基于家庭教育的观念传承与个人伦理决断的勇气成全了传统的惊险一跃。
由于既有空间格局并不适配于传统祭祀活动,房产购买后,随即按照祖厝的要求进行改造。一层内部的所有隔断都被去除,部分电线、管道也根据需要重新改线。正门进行了扩大,原先面积较小的单开门被改成了更接近传统样式的双开大门,使神主正前方的视野开阔通透,同时也便于祭祀时人员出入。东面壁原本有通向阳台的侧门和窗户,现今一并堵死,以保证神主所在处阴凉昏暗,没有风吹日晒,合乎传统祖厝的规制。在洪穆兄弟、洪明等人看来,这些改造并不是对传统样式的死守和生硬移植,而是带有伦理情感的举动,他们在谈论新祖厝时,反复说的是:“买一套房子给祖公们住。” 祖宗的牌位、香炉与遗像并不仅仅象征灵力的“物”,也不是俨然与生者相别的陌生神灵,而是有着近乎生者的感受,需要用舒适恰当空间安顿的亲人,需要将心比心的体贴对待。既然是给祖宗们买房子住,那就不能只图自己祭拜祈福的方便,随意放置,敷衍了事,而要将祖宗们视为有知觉、有感受的“如在者”,考虑其可能的感受。而对于祖宗可能感受的推测,是以生者在空间中在场时的身体经验为基础出发的。
根据洪仁的提议,也经过族人的同意,祖厝命名为“思源堂”,取饮水思源之意,并制作悬挂牌匾。2015年2月9日(农历甲午年腊月廿一),祖宗们的牌位、香炉、遗像迁入思源堂,日期为村中真武庙卜问所得。当日,各家从鼓浪村驱车接祖宗上楼。牌位、香炉、遗像置于春盛中,用盖封闭,转运全程由一人双手捧住。进入思源堂后,仍保持封闭状态。直到腊月三十祭祖时请出,依次列位,正式迁入思源堂。其后,族中祭祀无论大小都在此进行。
通过洪穆家族重建思源堂的前后经过,首先应当看到,定位祖厝的行动受到了超出建筑的、更广阔范围上空间示能性的引导,这种引导是以身体在空间中的经验为基础,在地方性宇宙论知识的特定文化背景下得以实现,身体在场和文化语境共同构成了示能性显现的情景。洪瑞、洪明二人为新祖厝选址的过程中,东南西北与上下的空间方位是引导他们定位合宜选址的重要因素。我们不能将这个过程简单用象征符号—意义的机制加以解释。空间方位固然可以充当象征符号,但在狮峰镇乡民活生生的生活经验中,它首先关联着对于通风、明暗、冷热、干湿等环境因素的身体经验。在此基础上,具身性地理解和运用诸如“气”这类带有文化差异性的观念。例如,楼层太高或者背靠江河湖海等水体,容易让人感觉太“虚”,楼层或者地势太低,则可能让人感觉“湿气”太重,临近树木、地势、高层建筑受到遮挡则带来气场不畅的感觉。这些经验既不是单纯物理—生理的,也不是单纯文化的,而是以身体经验为基础,渗透着文化意义。洪明等人用“买一套房子给祖公住”理解重建祖厝这一活动,并在祖厝的选址、改造之中以在场的身体对于明暗、高低、通风、“气场”通畅与否的感受来把握和确定空间的合宜性。这表明,空间对他们而言首先呈现为身体的经验,这种经验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显现为限定或引导祭祀活动的示能性。对于空间方位的把握不是从象征符号到意义的过程,而是意义在身体经验中显示的过程。这同样适用于洪家对于梁山的理解。首先,梁山和“子孙后代读书好”之间的关联有其实在论的基础,即地方宇宙论意义上、包含在自然地理景观中的生机力量。其次,梁山这一地理景观所能产生的意义,是以其在视野中的出现为基础的。洪仁强调梁山的可见性,而非其和祖厝方位的相对性,这意味着洪家同梁山这一文脉建立关联的方式,不是通过抽象意义上的空间方位与景观的符号性,而是身体在场的感知。只有当洪家人在祖厝门口能够以自己的身体感知梁山的在场时,地方性宇宙中的生机力量才和祖厝、家族成员的整体生命节奏(“子孙后代读书好”)建立起联系。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洪明“买套房子给祖公住”这一句话以及与之相关的实践,正是这句话中蕴含的子孙以身体感受推想祖先感受的行动方式,提示我们注意,祖先、祖厝和地方性宇宙的关联,是通过生者的身体经验实现的。与此同时,身体对于特定经验的感知并不是纯粹生理性的,诸如“上无天,下无地”“湿气”“气场”等经验,都有赖于地方性的文化背景。因此,行动者在现代建筑空间内找寻并不是一种单纯根据观念构想的行动,而是在更大范围意义上的空间(包括东西南北上下的物理空间方位、梁山景观的物质性存在)中进行感知、辨识与定位。这种空间示能性在在场的身体经验触发地方性宇宙论知识调用的情境中才得以显现。
其次,空间示能性在实践中调整改变,调整改变在既有空间示能性的基础上展开,循其条理,受其限制,这个过程可被概括为“琢磨”。如前所述,现代楼房的居住空间在规划者的构想中,示能性导向的是私人性的休闲与消费。但在重建祖厝的过程中,由于对住宅空间功能与意义的不同理解,洪家对于空间的物理存在进行了改造实践,从而使原本不具备引导祭祀活动的示能性的空间,转而适配于祭祀活动。这表明,空间的示能性不是自在、固定的属性,一方面示能性引导人的实践行动,另一方面人也在实践中调整示能性,使空间示能性合乎意图中的活动。这并不意味着人的行动相对于空间的绝对自由。相反,调整空间示能性的需求就表明了,特定的社会活动总是有赖于空间示能性以凸显其具身性。并且,调整空间的示能性在本案例的语境下也意味着调整空间规划者与空间生活者的权力关系。空间规划者试图通过空间规划引导的活动(私人意义上的休憩)在这里出现了裂隙,规划者想象中同质化的居住空间在示能性的调整中崩解,走向差异化(本“不应该”出现在现代居住空间中的祭祀)。调整示能性的实践是以原先空间的物质存在为前提与限度的一种“琢磨”,我在这里使用“琢磨”这一传统语汇,意在引入“文质”的语义,从而避免将特定文化语境中示能性的生成理解为一种“无中生有”的、形式施加于原初质料的“建构”。一方面,对示能性的“琢磨”包含了主体的意图;另一方面,这种意图又不可能超出既存现实的纹理。在本案例中,我们容易将祖厝重建看作是对于现代住宅空间同质性规划秩序的挑战,但往往忽略了,这一挑战的可能性仍然是由现代住宅空间具有的独特示能性所支撑的:正是现代商品房内部空间相对自由的可重构性这一原本导向现代人个性化定制生活需求的示能性,使得洪瑞等人有可能将空间调整为基本合乎传统宇宙论秩序的格局,封闭内墙,制造出合乎祭祀活动需求的亮度与氛围。同时,现代住宅高度的集约性也限制了这种调整,他们不可能真的制造出下面的“实”,也不可能将阻碍观瞻的、连接阁楼的楼梯去除,也无法改变低矮的层高。对此,策略就转变为在更大范围的空间中琢磨新的示能性,例如门所朝向的极远处的梁山山峰,其形状就被凸显,门前的露台增加了顶板,以遮蔽风雨,拓展聚众活动的空间。为了满足“上有天”,露台前方的开阔性、“气”的通畅也在感知中被凸显。通过生产与调用这些示能,空间无法完全合乎传统规制的情况下,仍然营造出一个能够生产出庄重祭祖活动的场所。
最后,示能性调整的限度,使得意图中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异,因此就需要空间感知和象征符号的调整作为中介过程。在进入新祖厝后,金银纸钱的焚化并不在严格意义上的祖厝内进行,而是在祖厝门口的露台。前文已经提及,如果在建筑范围外祭祀,有误祭孤魂之嫌。因而,对于“内外”的感知与理解就发生了变化。通过露台增加的顶板,洪家人将露台也感知为“内”的一部分,并决定在此焚化。但旋即,头一年的春节祭祀众人就发现由于金银纸钱量大,在露台上焚化的烟火太大,甚至有造成火患的危险。倒是露台阶梯下的空地上有足够的空间。但这一位置显然已经超出了通常能够理解的“内”。就在犹豫之际,有人提出,只要用炉,没有扔在地上焚烧,也算是给祖先的。于是众人接受了在露台下、空地上、在焚化炉内焚化金银纸钱的方案。可以看到,在搬迁后的祭祀活动中,传统家屋式的、以对建筑空间边界内外感知的身体经验为基础、将其符号化以象征社会关系意义上家之内外的模式已经无法维系。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调整内外的感知以及改变象征符号,来保持意义的一贯性。由此可见,空间的示能性不仅限定着身体性经验,同时也生产着新的经验与意义表达模式。
结 论
本文在田野场景上集中关注“家祭”这类在既有研究中较少受到关注的祭祀类型,展示了一个政府力量与地方精英主导之外的家庭的空间实践案例。通过分析狮峰镇拆迁前后两种住宅空间类型的示能性,揭示了日常生活所处的物理空间是如何实质性地参与到祭祀活动的生成中的。传统住宅空间的几何结构、建筑材质与内部空间组合方式等物质实存所带来的示能性,引导了一套与之相适配的祭祀活动的展开方式。现代住宅空间由于规划者的意图,其示能性指向一种区隔与工作生产等社会生活的私人休闲与消费,与祭祀活动不相适配。在狮峰镇进行集体拆迁安置后,进入现代住宅空间的家祭面对不同于传统住宅空间的示能性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这表明了祭祀活动并不单纯是一种观念意义上的文化行为,祭祀活动所开展的空间同样是祭祀有机构成的一部分,而不是与祭祀活动无本质关联的“容器”“背景”,也不仅仅是祭祀活动所指向的“意义”在时空中的表现或象征。
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承接了晚近宗教学研究中物质性转向的基本立场。在物质性转向所启发的视野下,我主要采用了“示能性”这一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用以刻画祭祀活动与空间之间的复杂关系:行动者受限制、导引的同时,仍然保有行动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在特定的语境中会导向对于空间示能性的调整。我将这种调整形容为“琢磨”,意在借助该语词在古典语境中隐含的“文质”语义,指出调整示能性的行动不是无中生有的建构,而是以既有的示能性为前提。通过洪穆一家重建祖厝的个案深描,我们可以看到,祖厝选址绝非单纯基于理想观念的按图索骥,更大范围上的空间方位、自然地理景观的空间示能性同样引导着辨识与定位。改造空间调整示能性的行动一方面以现代住宅内部空间的高度可塑性为前提,另一方面又受其高度集约性的规范,这使得行动不可避免地相对传统发生变异。在这种情况下,象征与诠释的调整就起到关键的中介作用。这表明,示能性并不是自在的属性,而是一个高度情境性的范畴,其显现与调整都以特定的文化为背景。因此,本文的个案分析尝试提出了对示能性分析中的拓展:关注特定示能性显现、遮蔽与调整的情景。在示能性的讨论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关系上,本文认为重建祖厝案例中的示能性调整,事实上指向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意义上的差异性空间。家庭在现代住宅中重建祭祀空间的努力,可以视为被规划与技术所统治的、高度同质化的“抽象的空间”走向崩解、“差异性空间”显露的过程,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正是被空间栖居者所体验的“表象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示能性理论完全有可能与空间生产理论相结合,通过观察分析空间示能性的调整情境、调整中权力关系的变化,揭示新的空间的生成。
本文对于祭祀空间与空间示能性的讨论也指向了对既有城市化实践的反思。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原有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居住与生产空间。尤其是在大规模的拆迁安置中,适配于乡村空间的生活方式被剧烈地嵌入到城市空间中,产生了种种变异。对于这种变异中出现的伦理失序现象,不应简单归咎于农村的观念与政策问题,而要注意以城市生产生活为模板规划出的同质化空间本身也以其示能性限制、引导着居住者的生活方式与具体行动。安置方案应当调整标准化模式,为农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有序过渡提供引导性的空间示能。
(本文注释内容略)
责任编辑:舒建军 杨 琼
扫码在手机上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