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将非人类叙事纳入考察范畴,可以丰富现有的叙事理论,摒弃叙事研究的“人类中心主义”。
关键词:非人类叙事;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转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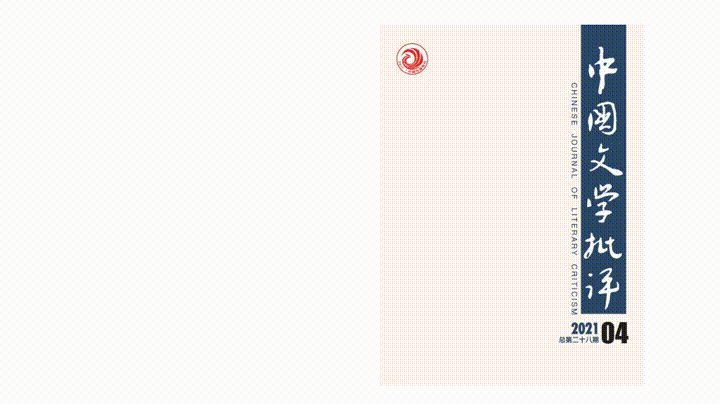
摘要:非人类叙事指的是由非人类实体参与的事件被组织进一个文本中,主要包括自然之物的叙事、超自然之物的叙事、人造物的叙事、人造人的叙事四种类型。在叙事作品中,处于故事与话语两个层面的非人类实体通常扮演叙述者、人物、聚焦者三种角色,由此发挥三种叙述功能,即讲述功能、行动功能和观察功能。将非人类叙事纳入考察范畴,既可以丰富现有的叙事理论,摒弃叙事研究的“人类中心主义”,同时也可以对文学史上大量存在的非人类叙事文本做出应有的批评和阐释。在“非人类转向”语境下提出非人类叙事,其目的不是否定人是“讲故事的动物”这一基本观点,更不是否定“文学是人学”这一立场,而是试图借此加深我们对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关系的理解,使人类更好地介入生物圈。
关键词:非人类叙事 人类中心主义 非人类转向
作者尚必武,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上海200240)。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人文社科界迎来一轮显著的“非人类转向”(non-human turn),引发众多学者的关注。乔恩·罗费和汉娜·斯塔克指出:“在思想史的当下时刻,不可能不在非人类转向的语境下思考人类。此外,不足为怪的是,非人类转向在总体上是一个跨学科事件,对非人类的研究并不是哪一个学科所特有的,它要求我们超越摆在面前的界限。”作为一门研究讲故事的学问,叙事学同样需要关注“非人类转向”,并在这一语境下思考叙事的样式与功能。受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一文的影响,叙事学家们通常把由人类书写的叙事等同于关于人类的叙事,由此导致叙事学被打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烙印。在《走向“自然”叙事学》一书中,德国叙事学家莫妮卡·弗鲁德尼克直截了当地宣称:“在我的模式中,叙事可以没有情节,但却不能没有人类(拟人的)体验者,无论其属于哪种类型、处于哪个叙事层面。” 从巴特到弗鲁德尼克,从杰拉德·普林斯到詹姆斯·费伦,叙事学家们无论是对于叙事的定义还是关于叙事研究的框架与模式,都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在现实的物理世界中,叙事作品是由人类书写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是“讲故事的动物”(storytelling animal),但在虚构的文学世界中,叙事作品所呈现的不一定都是人类的故事或人类的经验。长期以来,叙事学以模仿主义为参照范式,重点聚焦再现人类经验的叙事作品,而忽略了大量书写非人类的叙事作品,由此导致了现有叙事理论的不完整。从学理层面上来说,提出非人类叙事首先就是出于丰富和发展叙事理论的需要。
在“非人类转向”语境下提出非人类叙事,既不是否定人是“讲故事的动物”这一基本观点,更不是否定“文学是人学”这一根本立场,而是试图借此加深我们对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关系的理解,使人类更好地介入生物圈,同时使叙事学在理论建构上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傅修延指出:“人类的生存策略是进化出容量足够大的聪明大脑,这一策略固然使自己成为万物之灵,但在此过程中也付出了视听触味嗅等感知能力退化的沉重代价。从这个角度看,物联网的兴起可以说是对感官钝化的一种补偿。然而,人类毕竟不能只靠传感器生存,我们应当正视这一问题并尽可能地实现‘复敏’——为此必须抛弃高高在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像我们的古人那样首先把自己当成万物中的一员。” 他重点讨论了以听为主的感应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叙事作品中人与物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延续这一思路,主要聚焦再现非人类经验的叙事作品,尤其关注故事层面的非人类人物以及话语层面的非人类叙述者,重点讨论如下三个问题:什么是非人类叙事?非人类叙事有哪些基本样式与类型?以及非人类叙事的主要功能与意义何在?
一、什么是非人类叙事
长期以来,所有关于叙事的定义基本上都是围绕人类经验的再现,假定叙事是关于人类的故事。无论是经典叙事学还是后经典叙事学,关于叙事的定义都普遍存在一个明显的“人类主义偏见”。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一文的开篇,巴特写道:
世界上叙事作品之多,不计其数;种类浩繁,题材各异。对人类来说,似乎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叙事承载物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是固定的或活动的画面、是手势,以及所有这些材料的有机混合;叙事遍布于神话、传说、寓言、民间故事、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正剧、喜剧、哑剧、绘画(请想一想卡帕齐奥的《圣于絮尔》那幅画)、彩绘玻璃窗、电影、连环画、社会杂闻、会话。而且,以这些几乎无限的形式出现的叙事遍存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叙事是与人类历史本身共同产生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也从来不曾存在过没有叙事的民族;所有阶级、所有人类集团,都有自己的叙事作品,而且这些叙事作品经常为具有不同的,乃至对立的文化素养的人所共同享受。所以,叙事作品不分高尚和低劣文学,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命那样永存着。
巴特不断用“人类”一词来描述叙事的普遍性。他认为,人类可以选择任何材料作为叙事的媒介;叙事与人类共存于这个世界,所有人类集团都有自己的叙事作品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巴特似乎把由人类来书写的叙事等同于关于人类的叙事。这一观点在叙事学界被广为接受。如果说巴特的上述叙事观基本代表了经典叙事学家们的立场,那么弗鲁德尼克和费伦带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叙事观则大体代表了后经典叙事学家们的立场。
在《走向“自然”叙事学》一书中,弗鲁德尼克借用威廉·拉波夫的观点,将自然叙事等同于口头叙事。她指出:“口头叙事(更确切地说,自发的会话讲述的叙事)在认知上接近于人类经验的感知范式,这些范式即便在更为复杂的书面叙事中也同样起作用,哪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故事的文本构成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弗鲁德尼克用“人类体验”来强调叙事的属性,认为“体验性”构成了作品的“叙事性”。在弗鲁德尼克看来,所谓的体验性“反映了与人类存在和人类关切的具身性的认知图式。”可见,弗鲁德尼克在论述体验性时,她所倚重的是“人类存在和人类关切”(human existence and human concerns)。弗鲁德尼克认为,叙事理论家们实际上很早就注意到叙事概念的“人类主义偏见”。“叙事理论家们很早就注意到,叙事的人类主义偏见及其与人物、身份、行动等相关的主要故事参数被认为构成了故事的最基本要素。”在弗鲁德尼克所列举的叙事理论家们中,普林斯是比较突出的一位。在《叙事学词典》中,普林斯写道:“一个特定叙事作品的叙事性程度部分地取决于叙事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接受者的欲望,再现方向性的时间整体(从开端到结尾的前瞻性方向,或从结尾到开端的回顾性方向),涉及冲突,由分开的、具体的、积极的情景与事件所构成,它们从人类(化)课题或世界的角度来看是有意义的。”在普林斯看来,叙事之所以成为叙事,既离不开它之于人类接受者欲望的满足,也离不开它之于人类的意义。
当弗鲁德尼克指出自然叙事为研究所有类型的叙事提供了一个关键概念的时候,她意在强调几乎所有的叙事研究都需要聚焦人类的体验性。这一立场无疑忽略了那些再现非人类体验性的叙事。弗鲁德尼克这一带有“人类主义偏见”的叙事观在费伦那里也同样有较为明显的表现。在其经典作品《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和意识形态》中,费伦从修辞视角出发,将叙事界定为“某人为了某个目的在某个场合下向某人讲述某事。”此后,在诸如《活着是为了讲述:人物叙述的修辞与伦理》《体验小说:判断、进程和修辞叙事理论》等一系列论著中,费伦不断强化这一以“人”为核心的叙事概念。2017年,费伦直接以“某人向某人讲述”作为其著作《某人向某人讲述:走向叙事的修辞诗学》的题名。在论述修辞诗学的原则时,费伦强调读者之于叙事的三种不同反应,即模仿性反应、主题性反应和虚构性反应。费伦认为读者之于叙事的模仿性反应在于“将人物看作我们自己所处世界中的可能人物”。无论是叙事的讲述对象还是受述对象,费伦都把他们看作“某个人”,假定叙事作品是关于人类而不是非人类的故事。
在人类发展史上,人类除了讲述自己的故事之外,还讲述了自己的对立面“非人类”的故事。纵观世界文坛,我们可以发现大量关于非人类的叙事作品。无论是早期的古希腊神话,还是当代先锋实验作品,都有非人类实体的存在。譬如,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关于神的故事;中国志怪小说中关于神仙鬼怪的故事,典型的作品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承恩的《西游记》;科幻小说中关于机器人、外星人、克隆人的故事,如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伊恩·麦克尤恩的《像我这样的机器》;动物文学中关于动物的故事,如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麦克尤恩的《一只猿猴的遐思》、朱利安·巴恩斯的《 章世界史》、莫言的《生死疲劳》等;寓言和童话故事中关于动物的故事,如安徒生的《美人鱼》和《海的女儿》;变形文学中关于变形人物的故事,如卡夫卡的《变形记》、麦克尤恩的《蟑螂》、菲利普·罗斯的《乳房》、玛丽·达里厄塞克的《母猪女郎》等,不一而足。遗憾的是,现有叙事理论大多聚焦于再现人类经验的叙事,而忽略了文学史上那些书写非人类的作品。
章世界史》、莫言的《生死疲劳》等;寓言和童话故事中关于动物的故事,如安徒生的《美人鱼》和《海的女儿》;变形文学中关于变形人物的故事,如卡夫卡的《变形记》、麦克尤恩的《蟑螂》、菲利普·罗斯的《乳房》、玛丽·达里厄塞克的《母猪女郎》等,不一而足。遗憾的是,现有叙事理论大多聚焦于再现人类经验的叙事,而忽略了文学史上那些书写非人类的作品。
进入21世纪以来,受到行动者网络理论、情感理论、动物理论、新物质主义理论、媒介理论以及思辨现实主义等多种思潮的激发和影响,人文社会科学迎来了一轮声势浩大的“非人类转向”。这一转向无疑为非人类叙事研究提供了契机。理查德·格鲁辛指出:与“后人类转向”不同的是,所谓的“非人类转向”指的是“人类始终与非人类共同进化、共同存在或协作,人类的特征恰恰在于其和非人类总是难以区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就文学研究而言,“非人类转向”的最基本含义是“转向非人类”(turn to non-human),即认识到文学书写的对象不仅包括人类,而且也包括非人类。从理论层面上来说,将非人类叙事纳入讨论和考察范畴,可以丰富和扩展现有的叙事理论,使之更加完整,也可以对文学史上大量存在的非人类叙事文本做出应有的批评和阐释。
在论述广义叙述学的时候,赵毅衡提出了一个关于叙述的底线定义,即“有人物参与的事件被组织进一个文本中。”参照他对叙述的定义,我们大致可以给非人类叙事提供这样一个底线定义,即由“非人类实体”(non-human entity)参与的事件被组织进一个文本中。在具体叙事作品中,非人类实体主要存在于故事和话语两个层面。在故事层面上,他们以人物的身份出现;在话语层面上,他们以叙述者的身份出现。
二、非人类叙事的主要类型:从自然之物到人造之物
通过考察人物和叙述者的非人类身份,我们不妨将非人类叙事大致分为如下四种类型:其一,自然之物的叙事,主要包括以动物、植物、石头、水等各类自然界的存在物为核心对象的叙事;其二,超自然之物的叙事,譬如以神话、传说、史诗中的鬼神、怪兽,以及科幻文学中的外星人为主体的叙事等;其三,人造物的叙事,主要包括以诸如钱币、玩具、布匹、线块等人类创造出来的无生命物体为主体的叙事;其四,人造人的叙事,主要包括以机器人、克隆人为主体的叙事,这在科幻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非人类叙事作品中,无论非人类实体是否有生命,它们都不再是作品场景的一部分,而是作品的人物,即故事的参与者,抑或是作品的叙述者,即故事的讲述者。
第一,自然之物的叙事。人类在诞生之初,首先接触到的就是自然之物。在《圣经》中,上帝在造出亚当和夏娃后,将他们安置在伊甸园。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品尝着甘美的果实,信口给所见的动植物命名,无论是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还是园中的嘉树与鲜花。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动植物看作故事世界的背景环境,忽略了它们作为叙事主体而存在的可能,但后者的例子却屡见不鲜。在《山海经》中,山川河岳、植物、动物都成了作品的叙事主体,作品的“基本格局是‘依地而述’,不是‘依时而述’或‘依人而述’”。比如“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海内经”等。此外,作品还叙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各类动植物。比如在“招摇之山”有一种名为迷榖的植物,作品中还记载了一种会冬眠的鱼。在傅修延看来,《山海经》“是人类中心主义建立之前的产物,因为书中的叙述者并没有把自己与自然界分开,《山海经》中诸如 ‘朴野’、‘荒芜’之类的词语恰好说明古人并未自诩为‘万物的灵长’”。
放眼世界文坛,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诸多以自然之物为主体的叙事作品。英国作家安妮·凯里(Annie Carey)的《一团煤、一粒盐、一滴水、一块旧铁和一个燧石的自传》即是如此。在作品中,煤块、盐、旧铁和燧石分别化身为叙述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丹麦作家安徒生也同样书写了很多关于自然之物的故事。比如,在《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中,某个豆荚里面的五粒豌豆成为会说话的个体,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其中最后一粒豆子在楼顶的窗户下发芽了,给屋里病重的小女孩带去了生命的希望。在《老栎树的梦》中,一棵365岁的老栎树在圣诞节的时候,做了一个美丽的梦,梦见自己越长越高:“它的躯干在上升,没有一刻停止。它在不断地生长。它的簇顶长得更丰满,更宽大,更高。它越长得高,它的快乐就越增大;于是它就更有一种愉快的渴望,渴望要长得更高——长到跟明朗和温暖的太阳一样高。”遗憾的是,老栎树的梦还没有结束,就被一阵狂风连根拔起,崩裂而死。
在巴恩斯的《 章世界史》中,木蠹叙述者说:“动物们也有许多浪漫的神话故事。”实际上,书写动物们的故事一直都是小说家们的重要兴趣。在中外文学史上,存在着大量以动物为主要叙述对象的叙事作品。在《
章世界史》中,木蠹叙述者说:“动物们也有许多浪漫的神话故事。”实际上,书写动物们的故事一直都是小说家们的重要兴趣。在中外文学史上,存在着大量以动物为主要叙述对象的叙事作品。在《 章世界史》的第一部分“偷渡客”中,木蠹讲述了在大洪水来临之际,动物们如何登上挪亚方舟,躲避灾难的故事。木蠹一开始便亮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是个偷渡客,也存活下来,又逃离(离舟一点都不比登舟容易),而且活得很好。”不过,大部分其他动物就没有木蠹那么幸运,因为挪亚立下的规矩是,可以允许七个洁净的动物登上方舟,而不洁净的动物中只有两个可以登舟避难。对于这一规定,有的动物选择扬长而去,走进了丛林;有的动物不愿意和配偶、子女分开,选择了留下;部分入选的动物上船前食物中毒,需要再选一次;那些试图偷渡的动物,比如驯鹿,则被吊死在方舟的栏杆上。木蠹特别强调,地球上五分之一的物种随挪亚的小儿子法拉第负责的那艘船一起沉没,而其余那些失踪的都被挪亚那伙人吃掉了。就书写濒临灭绝的动物的叙事作品而言,我们不禁想起陈应松的小说《豹子的最后舞蹈》。在作品中,叙述者是神农架地区的最后一只豹子。他讲述了自己家族,尤其是父母兄弟姐妹被以老关父子为首的猎人捕杀,最后自己也被猎人打死的故事。众所周知,卡夫卡也是擅长书写动物的小说家。在《地洞》中,他写了某个种类不明的打洞动物;在《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中,叙述者向科学院的先生们汇报了自己作为猴子的经历,尤其是它最后如何通过模仿人类来进入人类世界的故事。
章世界史》的第一部分“偷渡客”中,木蠹讲述了在大洪水来临之际,动物们如何登上挪亚方舟,躲避灾难的故事。木蠹一开始便亮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是个偷渡客,也存活下来,又逃离(离舟一点都不比登舟容易),而且活得很好。”不过,大部分其他动物就没有木蠹那么幸运,因为挪亚立下的规矩是,可以允许七个洁净的动物登上方舟,而不洁净的动物中只有两个可以登舟避难。对于这一规定,有的动物选择扬长而去,走进了丛林;有的动物不愿意和配偶、子女分开,选择了留下;部分入选的动物上船前食物中毒,需要再选一次;那些试图偷渡的动物,比如驯鹿,则被吊死在方舟的栏杆上。木蠹特别强调,地球上五分之一的物种随挪亚的小儿子法拉第负责的那艘船一起沉没,而其余那些失踪的都被挪亚那伙人吃掉了。就书写濒临灭绝的动物的叙事作品而言,我们不禁想起陈应松的小说《豹子的最后舞蹈》。在作品中,叙述者是神农架地区的最后一只豹子。他讲述了自己家族,尤其是父母兄弟姐妹被以老关父子为首的猎人捕杀,最后自己也被猎人打死的故事。众所周知,卡夫卡也是擅长书写动物的小说家。在《地洞》中,他写了某个种类不明的打洞动物;在《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中,叙述者向科学院的先生们汇报了自己作为猴子的经历,尤其是它最后如何通过模仿人类来进入人类世界的故事。
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很多书写由人变形为动物或动物变形为人的叙事作品,如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作品主要讲述了地主西门闹先后投胎为驴、牛、猪、狗和猴子的故事。比如,在第一次投胎的时候,西门闹掩饰不住自己的惊讶:“我睁开眼睛,看到自己浑身沾着黏液,躺在一头母驴的腚后。天哪!想不到读过私塾、识字解文、堂堂的乡绅西门闹,竟成了一匹四蹄雪白、嘴巴粉嫩的小驴子。” 又如,法国作家玛丽·达里厄塞克的小说《母猪女郎》。作品讲述了一位在香水连锁店工作的漂亮姑娘变形为一只母猪的故事。变成母猪后的女孩失去了工作,惨遭男友抛弃,甚至遭到动物保护协会的追杀。所幸的是,她在狼人伊万那里收获了一段爱情。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后变成了一只甲虫。变成甲虫的萨姆沙遭到所有人的嫌恶,就连自己最喜欢的妹妹也慢慢对他弃之不顾,最后悲惨地离开了世界。麦克尤恩的小说《蟑螂》仿照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不过,在麦氏的笔下,不是人变成了甲虫,而是甲虫变成了人。在作品中,一只名叫吉姆·萨姆沙的蟑螂变形为英国首相,并率领其他同样由蟑螂变形而来的内阁成员,在英国成功推行了违背经济规律、旨在撕裂国家的“逆转主义”政策。
第二,超自然之物的叙事。与自然之物的叙事相对应的非人类叙事是超自然之物的叙事,如以鬼神、怪兽、外星人等为主体的叙事作品。在中外文学史上,都存有大量以超自然之物为叙事主体的作品。比如,《荷马史诗》书写了包括众神之王宙斯、文艺女神缪斯、太阳神阿波罗、海神波塞冬、智慧女神雅典娜等在内的希腊众神。《伊利亚特》的第20卷讲述了诸神直接出战,各助一方的故事:
众神纷纷奔赴战场,倾向不一样。
赫拉前往船寨,一同前去的还有
帕拉斯·雅典娜、绕地神波塞冬和巧于心计、
分送幸运的赫尔墨斯,自以为力大的
赫菲斯托斯也和他们一同前往,
把两条细腿迅速挪动一拐一瘸。
前往特洛亚营垒的是头盔闪亮的阿瑞斯,
还有披发的福波斯、女射神阿尔忒弥斯、
勒托、爱欢笑的阿芙罗狄忒和克珊托斯。
与《荷马史诗》类似,在讲述人类故事的同时,涉及神的介入的作品还有古希腊罗马神话,以及中国古典作品《封神演义》。在《封神演义》的第九十九回“姜子牙归国封神”中,姜子牙请求天尊,“将阵亡忠臣孝子、逢劫神仙,早早封其品位,毋令他游魂无依,终日悬望。”在得到原始天尊的允许和敕命后,姜子牙在封神台一共分封了365位正神。20世纪60年代,叙事学发轫之初,部分叙事学家试图参照语言学模式对神话展开研究,揭示神话的叙事语法。譬如,法国经典叙事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曾参照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研究了俄狄浦斯神话、美洲神话等。通过研究,列维-斯特劳斯得出结论:“所有的神话都具有一种‘板岩’结构,这种结构可以说是通过重复的手段显示出来的。”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研究对象就是非人类叙事。遗憾的是,这些以神话为对象的非人类叙事遭到了当代叙事理论家的淡忘或漠视。类似书写神仙、鬼怪等非人类的叙事作品还有《聊斋志异》《搜神记》《西游记》等。以《西游记》为例,作品涉及各种类型的神仙、妖怪。在经历八十一难后,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最终取得真经,修得正果。英国史诗《贝尔武甫》则是以怪兽为叙事主体的另一个经典例子。该诗的主体部分讲述了英雄贝尔武甫战胜怪兽格伦戴尔母子的故事。此外,以超自然之物为主体的非人类叙事还包括那些关于外星人的叙事作品,常见于科幻文学作品中,譬如厄休拉·勒奎因的《黑暗的左手》和刘慈欣的《三体》等。
第三,人造物的叙事。在很多非人类叙事作品中,无生命的器物被赋予了生命,成为作品中的人物或叙述者。18世纪英国文学大量涌现出此类叙事作品,学界一般称之为“它—叙事”(It-narrative)或“流通小说”(novels of circulation)、“物故事”(object tales)。诸如钱币、马甲、针垫、瓶塞钻、鹅毛笔等没有生命力的器物都被赋予了生命,成为作品中的人物,向读者讲述它们的故事。卡夫卡的作品中也有很多关于人造物叙事的例子。譬如,在短篇小说《家长的忧虑》中,主人公是一种名为“奥德拉德克”(Odradek)的线块。尽管叙述者这样描述奥德拉德克:“初一看,它像是个扁平的星状线轴,而且看上去的确绷着线;不过,很可能只是一些被撕碎的、用旧的、用结连接起来的线,但也可能是各色各样的乱七八糟的线块”。但在作品中,奥德拉德克分明又是有生命的个体,身形灵活,交替地守候在阁楼、楼梯间、过道和门厅,他发出的笑声听起来像是落叶发出的沙沙声。让叙述者无法接受并感到痛苦的是,奥德拉德克能够拥有比自己更长久的生命:“显然,他绝不会伤害任何人;但是,一想到他也许比我活得更长,这对我来说,几乎是一种难言的痛苦。”
安徒生创作的大量作品也可以被纳入人造物叙事这一类型。比如,在《钱猪》中,婴儿室中的各种玩具包括桌子的抽斗、学步车、摇木马、座钟、炮竹、痰盂、钱猪等,在某天晚上突发奇想,要表演一出喜剧。玩具们一边看剧,一边吃茶和做知识练习。后来,激动的钱猪从橱柜上掉了下来,摔成了碎片,而钱猪肚子里的大银洋跑去了大千世界。在《瓶颈》中,一只瓶颈对小鸟讲述了自己和瓶子的故事,尤其是自己如何见证了一对年轻男女在森林中订婚,后来身为船员的年轻男子在遇到海难沉船前,把写有未婚妻的名字、自己名字和船名字的纸条塞在了瓶子中。后来有一次,瓶子被一个飞行家从腾飞的气球中扔出去摔碎了,从此只剩下了瓶颈。在《烂布片》中,一块挪威烂布片和一块丹麦烂布片为自己的产地国挪威和丹麦,争论不休:
“我是挪威人!”挪威的烂布说,“当我说我是挪威人的时候,我想我不须再作什么解释了。我的质地坚实,像挪威古代的花岗岩一样,而挪威的宪法是跟美国自由宪法一样好!我一想起我是什么人的时候,就感到全身舒服,就要以花岗岩的尺度来衡量我的思想!”
“但是我们有文学,”丹麦的烂布片说,“你懂得文学是什么吗?”
故事最后,挪威烂布片和丹麦烂布片都被造成了纸,而用挪威烂布片造成的那张纸被一位挪威人用来写了一封情书给他的丹麦女友;而那块丹麦烂布片做成的稿纸上写着一首赞美挪威的美丽和力量的丹麦诗歌。在安徒生笔下,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在《衬衫领子》中,衬衫领子向袜带、熨斗、剪刀吹嘘自己有过一大堆情人的经历;在《老路灯》中,那个服务多年的老路灯待在杆子上的最后一晚,回忆了自己的一生;在《笔和墨水壶》中,一个诗人房间中的墨水壶和鹅毛笔相互嘲讽;在《坚定的锡兵》中,锡兵哪怕就要被火化为锡块时,依然保持扛枪的姿势,坚定不动。
第四,人造人的叙事。随着文学与科技的相互交叉,人造人也被写进文学作品中,成为非人类叙事的又一类型。论及这一叙事样式,我们不得不提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在小说中,科学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开始对生命的原理能否延伸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用他的话来说,“有一个大自然的杰作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人体结构(事实上是一切有生命的物体的身体结构)。我常常问自己:生命的原理可以延伸吗?这是个大胆的问题,是对生命(一个一直被认作是奇迹的东西)的质疑。”为此,弗兰肯斯坦开始调查生命的起源,研究死亡,研习解剖学,最终成功破解了生命密码。他说:“在经过多少个难以置信的辛苦和疲劳的日夜后,我成功发现了生命的演化与形成的原因。不,还不止于此,我自己就成了可以让无生命的东西获得生命的人。”弗兰肯斯坦口中的“让无生命的东西获得生命”几乎是关于人造人故事的一个重要动因。经过艰苦的努力,他成功制造出了一个有生命的物体,不过他自己都受不了这个怪物的丑陋外貌,避之唯恐不及。尽管怪物不断向人类示好,试图和人类交往,但因其丑陋的外貌,遭到人类的厌恶和误解,进而他开始报复人类、杀戮人类。最终,怪物在杀死弗兰肯斯坦新婚妻子伊丽莎白和弗兰肯斯坦本人后,用火烧死了自己。
弗兰肯斯坦式的人造人故事在后世文学作品中以不同形式得到不断延续。譬如,石黑一雄的小说《千万别丢下我》讲述了一群克隆人的故事。在作品中,叙述者凯茜既是克隆人,也是克隆人的看护者。根据她的讲述,人类创造出克隆人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人类捐献器官。一般情况下,克隆人在给人类捐献器官三至四次后,就完成了使命,其生命也随之走向尽头。尽管凯茜和另一位克隆人汤米真心相爱,但因为无法从人类那里获得延迟捐献的许可,她在亲眼看见汤米完成自己的最后一次器官捐献后,也由看护人变成了器官捐献人。麦克尤恩的小说《我这样的机器》讲述了一则人造人如何介入人类生活并遭遇失败的故事。小说场景设置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人造人开始投放市场:“第一批机器人中,十二个名为亚当,十三个名为夏娃。平淡无奇,每个人都这么说,但符合商业需求。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观念,在科学上受人诟病,所以这二十五个设计成了多个种族的样子。”在小说中,亚当表现出超强的机器学习能力,学会了在网上挣钱。他同女主角米拉达发生了关系,并宣称自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还不断地为她撰写情诗。在石黑一雄的新作《克拉拉与太阳》中,叙述者克拉拉是一台AF机器人(人工朋友机器人)。按照人工智能工程师卡帕尔迪的设计和要求,克拉拉模仿和学习她的主人乔西,以便在乔西生病离开世界后,自己可以延续她。克拉拉根据自己的判断,努力去做对乔西最有利的事情,用自己的信念和行动帮助乔西恢复了健康,长大成人。有关人造人的非人类叙事作品还有大卫·米切尔的《云图》中的克隆人星美反抗人类的故事,以及菲利普·迪克的《仿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的仿真人故事。
三、非人类叙事的主要功能:讲述、行动与观察
在叙事作品中,非人类实体主要存在于故事与话语两个层面,分别承担叙述者、人物、聚焦者三种角色,相应地发挥三种叙述功能,即讲述功能、行动功能和观察功能。
第一,叙述功能,即作为讲述者的非人类。谭君强指出:“作为叙述主体,叙述者首要的功能就在于叙述。只有叙述才能成为叙述者,也只有存在叙述者的叙述才有叙事文本的存在。”从叙述内容上来说,作为叙述者的非人类主体既可以讲述非人类的故事,也可以讲述人类的故事,或者讲述非人类与人类相处的故事。譬如,在《豹子的最后舞蹈》中,叙述者是一只豹子,它讲述了自己的家族如何被人类灭绝的故事;在《千万别丢下我》中,叙述者凯茜是一个克隆人,她主要讲述了一群克隆人如何在给人类捐献器官的过程中走向生命尽头的故事;巴恩斯的《10章世界史》中的木蠹叙述者讲述了动物们在洪水来临之际的命运。在《生死疲劳》中,叙述者是由地主西门闹投胎而来的驴、牛、猪、狗和猴子,然后这些动物们轮流出场,分别讲述了西门闹及其妻女和子孙后代的故事。在《克拉拉与太阳》中,AF机器人克拉拉讲述了她与小女孩乔西及其家人共同相处的故事。
第二,行动功能,即作为行动者的非人类。自亚里士多德以降,人物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作为行动者而存在。譬如,经典叙事学家格雷马斯将人物称之为“行动元”(actant),并且重点分析了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帮助者、反对者六种行动元。叙事作品中的行动元既可以是人类,也可以是非人类。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受到格雷马斯的启发,提出了著名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简称ANT)。拉图尔说:“行动者网络理论借用了来自于文学研究的技术词汇行动元”。在拉图尔看来,“行动者网络理论并非一种关于用物‘取代’人作为行动者的空洞论点:它仅仅指出,任何关于社会的科学都无法开展,除非我们先深入研究什么人和什么东西参与了行动这一问题,即便这可能意味着纳入一个我们因缺乏更好的术语只能称之为非人类的因素。”换言之,在拉图尔的理论体系中,行动者或参与行动的主体既可以是人类,也可以是非人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拉图尔强调检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非人类必须是行动者,不能只是悲哀地发挥着承载象征投影的作用。”在大量的非人类叙事作品中,非人类实体是作为行动者而存在,成为故事世界的主角,其行动也由此成为作品所要再现的故事内容,直接推动了作品的叙事进程。譬如,在奥威尔的《动物农庄》中,一群动物反叛人类,在农场上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在《像我这样的机器》中,机器人亚当积极介入人类世界,不仅同女主角米兰达发生了性关系,而且还擅自主张,坚持“真相就是一切”(truth is everything)的说辞,枉顾米兰达为自己好友伸张正义的伦理真相,将米兰达曾在法庭说谎的证据交给警方而导致她被捕入狱。在《克拉拉与太阳》中,机器人克拉拉跨越茂盛的草地走向麦克贝恩先生的谷仓,因为她坚信可以找回藏在那里的太阳,而太阳可以给予女孩乔西力量,让她重新恢复健康。在乔西生命垂危之际,克拉拉看到太阳出来后,立即与乔西的母亲和梅拉尼娅管家冲入乔西的房间,让太阳照射在乔西身上。克拉拉说:
“该死的太阳!” 梅拉尼娅管家大叫着,“走开,该死的太阳!”
“不,不!”我赶忙走到梅拉尼娅管家跟前,“我们必须拉开这些,拉开一切!我们必须让太阳尽他的全力!”
我试图从她手中拿走窗帘的布料,尽管她一开始不肯放手,最终却还是让步了,一脸惊诧的神色。这时,里克已经来到了我的身边,似乎凭着直觉做出了一个判断,于是他也伸出手来,帮忙升起百叶帘,拉开窗帘。
太阳的滋养随即涌入房间,如此的充沛饱满,里克和我都摇摇晃晃地向后退去,几乎要失去平衡。梅拉尼娅管家双手遮着脸,嘴里又说了一遍:“该死的太阳!”但她没有再试图阻止他的滋养。
由于克拉拉的积极行动,乔西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
第三,观察功能,即作为聚焦者的非人类。在《超越人类的叙事学:故事讲述与动物生活》一书中,戴维·赫尔曼主要通过考察动物叙事作品来探讨叙事何以再现非人类的经验,建构一个非人类的世界,而这恰恰可以通过非人类聚焦实现。不仅如此,作为聚焦者的非人类还为观察和审视人类行为与人类世界提供了一种他者视角。譬如,在《 章世界史》中,木蠹以观察者的身份,不仅讲述了自己对其他动物命运的思考,同时还传递了自己对挪亚的观察与判断。它讲述了挪亚裸身的故事:挪亚醉酒后,脱完衣服就躺在帐篷中;后来,含和他的弟兄遮盖了挪亚的裸体,并把他安顿在床上,但挪亚醒来后,“他诅咒看到他醉酒裸睡的儿子,宣判所有含的后代都要在那两个屁股先进他房间的弟兄家里做奴仆。”对于挪亚的这一举动,木蠹说:“这当中有什么道理?我能猜到你的解答:醉酒影响了他的判断力,我们应该怜恤他,而不是谴责他。这也许有道理。但我只想提一句:是我们在方舟上认清了他”。依它所见,挪亚动作笨拙,不讲卫生,甚至认为如果上帝选了大猩猩做他的门徒,就不会有这么多犯上作乱,“兴许根本就不需要来一场洪水。”在故事世界中,木蠹作为一个观察者来陈述自己的所见所思:“我要揭示的真相到此差不多说完了。这些都是出于好意,你一定要理解我的意思。你如果认为我这是故意挑起争端,那可能是因为你们这一族武断得不可救药——但愿你不会在意我这么说。你们只相信你们愿意相信的,然后就一直相信下去。想想也不奇怪,你们都有挪亚的基因。”又如在《克拉拉与太阳》中,克拉拉这样描述她和其他AF伙伴们透过橱窗对人类世界的观察:“我们能够看着外面——行色匆匆的办公室工人、出租车、跑步者、游客、乞丐人和他的狗、RPO大楼的下半截。”在克拉拉被乔西买回家后,她的重要任务就是负责观察乔西。克拉拉说:“在多种环境下观察乔西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克拉拉对人类世界的观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对人类行为的认知和判断,同时也使她认识到自己与人类之间的差异。在生命走向尽头时,克拉拉遇到了来回收站寻找自己销售出去的那些AF机器人的商店经理,她动情地说:“经理,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来学习乔西;如果真的有那样做的必要,那我是会竭尽所能的。但我认为那样做的结果恐怕不太好。不是因为我无法实现精准。但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去尝试,如今我相信,总会有一样东西是我无法触及的。母亲、里克、梅拉尼娅管家、父亲——我永远都无法触及他们在内心中对于乔西的感情。”
章世界史》中,木蠹以观察者的身份,不仅讲述了自己对其他动物命运的思考,同时还传递了自己对挪亚的观察与判断。它讲述了挪亚裸身的故事:挪亚醉酒后,脱完衣服就躺在帐篷中;后来,含和他的弟兄遮盖了挪亚的裸体,并把他安顿在床上,但挪亚醒来后,“他诅咒看到他醉酒裸睡的儿子,宣判所有含的后代都要在那两个屁股先进他房间的弟兄家里做奴仆。”对于挪亚的这一举动,木蠹说:“这当中有什么道理?我能猜到你的解答:醉酒影响了他的判断力,我们应该怜恤他,而不是谴责他。这也许有道理。但我只想提一句:是我们在方舟上认清了他”。依它所见,挪亚动作笨拙,不讲卫生,甚至认为如果上帝选了大猩猩做他的门徒,就不会有这么多犯上作乱,“兴许根本就不需要来一场洪水。”在故事世界中,木蠹作为一个观察者来陈述自己的所见所思:“我要揭示的真相到此差不多说完了。这些都是出于好意,你一定要理解我的意思。你如果认为我这是故意挑起争端,那可能是因为你们这一族武断得不可救药——但愿你不会在意我这么说。你们只相信你们愿意相信的,然后就一直相信下去。想想也不奇怪,你们都有挪亚的基因。”又如在《克拉拉与太阳》中,克拉拉这样描述她和其他AF伙伴们透过橱窗对人类世界的观察:“我们能够看着外面——行色匆匆的办公室工人、出租车、跑步者、游客、乞丐人和他的狗、RPO大楼的下半截。”在克拉拉被乔西买回家后,她的重要任务就是负责观察乔西。克拉拉说:“在多种环境下观察乔西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克拉拉对人类世界的观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对人类行为的认知和判断,同时也使她认识到自己与人类之间的差异。在生命走向尽头时,克拉拉遇到了来回收站寻找自己销售出去的那些AF机器人的商店经理,她动情地说:“经理,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来学习乔西;如果真的有那样做的必要,那我是会竭尽所能的。但我认为那样做的结果恐怕不太好。不是因为我无法实现精准。但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去尝试,如今我相信,总会有一样东西是我无法触及的。母亲、里克、梅拉尼娅管家、父亲——我永远都无法触及他们在内心中对于乔西的感情。”
非人类实体的叙述功能、行动功能和观察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指涉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引发读者对人类与非人类共存于同一个世界这一问题的关注,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换言之,研究非人类叙事的重要旨趣在于更好地理解人类,使人类以更好的方式介入生物圈,建构更大的有机体。用赫尔曼的话来说,关于非人类叙事研究的一个基本目的是探究叙事何以作为一个“场所来重新思考——批判或重申,解构或重构——对于在一个不仅只有人类存在的世界中人类地位的不同理解方式。”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关注和研究非人类叙事无疑有助于激发我们对人类何以成为更好的人类,以及世界何以成为更好的世界等问题的思考。
在解读库切的《动物的生命》时,人类学家芭芭拉·斯马茨讲述了自己在非洲实地考察的一段独特经历。斯马茨当时正在观察一群进食的母猩猩和玩耍的小猩猩,突然间她的目光和一个名叫潘朵拉的雌猩猩相遇了。这只雌猩猩感受到了斯马茨的友善,径直走到她的身边,站立起来,把鼻子贴到斯马茨的鼻子,用长长的手臂将她抱在怀里几秒钟。它在放开斯马茨后,又用眼睛看了看她,然后继续回去进食。回到美国后的斯马茨始终难以忘却这段经历,她说:“从非洲回来以后,没有非人类的伙伴,我感到非常寂寞。是我的狗莎菲大大缓解了我的怀念。莎菲的样子很像狒狒,它给了我机会去体验一种超越物种界限的互为主体性。”斯马茨的经历触及非人类叙事的一个重要命题,即跨物种的共情。库切在《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通过虚构的女作家科斯特洛,抗议动物们所遭遇的不公。科斯特洛说:“在古时候,人类的声音虽然由理性提升,但会遭遇狮子的咆哮、公牛的吼叫。于是,人类与狮子和公牛开战;许多年代之后,人类确定无疑地赢得了战争。今天,这些动物再也没有那样反抗的力量了。它们只剩下了沉默,只能用沉默与我们对抗。一代又一代地,我们的俘虏们显现了英雄气概,拒绝跟我们说话。”无论是现实世界的人类学家斯马茨还是虚构世界的小说家科斯特洛,都试图呼吁我们去关注诸如动物等非人类同伴物种。人类是讲故事的动物,但人类不仅讲述自己的故事,记录和分享自己的经验,而且也讲述非人类同伴物种的故事。对非人类叙事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在理论层面上丰富和推进现有的叙事学,同时也为人类反思自我和完善自我提供了素材,在实践层面上成为激发人类重审自我、审视人类世界的一个动因。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
扫码在手机上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