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心居》是以万紫园小区顾家为中心讲述的当下上海故事。
关键词:世情小说;风俗史;城市文学;市民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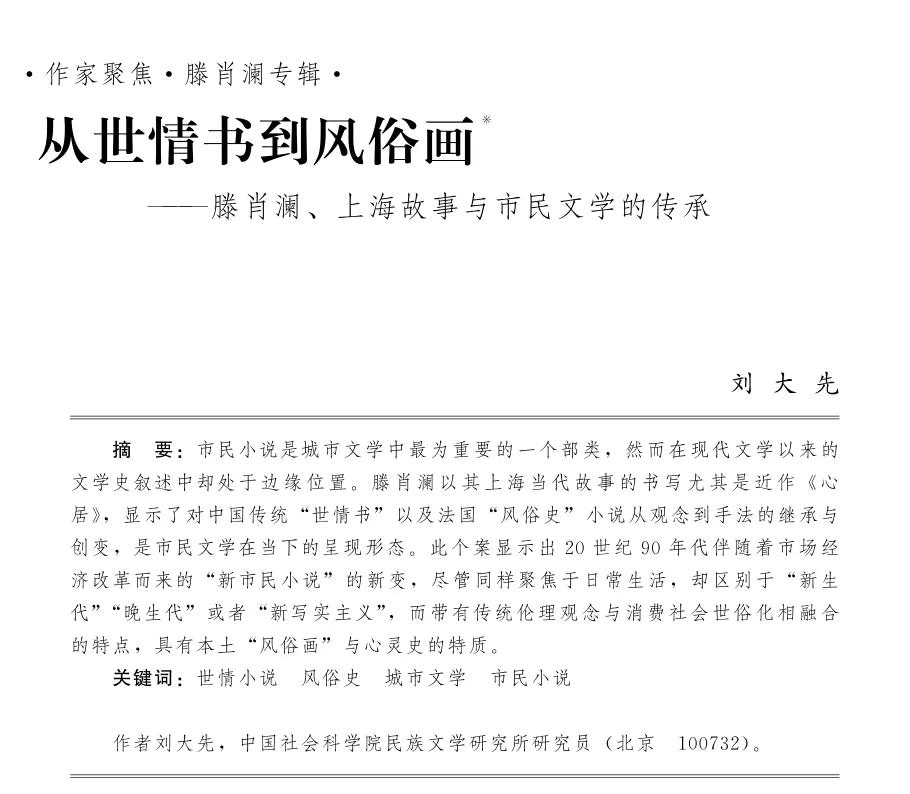
摘要:市民小说是城市文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类,然而在现代文学以来的文学史叙述中却处于边缘位置。滕肖澜以其上海当代故事的书写尤其是近作《心居》,显示了对中国传统“世情书”以及法国“风俗史”小说从观念到手法的继承与创变,是市民文学在当下的呈现形态。此个案显示出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而来的“新市民小说”的新变,尽管同样聚焦于日常生活,却区别于“新生代”“晚生代”或者“新写实主义”,而带有传统伦理观念与消费社会世俗化相融合的特点,具有本土“风俗画”与心灵史的特质。
关键词:世情小说 风俗史 城市文学 市民小说
作者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一
“城市文学”在晚近几年——至少在媒体上与批评视野中——几乎完全遮蔽了“乡土文学”的形象,这当然与城市化的快速进程有关系。然而当人们在使用“城市文学”这个词语的时候,往往缺乏细致辨析,因为它们会涉及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城市题材写作,其中有着独属于城市经验的人物、现象与故事;带有城市观念与视野的多种题材写作,可能会涉及边远乡村乃至跨国的素材;从属于城市文学的市民通俗文学,它们只是其中的一个部类,并且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现代文学以来,文学史中谈论的城市文学,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部分东南沿海口岸城市和少量内陆颇具特色的城市,其话语多强调有别于占据主流的“乡土文学”大宗的断裂性体验,也就是说“城市”会被视作“现代性”展演与操练的处所与空间,而“城市文学”则连接着进化论式的时空观与世界观。这种情形尤为突出地体现在关于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施蛰存)的书写与叙述之中,而比他们更早的“鸳鸯蝴蝶派”那类基于城市生产、传播与消费的作品则很少被纳入“城市文学”的视野之中——它们会作为通俗文学现象被加以研判,一般不会视作具有美学或观念上的创新性。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因为“鸳鸯蝴蝶派”的创造固然不乏吸收了现代西方文学因素,但从观念上来说是传统市民文学的当代继承者,它们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唐宋变革”后市坊瓦肆里通行的市井文艺(说书、戏曲等)。在现代文学观念的观照下,市井文艺、市民文学不唯缺乏革命性,甚而在激进的革命文化话语之中时常还有被污名化的风险与事实,因而成为文学史书写的一股潜流。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通俗文学”重新被进行价值评估,市民文学才开辟出自己的合法性领地,而市民小说真正被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增量(不同于王朔那种拆解与颠覆革命话语的写作),则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1994 年9 月,《上海文学》开始推出“新市民小说”联展,同时还相继开辟了“都市歌谣”“都市女性小说”等栏目,持续了三年左右。后来上海三联书店将此类相关作品及关于市民社会与市民文化的讨论择要结集为“新市民文丛”,包括《手上的星光》《都市消息》《几度风雨海上花》等书出版。
当时主持《上海文学》的周介人曾经指出,推出“新市民文学”并不是想倡导某种新的文学观念或方法,而是想寻找一个“生长点”,而这个生长点可能不在于作家的学识、才华或经验回忆,而在于作家主体与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对应关系之中,也即它是有着明确的现实对话性诉求的:“希望作家从一个时段的种种政治的、文化的情结中伸出手来,抚摸当下的现实,对结束了僵硬的意识形态对峙的世界格局有新的把握方式,对逐步市场化的中国社会结构与运作有新的感应与认知,使文学对于民族的现实生存与未来发展有新的关怀”。在周介人的设想中,这个“新市民小说”并非“新—市民小说”,而是“新市民—小说”,着眼于变化了的写作主体与写作对象——“指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启动后,由于社会结构改变,社会运作机制改型,而或先或后改换了自己的生存状态与价值观念的那一个社会群体。这个群体的涵盖面不仅仅局限在‘都市’,而且辐射到我国广大的农村与乡镇。” 他所点评的邱华栋、张欣、唐颖、殷慧芬等人的作品也确实显示出“新市民”(外省青年、白领丽人、正在兴起的“小资”)在情感结构与感觉方式上的新质——他们普遍有着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的混乱、迷惘、沾沾自喜而又雄心勃勃的气质。
“新市民小说”的召唤与扶持,不仅是20世纪90年代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作用于普通民众的现实结果,也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知识分子在思想层面上对于宏大叙事与崇高意识形态解构的反映:文化上呈现为主流意识形态、精英知识分子与市民社会的三足鼎立的格局,在文学上出现逃遁与入“市”的不同形态。 “王朔热”的出现,意味着精英文人启蒙与“代言”的形象或幻象,从内部和外部都遭到冲击,市民文化作为世俗生活的实在表征,被批评家视为映衬出虚假的知识分子话语的平民化真诚的“内心话语”。从话语空间的角度来说,市民文学与彼时关于“市民社会”的政治制度与公共空间的讨论形成彼此的互文与同构,也即,在“现代化”的共识中,谋求“‘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观’替代‘权威本位(转型)观’”。但是,今日回头再看,中国的国家建构与社会治理无法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市民社会”理论一言以蔽之,因为“国家”与“社会”长期以来并没有构成二元对立项,所谓的“公共空间”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主流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与市场化)的深度参与。如果粗略一点说,二者毋宁是彼此包容的,无法剥离开来进行讨论,在涉及社会主义中国的土地与农业改造以及工业化发展的过程时,尤其如此。
20世纪90年代“市民社会”的讨论可以视为个人意识、市场逻辑与科技传媒所开拓的公共场域融合的产物,在文学中反而是自上而下的精英观念占据主导,而非自下而上的平民意识的自觉生长与蔓延。改革的“阵痛”中夹杂着日常生活与市民话语的欣喜与吁求,更多延续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后革命话语,顶多增加了消费主义的新质因而顺理成章地,可以看到“新市民小说”以降的城市文学的形形色色浪潮,诸如散文热、新写实小说、美女写作、青春文学、中产阶级美学、底层写作……更多是由精英文人倡导或者商业化的操作。这其中被仓促命名的“新生代”“晚生代”“新状态”(韩东、朱文、刁斗、徐坤、李洱、东西等)或者早期的“70后写作”(卫慧、棉棉、安妮宝贝等)基本上可以视为个人主义、世纪末的颓废与消费观念的糅合。他们与艺术界出现的“玩世现实主义”(方力钧、岳敏君、刘炜、杨少斌等)在传递无聊情绪、“一点正经没有”的犬儒感上如出一辙。但有一个关键的共同变化体现在,日常生活成为一个统摄性的主题,它成为各种表述都无法摆脱的一个大话语。
只有在晚近三十年城市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才能更清楚地给予滕肖澜一个定位。作为一个“70后”作家,她的题材主要集中于现实的上海故事,早期的写作并没有呈现出有别于其他同龄作家的特色,可以概括为现代小资美学在城市书写中具体而微的表现,而日常琐碎的细节刻画、细腻情感与情绪的弥漫、个人化与身体感觉的关注都显示出新世纪城市题材小说的共性——可以视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市民—小说”的精致化。但近期的作品则出现了文体与观念上不自觉的改变。《心居》是其最新长篇小说,以房屋为中心讲述当下的上海市民生活。住房制度改革是1994年在全国大规模展开,但1991年2月上海就出台了《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可以说是住房市场化改革的试点与起点之一。以关系着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为主题切入点,让购房、卖房、炒房、置换、出租成为市民生活的中心连接点,使得《心居》成为继王安忆《长恨歌》、金宇澄《繁花》之后书写上海最为有力的作品。
上海故事从韩邦庆《海上花列传》、朱瘦菊《歇浦潮》开始,到张爱玲与苏青,有着较为成型的市民文学线索,这条线索与茅盾《子夜》、周而复《上海的早晨》构成映照,一度在激进意识形态的压抑下藏匿隐没,但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的城市文学中重新被发掘出来(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新感觉派”,反而没有张爱玲、徐訏这样更具都市浪漫传奇意味的作家更为流行)。《心居》接续了这条倾向于通俗大众的“海派”线索,一方面吸收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以及新传媒叙事方式的滋养,而又并不集中于“新市民”人物性格与命运的描摹;另一方面则伴随着市民文化的日常化,体现出“新—市民小说”的传承,回归了古老的世情小说与奇情戏曲的传统,最终成为貌似接近巴尔扎克意义上的“风俗研究”而实际上则具有中国特色的“风俗画”。
二
《心居》是以万紫园小区顾家为中心讲述的当下上海故事。老二顾士宏妻子早故,一人拉扯大双胞胎儿女顾磊与顾清俞;顾磊怯懦无能,却娶了一个精明能干、一心要在上海扎根的安徽媳妇冯晓琴,并且有了一个儿子;顾清俞作为外企高管尽管事业有成,却因为暗恋初中同学、没落的世家子弟施源,三十多岁还一直未婚;靠炒房发家的展翔则一直迷恋顾清俞多年,也单身一人。老大顾士海、苏望娣夫妇原先是下放黑龙江的知青,返沪后含辛茹苦培养儿子顾昕,后者不负众望当了公务员,并被局长看重,将女儿葛玥嫁给他。妹妹顾士莲与妹夫高畅则是工厂职工,两人收养了女儿高朵朵,要送她去国外读音乐。外围人物主要有冯晓琴的妹妹冯茜茜,一个野心勃勃到上海打拼的女孩;万紫园开按摩店的史老板,后来投资垃圾回收业务;顾清俞的闺蜜李安妮,有过一场跨国婚姻。人物关系交错繁复,情节琐碎曲折,举凡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育儿养老、柴米油盐、吃喝拉撒、求职创业都有所涉笔,而线索倒是清晰分明,就是“心”与“居”。
“心”是情感纠葛,包括看似淡漠而又坚韧无比的血缘亲情,虚幻而又惊心动魄的爱情,契约式的婚姻与利益纠缠的偷情与友情;“居”则是围绕赠房、购房、租房、建房的生意买卖、奋斗升迁及外乡人的融入与离去。“心”与“居”的汇聚点无疑在“家”,以至于虽然故事一开始的重心和关键冲突都放在房屋上,但随着情节的进展,重心失焦了,变成了一个带有浮世绘色彩的生活流。从总体上看,这个小说可以称之为融合了感情、家庭生活与社会问题的当代世情书。
所谓世情书,在中国小说发生演变过程中由“志怪”与“记人”两类题材的区别发展而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明代“人情小说”时说道,区别于此前神魔小说的“记人事”的小说,主要写“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 他称之为“世情书”。向楷在鲁迅的基础上将世情小说界说为“描写普通男女的生活琐事、饮食大欲、恋爱婚姻、家庭人伦关系、家庭或家族兴衰历史、社会各阶层众生相等为主,以反映社会现实(所谓‘世相’)”。明代世情小说以“三言二拍”、《金瓶梅》为代表,写世态百相、欲望宣泄、间杂谐谑讽刺与道德教化,未必入木三分,倒也穷形尽相,对后来的小说影响深远。常被人论及的《红楼梦》《姑妄言》《蜃楼志》《泣红亭》《老残游记》《孽海花》等,可以视为世情小说的开拓、余绪或变形。清以后的世情书从主题上主要分化为三种趋向:感情(“才子佳人”)、社会问题(《儒林外史》)、家庭生活(《醒世姻缘传》《歧路灯》)。按照小说史的一般描述,世情小说在清后期基本上已经走入末路。但是兜兜转转,草蛇灰线,世情书的这三种趋向在《心居》中汇聚到了一起,见证了小说发展的隐秘脉络。关于这一点,后文再作阐说。
《心居》并没有像一般被视作世情小说的汪曾祺的作品那样对风景物象过多着墨,但对于人情风俗、心思情绪的细致描摹并不缺少。它的语言清畅好读,人物及故事平易动人,作者没有太多“想法”,但是有丰富的“生活”,没有先行的理念,只是在故事讲述中有着朦胧的意识。这一切使它具有简·奥斯丁式情节剧小说(melodrama)色彩,也显示出了市民大众的趣味。爱·缪尔(Edwin Muir)谈到“人物小说”与“戏剧性小说”的区别时认为,戏剧性小说“背景不变,向我们展示出行为者本身的一整套人生经验……场景不变人物变,人物因他们间的相互作用而改变”,是“各种经验方式的意象”。《心居》正是如此,人物性格典型的刻画并不重要,甚至通篇都没有景物与外貌描写,更多是细描处于复杂关系网络中的生活经验,整个文本从语言到观念都是张爱玲式的,大量自由间接引语的插入与评价,让第三方视角既是全能的、洞察一切的,又是体恤的、与叙述对象和读者形成共情的,便于故事的铺展、接受和理解。
这是融合了古典世情小说与现代电视剧表现方法的结果。古典世情小说颇为戏剧化,体现为回环曲折有时甚至离奇荒诞的“奇情”。如同浦安迪(Andrew H.Plaks)在分析明代的“四大奇书”时谈到的,通俗说部转为文人小说过程中传奇剧在技法与观念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之不可能不具有那些曲折奇情的结构与修辞。《心居》中的许多人物设置,就如同戏曲中的生、旦、净、末、丑的类型角色,只是功能化与工具化的存在——尤为明显的是施源(生)、顾清俞(旦)与展翔(丑)——有血有肉的反倒是顾家老一代三兄妹为代表的那些小市民。同时,小说中有太多的巧合与牵强的情节,暴发户展翔暗恋顾清俞数十年如一日,顾清俞为了买房假结婚居然就遇到了暗恋数十年的施源,顾磊下楼追赶负气出走的冯晓琴失足跌死,冯茜茜为了业绩与顾昕发生偷情,更狗血的是冯晓琴十五岁时候就生有一个私生子而这一切顾清俞早就洞若观火……过于集中的事件发生在这些亲戚与邻居之间,固然显示了展示更为宽阔的社会问题的意图,却非常牵强。吊诡的是,它的细部与细节却又非常扎实可信,这种张力使得《心居》成为一出冲突密集的“戏”,并且是时下颇为流行的双女主戏(顾清俞和冯晓琴)。人物活动的场景变化与情节的转换,潜在地体现了电视剧编剧的痕迹,设想一下,如果要改编剧本,都不用大动干戈。
顾清俞与施源(假)结婚后第一次与顾家人聚餐,顾家三兄妹在一起聊天,其中有一段描写非常典型地体现出《心居》的语言运用、心理勾勒与娴熟的并置式结构:
苏望娣坐在一边嗑瓜子。这场谈话她并不十分参与,主要是倾听。顾士莲问一圈,信息搜集得差不多了。上海人,年龄相仿,国营旅游公司当导游,住在杨浦区。大概位置一查,老房子无疑,而且还是笃底的老房子。长相是不差,但以她多年阅人的眼光,总觉得干净得过了头,气质忒清汤寡水了。这年纪的男人若是混得好,多半都有些油腻,豁胖,话里夹着肉呷气。他竟有些学生模样。除非是再高一个层次,那就另说。但一个导游,又能高到哪里去,再怎样也有限。苏望娣一边想,一边得意,神情却愈是不露。这家里几个小的,顾清俞算拿得出手的了,拖到现在,也只是草草嫁了。女人事业上再优秀,嫁得不好,那就等于零。顾磊就更不用提,半瘸子,还娶个外来妹,都叫不响。自家儿子真正是鹤立鸡群了。本来还被这个大堂姐压着,现在这样,瞎子都能看出谁好谁孬。刹那间,苏望娣觉得人生的意义都不同了,五色祥云在头顶环绕,忍不住便想要大叫几声。先抑后扬。满脑子都是这个词。谁能想到黑龙江混成狗的一家人,今时今日竟能如此?那时吃剩饭剩菜,自尊被踩在地上,蹍了又蹍。苏望娣每每想到那时的光景,就忍不住想哭。亏得儿子争气,夹缝里开出花来,好日子拦都拦不住。
这是典型的上海市民之眼与市民思维,充满了盘算、计较、权衡,兄弟妯娌之间的比较也不乏争强好胜与洋洋得意,但这种市侩般的俗气却也无伤大雅,只是普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生态。《心居》整体上的观念认知,基本上就停留在与市民等同的层面:它一定要形成完整的情节命运链条,要给予每一个人物与事件一个交代,而不是像现代主义小说那样很多时候留白,并且更主要的是,每个人的结局中隐藏着的伦理逻辑是最为古老而质朴的道德价值观念(善恶有报)。他们在小事上斤斤计较,有时候钩心斗角,但紧要关节却也不至于丧失大义。
整个小说中,与落难公子式的施源以及中产阶级白领顾清俞的缺乏人情味与自私相比,进城的“乡下人”展翔与冯晓琴的形象与性格更为立体与讨喜。尤其是冯晓琴,少时在老家生了私生子后远走上海,游走在男人之间,一心想往上爬,终于嫁给上海人顾磊,却因为过于强势造成了后者的意外身亡,与顾磊姐姐顾清俞之间可谓尔虞我诈,竟至于到了撕开脸面的程度。这似乎是一个不择手段的女人。然而,她又有情有义、勤奋进取。当陌生的工人老黄出事,因为受到工厂阻挠被迫找到私人疗养机构,进入她操办的养老院时,她不仅贴钱看护,还拒绝了上门来说合的顾昕——因为此事牵连到顾昕在政府部门与工厂的违法操作。出于自保的考虑,顾昕希望她能够将心比心,但是冯晓琴本能地拒绝了他:
冯晓琴没想好该怎么回答,嘴巴比大脑快了一秒,“——我要是站在你的位置,大概不会。”他怔了怔。她说下去:“老黄我收了。不是故意跟你过不去。如果今天姑父不来找我,那就什么事也没有。可问题是,他找了我。不晓得是一回事,晓得了就是另一回事。你新闻里听说有车祸,哪怕死一百个,眼皮也不会抬一下,可如果在你眼前,一个人活生生被撞死,那就完全不同了。我也是有儿子的人,能理解老黄爸爸的心情。其实到这一步,最可怜的不是老黄,是他们老两口。你讲得没错,我来上海是想过好日子,但良心要是过不去,日子又怎么会好过?不要说‘将心比心’这样的话,我心里想的,跟你不一样。我要是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接这差事。伤阴德的。”
冯晓琴最终诉诸“良心”与“阴德”,可见商业与市场逻辑并没有泯灭素朴的道德操守——这是一个新故事外壳中讲述的古老的世道与人心,传统的情义观抵抗了“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实用理性。20世纪90年代在关于市民文学的讨论中,曾有论者将市民社会归为相对于“官方”的“民间”,三十年后再来看,《心居》中的这种民间道德,并不一定是对立于一个假想的“官方”,它实际上是一种更广泛而普遍的心理积淀,远超越于任何“官方”以及新近勃发兴盛的商业化、市场化思维,而是将后者包容在自身之内。
于是,在形式与内容、叙述手法与价值观念上,当代世情书都获得了与当代市民的亲近性,这是一切通俗文艺的本能。笔者将《心居》视作通俗的市民小说,丝毫没有贬低的含义,雅俗之分经过20世纪末一系列“后学”的洗礼已经不再有明确的界限,甚至可以说文体与文本类型都在趋于融合,显示了本土美学传统在经历了先锋文学等一系列创新变革后的重新复归。
三
1995年,作家李国文在给一本“新市民小说”选集作的序中,简单地梳理了小说与市民的关系,对市民及其文学趣味并不抱很高的期望。在他看来,已经很难用经济或阶级分析的观点去认识“市民”了,“尤其是大城市里的小市民,既是一股涌动的力量,也是一种可怕的惰性。每一个细胞都有逃逸出这个整体的企图,无法实现以后,也能迅速找到乐在其中的理由。会对比他强的人嫉妒得心痒难禁,也会对比他不如的人,奚落耻笑而由此获得慰藉。这等人,永不满足又永远满足,有吞吃一头大象的欲望,而无捉拿一只耗子的决心。拜金和对权势的慑服,使得某一部分神经特别发达和敏感,但对庸俗、卑劣、堕落和无耻,又往往显得麻木和习以为常。一个个活得既开心,也不很开心,似乎痛苦,又并不十分痛苦。他们经常幻想上帝给他笑脸而不得,胆子特别小,野心又格外容易膨胀,自怜自虐,又自作多情。所以,那些编织出来的公子落难,小姐多情,后花园私订终身,上京赶考,状元及第,衣锦还乡的故事,还有苦尽甘来的大团圆故事,灰姑娘和白马王子的故事,穷书生的黄金屋故事,最能给他们以满足了。所以文学史上那么多小说,能够弦歌不绝地传诵,就因为这些玫瑰色的梦,给他们带来心灵上的慰藉。”李国文认为,满足“荒唐的白日梦”形成了市民小说的模式,如果置换一下位置,从精英视角转移到平民视角,则会有一层同情之理解,而这种平民视角在21世纪作家那里已经完全习以为常、习焉不察。
回顾小说的历史,最初不过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的娱乐消闲读物,世俗性是其原生的本性。只是在近现代转型中出于底层启蒙的需要,小说才被精英士人提升了在文化等级中的位置,乃至于在现代文学时期成为塑造“想象的共同体”的利器,承担起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诗文正典的功能。尽管不乏种种“为艺术而艺术”类的争辩,但在审美愉悦、娱乐认知之外,现代小说被赋予了感时忧国、教育民众、抨击时政、揭批社会、改造思想、规划未来的各种责任却是事实。这本无可厚非,也是小说作为现代强势文体的多重意蕴所在,然而当文学外部功能被过于强化至其极致,则很容易落入所谓的工具论陷阱,从而丧失其主体性——它所表现的人及其生活是抽象的、理念的与符号的。这种情形在激进政治年代达到了极端,因而引发了“新时期”文学话语的反拨,将对于人与人性的追求拉回到文学的中心,乃至走向了对现代主义的推崇备至。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性在先锋小说及其后来者的表述中被狭隘理解,人的理想化维度被抽离,人及其生活则被贬低为自然的、肉体的与欲望的。无疑,这些关于文学的认知都是精英性的、文人化的,某种意义上在日益脱离小说亲近于民众的通俗本旨。
时至今日,文学在现代时期被赋予的众多责任与负担,以及在新时期以来所形成的文化资本,不管被动还是主动,都已经卸载掉泰半。在文学的读者日益被其他类型的媒介文艺所收割与吸附的背景下,必须重新思考文学在这个时代与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斟酌它的限度与可能性,以及实现美好愿景规划的潜能时所需要使用的手段、形式与技巧。笔者认为,《心居》对于市民小说的传承与开拓,是其中本色当行的一脉。它与张爱玲那些在“鸳鸯蝴蝶派”杂志上发表的小说相似,带有平行于书写对象的共情与悲悯。理念与思想在这个时候让位于写作冲动与行动的本能,意义与价值则在故事世界中自行形成,并会在读者与更广泛的受众那里得到回应、解释与阐发。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显示出它的开放性以及较之于其他文体真正的独特性所在。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对司各特(Walter Scott)推崇备至,认为他“将小说提高到了历史哲学的水平……他给小说注入了古朴之风;他使戏剧情节、对话、肖像、风景和描写浑然熔于一炉;他兼收并蓄了神奇与真实这史诗的两大要素;他让高雅的诗意与粗俗的俚语辉映成趣”,但是他却没有构想出一套体系,因而自己要完成前人所遗忘与忽略的“风俗史”,“编制恶习与美德的清单,搜集激情的主要表现,刻画性格,选取社会上的重要事件,就若干同质的性格特征博采约取,从中糅合出一些典型;做到了这些,笔者或许就能够写出一部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那种历史,也就是风俗史”。巴尔扎克在这样的宏大写作规划与目的中,陆续完成了一系列名之为“风俗研究”“哲理研究”与“分析研究”的小说。晚清至民国,从曾朴的《孽海花》到李劼人的《死水微澜》不无带有风俗史的意味,但这条小说路径很快因为前述各种文学内外因素的影响,而让位于社会剖析与批判式的现实主义小说,直到邓友梅、汪曾祺那些被认为是“世情小说”的作家作品那里才恢复了关于风景、风俗、风情的书写。此类作家都不是长于思想型的作家,作品题材与内容也往往与某种地方性文化相结合,侧重于景观物象与人情世故,所以不是巴尔扎克那种试图融合政治、伦理和审美一体化的“绝对文学”。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中国化的“风俗画”小说。
风俗画小说的最突出特点在于从深度模式向表象模式的转变。深度模式侧重结构(分析)与观念介入,而表象模式则转为日常生活的直观映现,而尽量游离在意识形态论争之外。之前谈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往往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将日常生活本身单维度化了,将它等同于物质、肉体与欲望的生活,但完整的日常生活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与心灵的向度。风俗画小说在社会生活的意义上,就是风俗人情与心灵变迁的相互结合,只不过后者是通过前者的描摹曲折表现出来。滕肖澜的《心居》就是这种“风俗画”小说——大上海的小日子,这种市井风情画是市民文学在当下的呈现。它已经摆脱了精英文学或者“严肃文学”的观念束缚,而让文本呈现出奇情戏的模样,在这个过程中它还注重可读性——到滕肖澜这里,技法的运用某种意义上合乎接受的需求,带有为消费主义辩护之意,但也并非刻意迎合,而是适应。
置入市民文学的脉络中,无论是手法还是观念,风俗画小说均是“日光之下无新事”。这种“无新事”并非没有外在表象、物质乃至制度的变化,而是说某些基于人的饮食男女、趋利避害的本能,对于世俗快乐与安稳生活的追求,沉淀在集体记忆中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长久以来看似被历史的飓风吹得七零八落而终究并未烟消云散的基本伦理观念与道德倾向,都还在那里。在细琐生活与赤裸心灵的短兵相接中,它让小说回到了它发生时候的状态,演绎一段人事过往或者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至于故事的意义与道德内涵则任由评说,因为风俗画自身就是一种心灵史。
(本文注释内容略)
(责任编辑:陈凌霄 )
扫码在手机上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