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该刊关注医学人类学范围内的各种问题,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健康相关学科的关系。
关键词:《医学人类学季刊》;选题

刊物概况
《医学人类学季刊》(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MAQ)是美国人类学学会分会之一医学人类学学会的会刊,由Wiley-Blackwell公司出版发行。该刊关注医学人类学范围内的各种问题,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健康相关学科的关系。刊物的定位是刊发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进行修正的论文,并且有意识地试图增强弱势文化和弱势群体在学术领域的能见度。其选稿方向包括疾病、健康和治愈的意义和经验,治疗实践和健康服务的结构、文化、语言学语境分析,健康和治疗的文化和生物学维度,对健康相关的政策研究和干预措施的批评性分析,医学实践、技术和知识生产的民族志研究,健康和医学服务的全球和跨国维度,以及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在健康相关领域的应用。该刊目前的主编是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亚历克斯·纳丁(Alex Nading)教授。本文是对该刊2018—2020年(第32—34卷)一些重要选题的概述。
关于研究范式和学术概念的讨论
《医学人类学季刊》对近些年兴起并传播的“全球健康”概念和研究进行了专门讨论和重新审视。这是该刊对于学科既有研究范式提出反思与挑战的办刊思路的贯彻。希纳·舍茨(China Scherz)的《困在诊所里:乡土疗法与当代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医学人类学》(第32卷第4期)以在乌干达坎帕拉的“ssabo”(乡土治疗场所)为田野,描述乡土精神/宗教疗法、草药等方式对当地居民的重要治疗作用,并借此批判以现代医学诊所为中心的医学人类学研究方法。文章认为,“全球健康”概念的出现,迫使非洲的医学实践研究被生硬地纳入现代化研究的范畴,医学人类学和宗教人类学日益分化,导致对神秘巫术的经济机制的误解,以及对医学人类学中曾经流行的文化主义的批判,这些因素共同使得该学科对于西方现代医学研究方式过度重视。
吉利·哈默(Gili Hammer)《“只要倾听病人进门的方式就可以了解”:感官医学知识的传播》(第32卷第1期)一文,通过对盲人学生医疗按摩培训课程的观察,描述了在这一人群中感官医学知识的转移方式。文章论证医学并不仅仅是视觉感官统治的领域,触觉和听觉同样可以经历医学化和科学化,成为感官医学知识传播的方法,医学由此进入感官的领域。文章挑战了视觉作为科学知识传播手段的主导地位。
借用物质符号学的方法,艾米丽·耶茨-多尔(Emily Yates-Doerr)的《重塑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应对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中的物质—半物质不确定因素》(第34卷第3期)通过描述危地马拉的产妇营养项目中社会决定因素(结构性因素)如何发挥作用,展示了僵化的“健康”标准(“社会决定因素”)对上游公共卫生决策的影响,以及如何在具体的社区中强化了不平等,从而破坏其宣称的健康正义目标。例如,将身高视为个人营养和健康状况的硬指标,导致了身材矮小的人在社会上遭到系统性歧视,只能从事低微的职业,而身材矮小的土著人则作为一个种族遭到歧视。物质符号学强调,用什么样的叙事语言去叙事是很重要的问题,该文基于这个方法,论证以怎样的标准定义“健康”,理解“社会决定因素”,直接影响着公共卫生决策和人类健康平等本身。文章呼吁在批评地审视社会决定因素的僵化定义的同时,寻找这一框架带来有益结构性改变的案例,从中总结经验。
塞萨尔·埃内斯托·阿巴迪亚-巴雷罗(Cesar Ernesto Abadia-Barrero)的《哥伦比亚的袋鼠妈妈护理:一种针对盈利性生物医学护理方法的庶民健康创新》(第32卷第3期)通过观察哥伦比亚的一个新生儿机构的护理实践发现,基于本土传统、低成本的护理方法在被全球化资本贴上“反向创新”的标签后遭到巨大负面影响,而这种创新实际上是有效的,可以作为“全球南方”应对护理需求的选择。文章从后殖民主义中汲取灵感,提出“庶民健康创新”(subaltern health innovation)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创新,希望它在“全球南方”得到推广。
文森特·杜克洛(Vincent Duclos)的《有问题的照料:自下而上和自外而内的支持生态》(第34卷第2期)一文借助STS理论、新物质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等视角,对旨在“修复”身体和生态的“照料”概念提出批评。文章认为这种理解(对“照料”的抽象化、整体化、道德化理解)削弱了照料本身可以具有的意义,还使照料成为民族主义和身份主义政治的帮凶。文章提出“支持的生态学”作为方法,提倡人类学家实验性地看待照料,参与照料概念的建构过程,在实践中理解它。
专题讨论
人类动物健康
2004年,世界野生生物保护学会提出“一个世界,一个健康”的理念,兽医、野生动物和热带疾病专家、公共卫生专家和医生以及社会科学家发起了面向全球的“一个健康”倡议,将动物纳入了政府健康治理的范畴。医学人类学中的相关讨论正在兴起。《医学人类学季刊》的第33卷第1期是“人类动物健康”专刊。这是医学人类学的一个新兴领域,讨论非人类动物作为宠物、牲畜和野生动物,如何在种植、养殖、消费和共居的实践中对人类健康和治疗产生影响。专刊中的文章将生物政治的概念提高到超越人类的范畴,提示护理实践正在跨越物种的界限,同时将健康视为超越人类的观点,共同质疑既有的学科研究范式,推动医学人类学的重构。汉娜·布朗(Hannah Brown)和亚历克斯·M.纳丁(Alex M. Nading)撰写的导言,从相关领域的“多物种民族志”和“人类世”概念语境出发,阐释了人类动物健康的三个关键概念:生态学、生物政治学和照料。全球生态的持续恶化使得危机成为人类和动物健康的常态;人与动物、微生物之间的分野不仅是本体论的,也带有政治经济学因素;对人类的护理正在日益紧密地跟与动物相关的照料结合起来(实验动物、宠物的陪伴作用、微生物群对免疫力的调节作用等)。该文提出几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人畜共患疾病、兽医人类学、动物治疗学、养殖业和食品生产。
此外,该期专刊中,莱斯利·A.夏普(Lesley A. Sharp)在《医学人类学中的物种间交往》一文中提出,对动物的照料和对人的照料之间的回环关系不是一个方向的,而是多向、互相影响的。同时认为,跨物种的照料带有道德性,而意识到人类道德责任之后,人类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实践乃至哲学、道德努力去克服物种等级制度。
全球心理
《医学人类学季刊》的第34卷第1期专刊针对“全球心理”展开讨论。斯特凡·埃克斯(Stefan Ecks)的《关于“全球心理”的医学人类学》在总结该期文章的基础上,提出古希腊哲学中的本质性的、一致的“全球心理”概念并不成立。文章借用哈贝马斯对于科学研究的三种主要价值的区分,理解关于全球心理的研究,这三种价值是:理解、控制和解放。专刊中所有的文章都视图理解是什么驱动了其他人的行动:关于有毒环境、社会经济不平等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的研究,关注技术官僚对控制的渴望的副作用。关于日本的痴呆症情况、美国军方对于士兵使用精神药物的控制的两项研究同样关注对于精神状态的控制。对于科索沃平民冲突后心理治疗的研究关心如何干预心理创伤。对于意大利南部寻求庇护者的研究,关注拒绝控制如何能成为一种解放。虽然所有的文章都谈到心理科学知识的全球传播、心理问题原因的全球性联系,但是心理学没有简单的解脱之路,科学主义过度扩张产生的“全球心理”概念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这一期中,安妮·M.洛弗尔(Anne M. Lovell)的《激活心理》一文认为,全球心理健康(GMH)的标准如果要在全球心理健康事业中真正起到重要的作用,就必须在指标设计上将全球标准与地区特征结合,必须被“量化精神”所渗透,并且吸收韦伯理论的精髓,且必须带有实践性。
第34卷第4期是新冠肺炎时代的医学人类学专刊。温康妮·亚当斯(Vincanne Adams)和亚历克斯·纳丁(Alex Nading)的导言探讨这个时代下何为人类学的问题。他们强调人类学的批判性参与的方法。这一期文章主要探讨的问题如下:在疫情传播中,谁是关键问题,什么是关键问题;围绕大流行病的统计数字制定社会封锁的政策是否合理(文章的答案是它们缺乏强大的测试、隔离和追踪系统,增加了社会在安全的名义下造成的伤害)。一些文章从对艾滋病的历史性研究中寻找可供参考的信息;另一些文章分析公众、政府当局和医疗保健机构如何利用大流行病来划分排斥线,决定谁承担社会债务、谁做出牺牲、谁负责任的问题,比如对老人、移民工人和黑人在流行病中承担的社会角色进行反思。
关注边缘群体
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医学人类学同样关注边缘和少数群体。马克·帕迪利亚(Mark Padilla)等发表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旅游业劳工、身体苦难和驱逐出境制度》(第32卷第4期)研究了美国对非法移民实行严格驱逐出境制度的情况下,被迫返回多米尼加的移民个人重建身份和对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的影响。因为带有非法移民的“污点”,他们具有群体脆弱性,很多加入到加勒比海旅游业成为非正规经济的劳工,卷入性和毒品的交易(这些在当地旅游业很常见),承担了社会结构性风险,处于更高的健康脆弱性中。文章使用联合体理论研究社会结构因素,对新自由主义劳动和全球驱逐制度对加勒比男性健康的负面影响提出批评和警示。
伊丽莎白·克劳斯(L.Elizabeth L. Krause)和艾琳·C.古布里姆(Aline C. Gubrium)合作发表的《潦草的拼字:移民、年轻的拉美裔母亲,以及作为叙事冲击的数字化讲述》(第33卷第3期)关注在美国的拉美移民中年轻的母亲。作为一个新媒体故事讲述项目的参与者,一些这样的年轻母亲受邀参加研究,以可视的方式讲述自己的生命历程和家庭关系。观察中得出,她们普遍处于频繁的流动中,缺乏稳定感,具有结构脆弱性。
社会治理相关问题
针对社会治理和医疗服务管理等问题,一些文章进行了个例研究和现状描述,并试图提出建议。马克·D.弗莱明(Mark D. Fleming)等人的《照料“超级使用者”:安全网中的新自由主义社会帮助》(第33卷第2期)描述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社会治理思路下,针对长期病、慢性病患者等医保资金的“超级使用者”,医疗系统和社会工作系统如何通过对住房、食物、交通、心理健康、社会帮助等方面的安排,尽量降低社会的总花费。
伊桑·巴尔格里·马内林(Ethan Balgley Manelin)的《医疗质量改进与模糊的照料商品》(第34卷第3期)讨论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医疗“质量运动”(旨在提升医疗质量的改革)的背景下,如何衡量医疗质量成为一个问题。一方面,对于量化指标(检查率、健康数值)的追求继续成为一个普遍认同的标志;另一方面,医生的人文关怀也是一个衡量标准,二者的出发点不同。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结构逻辑下,对前者的追求带有医疗作为金融化商品的特征,但同时后者又提示,医疗又不能完全商品化,具有模糊性的特征。
西西莉亚·科尔·范霍伦(Cecilia Coal Van Hollen)的《小心处理:重思印度的癌症信息披露中的权力与文化的对立》(第32卷第1期)一文关注印度文化语境中,是否向癌症病人披露病情问题所蕴含的知情权与文化习俗之间的矛盾。文章提出,矛盾双方都过于强调癌症信息本身,而忽视了披露/隐瞒这个行为本身应该作为关怀的重要部分,也就是说医护人员富有人文关怀的护理行为对于患者来说更重要。
医疗方法和精神健康问题
关于治疗方法的讨论
杰西卡·C.罗宾斯(Jessica C. Robbins)的《将个人扩大到被铭记的自我之外:波兰一个阿尔兹海默症治疗中心的社会性记忆》(第33卷第4期)提出,对阿尔兹海默症的治疗一向以个人为中心,但田野观察显示,以调动群体记忆为方法的治疗与个人化治疗结合,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伊本·M.格德斯波尔(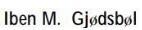 )和梅特·N.斯文森(Mette N. Svendsen)的《辨识痴呆症:一个丹麦记忆诊所中的建构解构性实践》(第32卷第1期)通过观察痴呆症的诊断发现,对患有痴呆症的患者,需要陈述病情的时候医生相信患者家属而非患者本人,而需要做实验时则必须患者本人参与,这对于患者的自我认知是一种解构性的羞辱。文章认为,当有人无法独立生活时,周围的人应该摒弃“完整的人必须是独立的”这一想法,而想象人与人的关系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和梅特·N.斯文森(Mette N. Svendsen)的《辨识痴呆症:一个丹麦记忆诊所中的建构解构性实践》(第32卷第1期)通过观察痴呆症的诊断发现,对患有痴呆症的患者,需要陈述病情的时候医生相信患者家属而非患者本人,而需要做实验时则必须患者本人参与,这对于患者的自我认知是一种解构性的羞辱。文章认为,当有人无法独立生活时,周围的人应该摒弃“完整的人必须是独立的”这一想法,而想象人与人的关系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关于心理健康和道德伦理问题
朱莉·S.阿明(Julie S. Armin)的《患者结构性脆弱的管理层面(不)可见性与医护人员中的道德压力等级》(第33卷第2期)一文提出,特定的医护人员,比如资质较低的诊所工作人员,更有可能面对那些没有医保、经济困难的癌症患者,而是否为他们治疗的问题则使这部分人员更多地面临道德压力。
H.J.弗朗索瓦·邓戈(Dengah II)等人的《“寻找平衡”:文化一致性与非一致性对犹他州摩门教妇女精神的影响》(第33卷第3期)基于文化一致性理论(cultural consonance theory),调查了美国犹他州摩门教女大学生的心理问题,证明在矛盾的世俗规则和宗教规则下,这部分人群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也许可以解释犹他州出现心理健康危机的原因。
正如温康妮·亚当斯和亚历克斯·纳丁在为新冠肺炎专刊所写的导言中所言,在新的社会状况下,人类学家还是应该“做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观察。我们体验。我们参与。我们写作。我们设法将批判性的洞察力融入看似明显和默认的情况。我们设法批判性地参与社会现实……”(Adams and Nading, “Medical Anthropology in the Time of COVID-19”,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vol.4, no.4, 2020, p.461)。政府和管理部门倾向于关注紧迫性,按照紧急程度考虑医学相关问题,而人类学以反思和批判为基础,从更长时段角度关注和参与医学相关问题的社会进程。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南茜
扫码在手机上查看